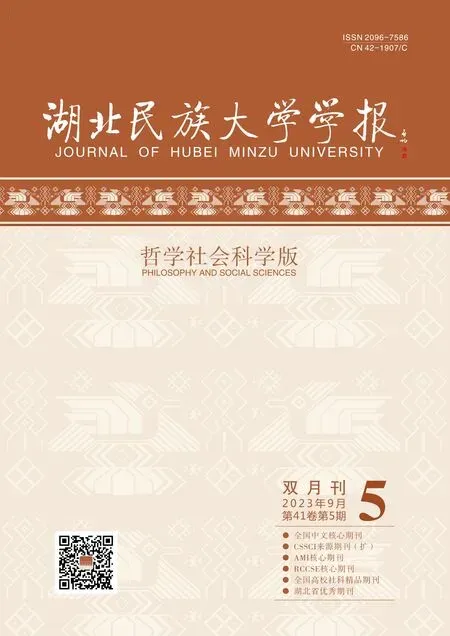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宗子维城》与西周史重构
吴玉萍
讲中国文化、述中国文化史,这类学术大命题需要有先进的方法论,需要打通有文字书写的小传统和无文字的大传统,打通文本到文化的基因链。“充分利用考古发现所建立的新知识系统,以第四重证据为代表,然后再去对照后世文献记录中相关的内容(第一、第二重证据),先做出真伪虚实的判断和筛选,在此基础上选择思考和求证方向,尽量找出从无文字大传统到文字小传统的‘榫卯结合部’,从而形成文化整体的和深度的源流认识。”(1)叶舒宪:《物证优先:四重证据法与“玉成中国三部曲”》,《国际比较文学》2020年第3期,第415-437页。文学人类学倡导的“物证优先”,旨在以考古出土物为第四重证据,试图弥补文字文本(第一重证据:文字)在文化整体性中的缺漏,重新发现新文本“物”的作用,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重释中华文化。
《宗子维城》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hausen)先生的一部力作。该书很好地应和了文学人类学的这一观点。在以往对西周史的研究中,出土器物的不在场使得西周史出现了很多争议。事实上,对于西周史而言,第四重证据尤为关键。利用第四重证据可以还原不断演变的文化符码系统,经“物”叙事,再现文化文本。《宗子维城》一书最初以英文写成,于2006年在美国出版,并荣获2009年由美国考古学会颁发的最佳图书奖,中文版于2017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三部分、九章,主要讨论了中国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000—前250年)有关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和社会变化的考古材料。由于作者精通德、英、日、中文,所以该书所引用的材料十分广泛,视野非常开阔。更为突出的是,作者不依附于文献记载,尝试通过考古材料即第四重证据重建西周历史,这一方法论无疑为西周史的研究开了一扇敞窗,也让我们把握住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的密钥。
一、文字文本《宗子维城》
在《引论》部分,作者开宗明义,指出“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不受外在文献历史学干扰的前提下,考古资料才能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2)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王艺等审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页。。基于这一观念,作者对文献记载的周公制礼作乐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历史虚构。作者指出,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西周的前200年内实行的制度基本上都是从商王朝那里继承下来的。孔子及其弟子们所向往的礼制源头,其实来自周朝历史上的两次礼制改革,分别是“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约公元前850年)和“春秋中叶的礼制重构”(约公元前600年)。这两次礼制改革都没有在传世文献中得到体现,所以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去证实这两次改革。西周礼制改革的时间在哪一个王朝时期,这对西周史有“定调”式意义,对西周史的重构也有重要参照。
书中第一部分题为“等级制度及其实施”,通过讨论氏族及其内部组织来解答疑问。作者指出,氏族“是一个血缘集团,其成员通过一系列联系可以追溯到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父系或母系祖先”。(3)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王艺等审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页。作者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氏族内部的等级差别越来越明显:青铜礼器的拥有权紧紧依附于等级贵族的身份;女性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较之西周初期明显下降;儿童、奴仆、外族人均被排斥在祭祀礼仪之外;辈分不再是氏族成员拥有财富和享受特权的决定因素,一些辈分较低的成员反而拥有更多的财富,享受更高的权利,说明氏族的分化进一步削弱了支系的权力,干系成员的世袭权力得到了突显。作者特别强调,上马墓地中出现了与本氏族地位不相匹配的“七鼎”组合,说明春秋时代一些等级较低的群体“僭越”更为显赫、尊贵的氏族方可拥有这样的特权。
书的第二部分题为“内部融合与外部分界”,主要通过考古资料分析姓族和民族的等级差别。作者意识到,在民族和姓族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也热衷于此一研究,但因为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使得最终的结论存在严重问题。作者力求对这些结论做出阐释,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其中,第四章着重分析了周文化圈内的姓族差异。作者首先界定了氏族和姓族的差别,指出氏族是一个较小的单位,而姓族则是大得多的实体;氏族拥有中央组织和与祖先崇拜相关的宗教活动,姓族则没有。以周人和商人而言,周人来自姬姓,商人来自子姓;周克商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来自中原西部边境的姬姓及其同盟势力凌驾于华北东部的由商王室子姓领导的姓族联盟之上”(4)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王艺等审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原来属于商人的联盟组合经过重新整合后加入以姬姓为中心的新网络(如第一章提到的微氏家族,有人认为史墙盘铭文中提到的“高祖”就是商人后裔微子启)。
要研究周文化圈内的姓族差异,子姓和姬姓是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先是否定了那种从文献上来区分子姓和姬姓物质文化差异的可能性,然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来自洛阳和曲阜的考古资料进行仔细甄别,指出那种试图通过物质文化来区分姓族之间差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种种迹象表明,姓族之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姓族内部氏族层面上的差异。针对中国学者们提出的用来区分子姓和姬姓墓葬的12条标准,作者指出其中大部分标准都属于主观臆测,不少甚至反映出报告者对洛阳以外的考古资料不够熟悉。
第三部分题为“变化与调整”,重点讨论了周代历史上的第二次礼制改革。作者指出,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所规定的那套标准的用器制度只持续了200多年,到了春秋中叶(约公元前600年),开始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器物组合方式,具体表现在青铜器群的二分化。物质文化的转变必然会反映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春秋中叶以后,各国国君的地位出现了调整,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逐渐与等级贵族分离;在西周和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严格维护的氏族内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根本差别,在战国时期逐渐消失;祖先崇拜的重要性在东周时期日益降低,氏族组织的首要地位也随之衰退。
在结语部分,作者呼吁像中国青铜时代如此重大的课题,要想取得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大规模、有统计价值的资料,需要中国学者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与更加先进的方法论。有些领域也可以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有机会参与这样一场意义重大的考古学研究当中来。
对于西周史中诸多问题,作者重点利用的是出土器物,让“物”言说,从证据中还原事实。尤其是周代历史上的两次礼制改革,书中呈现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总而言之,物证优先是该书的根本宗旨,据此作者重构了西周史,展现了以文字书写为主的小传统以外的文化大视野。
二、物证优先:第四重证据重构西周史
西周史是一部宏大史,传统的研究基于一二重证据(历史文献和古文字)的便利,就政治、经济、军事、精神等诸多层面做了汗牛充栋的研究。罗泰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宗子维城》摒弃亦步亦趋,而是全面细致地考察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资料,尽可能避免主观判断,所有的立论均建立在对出土器物细致入微的考察之上。诚如张良仁所说:“本书故意舍弃历史文献和古文字材料而不用,只利用考古资料,不承想‘柳暗花明又一村’,新发现和新见解层出不穷,大幅度地修正或丰富了我们对于周代社会原有的认识。”(5)张良仁:《建德垂风 维城之基——读罗泰教授〈宗子维城〉(上篇)》,《文汇报》2019年6月14日,文汇学人第13版。罗泰先生综合借鉴中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但绝不盲从,即便是对一些学界所公认的结论,他也能大胆地质疑。由于罗泰先生兼具学者的敏锐与谨慎,所以得出的结论令人难以反驳。
罗泰先生在该书中所使用的方法论,集中在第四重证据,可以概括为“物证优先”,这一带有“硬科学”色彩的研究方法值得国内研究先秦史和上古史的学者们借鉴。他对于中国古代丰富的传世文献始终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绝不拿考古材料去附会文献记载。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们所重视的铜器铭文,他也明确指出这些材料绝不应该被视为“纯文本”,而是“要与铜器本身的材质外观、风格、类型和在器物组合的位置结合起来”,因为“铭文不是一手史料”,而是“经过加工并通常大幅度删减后的版本”(6)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王艺等审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5-58页。。正因为这样一种用“物”的勇气,让我们看到了有别于倚赖文献而建构的西周史。
比如书中第一章以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103件微氏族青铜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口学、铜器风格序列和史墙盘铭文的分析,作者对中国学者李学勤的研究提出了异议。作者指出,李学勤关于史墙盘作器年代的判断可能比真实年代提前了一代王室,其原因就在于李氏忽视了人口学这一关键因素。“西周自公元前1106年周武王建国,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亡国,传11代12王,享国336年。”(7)曾鹏:《西周一代帝王事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25-136页。周王世系中自文王至共王共7代,平均每代的年数为28.4年,自周初至史墙的时间范围内,微氏族只记录了5代,如果像李氏所言将史墙的年代定在共王时期,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每一代40年左右的年数。据此,作者认为史墙盘铭文记录的微氏族世系并不完整,其间至少忽略了几代人。
其次,从铜器的风格序列来说,西周中期的纹饰风格表现为分解的鸟纹和兽纹,而窖藏22件兴(史墙的儿子)器中只有4件铜器属于此类风格,有16件都是典型的西周晚期的几何类纹饰,其出现的时间约在厉王以下至东周初年。
最后,史墙盘铭文中提到的“亚祖”其实与整个氏族大宗的始祖相隔好几代,而那些向“亚祖”献祭的人或是来自由氏族大宗分出后又另成的一个小宗,或是已经将自身重建为一个新的、低一级的氏族支系,“亚祖”即是这些氏族大宗内次一级的氏族。这种情况,也正好与《礼记》中记载的“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而迁之宗”的说法基本吻合。
基于以上三点,作者将西周的礼制改革定在了夷王时期,约公元前850年左右。礼制改革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代至西周中期流行最多的“酒器”消失不见,代之以列鼎和簋为中心的食器组合;其次,按照严格的用器制度规定各级贵族的铜器标准组合开始出现;第三,“礼制改革”引入一些更加简单、普通的新器形,比如鬲、簠、罃等。确凿的证据加以翔实的论证,让读者看到了不一样的西周史。
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后的最直接体现即是用器制度,就此而言,出土器物就是最好的物证。这在本书第二章节尤为明显,倚靠墓葬资料的支撑,作者以人类学的方法对这些器物背后所体现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考察。这一章的材料主要来自陕西宝鸡南郊的鱼国氏族墓地、山西曲沃天马—曲村的晋国氏族墓地、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氏族墓地的出土器物。作者指出,从这些墓地所提供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后,标准化、等级化的青铜器组合已经出现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些组合器物所反映的礼仪地位的差异也等同于社会等级的差别。重要的是,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氏族内部,而不是氏族之间。简言之,成套礼器足以反映氏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地位差别。
作者以鱼国氏族墓地为例,指出氏族首领与其低等级亲属之间的差异清晰地体现在随葬品的绝对数量上。就性别差异而言,作者的结论是,在父系社会中女性获得的特权整体低于她们的丈夫,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夫妻毗邻而居的现象只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这说明女性作为氏族联盟纽带的象征价值愈来愈突出;其次,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来看,女性要普遍比她们的丈夫低一个等级,但在规模上又比同等级的男性成员高出许多;再次,女性墓葬中多出土大型陶质炊器组合,说明女性与家居环境中的膳食准备有关;最后,女性的地位虽然整体上不如男性,但是远没有后世那么卑下。种种资料显示,当时不但存在独立的女官等级,而且贵族女性在出嫁后甚至可以继续祭祀自己父辈的祖先。
比氏族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单元是民族或民族国家,针对周文化圈内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差异的讨论,作者指出,相较于姓族来说,这方面的差异要明显得多。青铜时代的晚期文献已经证实了周文化圈内存在“异族”群体,物证方面又是如何展开的呢?就西周的考古资料来说,张家坡的洞室墓显示了一种与周人的竖穴土坑墓截然不同的墓葬形式,说明墓主人与周人分属不同的族属;洞室墓中出土了与同时期竖穴土坑墓相同的祭祀器物,说明墓主人此时已经融入周人的社会当中,洞室墓只是他们用来标记其民族特征的一种象征而已。
就东周的考古资料而言,益门村2号墓和渭河盆地的秦墓则显示了另一种可能,即生活在周核心氏族中的“异族”人主动或被动地与核心氏族隔绝。这种现象说明,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产生了更为严格的社会秩序,相比于西周早中期,它更加不能或不愿意容纳外来者。基于以上的判断,作者总结道,周代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周文化内部的进一步融合;二是对周文化之外族群的进一步分离。
“物证优先”重构后的西周史向我们展示了周代社会发展的第三个趋势,即周代社会组织模式向周边非周代统辖区域的扩张。作者指出,这种扩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周人氏族集团从周文化圈的核心区域向外迁徙;二是非周代人口按照周氏族的原则进行重组。早期阶段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封建制度来实现的。周王室的支系氏族将王室的礼仪行为带到了包括黄河中下游、淮河及长江中游在内的广大区域,促成周文化圈的形成。
到了西周晚期礼制改革之后,王室内部贵族阶层的凝聚力得到增强,西周早期因封建形成的社会网络有效推动了新制度的全面实行。来自莒国和中山国的考古资料显示,礼制改革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开始加入周文化圈,这种趋势尤以“东夷”“北狄”的融入最为显著。长江流域的情况要比北方复杂一些,巴、蜀、吴、越、徐等国直到春秋中叶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相对独立。至于楚国,作者认为过去中国学者提出的所谓“楚文化”——也包括“秦文化”——的说法是一种偏见:楚国和秦国的文献都是用汉语撰写,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字别无二致;楚国的青铜器铭文和竹简文书的书写风格与北方地区极其相似,完全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字系统;《左传》《国语》以及其他传世文献描述的楚国政治体系也与周边的其他诸侯国近似;楚国墓葬材料在所有核心方面都遵循了周的用器制度。于此,作者得出的观点是,与其将楚国视为一个独立的南方文明,不如将它看作周文化主流的一个地方类型(原因后文有讨论)。至于长江周文化下游,作者认为这里不在周文化的扩张范围之内,该地区出现的周文化因素,是通过楚国传播过去的。
三、作为文化文本的新释读
从文字小传统进入更为久远的文化大传统,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如果说考古学的证据是“器”,那人类学的方法就是“道”。由“物”开路后,利用人类学的方法进入文化文本就不是难事。张光直先生在评价美洲的考古学时曾引用过一句名言:“美洲的考古学便是人类学,不然它便什么都不是。”(8)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页。言外之意是说,考古学家们要进入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借助人类学的方式。
对于考古学与人类学(包括历史学、文献学)的关系,罗泰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判断。在他看来,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方法,它不必去依附任何学科,而是要保持一种平行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作为张先生的得意门生,罗泰在重构西周史时将人类学和考古学综合研究的巨大张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讨论微氏家族的世系和礼制改革的具体年代时,由于运用了人口学的方法,他所得出的结论较之李学勤先生更有说服力。书中利用人口统计学对周代社会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面对西周的礼制改革这样一个史无记载的重大问题时,罗泰教授也向我们展示了考古学是如何通过自身特有的方法去重新建构一套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一套非文献的西周史。当然,这种建构也需要一定历史底蕴,正如我们在该书中所看到的,假如没有对先秦史料的仔细研究,作者是不会意识到文献上的记载与考古学证据形成了冲突。也正是基于作者以第四重证据重构出的西周史,让我们看到了文字文本以外的文化文本。
文化文本是一种深度认知。在“词”与“物”之间的认知跨越,就是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的认知跨越。在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模式中,词语,属于传世文献的一重证据;物,属于考古发现的第四重证据。在前考古学时代,知识人关注的只能是词语或文本;在人类学和考古学勃兴的时代,我们更关注词语的活态语境——仪式歌舞和词的所指对象——物。(9)叶舒宪:《文化文本:一场认知革命》,李继凯、叶舒宪主编:《文化文本》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1页。在西周史的构建中,具象化的“物”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它们讲述西周的文化,首当其冲的便是铜器。
西周时期铜器组合在种类上的变化,其实早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容庚、郭宝钧、邹衡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们对此现象都曾有过探讨,但是没有深入下去。首位对铜器种类进行明确分期的是陈梦家先生。他根据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的演变将西周铜器划分为三个阶段:西周初期80年,包括武、成、康、昭时期;西周中期90年,包括穆、共、懿、孝、夷时期;西周晚期87年,包括厉、共和、宣、幽时期。(1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第137-175页。这就是被学者们普遍接受的西周铜器断代的三期说。可惜陈先生没有对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做出解释。直到1989年,英国学者罗森女士才从“礼制革命”的角度对青铜礼器的这种变化做出了解释,下面的一段话是经常被西方学者们所引用的。
一个在公元前950年需要成套酒器的社会,却在公元前880年左右废弃了它们,并以大规模成套的食器取而代之,这一定意味着在礼仪、信仰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青铜器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今日看来仍十分显著。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相对较小且精细复杂。要充分欣赏它们,就必须近距离观察。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时的礼仪可能是一种相对私人的活动,由与青铜器距离较近的少数人举行,后来的西周青铜器则通过巨大的数量和体积,由远距离观赏达到其效果。它们的表面不再装饰极小的细节。实际上,当时流行的直棱纹或是波曲纹并不利于近距离观察。其相对粗犷的设计更适合从远处来观察。(11)杰西卡·罗森:《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邓菲、黄洋、吴晓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1页。
这一观点提出后,立刻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热烈响应。《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第五章《西周史》由夏含夷撰写,对于罗森提出的礼制革命,夏含夷先是表达了认同,但对于“礼制革命”的具体年代和性质,他却提出了异议。夏含夷结合《诗经》《尚书》以及数十篇铜器铭文证明这一场礼制革命大约发生在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50),而且它只是西周更加广泛的整体性革命中的一部分,军事、政治势力的重组也参与其中。(12)此部分内容后来被翻译为中文,参见夏含夷:《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张淑一、蒋文、莫福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5-61页。罗泰在《宗子维城》第一部分的研究,显然也是受到了罗森的启发。
与罗森和夏含夷不同的是,罗泰认为这场西周时期的礼制变化不能算是一场“革命(Revolution)”,称之为“改革(Reform)”似乎更为恰当。在具体年代上,他也不认同夏含夷的观点,坚持认为礼制改革的具体年代就是发生在西周晚期(约公元前850年),而不是西周中期。罗泰虽然也暗示了这场礼制改革背后的政治原因,但是因为对传世文献缺乏信任,所以显得欲言又止。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周的礼制改革是始自周王室内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随着王室成员的不断增加,已经不可能再像西周初期那样将多余的后裔派遣到周边地区。嫡长子继承制虽然消解了一部分王位继承的权力斗争,但是成员内部为争夺其他权利的斗争却愈演愈烈。为了调节这种无休止的争斗,于是就催生出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
至于春秋中叶的礼制改革,罗泰的灵感可能来自李零。在研究战国中期的四座楚墓时,李零注意到两种规格的铜礼器,并且明确指出这四座墓是“介于主要随葬铜器的王、令尹、司马等高级贵族墓和主要随葬铜器的土庶墓之间。”(13)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待兔轩文存(说文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罗泰的研究可能是基于对这些器物组合的分析之上,并且用“特殊组合”和“常规组合”区别之,以显示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出现的两极文化现象。
高级贵族与低级贵族的分野同样可以用来进一步讨论春秋中叶的礼制重组。来自甘肃、陕西的秦宫大墓和山东临淄六王墓的出土器物显示,诸侯国国君和贵族阶层之间的等级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日益专制的统治者不断增长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旧的世袭贵族不断没落。作者分析了河南淅川下寺的春秋墓葬,发现了两种规格的铜器组合,即上文提及的“常规组合”和“特殊组合”。“常规组合”的铜器适用于大部分的贵族墓,而“特殊组合”的铜器则仅限于极少数地位突出的贵族墓中。这种铜器两分的现象说明,东周以后贵族也出现了明显分化,有了高级和低级之分。这也说明春秋中叶的这次礼制改革在强化高级贵族特权地位的同时,又进一步削弱了低级贵族的权利。这必将导致低级贵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直到与平民无异。
作者以秦国为例,指出商鞅变法之后,低等级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在其他诸侯国——尤其是楚国,原来标志贵族身份的椁的使用逐渐增多,并非意味着贵族阶层的扩大,而是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平民也开始拥有使用椁的权利。与之相对应的是,过去那种用来标志贵族身份的礼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平民墓中。将此现象与当时普遍出现的“僭越”情况相对照,说明战国时期礼制出现了松动。另一方面,作者也提醒读者注意,战国时期物质文化在丧葬礼仪中的“下移”可能预示着一场思想上的启蒙,即对于贵族来说,标志其自身身份的物质因素开始被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德”的观念所取代。种种物象显示,西周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变迁。
西周史中还有一个问题,即楚文化与周的关系问题。这同样也是罗泰在本书中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部分,那就是他对于“楚文化”——不妨也包括“秦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反对。罗泰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考古学者们利用“楚式鬲”定义楚文化的做法,并且认为“受到这种独特的考古学宝藏的震撼,许多学者和业余爱好者于是保守一种浪漫的观念,认为楚国是一个独立的南方文明,一个高贵而华丽的文明,与北方的沉闷的、等级森严的周朝截然不同”(14)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王艺等审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罗泰做出这种判断,出自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认为文献上关于楚文化源头的记载过于模糊,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支外来的文明;其次,已知楚国的墓葬材料在所有核心方面都遵循了周的用器制度。这些都是“物”归原“位”后厘清的文化文本,对于西周史的还原与重建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然,罗泰所谓的“证据”主要还是偏于青铜器,对于具有鲜明特色的漆器、木漆则缺乏相关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器物所体现的萨满巫术,罗泰似乎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萨满术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宗教技巧。但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陶器和萨满术正是构成“楚文化”核心价值的最主要特征。我们再怎么去怀疑西周的史料,但是对于孟子称楚国来的徐行为“南蛮鴂舌之人”,楚国第六任国王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谥”,以及《史记》中频繁记载的楚国“弑君”行为,总不能均以“伪史”视之。此外,罗泰在预设了“楚文化”不过是周文化的一个主流文化的前提下,以曾侯乙墓的墓葬布局去代表整个周文化圈的宗教宇宙观,似乎也陷入先入为主的偏见。殊不知,中外学者正是在对楚国这一独具特色的“宗教宇宙观”的审视中,才将“楚文化”判定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而且,曾侯乙墓的墓葬布局也可以解读为是为祖先准备的一场精神之旅,其中祖先崇拜的氛围却要淡薄一些。
不管是礼制的改革,或者是阶层的融合,抑或是楚文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借由作为文本的“物”在整体性上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于以往的西周文化,因为文化文本重视“物”的存在,重新发现“物”并让“物”置于表达文化的中心位置,故而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物”在发声的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新的西周史。
四、结语
作为一部拓荒之作,《宗子维城》中的相关论点出现一些争议在所难免,比如西方汉学家中,除了前文提到的夏含夷外,杜朴、马思忠、杜德兰等也有过批评意见。(15)罗泰学生张仁良就此曾做过详细总结。具体可参见张仁良:《建德垂风 维城之基——读罗泰教授〈宗子维城〉(上篇)》,《文汇报》2019年6月14日,文汇学人第13版。当然,作为一名汉学家,因为“他者”的身份,研究中国文化也或多或少带有某些“隔”,然而价值多于争议。以出土器物为利器,结合人类学方法,书中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文化还有很多,譬如祖先崇拜的变迁。
人类学的证据表明,许多民族都会将自己视为某种动物的后代,商人也不例外。商人的祖先崇拜仪式带有更多“巫”的成分,《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这是文字记载的动物图腾证据。而商人将自己的祖先神以动物的形式表现在铜器上,通过萨满出神的方式与祖先神沟通,则是物证。
周初的开创者们完全继承了这种传统,从铜器上的各种动物形象来看,当时的人们似乎重构了一个由众多的神祇组成的神灵世界。而到了西周中叶,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逐渐消失,证明祖先崇拜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死亡、灵魂和死后世界的信仰在整个东周时期发生了全面转变,祖先崇拜的神圣性开始下降,人们对待祖先不再像过去那样迷信,而是用一种“事死如生”的方式对待死去的祖先,祭祀礼仪的重点已经从祖先神灵转移到现世的利益,冥器的出现更是为了将生者与死者截然分开,死者墓葬的布局开始模仿生人的世界。这也意味着,过去那种祖先崇拜中“巫”的成分逐渐减少,而“礼”的成分则逐渐增多,一种全新的宗教宇宙观开始出现。
到了孔子时代,经过孔子的改良,用一种更加虔诚的方式去对待祖先,这就接近了孔子所谓的“仁”的范畴。这一转变,用李泽厚的话说就是“由巫到礼,释礼归仁”。
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到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文化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建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属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列入国家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16)孙正国:《非遗传承人的理论拓展及其文化价值》,《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23-133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离不开考古。文本不限于文字,走出文字书写的牢房,探索文本新样态,让“物”发声,中华文化才会更加多姿多彩,正所谓“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回到《宗子维城》,集中力量于考古,并倚靠其讨论分析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朝代,这是大胆的,求证的过程亦是小心的。如能在求证的过程中兼顾多重证据,相信对西周史的新释会更加夺目,西方汉学家提出的质疑声或许也会减弱。文化文本作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主攻方向,重视物,但也始终秉持整合语言文字符号和非语言文字符号,用整体性视角有效还原文化的深层符码,赓续文脉。唯有如此,对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以及从发生学上再现华夏精神的意义才会更深远,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才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