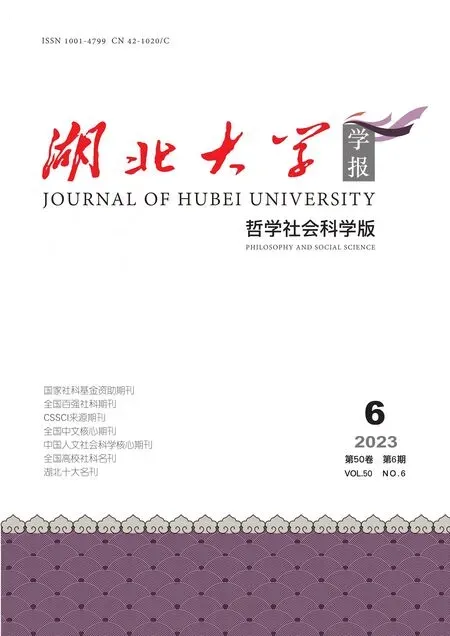思辨与实践之间: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
——以冯友兰、熊十力和牟宗三为中心
陈 鹏, 韩乔治
(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048)
随着现代知识体系、学科体制的建立,传统儒学的经学体系被分解到若干人文学科分支,如“诗”基本上归文学,“书”、“礼”、“春秋”基本上归史学、文献学,“易”基本上归哲学,而传统儒学的“义理之学”则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在新的学科体系下,传统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哲学化”的进程。儒学的哲学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儒家义理之学进行“哲学式”的诠释和研究,属于儒学的哲学史研究;另一是儒家义理之学的“哲学化重建”,属于儒家哲学的现代创作,所谓“现代新儒学”就是指儒学哲学化重建的现代历程。此“哲学化重建”或“哲学转化”可以理解为基于哲学方法、哲学范式对儒家思想、义理进行现代重建的过程。现代新儒学的哲学转化基于相当程度的方法自觉和方法探索,也呈现出时代交替、范式转换所带来的方法纠结,理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是理解现代新儒学哲学化重建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为更深层次或更广视域的方法反思奠定基础。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可以概括为两大方向:一是知识性、思辨性的哲学方向,主张哲学是一严格理智下的理论系统,以冯友兰为代表;另一是生命性、实践性的哲学方向,主张哲学虽不离思辨,却以转化生命为归宿,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对峙与论争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哲学观演变的主体内容,且关涉事实与价值、概念与直觉、知识与道德、理性与生命等重要议题。本文即从“思辨性”与“实践性”之辨的线索讨论现代新儒家冯友兰(1)熊十力与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建构基本属于同期,本文将冯友兰放在前面,主要是出于行文逻辑的考虑。、熊十力和牟宗三的哲学观,以见其各自的方法特质。
一、哲学是“形式底释义底知识”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在制度上是相关教育、学科体制的确立,在学术范式上是一个学科知识系统的引入。这个体制、系统的背后有一个方法的支撑,即逻辑化、科学化、知识化的方法,在这个方法意识和方法规范下,才算建立起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世界。与此相应,在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之初,哲学的形式化、逻辑化、知识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线索。在这一进程中,早期的严复、王国维、蔡元培,还有稍后的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起到关键的作用。王国维在《哲学辨惑》(1903)中称西方哲学“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而中国向无“纯粹之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虽有真理却“不易寻绎”,中国哲学之振兴必有赖于深通西洋哲学(2)参见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页。。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的序中,明言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不得不“依傍”西洋哲学史,“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序言”,第1页。。
这个“西方的形式”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一般内容结构,更有相关的逻辑的、知识的、思辨的方法(4)“知识性”与“思辨性”都注重概念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构造;它们之间也有区别,一般地说,“思辨性”注重概念(存有)的逻辑分析、先验分析而非概念的经验客观性,“知识性”则注重概念、命题的经验客观性。,即注重知识基础、概念分析、逻辑论证、系统建构的方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此种写作范式的发端,但相关方法的阐明并不充分。冯友兰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时则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方法说明。于此,冯友兰提出了关于哲学之为“知识形态”的经典阐述:
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故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的经验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个哲学则不可。换言之,直觉能使吾人得到一个经验,而不能使吾人成立一个道理。……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这是对“直觉”本身即为哲学方法的否认,直觉只是一种经验,而不能成立道理,成立道理就必须经过思议言说,必须运用概念的逻辑的方法。哲学的宗旨在于成立道理,必须运用分析、论证的方法证明之,“成立道理”不同于“实行一事”,必包含一理智的论辩过程,这正是哲学知性方法的本义。所以,冯友兰对哲学作如下界定:“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实在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之者。惟其如此,所以哲学中所有之命题,多为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6)冯友兰:《哲学与逻辑》,《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5页。冯友兰明确主张哲学方法的逻辑性、概念性(语言性)、形式性(不作事实肯定)等思辨性特征。
在《新知言》中,冯友兰明确提出了四种知识形式即逻辑学、哲学(主要指形上学)、科学和史学(7)参见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74页。,这是一个基于形式性强弱的排序。他认为,哲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对实在作“事实底”、“积极底”释义,而哲学是对实在作“形式底”释义。这种“形式底”分析体现为概念构造及其逻辑展开的“思辨”过程,比如,在此思辨过程中,我们不必实际地肯定有“方”或“存在”,但是可以逻辑地(也是先验地)肯定有“方”或“存在”,这个逻辑地肯定的“领域”,冯友兰称之为“真际世界”或“理世界”。哲学是与“真际世界”打交道,而科学则面对“实际世界”,并作出积极的判断或肯定。所以,冯友兰所说的逻辑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先验分析”。按照冯友兰的知识分类,史学与科学更具有对实际作肯定的“知识性”,哲学则趋向于对概念作逻辑构造和逻辑分析的“思辨性”,而逻辑则是纯粹的“形式性”。此“形式性”也是一个有强弱的概念,对实际肯定越少就越具有形式性,对实际不作任何肯定则是纯粹的形式性。
正是基于此种知识化、逻辑化的方法立场,冯友兰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的“弱点”是在“论证及说明方面……大有逊色”。中国哲学讲了许多道理,而关于这些道理的讨论、论证往往陷于“简单零碎”。中国哲学多未有以知识之价值即在于其自身,故没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传统,“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2卷,第249页。。
冯友兰实际上已明确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性”(9)本文的“实践”概念在内涵上与概念化的知识、思辨活动相对,指向具体的生命活动、生命体验。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指向一种对生命本原的体认和觉悟,它不同于各类社会文化活动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特征,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宗旨主要不是获得某种知识,而是养成某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只是他的选择并不是要挖掘、突显传统哲学的这一实践性特征,而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2卷,第253页。,即基于概念的、逻辑的方法整理出传统思想中相关哲学问题的实质系统。这一“哲学化诠释”的努力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传统思想或哲学中存在一个内在的逻辑化的思想结构或系统,并可以运用现代哲学话语将其表述、显现出来。这一研究范式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方式,它的方法论实质是将哲学视为一种普遍的根源性、系统性的思想建构,当我们在传统思想文本中找到相关论域、问题的概念命题系统时就意味着找到了某种“哲学”(11)至于传统思想中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理论化、可逻辑化的系统,后来才有广泛的讨论。诸如郑家栋指出“由中国传统思想所蕴含的‘实质系统’根本不能够推导出西方意义上那种逻辑化的‘形式系统’”(郑家栋:《“合法性”概念及其他》,《哲学动态》2004年第6期),李景林提出“存在性的哲学史”(李景林:《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等,都提示需要重新思考传统思想的“实质系统”是否可以被理论化、逻辑化。。
由于受维也纳学派批评形上学的影响,冯友兰在建立自家的哲学系统——新理学时,在思辨性、逻辑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冯友兰主张形上学作为“最哲学的哲学”应该是充分的形式化和分析化,真正“形上学底命题”可以说是“一片空灵”,它至多只是肯定“主辞的存在”,对实际不作肯定,或甚少肯定。冯友兰一再申明其新理学的演绎特征:“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1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1页。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友兰着意清除任何可能的“独断”,比如不承认有宇宙道德,不肯定有宇宙天地之心;其形上范畴“理”只承认一类事物必所以为此类事物,从概念逻辑上说,此“理”只是个类名,并不承认有包含万理的理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的新理学可以看成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现代的分析的转化。
冯友兰并非完全忽视哲学的实践性,只是这个实践性是哲学本身的实践效用,而不被视作成立哲学的内在的必要环节。与哲学相关联的实践性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哲学内部的实践性,没有实践就不成其为哲学。这就是熊十力、牟宗三所强调的实践性,即必须是在实践、体认中才能完成哲学。另一种是哲学外部的实践性,即通过思议言说建立一套哲学之后,此哲学所可能产生的实践效用。冯友兰主要是从哲学的实践功用来讨论哲学的实践性。强调哲学为一种理智的纯思,是侧重于对哲学方法的界定,冯友兰对哲学还有另外一种界定,他在《新知言》中说:“假使我们要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甚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13)冯友兰:《贞元六书(下)》,第861页。这是冯友兰关于哲学之内容与功用的界定,他常说哲学是无用之大用,哲学因其纯思、不着实际而“无用”,因其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有“大用”。冯友兰在《新理学》之后,至《新原人》才建立起一套“境界说”,方才完成对哲学之意义归宿的思想建构。新理学形上学的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但理及气的观念,可使人遊心于‘物之初’。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遊心于‘有之全’。……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14)冯友兰:《贞元六书(下)》,第855页。。冯友兰试图通过境界论来说明,他的哲学(主要是形上学)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思”,却可以通过此形式化的“形上觉解”知天、同天,从而达到“天地境界”。这就是形上学的“大用”。
只是,过分形式化的概念和命题如何能引发出一种内在真实的生命境界确实引起诸多的质疑。比如,洪谦指出冯友兰的玄学命题,如“山是山不是非山,必因有山之所以为山;水是水不是非水,必因水之所以为水”等,并不能给人带来丰富的感觉、优美的境界,人们甚至会“无动于衷”。洪谦说:“传统的玄学虽不能成其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的体系,但有其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深厚意义。但是冯先生的玄学似乎是两者俱无一厝。”(15)王仁宇编:《民国学者论冯友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3页。即使是与冯友兰在哲学立场上多有近似的金岳霖,也承认研究知识论时可以站在对象之外,而研究元学时则不能不带有情感。对于此类知识化、思辨化的哲学路向,熊十力提出了系统而强烈的批评。
二、本体“非知识所行境界”
熊十力建立新哲学的基本思路与冯友兰截然相反。冯友兰是要吸收西方哲学方法以弥补传统的不足;而熊十力则是发扬传统,显示自家本色,对治西化浪潮。熊十力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因是惶惧,而殚精竭力以从事于东方哲学之发挥。”(16)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此所谓“西洋势力”,即西方科学的浪潮,依赖客观的方法,一味向外求理,而失却了自家生命的真谛。
与概念化、知识化的哲学路向不同,熊十力在《新唯识论》开篇即言:“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17)熊十力:《新唯识论》,《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页。哲学所穷究的“本体”不是外在的某种存在,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不离吾人本心的真实的生命存在,与之相应的方法不是外求而是逆觉,不是认知而是体证。
在熊十力看来,科学与哲学虽都是求真之学,却有着方法、对象和领域的不同。熊十力对“科学真理”与“玄学(哲学)真理”作出如下分疏:
第一,对象不同。“科学尚析观,得宇宙之分殊,而一切如量,即名其所得为科学之真理。玄学尚证会,得宇宙之浑全,而一切如理,即名其所得为玄学之真理”(18)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184页。。科学由析观得宇宙之分殊,其对象是外在事物之理;玄学(哲学)的“对象”是宇宙浑全之实相,这个“宇宙之浑全”不是指整体宇宙,而是指宇宙万物所以生之理,亦即本体。
第二,领域不同。“玄学上‘真理’一词乃为实体之代语,科学上‘真理’一词即谓事物间的法则。前者为绝对的真实,后者之真实性只限于经验界”(19)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193页。。所谓经验界、现象界就是吾人心识所现起的现象、境相,也就是与心相对的外物、对象,科学旨在追求这一现象世界中的关系与理则。而玄学(哲学)的领域是本体界,是生化之原,是究竟真实。
第三,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是理智的、解析的、向外的,玄学(哲学)的方法是证会的、向内的、内外合一的。“理智只是推度,思辨只是构画,毕竟与真己不相干”(20)熊十力:《新唯识论》,《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546页。。理智化的概念世界属于理型世界,由思维构画(概念构造)而成,只限于现象界、经验界;玄学(哲学)所究者是宇宙与吾人所以生之理,其方法必是一种内在的体认。熊十力云:
哲学所穷究者,则为一切事物之根本原理。……夫吾人所以生之理与宇宙所以形成之理本非有二。故此理非客观的,非外在的。如欲穷究此理之实际,自非有内心的涵养工夫不可。唯内心的涵养工夫深纯之后,方得此理透露而达于自明自了自证之境地。前所谓体认者即此。故哲学不是知识的学问,而是自明自觉的一种学问。(21)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202页。
哲学不是“知识的”学问,因为知识把握的对象只是现象事物之理,而哲学要把握本原性的生化之理,此生化之理不是抽象的理则而是真实的生命,所以只能在工夫实践、自明自证中呈现。熊十力每每说“吾学贵在见体”,其所谓“见体”就是体认本体或是真实生命的自明自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在根本上不是知识性、思想性的,而是存在性、实践性的。
熊十力无意将哲学与科学当作两种“并列的”学问形态,而是基于存有论上的二分,将哲学、科学之别认定为本体现象、体用之别,也是中西文化之别的哲学反映。在熊十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二元模式:经验界/本体界、现象/实体、理型/真实、理智构画/真己、分殊/浑全、解析/统会、外求/逆觉、知识/超知识等等。这是一个“存有—方法”的两分:与现象界相应的方法是“知识化”的解析、概念、理智,与本体界相应的方法是“超知识”的实证、明觉、性智。依此,熊十力给出西、印、中三种哲学次第:
当今学哲学者,应兼备三方面:始于西洋哲学实测之术、分析之方,正其基矣,但彼陷于知识窠臼,卜度境相,终不与真理相应。是故次学印度佛学,剥落一切所知,荡然无相,迥超意计,方是真机,然真非离俗,本即俗而见真。……故乃应学中国儒家哲学,形色即天性,日用皆是真理之流行,此所谓居安资深,左右逢源,而真理元不待外求,更不是知识所推测的境界。(22)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86页。
概言之,西洋哲学长于实测、分析,却陷入知识窠臼,而与本体不相应;印度佛学虽超越了知识构画,却流于空寂,本体未落实;而中国儒家哲学则体用不二,即知识而超知识,即超知识(本体)而开显知识。这说明,熊十力既不认同西方的以理智思辨为中心的哲学概念,也不认同以本体为空幻的佛学的哲学概念,而是以中国特色的即流行即主宰的实践性的哲学概念去统摄西方和印度的哲学概念。
金岳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撰写的《审查报告》中曾提出写中国哲学史的根本态度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中国哲学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23)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第617-618页。金岳霖对前一种态度表示质疑,因为中国传统的“特殊的”学问很难成为一种“普遍范式”,他心目中哲学的“普遍范式”应该是逻辑化、系统化的西方哲学。与此不同,熊十力正是要根据“中国传统”提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普遍哲学”,这个哲学概念的实质不是对象化、知识化、逻辑化的理论系统,而是把握生命真理、纯化生命存在的“修养”或“实践”。
熊十力并不一味排斥思辨,而是在生命实践的整个过程中给予思辨一定的地位,他提出哲学是“思修交尽之学”:“玄学亦名哲学,是固始于思,极于证或觉,证而仍不废思。亦可说,资于理智思辨,而必本之修养,以达于智体呈露,即通过理智思辨境界,而终不遗理智思辨。亦可云此学为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24)熊十力:《新唯识论》,《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548页。这是超越单一的概念思辨模式,试图将“理智思辨”与“修养体证”结合起来的哲学观。“逻辑无论有若何派别,要之不外为慎思明辨之术而已,是固哲学之所必资。然哲学家之所自得,毕竟由脱然超悟,神妙万物,初不由思辨之术。……惟其有超悟立于先,则思辨不至流于纷碎与浮乱。辨之明,思之慎,则超悟益引发而无穷”(25)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335页。,思维与修养交致其力,而修养所以立本。从熊十力与张东荪的相关讨论中也能看到熊十力结合“知识”与“修养”的尝试。张东荪认为,西方人所求的是知识,东方人所求的是修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可以独立发展,而很难融合。而熊十力则说:“吾兄必谓中西可以分治,而不堪融合,则愚见适得其反。吾侪若于中国学问痛下一番工夫,方见得修养元不必屏除知识,知识亦并不离开修养。”(26)熊十力:《十力论学语辑略》,《熊十力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7页。
熊十力虽然提出“思修交尽”的整体性的哲学方法观,但他基本上还是从“推度”、“构画”等“负面的”角度来定位思辨,很少给予思辨的作用及意义正面的、积极的讨论,尽管他自己的哲学建立已经相当思辨。从方法论上说,“思辨”的内涵、作用以及如何与“超思辨”相结合,在熊十力这里并未得到充分展开。
三、哲学是“实践的智慧学”
至牟宗三,其哲学方法论基本继承了熊十力的理路,而对哲学方法思辨性与实践性之间的关系辨析则有了更充分的讨论。牟宗三自述其一开始曾着迷于纯客观论、泛事实论、泛物理数学的外延论,“用生命而不自觉生命”(27)参见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52页。。后因各种机缘他才逐渐由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认识到知识、概念、科学、逻辑是针对现象世界而不是真实的生命,此类抽象的思想只是指向一“悬挂的存有领域”,此“存有”是逻辑的、数学的,不必是“本体的”,逐渐由“架构的思辨”转向“现实的存在”(28)参见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卷,第73页。。
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明确指出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特别的内容和方法,就是特别重视“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
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它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成圣成佛的实践与成圣成佛的学问是合一的。这就是中国式或东方式的哲学。……它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这是独立的一套,很难吞没消解于西方式的独立哲学中。(29)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4-6页。
西方哲学在根本上是知识形态,是把对象推出去,运用抽象的概念加以分解、固定,在逻辑的规则中形成系统,是一个知识、思辨型的传统。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它要给生命存在一个方向,是教训、学问与修行实践的综合,是另一个不同于西方哲学范式的独立的传统。在这里,以“生命”为中心的“实践性”是中国哲学的关键特征,生命是一主体,主体是不能被对象化的,主体只能建立对象(知善知恶、善善恶恶),而不能成为对象,把握主体只能是主体自身的自明自觉。
从“解悟”的角度说,这个主体之“明”是“具体的解悟”,不同于概念思辨的“抽象的解悟”,牟宗三说:“具体的解悟是把握形而上的原理的,抽象解悟是把握属于知识的概念的,……抽象的解悟就是由逻辑的我而发出。它是通过逻辑定义或是归纳手续而把握抽象的概念或抽象的共理。”(30)牟宗三:《人文讲习录》,《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卷,第55页。抽象的解悟成就知识,具体的解悟成就智慧。抽象的解悟是由“逻辑的我”出发,它所把握的是抽象的共理;具体的解悟是由“道德的我”、“智的直觉”出发,它所把握的是“形上原理”,这个形上原理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具体的生命的普遍,也就是熊十力所说的“吾人真性”,所以,“具体的解悟”实质上是内在的自我生命的自觉自悟。
虽然哲学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实践性的德性之知、生命之理,但是哲学终究须内含一个思议言说的系统。相较于熊十力,牟宗三更充分地意识到哲学不能离开思辨性的开展。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牟宗三这样界定哲学:“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3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卷,第3页。这里明确指出哲学是一套观念的、理智的“反省说明”。牟宗三自述,在写《圆善论》的时候才真正明确:“爱最高善,热情地追求最高善,使最高善实现,通过实践来实现最高善。这一套才是真正的哲学。”(32)牟宗三,《实践的智慧学》,《牟宗三先生讲演录(五)》,新北:财团法人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2019年,第52页。他同时强调,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既是爱智慧,也是爱学问:
依哲学之古义之为“最高善论”这一限制而言,哲学一方固是“爱智慧”,一方亦是“爱学问”,“爱一切思辨性的理性知识”。“爱学问”就是使“爱智慧”成为一门学问,有规范有法度的义理系统,这就是所谓“智慧学”。(33)牟宗三:《圆善论·序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7页。
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是不离实践并且归极于追求最高善的实践的,这个最高善就是生命的终极真实,它是实践的、具体的;可同时,哲学又是“智慧”之“学”,它也涵着爱学问,要讲一套义理系统,只是这一套思辨学问必须涵摄在实践智慧之中,即“爱学问”涵摄于“爱智慧”之中。
在此,牟宗三关于哲学语言的进一步讨论值得关注,其中,牟宗三对“非分别说”、“启发语言”等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有关实践性哲学语言的方法论。牟宗三不同意逻辑实在论关于科学语言(概念语言)与情感语言的简单二分,更反对把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的语言归属为情感语言的论调。从实践哲学的言说形式上说,使用“概念语言”来规定生命实践的道理、意境就有相当的局限,一旦使用“概念语言”,就会将活泼、真实、具体的生命抽象化、凝固化、破碎化了,所以,对于“生命道理”要通过独特的非知性的言说方式给予某种呈现、点示或启发。那么,哲学的说教或说法(saying)在语言上就应该与知识语言或概念语言有所区别。如此,实践哲学语言就应该采用一种“非分解”的“非分别说”。比如,“象山之学并不好讲,因为他无概念的分解,太简单故;又因为他的语言大抵是启发语、指点语、训诫语、遮拨语,非分解地立义语故”(34)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1页。。此类言说不再是界定、分析一个概念对象,而是去启发、唤醒主体自身内在的体验和感悟。牟宗三对“非分别说”、“启发语言”的讨论类似于冯友兰所谓对不可思议言说的思议言说的“负的方法”。只是,冯友兰注重的是大全、整体因其绝对整全性而无法成为思议言说的对象,而牟宗三所关注的则是实践、生命、具体存在无法由对象化的抽象概念去掌握、构画。两者同样强调思议言说的界限,其内在的理路却有区别。
从各方面看,牟宗三对实践性的哲学形态如何结合“思辨”与“超思辨”提供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讨论,但是,哲学的思辨性与实践性的紧张仍然存在。牟宗三说:“知不只是‘知性之知’,还有实践的德性之知。理解不只是知识意义的理解,还有实践意义的理解。我们不只是思辨地讲理性之实践使用,还有实践地讲理性之实践使用。不只是外在的解悟,还有内在的证悟,乃至澈悟。知性之知展开自然界,成功知识系统,如物理学等。实践的德性之知(证悟)展开价值界,成功德性人格的发展,最高目标是成圣。”(3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174页。如此,可以引发诸多问题:“知识意义的理解”与“实践意义的理解”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实践意义的理解”是“实践”还是“理解”?实践式的理解能否代替知识性的理解?哲学是思辨地讲实践,又是实践地讲理性之实践,两者如何结合?哲学的目标究竟是“成学”(成就一理论系统)还是“成就人格”?“成学”与“成就人格”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四、思辨之“学”与成德之“教”
可以看出,冯友兰与熊十力、牟宗三所代表的是两种哲学概念、两种哲学路向。此两种哲学观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他们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冯友兰以“理世界”为本原(事物之所以然),熊十力、牟宗三则以“生化”、“创生”为本原(天地宇宙的生命真性)。从“存有—方法”的对应来说,一是知识、思辨取向的哲学概念(注重思辨之“学”),一是生命、实践的哲学概念(注重转化生命的成德之“教”)。当然,他们之间也有面对传统的视角差异,冯友兰是要以逻辑化、系统性弥补传统儒学在此方面的不足,熊十力、牟宗三则是要发扬传统儒学的实践性。前者的目标形态是知识、理论系统的建构;后者的目标是实践的开展、生命的转化,学问、道理涵摄于生命实践过程之中,思辨之“学”并无独立的地位。换言之,前者是“知识化”的哲学观,注重思想系统的建构,实践性是要收摄于思想之中的,至于它的实践效应则是建立了完整的思想系统之后的事情;后者则是“合知行”的哲学观,注重生命的转化,哲学不能停留于思辨、思想,而要转化为生命、精神或人格。
学界对于此两类哲学观均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对于注重理智思辨的哲学观,有学者认为它代表了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冯友兰讲理气形上学,其良苦用心乃在于改造传统笼统、浑沦、不讲逻辑,以价值取代事实的思维模式,具有现实意义”(36)郭齐勇:《熊十力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1页。;“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道》《新知言》诸书即旨在用充分的论证、细密的逻辑、首尾一贯的结构为现代中国哲学的著述方式开出新的局面”(37)张学智:《中国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14页。。这些评价认同清晰的、有逻辑的概念系统是建立中国现代哲学的应有之义,概念的逻辑生成是“讲哲学”的现代典范,是“哲学性”的重要体现,哲学的发展离不开概念的生成或构造。
但是,这种形式化的逻辑建构也遭到质疑。有学者指出:“自冯友兰等人开始……追求逻辑、系统和清晰性乃成为重建中国哲学的不二法门。可是人们忽略了,在逻辑、系统、清晰性的背后隐含的是静止、抽象、客观和可测度性等等预设,这一类预设可以说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精神和整体风貌是南辕北辙的。”(38)郑家栋:《“合法性”概念及其他》。概念的构画、逻辑的分析成就了“清晰”、“系统”,却将传统思想转化成了一个知识化、理论化的系统,而传统思想的内在精神和基本形态很难说是一个知识化、理论化的追求,那么,这种“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传统的“背离”。“将中国古代学术中的某一部分叫做‘哲学’,并按照冯友兰先生的主张,认为‘科学的方法,即是哲学的方法’,然后循名责实地建构出一个‘逻辑的、科学的’中国哲学,这条道路已将中国古学研究和使古学当代化的努力引入了困境”(39)张祥龙:《“中国哲学”,“道术”,还是可道术化的广义哲学?》,《哲学动态》2004年第6期。。如果我们的“古学”旨在把握作为一种生命状态的“终极的真实”,那么过度逻辑化、形式化的方法则背离了传统学术、思想或“道术”的内在精神,有将近代西方式的哲学概念用来宰割传统学术的嫌疑。这些评价与熊十力、牟宗三的立场一致,认为概念化的哲学无法把握真实的生命,也不能体现传统儒学的真精神。
可是,哲学仍然是要通过“思维”、“言说”来“表现”或“揭示”这一“生命领域”,或者说,哲学仍然要呈现为“思想”。有学者指出,“‘爱智慧’而不是‘有智慧’才是‘哲学’的本义”,“哲学具有共同性,不过这种共同性更多地表现为起源、问题和对象,而不是概念、方法和体系”(40)张志伟:《全球化、后现代与哲学的文化多元性——简论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彭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36页。。哲学不即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追寻、理解和思考,只是这种理解、思考不一定是概念化的、系统化的方式,而可能是非概念化的方式。“通过这些非概念建构的但又是更纯粹、更生动的理性探讨方式来分析和接近中国古代思想就比较有可能找到沟通的脉络……我们仍是在向西方学习,只不过不再只向概念化的传统学习,而也要或更要转向后概念化的新视野罢了”(41)张祥龙:《中国古代思想能否被概念化》,《读书》1999年第7期。。这一类批评在反对将概念化体系作为唯一的哲学范式的同时,仍然强调哲学的“思想性”,它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回到“古学”的立场,将哲学视作一种生命实践或精神修炼,也就与强调“合知行”的哲学观拉开了距离。这一思想倾向是值得关注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思辨性哲学观的升华,它强调在思辨化的哲学形态之外,要发展出本源性或根源性思想的哲学形态,这一方向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或“后概念”的哲学方式。
在“合知行”的哲学模式下,思辨之“学”与实践性的成德之“教”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内在紧张。牟宗三明确提出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教”,既是“教”就有一种讲法、一种教训(teaching),更重要的是,对于教义不仅要了解,而且更要去实行。如果我们将一套系统性的思议言说称为“学”,将实现生命的转化称为“教”,那么在“教”的“哲学”模式下,知识性、思想性、道理性的活动是收摄、消融于生命实践之中的,正如梁漱溟所说的:“假如说他们亦有哲学的话,那在印度只不过是其宗教生活中无意而有的一种副产物,在中国则只是其道德生活(人生实践)中无意而有的一种副产物。”(4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7页。在以道德生活为究极的修养实践中,“思想性活动”之“学”既无独立性,也就无充分、系统展开的必要。在这一视域下,“学”要么完全收摄于实践,要么只是副产物,否则只能是“支离”。
实际上,无论是在熊十力还是在牟宗三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哲学观与哲学建立之间,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思辨的展开”与“实践的智慧”之间的紧张。他们一方面强调简易、直接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则进行着一定程度的概念分解和逻辑思辨。牟宗三曾这样描述思辨之“强力求索”:“凡客观地思参造化以明各概念之分际以及其分合,此确不易,故常不免‘有苦心极力之象’,所谓强探力索者是。若非只是主体之冥契,而复欲由客观分解以展示之,则非‘苦心极力’,即不足以尽其中之奥蕴。”(4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卷,第447页。他对“强力求索”的描述,实可以看作是他“苦心极力”消化康德的自况。
可是,牟宗三自己也说:“智慧之造始与思想之开发固是两事,即思想之开发与践履造诣之高下更是两事,非可一概而论。”(44)牟宗三:《圆善论·序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卷,第15页。从成就人格、转化生命的实践立场来看,一个逻辑严密、充分展开的思辨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必要条件。相应地,思辨的展开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何种具体的生命实践,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现代之“学”的立场上,我们须承认“思想的开发”有其内在的逻辑,也有其独立的意义。“思想的开发”或许有多种方式(不限于概念思辨系统),即使从概念思辨的方式看,思辨性的系统将生命实存对象化、概念化,确实拉开了与生命实存的“距离”,但同时也避免了实践对思想性的淹没,从而使思想性保持观照与反省。哲学作为“思辨地面对实践”,而不是“实践地面对实践”,它也是独立的一套,不能完全收摄或消融于实践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