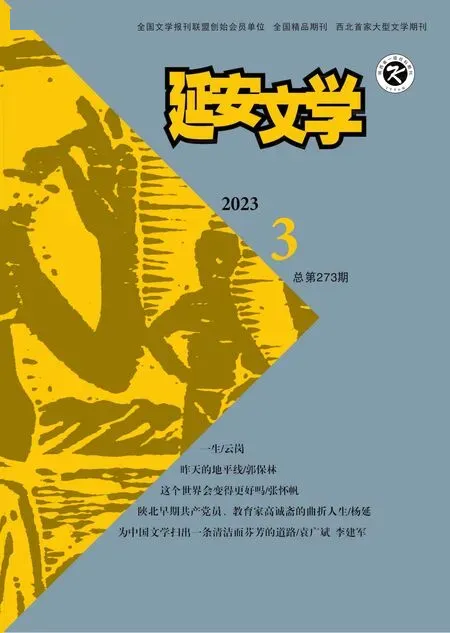我的文行之士(续)
朱 鸿
阎纲与周明
北京文学界的陕西人,我认识最早、敬意最深的,当是阎纲和周明。
阎纲和周明也有其异,我指的主要是性格。阎纲凝思,沉重,爱憎分明;周明朗畅,喜悦,世界大同。他们的名字似乎也透露了这种信息:纲者,提要也,明者,光亮也。
阎纲和周明也有一致,我指的主要是对陕西作家的态度。他们都关注陕西作家,凡有才华的展示,一旦发现,就高兴,就传播。只要求助,他们便伸手以扶助。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京夫、高建群,皆在中国文学界腾声千里,试问,谁没有得到过阎纲和周明的鼓吹与举荐呢?既使成绩微小的作家,缺乏影响的作家,甚至现在还很年轻的作家,他们仍怀以热望,涌以热情,并会对其成长施以大力。
所谓的伯乐精神指,马有良有驽,相马师善辨千里马之能,从而让其奔腾,免其死于槽枥之间。以伯乐精神称颂阎纲和周明,不妥且庸俗。我以为阎纲和周明的所为,几近于推贤进士,是汉唐以来的一种立人达人之传统。材属于天下之材,有地位和有权力的人,皆有义务推贤进士。
司马迁无权力,有地位,任安遂提醒,让他注意擢奇,以为朝廷用之。韩荆州得地位之势,具权力之重,所以李白请求,盼韩荆州使自己激昂青云,扬眉吐气。如果司马迁能像任安所嘱,韩荆州能像李白所吁,那么他们就是推贤进士了。
阎纲和周明如此所为,不是推贤进士吗?我不懂政治和经济,然而知道成文学之事。从陕西看北京,北京当然是文学的中心和顶峰,这是由文学的资源决定的。从北京看陕西,陕西是否属于文学的边缘和低地,我不清楚。不过我明白,在陕西,文学的资源不足,尤其是展示平台不足,虽然这里并非无才。
陕西作家要成文学之事,无不希望北京有人提携,而北京文学界最亲近最方便的则只能是陕西人。故乡之情,几近于血脉之情,在中国的任何畛域都是根本。
阎纲和周明不薄陕西作家,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贫的,富的,贵的,贱的,统统支持,做到了推贤进士。我认识阎纲和周明是在1985年春天,当时我在陕西一家文学杂志社工作。大学毕业,入职不满一年,打开局面是紧迫的。一天早晨,头儿招呼了一声,阎纲和周明马上要来。我正暗忖阎纲和周明是谁,骤闻几位编辑匆匆下楼,以喜悦迎接。我也随之下楼,恰恰一辆黑色轿车缓缓进门,停在出版社的院子。只见阎纲和周明笑着下了车,出版社三级领导一一向前握手。旋转了几圈,轮到我,也就行了一个握手的礼,从而认识了。
不料认识以后,竟交游了近乎四十年。今天仍有往来,真是幸甚至哉!
实际上我与先生的交游平淡极了,无非是过节问候,偶尔往北京去出差,顺道看一看,碰到组稿之事,请其帮忙。他们永远是诚恳的,可靠的,既使帮忙无果,也感觉温暖。
周明和阎纲,各有一事,我反复回味,始终觉得一种贤者之德馨。
有一年,我带妻儿过北京赴北戴河,忘了带照相机,便向周明借用。由于时间甚紧,约定在一个地铁口见。我辗转到了地铁口,就远远地游目搜寻。眼光逾越车辆和身影,发现他已经在等我。周明坐在地上,背靠着墙,两腿伸长,很舒服的样子。我赶紧跑过去,一声感谢,拿了相机,便辞他而去。
有一次,我和安哲探望阎纲。相叙之间,方庄一带停电,遂在黑暗之中继续论天论地,直到深夜。电灯不亮,电梯不行,就劝阎纲不必送了。阎纲说:“远道而来,怎么也要送。”便举着手电,从十七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送下楼。想着他将再移趾返上十七层,我和安哲不仅慨叹。那年,阎纲应该74岁了。
2019年秋天,阎纲回到陕西礼泉,养老于梓里。
虽然是高寿,且在养老之中,但阎纲却一直很忙碌。除了接待宾客以外,他还写作,编书,为青年作家传道、授业并解惑。岁月匆匆,阎纲也已经过了九十华诞。
2020年冬天,我约了几个朋友同行,看望了阎纲。他的身体刚柔并存,他的思维清晰且活跃,他的日常生活充实而舒适,这一切无不令人欣慰。这次见阎纲,我还意外地获得了他的墨宝,阎纲鼓励我,其书一幅:博观约取。他在落款处又撰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把阎纲和周明并列在一起,是因为我认识他们的一瞬之间,他们就在一起。他们也总是结伴,一起应邀回陕西参加文化活动。还有一点,他们的家都在关中。阎纲宅九嵕山下,周明宅终南山下,秦川之旷荡,也必会熏染他们。还有一点,阎纲1932年生,周明1934年生,少年是在民国度过的,他们难免会沿袭一些古风、古道和古典。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这是唐的气度,长安的精神,由阎纲和周明带到了北京文学界。
我愧无项斯之标格,然而经常得到先生的美言,是十分快乐的!
我收藏着阎纲和周明的贤者之风。时间会消蚀并湮没所有的破铜烂铁,但玉的光泽却会永在。
阎纲和周明,念及先生,想到先生,我总是喟然!
邢小利与仵埂
邢小利与仵埂是亲密朋友,曾经共学,可以论艺,可以适道,可以权,可以戏,也可以谏诤。若有事,便几近为盟好。不过性格之异,各如其面。
二十九岁,我尝有一蹶,然而并未不振。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发愿不仕。一蹶之后,就更无什么奢望和妄念了。古者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我至诚地想做这件事,没有不振,是指现在干干净净,除了生存,要专务文学。
不过文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埋头工作的精神是必须的,但唯埋其头,却大约不行。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前往邢小利家。我有关于大学生活的散文集出版,请他评论。
这件事是我和小利交游的发轫,印象至今清晰。那时候他已经调到陕西省作家协会,遂住了高桂滋公馆。高公馆有一座小楼和三进四合院,小利居四合院里的一间房。他这一间房又分一客厅,一卧室。我是冬天见小利的,尽管脚踩红木地板,我仍感觉湿冷。小利的文学以评论为主,他的评论文章不枯,不硬,观点氤氲于感受之中,所以我要拜托他。
小利答应爽快,且行动迅速,评论文章俄顷发表,对我是可贵的鼓舞。
评论我的散文,最早的是刘路,最多的是小利。不算在陕西文学综合评论中分析我的作品,只算小利对我的单独评论,共计五篇。这个分量非常重了,这份情意非常重了。
陕西评论家对陕西文学的发展,贡献甚大。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位评论家始终在追踪陕西作家的艺术探索,并全面地频繁地予以评论,一是李星,一是邢小利。其他评论家的声音也很宏亮,且有卓见,但李星和邢小利的声音却更为持久,尤能多重奏,多旋律,不分朝野,不分贵贱,不分亲疏。
在对陕西文学的研究上,邢小利和李星还有不同。邢小利显然超越了对某位作家的个人研究及某部作品的具体评论,这体现在他的多部著作之中。
实际上,邢小利不仅是文学评论家,而且也是散文家和小说家。作为散文家,世人皆知。作为小说家,过去其面目还比较模糊,不过2021年,邢小利有一部长篇小说行销,遂使其小说家的业绩骤然杰出起来。我以为他应该有一顶别的文人难戴的帽子:文学家。
也许在正式拜托小利以前,我和他在某种公众场合还打过招呼,礼节性地聊过,或共同旁观过路遥的发言,凡此统统忘了。唯在府上那天,会晤之际,我凝视了他。小利的脸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白净且泛红晕,遂想到了两个俗语:颜如宋玉,貌比潘安。这样的长相是容易吸引女孩的,然而我从来不指出这一点。1994年,参加汉中笔会,李燕珍,一个北京的编辑,竟高调明言:小利会受女孩喜欢。
小利也知道自己的佳长相,不过鲜有自矜的,唯李燕珍赞赏以后,他得意起来。那天他笑了三分钟,不,他一直在笑,甚至为了留住笑的样子,他连晚饭也不吃。
小利的佳长相似乎给他增加了特别的自信,一旦冲动,他就说:“谁能聪明过我邢小利。”众朋友皆乐,然而暗忖,小利也并不是吹嘘。
反顾岁月,凡过来之士,都会承认,1992年以后的一些日子是纵意的,率性的,欲望的满足大于理想的追求的。这些日子,我和小利及众朋友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且格外痛快。
讨论艺术、道德或政治,热火朝天,忽然便到了凌晨,肚子当然饿。这时候,保证营业的餐馆,是西安鼓楼北街一带的铺子。小利说:“走,咥面条。”齐声响应,就乘出租车两辆或三辆,骏奔吃面条。鼓楼北街的砂锅、烤鱼、炒米、煮馍或包子,什么没有,不过众朋友多是关中人,胃以面食为宜,又是夜宵,遂呼啸而去,咥了面条。小利提议,也就是小利结账了,屡屡如此。虽然面条不贵,不过毕竟也是支出。目击小利掏钱,数钱,我总是想这家伙干什么呢?除了工资和稿费,还从何处赚钱呢?
三十年以后,小利偶尔会慨叹经济紧张,并列出他的花费清单,包括父亲的、儿子的和诸弟的。小利深灌儒家文化,遂义要行,责要尽。
每隔旬日,众朋友要约陈忠实会食,陈也飨宴众朋友,愉悦之至。饭讫,往往要至歌舞厅唱几曲。陈忠实说:“你们去吧!想弄啥弄啥去。”极其开明,然而他的羡慕之情也不禁而露。我没有音乐天赋,嗓子也差,不过是作陪罢了。然而偶尔,兴致骤起,我也独入歌舞厅。有一次,唱了数曲,觉得乏味,遂至吧台付款。手伸进口袋,竟是空的。我打电话给小利,称不买单不能回家。小利说:“有钱,不过我在四川开会呢!这样吧,你告地址,我让我弟送钱。”半小时以后,他弟便送钱来了,并说:“我哥让我给你多留一些。”
由我和小利负责,为陕西作家出版过一套散文丛书。各有分工,一位在别的出版社当总编辑的兄长有权力,遂分派他印刷招贴海报。春节以后,北京有订货会,当此之际,用以推广此散文丛书。总编辑承诺慨然,保证办妥。不过到了春节放假之日,仍没有消息,我和小利便同行,诣总编辑。总编辑倒是拿出了一张设计页面,诸作也都有了位置,可惜放假了,往哪里去印刷呢?过年以后,就是订货会,毫无回旋余地了。总编辑舌头缠绕,不知所云,不过小利已经清楚此事落空。我也明白计划破灭,不快至极,只是碍于面子,沉默了。小利是散淡之士,偶尔还显腼腆之色。这天晚上,楼道空空荡荡,灯也不明。他突然暴怒,圆睁着眼睛骂总编辑,总编辑吓软了,其既未回嘴,更未动手。出了楼门,除夕之夜的寒气遍布天地,不过有热血流着,并不觉其冷。
小利喜欢朋友,对朋友很慷慨。他在樊川有一院房,经常邀朋友至其老家,品味田园生活。有一年中秋节,他电话一呼,近十位先生和女士呼啸而集。他也是几周才返故乡一次,到了老家,他必须洒扫庭阈,铺张桌椅,并陈设瓜果,涮壶洗杯而沏茶,一一安顿各位。七嘴八舌,海阔天空,月便明了。还得吃饭,就吩咐王悦下厨。须臾之间,几个菜蔬上来了,一盘锅盔携着热气和香气上来了。众朋友无拘无束,大快朵颐,有的不禁冒汗,难得体验了什么是酣畅。随之沿曲径登少陵原,以接天赏月。或席地而坐,或踟蹰而行,自主且自在。清辉普照,清风轻拂,瞬间脱离了尘世。忽然谁朗诵起了诗,其他人立即跟着朗诵。诗落,歌便起。深巷犬吠,犬不得不吠。东方未白,鸡竟争唱。
改革开放拓宽了中国人的见识,遂思想活跃,希望表达。嘤其鸣矣,一聚再聚,以求明道。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我和仵埂成了朋友。
小利做了我和仵埂的媒介,不过彼此往来无非是清谈。罕有实务,遂无利益和荣名。然而清谈也很费神,因为清谈难免显示是非、雅俗和善恶,也连接着价值观。清谈之范围颇为广泛,凡文学、哲学、宗教、读书、爱情、死亡及国家命运,皆有涵盖,且反复探索。
我和仵埂从来不研究怎么赚钱,仿佛自己是富翁似的。当然,仵埂比我有财,曾经向他借过一笔。也许仵埂早就忘了自己是债主,他也没有于公开场合披露过我是如何借钱的。顺便指出,须臾偿债,在下不欠账。
有一种时间似乎不能以长短衡量,也许应该以美丑判断才合适。我和仵埂起码有三个时间是美的,并能营养精神。
为了验证普通投影识别法的可用性和改进后的投影法具有更加优秀的识别性能,下面利用上述所抽取的各种特征矩阵,结合PNN神经网络,进行对比分析实验。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至西安音乐学院见仵埂。不遇,他在城北活动。我也是顺路所谒,没有约。到了仵埂的楼下,我才打电话给他。他嘱我敲门,其妻小龙在家。我诺诺,不过并未至其府上。我和小龙也很熟悉,然而还是觉得在宅外恭候合适。我遂盘桓于楼角,足有一个小时。新雪以后,空气清冽,杨树峻拔,尽管我的耳轮和鼻尖冻得生疼,我仍在楼角的旷地上踱着,直至仵埂归来。他步履匆匆,并未注意到我正徘徊着,是我喊了他。仵埂又是道歉,又是埋怨我不进屋,使我受了冷。我随他登其堂,坐且喝茶。久等以后,也不过问了问他和小龙的情况,聊了聊新闻。相晤为乐,欣然而去。
有一度,我生存的压力甚大,仵埂也颇为惆怅,我便邀他游了一次少陵原。先乘车至樊川局连村一带,再举足渐行,过华严寺,至朱坡村。站在一个高台,北望少陵原,玉米在田,谷子在亩,几十里平畴,一片青葱。我引仵埂沿朱坡沟向蕉村走,尽管是土路,小路,不过旷野广矣,自然而然,令人踏实,舒服。那几年我父母租房居韦曲,遂不入蕉村,未至我老家。我引仵埂从皇子坡下少陵原,西望夕阳,在长安饭店吃了面条,再乘车各返其家。彼此持肝吐胆,从而卸掉了累累负担,秋气也顿显高远。
几年以后,我和仵埂坐在陕西省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讨论人生与婚姻。大约晚上九点聚于此,原本计划随便交流一下,算是小憩。不料陷进了问题深处,勒马也难。光阴确乎是白驹过隙!我到这里的时候,长安路上满是夜行的人,离开之际,天色趋亮,早行的人已经熙攘了。夏月皎洁,露水微凉。
仵埂始终当老师,并以文学研究的成果晋升为教授。他知识博洽,期在打通东西和古今。他的评论总是潜藏着一种思想超拔的韧性,风格之鲜明,截然区分了谁是仵埂,谁不是仵埂。
2002年春天,为我的一部散文集举办了研讨会。此书由东方出版中心行销,学者多认为是所谓的文化散文,实际上属于思想随笔。这个研讨会,主要由小利策划,并执事于朝夕。前一日晚上,我在邢邸,商量明天早晨的议程。大约二十二点前后,我打算回家了,陈忠实打电话给小利。我向小利摇手,示意不语我在此。听得很清楚,陈忠实羁旅广州,不能出席研讨会,遂要口述一个发言稿,让小利记录,并在明天早晨宣读。小利且接电话,且在桌子上找纸。抓住了一叠纸,展平,便匆匆记录。我坐其旁边,且闻铿锵之音,且观飞舞之笔,忐忑着,置我的感恩于心底。陈忠实十分认真,口述了近乎一个小时。小利放下笔,站起来,一边甩着手,一边来回转。他叮咛我赶紧回家,自己再整理一下发言稿,明天见。
研讨会的举办,怎么也需要一定的经费,其来源如何?仵埂妻小龙适在上海工作,负责企业文化。小龙所在的公司欲资助西北地区艺术品质纯粹的作家、画家或别的艺术家,便咨询仵埂,应该资助谁。仵埂屈指算了算,向小龙推荐了我。有上海的公司提供研讨会的经费,遂能顺利进行并告成。
我的母亲患病,仵埂侧闻,专程看望了我的母亲,此事我不敢忘。我也看望过仵埂的母亲,其高寿,八十六岁了。我祝福她,宛若祝福我的母亲!
小利也是有脾气的,不过总体平和,温润,凡进退、盈亏和荣辱,皆有空间节度。五十岁以后,他变得敏感,易怒,甚至勇猛和峥嵘。也许才不得尽用,道不能直通,遂胸存伤感,意有郁结。当是时也,他的批判性和深刻性就变得突兀了,这在文章中有表现,在日常交流中也有表现。2011年,碰到陕西省文艺学论家协会换届,见非驴非马执掌,如乌合之众相凑,虽然任常务理事,他也公开声明:退出此会。为此,陕西文学界不禁一震。
仵埂大有风度,其修养冠乎群伦。在学术会上发言,以思想的推动,他往往眉间扭结,目光四射,显然要震山川,惊鬼神。除此以外,人不管男女,不管长幼,他总是彬彬有礼的。他不仅给人以安全感,也给人以温馨感。不过我偶尔会想,仵埂的城府也冠乎群伦吧,甚至他的城府从其当村干部的时候就开始建筑了吧!然而仵埂的基调是仁,是慈悲,是爱,我几乎没有视听过他对谁表现出恶意。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能穿越各界,四通八达。
我难免会怼他,小利更是数怼仵埂。有一次,方英文请李建军吃饭,小利、仵埂和我作陪。仵埂不失良机,还带了学生,盼其开阔眼界。可惜不知为什么事,小利认为仵埂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确,愤然作色,弃席而去。仵埂多少显出了一些委曲,不过并未发火。也许他理解小利,且要包涵小利,这也正是他修养的见证。
小利心直,仵埂心曲。我曾经同时发了一篇某学者的文章给小利和仵埂,以求鞭挞。对此,小利说:“混子,狗屎一堆。”仵埂说:“这个人干这个事,正常。”
在我最悲痛和最高兴的瞬间,小利和仵埂没有一次不出现在我身边。吾兄啊,想起这些,我的热泪就来了。
田和平与陈凡
几十年了,田和平与陈凡互为朋友。在陕西,他们都是出色的出版专家。
中国的出版工作特别难做,图书中不能有标点符号之错,不能有文字和语法之错,尤其不能在内容上有政治的、宗教的、外交的、法律的、色情的和版权的失误。问题是,凡属于内容的皆具弹性,不易把握。一旦有错,出现了失误,处理起来也非常离奇和吊诡。
和平与陈凡的职业生涯以出版始,将以出版终,我钦佩之至。
我跟和平也是朋友,跟陈凡也是朋友,彼此皆是朋友,且有三十余年,足矣!
和平是陕西富平人,读西北大学文学专业,1986年毕业,径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从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其辛劳和功行不言而喻。
陈凡是陕西礼泉人,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专业,1986年毕业,留校,直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谚曰:人挪活,树挪死。陈凡遂调至未来出版社,又调至西安出版社,现在任副社长。陈凡的辛劳也到了,功行也到了。
20世纪80年代,显然是中国的黄金时期,一瞬之间,百废俱兴,百姓振奋,中国人无不感到一种前途的光明。我对那个历史阶段的体会是:云开雾散,太阳出来了。当此之际,出版行业不仅活跃,而且力求发展。和平与陈凡的单位皆在吴家坟一带,离得近,又是同仁,又是单身,遂联络起来。
我稍长和平与陈凡二位,也早他们两年至陕西人民出版社当了编辑。人不亲行亲,行亲便人亲,这合情合理。我不知具体缘于何事认识了他们,然而总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跟他们竟往来了几十年。我御改革开放之风,颇为自信,从而会在出版系统组织一些活动。大约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识和平与陈凡的吧!岁月累积,难免淡忘,是否如此,也未可知。实际上具体缘于何事认识并不重要,关键是,三十余年的交游已经酿造了人生的馨香,并形成了人生的珍宝,价值大矣!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可惜我的十有五之年,施行教育学大寨的方针,不得志于学,反之要在校园里养猪或养鸡,我的而立之年,又遭遇了一堆麻烦。当此之际,我只能孤绝发愤,希望以情思的表达通其道,且争取发表文章,以免磨灭于世。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陈凡做的编辑,若欲避祸,他完全可以放弃此书,然而陈凡并未推辞。那时候,李峰是领导。其尤为支持我的书,是用了鼎力的。我确信,第一本散文集之所以能行销,是碰到了义人。我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和第三本散文集,也是碰到了义人。1993年,我的第四本散文集面世,责任编辑是和平,他当然也是义人。
经一事,便熟悉了。我觉得和平颇为厚道,易于明望,旋踵又找和平,请他给我的老师刘路先生出版一本论文集。这应该是有难度的,不过他也接受了。
凡此义人,尽在常念之中。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慷慨地予以帮助,但你却没有机会帮助朋友,这令人不安且内疚。应你之嘱,朋友为你做这个,做那个,做得自然而然。这样的真情,只能使你对朋友肃然起敬。
2002年,我离开了出版社,不过职业的变化并未意味着疏远朋友,反之觉得和平与陈凡更亲切了。朋友就是朋友,我跟他们一直保持着交游,且是一种恒温状态。
看得出来,和平与陈凡一直有自己的节奏,相互理解、鼓励并支持。他们臻于默契,也享受着默契。
和平与陈凡长得墩墩实实,朴朴素素。他们的性格也都倾向内敛、低调和宽容,略无伶牙俐齿,也不会甜言蜜语。他们知识渊博,文化视野开阔,然而从来不去炫耀。
他们以求学的途径,从渭河北岸起步,落脚在古都,并于斯躬耕出版界,从而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养大了孩子,唯赖自己的勤奋、能力和品德。
多年以前,我跟和平、陈凡便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三个人的时间可以错开,遂相聚于某家泡馍馆,简单地吃一碗羊肉泡馍或牛肉泡馍,见见面,聊聊天。似乎从来没有为一件具体的什么事会晤,无非是求得释怀,作一番精神的交流。
虽然饭很平淡,不过茶好,绝对是上品。陈凡久攻茶道,九州万千之茶,他懂得什么茶没有打农药,没有上化肥,懂得什么茶醇香,什么茶厚味,什么茶偏重什么营养。他也不会以丽辞嘉言介绍,只是邀你品尝。辞别之际,每每要从包里掏出一种赠我与和平,或说:“这个普洱熟茶,二十年的,感觉一下柔滑细腻吧!”
——喜迎十九大 追赶超越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