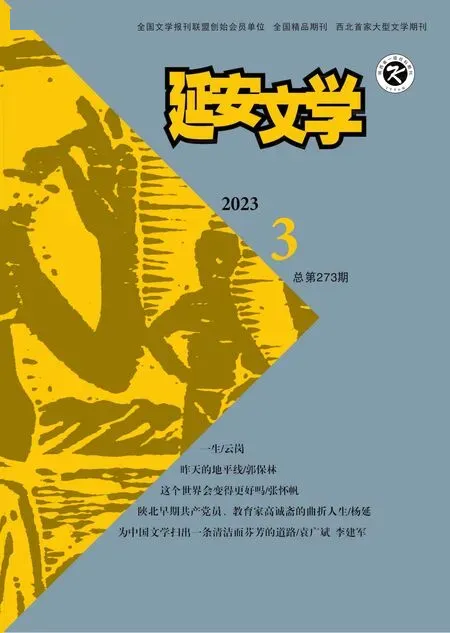换牛记
田 华
一
1982年包产到户,王得贵家分到七亩八分责任田,加上自留地,山原共有八亩多地。分完地,生产队紧锣密鼓着手分大牲口。为彰显公平,队里先后出台了几套分配方案,但都不尽如人意。最后,只好用古老的抓阄法来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规则是:不管你家口大小,土地多少,一切全凭运气,抓个牛是牛,捡个驴是驴,摊上瞎眼瘸腿老掉牙的算你倒霉。
前一夜,王得贵和叶荞麦兴奋地睡不着觉,他们热切地讨论着第二天抓阄的事,两人将生产队里有名头的大牲口悉数盘点了一遍。
花青怎么样?
花青还用说,狗日的脾气犟,可力气好,拉独犁一晌能耕几亩地。花青是头大骡子。
一撮毛呢?一撮毛能给咱也不错,叶荞麦巴结王得贵似的笑着问。
王得贵说,一撮毛比花青还厉害,就怕你使唤不住。一撮毛是匹红鬃烈马,额头正中有一撮长白毛,开了天眼似的。
叶荞麦思想了一阵说,骡子马就是不好使,专欺负女人娃娃,还是抓头犍牛吧,牛性子凉,好使唤。她掰指头算起生产队里的大键牛,黄毛、黑蹄、斜眼、轱辘、独角……王得贵当饲养员多年,牲口的绰号成天吊在嘴上,就没有叶荞麦不熟悉的。
王得贵说,三头壮骡子,四匹高头马,八个大犍牛,头梢牲口里头随便抓,抓到哪个都好。再就剩下五头麻驴,几个瞎眼瘸腿老掉牙的瞎瞎牲口了。叶荞麦认为瞎瞎牲口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她说,咱心不高,只要是能使力气的犍牛就行。
王得贵说快睡,快睡,明儿照你说的抓就行了。王得贵心里不装事,头一挨枕头呼噜就打得吼天雷地。叶荞麦却睡不下,吹了灯盘腿坐在炕上想心思。月亮渐渐升高了,能看得见她翘翘的嘴角和明亮的眼睛,叶荞麦热切地期待着一头即将属于她家的大牲口。
那些日子,叶荞麦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与激动,连走路都踮着脚。头一次拥有了这么多土地,叶荞麦心里头尽是想法,首先,就是一头得力的大牲口,不管咋说,土地总归要牲口耕种。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头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的牲口最终会走向他们。叶荞麦和王得贵有一个时期关系不好,甚至不在一个炕上滚就是那时候的事,说严格点,就是从一头她想都没想过的瞎瞎牲口走进家门开始的。
叶荞麦想得多,想到实在累了,倒头就睡。水银一样的月光从天窗里倾泻进来,铺洒在炕头上。叶荞麦那时还年轻,睡梦里浅浅地笑着,圆圆的面庞在月亮底下很好看。
天刚亮,两只喜鹊在院门外的杨树上喳喳喳叫开了,叶荞麦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催促王得贵赶紧起床烧香。王得贵起床净了脸和手,在灶神前点燃三炷香,跪在地上默默祈祷后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据说灶神掌管家里一应大小的事务,他们一直都习惯将自己的愿望寄托于神灵。
叶荞麦说,运气好,抓一头膘肥体壮的大犍牛;运气差,抓头次一点的也行。他们不是贪心的人,但绝不想得到一头瞎瞎牲口。在叶荞麦的期望里,犍牛是抓阄的底线,只要是犍牛,哪怕是个犊子,就不算运气太差。
怕狼偏偏狼来敲门。很不幸,只一个早晨的工夫,情况就起了变化。脚步轻快的叶荞麦在院子里干活时,时不时要朝门外瞥上一眼半眼,她想象着一头大牲口庄重地走进大门时的情景,硕健的牲口使大门显得局促,她甚至已经开始计划要将大门拆掉,加宽重修,好使牛出来进去走得畅快些,这情形一直持续到大门外闪过一头牛的影子时。
王得贵回来有一阵子了,他拉着牛在家门口徘徊,抓到这样一头牲口,自觉颜面无光,不知该如何向女人交待。
跟牛短暂地相见,叶荞麦突然生出不可一世的傲慢来。一头小牛怯怯地跟在王得贵身后,它瘦弱干瘪、皮粗毛糙,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样的牛分到谁家会受欢迎?
叶荞麦恍若在做梦,有些不敢相信地问,就抓了个这?
王得贵尽量表现出一个男人遇事豁达的样子,故做轻松地笑道,就抓了个这么!他笑得很牵强,自己都觉着难受。叶荞麦反应过来,一拧身进了院子,王得贵和牛被晾在了外边。
二
叶荞麦气得脸都青了,开始数落起长了双臭手的男人来,亏你还在饲养室喂了那么多年牲口,竟然抓回一头比猫大不了多少的牛,这也叫牲口?
抓回这样一头牛,王得贵心里比谁都难受,比谁都冤屈。他想不通,就凭自己这么多年尽心竭力给生产队喂养牲口,老天爷也不该赏他这么个东西呀!想想他手里头捋过去多少高头大马壮骡子、山一样的大犍牛;想想他早上抓阄前的踌躇满志,而他最终牵回这样一头牲口,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王得贵欲哭无泪,可他毕竟是男人,很快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他将牛拴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走进窑洞同叶荞麦理论。
刘拐子家还抓了一头瞎驴呢!张百忍家不也抓了个瘸腿老牛吗?照你这样想,还都不活了?好歹也是头母牛呀!愤怒的叶荞麦把手里的针线活摔到桌上问,你给我说这瘦得像板夹了的母牛能干啥?
母牛咋了?瘦又咋了?瘦了能肥呀!只要好好喂,一样见风见雨地长,说不定日后给咱生一院犊子哩,王得贵辩解说。叶荞麦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冷笑,她已听不得半句辩解的话了,黑着脸兀自出来进去,所过之处煽得风吼。
很快到晌午了,叶荞麦对人和小母牛还是不理不睬。三个放学回家的娃娃却毫无偏见地表现出了热情,围着小母牛像看村里娶来的新媳妇一样。他们的评头论足很快招来了有气无处撒的王得贵的呵斥,娃娃们觉得无趣,各干各的事去了。小母牛刚到新家就不被女主人待见,估计心里很窝火,它开始发出抗议声,冲着叶荞麦进出的窑洞哞哞大叫,不耐烦地绕着树转圈子、刨蹄子——它大约是饿了。
饭做好后,叶荞麦端着半筛子草料走向小母牛,草料里拌了几把人吃的黑面。叶荞麦并不和小母牛说一句话,而是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它。看着瘦牛自卑地低着头,偷吃一般将草料卷进嘴里,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叶荞麦的火气又上来了,她真想问牛几句,你看你那怂样子,你的气派里?你还有一点大牲口的气派吗?
这天,王得贵和三个娃娃自己舀饭吃。以往都是叶荞麦舀好端上桌,王得贵觉得这顿饭是从脊梁骨上吃下去的。
晚上,叶荞麦出了奇事,她不让王得贵跟她一炕滚了。她说,抓了这么个能吃不能用的废物,还有脸上我的炕。王得贵也不说一句软话,黑着脸,窝着满肚子火,夹着铺盖卷到粮窑里睡去了。
无论心里多么气愤,既成的事实已无法改变,思想了一夜,叶荞麦强迫自己接受了这头牛。人老几辈子,头一次有了这么多土地,也有了一头所谓的大牲口,尽管这头大牲口实在不像样,但聊胜于无。她虽然态度恶劣,但还是跟着王得贵开始修牛圈、砌牛槽,在大门外给牛搭凉棚。
干了几天活,叶荞麦跟王得贵总共说了一句话,其实是下了一道命令,暂且先养着,七月交流会上拉出去倒换了去。
王得贵不以为然,他深知这样的牛不是说倒换就能倒换了的,分牛时,这头牛按168元搁价,拉到牲口市上,也许140元都没人出。王得贵心里默默盘算着,先得把小母牛喂好,喂好了才能卖上价钱。
王得贵见叶荞麦每天饭照做,活照干,冷着个脸就是不和他说话,心里又气又悔,他想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让叶荞麦去抓阄,如果依然抓到这头牛,看她还怎么怨悔?王得贵很想骂叶荞麦,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死不讲理,这事能由得了我吗?就像生娃娃,生男生女能由得了女人吗?王得贵甚至还想打叶荞麦,但这些都仅限于想法,而不会付诸行动,他哪有那能耐。在吉村,王得贵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可王得贵从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自己是疼老婆,疼老婆的男人一般都不会惹老婆。如此,王得贵只好一忍再忍。
一天,王得贵拉着无精打采的小母牛去看兽医,牛总不好好吃喝,得给开些中草药调理调理脾胃。一头牛不能吃,如何能长得膘肥体壮呢?在兽医家,王得贵碰上了一个远亲表弟。满脸指甲印的表弟也来给牛看病,那牛是个犍牛犊子,比他家的牛看起来搭眼。原来表弟的牛跟王得贵家的牛一个毛病,都是嘴刁不肯吃喝,身上的毛刺刺啦啦的。
开好中药后,王得贵和表弟拉着牛边往回走边拉话,自然就说到了生产队分牛的事上,两人都感叹自个命运不好,连头称心如意的牲口都分不到。表弟一连打了几个唉声说,淘气得很,以前淘生产队的气,没想到现在又要淘自家的气。表弟说表弟媳非要一头母牛不可,哪怕老鼠大点都行。表弟媳认为,母牛能生犊,家有一头母牛就等于栽了摇钱树。表弟说自打他把牛拉回去后,家里就骂声不绝,他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表弟说你看我的脸,就是让那母夜叉给抠的。王得贵万分同情地看着表弟,觉得自己的命运再怎么不济比他还好些,不管怎么说,叶荞麦总算给他留了脸面。
王得贵说,还不都一样,这边家里也是把气往死里淘,他忍不住向表弟大吐苦水,说起了叶荞麦把他从他们两口子的炕上赶走,差一点就不给他和娃娃们做饭,成天吊着个脸给他哑气受的事。表弟不解地问,你家不是母牛吗,表嫂还闹啥呢?王得贵说,一人一个脾气,一个沟子(屁股)一个渠渠,叶荞麦跟你屋里的正好相反,偏偏想要头犍牛,哪怕猫大点都行。王得贵解释说,叶荞麦认为地多庄稼大,牛使力气是第一考虑的。
我的个天!果真一人一个脾气,-个沟子一个渠渠,表弟觉得不可思议。他感叹道,咱俩咋都这么命苦呢!
走了一阵,表弟恍然大悟似地说,为啥咱不换了牛呢?你想,我屋里的死活要个母的,你屋里的非要个公的,这不正好现成吗?咱换一下不就得了。
王得贵愣了一下说,这恐怕不行吧?
表弟说,有啥不行的,这件事上,我屋里的事我完全能做主,换头母牛回去,她没准会高兴疯的。
王得贵心里暗喜,但他不露声色,怕表弟是戏弄他。
表弟卷了根旱烟棒,一拧为二递给他一半说,咋想的?快说说啊!
王得贵说,咋想的?肯定是母牛好,母牛能生犊,一本万利的买卖,可叶荞麦这个猪脑子不干,天天给我找事。
表弟说,知道你拿不了表嫂的事,要不咱顺路去你家问问,我是真心实意想换。
三
叶荞麦一看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表弟来了,爱搭不理的。王得贵说了表弟的来意后,叶荞麦虽然似信非信,但人总算热情起来了,忙着给表弟安烟泡茶。表弟问叶荞麦啥意见?叶荞麦说,这事突然的,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咱暂且不说。她安排说,你俩坐院子里喝茶说话,我给你们做饭去,一顿饭的工夫,咱都再考虑考虑,毕竟是大事。考虑好了,咱就换,考虑不好,权当你走了一回亲戚。
这顿饭叶荞麦做得是鸡蛋面片子。王得贵进屋端饭时,叶荞麦没有像前几天一样将饭碗搁到灶台上让他自己端,而是递到了王得贵手上。王得贵一看大叶面片擀得薄厚均匀,上头漂着鸡蛋花,菜绿辣椒红,搭配得煞是好看,心想这事有门道。
吃饭时,叶荞麦问表弟,换牛的事你媳妇不知道,你做得了她的主吗?表弟面片咥香了,边夸叶荞麦厨艺好边说,其他事我不敢说,换牛的事我百分百能做主,这本来就是我媳妇的意思,她睡梦里都想要一头母牛,真是瞌睡来了遇枕头,这回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叶荞麦听后说,我要犍牛为耕田种地使力气,顾的是眼前一坨坨,你媳妇要母牛为生犊子,考虑的是长远事,她面露难色接着说,按说我用母牛换你犍牛算吃大亏了,但我情愿,也就无怨无悔,既这样,吃亏占便宜咱谁都不许反悔。
表弟把碗递给王得贵说,还有吗?再来一碗。叶荞麦说,放开肚子尽饱咥,饭多着呢!表弟说,只要你俩没问题,我们那边还能有啥问题?不为母牛,我今天也不可能到你家里来。
表弟带着药,拉着小母牛,拐过山梁不见了时,叶荞麦才如释重负般说,总算把瘟神送走了!王得贵气呼呼地说,按你心上来了,这下你高兴了!可我看送走的不是瘟神,倒是财神,你这个败家子。
叶荞麦也不恼。反正,换牛之后,他们家的角色也互换了,这下是王得贵吊着个脸,叶荞麦反要陪上笑。这天晚上,叶荞麦把王得贵的铺盖卷又抱回自己炕上了。王得贵又恢复了睡在自己女人身边的权利。可王得贵心里很失落,眼前老是浮现出小母牛离家时怯怯的眼神,探路般似乎不情愿离开的步子,他觉得很对不起小母牛。
要是放在从前,叶荞麦未必看得上这头小犍牛,但经过抓牛事件的打击后,她的心气不高了,小犍牛对她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叶荞麦搜罗出家里的大麦、玉米、豆子、小麦和在一起给牛炒精饲料,亲自给牛煎药灌药,有空就打发娃娃去割青草,一心一意想把小犍牛喂成大犍牛。
有一天,叶荞麦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说,你说换牛这事咱跟表弟媳也没见面,她会不会把牛退回来?王得贵没好气地说,你没听表弟说这是他媳妇的意思吗?人家占大便宜了,还能给你退回来。叶荞麦说,这世上的事难说呢,这几天我右眼皮老跳,好像有什么倒霉事。王得贵自言自语地说,捡了便宜的人不担心你反悔,你反而担心人家,简直是猪脑子。
王得贵说这话的时候,叶荞麦手拿一把木梳子,蘸了水正仔细地给牛梳理毛,她的另一只手拿一块湿抹布,随时将粘在牛身上的脏东西擦掉,然后再梳理。这头有着宝石般的大眼睛,湿漉漉的嘴唇,性情温顺的枣红牛犊令她越看越喜欢,她觉得这是王得贵自抓了那个瘟神母牛之后干得无比攒劲的一件事。
一日,王得贵赶集回来,刚进村就有人告诉他,说换牛的人正在你家闹事。王得贵一口气跑到家门口,见许多人围了一圈正看热闹。透过人缝隙,王得贵看到叶荞麦和表弟媳手里攥着枣红牛犊的缰绳,正使出生娃吃奶的劲朝两边拽,像是在拔河比赛。叶荞麦脸涨得通红,说,你想硬抢还是咋的?
表弟媳呸啐了一口,说,吉村人都给评评理,是我硬抢,还是王得贵家骗人?王得贵挤进人群对表弟媳说,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商量,大吵大闹,不嫌丢人现眼吗?表弟媳冷笑一声说,骗子都不嫌丢人现眼,我拉自己的牛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她转身向围观的吉村人说,你们恐怕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吧?我外前人到街上给牛看病,王得贵把我外前人哄骗到家里,两口子一唱一和,又是好烟好茶,又是鸡蛋面片,把我那瓜怂哄转了,把好牛换给了他们。
听到这里,吉村人将目光齐刷刷地对准王得贵,紧接着,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像在相互求证。王得贵面不改色对吉村人说,你们千万别相信她的鬼话。他质问表弟媳,谁是骗子,你咋诬陷人呢?什么叫把你外前人哄转了?换牛的事可是你外前人——我表弟提出来的。
哼哼!你还知道是你表弟啊?是你表弟为啥要哄骗他?表弟媳说着扒开人群,把晾在一旁波澜不惊的小母牛拉到枣红牛犊跟前,说,大家伙瞅瞅,我家牛什么样子,王得贵家牛什么货色,用能生犊的母牛换小犍牛,瓜怂才会这么干,这不明摆着吗,这牛没有毛病才怪呢。
表弟媳又说,王得贵,叶荞麦什么人?猴嘴里掏酸枣的人,能做亏本买卖?王得贵愤怒了,他说,你这个女人不要满嘴胡然,你咋血口喷人呢?可当王得贵看向枣红牛犊和小母牛时,他惊讶地发现,也就才十来天时间,枣红牛犊俨然已脱胎换骨,仿佛另一头牛似的,而小母牛却更加不像样,原先大小差不多的两个牛,现在距离一下子拉开了。
这时围观的人群起了骚动,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个吉村人带点倾向性地问,既然不同意,牛刚拉回去为啥不来换?为啥要等十天半月呢?表弟媳一把将裤管抹上膝盖处说,牛刚拉回来我就不同意,我当天就要把自己的牛换回去,可王得贵表弟嫌丢人,死活不让我来,还打我,我腿上的伤就是他打的。为了二量烂面子,王得贵表弟居然动手打我,表弟媳悲愤地哭了起来。哭了两声,表弟媳又说,他居然敢打我,本来我要去死的,但一想,死了还便宜这俩大骗子了!至于为什么没早早来,因为我腿疼得走不了路,这两天勉强能走了,我就来了,我要把我的牛换回去。
叶荞麦说,你弄清楚好不好,是你外前人说你想要一头母牛,缠上门来主动要跟我们换,不是我们找他换的。表弟媳说,我是想要一头母牛没错,可不是你家这号母牛,我们村的人都说了,这牛要能生犊,太阳打西边就出来了。你想,你都不要的牛,我能要吗?
王得贵气坏了,他脸色煞白,一扬手说,行了,行了,把你的牛拉走!叶荞麦拽住表弟媳要算账,说牛吃了她多少精饲料,为追肥喝了几斤清油,让把账算清了再拉牛。表弟媳用嘲讽的口气说,你哪怕给牛吃的是海菜席,那是你的事,说明你是有家子,你爱给吃,关我屁事!再说了,你家牛是喝风屙屁的?这些天难道没吃我的?王得贵从未干过如此丢人折马的事,觉得脸上实在挂不住了,便一腔喝住叶荞麦,让表弟媳把牛拉走。
这天晚上,王得贵又从叶荞麦的炕上把铺盖卷抱走了。
四
小母牛回家后,王得贵家的气氛坏到了极点,叶荞麦连续不断地骂了好几天人,主骂表弟两口子,兼骂王得贵。可骂归骂,牛还得想法子往好里喂,因为一个多月后就是物资交流会,牛要上牛市去。叶荞麦心里着急,她强迫自己平复心情,十八般武艺全拿出来,她想尽快把牛喂得变过样子来。
也许这头小母牛的命运就是这样,总是无法走出王得贵家。物资交流会总共十二天,王得贵上了十二天牛市,可牛缰绳却一直在他手里。原因不外乎两种,要么看不上牛,说什么都白搭;要么勉强能看上,却只想拾便宜,出一百二十元就极具侮辱性了,可出八十元的也大有人在。随便一个犍牛犊子都在一百八之上,再怎么说也是头母牛啊!这价钱你说能卖吗?王得贵气得能吐血。卖的卖不掉,买的自然买不进来,家里的日子就等着一勺倒一碗,王得贵家倒换牛的希望落空了。
散会这天,王得贵和叶荞麦拉着小母牛往回走,路遇同样从牛市上下来的两口子,他们同王得贵两口子一样灰头土脸,唉声叹气。借火吃烟时男人问,为啥没卖了。王得贵说,咱牛不搭眼,人不出价。女人说,我看你家牛挺好的,母牛嘛,肥瘦没关系,能生犊子就行,就像女人生娃,又肥又大的,不见得能生养,瘦麻杆反倒生得凶。王得贵有大遇知音之感,不由将那女人多看了几眼。
叶荞麦问,你家的又是为啥没卖了?男人说,不知道。不如我家的都卖得一个劲儿的,但这个瘟神就是卖不了。叶荞麦说,我看你家牛也挺好的,瘦是瘦点,但骨架子大,将来准能出息个好犍牛。男人也有大遇知音之感,感激地说,要都像你这么识货就好了。他们顿时就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一路走一路相互安慰,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简直鬼使神差一般,那家人居然提出要换牛,说他们本就打算将这头犍牛犊卖掉之后买一头小母牛。
世上换牛的事尽让王得贵家碰上了,究竟是天意还是缘分,谁能说得清。因为有前车之鉴,王得贵两口子很谨慎,起初并未答应,那边一个劲地给他们做工作,王得贵两口子便心动了。叶荞麦其实蛮看上那头黄牛犊的。但王得贵和叶荞麦还是没有当场做决定,他们一旁商量了一番后,王得贵说,我怕我们会后悔,容我们回去再想想,你们也找人参谋参谋,看划算不划算,如果都是真心实意,咱们三天后见话。
换牛那天,为防止日后生变,叶荞麦觉得需要郑重承诺一下,他们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不会写保证书什么的,便口头做了保证。王得贵说,谁反悔谁不是人。对方男人说,谁反悔谁就是牲口。
分别的那一刻,王得贵分明看到了小母牛眼里的哀怨,它默默地注视着王得贵和叶荞麦,仿佛有满肚子的委屈话要对他们讲。王得贵受不了那眼神,别过脸去,不忍直视。他想幸亏小母牛不会说话,否则的话,它一定会跳起来美美实实把他们骂上一顿:你王得贵两口子什么人嘛,一会儿把我换给张家,一阵子把我换给李家,全然就没把我当个牛看。
五
卖又卖不掉,换也换不成,受此几番打击,王得贵和叶荞麦彻底死了心,也认了命。他们终于相信,世间的事都是有定数的,舍多少,得多少,上天早替你算好了。钱财也好,牲口也罢,该是谁家就是谁家的,一点都强求不得。如此,不再报希望,心反倒安定下来,一心一意对待起小母牛来了。
叶荞麦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她觉得还是自己对小母牛不好,才有了今天这种结局。她将小母牛和家里的鸡狗作了对比,母鸡给她下蛋抱鸡娃,狗忠心耿耿给她看家护院,前提是她是多么看好它们啊!小鸡从破壳而出到变成大母鸡,它们是在她充满爱意的目光中长大的,她时常能想起她端着小簸箕,站在院当中咕咕咕叫它们来吃食的情景,起初,它们像一堆嫩黄色的绒球欢快地滚向她,很快,它们像淘气的娃娃争先恐后奔向她,长成大母鸡时,它们像生育过的女人,摆动着肥胖的身体,有些笨拙地奔向她,让她的心欢喜得一颤一颤的。
狗呢,就更不用说,时常偎在她身边,像卫士一样随她走来走去,家里的事没有狗不知道的。吃饭时,狗就蹲在她身边,她最爱用筷子将饭团夹起来扔在半空中,让狗跳起来接着吃,她管这游戏叫“打卦”,狗乐得享受其中。叶荞麦这才想到无论家里的鸡、狗、猪,还是庄稼,她从一开始就一心一意对待它们,对它们抱有美好的期望;而这头小母牛,一到家她就厌恶嫌弃它,在牛面前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甚至都不愿好好看它一眼。叶荞麦想起一句老话叫“想啥来啥”,可不是吗,当初她要讨厌鸡,说不定鸡就不好好下蛋,她要嫌弃狗,说不定狗早离家出走了。
叶荞麦又想起鹿儿岭上那半亩石头地,吉村没人愿在那里下功夫,石头缝里能长什么庄稼?而她却不这么认为,叶荞麦监督王得贵一镢头一镢头将地深挖三遍,冰草芦苇斩草除根,指拇蛋大点石头瓦子也要一一捡净,肥料呢,上足上饱。那块地果然没有辜负他们,粮食不比原地产得少。叶荞面知道,那样的地之所以能长出好庄稼,一是她想得好,二是付出得多;可这头母牛呢,一开始她就认为它不中用,而它果真就不争气。
叶荞麦认为是自己将牛想坏了,牛才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你不把人家当盘菜,就休要怪人家端不上桌。反思的结果是:叶荞麦觉得首先得改变自己的心态,再看牛能不能朝好的方向发展。
不争气的小母牛第二次回家后,王得贵两口子态度大变,他们发誓要把牛喂出个名堂来。王得贵在西山屲不太好的地里种上紫花苜蓿和禾草给牛当青草,叶荞麦隔段日子就趴在大铁锅里给牛炒料。尽管那时粮食短缺,人尚欠着肚子,但牛的精饲料不能欠下。每天拌草时,王得贵总是出神地望着小母牛,有时伸手摸摸牛头,有时拍拍牛身子,有时悄悄跟牛说说话。他最爱对牛说,牛儿牛儿快吃饱,黑了爷给你拌夜草。面对着牛,王得贵总在心里祈祷,牛儿你早些长得膘肥体壮,好歹给我长点脸吧,当然,最好能下个犊子,要不然,吉村人会把我笑话死的。
这样的时候,小母牛往往会停止反刍,两只耳朵轮番动一动,一双大眼睛静静地望着王得贵,好像知道他的心思一样。王得贵觉得这不光是牛的事,还关乎一个家庭的尊严,他家在人前因这头牛失掉的颜面,还得靠这头牛给赎回来。
王得贵两次换牛的事在吉村成为笑谈,一次以表弟媳上门大闹把牛换回去而结束,一次以叶荞麦学表弟媳的样子去对方家大闹换回自家的牛而告终,他家换牛的事后来成为经典,几十年经久不衰地流传在吉村。当年有:“刘拐子家的女子,王得贵家的牛”这样的说法,这话什么意思?刘拐子家的傻女子嫁了三回,退回来了三回,王得贵家的母牛换了两次,还是在王得贵家。
王得贵心里憋着一口气,不把牛喂好,誓不罢休。天冷后他在牛圈里盘了火炕住进去。马无夜草不肥,牛也一样,王得贵一夜几次起来给小母牛添草,额外增加精料。此后十余年时间里,王得贵一直住在牛圈里,直到家里不再养牛。
眼看一年将尽,小母牛依然没有多大起色。吉村喂牲口有经验的老人说,牛毛色杂乱不亮,嘴刁不长膘,是肚子里有虫。王得贵便拉了牛,三番五次去找兽医。吃过大把打虫的西药片子,被三两个人摁住头,强行灌进好多汤药后,小母牛慢慢变得肯吃肯喝起来。
季节更替,不知不觉中,瘦牛脱胎换骨,新毛如同枣红锦缎。它长大了许多,也变壮实了,看人的眼神不再躲闪,连叫声都浑厚了。
小母牛是比先前长得健壮了,但雀儿长不了鸡大,咋说它还是个小号牲口,王得贵只好认为就是这么个品种。如此,耕田种地还是成问题。一头大犍牛能拉独犁下地干活,小母牛这样的牛得一犋才行。可很少有人愿意跟王得贵家合牲口。张百忍把瘸腿老牛倒换了后,全村就数刘拐子和王得贵两家牲口弱,刘拐子倒是很愿意同王得贵家合牲口,可他家那头瞎犟驴又踢又咬,死活不肯跟小母牛合作,也只好作罢。
可养牛不是为了看,牛天生就要下地干活,这是它的使命。农忙时节,即使找不到合牲口的人家,小母牛也得下地干活。叶荞麦是刀子嘴豆腐心,骂得比谁都厉害,却比谁都更心疼牛。犁地时,需要一个人充当另一头牛,娃娃们身子嫩,怕伤了筋骨,王得贵要扶犁,背麻绳的就只能是叶荞麦。叶荞麦和牛并排走在一起,弓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犁沟里。
大凡牲口,都有些脾气。马刚烈,驴奸滑,牛野蛮。红鬃烈马一撮毛,挨了鞭子可以拉着犁铧任性地狂奔出几十里,它在向人示威,高贵的牲口是不甘心被奴役鞭打的;像堵厚实的墙一样的大犍牛,犯了疯病可以将驱使它的主人一头打落河中,表现得牛气冲天;而一头身单力薄、被主人嫌弃的小母牛,是没有资格耍脾气的,它只能温顺踏实地去干活,将扛起扛不起的活都硬扛上干,而且得将活干的有模有样才行。
这样子使叶荞麦不免就想起第二次用小母牛换回来的黄牛犊,好吃好喝喂养了一段日子后到了秋播时节,王得贵把黄牛犊套到犁上耕种时,才发现这牛像没调教过一样,不认犁沟,拉着犁满地乱跑不说,稍不留神还会偷吃麦种。王得贵想给牛点教训,一鞭子打过去,黄牛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里,吓得王得贵不轻,叶荞麦直埋怨他下手重,把牛打疼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这头牛只要你让它干活,只要你吆喝一声,鞭子响一下,它立即就会趴到犁沟壕里,任你抬头提尾怎么也弄不起来,就像睡地上耍赖皮的人。这样的牛王得贵从未见过,更是闻所未闻,赶紧请教吉村有经验的老人。老人们说,瞎了!瞎的瞎瞎的了!这是“奸牛”,几千头牲口里面都出不了一头,就像人里头的瞎瞎人一样,游手好闲啥事没有,干点活就要出人命。这时候,王得贵两口子才知道上当受骗了,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不能干活的牛要它做什么?总不能当神一样供起来吧?王得贵两口子当即决定换回自己的牛。寻到那家才知道,事情远比他们想的更麻烦。见好话说尽不管用,叶荞麦急了,说你们个大骗子,把干不成活的“奸牛”换给我们。那女人冷笑着说,恐怕你们是“奸人”吧?要不好好的牛,到你家咋就变成“奸牛”了?叶荞麦说,自己的东西自己清楚,我要把我家的牛牵回去。那男人说,那你们就是牲口。
尽管王得贵两口子一点都不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事情还是发展到了拳脚相见的地步。很快,四个人衣撕破,脸抠烂,头上起了大肿包。好在让邻居给扒拉开了。那次的事费尽了周折,叶荞麦把自己的厉害发挥到极致,外加学习表弟媳那一套,再加上以死相逼,总算把自己的牛弄回来了。其实叶荞麦最痛恨出尔反尔的人,不想自己也成了那样,可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六
地还是要自己种,这话一点不假,分产到户头一年,粮食欠收的局面迅速发生了扭转。接下来的几年风调雨顺,粮食连年大丰收。王得贵家那几年好事不断,猪产仔,鸡抱窝,牛寻犊。小母牛怀孕后,王得贵心疼它,去地里干活,手里的鞭子多是在空中虚张声势地啪啪乱甩,犁铧吃土也比原先浅了好些。叶荞麦则天天给牛加精料,喝糊汤。
母为子贵,一头枣红牛犊的出生,使这头母牛在王得贵家终于有了地位,没有人再敢轻看它。别看母牛身形瘦小,生出的牛犊却俊秀体健。王得贵说,这就叫瞎马下好驹。牛犊在槽上精心喂养七八个月,鹑觚镇七月过交流会时牵出去卖掉,得到一笔钱。从此以后,这头小母牛像能生的女人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连续产下几头健壮的牛犊。而这些牛犊均是在精心喂养一段时间后,一个个被拉出去卖掉了。吉村人曾劝说王得贵留下其中一头,来分担或接替母牛的工作,原因是这头牛年岁渐长,再不倒换,恐怕有一天会老死在王得贵手上。
王得贵不听劝,贪心的他怎能丢手这棵摇钱树?按说母牛生了那么多牛犊,确实该有一头留下来,替它分担地里的活计,可窘迫的日子总是寅吃卯粮,鸡屁股里往外掏蛋,牛犊一个也没留下。
小母牛到王得贵家十三年,前后产犊八头。牛犊换来的钱,为家里盖了大瓦房,给大儿子娶了媳妇,供女子上完了中专,供小儿子读到了高中。这让吉村人羡慕又嫉妒,感叹王得贵家的牛可真能生,真是牛也不可貌相啊!
这年七月,鹑觚镇过物资交流会,王得贵准备把一头八个月大的牛犊牵到牛市上卖掉。这是母牛到家后产下的第八胎。王得贵去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寻找早上打出去放牧的牛母子。远远地,他意外地发现母牛垂头卧在草坡上,牛犊正试图用嘴将母亲拱起来,王得贵的心一下子蹦到嗓子眼上,拔腿就往牛跟前跑。
母牛就这样突然死了。在此之前这头牛干活已大不如从前,反应迟钝,步履蹒跚,王得贵知道它已经很老了,终究有一天会死掉。可这一天突然来临时,王得贵还是一下子懵了,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邻居们帮忙来抬牛,王得贵让抬到他家的一块自留地里。时间不大,来了好些帮忙宰牛的刀斧手。以前吉村每有牛老死,只要没什么大毛病,通常都是大家凑份子,宰了牛全村人吃肉。皮钱牛肉钱多少能弥补些损失,这是辛劳一生的牲口死后为主人所做的最后的贡献。
看到七八个刀斧手围着牛摩拳擦掌,王得贵突然咆哮起来,我家的牛不宰!谁说我家要宰牛?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莫名其妙,既然不宰,费这大劲抬个死货回来干啥?
王得贵要将母牛埋在他家的自留地里。王得贵的决定遭到前来宰牛的人的空前嘲笑,更遭到大儿子的强烈反对,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望着这块埋葬着太爷太奶爷爷奶奶好几位亲人的风水地,大儿子口气强硬地说,埋哪儿不行,为啥偏要在这儿?这是埋先人的地方。
王得贵说,就埋个牛,影响先人啥事了?大儿子态度恶劣地看着王得贵说,人跟牲口能埋一起吗?你不知道人骂人的那句话吗?王得贵问,什么话?大儿子说,“你先人坟里把四条腿埋下了吗?”大儿子又说,你不怕人笑话,不怕影响咱家脉气吗?王得贵说,谁爱笑话慢慢笑话去。脉气这东西,有就有,没有跟皇上埋一起都没有。他接着说,咱个农民,吃喝哪样不靠牲口,活着天天在一起,死了怎么就不能埋一起?不要太相信那些臭讲究。王得贵蹲下身子抚摸着牛头继续说,埋这里,日后我死了也能见着它。宰牛的人只好散了,只好认为吉村出了神经病。
王得贵父子间那天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可争吵得再怎么厉害,都无法改变王得贵的决定,只好任由他胡整——把母牛埋在风水地里。先人们枕着田埂依次安眠在地头,老牛安睡在地脚,人畜算是分开了。风水地里埋四条腿的事让王得贵在吉村的威信一落千丈,大家伙从此对他带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不将他当正常人对待了。大儿子为此好些年来内心充满担忧,并对王得贵一直存有深重的偏见,直至王得贵的孙子里出了两研两博,这种偏见才慢慢消散。
母牛突然死去让王得贵黯然神伤了好些日子,十几年的共同劳作,牛早已成了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即使过了许久,一家人依然无法释怀。后来的好多年,每到田间地头干活时,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说起小母牛,回忆牛活着时的点点滴滴,细数牛的种种好处。养牛的经历教给王得贵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干什么都得全心全意,用心了,麻袋都能做成绣花衣。
王得贵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牛是这世上最不能辜负的大牲口,虽然不能开口讲一句话,但同人一样有情有义,懂得知恩图报,你敬它一尺,它会敬你一丈。
七
多年后,王得贵因为衰老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再到田间地头去干活了。但每年春种秋收,他依然会戴起挂在檐下的旧草帽,拄着棍子颤颤巍巍走出去。他长时间呆呆地望着田野里的庄稼和挥汗劳作的人们。王得贵远离的不光是热火朝天的劳动,还有世界的喧嚣。不管地里的人怎么使劲跟他喊话,他都没有回应。王得贵耳朵聋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总是深陷回忆,自言自语,说着庄稼;说着从前的人和事;说着死去多年的老牛。王得贵觉得人和牛的命运是一样的,汗尽力竭就没什么用了,离死就不远了,这令王得贵伤感,总有泪水从他昏花的老眼里流出来。
一直到王得贵老得下不了床,整日只知道昏睡时,偶尔清醒,他还会说到牛。他说牛槽里没草了,说该饮牛了!到去世王得贵都不能停止对那头母牛的回忆。没有几个人能理解他,不就是头牲口嘛!何至于此。可王得贵觉得牛实在太可怜了,好像前世欠他们王家什么债似的,作为一头母牛,它无疑是最出色的,但却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优待。它的另一重身份是头耕牛,十多年时间,母牛总是扛着大肚子,却总是在田间地头耕作。
王得贵家后来还养过好几头大牲口,但在他心里,没有哪个能同这头牛相提并论。如果要给他家牲口写功劳簿,这头母牛当之无愧应位列第一。
王得贵去世前说过,细细思量他这辈子是个有福的,一是他娶到了叶荞麦这样攒劲的女人,二是包产到户那年,他分到了一头攒劲的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