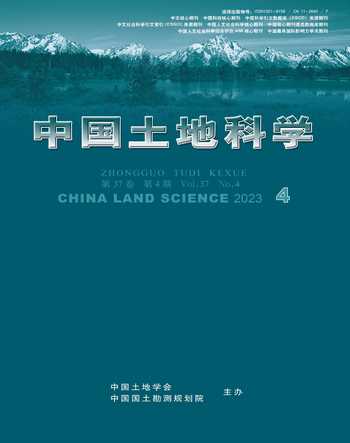耕地发展权制度构建研究
刘锐 房昀玮
摘要:研究目的:探求与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管制相适应的耕地权利人市场化补偿机制,为耕地保护法建立公平、长效耕地补偿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耕地保护责任承担出现了错位,并且随着耕地用途管制的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财政补偿明显不足。立法上应当建立以耕地发展权为基础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耕地发展权是耕地非农建设和非粮种植的权利,属新型用益物权,由耕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享有。应建立耕地发展权银行,推动耕地发展权转移,发展权受让人不仅要支付新增指标(限额)交易的费用,还应支付以所在地区指标(限额)交易价格为标准的费用,用以补偿既有耕地权利人。研究结論: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严格用途管制,是对耕地权利人耕地发展权的限制,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建立与耕地用途严格管制相适应的耕地补偿制度,以保障地区公平发展,提高耕地保护积极性。
关键词:耕地保护;非农用化;非粮化;横向补偿;耕地发展权;耕地发展权银行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58(2023)04-0023-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研究”(20VHJ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严禁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2022年8月1日实施的《黑土地保护法》在严格限制黑土地非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黑土地非粮化予以限制。2022年9月自然资源部公开征求意见的《耕地保护法(草案)》,延续《黑土地保护法》限制黑土地非农化、非粮化思路,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应当重点用于粮食生产,禁止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等其他农用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严格管制,实质上是对耕地权利人权利空间的挤压行为,必然会影响到权利人的利益实现。
为了弥补严格用途管制给耕地权利人带来的损失,调动地方政府和耕地权利人保护耕地的积极性,《黑土地保护法》提出“建立健全黑土地保护财政投入保障制度”,《耕地保护法(草案)》也提出“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现实中承担耕地保护重任的重点区域一般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仅仅依靠财政投入和奖补机制无法对地方政府和耕地权利人形成耕地保护的稳定、有效激励。因此,有必要借鉴相关国家耕地保护的做法,建立与我国未来全面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相适应的耕地发展权制度,以保障耕地权利人的根本利益,切实落实耕地保护目标和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1 严格用途管制下我国耕地保护补偿问题
考察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既要考虑耕地空间分布的客观状况,也要以耕地权利人的权利保障为核心,分析制度的配给情况。
1.1 耕地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变化趋势
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建设,首先应当考虑耕地空间分布状况。在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要求趋紧的背景下,分析我国耕地分布的区域性特点及其变化趋势,有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空间分布格局随城市化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199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总面积(19.5亿亩)中,80%左右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20%左右分布在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4个区耕地占全国的71.7%,西南、西北两个区耕地仅占全国的28.3%[1]。然而,近20多年来,耕地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其空间变化特征可以概括为“西增东减,北增南减,山地增平地减”。耕地净增加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净减少的区域主要位于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2]。伴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这些地区的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大。根据欧航局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在空间分布上,1990—2015年中国建设用地新增区域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是建设用地扩张最明显的区域。尤其是华东地区,在2010—2015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117.92万hm2,是1990—1995年的10倍以上[2]。
耕地空间分布的上述变化,意味着耕地保护责任在逐步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区转移,而有效利益平衡机制的缺乏一定程度强化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尤其是建立跨省域乃至覆盖全国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非常必要和紧迫。
1.2 既有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耕地保护补偿的主要制度是2016年由财政部和原农业部下发的《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补贴通知》),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以及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此外,一些地方也出台了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如浙江省《关于全面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通知》、杭州市《关于全面建立杭州市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北京市海淀区《关于本区建立农田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等。
总体上,现行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及实践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制度层级低,尚未出台成熟的法律规定。二是补偿标准总体比较低,各地差别比较大。从全国来看,据统计,截至2021年9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覆盖2.2亿农户、近13亿亩承包地,亩均补贴约95元[3]。从地方来看,北京市海淀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为每年2 500元/亩,其他农用地补贴标准为每年1 500元/亩;浙江省余杭区一般耕地补偿标准为200元/亩,永久基本农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耕地均为400元/亩;而2022年甘肃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仅为48.43元/亩[4], 岷县更是低至13.28元/亩。三是受补偿主体不统一,难以保证补偿到位。《补贴通知》规定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但地方的做法并不统一。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补偿对象为承担耕地保护任务和责任的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并且补偿资金必须用于特定用途,农民个人得到的补偿微乎其微。
1.3 《黑土地保护法》和《耕地保护法(草案)》的不足
《黑土地保护法》和《耕地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两法”)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同时,也规定了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两法对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黑土地保护法》规定“国家加大对黑土地保护措施奖补资金的倾斜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奖励补助机制”;《耕地保护法(草案)》规定“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对符合特定要求的地区和集体经济组织、国有农场等给予奖补。这些概括性的补偿规定与具体化的用途管制制度不匹配,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供给不足。二是两法中的补偿对象仅为黑土地、特定地区的耕作主体,缺乏普遍性和公平性,无法形成可靠和持久的耕地保护激励。《黑土地保护法》调整的仅仅是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4省区内的优质耕地,《耕地保护法(草案)》也只规定对重点地区、耕地保护任务重且完成好的集体经济组织、国有农场等给予奖补。“奖补”的定位意味着其不可能是普惠制度,不是基于耕地权利人利益受损的普遍、稳定的补偿制度,这与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要求还有距离。三是单一的财政补偿无法保证补偿的充分、持续和高效。以国家财政支撑的耕地保护补偿,既无法做到补偿的充分,也很难实现补偿的持续稳定及为被补偿人提供可靠预期。实践已经表明,国家财政对耕地的补偿取决于财政收入和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变迁,基本的运行逻辑是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总之,既有的处于低位、尚未成型、不甚合理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无法保障耕地权利人的权益,不能为地方政府和耕地权利人提供保护耕地的有效激励。由《黑土地保护法》和正在制定的《耕地保护法》开启的严格的耕地用途管制,并未能跳出固有耕地保护补偿依靠政策、财政的局限,未能找到与严格用途管制相适应的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和稳定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完善,需要借鉴域外有益做法,建立以耕地发展权为核心的可靠、稳定、长效补偿与激励机制。
2 严格用途管制下耕地发展权制度建立之必要
2.1 耕地权利的限制与补偿
土地负有社会义务,这是各国法律的普遍规定。但任何义务都有限度,附加在土地权利上的社会义务也应当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超范围施加义务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且应该给予公平合理补偿。
在国家施行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规划控制之前,土地使用仅受实际需求和供给能力限制而不受法律限制,在此情形自然没有补偿的必要。随着土地权利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土地尤其是耕地用途管制和国家建设规划控制的推行,土地权利限制及其相应的补偿问题日渐暴露:经济欠发达地区及其耕地权利人,反而要承受国家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的重任,其不公平性显而易见。不仅如此,随着耕地保护新法对耕地非粮化的严格限制,其不公平性进一步凸显。《黑土地保护法》不仅限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而且明确规定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黑土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在种粮和种蔬菜、经济作物,以及经营果园等在收益方面存在剪刀差的背景下,对耕地的严格用途管制,事实上剥夺了耕地权利人获取更大收益的机会,这种机会在法律严格限制非粮化之前是法律明确赋予的,即《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现行法律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耕地上种植非粮作物或种树经营果园。如果不建立新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仅靠财政支撑的耕地补贴或许连耕地权利人因非粮化限制而受到的损失都无法弥补,更何况非农化限制的损失。非农化、非粮化已超出土地的一般社会义务负担,应当予以补偿。通过征收补偿方式政府财政无力负担,由国家财政负担的行政补偿、奖励无法实现充分补偿和权利限制与补偿的平衡。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限制,实质上限制的是耕地的发展权,应当通过构建耕地发展权制度予以解决。
2.2 比较法上的土地发展权
土地发展权(Land Development Right)概念来源于英美法。狭义的土地发展权是指“将一块土地的用途从收益较低的用途(农业)改变为收益较高的用途(城市住宅、商业或工业)的权利,其结果是土地的增值”[5],广义的土地发展权不仅包括改变土地用途的权利,而且包括提高土地利用密度的权利,强调“空间上纵深方向发展”(土地集约度提高)的土地再利用、再发展,是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6]。由此可知,土地发展权人不仅享有变更土地用途的使用权,而且享有通过利用土地而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
英美法最早确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土地发展权植根于英美的财产法,其构成土地所有权权利束中的一项权利,能够与所有权中的其他权利相分离而单独转让,而不影响土地所有权人对于剩余权利的行使。英美法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在运行模式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均源于耕地因城镇化大量流失背景下,运用市场机制限制土地用途管制权力和减轻征收补偿给财政带来压力的需要[7]。因政府行使警察权限制私权无需对土地权利人予以补偿,而土地征收则需要给予公平补偿,如果警察權的行使超过一定的界限,则构成征收需要补偿,二者之间的界限不甚明了。而且土地价值飘忽不定,难以准确预测,征收补偿可能会给政府带来不可估量的负担[8]。因此,通过土地发展权给予土地权利人以合理补偿成为协调土地分区管制和土地征收补偿的第三条道路。土地权利人发展权利受到限制的同时能够获得适当补偿,政府保护耕地、利用建设用地发展经济也不必付出高昂代价,土地权利人和政府的利益实现了平衡,能够有效激励二者保护耕地。美国除土地发展权收购以外,土地发展权转移(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TDR)是其富有特色的土地发展权制度。该制度通过划分发送区与接收区,将开发受限地区的土地发展权转移至适合更高密度发展的地区。其中,土地发展权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大陆法国家,意大利借鉴美国经验,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了国家土地用途管制与土地发展权转移相结合的土地发展权制度[9]。意大利现有两种土地发展权转移模式,一种为“发展权的本地性转移”(localized TDR),类似于我国补充耕地指标的省内转移制度,土地发展权在划定发送区和接收区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空间转移,参与转移的土地是有限的,且不存在市场交易,发送区的发展权移转后主要用于公共用地;另一种是“发展权的全域性转移”(generalized TDR),类似于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移项目,土地发展权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与美国不同的是,意大利未建立土地发展权银行,土地发展权登记制度又不健全,导致土地发展权往往通过以政府作为中间人的非正式方式开展交易[10]。
2.3 土地发展权对耕地保护及其补偿的意义
土地发展权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对农用地尤其是优质耕地侵吞背景下,为了保护农用地而采取的激励性措施。以美国新泽西州的松林地发展信贷项目(Pinelands Development Credit Program)为例,截至2022年6月,松林地区57 268英亩农地和生态脆弱土地通过这一项目实现了永久保护[11]。美国的土地发展权项目在农地保护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我国,如何顺应城镇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又能实现保护耕地的基本目标?如何保障耕地权利人的土地发展权益又能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加以解决。长期以来,我国为了保护耕地尤其是优质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指标,但实践中建设用地通过土地隐形市场不断扩张,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建设用地的利用得不到规范,摊大饼式的建设不仅影响发展的质量,而且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我国需要从粗放式的发展向集约型的发展转变,实现耕地保质保量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这一目标只靠公权力的管制是难以实现的,需要以市场机制推动的制度创新为先导。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直接惠及耕地保护义务主体,目前尚需建立市场补偿、横向补偿制度以对纵向补偿制度形成必要的补充,以平衡贡献区和受益区的利益,量化贡献区因耕地保护受到的损失并由受益区予以补偿,这对于调动贡献区耕地保护积极性、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尤为重要。通过土地发展权制度,能够协调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和农村耕地保护需要,优化空间利用格局;以土地发展权作为交易媒介,通过市场机制,平衡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的积极性,实现耕地保护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很有特色。一方面,土地实行公有制,土地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农用地一部分也交由集体发包农民使用,一部分由国有农场、牧场和林场等使用,后者又将部分土地以口粮田、身份田等名义承包租赁给职工等主体长期使用。因此,我国的农用地之上存在比较复杂的所有权、使用权关系。另一方面,不仅农用地受到用途管制,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使用也受到法律政策的严格限制,而且在农用地内部,耕地、林地和草地受到的管制程度并不相同,国家对耕地的管制最严。考虑到耕地相对于林地、草地而言因其所处位置的优越性更容易被建设所侵占,耕地也因质量良好、种粮收益低等原因更易被非粮种植,同时耕地保护对于耕地权利人基本保障乃至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不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发展权,仅仅探讨耕地发展权。
3 我国建立耕地发展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中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和土地权利的复杂性,以及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中国的耕地发展权一定是中国式的。而要构建中国式的耕地发展权,首先需要解决耕地发展权的内涵、性质界定及利益分配等基本问题。
3.1 耕地发展权的内涵
现阶段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耕地发展权,其内涵界定应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以英美法原初意义上的土地发展权为基础构建我国耕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的核心是因用途管制造成土地的农业使用和建设使用之间的价值悬殊及其平衡。我国的耕地发展权构建,也应当以此为基本遵循。
第二,耕地发展权的构建,还要考虑我国的耕地用途管制包括对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双管制。耕地的非农化使用属于土地开发权的范畴,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发展权也限于此。但在限制耕地非粮化的背景下,我国的耕地发展权还应包括耕地非粮利用的权利。
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经营权人等耕地使用权人,有对耕地非粮使用的权利。耕地的非粮化限制,主要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的限制。不仅如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等虽为用益物权,但由于我国实行长久不变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二轮承包30年期满后再延长30年,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多数是无偿划拨取得、无限期使用,部分国有耕地被无偿交由集体发包农民使用,这和传统大陆法系有期限限制的、定限物权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并不相同。而且,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实践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补偿。因此,我国耕地发展权的构建,应当考虑非粮化的特殊用途管制,以及部分耕地用益物权因长期化甚至无期限限制而接近所有权的特征。
3.2 耕地发展权的性质
关于土地发展权的权源及权利属性,理论上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土地发展权源于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权下的一项权能,后独立为一项权利,是一项民事权利,有学者更进一步论证土地发展权不仅是一项财产权,而且是一种物权类型[12-15];第二种观点认为土地发展权源于国家管制权这一公权力,土地发展增益主要源于外力,是全体社会大众努力的结果,具体地块的发展增益与国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非农用地供应政策、城市化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16-18];第三种观点认为土地发展权是土地私有产权和公权力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性质可以界定为一种社会权[19-21]。笔者认为,上述关于土地发展权性质的界定,主要还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土地制度的讨论,对我国土地制度及其实践的特殊情况考虑不多。因此,界定我国的耕地发展权,既要遵循各国土地制度的共性,也要顾及我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
在西方土地发展权语境下,可分离性是所有权的一项屬性[22],将土地所有权中的部分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分离出去,分离出来的数项权能集合为一项权利。土地发展权也基于此逻辑产生,土地所有权是土地发展权的母权,并不是因为规划或者国家管制权力,土地发展权才得以产生,而是因为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土地发展权才有必要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独立发挥其使用、收益的权能,才会发生农地价值和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市场价值相差甚巨的现象,土地发展权的市场价值才得以显现。
就我国特殊土地制度框架下的耕地发展权而言,不仅要认可土地所有权是耕地发展权的母权,也要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农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也是耕地发展权的权利来源。单一的所有权作为耕地发展权的权利来源并不符合中国土地权利制度及其运行实际,事实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耕地补偿应在耕地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分享的现实做法,更不利于未来耕地补偿利益的合理分配和精准到位。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上产生耕地发展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关于该权利的定性,后文详细阐述),也不违背一物一权原则,这如同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可以产生土地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在“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目标下,耕地发展权的构建不可能简单地将其权利赋予土地所有权人,而是要在所有权人和承包经营权人等使用权人之间合理分配。
耕地发展权是一项私权,属于新型的用益物权。耕地发展权符合物权的支配性特征,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特定性以及可公示性。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耕地发展权人可依自己的意思变更土地用途,而且,在同一地块或者空间范围内,只能存在一个耕地发展权,该地块或空间对应的耕地发展权可以予以登记公示[23-24]。耕地发展权作为用益物权,其产生方式与传统的用益物权类型有所不同,性质上构成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类型,耕地发展权人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不同于传统的用益物权。耕地发展权人虽然没有现实地、直接地占有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土地,也没有按照土地原有的用途利用土地,但是耕地发展权人通过将改变土地用途的权利转让给他人获得收益,受让人利用该权利可以改变接收区土地的用途,符合用益物权的制度设定。耕地发展权类似于采矿权、取水权等准物权,但耕地发展权无须通过行政许可而取得,只是其因受到公权力的限制无法得以行使。地役权具有的通过合同约定为自己不动产的利益在他人不动产之上设定负担的功能与耕地发展权明显不相符合。既有的用益物权类型无法全面反映土地发展权的属性和功能,因此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更为妥适。
3.3 耕地发展权的收益分配
耕地发展权的收益归谁是与权利性质争议紧密相关的问题。关于土地发展权的收益分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所有权的绝对性”,土地增值收益由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即土地所有权人获得第一次分配,国家通过税收进行第二次分配。我国国家土地所有和集体土地所有二元制下,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应当归集体所有,即“涨价归私”[23,25]。另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所有权受到限制的原则,土地增值收益应由国家支配,同时要对受到限制的土地所有权人进行公平、合理补偿。此观点反对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归集体所有,认同“涨价归公”[2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基于土地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性,土地增值收益应当由社会共享,即“涨价共享”[27]。
土地增值收益是耕地发展权行使的结果,这一收益由耕地发展权人享有是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前文已经将耕地发展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耕地发展权的收益应当根据耕地发展权的权源,并结合耕地征收补偿的实践等综合判断。考虑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等的实际权利人本享有非粮化使用耕地的权利,因此,在《黑土地保护法》及未来的《耕地保护法》严格限制非粮化之后,限制非粮化的补偿应当归土地使用权人。至于耕地非农化限制的发展权收益,应借鉴耕地被征收后补偿分配的实际做法予以综合判断。现行法律规定,征收耕地不仅要补偿所有权人,还要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等用益物权人。从实践来看,征收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并不统一,有的完全分配给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的在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地被征收的农户之间按比例分配,即使是按比例分配的,具体分配比例差别也比较大。因此,耕地发展权的收益应当在土地所有权人、不同类型的土地用益物权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即使是国有耕地,也要考虑农民等承包经营权人、土地经营权人以及国有农场及其职工等使用权人的利益,非农化的利益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分享,非粮化的利益应当赋予实际使用权人。
4 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构造
我国的耕地发展权是耕地所有权人及其耕地用益物权人使用耕地种植非粮作物或者使用耕地进行开发建设的权利。耕地发展权的权利人包括耕地所有权人及其耕地承包经营权人、耕地经营权人、国有耕地使用权人等。我国构建耕地发展权制度,一方面要以英美法的土地发展权制度为基础,另一方面应当汲取意大利借鉴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经验教训,吸收美国土地发展权银行的制度精髓,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耕地发展权的交易。
4.1 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
耕地发展权与耕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不同,在严格用途管制的情况下,该权利往往是一种期待权。如果国家不创造该权利的实现机制,耕地发展权或许根本无法实现。
从比较法上的土地发展权实现方式来看,主要有英国的土地发展权征收模式、美国的土地发展权收购模式和转移模式,以及意大利的土地发展权转移模式等。土地发展权转移的前提是划定发送区和接收区,发送区通常为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的地区,接收区为国土空间规划下开发需求旺盛的区域。
就我国耕地发展权的实现机制而言,由国家征收耕地发展权现阶段不具可行性,由国家收购耕地发展权虽不失为一种选项,但不能作为主要方式。比较可行的选择是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原因主要有:一是符合国家生态横向补偿的发展方向。建立横向补偿机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是典型的横向补偿。二是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我国近年来开展的土地整治和耕地指标交易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基于耕地后备资源主要集中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耕地后备资源面临接近枯竭的现实[2],未来耕地指标交易仍有巨大市场。三是推动耕地发展权大范围转移,有利于耕地发展权的充分实现和促进共同富裕。
不过,我国现有的耕地指标交易制度无法充分实现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普遍、公平补偿。一方面,通过土地整治、土地开垦新增耕地数量有限,通过指標交易受益的仅为个别地区、个别耕地权利人;另一方面,补充耕地指标交易主体为地方政府,多数指标交易收益可能归于地方政府。构建我国的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不能限于现有占补平衡制度下对应的补充耕地指标转移,即建设开发需求旺盛的地区占用更多耕地需要从发送区购买补充耕地指标,还要兼顾非新增耕地的耕地权利人的发展权补偿。同时,在《黑土地保护法》及未来的《耕地保护法》限制耕地非粮化的背景下,我国也应当建立耕地非粮化权利转移制度,实现耕地种粮面积的动态平衡。
基于以上讨论,我国耕地发展权的转移要立足于耕地非农占补平衡、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制度以及耕地非粮使用进出平衡的实践,探索耕地发展权的实现机制。考虑到新增耕地指标、新增耕地非粮使用限额受让人占用耕地进行开发建设或非粮使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又享受既有耕地提供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指标受让人以发送区的新增耕地指标和新增耕地种粮限额价格购入并不足以平衡指标(限额)所在地耕地权利人的利益,因此,指标(限额)受让人在购买新增耕地指标或耕地非粮限额时,还应当购买受让人所在市县同等数量耕地对应的发展权,以弥补耕地权利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的成本(这部分的成本本应由指标(限额)受让人承受,但是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却由出让人承担)以及耕地权利人潜在的利益损失。对于购买此部分发展权的费用,指标(限额)受让人应向耕地发展权银行缴纳,以补偿广大耕地权利人。
4.2 耕地发展权银行
在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中,土地发展权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银行由政府管理,可以设定土地发展权的最低购买价格,可以接受土地发展权作为抵押,亦可直接购买土地发展权,其可作为土地发展权的买方和卖方以填补市场主体买入和卖出的时间差,可以作为交易所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信息,以促成交易等[28]。
我国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建设,一方面应当鼓励地方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直接开展耕地发展权交易,类似于目前的耕地指标交易。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也可以推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耕地发展权银行,该银行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管。国家耕地发展权银行通过网上统一平台,集中耕地发展权交易信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促成交易,同时也可以直接买入和卖出耕地发展权。另外,国家应当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耕地保护成本等对各地耕地发展权交易的起始价格予以规定。
此外,通过占补平衡转移补充耕地指标和通过进出平衡转移耕地非粮化限额无法实现对全部耕地权利人的有效补偿。因此,耕地发展权受让人应按上文所述向耕地发展权银行缴纳指标(限额)受让人所在市县同等数量耕地发展权的费用。
至于耕地发展权交易收益的分配,非农化的耕地发展权交易收益由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用益物权人区分用途管制类别及程度不同进行第一次分配,地方政府通过税收进行第二次分配,非粮化的耕地发展权的交易收益归土地用益物权人。通过耕地发展权银行进行转移的,交易所得由银行转入补充耕地指标或耕地非粮利用限额交易出让人的账户(通常为地方政府),然后由地方政府按照前述原则向该地的耕地权利人分配。
4.3 耕地发展权转移配套制度
耕地发展权的转移需要配套制度支撑。首先,耕地发展权交易的前提是对耕地发展权的科学评估。由于各地耕地质量和产能差别比较大,国家需要研制耕地发展权价格的评估规程,以实现对不同地域、不同等级耕地发展权价格的评估。其次,建立耕地发展权登记制度和监测系统,对耕地发展权及其流转情况进行登记,对已出让耕地发展权的耕地进行定期监测并适时纳入永久基本农田予以保护。再次,建立耕地发展权转移与土地征收补偿之间的衔接制度。耕地非农使用指标交易后,耕地权利人不再享有耕地非农使用发展权;耕地非粮限额交易后,耕地使用权人不再享有非粮种植发展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时,补偿的标准中不应再含有耕地发展权的补偿。
5 结语
制定《耕地保護法》的主要使命是严格保护耕地,遏制耕地非农化,限制耕地非粮化,确保耕地主要用于种粮。然而,实现这一目标,不能只强调严管,简单一禁了之、一限了之,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限权的同时赋权,通过权利平衡、权利有序流转,保障耕地权利人的根本利益,形成耕地保护的稳定激励机制,调动耕地权利人和地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基于此,本文建议正在制定的《耕地保护法》要明确规定耕地发展权类型,并对耕地发展权运行的基本制度予以规定。耕地发展权分为非农化耕地发展权和非粮化耕地发展权,在国家土地用途管制范围内,耕地权利人可以通过国家耕地发展权银行转移耕地发展权并享有相应的出让收益,出让后耕地权利人必须严守耕地用途。同时通过指标(限额)交易获得耕地发展权并占用接收区耕地进行建设开发或非粮种植的主体,还应按照所占用耕地对应数量的耕地发展权价格向耕地发展权银行缴纳相应费用,以实现对其他承担较重耕地保护责任的耕地权利人持续、公平的补偿。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李元.中国土地资源[M]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141.
[2] 张凤荣,张天柱,李超,等.中国耕地[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21:81,96,135.
[3] 张曦文.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取得显著成效[N] .中国财经报,2021 - 09 - 16(8).
[4] 2022年宁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EB/OL] .(2022 - 05 - 19)[2022 - 11 - 20] . http://www.ningxian. gov.cn/zwgk/fdzdgknr/jczwgk/snbt/content_18775.
[5] MONSON D, MONSON A.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British planning law[J] . Ill. L. Rev., 1949, 44(6): 779 - 804.
[6] 王霞萍,赵谦.土地发展权三十年:功能进路与实践面向[J] .中国土地科学,2019,33(6):37 - 43,52.
[7] CARMICHAEL D M.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as a basis for land use control[J] . Fla. St. U. L. Rev., 1974, 2(1): 35 - 107.
[8] UTHWATT COMMITTEE. Expert Committee on Compensation and Betterment: Final Report[R] . London: H. M. S. O, 1942: 14.
[9] MICELLI E. Development rights markets to manage urban plans in Italy[J] . Urban Studies, 2002, 39(1): 141 - 154.
[10] FALCO E, CHIODELLI F. Th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in the mids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potential, innovation and limits in Italy[J] . Land Use Policy, 2018, 72: 381 - 388.
[11] STATE OF NEW JERSEY PINELANDS COMMISSION. Pinelands Development Credit Program[EB/OL] . (2022 -06 - 30)[2022 - 11 - 20] . https://www.nj.gov/pinelands/ landuse/perm/pdc/.
[12] 程雪阳.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J] .法学研究,2014,36(5):76 - 97.
[13] 姚昭杰,刘国臻.我国土地权利法律制度发展趋向研究——以土地发展权为例[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134 - 150.
[14] 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J] .河北法学,2002(2):143 -146.
[15] 方涧,沈开举.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属性与本土化权利构造[J] .学习与实践,2019(1):57 - 65.
[16] 陈柏峰.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J] .法学研究,2012,34(4):99 - 114.
[17] 孙弘.中国土地发展权研究:土地开发与资源保护的新视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9.
[18] 崔文星.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法理基础[J] .政治与法律,2021(4):122 - 134.
[19] 张先贵.中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37(1):154 - 168.
[20] 陶源.二元公有制下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37(4):101 - 110.
[21] 张先贵.中国法语境下土地开发权理论之展开[J] .东方法学,2015(6):18 - 28.
[22] [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M] . 张双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2.
[23] 孙建伟.土地开发权应定性为新型用益物权[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22(6):137 - 150.
[24] 王育红,刘文海.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性质[J] .河北法学,2017,35(4):134 - 140.
[25] 魏来,黄祥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实践进程与前景展望——以土地发展权为肯綮[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9(4):34 - 42.
[26] 彭錞.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国问题与英国经验[J] .中外法学,2016,28(6):1536 - 1553.
[27] 张伟.比较视野下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J] .法律适用,2022(4):159 - 166.
[28] STENVENSON S J. Banking on TDRS: the governments role as banker of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J] . N.Y.U.L. Rev., 1998, 73(4): 1329 - 1376.
Study 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LIU Rui, FANG Yunwei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Legal Educatio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explore a market-orien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cultivated land right holders consistent with the strict use control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o establish a fair and long-term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unde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aw.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ormativ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u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bear increasingly heavy responsibility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he current financial compensation driven fails to provide a legitimate basis for the stricter cultivated land use control unde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aw. The cultivated land compens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legisl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the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system in the form of usufructuary right, which covers the right to use the cultivated land for non-grain-growing or for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The first step is to entitle the right holders to the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and then, the development right transfer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can be set up through the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bank. The income of the transfer should be reasonably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land owner and the land usufructuary owners. In conclusion, strict use control of non-agriculture and nongrain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trains land development right. Therefore,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should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transfer to align with the strict use control system, to ensure equal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ctive ac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non-agriculture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non-grain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horizontal compensation;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bank
(本文責编:陈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