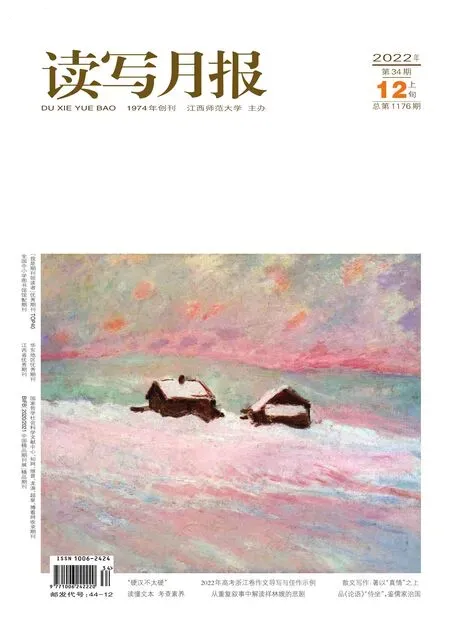因“无我”以致“坏我”的祥林嫂
——《祝福》文本解读
张红英

一、这一生:“无我”中“被奴化”的“我”
纵观祥林嫂短暂的一生,她始终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恰是“无我”中“被奴化”的“我”。
祥林嫂是谁?是一个叫祥林的人的妻子,她连名字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名字?她嫁给了谁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被称为“某嫂”。这是典型的“无我”,一个人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可见她的卑微低贱。无形却顽固的封建思想让她没有了姓没有了名,这也恰是她“被奴化”的渊源。
初到鲁镇:
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
“顺着眼”是顺从的样子,文中写到祥林嫂初到鲁镇“年纪大约二十六七”。放在现代,这个年龄的女性,往往很活泼、开朗、率性,但祥林嫂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却是“顺着眼”,这应当是长期受到一些无形的规则、规矩的限制所致。可以想见,她在夫家,有严厉的、精明能干的婆婆。从后面她被迫再嫁来看,婆婆很强势,绝对权威,她在夫家没有地位,受夫家人的压制,甚至是折磨虐待。从后文卫老婆子的解释“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婆婆的呢”,可以知道她来打短工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低眉顺目的祥林嫂连姓名都没有,在夫家是一个“被奴化”的“我”。
1.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
2.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在四叔家做工她不惜力气,不论食物,整天的做……几个人的活,她一人担当。她没有嫌苦喊累,默默地承受着繁重劳动,“无我”中“被奴化”的“我”更明显。这种“奴化”是“无我”的她求之不得的,甚至是主动争得的。日夜的辛苦劳作她反倒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些细微的变化证实了她在四叔家“暂时做稳了奴隶”,即便没有人格,至少有了“奴格”。
再到鲁镇,是她再嫁后又遭遇了夫死子亡,大伯来收屋,她被赶出,走投无路又来到了这里。再来四婶家,祥林嫂“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驯熟”指熟练、纯熟,可见她对做工的顺从和安然。这样一个无亲无家无处安放躯体的可怜人,在暂时享受了一段没有婆婆、夫强子乖的人生高光岁月后,回到了原形,回到了那个“被奴化”的“无我”中。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先前她包揽的准备祭祀福礼的活被彻底剥夺,并被贴上了败坏风俗的标签。此时,“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可见,她的改嫁是违背伦理的,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她始终是祥林的一个“未亡人”,而不是“老六嫂”。这样活着,真的是“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人可以在忙碌的劳作中忘却痛苦的经历,然而祥林嫂仅剩的辛苦劳作的资格都被无情地剥夺了,留存给她的是百无聊赖,对痛苦往事一次次痛苦的咀嚼,愁肠百转,肝肠寸断。“被奴化”的“我”走进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困顿之中。
精神的折磨让祥林嫂最终崩溃,她终于在柳妈的点醒下拿出做工所得的全部积蓄捐了门槛。然而“分外有神”的眼光却在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中瞬间变得黯淡至极,从此她精神颓萎,胆怯、惴惴、呆滞……行尸走肉般。“被奴化”的祥林嫂终究成了鲁镇上的乞丐,在祝福的爆竹声中结束了她“奴化”的“无我”寂寥的一生。
二、这一人:“无我”中“被异化”的“我”
环观她周围的人,祥林嫂又恰是“无我”中“被异化”的“我”。
鲁镇上“被奴化”的远不止祥林嫂一个人。同样在四婶家做工的柳妈、短工,还有鲁镇上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被“奴化”了。同一类人理应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然而他们对祥林嫂并没有同情,甚至冷漠。他们跟祥林嫂一样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并不认为祥林嫂是他们的同类,而是视其为“被异化”了的“异类”。祥林嫂到底怎么跟他们不一样?文中并没有具体写出来,但是从他们对她的态度中可以深味这种“异化”的悲凉。
先看同样在四叔家做工的“善女人”柳妈。
1.“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
2.“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
3.“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当祥林嫂自责于“阿毛被狼吃了”的无尽痛苦中时,她报以的不是同情而是厌烦,甚至有点嫌弃,责问“祥林嫂,你又来了”。这还不算什么,更让祥林嫂自愧于罪孽深重的是:柳妈认为她再嫁是最不该的,甚至她当时“索性撞一个死”也比现在活着强。最让她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在活的世界她已经无可挽回,而在死的世界中,柳妈告诉她还要遭受无尽的折磨。柳妈始终没把祥林嫂看作是跟她一样的底层劳苦妇女,而是把她看成一个不守贞节的女人,甚至到阴司还会受到惩罚。当别人不断在她耳边说“你嫁两个丈夫,罪孽深重”,说得多了,原本对此一无所知的祥林嫂就更觉得自己有“罪孽”,这在心理学中叫“外部信息强力投射”,渗透力量强大,以至于她本人也深信自己是一个“异类”。这种“异类”的外部信息不断投射,足以击垮人的精神堡垒。
她是一个“异类”。而这个不杀生的善女人自然觉得自己比祥林嫂“高贵”不少。而跟祥林嫂一样打工的短工又是怎样看的呢?
1.“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2.“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
短工本是跟她一样“被奴化”的同类,然而对于祥林嫂的死,短工的回答却是如此的淡然——“还不是穷死的?”难道他不是因为贫穷才到富人家里做工的吗?所不同的是祥林嫂“想做奴隶而不得”,而他是“暂时做稳了奴隶”,所以他认为祥林嫂不是自己的同类,是“异类”。所以他自然以一种鄙夷的眼光审视那个在祝福声中寂然死去的祥林嫂。
如果只是柳妈和短工把她当作“异类”,或许她还有生的希望。更可怕的是,在鲁镇人眼里,她也是“异类”。
1.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2.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应该包括那些无恶意的“看客”。当鲁镇上的人们来寻祥林嫂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的时候,祥林嫂已然是一个“异类”了,大家咀嚼鉴赏“阿毛的故事”,却从未把祥林嫂当作一个正常的“母亲”看待,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凉薄让人脊背发凉。
三、这一魂:“无我”中“被厌弃”的“我”
微观善恶人心,她恰是“无我”中“被厌弃”的“我”。
当“个体”不被“集体”接纳,就容易被“厌弃”,集体的力量不断地强调你是“异类”,最终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异类”,以致自己也厌弃自己。祥林嫂从四叔家出来后沦为了乞丐,是一种彻底的“无我”状态,在人性凉薄的鲁镇,她“被厌弃”了。
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空的”,没有乞讨到任何东西。鲁镇的人把她“遗弃”了,已经不在意她的死活了,连施舍也不愿给了,她被彻底“厌弃”了。具体表现在代表不同阶层的人对她的“厌弃”,一个是鲁四老爷的“厌弃”,鲁四老爷的一句“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谬种”一词,充斥着鄙夷、无视、厌弃,没有一丝的怜悯、同情。作为底层百姓短工淡然的一句“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淡然”“穷死”可见短工的漠然和冷淡。
不仅鲁镇的人厌弃她,连祥林嫂都“厌弃”自己了。
1.“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2.“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3.“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从提问可知,她似乎对生活于这个世界的自己“厌弃”了,寄予死后的灵魂和团圆的一丝希望。而“我”的“说不清”让她的自我厌弃更加彻底。终于,在这个充满“年味儿”的众神歆享“福礼”的祝福中,祥林嫂被彻底厌弃了,享受不到一丝的暖意和祝福。“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里,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死似乎是本就“无我”的祥林嫂最好的归宿,她被整个世界彻底“厌弃”了,“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为何整个世界都“厌弃”她,连她自己也“厌弃”自己?是因为她的内心不够强大,没有一个心性成熟的“自我”。她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彻底的“无我”,不能坚守自己的内心,她被婆婆卖了,竟依了;柳妈说阴司要锯开她,她信了;鲁四老爷让她沦为了乞丐,她认了……心理学上的伤痕实验表明,“别人总是以你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你的”。那个反复唠叨着“我真傻”的祥林嫂其实真的就没有觉悟到“我是我的”——这也是她与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爱姑最大的不同。
自始至终,祥林嫂都处于一种“坏我”之中,“被奴役”“被异化”“被厌弃”。在那个封建礼教思想浓厚、人性凉薄的社会,祥林嫂很难完成由“坏我”到“好我”的转变。一个“好我”要不丢失自我,并坚守自我,更要对当下的生命状态有一种觉醒。然而在那样的社会里,祥林嫂是断然做不到这一点的,由此更可见出人物及社会的悲剧性,更可见出这一典型形象在当代视域下的普适意义。
——以《祝福》中三处细节描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