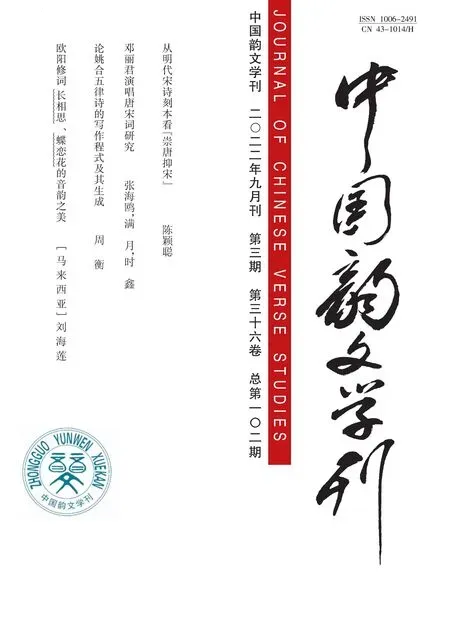速度与激情之歌:李贺古体诗转韵技巧与诗风生成
龙成松,张晖敏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3)
转韵(古人亦称“换韵”“转调”)手法早在诗骚中已广泛使用,古典文学批评家针对转韵的论述则可上溯至魏晋。《文心雕龙·章句》中说:“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虽然谈的是以赋体为主的韵文创作,但可见至迟在魏晋时期,便已有意将转韵作为文学技巧进行考察了。南朝时期,声律学说兴起,诗人愈发重视韵的应用,对转韵的探讨也进一步深化。这种探索在唐代并没有随着近体诗的形成而停止。和近体诗相比,转韵更为不可控和多变化。在应用情况上看,转韵与诗体的关联较为密切,在五言诗等文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相对较少,而七言诗,特别是七言歌行,以及拟古乐府中则出现频率更高。其次,关于转韵的应用和评价历来说法不统一,规范的缺乏使其更多地与文人个体的创作习惯相关联。因而从转韵手法出发,或可作为理解个体诗风的一个侧面。
在中唐诗人之中,李贺以“辞尚奇诡”闻名。前人从思想个性、语言艺术等角度论述过这种诗风的成因,似乎未注意到转韵对其奇诡诗风的影响。在其243首传世诗歌之中,古体诗有178首,占绝大多数,这为转韵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而在这些古体诗中存在明显转韵现象的又超过半数,有99首之多。李贺本身曾任协律郎,其诗作“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对于诗歌文本和音声的配合有着深刻的理解,更有自觉运用转韵手法以达到奇诡艺术效果的可能。因此李贺无疑是一个合适的考察对象。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李贺古体诗歌中的转韵现象进行了归纳整理,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些特点对于其诗歌风格生成的催化作用及影响。
一 李贺古体诗转韵的文本特征
(一)转韵基本概念的界定
由于历来各家对于转韵手法众说纷纭,在对李贺古体诗中的转韵现象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转韵的几个基本概念作出界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转韵的概念。《文镜秘府论·天卷》中所记载的“八种韵”便包括了“转韵”。这一段引李白《赠友人》为例,全诗前四句韵脚字“草”“老”押效摄下的上声晧韵,后六句韵脚字“枝”“池”“吹”“随”押止摄下的平声支韵。正是这一手法的典型案例,即在同一首诗歌之中,出现了以数句诗为单元的韵脚转换现象。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韵脚字和韵段的问题。律诗的韵脚字位置相对固定,多为偶数句句末押韵,古体诗之中限制则较少,首句是否入韵的规定不如律诗严格,诗中一叠数句,句句入韵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且在句数参差不齐的仿古乐府歌行之中,韵脚字时有落在奇数句句末的。为使对于转韵现象的描述更为明确,本文首先以偶数句作为韵脚字考察对象,对于句数不规则的文本,则结合句读及内容判断。而以两处明显发生转变的韵脚字之间的句子段落为一个韵段。韵段之中以两句韵段较为特殊,大部分两句韵段是伴随着连韵现象出现的,但也有个别存在不连韵的情况。此时依旧以句末字作为韵脚考察,因其存在了韵脚转换,不能计入前后的韵段之中,因此即使不连韵,也独立划为两句韵段。
在考察李贺诗歌的转韵现象时,有一些问题不能被忽视。以《广韵》为基准,李贺的用韵韵摄大致与《广韵》相符合,而在同一韵摄下不同小韵的同用独用,以及临韵是否通押的问题上则存在着许多出入,整体上较为宽泛,韵的选取更倾向于表现效果而非固定规范。因此在讨论其转韵手法时,为使重点更集中于其艺术特征,首先采用韵摄作为判断标准,而将同韵摄下四声小韵的同用作为补充,暂不计入转韵。此外,在不同韵摄的通押问题上,参照了前人的统计进行判断。中唐至晚唐诗中,梗摄下的陌、锡韵与曾摄下的职、德韵,臻摄下的元、阮、月韵与山摄下的先、仙韵,果摄下的歌、戈韵与假摄下的麻韵等等,存在大量并用现象,一般被认为是押韵的。因此在李贺诗中诸如此类的用例,虽韵摄存在变化,也不作为转韵现象处理。而用例仅见于李贺诗中,或相对个别的通押,则划为转韵。
在明确了以上问题的基础上,对于转韵现象外在特征的描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根据韵段中包含句子的数量,韵段的特征首先表现为长短的不同。在对转韵手法的认识之中,长短也是最易于被定量衡量的一部分。《文心雕龙》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特征:“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这一对转韵技法的认知正是围绕着韵段长短进行的。“两韵辄易”即以两句韵文的句末一字为韵脚,两句为一韵,两韵即四句。这种四句韵段在刘勰看来是“声韵微躁”的,与“百句不迁”的极端长韵段并举,可见刘勰认为四句韵段过分短促了,读来急迫。而参考与之同时的《南齐书·乐志》,其中也有着对于转韵间隔句数,即韵段长短的规定:“又寻汉世歌篇,多少无定,皆称事立文,并多八句,然后转韵。时有两三韵而转,其例甚寡。”可见八句四韵的韵段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属于长短适中。
至唐代,随着创作风气的变化和诗体的大丰富,这种相对的“长”“短”认知早已失去了限制作用。仅以盛唐时具有代表性的歌行一体而言,盛唐歌行相较于初唐四杰的长篇歌行,体量已显著缩小,表情达意更加灵活。八句一转已显冗长,四句韵段反而成了常例。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判断标准显然不适用了,此时四句韵段应被视为相对适中的,而更短的三句、两句韵段属于短韵段,四句以上则属于长韵段,一般出现于篇幅较长的诗中。
由此可以延伸出转韵现象的另一特征:同一诗篇内韵段的组合形式。一般而言,出现的韵段数量越多,则转韵的频率越高,其可能的组合形式也更复杂。与韵段在诗篇中的不同位置、平仄四声的安排、连韵和隔句韵的应用等问题相结合,则能够呈现出更加多样的表现效果。可以认为,在两个特征之中,韵段的长短更为直观,而韵段的组合则和诗人个人创作习惯、诗歌文本内容的生成具有更加紧密的关系。长短和组合构成了描述转韵手法特征的两个主要向度。
(二)李贺古体诗转韵基本规律
从韵段的长短特征上看,李贺存在转韵手法的99首古体诗中,共可划分出325个韵段。其中276个韵段为四句及四句以下的短韵段,两句韵段出现97次,四句韵段出现179次。而四句以上的长韵段在全部韵段中的比例较低。在长韵段中五句韵段共出现7次,六句韵段共出现13次,七句韵段共出现1次,八句韵段出现13次,十句韵段5次,十一、十二、十三句韵段各1次。整体上韵段的使用是更倾向于短韵的。而存在长韵段的诗中,32首为乐府歌行,出现的场合相对固定。韵段的组合方式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其一是同一诗篇内包含韵段的数量,其二是同一诗篇内包含韵段的种类。
李贺作诗,不拘长短均有转韵。在其存在转韵手法的诗中,句数最少的一首是五言四句的古体乐府《塘上行》,由两个两句韵段构成。而句数最多的杂言歌行《荣华乐》韵段也最复杂,共由10个长短不一的韵段组成。句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韵段的使用,一般而言,篇幅短小的诗歌容量较小,转韵的余地不大,而篇幅较长的诗歌则有容纳更多韵段的可能性。但这一影响并不绝对。在这些诗中,仅由两个韵段组成的诗共31首,多数为受篇幅所限的短诗。如《塘上行》《蝴蝶舞》本身仅有四句,至多只能分为两个两句韵段。而容量为八句的最多,稍多的也在十句左右。而余下68首诗中,32首包含了3个韵段,24首包含了4个韵段,4首包含5个韵段,6首包含6个韵段,包含7个韵段和10个韵段的各一首。包含韵段的数量越多,转韵越频繁。在篇幅限制的前提下,李贺同时考虑到了句式和韵律的影响因素,短诗求变,长诗多变,尽可能地增加了变动的元素,避免了表现效果上的“平铺直叙”。
这种变动还体现在韵段的种类上。如前所述,长短是韵段最直观的特征,不同长度的韵段构成了音韵上的长短句,因此同一首诗中出现的韵段种类越丰富,则音韵“句式”越丰富。在诗歌基本的谋篇布局之外,韵段与韵段之间由于不同组合方式生成的结构关系构成了第二重布局。99首诗中,由单一韵段组成的共39首,其中全诗仅包含两句韵段的有6首,仅包含三句韵段的1首,余下32首都仅由四句韵段组成,韵段匀齐,步调一致,相当于文本中的齐言诗句。且这些诗多为七言四句古体,是当时七言掷韵诗流行的痕迹。包含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长度韵段的则有60首,其中不乏精心安排的成分存在。在转韵本身的“变”之外,韵段的长短变化构成了第二重“变”。
短韵段的大量使用和转韵章法上的多变构成了李贺转韵手法最基本的外在特征。在此基础上,韵段本身的艺术特性,乃至韵段与诗体、韵段与文本内容的配合共同影响了李贺独特诗风的生成,是奇丽诡谲的辞藻和虚荒诞幻的意象之外的重要补充。而这些诗歌同样是探究转韵手法中所蕴含的艺术可能性的典型样本。
二 李贺古体诗转韵艺术特征
(一)韵段长短与“速度”的呈现
尽管是批评之语,但《文心雕龙》中的“声韵微躁”已经直接切中了韵段长短对转韵效果造成的作用。“躁”是挪用人品以评文,主要取其急迫之意。韵段越短,代表着韵的更替越快,韵脚倏忽一现而转为另一韵,观感促急。反之,韵段越长,同一韵脚在诗中持续的时间也越延长,读起来相对舒缓。速度的缓急变化是韵段长短这一直观特征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李贺诗惯用短韵,尤其常见的是四句、二句韵段。这些偏短、快的韵段为其诗歌添加了一层急促的节拍。
短韵中两句韵段的节拍最快,特点鲜明,应用的变化也最丰富。两句韵段的使用通常伴随着连韵,韵脚密集,变换迅速,如同跳跃的鼓点。两句短韵韵段的连缀更是一种具有古歌谣风味的笔法,李贺所使用的两句韵段,连用也是多于独用的。有23首诗中均出现了两组及以上的两句韵段连用。《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九月》《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十一月》《蝴蝶舞》《贵主征行乐》《染丝上春机》《塘上行》更全篇由两句韵段构成。促急的韵段变换与不同题材的文本结合,适宜于多种氛围的营造。
《美人梳头歌》与《染丝上春机》两首可以作为古歌流丽格调的代表,二者题材和风韵均相近,论者常将其并举,称其“婉丽精切,自成一家机轴”。《美人梳头歌》的短韵连用体现在起首八句上。“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押山摄寒韵。“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押通摄烛韵。“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押宕摄唐、阳韵。“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押止摄至韵。后八句则转为四句韵段,分别押曾摄职、德韵和假摄麻韵。前四组韵段的声调也经过了精心布设,由平声到入声,回到平声,再到去声收尾,声的切换中包含了静态到动态的两次转换。美人沉睡是静,惊起是动。立在镜前是静,长发滑落、玉钗坠地是动。促急的节奏四笔勾勒出画面,配合声调共同营造出了连贯而层次分明的动感。而韵段一转为四句,“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春风烂漫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细摹梳妆情态。“妆成婑鬌欹不斜,云裾数步踏雁沙。背人不语向何处,下阶自折樱桃花”又一笔宕开,写美人梳妆停当后之事。韵段稍有延长,承接在短韵之后,有舒缓语调之意。
《染丝上春机》则通篇均是两句韵段。短韵的使用更加轻盈灵动。“玉罂汲水桐花井,蒨丝沉水如云影”押梗摄静韵、梗韵,“美人懒态燕脂愁,春梭抛掷鸣高楼”押流摄尤韵、侯韵。“彩线结茸背复叠,白袷玉郎寄桃叶”押咸摄怗韵、叶韵。“为君挑鸾作腰绶,愿君处处宜春酒”押流摄有韵。从题材到笔法上仿古之意都显而易见,因而四个短韵用在这里是恰如其分了。流转而下,一气呵成。在每个韵段分隔出的两句诗中,又分别可以找到明显的动词成分。这一点和《美人梳头歌》相似。四个促急的韵段便恰好成了“汲水”“抛掷”“寄桃叶”“挑鸾”四个动态场景的定格,自然流转而不落痕迹。
除这二首典型外,在其他诗的短韵片段中也可以寻找到类似的韵味。如《残丝曲》起首四句“垂杨叶老莺哺儿,残丝欲断黄蜂归。绿鬓年少金钗客,缥粉壶中沉琥珀”分别押止摄支、微韵和梗摄陌韵;宫娃歌起首四句“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象口吹香毾覴暖,七星挂城闻漏板”分别押通摄东韵和山摄缓、潸韵;《江楼曲》起首四句“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晓钗催鬓语南风,抽帆归来一日功”分别押效摄晧韵和通摄东韵,虽内容各异,笔法却相似,两句韵脚一转,句中景、事、人随之一变,节奏干净流丽,颇具古风。
短韵连用的表现效果并不局限于此。如《吕将军歌》中间八句,“北方逆气污青天,剑龙夜叫将军闲。将军振袖挥剑锷,玉阙朱城有门阁。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铁骑请金枪,遥闻箙中花箭香”,转了四次韵脚,分别押山摄先韵、宕摄铎韵、假摄马韵、宕摄阳韵。所描绘的场景接在将军悲哭之后,两组写将军赋闲,两组写宦官当阵。急迫的韵脚更催出场景之荒谬,构成两幅有力的定格画面。《公莫舞歌》末尾四句同样如此,“铁枢铁楗重束关,大旗五丈撞双环。汉王今日须秦印,绝膑刳肠臣不论”分别押山摄删韵和臻摄震、魂韵。充斥着促急如鼓点的节奏感,又以去声连韵作为收束,铿锵有金石之声。而《浩歌》中间四句,“青毛骢马参差钱,娇春杨柳含缃烟”押山摄仙、先韵,“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押止摄支、脂韵。写游春饮酒的实景而不全着实笔,承接了起首四句虚处落笔的韵味,两个连韵叠下,节奏如纵马放歌般轻快,亦真亦幻之感更为强烈。
但两句韵段有限的容量,同样决定了它在文本中作用的局限性。单独出现的两句韵段因其独立性过强,而易有破碎阻滞之弊。李贺常用叠下的两句韵段来描摹人、事、景,但独用的两句韵段也并非孤例 。这些韵段通常出现在全诗首尾,且明显带有“论”的用意。与李贺诗常不能“少加于理”有关,这种作为起首和收束的点题之句,不仅不像一般的促起、促收那样“易于遒劲”,反而在促急的速度下变得更加含蓄难明了。
此处取《官街鼓》一例。该诗前八句均四句一韵:“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汉城黄柳映新帘,柏陵飞燕埋香骨。磓碎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皇听不得。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分别押臻摄术韵、没韵和曾摄德韵。由京城的朝暮之鼓延伸到人世变换。而末尾两句则打破了这一整齐的格式,“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独立而出一组两句韵,一笔由人间画到天上,鼓声与天界漏声相重合,由实有的鼓漏声虚化为时间线性流逝的符号。可见其中有为全诗作一提纲挈领的升华的想法存在,但篇幅有限,韵脚又促急,便难免有言犹未尽的断续感。
和两句韵段相比,其他长度的韵段自身特征便并不那么鲜明了。在李贺诗中,四句短韵的应用相对整齐合规。出现的四句韵段大多符合一、二、四句入韵的掷韵诗惯例,文意四句一转,笔法并不新奇,而胜在整体诗意的构建上。更长的韵段则因其容量的延长,而多被用来进行渲染、铺排的工作。相比叠下的两句韵,长韵段用在篇幅较长的古体诗中,则更具连韵而下的恢宏气势。这种对韵段自身特性的理解和着意安排,是转韵进入李贺诗风生成过程的前提。
(二)韵段位置与节奏的变化
在韵段的组合之中,长短韵段的缓急相配合,便构成了由短韵到长韵的加速和由长韵到短韵的减速两种基本变化。李贺全诗韵段单一、匀速前行的并不占多数。而在速度发生变化的60首诗中,细分下来,全诗由两种韵段构成,且只出现一次速度变化的有45首,其中加速和减速的各占一半。而出现多次加、减速变化且变化不规则的则有15首。整体上的变化情况较复杂。
同样是速度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又有缓急之分。尽管李贺的诗少有完全符合促起、促收规则的,但王力在《汉语诗律学》中对于这两种技法的界定,实际可以挪用来解释韵段组合中的加减速变化。从书中所引的例子看来,这一定义的隐含条件是全诗除“起头”“煞尾”外基本通篇一韵,且篇幅不能过短。因此其中包含的还是韵段长短的问题,只不过两句短韵和长韵段的对比将其极端化了。这也侧面说明了韵段的长短差距大,则更给人陡然转变的急促感。匀速转韵诗每一韵段长度都相等,衔接起来也便较为平缓。而衔接的韵段长短越悬殊,快和慢的转变也越突兀,加减速的观感越强烈,配合诗意,可以构成回转动荡的独特转折效果。
在句式匀齐的诗中,长短韵段的落差常常可以打破整齐的结构,在有限的文本中制造出清晰的层次感,加减速的变化又与文本整体的节奏相配合。如《李凭箜篌引》,这首十四句的七言歌行由4个韵段构成。前四句“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押流摄尤、侯韵。中间四句“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两句一韵,分别押效摄啸、笑韵和宕摄唐韵。末尾六句“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押遇摄麌、暮韵。
起首先点明其人其事,段中前三句又都是整齐的流摄尤韵,简单的铺排之后将“李凭中国弹箜篌”一句重点托出。紧接着两组两句韵段将速度一转加快,即刻将乐声推入高潮。“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香兰笑”“融冷光”“动紫皇”,一连串令人目眩的意象叠下,运用了通感笔法状音乐之精妙,本身便有亦真亦幻的流动闪烁感,韵段的加速又正与这一组纷繁的意象相呼应。乐声延续,后六句忽然连为一个完整的较长韵段。速度骤然放缓,依旧是赞美乐声,而自然和前两组促急的韵段划开界限。
在韵段的减速作用下,音乐带给人的直观感受进一步被虚化和延长,由摹其声貌逐渐过渡为评其技法之出神入化。长韵段中又包含了细微的变化,六句全押遇摄,在声调上,“处”“妪”是去声,“雨”“舞”是上声。《词概》中有“去声当高唱,上声当低唱”的说法,《四溟诗话》也认为去声是“扬”而上声是“抑”。四声之中上声和去声是一组具有对应关系的声调。这里上去声交错两次,声调抑扬有致。而结尾处以双去声收尾,声调上稍有加速而转为高扬。从小韵上看,“雨”“舞”的麌韵和“妪”“树”的遇韵又是一组小的回环,声调和小韵相互勾连,在六句韵段缓和的速度之中营造出了跌宕起伏的紧凑韵律,余音不绝如缕。
又如《长平箭头歌》前十句:“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白翎金竿雨中尽,直余三脊残狼牙。我寻平原乘两马,驿东石田蒿坞下。风长日短星萧萧,黑旗云湿悬空夜。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尽将羊炙。”押假摄麻、马、祃三韵,是一个极舒缓的长韵段。镜头由箭头的特写徐徐拉开,长韵留下了铺叙的空间,因此接下来的诗句带着情节渐次展开。极言独游古战场的满目萧索,鬼气森森升腾而来。而“虫栖雁病芦笋红,回风送客吹阴火”两句押通摄东韵和果摄果韵,连续的长韵在此截断,近似于一帧画面的闪回。“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南陌东城马上儿,劝我将金换簝竹。”四句押通摄屋韵,阴魂鬼火散后倏忽转为人间之事。韵段再次减速,从古战场离去的部分在韵的加速中被省略,而跳接到去后的见闻,此时韵段的加减速是和全诗内容高度同步的。
句式错落的杂言诗中,韵段对于速度的作用则常需要与句式结合来观察。《苦昼短》便是一例。这首杂言歌行通篇几乎全由短句构成:“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押流摄有、宥、厚三韵。“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押通摄钟、屋、烛三韵。“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押遇摄鱼韵。
长韵段适于铺排的特点被发挥了出来,配合短句,韵脚密集而富有压迫感。起首十句为紧追不舍的质问,中间十句则一转入声,带上了激愤之意。因此韵段虽长,沉缓的步调里却隐含着巨大的张力。结尾四句韵段突然一加速,短而快地慨叹了人世求长生者的荒谬不经。但句子也延长了。以两个七言句结尾,将这声叹息拉得悠长,气势反而不如前两组长韵。
三 李贺古体诗转韵手法的本质和效果
(一)从“妙才”与“中和”看李贺古体诗转韵艺术的本质
转韵手法并非李贺的独创,但李贺古体诗的转韵却具有诗学史上的典范意义,其特质可以从“妙才”与“中和”两个的角度辩证地观察。在《文心雕龙》中,刘勰首先肯定了转韵的艺术价值。但在对句数等细节做出规定时,却并未完全从技巧的层面出发。在刘勰看来,“妙才激扬”不如“折之中和”,这一论断已经离开了转韵本身,而将矛盾从文本转移到了作者的“才”上。进而引入了更为宽泛的“中和”概念。在文思畅达的情况下,频繁转韵并非不能出佳作。只是倘若不能应用得当,则为技巧所累,反而不如退而求其次,“庶保无咎”。
这一观点在转韵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之后关于转韵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出现了在“妙才”和“中和”间摇摆的痕迹。理论上要数明清两代较为详切。明人陆深指出:“但作长篇须要转折变化。转折在换韵,变化在押韵。若押韵不稳贴,便成薄弱。”押韵不恰当则破坏整首诗的效果,换韵同理。叶燮的《原诗》指出了转韵之难:“直叙则无生动波澜,如平芜一望;纵横则错乱无条贯,如一屋散钱;有意作起伏照应,仍失之板;无意信手出之,又苦无章法矣。此七古之难,难尤在转韵也。”明清学人于转韵,多以“古诗”为典范。顾炎武论“古诗用韵之法”:“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这种崇古的态度和《姜斋诗话》近似,《姜斋诗话》在批评后人“蠹虫相续”强作转韵之诗的同时,也称赞了古诗转韵的“不待钩锁,自然蝉联不绝”。《说诗晬语》中则认为:“转韵初无定式,或二语一转,或四语一转,或连韵几转,或一韵叠下几语……此亦天机自到,人工不能勉强。”
对上古转韵诗的推崇最后都殊途同归地落到了“自然”上,那么古诗代表的理想范式,便应当是一种转韵与诗意高度契合、宛若天成的转韵笔法。刻意模拟,为转韵而转韵,则如东施效颦,不得其法。这种模糊了“定式”而主张自然而为的观点,正是对“妙才”之转韵的肯定。《白雨斋词话》中又有“盖转韵太多,真气必减”的说法,实际是正话反说,以称赞《梅花引》一词虽然频繁转韵,却“层层入妙,如转丸珠。又如七宝楼台,不容拆碎”。可见论家虽对转韵手法的应用颇有微词,却殊途同归,并未在根本上否定这一手法的艺术表现力。为确有“妙才”的诗作留下了转圜的余地。这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正反映了在繁杂多变、相对不可控的转韵手法面前,论家是倾向于固守“中和”之阵地的。
唐代转韵诗作众多,但对于转韵手法的独立论述却相对贫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文镜秘府论·南卷》中《论文意》节引王昌龄的观点:“诗不得一向把,须纵横而作。不得转韵,转韵即无力。”这一观点属于相对负面的评价。《论文意》前半部分出自王昌龄之手,其中论及声律的有“意高则格高,声辨而律清”和“夫诗格律,须如金石之声”两处,所崇尚的是自然简洁的轻健之美,与唐人对于风骨的追求一致。而批判转韵“无力”当指为追求技巧繁复,刻意变转,破坏了诗歌的连贯性,进而有损风骨气韵。这同样是过犹不及的观念。与之相应地,这时相对主流的转韵手法成了七言掷韵诗,本应与七言掷韵诗并行的五言掷韵诗在唐代的创作则相对沉寂。
五言转韵在魏晋之前并不少见,李锳在《诗法易简录》中便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转韵手法有精到的分析,如论“君家妇难为”至“遣去慎莫留”一节:“以上三段,因三人语,分为三韵。此换韵之最清显者。又有韵则连上,而意则已转,然后复换韵者……盖自叙苦情到最苦处,不觉气咽声悲而音节亦为之一变,声音之道通于性情即此可见一斑。”韵的变化和章法、声情已经有了紧密的结合。而魏晋之后直至唐代,更活泼自由的七言诗成了转韵的主力,五言诗却因文人化程度更高,反而成了作一韵到底长诗以逞才的阵地。这一变化正是转韵手法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徘徊的缩影,转韵的一流作品当有“妙才”,而“妙才”难得反而使主流标准向着更规范、更僵化的方向偏移。但主流的标准又并不能限制住真正的才气之作。这是一场围绕着“中和”不断进行的离心运动。
李贺的转韵无疑应当划入“妙才”一流。诗体、题材、篇幅都不能成为其诗歌转韵的限制因素,其转韵纯然是在把握了各种转韵手法特征的基础上,以此为工具来实现诗意的创造,而非刻意拟古者意脉断裂、文辞生硬的转韵之作。尽管在其想落天外的意旨主导下,转韵手法与诗歌共同营造出了常遭诟病的转断之感,看起来谋篇布局颇为散漫随意,实际上,在断续的外表下仍是隐约有文气贯注的。这样的特征让其诗风拥有了和转韵手法相似的命运。
在同时代乃至晚唐,李贺之诗都受到了较高的赞誉。即使如杜牧“少理”的经典批评,也是与楚骚相比而言。《旧唐书》中“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似乎更能反映出时人对其诗歌的接受状况。宋儒尽管多指摘其少理,却也衍生出了对其诗风艺术性的高度赞扬。如严羽家喻户晓的评断:“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
变化多端的转韵加深了李贺诗风的奇崛,使其更加不可仿效,这种在“妙才”和“中和”间徘徊的命运同样落在了李贺身上。李贺对于转韵手法的巧思妙用,也正在极大程度上呈现和拓展了转韵手法存在的艺术可能性。
(二)转韵手法对李贺诗风的影响
对于李贺诗风的特点,杜牧的评断可谓精当:“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这几乎成为历代定评。“虚荒诞幻”的奇峭诗风和“理”的不足构成了后人评价李贺的两个主要方向。诗风方面,赞赏者多其“辞”之奇,而“理”的不足则又有不同的批评角度。一方面是以宋儒为代表的观点,将杜牧原本并不甚严厉的指责加深了程度。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将李贺与张籍对举:“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辞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
将李贺的“少理”集中在文意的不足上,是侧重于“质”而非“文”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注意到了李贺在诗歌整体布局上的不足。这一方面的评价常和诗风的批评相混同。如朱熹评李贺“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周紫芝则认为“李长吉语奇而入怪”。但这样的批评毕竟侧重于体悟,实际仍落在李贺诗中的神仙精怪和幽冥鬼蜮之中,深究起来并未真正离开“辞”的范畴。
今人对于李贺的研究之中,钱锺书首先在《谈艺录》中将这两个方面再次深入挖掘了。对于“辞奇”,钱锺书所提出的“曲喻”和“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切入点,而对于“谋篇命义,均落第二义”,在后文中也作了更精确的阐释:“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犿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其中“忽起忽结,忽转忽断”正点明了李贺诗断续、跳跃、缺乏连贯性的缺陷,这一缺陷也正是其独特诗风的组成部分。
回到转韵的问题上,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多种应用所揭示的,这一手法常常出自着意安排,并且在文本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文辞配合,韵段自身的艺术特性成了奇峭瑰丽之词句的点缀和补充,而更进一步看,转韵更是与文意的传达,乃至更深层的意蕴生成具有潜在的联系。因此在对其艺术特征进行考察之后,重新将视角放在诗歌整体上,则可以通过转韵看到这种转断起结风格的部分成因。
前文在谈及韵段组合与速度变化的影响时,实际已经涉及了转韵手法在全诗谋篇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分隔诗意层次。以韵分隔诗意并非李贺独创,早在《诗经》中便有着一章一转韵,转韵即转意的现象。《诗概》中则指出了这一手法和上古诗乐不分有关:“此即古乐节之‘升歌、笙入、间歌、合乐’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乐府家转韵、转意、转调,无不以之。”
而后随着诗歌逐渐脱离民歌一途,重章复唱的手法少有沿用,乐的影响更有所减弱。唐代虽有配乐声诗,也渐渐淡出主流创作,但韵和意的关联却并没有断裂。刻意仿古的七言四句掷韵诗便是这一传统留下的痕迹。李贺32首纯由四句韵段构成的转韵诗,或许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流行的七言掷韵诗的影响。
但放在转韵技法之中,四句韵段的特征本不鲜明,且四句一组,又与近体律绝节奏相似。同样的速度连缀而下,便易有《姜斋诗话》中提出的“以转韵立界限,划断意旨”之弊,乃至“有长篇拆开可作数绝句者,皆蠹虫相续成一青蛇之陋习也”。韵段之间为转韵而强行转意,容易导致韵段之间互相隔绝,貌合神离。
李贺的四句转韵诗则避免了刻意、无效的转韵,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意味。转韵是因为诗意要在此停顿或转折,韵配合诗句而行动,因而不得不转。《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这种作用便非常清晰。“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押梗摄陌韵、昔韵。“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押止摄止、旨韵。“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押效摄晧、小韵。起首四句是当前时间线下的实景,由眼见之景引发怀古之思,中间四句便自然过渡到怀古之古,还原了铜人“潸然泪下”的传说。末尾四句则从古引回怀,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为眼,将金铜仙人和“唐诸王孙”的命运关联起来了。整首诗脉络清晰,诗意层层递进,韵随之而转,结构严明。
但这样清晰的结构并不是每一处转韵中都能找到的,如《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押梗摄陌韵。“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押假摄马韵。与诗题一致,这首诗开篇便是四个新奇的意象叠下,是冷色调的仙宫梦境,而随着梦境深入,又有从梦天转为在天上梦见人间之意。梦境倏忽来去,似乎只是一场奇景的片段化展览。韵的切换仅仅在天上和人间之间做了一个微弱的区分,便服从于支离破碎的梦境画面。
规则的转韵格式尚且如此,遑论不规则的转韵了。即便如前文中阐释过的《李凭箜篌引》,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也是伴随着“忽起忽结”的断续文意的。李贺的构思穿梭不定,忽而鬼蜮,忽而仙境,忽而天上,忽而人间。此时单从文本层面的某一个角度介入,无法直接梳理出一条脉络。如《李凭箜篌引》的结尾处,长韵段在传达出作者听乐时飘忽不定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将诗意无限引向虚处,并且再无落实。而韵的断续在无形中加深了文意的断续和跳跃,强化了其中隐约的割裂感。审美效果空前强化,而诗的完整性、严密性则被搁置了。
复杂多样的韵段安排有时并不单纯服从于意旨指挥,当几种韵段各司其职,转韵便在意旨之外构成了另一种表达的逻辑。如《致酒行》的末尾两句,“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押臻摄文韵和蟹摄怪韵,少年意气未舒的怨怼在呜呃中失声,而这两句打破了前文流畅抒情的突兀韵脚,也同样如一处吞声的哽咽。《苏小小墓》中这样的设计也十分明显,“西陵下,风吹雨”看似延续了前文中“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的一组铺排,实际上则已经由蟹摄悄然转为遇摄。在令人猝不及防之时骤然打破节奏,再次点明全诗实为鬼蜮之景。于是佳人踪迹不再,凄风冷雨之下森森鬼气油然而生。
总体而言,李贺基本完美地利用了韵段自身的特性,使之恰当地服务于自身表达的需要。如促急的两句短韵,符合时俗的四句韵,以及容量更大、易于铺排的长韵段都在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韵段又反过来放大了他诗歌跳跃、荒诞、意蕴多重而隐晦的特点,在这种相互作用下,转韵彻底化入了李贺独特诗风的生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