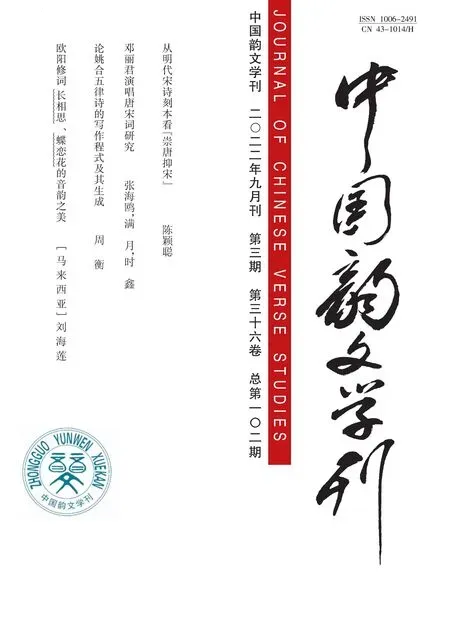禅思与诗法
——论陆游自嘲诗的禅宗渊源
朱子良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禅宗在中唐以后的大盛,尤其是“居士禅”在北宋中叶以后的极盛,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各种古典文学体裁中,古典诗歌与禅宗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不仅是因为“诗情、诗思与禅趣、禅机本来就易于交融”,而且“诗歌正好以其非概念化、反说教式的文字成为禅宗传心示法的理想工具”。宋代禅门的文字禅、诗偈、评唱的兴盛以及说法时引诗的现象,与诗坛“援禅入诗”风气正好说明了宋代诗禅交互建构的独特景观。目前学界关于禅宗镜照下的宋诗研究成果已颇丰,无论是关于宋代诗学与禅宗关系这样宏大的命题,还是从微观着手,讨论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杨万里等宋名家以及江西诗派与禅宗的渊源,学界已申说甚夥。相较之下有关禅宗对陆游诗歌创作影响的发掘却稍显不足,还有较大可供开掘的空间。
其实陆游与禅宗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陆游《剑南诗稿》《渭南文集》中保留了大量他为禅师所作的赞颂、塔铭与序跋,如《大慧禅师真赞》《〈佛照禅师语录〉序》《退谷云禅师塔铭》等等。题咏禅门佛寺、与释门酬唱赠答更是陆游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内容。陆游与马祖一系禅师渊源颇深,受马祖道一三传弟子临济义玄所开创的临济派之沾溉尤多。《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佛法金汤编》卷十五、《五灯全书》卷四十八等佛禅典籍都记载陆游曾向临济宗松源崇岳禅师问“心传之学”,《渭南文集》卷四十还收有陆游为其所撰《松源禅师塔铭》。陆游与禅宗门人的交往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与生命意识,且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其诗歌创作的面目与相关特质。
笔者根据《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发现陆游创作的200余首自嘲诗与禅宗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揭示这些联系不仅可以深化对陆游诗歌与禅宗渊源的认知,也对认识宋代自嘲风气与禅悦之风的内在关联不无裨益,尤其对宋人如何运用禅宗思想自慰自解,追求超脱旷达的人生境界更具有直接的揭示作用。
一 禅思:陆游自嘲诗中的禅宗思想因子
即使仅从词汇考察,陆诗中如“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功夫二十年”(《赠王伯长主簿》)、“禅欠遍参宁得髓?诗缘独学不名家”(《南堂杂兴》)、“快哉天马不可羁,开口便呼临济儿”(《寄黄龙升老》)等诗句业已将陆游诗歌创作与禅宗思想的渊源表露无遗,清王复礼《放翁诗选·凡例》就曾指出陆游集中大量化用禅语以至于他不得不“概行删削”的事实。而探析陆诗创作与禅宗思想的暗通款曲之处则无疑能从更深的学理维度揭示这一事实,陆游自嘲诗中所蕴含的禅宗“平常心是道”与“游戏三昧”思想,就为我们探讨禅宗思想与宋人自嘲精神的诗学联动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平常心是道”为马祖洪州禅的核心理念,即所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平常心是道”这一修行法门极大颠覆了佛教对经典与偶像的崇拜,将烦琐神圣的宗教修行一变而为习禅者心灵的自我体悟,认为修行者“能够在生活中体验到人生的终极境界”。如上文所揭,陆游与马祖法嗣临济派禅师交往密切。临济派虽然在马祖禅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然而却继承了马祖禅“平常心是道”的基本核心,这一点从临济义玄在说法过程中频繁引用与阐述马祖禅“平常心是道”思想即可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言生认为:“洪州禅沿着慧能所提示的方向,建立起‘平常心是道’的禅学理念,主张‘立处即真’,即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都呈现为真理、具有真实价值。临济禅大力弘扬了洪州禅中的这种思想,《临济录》全书都‘贯彻着全盘肯定现实人生的观点’。”。陆游与马祖系临济派禅师的交往,使得他的诗歌创作亦时时显露出“平常心是道”思想的痕迹,其《日用》诗“日用无渊奥,其中妙理存”云云即是此思想的集中体现。施之于自嘲诗这一题材中主要是以大量“着衣吃饭,困来即卧”的日常之事来予以自我调谑,有意塑造自己世俗化、日常化的“俗我”形象。先看陆游在庆元四年(1198)谪居山阴期间所作的《龟堂杂题》组诗中的两首:
龟堂端是无能者,妄想元无一事成。
最后数年尤可笑,饱餐甘寝送浮生。
(《龟堂杂题》其一)
痴顽老子老无能,游惰农夫酒肉僧。
闭着庵门终日睡,任人来唤不曾应。
(《龟堂杂题》其二)
上二诗作于“庆元党禁”期间,在此期间处于党禁边缘的陆游与党禁名单中如朱熹等人依旧往来密切,朱东润曾说陆游在此期间自绝祠禄是要“和权贵划清界限”,可见陆游对于党禁的态度。因此陆游在诗中着重突出自己“饱餐”“终日睡”的形象,不排除有对“党禁兴来士气孱”(《寄别李德远》)时风的反讽,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作者平时浸润马祖禅与临济禅的思想而不自觉地流露。《五灯会元》卷三记载了一段有关马祖道一的对话:“洪州廉使问曰:‘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曰:‘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可见马祖并不泥执于“吃”与“不吃”之任一端。而马祖后嗣临济宗无德禅师更是在众僧“酒肉僧,岂堪为师法耶?”的质疑中“饮啖自若”。陆游上诗中的“酒肉僧”正自揭出了诗中“饱餐”“终日睡”的自我嘲谑与马祖禅“饥餐困眠”“立处即真”精神之间的渊源。这种认为俗即是真、佛法妙谛不离吃饭睡觉,修行者随处作主就能圆悟解脱的精神,正是陆游自嘲诗所塑造的凡俗自我形象下的深层意蕴所在。
《剑南诗稿》中这一类的诗歌还有很多,如:
汤饼满盂肥羜香,更留余地着黄粱。
解衣摩腹西窗下,莫怪人嘲作饭囊。
(《早饭后戏作》其一)
世念秋毫尽,浑如学语儿。
得床眠易熟,有饭食无时。
纱帽簪花舞,盆池弄水嬉。
从今转无事,静坐不吟诗。
(《自嘲老态》)
心如顽石忘荣辱,身似孤云任去留。
酒瓮饭囊君勿诮,也胜满腹贮闲愁。
(《解嘲》)
在宋代“以俗为雅”的文学思潮下,这些诗刻意描摹自己和光同尘、饥餐困眠的世俗生活与凡俗形象,可以见出禅宗思想尤其是马祖禅“平常心是道”思想对宋代士子的日常解脱与世俗超越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种解脱与超越是因为马祖禅“直接把禅道行为化、生活化,从而使禅修转移到自然的日常生活轨道上来”,认为在世俗中触事而真、自然运作就是禅修的过程进而体会大道。我们看上列诸诗中“酒瓮饭囊君勿诮,也胜满腹贮闲愁”“世念秋毫尽,浑如学语儿。得床眠易熟,有饭食无时”等句表面上是诗人的自我调谑,其内里却无疑指向立处皆真的“真我”所在与圆融照澈的“证会”状态。从创作时间上看,上三诗均作于庆元五年(1199)陆游自请致仕之后,自绝宦途不仅出于年龄老迈的考虑,更源于自身名利的剥落而走向真我,证得无往而不自在的人生境界,这些诗歌正可见出禅宗给陆游晚年思想带来影响。
“游戏三昧”作为南禅宗的重要解脱法门,是禅宗典籍中习见的宗门术语,如《景德传灯录》“扣大寂之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其宗教原义本来接近于“入道之后的生命所呈现出的自在和欢愉的意境”,但是随着禅宗思想在中唐以后士大夫阶层中的流行与普及,尤其是宋代士大夫在吸收佛教思想的过程中不断予以本土化改造,是以“游戏三昧”的禅法在北宋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它指引士人阶层“只要对生活采取随意游戏的态度,哪怕是在声色场中照样能获得宗教解脱”。这种思想在陆游的自嘲诗中往往与“般若空观”相结合,体现出不汲汲于功名、不营营于官场的主体意识,以及随处自在、游戏无碍、追求超脱的精神境界。下面以具体诗歌试作分析,先看作于淳熙六年(1179)建安任上的《自咏》诗:
游戏人间岁月多,痴顽将奈此翁何!
放开绳棰牛初熟,照破乾坤镜未磨。
日落苔矶闲把钓,雨余篷舵乱堆蓑。
明朝不见知何处,又向江湖醉踏歌。
陆游自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离开南郑出任成都府安抚使参议官,此后直到淳熙五年(1178)别蜀东归赴建安任,他先后淹留在成都、嘉州、荣州、建安等地。与前线南郑慷慨激昂的生活相比,别处的生活是如此的枯燥乏味,何况在这几年中陆游的生活并不平静,他在这段时间的“放翁”自号正见证了党派倾轧、政敌构陷的险恶境况。在这期间陆游“宦情淡薄,生活寂寥”,他对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常常发出类似“浮生触处无真实,岂独南柯是梦中”(《遣兴》)的喟叹,这正是此阶段陆游认识到自嘲意识与禅宗“游戏三昧”思想暗合之处的现实基础。
诗的首联“游戏人间”的说法在陆游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作于庆元元年(1195)山阴奉祠期间《白首》一诗中“招呼林下客,游戏梦中身”的表达,作于开禧三年(1207)老退山阴期间的《杂咏十首》其三亦有“作尽人间儿戏事,谁知空橐一钱无”之句,这些句子正是禅宗“游戏三昧”思想的体现。无所执碍,自在游戏,是宋人在仕途失意的低迷状态下惯用的禅门解脱法。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诗“放开绳棰牛初熟,照破乾坤镜未磨”一联。“牛”在禅宗中象征着“真性”“自性”,“牧牛”则象征着“修行”,唐宋以来禅师们创作的为数众多的“牧牛诗”“十牛图颂”“牧牛图颂”等图文作品,以及频见于《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禅宗灯录语录中以牛说法的公案正揭示了“牧牛”这一术语在禅宗乃至佛教中的独特地位。
关于“牧牛图”所代表的不同佛法境界,宋普明禅师作有《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伏》《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泯》十偈。从偈子内容来看,自“驯伏”开始牧童牧牛已不再用绳索牵引,达到了“放去收来得自然”的状态。大慧宗杲谓“学道人制恶念,当如懒安之牧牛,则久久自纯熟矣”,朱熹亦谓“飞腾莫羡摩天鹄,纯熟须参露地牛”(《借韵呈府判张丈既以奉箴且求教药》),此正是陆诗“放开绳棰牛初熟”所指向的禅门意义,即“放去收来得自然”以入“纯熟”之镜。
我们再看写于庆元四年(1198)的另一首《自咏》诗:
平生万事付憨痴,兀兀腾腾到死时。
夜踏乱云过略彴,晓分寒溜注军持。
束薪山客招烹石,渡海蕃僧乞制碑。
作个生涯君勿笑,拄天勋业亦儿嬉。
绍熙、庆元年间南宋政坛纷乱,先后发生“绍熙内禅”、赵汝愚与韩侂胄争夺国秉、庆元党禁等乱象。在这种宰执更变如走马的局面下,陆游远离争斗、脱离现实的思想愈发强烈。再加之庆元元年(1195)以来陆游的身体每况愈下,故有上诗“平生万事付憨痴,兀兀腾腾到死时”之自嘲。妻子王氏庆元三年(1197)的病逝、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与庆元党禁等一系列变故都让陆游身心俱疲,而宋代士子又普遍有向禅门寻求解脱法的倾向,所以在诗中出现“作个生涯君勿笑,拄天勋业亦儿嬉”这样的句子来也就可以理解了。可见当诗人晚年名利剥落后,其对功名执念的自省与生命存亡的豁见促使其自嘲诗逐渐与禅宗“游戏三昧”思想得以缔合。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游戏三昧”思想的一个重要法则是对自在性的强调,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游戏三昧”思想“是对禅境界的一种印证,他描述的是一种精神上自在无碍的状态”。也就是说陆游这种对功名勋业的嘲谑态度正是勘破执着之后在无碍状态下的自我证得与解脱,不仅与“赖无权入手,软弱实如泥”(《遣兴》)一类满含愤懑的自嘲有别,就是与“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和范待制秋兴》其一)之类表面放旷而婉含讥刺的自嘲亦有精神与境界上的不同。
二 诗法:禅宗文字观与自嘲诗的语言艺术
禅宗发展至宋代经历了由“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语言观转向,这种转向即葛兆光所言宋代禅宗“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义,由严肃走向荒诞”,宋代风靡一时的“文字禅”即是这种转向的产物。几乎与禅林“文字禅”兴盛同时,北宋中叶以后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以文字为诗”的时代。显然宋代“文字禅”风气对宋诗某些特点的形成不无推促之力。周裕锴在《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一书中曾论及宋诗创作中“翻案”等方法与禅语机锋的关系,认为“对宋代诗歌困境的清醒认识,迫使宋人只能在‘如来行处’另谋出路,而禅宗典籍中常见的‘翻案法’,无疑提供了超越前人的最理想的途径”。陆游的自嘲诗中即多次应用这种“翻案法”。此外陆游自嘲诗中还出现了与禅门问答极为相似的答非所问、逻辑悖谬的表达方式,周裕锴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将这种禅门表达名之曰“无义语”与“格外句”。下面试以陆游自嘲诗为例剖析宋人如何借用禅宗语言形式来予以自嘲。
据相关研究指出,“翻案法”作为诗学术语的提出首见于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如评论老杜《九日》诗“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评东坡《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三“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句云“此皆翻案法也”。作为宋代备受追捧的诗学批评术语与诗歌创作法门,“翻案法”正显示出宋人在前人尤其是唐人“影响的焦虑”下之创新路向。这种反常合道、别出异思的创作思维在宋代诗坛的大炽与禅门起疑情、唱反调的翻案风气密不可分。元人方回《名僧诗话序》就曾指出:“北宗以树以镜譬心,而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南宗谓‘本来无一物,自不惹尘埃’,高矣。后之善为诗者,皆祖此意,谓之翻案法。”今人周裕锴在《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一文中亦认为“禅宗呵佛骂祖的精神,尤其是偈颂点铁成金的形式,无疑是宋诗翻案风形成的最直接的催化剂”。陆游诗歌创作中常用此法,魏庆之《诗人玉屑》评其《海棠》(蜀地名花擅古今)诗曰“此前辈所谓翻案法,盖反其意而用之也”。陈衍《宋诗精华录》则谓其《黄州》(局促常悲类楚囚)诗“翻案不吃力”。其自嘲诗中亦多次使用这种受禅宗影响的“翻案法”以增强自嘲的力度与深度,典型的如《齿落》一诗:
昔闻少陵翁,皓首惜堕齿。
退之更可怜,至谓豁可耻。
放翁独不然,顽顿世无比。
齿摇忽脱去,取视乃大喜。
譬如大木拔,岂有再安理。
咀嚼浩无妨,更觉彘肩美。
所谓“昔闻少陵翁,皓首惜堕齿”盖指杜甫“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春日江村五首》其三)诸诗,而“退之更可怜,至谓豁可耻”则调谑韩愈《齿落》诗中“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之句。接着陆游一反二人嗟叹忧愁之态,以“齿摇忽脱去,取视乃大喜”翻案杜、韩二公诗,突出创作主体“顽顿世无比”的文化性格。最后诗人发挥宋诗“以理入诗”的特质,将“齿落”一事进行普遍性的哲思升华,这当然与宋代理学“格物”之风气不无联系,但却亦有上文提及的马祖禅“平常心是道”之思维在,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是以“齿落”一类的平常琐事亦包含有万物运转之理——“譬如大木拔,岂有再安理”。
有时陆游还特意利用“翻案法”所特有的“反语”形式造成诗歌意涵与文字表面的矛盾张力,形成“冷嘲”的效果,这与禅语中“戏言而近庄”“反言以显正”的表达形式亦颇为接近,如《自儆》其二:
世事如云日日新,瓦盆黍酒却关身。
细思只有穷居好,寄语玄翁莫逐贫。
此诗作于嘉定二年(1209),是时陆游已自绝祠俸,半俸也已经取消,身体又到了极度衰弱的地步,以至于在这年的诗中有“今年病卧久,惨痛不可言”(《病小减复作》)、“病入秋来不可当,便从此逝亦何妨”(《病少愈偶作》)的凄然之句。贫病交加,陆游却于此诗中一反扬雄《逐贫赋》之意,反而说“细思只有穷居好”,这自然是强作反语以自嘲。
陆游此类自嘲并不鲜见,以上只是随摭数例。这些自嘲诗利用禅宗惯用的“翻案法”跳脱古人思维而反其意以用之,在戏谑的语言下潜藏着诗人不主故常的诗学路径,不仅可见宋人在禅宗思想影响下圆融无碍的性格,亦可见出禅宗“翻案”精神对宋人诗歌创作“推陈出新”思维的启示作用。
我们再来看禅门问答中“无义语”与“格外句”在陆游自嘲诗中的应用。众所周知,禅宗语录中充满了无数的语言陷阱,大量不可理喻的禅门问答都以答非所问、匪夷所思的“丛林活句”形式呈现,例如禅宗典籍中经典的几则公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洞庭湖里浪滔天。’”“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春来草自青。’”“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虚空架铁船,岳顶浪滔天。’”前二则公案完全不顾及语言问答在指义功能上的关联度,所问和所答了不相涉,此之谓“无义语”。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认为交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应包含四个准则,其中“关系准则”(Relevant Maxim)即要求交谈双方在对话上具有相关性(Be relevant),而禅宗语录中的所谓“无义语”即故意违反“关系准则”而跳出正常的对答序列。第三则公案则完全跳脱现实逻辑,以反理性与反经验的言语序列来揭橥存在于语言本身之外的禅门“第一义”,此之谓“格外句”。陆游自嘲诗中亦有类似于禅门“无义语”“格外句”而以诗歌意脉的断裂或诗歌逻辑的悖谬来展现诗歌艺术张力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出、对句之间意义关联度极低,或径以“不可思议”的荒谬之语连缀出句,如:
自笑劳生成底事,黄尘陌上雪蒙头。
(《雨中泊舟萧山县驿》)
要识放翁顽钝处,胸中七泽著犹宽。
(《庵中晨起书触目》其一)
如果我们按照周裕锴的方法将上列陆游的两联诗换成禅宗的语录形式,或许更能体会陆游自嘲诗对禅宗意不相属、逻辑悖谬语言形式的借用:
问:劳生成底事?曰:黄尘陌上雪蒙头。
问:如何是放翁顽钝处?曰:胸中七泽著犹宽。
这两联诗的相同之处在于,“劳生成何事”与“黄尘陌上雪蒙头”、“顽钝处”与“胸中著七泽”在正常的意脉承续中根本完不成意义的对接,因为“黄尘陌上雪蒙头”“胸中七泽”所提供的不是表意清晰的具体答案,而是与出句毫无关联的“无义语”,而“胸中七泽著犹宽”则更是跳脱出现实逻辑的小大之辨,以佛教“芥子纳须弥”“周遍含容”观挑战现实生活的理性逻辑,又是典型的“格外句”。
又如其晚年闲居山阴期间所作《居室甚隘而藏书颇富率终日不出》二首,通过诗中所谓“危机已过犹惊顾,恶梦初回一欠伸”“岂知蝉腹龟肠后,更寄蜂房蚁穴中”“积书充栋元无用,聊复吟哦答候虫”云云可以很明显见出,此是以自嘲早年耽于宦途、晚年却仍一事无成为主旨的一组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首:
掩关小室动经旬,蠹简如山伴此身。
百亿须弥藏粒芥,大千经卷寓微尘。
危机已过犹惊顾,恶梦初回一欠伸。
此段神通君会否?听风听雪待新春。”
其中颔联“百亿须弥藏粒芥,大千经卷寓微尘”很明显即上文所云佛教“周遍含容”“圆融互摄”观的显现,而其尾联问答互不相属,而以“听风听雪”之“无义语”指向无法诉诸文字的“神通”所在,此亦禅宗文字法之一例。
此外周氏还曾指出古典诗歌创作中深受禅宗语言影响的“陡转”法,这种方法在诗歌中以“出现结构上的大跨度转折,上下句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对立冲突”为特点,并认为此法以黄庭坚为最擅,如其诗“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杨绾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五)等联上下句之间陡转疾折,语意跳动极大、对比极其鲜明,亦即清人方东树评山谷诗所谓“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鉴于陆游与江西诗派的诗学渊源,我们有理由相信,陆游自嘲诗中“无义语”“格外句”所体现的意脉断裂、逻辑悖谬之章法行布是在禅宗“活法”与江西诗派诗法双重影响下的产物。
三 陆游“借禅自嘲”的生发契机与诗学特质
“借禅自嘲”是陆游自嘲诗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一个运用成熟的创作方法,分析这种方法的生发契机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诗学特质是认识陆游自嘲诗特点与价值的必要步骤,对解码宋人自嘲作品中的禅宗基因序列亦不为无益。何以自嘲精神与禅宗思想之间可以暗通款曲?或者说自嘲诗与禅宗的结合如何成为可能?这可从宋代诗坛诗禅交融的创作风气以及创作主体本身所处的境遇等维度予以阐释。
首先是由于宋代禅宗的极盛与“诗禅互通”观念的流行,“打诨通禅”与“自嘲自谑”在形式和精神上具有某种“异质同构”性,从而使后者吸收、借鉴、融合前者成为可能。有宋一代临济、云门诸宗声势煊赫,灯录、语录、偈颂等禅门文学形式极度风行,禅林与士林的交流日趋热络活跃,“文字禅”“默照禅”“看话禅”等禅门宗风全面渗入士林,士林的文字风气亦在禅门大炽,禅门中“儒僧”的涌现与士林中声势浩大的“居士禅”等均表明,宋代禅林与士林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禅学对宋代知识分子的浸溉已成全面滔汩之势,影响所及,如盐着水,就是一再声呼抵制佛禅的道学家亦不免“外儒内禅”。禅风的全面渗透,再加上禅门“打诨通禅”“游戏三昧”等宗风所蕴含的戏谑精神及“戏言而近庄”“反言以显正”的表达形式,极其契合文人某一部分自嘲诗诙谐的语言特点、超脱的情感指向以及矛盾的戏谑效果,随着诗坛“援禅入诗”之风流衍至南宋,与禅门联系颇密且热衷于自嘲的陆游“以禅自嘲”当然也是理之所宜了。
其次是宋人对禅宗“呵祖骂佛”宗风与“丛林活句”形式在自嘲诗的思维上借鉴价值的认同。禅宗一方面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另一方面又大胆宣称“这里无祖无佛,达磨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禅的魔力的确在于自嘲,在于‘呵祖骂佛’的自我否定”,禅宗问答所显示的语言悖反本身就存在极其强烈的自我否定、自我嘲谑色彩。再从其深层义理来看,禅宗要否定的“佛”,其实是偶像、是权威、是执着、是空相、是外障,而禅宗欲成之“佛”则无疑指向本心、自性、日用、内觉,甚至是“自己”。禅宗“无佛”与“成佛”所蕴含的两极对立又辩证统一的思维,以及“直指人心”的究旨隐隐地已为士子们在仕与隐、巧与拙、真与伪、自由与物役等命题的表达及思考上提供了思维借鉴与精神指引,而这些正是自嘲诗的常见主题。至于禅宗的“活句”形式如“翻案法”“无义语”“格外句”等讲究逆向表达、跳跃阐述与反常书写等方式对自嘲深度与力度的增强,已申说于前,就不再烦絮了。
此外,作者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为追求精神自洽、自我超脱的努力是自嘲诗主动向禅宗皈依的又一重要因素。《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谓苏轼“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憏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陆游的情况亦庶几近之,故其诗有“早知壮志成痴绝,悔不藏名万衲中”(《观华严阁僧斋》)云云。陆游自三十四岁出仕,七十五岁自请致仕,四十余年间遭到了频繁的弹劾与贬谪。根据于北山《陆游年谱》与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作品系年,笔者发现统计的两百余首陆游自嘲诗中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贬谪以后的达一百余首,写于庆元五年(1199)致仕以后计九十余首。当然这里要考虑作者诗集刊刻时大量删诗而导致早年作品留存较少的因素,但可以断定的是,不偶思想与贬谪心态是陆游现存自嘲诗的主要创作触机和主旨类型。宋人普遍追求不滞不粘的生活态度与圆融无碍的人生境界,而“诗禅相融的诗意禅境是士大夫追求精神愉悦感的首要选择”,所以“以禅自嘲”自然为陆游诗歌“对悲哀的扬弃”提供了绝佳的思维方式与表达形态。
那么禅宗思想究竟为陆游的自嘲诗带来了何种诗学特征?撮其大要表现在以下两端:
其一即日常化、生活化与去政治隐喻化的特点。刘子健称“尽管宋代以善待士大夫而著称,但是,从11世纪到12世纪,同专制权力相比,士大夫们对权力的分享程度却在日渐下降”,这是促使两宋之际士子“走向内在”的原因之一。在此种政治态势下,加上禅宗内观自我、反观自性的影响,陆游很多自嘲诗都具有反躬自省的“内向”特征。相关诗作如《自嘲》(僻学论交少)、《饭后自嘲》(岁熟家弥困)、《起晚自嘲》(辛苦一生何所获)、《自嘲老态》(世念秋毫尽)与前文已论及的《早饭后戏作》其一、《齿落》诸作多描摹日常琐事、注重心态调适,日常性、去政治化的特点均十分突出,这种日常性的特点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同类创作。清代是陆诗的接受高潮,陆游的地位一度崇隆至于“《渭南》《剑南》遗稿家置一编,奉为楷式”的程度,查慎行《旅舍落一齿自嘲二首》(毁理生时具)《腰痛自嘲》(平生耻折腰)、赵执信《病目自嘲》等清人的日常自嘲就明显带有放翁同类诗作的影子。赵祥河《俞东川太史见示脱齿自嘲诗为作一解》云“杜韩脱齿咸嗟惜,取视偏欣独放翁”,其与上文所提及的陆游《齿落》诗之渊源不言而喻,恰好说明了陆游此类诗作的影响所及。
其二在于标举了文人自嘲诗“俗化”的语言风格,强化了创作主体的感情色彩,借用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话说,即陆诗存在对“过于冷静的北宋诗风进行反拨的倾向”。陆游在禅宗影响下带有浓厚日常甚至俚俗色彩的自嘲诗为这种诗歌题材注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正是因为诗人不过分拘泥于语言的拣择与句法的锤炼,以“平常心是道”的思维观照日常并付诸诗歌,这些作品才极大地保留了诗人情感兴发之初“枢机方通”的神思状态与“直下便是”的语言原貌,诗人的真实情感更容易剥落诗歌的结构与形式而予以显豁地表露,像其《昼眠》(困睫瞢腾老孝先)、《早饭后戏作·其一》(汤饼满盂肥羜香)、《解嘲》(《心如顽石忘荣辱》)、《起晚自嘲》(辛苦一生何所获)等诗均俚俗浅白,并不考虑诗歌语言的曲折回环,而是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喷薄而出,将自己的现实心境与人生状态不假修饰地予以揭橥。将陆游此类自嘲诗与王禹偁《自笑》(年来失职别金銮)、司马光《自嘲》(英名愧终贾)等诗风典正曲隐的同类题材参看,便可知这种俗化的自嘲诗在还原诗人心态、复现作者经历、投射主体精神等方面的巨大意义。
四 结论
陆游自嘲诗中“饥餐困眠”的日常书写与南禅宗马祖禅“平常心是道”思想关联甚大,利用中国本土化的禅宗表达方式,陆游在“饥餐困眠”一类的自嘲中显示自己处处任真的超旷状态,从而实践了马祖禅以体验日常俗事为禅修过程的宗风。“游戏三昧”思想是陆游自嘲诗表露出的另一重要禅宗思想,它所指向的人生态度在陆游自嘲诗中显示为随处自在,游戏无碍,不滞不粘,不汲汲于功名、不营营于官场。
随着禅宗语言观由“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向,禅宗文字观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陆游自嘲诗中就多处使用了禅宗典籍与语录中惯用的不主故常的“翻案法”、意不相属的“无义语”以及挣脱逻辑的“格外句”,不论是语意的翻新,还是意脉的断裂与逻辑的悖谬,它们都为陆游的自嘲诗带来了不落窠臼的表达方式与想落天外的表达效果,在逆向表达、跳跃阐述与反常书写中增强了自嘲的深度与力度。
陆游“借禅自嘲”的实现契机在于:其一,自嘲自谑与“打诨通禅”宗风在表达形式及思维上具有天然的互通之处;其二,禅门“呵祖骂佛”“游戏三昧”等思想极其符合自嘲诗的自谑倾向和创作意图,而禅宗语录中诸如“翻案法”“无义语”“格外句”等表达方式也契合宋人不主故常、锐意创新的诗学路径;其三,作者壮志难酬的政治境遇与圆融无碍的人生追求又促使其向禅门寻觅解脱法。陆游“借禅自嘲”极大地推动了自嘲的日常化、生活化与去政治隐喻化,同时也强化了创作主体的情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