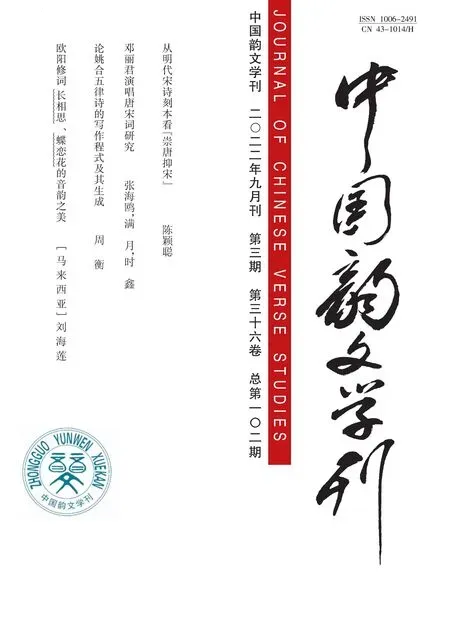论姚合五律诗的写作程式及其生成
周 衡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程式”一词,古已有之,《管子·形势解》:“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程,《荀子·致士篇》:“程者,物之准也。”式,《说文解字》:“法也。”故“程式”基本意义是法式、规程,固定模式。“程式”一词频繁出现于唐代文学、史学文献中,如韩愈《上宰相书》:“而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缋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此“程式”当指科举评价过程中的要求和标准。赵璘《因话录》卷三:“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此“程式”应指科场词赋契合科举评价的写作规范。唐人使用“程式”多与科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见诗赋创作的规范和准的受到国家政府选拔人才主旨和评价文学标准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程式的存在对以应举作为入仕途径的唐代诗人而言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也是促进唐代律诗创作产生程式特征的重要来源。
方回《瀛奎律髓》评姚合《游春》诗云:“予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姚之诗专在小结裹,故‘四灵’学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体则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几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所谓“小结裹”,应指姚合诗歌致力于诗歌形式和写作技术的经营,忽视诗歌整体艺术和思想的塑造。正是这种“小结裹”的创作思维,姚合的五律诗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极为鲜明的写作程式。研究姚合的写作程式,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姚合诗歌的艺术特征、中晚唐诗歌嬗变以及姚合诗后世接受有重要的价值。
一 姚合五律诗写作程式的表现
(一)姚合五律诗歌结构的写作程式
诗歌结构是诗人进行艺术创作时整体构思和经营的结果,诗人借助特定的结构方式进行语言组织和写作表达,从而构造出具有特定章法、篇法的诗歌结构来承载诗人的情感、思想和观念。对于诗人而言,结构脉络是其创作情感的走向和思想表达的线路。通过分析诗歌的结构脉络,可以观察诗人的情感动态、逻辑思路。由于受到长期的诗歌机械性训练的影响,姚合的五律诗在结构脉络上具有一定的程式化趋向,其五律四联在功能区分上存在首联叙事、颔联评论、颈联写景和尾联言情的结构模式。如以下三首作品:
《送雍陶及第归觐》:献亲冬集书,比橘复何如。此去关山远,相思笑语疏。路寻丹壑断,人近白云居。幽石题名处,凭君亦纪余。
《送张郎中副使赴泽潞》:晓陌事戎装,风流粉署郎。机筹通变化,除拜出寻常。地冷饶霜气,山高碍雁行。应无离别恨,车马自生光。
《送马戴下第客游》:昨来送君处,亦是九衢中。此日殷勤别,前时寂寞同。鸟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风。向晚离人起,筵收樽未空。
这三首诗皆送别题材,首联皆就题发端,借助叙事手法交代创作缘起和事件性质。颔联则围绕送别进行评论,这种评论具有融合议论和抒情的趋向。颈联则跳出送别当下场合,以从对面着笔之法来想象别者的路途环境,以此摹写别者心境。尾联则收笔回到当下,抒发诗人离别哀思和希冀。
即使是不同诗歌题材,也存在这种写作套路,如《秋晚夜坐寄院中诸曹长》:“腰间垂印囊,白发未归乡。还往应相责,朝昏亦自伤。穷愁山影峭,独夜漏声长。寂寞难成寐,寒灯侵晓光。”诗歌借助“映囊”“白发”来呼应诗题中的“秋晚”“院中”,具有一定的叙事性。颔联则承接“白发未归乡”而来,以秋晚夜坐反省的姿态来进行生存状态的评价。颈联从直抒胸臆中跳出去,借助具体意象来展现秋晚孤寂、生存穷愁,塑造诗人孤苦冷僻形象。最后又收回笔端,以“寂寞难成寐”来慨叹,只是在收束处以景作结,相对于那些直陈情怀的结尾而言,稍具余味,也稍具艺术联想。
同时,姚合诗歌结构脉络的相似也体现在尾联的处理上。从古典律诗创作艺术来看,律诗创作存在“法无定法”之说,李白律诗变化不定,并非其诗无法度,而是其法痕迹不显,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云:“诗不可无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唐代律诗结构存在以古行律之直线型结构和起承转合之环曲型结构,无论是哪一种结构,其艺术的完整性或完美性最终都取决于尾联的表达。故传统评论认为律诗用力之处多在尾联,故有“一篇全在尾句”之说。然观姚合五律结句,多平易之风,少涵泳之味,落笔又多表达雷同,如以下三诗:
《送李传秀才归宣州》:谢守青山宅,山孤宅亦平。池塘无复见,春草野中生。当日登楼望,今朝送客行。殷勤拂石壁,为我一书名。
《送陟遐上人游天台》:万叠赤城路,终年游客稀。朝来送师去,自觉有家非。石净山光远,云深海色微。此诗成亦鄙,为我写岩扉。
《送雍陶及第归觐》:献亲冬集书,比橘复何如。此去关山远,相思笑语疏。路寻丹壑断,人近白云居。幽石题名处,凭君亦纪余。
结尾都以书名、题壁作结,无论是取象还是立意,无论是情感还是句式都是相近的。这种结尾相似也表现在姚合与同一人来往的诗歌中,如:
《送崔之仁》:欲出还成住,前程甚谪迁。佯眠随客醉,愁坐似僧禅。旧国归何处,春山买欠钱。几时无一事,长在故人边。
《寄崔之仁山人》:百门坡上住,石屋两三间。日月难教老,妻儿乞与闲。仙经拣客问,药债煮金还。何计能相访,终身得在山。
《寄崔之仁山人》:不得之仁消息久,秋来体色复何如。苦将杯酒判身病,狂作文章信手书。官职卑微从客笑,性灵闲野向钱疏。几时身计浑无事,拣取深山一处居。
三首诗皆是与崔之仁来往之作,其结尾都是表现姚合对崔之仁退守山林、高蹈自在的艳羡,以及对自己无计归山的感慨。所表达的情感和所借助的句式、采用的结尾方式都是一样的。
(二)姚合五律诗歌句法的写作程式
“节奏、句式和诗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三个范畴。”其中,“诗歌的音义节奏与句子结构是诗境营造的语言基础。”诗歌的节奏一方面来自诗歌语言形式——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本身所具备的汉语韵律,另一方面来自诗歌所承载的语义和思理;而诗歌的句子结构不仅仅是五言、七言或四言等某种句式,也是借助特定句子规律所构建的句法。当前的诗歌句子结构研究多围绕句式、节奏进行,少有从句法角度思考古典诗歌的艺术法则或艺术效果。
姚合诗歌的句子建构中,常出现相似的语汇构建的相似句型,从而反映其诗歌创作在句法结构上的雷同色彩。如姚合《扬州春词三首》诗中“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和《送裴大夫赴亳州》中的“寒日严旌戟,晴风出管弦”两句,无论是句子语汇和意象、句子节奏和句型结构都有相似处。又如《山居寄友人》中的“晓泉和雨落,秋草上阶生”和《送右司薛员外赴处州》中的“瀑布和云落,仙都与世疏”两联上句皆是借助“和”句式,形成“名词性词组+和+名词+动词”的句型,同时取象思路和构境方式都是一致的。其他如《寄安陆友人》的“鸟啼三月雨,蝶舞百花风”和《送马戴下第客游》的“鸟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风”;《送郑尚书赴兴元》的“红旗烧密雪,白马踏长风”和《送田使君赴蔡州》“路遥嘶白马,林断出红旌”,《游春十二首》的“自知疏懒性,得事亦应稀”和《秋日闲居二首》的“自怜疏懒性,无事出门稀”,《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的“吏来山鸟散,酒熟野人过”和《山中述怀》的“晓来山鸟散,雨过杏花稀”,《游春十二首》尾联“并起诗人思,还应费笔毫”、《答李频秀才》尾联“衰老无多思,因君把笔毫”和《送刘詹事赴寿州》尾联“别后书频寄,无辞费笔毫”,也是句型结构和意象组合颇为相似。
姚合的诗歌在句子构建过程中,还经常出现相似的句式结构,从而形成具有规律性、程式化的句法特征。如“何计”句式,“何计”句式在唐五代诗歌中约出现四十七例,其中姚合诗句中出现最多,共计九例,如《送殷尧藩侍御赴同州》“何计因归去,深山恣意眠”、《秋夜月中登天坛》“何计长来此,闲眠过一生”、《别李余》“何计羁穷尽,同居不出城”、《寄元绪上人》“何计休为吏,从师老草堂”、《送朱庆馀越州归觐》“何计随君去,邻墙过此生”等,并且这九例“何计”句皆出现在五律诗尾联出句,即诗的第七句。又如“从来”句式,亦多出现在第七句中,如《送杨尚书赴东川》“从来皆惜别,此别复何愁”、《送萧正字往蔡州贺裴相淮西平》“从来皆作使,君去是时平”等,又如“几时”句式,在姚合诗中出现七例,亦多为第七句,如《从军乐二首》“几时得归去,依旧作山夫”、《送贾謩赴共城营田》“几时无事扰,相见得从容”、《送崔之仁》“几时无一事,长在故人边”等。其他尚有“好是”句式、“殷勤”句式、“和”句式、“无因”句式等等。这种频繁且具有规律性的运用,充分反映了姚合在日常诗歌创作中所形成的创作惯性,这种创作惯性既是一种思维定式,也是一种创作惰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诗歌创作的创造力和灵活性,反而增强了诗歌创作的模式倾向。
(三)姚合五律诗歌对仗的写作程式
对仗是古典律诗极为重要的形式特征,对仗强调出句与对句的字数相同、平仄相对、词性相应、节奏一致,从而形成一种类似镜像效果的对称模式。从民族思维来看,对仗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艺术呈现,也是中国文化中和之美的艺术范型。传统诗歌通过对仗来追求诗歌的和谐之美、动态之美甚至是对立之美。对仗的设计本意是追求诗歌表达的新异性和独创性,是诗人艺术技巧的重要体现之处。
姚合五律以宽对为常规对仗形式,毕竟宽对在具体诗歌实践中给予诗人的创作空间更大、创作自由度更高,从而更好地满足诗人情志的表达。但同时,姚合五律对仗又不满足于常规对仗,在追求对仗变化中又多有流水对等特殊对仗的运用。杨慎《升庵诗话》卷四“晚唐两诗派”条云:“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其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即为流水对,即葛立方《韵语阳秋》所云“五言律诗,于对联中十字作一意……诗家谓之‘十字格’”,而“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则指姚贾诗人对仗中常取景物作对。确实,姚合中二联对仗存在拾掇小景构成景物对的现象,同时也常出现十字一意流水对的对仗规律。如《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中颔联“何人荐筹策,走马逐旌旃”、《郡中冬夜闻蛩》中颔联“久是忘情者,今还有事来”、《送朱庆余及第后归越》中颔联“未得同归去,空令相见疏”、《送潘传秀才归宣州》中颔联“因君还故里,为我吊先生”、《送元绪上人游商山》中颔联“过来心已悟,未到行弥精”、《寄郁上人》中颔联“谁为传真谛,唯应是上人”、《山中寄友人》中颔联“却是去家远,因循往日多”、《寄默然上人》中颔联“天下谁无病,人间乐是禅”、《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五中颔联“何年得事尽,终日逐人忙”等,这些流水对皆被姚合运用在五律颔联之中,这种常见现象也正是姚合流水对使用的惯例。
另外,在姚合的对仗联中,其对仗意象或语汇常有雷同现象,姚合多借助相似甚至相同的语汇或意象来构造对仗结构,从而造成五律对仗联的“似曾相识”的阅读感觉。常见有“红”“绿”对仗,如《送李起居赴池州》“红旗高起焰,绿野静无尘”、《寄安陆友人》“烟束远山碧,霞欹落照红”;有“诗”“酒”对仗,如《送徐州韦仅行军》“晓日诗情远,春风酒色浑”、《答李频秀才》“物外诗情远,人间酒味高”、《过杨处士幽居》“酒熟听琴酌,诗成削树题”、《喜贾岛至》“饮酒谁堪伴,留诗自与书”等等。
(四)姚合五律诗歌“第七句”平仄的写作程式
姚合现存诗五百二十九首左右,其中五律诗约二百九十九首。如果从诗歌结构、诗歌句式、诗歌格律等方面去观察姚合的五律诗,会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姑且称之为“第七句”现象。
如上文已经阐述其第七句多用模式化的句式,如“何计”“从来”“几时”“殷勤”“好是”等,这是一种虚语承接之法。周弼《三体诗法》云:“绝句之法,大抵以第三句为主。首尾率直而无婉曲者,此异时所以不及唐也。”又“(虚接)谓第三句以虚语接前两句也,亦有语虽实而意虚者。于承接之间,略加转换,反与正相依,顺与逆相应,一呼一唤,宫商自谐”,周弼认为绝句创作以第三句为主,强调第三句用虚语来承接前二句语义,从而获得顺逆相应、宫商自谐之美。而姚合则将这种虚语承接之法运用于第七句,使诗歌具有更为流动的风格。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常见现象就是第七句常用特殊拗救平仄格。如以下诗句:
《闲居》: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殷勤问渔者,暂借手中钩。
《哭贾岛二首》:曾闻有书剑,应是别人收。
《哭贾岛二首》: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
《寄友人》:殷勤故山路,谁与我同归。
《送卢二弟茂才罢举游洛谒新相》:今朝赴知己,休咏苦辛行。
《送李植侍御》:无同昔年别,别后寄书稀。
《县中秋宿》:还知未离此,时复更相寻。
《寄无可上人》:终须执瓶钵,相逐入牛头。
《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从今巂州路,无复有烽烟。
《寄紫阁无名头陀》:何因接师话,清净在斯须。
《酬万年张郎中见寄》:何时得携手,林下静吟诗。
《寄张徯》:明年取前字,杯酒赛春辉。
《寄晖上人》:终期逐师去,不拟老尘缨。
《送李起居赴池州》:朝昏即千里,且愿话逡巡。
《送顾非熊下第归越》:秋风别乡老,还听鹿鸣歌。
《送李秀才赴举》:登科旧乡里,当为改嘉名。
将既符合人身从属性质,却又和传统用工关系有明显区别的这种特殊用工关系归入劳动法进行调整十分必要,是对财产和劳动者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重要措施,也是当代政府平衡两者关系的有效策略。所以,必须要对雇主责任明确划分。即劳动者进行劳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需要用人单位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十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财产安全和劳动者的人身权益。
《送敬法师归福州》:东南数千里,何处不逢山。
以上诗句皆出现在姚合五律尾联,其中第七句的平仄皆为“平平仄平仄”的格式。这种“平平仄平仄”在近体诗格律中属于特殊拗救,其本来格律为“平平平仄仄”,为了追求表达自由和声音顿挫,诗人以拗救方式将之处理成“平平仄平仄”。
从具体数据来看,姚合五律第七句特拗者存有二十九例;第三句特拗者存十五例,如《送徐州韦仅行军》第三句“山程度函谷”、《送顾非熊下第归越》第三句“家山去城远”、《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第三句“何人荐筹策”、《送邢郎中赴太原》第三句“如今并州北”、《送徐员外赴河中从事》第三句“凉飚下山寺”、《送萧正字往蔡州贺裴相淮西平》第三句“今朝郭门路”、《送李植侍御》第三句“谁知陇山鸟”、《送陟遐上人游天台》第三句“朝来送师去”、《送卢二弟茂才罢举游洛谒新相》第三句“离筵俯歧路”。第一句特拗者仅二例,即《游春十二首》第一句“朝朝看春色”和《春日同会卫尉崔少卿宅》第一句“诗家会诗客”。而第五句未出现特拗。
这种特拗形式在初盛唐五律诗中亦有出现,如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首句“寒山转苍翠”即是如此。但初盛唐格律诗正处于格律规范化和自动化过程中,其出现的特殊拗救往往是一种自发现象而不是有意为之,甚至是规范化过程中的格律生疏造成。但姚合五律送别诗出现如此频繁的第七句使用特拗的现象,这不仅是诗人自觉为之,也体现姚合在创作五律时进行的有意识设计。之所以如此设计,可从诗歌创作艺术角度来思考。姚合诗歌风格偏向平易浅切,整体上诗歌有体弱之嫌,又加上其尾联多抒情、议论结尾,又导致诗歌作结缺乏振举之气,故翁方纲《石洲诗话》认为姚合诗“恬淡近人,而太清弱,抑又太尽。此后所以渐靡靡不振也”。姚合对于这种诗歌结句“清弱”的卑格是存在清醒认识的,他在《答韩湘》诗中即直言“疏散无世用,为文乏天格”,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姚合在第七句使用“平平仄平仄”特殊平仄格是其对诗风体弱格卑的自觉挽救,从而使诗歌在纤仄、平拙之间追求平衡,形成语僻意浅的诗歌特征。
综合来看,姚合一些五律在第七句上使用了虚语承接和特殊拗救平仄格。句式上借助表达转折、顺承、设问、递进、时间等关系的虚语增强诗歌内在的流动性。而平仄的特拗使用却造成吟诵方面的阻碍,从而降低诗歌的流畅性。这种语义的流动性与声律的拗涩化形成诗歌结尾的内在张力,赋予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 姚合五律诗写作程式的生成
(一)诗人意识与姚合五律诗写作程式的生成
与初盛唐文人自觉追求政治身份相比,中晚唐文人的身份追求在盛唐消歇之后逐渐出现了迁移。“经过中唐的过渡,中国封建社会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转折对文士的思想、心态、创作、价值取向、审美趋向、命运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他们开始寻求失落后的归属问题,开始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身份建构与社会环境无疑存在共振现象,当恢宏灿烂的盛唐成为历史记忆,中晚唐文人失去了政治身份意识建构的外部生态,从而出现了身份意识的分化格局。一部分文人在艰难时局中坚持王道梦想,始终追求政治身份的表达,一部分文人追求放弃政治身份的探求,转而沉入文学的创作空间和世俗世界,追求诗性审美的文人身份实现。当然更多的文人在这两种情况中存在左右漂浮的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身份无疑会成为一种微弱的社会声响,而文学身份成为中晚唐文人较为自觉的表达。
姚合具有鲜明的诗人身份意识。姚合在《晦日宴刘值录事宅》中称“满堂宾客尽诗人”,在《送韩湘赴江西从事》中称“祖席尽诗人”,在《送崔约下第归扬州》中称“满座诗人吟送酒”,姚合所说的“尽诗人”“满座诗人”不仅是指向集会活动的其他诗人,也包括对自己的称呼,这就意味着姚合是从意识上自觉将个体认定为“诗人”身份,并以“满堂宾客尽诗人”“满座诗人吟送酒”的方式对“诗人”身份进行赞誉,可见姚合对诗人身份没有抗拒意识,而是自觉接受了这一身份,所以白居易在《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二首》其一中就以“且喜诗人重管领”来展现白居易对姚合身份的认识,也是进一步明确姚合身上的诗人身份。
对于“诗人”,姚合从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两个层面作了界定。在生存环境上,姚合常将诗人放置在幽雅清冷的生存环境中。姚合在《陕下厉玄侍御宅五题·吟诗岛》中写道:“幽岛藓层层,诗人日日登。坐危石是榻,吟冷唾成冰。静对唯秋水,同来但老僧。竹枝题字处,小篆复谁能。”在吟诗岛上,诗人以危石为坐塌,以老僧为吟友,以秋水、竹枝为场景,姚合为诗人塑造了一个清寒幽静的园林环境,这也是诗人日常生活和创作的精神空间。姚合又在《杏溪十首·渚上竹》中将竹林清流、微风冷月作为诗人的吟咏空间,也在塑造诗人脱俗清冷的外在形象。而在精神状态上,姚合则突出诗人孤峭冷僻的精神状态。姚合在《答韩湘》中说:“诗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岂随寻常人,五藏为酒食。”诗人的胸臆不同于寻常人之唯藏酒食,而有一种峭冷之气。所谓“峭冷”应指诗人在为人处世之时要具有超群脱俗之心,保持心灵与世俗社会的距离,从而能以一种冷静孤峭之心去观照社会、体悟人情,进而表达创作。
姚合具有鲜明的诗人身份认同和建构意识,并以诗歌写作作为士大夫重要的生命工作,强调诗歌创作的有意识性,追求诗歌写作的理性介入,从而形成以苦吟为重要表征的创作姿态和生产风格。姚合《游春十二首》其六云:“看春长不足,岂更觉身劳。寺里花枝净,山中水色高。嫩云轻似絮,新草细如毛。并起诗人思,还应费笔毫。”“诗人思”的发生源于姚合“看春”这一主体行为,“寺里花枝净,山中水色高。嫩云轻似絮,新草细如毛”一方面展现了诗人对外部世界细微的观察行为,另一方面也是诗人艺术体验和创作欲望萌发的外部刺激。在这种外部感应之下,诗人在产生诗歌构思欲望的同时,开始进入创作经营状态,通过“费笔毫”来实现内心的感物情怀和创作欲望。这一过程并非处于一种乘兴、自然的创作状态,而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主观经营和理性操作的趋势。具体来看,姚合强调诗人对诗歌创作的理性把控,强调诗歌活动在整体发展中注重微观刻画。姚合《闲居遣怀十首》其五云:“永日厨烟绝,何曾暂废吟。闲诗随思缉,小酒恣情斟。”所谓“闲诗随思缉”,是认为在诗歌创作中,通过“缉”这一具有理性和细微特性的艺术构思和刻画来控制、调整和推动诗歌的创作发展。姚合在《闲居晚夏》中云:“闲居无事扰,旧病亦多痊。选字诗中老,看山屋外眠。”这是通过“选字”来强调诗歌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通过字词语汇的精细推敲、审慎选择来追求诗歌艺术的精工妥帖。《闲居遣怀十首》其三云:“白日逍遥过,看山复绕池。展书寻古事,翻卷改新诗。”这是通过改诗的诗歌行为对诗歌进行理性审视和形式调整以达到诗歌境界的合理和诗歌艺术的完善。姚合这种“思缉”“选字”“改新诗”的行为都是一种诗歌“功夫”,只是这种“功夫”更多偏向诗歌的艺术构思和形式雕琢方向,展现姚合以理性为创作思维、以形式为关注重心的诗歌创作理念。
这种理性写作并没有引导姚合走向独创性的写作,受制于个人学养和诗歌能力,理性写作反而导致诗人更多地关注诗歌创作过程的可操作性,强调在创作过程中对诗思发生、艺术构思、文本表达的精细思考和理性辨析,从而构成由“思”而“格”的创作路数。这一创作路数无疑会使姚合的五律创作因理性监控而在语汇选用、意象经营、结构布置等方面进入一种创作“舒适圈”,从而自然而然出现重复性、雷同化的写作程式。
(二)“大众诗人”能力平庸与姚合五律诗写作程式的生成
毋庸讳言,姚合五律写作的程式化特征并非一种正向性的艺术风格,而是诗歌在个人禀赋、诗歌观念和文学潮流影响下的写作习气和艺术缺陷。闻一多先生在《贾岛》一文中称:“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子,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从文学接受来看,姚贾总是作为一个文人并称和群体而成为后世文学接受的对象,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贾岛时代”又何尝不是“姚合时代”,甚至,姚合对于晚唐以降的中下层文人的影响要超过贾岛。闻一多先生认为,晚唐五代文学界追捧姚贾的主要人群是“大众的诗人”,这一判断无疑极具联想力,也极有识见。纵观晚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姚贾接受历史,会发现真正热衷姚贾诗歌的诗人多数与庙堂、台阁、朝堂有着一定距离,无论是南宋的“永嘉四灵”还是清代的“高密诗派”,他们多数来自江湖文人或中下层官吏,这无疑可以说是一群“大众的诗人”。所谓“大众的诗人”,不仅仅是因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普通化,也是指其文学才能、创作能力的寻常化。大凡晚唐以来的诗坛大家、名家多不以姚贾为取法对象,而那些渴望通过创作练习和苦吟写作来提升社会地位和生存品质的中下层文人才会在姚贾那里得到更多的共鸣和好感。毕竟,无论是贾岛还是姚合,他们都不是天才纵横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成绩和诗坛命运是在日积月累的诗歌训练和苦吟写作中逐渐获取的。因此,在平庸的诗歌才能制约下,其诗歌境界、创作视野和写作魄力无法与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诗坛大家相提并论,创作上的狭窄与重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诗歌创作才能的平庸化也就导致其创作过程中存在套板反应式的模式生产。朱光潜《咬文嚼字》中说:“一种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板反应’。……就作者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就本质而言,套板反应具体到诗歌创作上就是一种诗歌的模式化、程式化表达。姚合诗歌在结构脉络上的程式化不仅由诗歌题材相同导致,更和诗人创作过程中所陷入的“套板反应”有密切关系。在套板反应这一文艺心理影响下,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变成简单的创作复制或剪裁,就如同创作“腹稿”一般,只是诗人根据特定写作环境和写作意图进行词句的调整和修饰,就像薛能评价刘得仁诗一般,“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其诗歌创作的创造性、个性化因创作程式沿袭而逐渐消泯。方回《送胡植芸北行序》云:“近世诗学许浑、姚合,虽不读书之人皆能为五七言,无风云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莺燕鸥鹭、琴棋书画、鼓笛舟车、酒徒剑客、渔翁樵叟、僧寺道观、歌楼舞榭,则不能成诗。”又于《瀛奎律髓》姚合《游春》注云:“予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姚之诗专在小结裹,故‘四灵’学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体则衰落不振。又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几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方回所指出的姚合诗歌“所用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这种“小结裹”正是姚合在“套板反应”影响下而产生的意象选用上的程式化结果。
(三)唐诗衰变与姚合五律诗写作程式的生成
姚合五律创作程式化是唐代诗歌发展至中晚唐之际的自然结果。汤因比《历史研究》认为“必须到我们所称的‘挑战和应战’相互作用的模式中去寻找文明的起因”,认为文明是在一系列挑战和应战的运动中得以发生和成长,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标准是“自决”,并且汤因比认为“成长是创造性的自决能力的伴侣”,同时,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因这种“创造性的自决能力”的丧失而造成。唐诗的发生与发展同样具有相似的演变轨迹。初唐诗在以虞世南、许敬宗、宋之问、沈佺期等为中心的宫廷诗人运作下,逐渐形成以高华典雅为核心的主流风格。从本质上来说,初唐诗是初唐文人在文学与政治互动发展中所做出的应战,是初唐文人在扬弃陈隋诗歌遗风的基础上,结合初唐政治需求和文化潮流探索出的“唐化”诗歌。进入开元阶段,唐诗延续了初唐以宫廷为中心的创作环境,玄宗君臣在开元清和生态的催发下共同改造初唐诗,并最终在天宝年间实现唐诗从台阁、宫廷走进江山、市井和塞漠的空间转移和范式转变,塑造出气象雄浑、情韵玲珑的盛唐诗风。
对于后世诗人而言,盛唐诗不仅是一种可资吸取和借鉴的文学经典,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和创新的文学传统,王安石所说的“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正是感慨强大的文学传统对后来文学的压迫和制约。如何彰显中唐文人及其诗歌的独立性?这其实就是盛唐文学对中唐文人提出的恢宏挑战。从结果来看,中唐文人在这场文学挑战和应战中确实有所突破,他们竭力追求诗歌独立表达和创造发展,从而打造出“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元和诗歌格局,方南堂《辍锻录》云:“唐诗至元和间,天地精华,尽为发泄,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旗鼓相当,各成壁垒,令读者心忙意乱,莫之适从。”但这种“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的诗歌风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盛唐乃至中古典雅审美的叛逆,但也不可避免地将元和诗歌从盛唐诗歌的康庄大道引入羊肠小道,在创新追求中促使诗歌创作走向精细、狭境,而丧失其浑朴之象。汤因比《历史研究》认为精细化是文明衰落的重要因素,同样,精细化也是唐代诗歌步入中晚唐之际衰微的重要因素。这种追求语言的着意安排、意象的刻意选用、结构的理性建构等诗歌特征都可以说是一种精细化的表征,它使中晚唐诗在普遍意义上失去了强大的生命力,诗人的诗歌写作也就沦落到简单重复的无意义制造之中。故钟秀《观我生斋诗话》认为“中唐五律佳句颇多,而元气已漓矣”,所谓“元气”,不仅仅可以理解为诗歌内部所蕴含的苍茫浑厚之气,也可以理解为诗人积极的创造力。
正如闻一多所说,“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姚贾诗人群体的五律创作具有“出路”动因,他们在踏入仕途之前,五律的创作是为了迎合科举考试的需要,五律创作具有鲜明的“训练”色彩。汤因比认为,“训练就是一种对人类行动和生活的机械化。”这种机械化的训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应战”,其丧失了创造性的自决能力。因此,在千锤百炼的机械训练中,姚贾等诗人的五律创作陷入诗歌写作的程式化状态中。顾安在《唐律消夏录》中云:“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合跌荡、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其所说的“法脉渐荒,境界渐狭”“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者,无疑是在批评中晚唐五律创作的生命力消歇、创造力平庸和程式化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