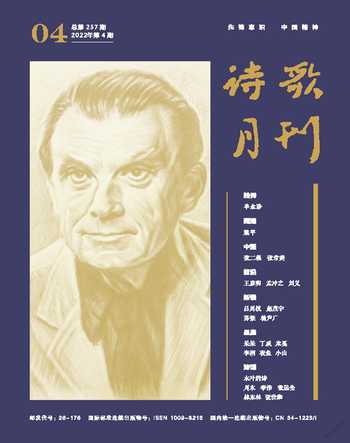萧关散去(随笔)
单永珍
公元1247年,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武威)白塔寺进行“凉州会谈”,宣告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史称“凉州会盟”。每次穿行河西走廊时,我都会朝着白塔寺的方向,一再回味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并且用文字记录下来,好让后来的人们知道“祖国之大,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道理。
公元2021年6月,我从宁夏西海固直奔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和天祝的众弟兄一起迎接《西藏文学》主编次仁罗布兄,当金黄的哈达挂在胸前,当河西的阳光照在罗布古铜色的脸上,我似乎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承诺。之前,罗布在电话告知,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关于西藏并入中国版图的故事,想亲身感受萨迦班智达走过的路。正好我要写一部长诗,河西走廊是绕不过去的重要素材,于是相约成行,共赴一场历史的盛宴。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面对一段历史的取舍,各自有各自的侧重。
那一年,王维来到凉州时,我以上描述的时代还没有诞生,会盟事件还没有发生。但冥冥中有一股力牵着我。
我总想把最优秀的写作者邀请到西海固,用他们的如椽之笔写下西海固的命运与喘息,摇曳与心跳。借着这次难得的机会,考察结束后,我拽着罗布,深入十万群山包围的西海固,互相接受灵魂的洗礼。
因为张承志的《心灵史》,沙沟拱北要去。因为秦始皇,秦长城要去。因为王维,萧关必须去。
晚上接风,罗布有点摇晃,拍着胸脯说,萧关太知道了,王维的伟大诗篇《使至塞上》就写到萧关了嘛!永珍,明天我们到遗址处看看。
我说,必须要去,不懂西海固,就不懂西北;不读诗歌,就不懂文学。固原是中华文明的一处要穴,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的身影穿行在这条大道上,多少诗篇埋在黄土之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罗布点点头,口齿伶俐地背出《使至塞上》。
次日,携带一夜的沉醉,舟车萧关遗址,一路检索从汉乐府到清代关于萧关的诗词,重温半部中国文学史。
萧关门前,一派寂静,鲜有人来此凭吊。院子里,就我们一行,多少有点孤独。
那就从汉乐府的《上之回》开始吧,沿着古代诗歌的脉络,重新发现西海固。
移步至王维的《使至塞上》前,罗布再一次轻轻吟出那辉煌的诗句: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好一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盛大的景象似乎在眼前又一次徐徐铺开。我想,全中国的小学毕业生,都会对这两句诗不陌生吧。可能大多人熟悉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但对王维的边塞诗,这首《使至塞上》,至少能记得住!
在命运不济、人生悖逆的时候,王维的笔下自然会生出悲凉。这似乎是惯性,我读中国诗歌史,从屈原以降,那些青史留名的大诗人,大多是在生命转折的时期,丰富和供养了诗歌的宝库。
王维也不例外。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奸臣李林甫当权,张九龄等一批重臣被贬,朝廷人心惶惶。王维郁郁不得志,接到敕令,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慰问战胜吐蕃的将士。
金秋时分,长安城的落叶簌簌飘零,曾经的报国之地,而今竟是伤心之所。与其和当政小人迂回苟且,不如奔赴旷野,看一看辽阔的河山和遍地的人民,给苦寒之地的勇士们带去安慰。
一行人出发了,一辆轻便马车,沿着咸阳、奉天、安定、原州的地界,眼见烽燧狼烟,落日沿着黄河的支流清水河滚圆落下,此情此景,不禁让王维感慨万千。毕宝魁先生在《人间最美是清秋——王维传》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王维看得出神,车轮依旧向前滚动。这时,只见从正面跑来三匹马,马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马跑的速度不太快,在有一段距离处站住了,其中一个高声问道:
“车上是什么人?快快通话。”
“这是从朝廷来的监察御史王大人,你们是什么人?”王维的随从反问道。
那三人一听是朝廷来的官员,立即下马,牵马走上前来见礼,并答道:“我们是驻守萧关的队伍,奉将军命巡视侦察边境。王大人从京师赶来,一路辛苦了!”
“原来是几位候骑,你们久戍边防,为国效力,也很辛苦。请问,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将军在凉州吗?”王维先礼貌性地宣抚两句,再问情况。
“回禀王大人,崔大人不在凉州,率军到燕然(今蒙古国杭爱山)去了。不过,崔大人已去很长一段时间,估计王大人到凉州时崔大人也该回来了,王大人鞍马劳顿,赶快到萧关驿站休息吧!”
当晚,王维就住在萧关。灯下,思绪翩翩,思前想后,一首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就在那时完成了。萧关有幸。固原有幸。
我问罗布,王维此去何干?
罗布说,慰问唐军。
我问,为何慰问?
罗布微微一笑,指着我说,你这家伙,不就是战胜吐蕃,赢得胜利。
我想起《三国演义》的第一回,罗贯中这样下笔:“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五千的中国历史,正是应了这句话。
二十多年了,自从我定居固原在此谋生,无数次经过这古代的关隘,想想那些通关的僧侣、商贾、从军者、文人、贩夫走卒、盲流……这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不知道演绎了多少人间的喜剧和悲剧。
要知道,汉唐时期,富庶的关中地区,有多少异族的眼睛盯着那块肥肉。因此,历朝的战略家明白关中的重要性,北萧关、西散关、东函谷关、南武关,四大关隘死死地守护着帝国的心脏。
而向北的萧关,出关便是黄沙漫漫、戈壁浩瀚的游牧草原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用南宋陆游的一句诗总结唐代边塞诗的美学特征,应当足够了。
站在新修的城墙上,罗布说道,向北是漠北的蒙古高原,向西是河西走廊偏西的西域,偏头西南,就是我的家乡拉萨了。
我说是的,从固原飞重庆,重庆飞拉萨,一顿功夫茶的时间,我们随时就见到了。
姑且在萧关城头醉一回,我從包里拿出本地的上等美酒金糜子,一人一口,迎着和煦的风。
而今的萧关,是今人为了旅游,根据史书的记载,推测出的大概位置。新修的城墙、新建的亭阁、今人粗糙的书法、七扭八歪的浮雕,让人对遥远的历史产生轻浮之感。任何对历史的修饰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尽管萧关消失在岁月的尘埃里,但当你打开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那扑面而来的诗文仿佛让人置身火热的现场,欲罢不能。
从武威到固原,次仁罗布和我,似乎走过了三千年的路程。
多少故事,多少烟云风流散去,唯有文字,依然会照耀着一代又一代人。何况萧关在我心里。
不如去看看对面的瓦亭古城,斑驳的黄土墙会告诉我们曾经的以往,至于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就是想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