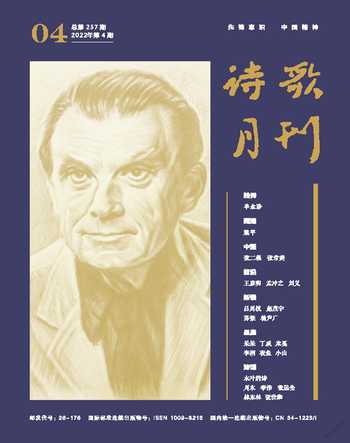废园谈诗(组诗)
刘义
谢灵运墓前
再次感受到汉语的流向
在这位早期同行魔幻般的
修辞术中获得了一次转机
当河流改道时
落日编织成一片余晖击穿密林
同伴走了一段路回过头:这是语言的魅力
是的,一千多年消失了,他的声音如此清晰
旁侧的稻田与溪流,一直保持原貌
油桐的白花泼在山道上,带有晚春的体香
竹林抖了抖肩,开始唱歌
很快,一块属于谢灵运的旧碑款待了我们
——他的名字被轻轻地
凿在石头上面,没有任何的修饰
只留下一个光辉的称谓:诗人
小野菊
十年前的小野菊又出现在后山的山道上
仿佛跟他谈论动荡年代的老人的化身
没有任何改变,除了水泥路已经更新到脚下
但围篱还凝滞于悖论之中
诗到了中途,生命是一只长腿的昆虫,惊扰光的精确度
他穿过死亡与午后下降的宁寂
叶子旋转着落地,没有声音
很多都是同步的,像故人离开
而你摘棉花的旧址,已荒废成草莽
新的声音从你的遗稿中聚集
复现在茶山与竹林的边沿,一丛丛客观的小野菊
答辩
像你写了这么多年,又没有
名气,是不是作品本身的原因
如果我也这样写是不是没有意义
那个晚来的青年人,照例开始提问
长者放下手里的《序跋集》
很平静地回答,并绕道疑问的根基
就像我们昨天所经过的
铭刻《金刚经》的斜坡爬山廊
它们的意义就是引领我们上升
(但必须身体力行)
直到看见秀江完整的江面
与城区四十里外——仰山闪耀的雪峰
废园谈诗
在山西饭店附近半废弃的公园里
我们沿着晚上九点钟的台阶、小桥与林荫小道走了两圈
谈论中世纪的诗歌:老杜与但丁当然是话题的中心
他们所经历的,也许仍在上演
但我们比他们幸运,还能在相对稳定的空间里面写诗
尽管写得很虚弱,不够丰富,也不准确
但多少可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局促
很多话题是很难展开的,譬如诗与时代的关系
个人与传统的关联……而我们的谈话
突然被喊着关门的保安打断,他用强光对着我们的脸
好像只有这一瞬间,我们才看见了自己
怀念仰山的一位故人
伴随舒适的弧度,那只披燕尾服的鸟
引领我闯入你早期语言的郊外
斜光渗透流水与圆石复沓的清音
赋予竹林傍晚的气息
竹箬滴水构成的清澈是椭圆形的
石级裸露的高古覆盖层层近代的绿色
梯田很自如地环绕到你的身后
山顶漫步的彩云,还认识你这位老友
而我多么愿意在你写诗的小径前徘徊
做你的书童,铺纸磨墨,记錄你口授的诗章
提起你读书的地方被修改成草堂,我们不禁
击掌大笑,慧寂大师也在附近的银杏树下微笑
开端
他用细竹篙搭傍晚的篱笆
给菜地铺上冬茅的叶子
松土,浇水,扯草,打叶
这些陌生的工作指向古老的技艺
就像那个桐花的白色组装的四月早晨
他在山背上挖到第一颗黄牙笋
那股新鲜的气味携带理想的甘芳
仿佛他经过多年的努力
赢得了一次开端
野鸭
把电瓶车停稳,取下早餐走向湖边
拌粉加一个鸡蛋还撒了很多辣椒是他喜欢的味道
其实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每天上班之前在这里待一会儿
那只野鸭照例旁若无人地拨出细微的水线
——清晨新鲜的回忆之光
他觉得自己也是一只野鸭
对着湖水朗读维特根斯坦……几年前
他在另一个消逝的湖边走着
暝色展开翅膀,两只野鸭在水面上浮游
他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活着
他不知道野鸭的命有多长?
蜘蛛
小家伙
在合金框架组合的空间里
横行、竖爬
甚至吊悬于空中
娴熟的技艺,仿佛孤独匠人,独旋
第八只脚,踏向不可见的绳索
它的身体距我
大约两厘米。距时代投影
无可测数
——整个过程,没有第三者
没有欢呼或雀跃
正面的熏陶
站在八中门口——喧嚣人群的一旁
他们谈论着诗,好像世界
只剩一个讲述者与一个倾听者。
阳光有点强烈,因为也蒙受到
这位长者正面的熏陶。
而经过一次次地唤醒与提示
那个年轻诗人开始像袁山大道
两侧的街树那样换叶子
直到他身后的书全换了一遍。
六年后,在路边的餐馆里
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自己正面临诗与生活的两种困顿
而现在,两者达到了平衡。
仰山
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的回返
从长安到袁州,再从北岩到仰山
在竹林与圆石之间
展开的是秋夜灿烂的星空
清澈的水声赋予圆的寂寞
但银杏树纷披先师变化的图案
我栖隐的书堂被后人修改成草堂
我只能与你击掌大笑,在另一个广告的时代
当那只从诗集中飞出的长尾巴的鸟
发出忧伤的鸣叫,一丛灰烬的声音
但我只能待在这里继续写注定要散佚的《宜阳集》
而你化成了两株银杏,有时我会散步到你的塔前沉思
三十年前,我们沿着观念的清溪溯源
来到那道哲学瀑布前,而我只沉迷于诗学
仿佛两条不同的轨道的对话
有时,我们仅仅在冰瀑前静坐,感受
巨大的无音,你讲述很多种形式
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一种巨变即使在出世的深山
我们也能感受到,白云危险的形状,但你信奉的观念的哲学
与我的纯诗有诸多殊异,我们在山道上辩论
不觉彩色的晨光勾勒曲线的梯田
所谓的哲学无非是对你与世界的一种理解
所谓的诗也是对我与世界的另一种呈现
但很多的疑问,我只能通过诗来跟你对话
而你已经成为山中飘移的岚霏,永夜的鸟鸣
你曾经说我的诗太凄苦
但除了诗,我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都将会成为这座山的背景
就像你的躯壳消失了,但整座仰山都是你叠褶的回音
冬天已经来了,我抬头看着积雪落在集云峰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我收集了很多银杏的叶子,好像这些都是你的裂片
雪很厚了,估计雪化后那个痴迷于诗的僧人还会来
跟我讨论诗的声音的秘密
但东庄的夜非常非常宁谧
渚田上的白鸟衔着一粒晨星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像汉语铸造的光线
语言是另一种背景,但我们的背景消失了
我能在诗中修复它吗?
但我的诗似乎可以像溪涧贯穿曲折而虚构的世界
后來的同行或你的同行都会不断地寻找我们
朝代几经损毁,但我们存在于仰山空无的清风中
在莽草起伏中他们通过诗与哲学的废墟之镜跟我们对话
他们从时代的反面出发来到你的圆塔前默祷
雪谷当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雪水融化后的道路
从雪谷到郑谷隔着一只静默千年的石龟与一首纯诗的距离?
慧寂当然不是寂静的智慧,而是一株拥有宇宙意识的植物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沿着这条永恒的溪流溯源,不仅仅是我们
还有后来的赵汝鐩、严惟中与傅仰斋……
他们的加入构成了一个永恒的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