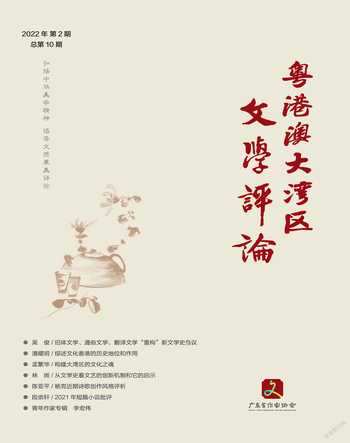从文学史看文艺的创新机制和它的启示
林岗
摘要:古人对易道周流深有体察,就像古代文论里的通变论就是诗文领域的创新论,它是文论里创作论的基本命题。但文艺史上还存在另一种古人未曾讨论的创新机制,它虽超出创作范畴但仍属于文艺的创新现象。这种创新机制在诗文作者个人求新求变的主动意识之外,由无意识的“跨界”,变换原来的写作赛道,不自觉之间实现了文艺创新。了解了文艺史,明白了创新现象的机理,今天的作者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在创作中为我所用。
关键词:通变;创新机制;雅俗;自在;自为
科技和文艺恐怕是人类工艺和精神活动里最讲究创新的两个领域。无论两个领域的创新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铁律都支配着这两个领域的人类活动。一旦创新活动停顿下来,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就止步不前,而文艺则只能重弹“老调子”,作家只能重复自己。科技被人类的好奇心和市场活动驱动着进行创新,而文艺为作者的激情和读者观众驱动着进行创新。你不创新,旧技术就被淘汰。你不创新,作家和作品无从获得应有的价值和位置。可以说,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对于科技还是文艺都是同等重要的。
从历史看,与古代中国技术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同,文学的创新老早就成为命题,进入了文论家议论探讨的视野。这就是古代文论持久探讨的“通变”命题。在古代生产技术属于日用百姓,“劳心者”可以不察不知不关注,但诗文属于安身立命的“三不朽”之一,士大夫是用心讲求的。所以他们早早知道“立言”而传之久远,其秘诀在于“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1] 然而古代文论家是将创新作为创作论问题来探讨的,所说的“通变”只在创作的范畴得到讨论,换言之“通变”只是诗文作者必备的本领。如刘勰论通变:“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那些能懂得通变道理的文士,其创作走得更远。而那些走不远的,写作有时而穷的诗文作者,就在于他们没有掌握通变的方法。“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疎耳。”[3]古人文论的通变思想,当出于易道。《周易》有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4]对天道周流不息,往复变易的观察,已经深深楔入中国人的文化深层心理。它能化入文论之中,成为古代文论创作论的基本命题,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因为通变局限在创作论的范围,一旦说到如何才能通变,文论家所能指出的具体门径,也就无非回归“文统”,谨守经典,博览精阅,变文为质,师法古人这几项。这些门径固然有其道理,对某些诗文作者,尤其是初学者是有效的。但这些通变的门径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以为不能高估,尤其是不能认为古人的通变论就说尽了文艺创新的道理。这并不是因为古人的通变论错了,并不是因为古人所论的通变门径与事实不符,而是因为古人将文学的创新仅仅置于创作论的范围来探讨,其眼光还是显得受限了。通变固然在创新的范畴,但似乎不是文艺创新的全部。还有,就创作而论,诗文作者能接受和领悟通变的道理仅仅触及创作者主体理性的层面,至于具体的创作者能否将这个通变的道理落实在创作中,还存在个人才华的问题。这不是理性层面能解决的。道理再正确,方法再得当,奈无才何?以创作的眼光看,作者最后能否实现通变,最为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懂得不懂得通变的道理,而是文学的才华到底如何的问题。若是缺乏文学的才华,懂得再多的通变道理也是白搭。所以古人以通变论文学创新,只触及到了文学创新的部分问题,决没有穷尽全部。以创作的通变论创新,固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必尽然。如果我们跳出创作论,以史的眼光观察文学,与创作通变论不同的文学创新景象赫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把它称作创新机制,因为它超出了作者创作的领域但也属于文艺的创新现象。其中的道理也值得我们略加阐述。
文学史上,我们看到与创作者主动“通变”不一样的文学创新,这类创新通常是在无意识中实现的。创作者为料想不到的文学新现象所吸引,逸出了原来的规范轨道,无意中走到了一片写作的新天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知不觉中更换了赛道,既没有谨遵经典师法古人,也没有主动求变,但事实上却实现了文学的创新。当然就创作者无意识这一点而言,所谓创新也是我们事后看出来的。这种创新颇有黑格尔“自在”概念的味道,它虽然不是主动求新求变那样“自为”的创新,却也通过漫长历史的积累,实现了文体、题材和风格的创新。一部丰富的中国文学史提供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比如五言诗的出现,那是诗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当然不是哪一位诗人求新求变的结果,五言体首先出现于民间乐府诗,然后文人士子仿效试作,逐渐完善而成为诗体的主流,其间跨越百年。词、戏曲、话本的演变大体上也经历了类似的故事。这种类型的创新如果给个说法,可以称为更换赛道式的创新。它在创新的方向、方式、途径和实现的效果上都不同于创作论意义的“通变”,我们有必要好好认识这种文学史上存在的“自在”式创新机制,这对于今天的文艺家进行文艺创新是有好处的。
中国文艺自古以来就存在雅俗分治的格局。雅俗分治意味着由文体、表现方式、修辞乃至用词等不同构成的趣味差异各有其存身的天地。雅的在社会上层,满足富有教养、断文识字的贵族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文艺需要;俗的在社会下层,满足那些不识字、缺乏教养的百姓的文艺诉求。雅俗分治的格局演变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雅的文藝流行一段时间就凝固、僵化起来,难以获得持续下去的动力。古代文论的“通变论”其实就是针对此种局面而提出的挽救之道,期待身处文统之内的士大夫具备自觉意识,在雅的文艺凝固僵化起来的时候扶衰救弊。至于这种雅的文艺在流行中易于凝固僵化的原因,乃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面对着生活的“原生态”,比较高高在上,流行既久,就陷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失去再生的动力。然而与此相反,俗的文艺因为在民间,它虽然粗俗、幼稚但不凝固、不僵化因而呈现生机勃勃的面貌。粗俗的生命力在俗文艺里是不缺乏的。如各地域的民歌,陕北的酸曲、青海甘肃的花儿、两广的客家山歌等。由于雅俗分治的格局,新文体新风格的形成往往在民间。它们活跃、有生机,但粗糙、幼稚、不完善,反映的是民间社会的趣味。雅俗相较正用得上一句老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单纯执着于雅俗在审美上的长短,我以为并没有大的意义。我们需要观察的是雅俗文艺在历史上的交往和互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雅俗分治并不意味着雅俗隔绝。分治只是指出了趣味分层的状况,分层不是隔绝。雅文艺历史上对俗文艺的影响主要便在于观念的示范和导向方面,可以说雅文艺的观念内容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俗文艺,渗透了俗文艺,它起着示范的作用。俗文艺史表明,通俗作品无论在趣味上如何“出格”,但极少见它们非难或违背儒家伦理和传统的道德信条。趣味可以不同,反调近乎罕见。即使有一二个例,也属于“正统的异端”。可以说雅俗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就是一体的,从这种一体性中可以看出雅文艺对俗文艺的示范和导向的影响。
雅俗分治又不隔绝的格局无形中给文艺创新开出了一片天地。处于社会上层的雅文艺当然是规规整整毫不紊乱的。当它的文统生机勃勃的时候其文艺创作也是生机勃勃的,然而当承平日久,它逐渐进入凝固僵化状态的时候,情形就起了分化。一方面是坚守文统的士大夫打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号,在“通变”的范畴内寻求出路。这种复归元古、师法古人由文归质的文学思潮,在汉唐宋明清都曾出现过,它是上层雅文艺内部发生的演变。另一方面是富有文艺修养士大夫当中的有心人,他们转向民间的俗体文艺模仿学习,汲取俗文艺在表现方式、题材、修辞等养分,为己所用,以自身深厚的文艺教养改造俗体形式,由此实现文艺的创新,给文坛带来清新的面貌。这些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能这样做,雅俗分治但不隔绝格局的存在是一个前提。在欧洲就很难设想这种文艺上雅俗渗透的情况出现。因为欧洲的文艺传统,其雅和俗,不但分治而且隔绝。雅和俗不但是趣味的差异,而且也是阶层的隔绝。平民的趣味、文艺形式和修辞不存在进入贵族和僧侣欣赏的渠道,就像它们的戏剧传统里悲剧和喜剧的截然划分一样。但是中国的文艺传统与此不同,文艺固然有雅俗,趣味固有不同,但社会存在强大的上下层沟通机制,像儒家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就是一端。雅文艺的趣味和形式,它们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当原本属于俗文艺的文体、表达方式和修辞得到文人雅士的改造提升,它们也能登堂入室,迅速成为上层审美追捧的对象。假以时日,原本属于俗的,日后即变身为雅。
如果追溯动机,士大夫当中的有心人当初也不像现今文艺家那样立意创新。他们往往对文艺趋向的变化,触角并不是那么敏锐。只是他们比较放得下文人雅士的架子,虚心看待周边的新事物;或者即使依旧端着文人的架子,但有今日当做今日事的随机应变能力,不被旧的条条框框束缚住手脚。于是迈得开不寻常的步子,模仿、学习民间俗界流行的文体、风格、文艺形式。他们只要能写出足够有新意的作品,自然就引来了更多的效法者,不断实践,不断完善,从而提升了俗界文艺形式的文艺性。其中好的作品在文艺史上获得长久的名声。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例子比比皆是,大家耳熟能详。由于文献疏于记载,很少留下具体的人名,今天还说得出姓甚名谁的鲜少,但案例却是俱在。比如词,它的前身原本流行于唐代丝绸之路各节点城市歌楼酒肆的寻欢酒宴,为胡姬艺妓所演唱,乐器、乐曲多来自西域而融汇华夏。这种文艺形式,不但流行于社会下层,而且舶来色彩浓厚,是典型的俗文艺。它们与正宗文体的诗文分属不同的艺文天地,但身处文化大熔炉长安的士子,得意或失意的,无不出入酒肆欢场,耳闻目染,或一时技痒,或为情所动,为自己为歌女谱将起来,变身为歌词作者。当时随作随毁的当不计其数,那些侥幸流传下来的,就成为词,一种此前未有的抒发情感的文艺形式。今天我们能读到的“词祖”是李白的《忆秦娥》,既有才子伤情,又饱含英雄气概,末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意境何等雄阔。又如,话本乃至章回体小说的产生,也与此相去不远。它渊源于佛教传入中原时行脚僧向百姓宣讲佛本生故事的底本,我们今日还可于敦煌变文看见其轮廓。行脚僧的传教行为无形中带起了口头讲故事的风气,引来了下层文人的模仿,于是故事题材由宗教向世俗转移,敦煌变文中又有讲史一类。这意味着口头讲故事这样一种佛教东传输入的表达方式,不仅脱离了宗教传播,而且被民间说唱艺人加以本地化。到了宋元时期,口头讲故事的风气流行,部分失意文人更加以模仿,孕育了话本、拟话本乃至章回体小说。如果没有文人加入这个行列,那口头讲故事也许就停留在说唱的阶段。又如,古代文学批评的评点方式,明以前仅用于诗文。晚明才子金圣嘆,才高傲物,屡考不第,作文嘲笑考官,是典型的落魄文人,但他将自己原本擅长批点诗文的批评方式,创造性地运用于批评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章回体小说。他应该不是第一位评点通俗文体的人,但他把这一批评方式做得炉火纯青,别开生面,成为一位通俗小说的批评大家。上述例子,都是在新的表达方式、题材、修辞等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不行旧路走新路,更换了赛道,无意中创新了文艺。古代文人能够这样做,站在他们本身的立场,眼光向下,汲取文艺“原生态”的养分,这是最重要的。
客观上,古代文艺史上的雅俗分治和交流融通给中国文艺带来了源源不断创新的土壤。然而土壤的存在不等于现成的创新,就像有了一片土地并不等于一定能获取收成。就算在古代也并不是任何一位作家都能利用好历史机缘给他们提供的条件,绝大部分作家还是习惯于原来的轨道,对创新机会的悄然到来浑然不觉,更何况那些客观上更换了赛道的作家也多在无意识中实现的。所谓机缘巧合,偶然性的因素扮演了创新更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可以胜过古人。中国从百年前的农耕大国已经变身为工业和科技大国,科技和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已经使得创新意识深入人心。文艺创新包括文艺评论的创新已经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这就说明现当代的文艺创新,它不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主动而有意识地进行创新实践已经变成文艺领域的普遍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已经不存在提升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作家对创新的自觉性能从“自在”的状态提升至“自为”的状态总是对文艺的正向发展有好处的。
除了变“自在”式的创新态度为“自为”式的创新态度之外,实际上现代中国社会的文艺创新土壤比之古代中国社会不仅辽阔得多,而且肥沃得多。这要拜科技改变人间的强大能力所赐。社会学上,用第几次“浪潮”、第几次“产业革命”来形容当今科技给予人类社会的影响。不用叨念那些词语,用我们日常生活的感知就能领悟如今正处于科技力量强有力塑造我们生活的年代。这种改变既给文艺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从未遇到过的挑战。比如日渐成熟的网络平台,它本来只是信息传输的技术,并不属于文艺。但文艺作品从来都存在传播的问题,网络技术的出现不但创新了文艺的传播方式,而且借助这种传播方式催生出新的表达方式,一大批寄生于网络天地的文艺表达形式,如网络小说、中短文艺视频、虚拟画廊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它们一如古代通俗文艺,虽不入于大人者的法眼,但却异常活跃,生命力强大。在技术的周期之内,它们的生存是没有问题的,随着技术的迭代,它们的形态当然也将随之改变。无论如何,我们今天面对由科技催生的新的表达方式及其文化,是不是有几分像前文讨论的雅俗分治的格局?其实这就是一种新时代文化上雅俗分治的状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不是也由此存在一片文艺创新的沃土?我认为是的。现代科技为文艺发展创造了另一个“民间”,不同于自古以来的山村乡野的民间,它是技术的“民间”。这两个民间都可以为文艺创新提供营养丰富的“原生态”。要实现具体的文艺创新,文艺家们如果能睁开双眼,迈开双腿,走向这两个“民间”的大地,就一定能实现其创新的目标。其实文艺界的有心人已经尝试这样做了,只是这片文艺创新的沃土还未被充分认识而已。当然也要知道,技术虽然是中性的,但它创造改变的可能性越大,也意味着借助它进行改变的风险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创新很可能走向单凭着创作者空洞畅想的途径。如果创新搞成创作者海阔天空的造作,那这种自我臆想出发的创新就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只是泡沫式的空洞的把戏。在创新意识高涨的今天,尤其需要避免空洞、为创新而创新的“创新”。
总括文学史呈现的文艺创新机制,它一直在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创作主体自身通变的层次。这个层次的创新多与经验的积累,与对先在传统的体悟师法有关。在文艺史上见到的“中年变法”“衰年变法”现象,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创新。但文艺史上还存在另一种更换赛道式的创新,它跨越原来的文艺趣味层次和表现方式,进入原来不熟悉的初生的文艺天地,以自身的教养趣味提升原来的表达方式,从而实现文艺创新。其实人类的生活无论古今,那些在生活里展开的粗糙幼稚不成熟的形式、表现媒介和风格一直存在。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向在“原生态”蓬勃生长的文艺汲取创作的养分,效法和学习其中有益之处,不失为一条可以借鉴的途径。只要有志的创新者有足够的思想和文艺觉悟,有足够的艺术敏感性和趣味的辨别能力,就一定能够发现这些粗糙幼稚和不成熟的形式、表现媒介和风格有价值的地方,也一定抛弃其中的糟粕和无聊的成分,从而完成文艺的创新。
[注释]
[1] 陆机:《文赋》,见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2][3]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见范文澜注本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9页。
[4] 《周易·系辞下》,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74页。
[5] 《礼记·大学》,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673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