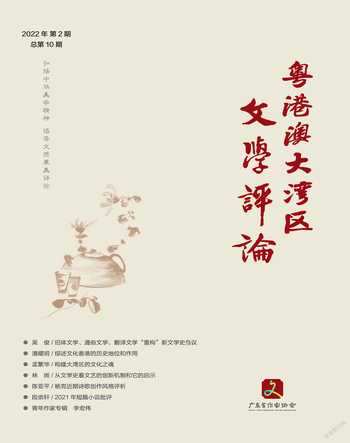写到生时:耿立散文
石岱
摘要:耿立是一个散文创作和理论思索并重的作家,本文主要考察他的新作《暗夜里的灯盏烛光》所呈现的散文创作的转向,从早期的美文的精雕细琢到现在的文本呈现的浑朴毛边现象,不拘泥于精致小巧,追求一种与精神合体的大气象,以及他所推崇的散文的精神高度和气盛言宜的话题,这是对他文字背后创作心理的探察,本文就是从他理论和实践的契合度,来观察他的散文创作。
关键词:耿立散文;暗夜里的灯盏烛光;散文毛边质感;气盛言宜
耿立是一个有清晰散文理论思考和文字实践的散文家,他曾出版理论著作《新艺术散文概论》《新艺术散文美学论》及《遮蔽与记忆》《青苍》《向泥土敬礼》《灵魂背书》《暗夜里的灯盏烛光》等多本散文集。主编过10年的年度散文、随笔、文史选本,曾两次进入全国鲁迅文学奖前十,有广泛的影响力。
耿立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认识很清晰,知道要什么,舍什么,不盲从不跟风,在自己的写作轨道上掘进,近年在创作的同时,也未放弃散文理论的思索,发表诸如《拒绝合唱:散文的同质化和异质化》《谈散文诗意和小说化陷阱》《散文:真的伦理》等。耿立在2021年8月的一个散文讲座上,说自己的散文“我的散文是留毛边的,毛边这个词,大家都明白,就像毛边书,那就是自然的天然的,凸凹不平”“我相信文章以气为主,口里含着一股气,一气呵成,保留现场感,一般不再动,只是改些错字,后来再修正,我总觉得已经离开当时写散文的感觉,就是换气了,或者就是原先的气断了。所以,看到我的散文文字,往往是泥沙俱下,但我要的就是这种原生的力度,野性,自由自在,不想修饰,不想美化,因为美文太多了,我不想掺和进去。我想追求的是散文本质的那种天生的自由。”[1]这是一个录音的整理,从耿立开始创作到他的散文新作《暗夜里的灯盏烛光》,看他理论和实践的契合度,来观察他的散文创作,是一恰切角度。
一 、从雕琢走向浑朴
耿立早期的散文,在乡土里穿行,非常讲究文字的精美,乡村叙事有着诗意的叙述,意象精致,篇幅不长,起承转合,篇中点题,符合美文的规范。我们在散文集《藏在草间》里,看他早期的散文比如《跛唢呐》《白棺》《一枝花》《白夜》这些篇章,就可窥见耿立早年散文里美文的因子。
《白夜的》里,雪停了,星星出来了,耿立却选择的是陌生化的字词。雪,住了,星星的闪烁,变成了蠕动。
雪夜是什么样子,狗减了喧嚣,觉得夜异样陌生,平原如太古,河堤如痕,苇垛如芥,这样古雅的词,就是从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来的,描摹一副夜的水墨。
那夜的颜色是什么样子?是蓝,是靛青的蓝,是春水里的小鸭屁股的翘起的蓝,耿立在这里变换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为春江水暖蓝先知。
这样的文字意象,如绝句一般,吸收古语,用一些人们不怎么用的词,苦心孤诣、孜孜乾乾,就是要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这样的文字,是茶点,精致,给人的胃口清新,但总觉得这不是正餐,有一种小品的味道,就如鲁迅所言的小摆设。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耿立的早期散文近似的是美文的形,特别是语言,而在内在的质地,他是偏于重的,这可看作他早期散文的一种撕裂,他是意识到的,在散文集《藏在草间》的序言里,耿立明确地写道:
作家陶醉于乡村的田园风光,这也是一种追求。但乡村真的是诗意盎然么?来自大地的夜哭呢,虽然田园的恬静是我们获得灵魂的安宁,但还有被遮蔽的一面呢,我记得自己读沈从文的文字的时候,曾被所谓的“田园诗人”所迷惑,有谁读懂先生的悲悯和悲哀呢?[2]
我们往往把美文理解为诗情画意,耿立早期散文也是从朱自清和杨朔的乳汁里成长的,在语言上,下过苦功夫,看他起步时的散文《白杨林的村庄》《童年的梦痕》,更是觉得,如一排童话,根本没有沉重的影子。
这些篇目别说是美文了,简直就是梦幻童话,不只语言的精雕细琢,而散文的内在的质地,从朱自清、杨朔对生活的诗意而抽空到了夢呓里,这个阶段时间不长,现实的生活既教会人向着生活生存,也教会了作家如何看待现实,美文对生活的疏离感、凌虚蹈空,对一些鸡汤文,对一些浅阅读是蒙汗药,这时,耿立就意识到自己的撕裂,他作为一个从曹濮平原乡村的人,身上本就带着沉重的生活烙印,于是在他早期没闻道时期,他已经解除乡间那些沉重的话题。
蝴蝶是美妙的,斑鸠、芦花公鸡、兔子也是乡间常见的物事,但这样的散文审美,离真实的乡村,离乡村的父老生活很远,于是他就借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追问田园诗意的散文,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
耿立的散文到了历史散文阶段,在写作《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悲哉上将军》《秋瑾:襟抱谁识》的时候,耿立的散文意识更加清晰。他追求散文的一种精神透视,一种还原。一种对历史散文的追求,他走出了早期的诗意,开始追求散文的精神高度,他不被那些历史的沉重拖垮,不是抄写冷僻史料,也不浅薄议论感慨,而是还原那些现场,同情理解,抱持人道主义立场,在《秋瑾:襟抱谁识》里, 李忠岳是山阴县的县令,官微言轻,他依了秋瑾的心愿不绞首,不脱衣,尽自己所能保证秋瑾死得有尊严一些。但他还是为自己没能保住秋瑾感到十分愧疚,秋瑾死后,李钟岳心如虫噬,老泪横流,为秋瑾死在自己的手下悲愤难抑,最后自缢于家中。“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在这篇文章里,耿立在此处停留片刻,站在精神的高度,赞扬面对恶政,不忘抵抗与自救,这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高于人顶的一厘米,是长在体制之上的一厘米,也是见证人类良知的一厘米。但这样的一厘米在历史上是多么的珍罕和稀少。
在经过了历史散文阶段之后,耿立从曹濮平原移居岭南,他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进一步打开,经过多年的创作和实践,他对自己的文章追求越来越明晰,那就是从美文的逼仄空间走出,追求精神的高度、精神含量,不再纠缠于局部,不再把精力放在细部精雕细琢,而是追求阔大,追求文字背后的灵魂,他在《谈散文诗意与小说化陷阱》中说:
所谓文字背后的灵魂,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格局,散文的背后是站着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这样的散文才会脱离平庸,走向阔大,有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就有什么样的散文。[3]
阅读耿立的新散文集《暗夜里的灯盏烛光》,我们总觉得,他的文字开始走入一种阔大的浑朴,浑朴,给它描述一下就是:浑朴近苍劲,浑朴近自然,不事雕琢,以气为主,是散文的原生态,即使这文本是有毛边的,是凹凸不平,也不再人为的修饰,接近下笔的自然状态。
二、毛边的质感
著名小说家曾维浩评价耿立的散文说:
自由确实是耿立作品非常独特的品质,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当代文学里的散文少有他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很适合他气血充盈的表达,在精神奔跑的途中,他似乎是不太在乎精心去打磨辞章。读精心打磨的作品多了,读耿立,我就从那些精耕细作的田垅走到了杂花生树的原野,神清气爽。在《灵魂背书》里,像他过去所有的作品一样,我还读到悲怆与追问。这种悲怆有时会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跨时空对接。[4]
曾维浩阅读耿立的散文,突破了曾维浩自己原先的散文的概念和内存,在他的阅读经验里,当代文学的散文不是耿立散文的这种样子,耿立似乎是不太在乎精心去打磨辞章,因为在精神奔跑的途中,有一种东西是有别于辞章的,那就是散文的自由精神,这种基于文字又超越文字的精神自由文字自由,岂能以寻章雕句所能限制?岂能把精神拘谨于起承转合的文章学,在写作的途中,精神裹挟的泥沙俱下,突破美文的限制,更能给人以文体的震撼,这也就是曾维浩所言,读精心打磨的作品多了,读耿立的散文,曾维浩就像从那些精耕细作的田垅走到了杂花生树的原野,神清气爽。
当下,大多数的散文,就如龚自珍《病梅馆记》所言“ 斫其正,养其旁条; 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价”[5],梅可病,散文也可病,无生机生气的散文就是一种病。这样的散文是盆景,就是求的精致,精巧,下功夫打磨把玩,最后就如收藏界把玩的摆件,满是手的痕迹,是一种设计好的,有着套路的制作。
在耿立的全新散文集《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里,也许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文字感觉,有的重故事,有的重叙述体验,那些乡间的、城市的生活,那些少年、青年成长;那些曹濮平原的风情雨岭南风情交织。亲情、成长、命运流转,伤痛,那些放逐与无处安放的乡愁。
在耿立的《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中,他称之为的那黄壤平原,那是人与万物的舞台,生生死死,春耕夏耘,劳作爬食,秋收冬藏,热血龙灯,有向命运的顺从,卑微,更有大地热血,强悍野性。
耿立不讳言早期自己与家人的卑微、苦难,他前几年的父亲意象,在这本散文集里也多次出现,我统计了一下,《赶在黎明前奔跑》里有,《一叶如来》里有,《乡间的雨》里有,而《父亲拔了输液器》则可看作父亲饮酒史记,他曾有散文《匍匐在土》,耿立是像祭文一样写父亲,那里有个经典的场面,被耿立无数次从多个角度书写,伤痛记忆,是不可能轻易被移除的“在我出生的时候,偏巧,我们生产队里一个在大队当干部的人的父亲死了,此人拿着生产队仓房的玉米、麦子、大豆成麻袋地送去,让他们待客。而我出生时,家徒四壁,盛米面的瓮与陶土的缸里无有粒米,于是就想着借队里一点谷子,脱下皮子弄点小米,为我的母亲温补一下身子。但生活的坚硬和冷漠拒绝了父亲,这个年方四十的男人,无力抚养妻子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儿子。那是雨天,深秋的雨天,早已没有了雷声,但他喉咙里像是有轰鸣的雷声从肺腑爆出,人们看到了这雷带来的水,他的脸颊汹涌的泪水。他不愿再在这个世道无尊严地活着,他像要倒净这如苦胆般的生活的汁液一般,冲向机井,被人在井口强行救下了。”[6]这个场景,耿立无数次追忆,张志扬说:“记忆,特别是创伤记忆,它历来就是自我重复的固置形式,只要你没有能力穿透它,它就会在未来的想象中而且是最美好、最富有吸引力的想象中悄悄地复活自身。”[7]这是张志扬先生从心理机制分析,但对耿立来说,这不是美好,我们毋宁相信,这创伤记忆,是他的耻辱红字,是激励他写作的一种提醒,这个记忆反复发作,每次,我觉得都是一种痛苦,并非张志扬先生所言是美好的,也许,耿立无力穿透它,因为那创伤记忆的源头,不是个人意志所能穿透的。但他觉得一个人,一个男人的尊严,被蹂躏,被践踏,被逼到自杀,也许,自杀,才是父亲展现男人尊严的最后的一道屏障,不能活,毋宁死,死也要壮烈些,这个场景出现在《乡间的雨》里。
人在最卑微的时候,才能洞察世态的真相人间的冷暖,这也许就是耿立精神的成长点,也是他散文情感浓烈的涵养点,他有的散文写的悲慨,写的激愤,我想,是与这些事态有关。
这也许是耿立散文的精神发生学。
也许,因为这,耿立的散文在浓重的情感和炽热的精神推动下,不择路而出的文字的洪流,就不管不顾地留下所谓的毛边。
这一点,张鸿看得真切,张鸿在谈到《匍匐在土》时,就注意到耿立散文的毛边,甚至毛病。
这样的毛边的散文,我们在《赶在黎明前奔跑》里见过,在《遍地都是棉花》里见过,有的理解耿立的毛边,会保留下毛边,但有的,则是把毛边剪掉,修饰了。他在《赶在黎明前奔跑》里,有一段写他高中时代,总是在黎明时分,不走学校大门,而是翻墙而过,而很多青春期迷茫的同伴,在晚上,在操场,在扮演那流传千年的吊孝的仪式,一个同学在前面示范,很多的同学跟在后面,那是有月亮的晚上,那放大的影子,宛似穿越到明清,唐宋,魏晋三国,一个个儒生,端肃地在凭吊。
耿立在这里曾把家乡的出殡吊孝的24叩拜的礼节,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好像是挣脱了主线,其实,真正的散文,是自由的,哪里是单一的或者线性的前行,也许,一个弯道,恰是一个风景,好散文不是赶路,而是山阴道上,且行且思,云蒸霞蔚,可缓缓归。
耿立散文,不避互文,有的在此处简写,有的在彼处浓墨重彩,气象万千。
散文《乡间的雨》的那祈雨求雨的场景,这仪式在《见龙在田》篇里也有,一个是母性的,一个是雄性的。
《乡间的雨》,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诗意,但耿立却是反向行笔,写的是生活之重,写曹濮平原的春天的干旱,耿立说:农夫靠天,大自然一使性子,农人就只能承受,咒骂、祈求,自然还是自然;所谓的顺祝它那是一种无奈。过去在农村很多就是老天的性子决定着收成,决定着农人的生活,那些父老没有科学意识,无法认识自然,神啊巫的东西,就滋生开来,于是,我们看到那些祈雨的祷词“神啊,盼您今年/让我们的大地下一场透雨/让我们沟满壕平/盼您明天给我们大地长出麦秆/麦秆上长出九十九个穗头//神啊,盼您今天/给我们东南风/别刮西北风”,这些词语都是现实的心理的显影,雨下到透,下到沟满壕平,大地的麦秆要有九十九个穗头,在春天的那个时间段,只有东南风才会带来雨。耿立在这个文章里,还写了另一段祷词,那是对着池塘和井口椎心泣血地祷告:
雨从草垛来,雨从池塘来,雨从大路来,雨从东乡来,雨从王庄来。
最后那些女人们哭起来,哀求雨神别把这一方的人收走啊,给这一方的人留一条活路啊。[8]
这些祷词的肢体语言更丰富,这些祷词连着乡村的肢体,连着乡村的哀乐,甚至那些面盆铁锅铲子斧头。这是一种乡间布鲁斯式的伴奏。
耿立的散文有极强的造型能力,有丰富的叙事性的因子,他有着农村生活的积累,在还原现场方面,有绘画的质感。在《见龙在田》里,耿立只交代来一句求雨的事,但那些舞龙者却写得惊心动魄,写出那个土地的血气硬朗,他们为了荣誉,在舞龙的时候,排山倒海,蹿房越脊,在舞龙的时候没有解的气,在河滩上解决,我觉得,这一部分才真正写出了耿立故乡的那股英雄气,他的老家,就是水浒的故地,是响马英雄,是黄巢、宋江的血地,耿立写那些舞龙的男人在舞龙后的直面对决,舞苍龙的直视舞银龙的,那些汉子们:
苍龙喊:豁出去了,百十斤,今天分分誰是公母?银龙喊:豁出去了,谁孬种,谁是妮子生的。
苍龙说:包你先出手。银龙说:包你先出手。
苍龙说:怕你了?银龙说:怕你了?
“揍你个狗日的”“揍你个狗日的!”[9]
耿立写的是古老的规矩,是从响马就传下的这对阵,叫养龙,把龙的骨头养壮,那个时候,每个舞龙的舞者,都卸下自己舞的那节龙的木柄,拿在手里,如水浒里董超学霸在野猪林对付林冲的水火棍。这里的对阵,讲平等,就是每个对手,用手中的木棒,向对方击三下,不能击头,不能击裆,也不能躲避。这头三下互相击打过后,可以混打了,谁败下来,谁就是孬种,草鸡了。
耿立故乡的民风的彪悍,散文的造型,在这种描述中毕现。耿立写故乡的两条龙,苍龙与银龙,每个龙的舞者是13个精壮的汉子,他们可以是程咬金,也可以是貂蝉,暴烈如火,温柔似水。从明朝到现在,相爱相杀缠斗了几百年,既有知音互相欣赏,又有瑜亮情结。在舞龙的时候,荣誉大于天,天王老子的话也不听,但又义气规矩,用舞龙的棍棒械斗,你一棍,我一棍,就如玉如意,不打不相识,相互寄生,相互依存,然后喝酒,然后抚摸着对手的伤痕流泪。这是耿立故乡父老表达感情的方式,这是一篇写实和写意结合的散文,缘起老家的人让耿立为舞龙申报,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书》的第一部分“项目简介”。
在《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中,我们看到嗜酒爱茶的“拔掉输液器”的父亲,形色猥琐,说话不利索,在街头靠打扫卫生,半乞讨性质讨生活的一个农民形象。耿立不讳言亲情里的暗黑和不堪,当大哥把父亲用来打制棺木的泡桐树卖掉的时候,这个平时没有性格被人欺辱的父亲,突然被激怒了。
耿立曾写过一篇散文《白棺》,就是写泡桐树在父亲生前自己看着木匠为自己打制棺材的坦然,但当他的泡桐寿材被树贩子伐倒的时候,我们看到父亲的愤怒,就如他最后的归宿被拆迁了,没有了最后的安息,最后的家,这种暴怒,我们透过纸面,还可感受得到。
《父亲拔了输液器》是一篇充满细节而情感节制的散文,耿立在这篇散文里,不再专注于生活的苦难,而是在苦难的底色之上,父亲生活的片刻的闲暇和轻逸,如农人锄禾日当午后,枕着鞋子在树荫下的片刻的休憩。
这是以酒对父亲活着有支撑意义的散文,人到酒里解脱,还是酒对人的拯救?酒成了苦难生活的亮色,成了父亲的一种生活选择,有心事对酒说,无法说出的话,有酒来说,在散文里,耿立写了父亲的伙计和朋友二哥,这是男人间的友情,二哥也是一个底层形象,他们互为自己的心里开了一扇窗,在父亲临终前,二哥在父亲的床头喝绝命酒,那场景令人泪崩。
这散文如雕刀,把生活刻录得立体,还原了现场,这里面的细节,特别是二哥的手指,作为一个酒萝卜在父亲的嘴唇上逡巡。这样的逼真还原生活、还原真实、还原友谊的散文,在当代亲情散文里是不多见的。
三、为文使气
耿立离开了故乡,熟悉耿立散文的人,在《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里是会隐隐读出变化的,也许是岭南文化的影响,耿立正从乡土散文里抽身,也从沉重的历史随笔泥淖里转身,开始走向弥散着海与城市气息的空间和文字。我们在《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里能读出故乡,在《编年切片》《赶在黎明前奔跑》《暗夜的喉咙》《这暗伤,无处可达》《替一只苍耳活着》《一叶如来》里,这些无疑是一个散文家精神编年的成长史记,也是一个乡村少年,在初中读《约翰·克里斯朵夫》,高中读《红与黑》那些异质的外部的世界,改变了这个乡村少年的文化心结,打开了他的眼界,让他知道了故乡天圆地方的世界之外,还有别样的秩序和人生,他在《编年切片》里写到第一次在乡间供销社的百货柜台,却发现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在乡间的这一眼,改变了这个少年。精神的种子在这个乡村孩子心里种下了,在《肉身考古学》里,我读到耿立在一年秋天在巴黎拜谒拿破仑的最后的栖息地,他的诗里透出这精神的轨迹。那也是初中,他在乡间的麦秸垛里读到《拿破仑传》,多年后,他到了拿破仑的灵寝来还处愿,我在《替一只苍耳活着》也看到耿立读《红与黑》的片段,法兰西的文化浪漫,深深地影响了这个乡间的少年。
从这些文字,透露的信息,在初中的某个文字时刻,也是精神时刻,耿立写出了他的心第一次被放到了平原的外面。鲁西南的曹濮平原,没有山、海、江、湖,但这些还不是主要,主要的是耿立的精神的饥渴,它想到平原的外面,看看平原外的山,山外的海,可以说《暗夜里的灯盏烛光》,就是耿立的精神的成长记,是他从平原到外面的世界,从山东到广东的物理南行记。耿立以故乡一个叛逆者的身份走了,从山东的鲁西南到广东的岭南,他不愿在故乡的酒场和各种人情中被围猎。到了岭南,就是拥抱另一种有别于中原腹地的鲁西南文化,有别于家乡的水浒文化,也意味着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耿立从山东到广东,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人的自我放逐,为了生活的尊严,不愿为五斗米屈膝,他只身漂泊来到南方,对平原深处老家的人他谁也没告诉。
其实耿立并不是潇洒地转身,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偷渡者,他说自己像是做贼一样,对父亲和那片黄壤终生亏欠,在《遍地都是棉花》里耿立写道:“回故乡,看儿时童伴,入狱的有,枪毙的有,带着淋病和梅毒的有,有谁衣锦还乡?我回去看姐姐时,觉得自己是愧疚于这土地与故乡的,正如我写不出他们的生存,我只能是亏欠,是终生打下的白条。我知道我的文字不会流泪,要是会流泪多好啊,那就能给故乡以抱慰!”[10]耿立的土地情结终生难解,他是故乡的囚徒,那片土地他是回不去了,但是他和那片土地的脐带是咬不断的,他终生都走不出来。
耿立散文的写作的毛边感,我觉得,是他散文行文的为文使气,是他的精神的灌注。耿立的行文推崇气盛言宜。我们读耿立的散文,就好像感觉耿立的文中有一股气,这股气贴近他的精神气质,这股气从行文的句式和语言中显现。他的散文,确实是散,内容编排是松散自由的,随心所欲地起笔,随心所欲地结束,但又有自己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无论是从语言还是内容,不拘泥于一些框架格调,不避俗俚,也不避高雅,其实无所束缚的随性之笔的背后,是他希望突破常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力量和一股气在。
从前,农村人总是想争取拥有城市户口,在城市里扎下根,安个家一样,耿立也希望逃离了那片黄壤平原,在城里的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归属,可是城市里都是钢筋和水泥,没有熟悉的泥土和裂缝可以钻进去,想要扎根,又谈何容易呢?在《这暗伤,无处可达》中,耿立详细地描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小城的身心历程,从结社拜师,到乡下亲戚,从学术讲座到化肥种子,耿立就像是一颗漂泊无依的种子,被风从乡村的庄稼稞上吹到城里,他说他知道他的头上是顶着土气、高粱花子气味的,他的胃底层还是红薯打下的,打嗝冒出的不是城里大米的味道鱼肉的味道,还是红薯,还是青菜萝卜。
耿立的这种困惑,在散文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无论是在黄壤深处的城市,还是在海滨珠海,无論是出入地委家属院,还是出入于自己任职的大学,无论是在学校食堂面对伙房师傅,还是在系里面对让人尊敬的长者教授,耿立总是被人拦下,总是不被认识,总是不被承认。他写道:“洗不掉的土气,不管走到哪儿,都有。几十年,我的脸上都刻着字。”在耿立诸多的散文作品中,都可看出他对于自己身上的土性的无奈和愤恨。
可是我们在文中,时时感到一股气在,散文虽然写满了岁月的雨雪风霜,虽然底色相当苦涩,虽然扑面而来全都是厚重的泥土气息,但那可不是土性,反而是狼性,是不甘,是不屈,是不卑,是不亢,是在夹缝中生存,在被排挤中绽放。
那股气,说是精神的力量也好,在散文中,耿立说是狼性。这狼性,是藏不住的。耿立散文的独特的狼性,在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耿立曾写道,他年轻时总是无端无故地流鼻血,无论是在熟睡中,还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讲座中。我想,这正是因为耿立身上的土性限制了他,牵绊着他,束缚着他,捆绑着他,遏制着他,而他体内又隐藏着蓄势待发的狼性,土性和狼性相互纠缠撕扯,导致他总是流鼻血。这是狼性,也是热血,是奔突的力。
在他的诸多散文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古人讲养气,在耿立这里讲的是精神,是精神的高度。
散文因何而写?耿立认为这是一个精神世界呈现的问题。“在可见的世界下面,沉潜着一个精神的光源,这精神是责任,也是一种终生的追求。没有精神的高度,所谓的真情实感限制了散文,使散文的格局显得偏狭,很多的人为文又开始情感作弊,撒谎,胡编乱造,有的则是情不胜文,一点感情,孱水作假,少了诚实,散文不是精神的载体,而是伪善,是炫情和炫疼。”[11]
正如他自己所说,耿立在散文里,实践着自己的主张,你能从他文字的艺术转化中感受精神高度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为文使气,你读他的散文时时随着他的文字的使转而心情激荡,这是精神的在场,是精神的不撒谎,是直呈和裸奔,耿立平时写毛笔字,他追求毛笔字的境界是:写到生时是熟时,这来源于郑板桥的诗,郑板桥的诗曰: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最后,我们以耿立的话作结,他说:散文很多的时候不是表达的问题,而是勇气的问题,是精神和灵魂的不撒谎。
[注释]
[1][4][5]耿立:《谈散文写作》,《金沙江文艺》,2021年第11期。
[2]耿立:《藏在草间》,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3]耿立:《谈散文诗意与小说化陷阱》,《山西文学》,2021年第5期。
[6]耿立:《匍匐在土》,《广州文艺》,2016年第6期。
[7] 张志扬:《〈创伤记忆〉引论·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三)》,《古典学研究》,2018年9月。
[8][9][10] 耿立:《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 年版,第318页、第184页、第137页。
[11]耿立:《随笔和散文的门槛》,《百家评论》,2013年第 5期。
作者单位: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