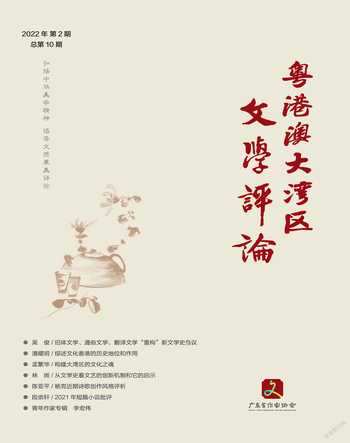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在群山之间》:一部非虚构的扶贫文学志书
刘艳
摘要:陈涛的《在群山之间》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和扶贫作品,具备非虚构写作的客观真实性、现场感,展现了作家强烈和浓烈的介入性写作姿态。作品还表现出浓厚的艺术气息和追求文学性、艺术真实性的审美趣味,这是对非虚构写作往往客观真实性表达有余而文学性和艺术真实性较为欠缺的有效反拨,弥补了非虚构写作容易罹患客观真实性有余而审美价值缺失的不足。文学性和艺术真实性的追求,作家强烈的情感投注和作品在叙事上的精心剪裁与巧妙取舍以及谋篇布局,令《在群山之间》呈现为一部别具审美意味和文学价值的“非虚构的扶贫文学志书”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扶贫文学;客观真实性;艺术真实性;介入性写作姿态
阅读《在群山之间》之前,也读过不少的非虚构作品和扶贫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类的扶贫文学作品,但是陈涛的这部作品还是以它独具的风貌,深深吸引了笔者。这部作品在文体和文类上,其实是被打上了“非虚构”和“扶贫文学”的双重标签或者说是印记,那么,它到底是因为独具什么样的气质和特质,令它在数目繁多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别具特色、脱颖而出的呢?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别具特色的地方或者说写作的“点”,令它如此具有可读性?令它竟然在“非虚构”作品这一很难特别出彩、也不会有戏剧化冲突的故事情节的作品文类中,具备能够深深打动人的能量、竟然能够吸引读者一口气读完呢?
一、非虚构写作兼具艺术真实与文学
审美趣味的自觉追求
在追求真实理念的“非虚构”写作这一写作潮流或者说是写作现象的海量的作品里面,陈涛的《在群山之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一向以体现真实理念为文体显著特征,同时这亦是作家主体、作家自身的一种刻意追求的非虚构作品中,这本书显示了作家陈涛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追求“艺术真实”的写作态度,彰显出作家在非虚构文类之上,重塑非虚构写作“艺术真实”的写作伦理和艺术追求。而且,《在群山之间》在艺术真实的追求和表达当中,完全无伤、无碍作品在非虚构写作通常所具备的文体特质“真实理念”方面的呈现和诉述。这在一段时期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和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当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和不同寻常。
非虚构写作,英文为“non-fiction writing”,算是一个舶来品。被称为“非虚构小说”的作品与新闻和报告文学等纪实类写作结合,曾经风靡美国。但在国内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大行其道,内涵有较大差别。在一次访谈中,力推此概念的李敬泽对该类作品予以冠名和命名:“像韩(笔者注:韩石山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这样的作品,当然不是小说,是报告文学吗?是散文吗?都不对;中药柜子抽屉不够用了……最后,就叫‘非虚构吧,看上去是个乾坤袋,什么都可以装。”[1]之后在写作者、评论者和学者的共同塑形当中,“非虚构”文学概念,得以成长和声势壮大起来。各个知名文学期刊也纷纷开设了非虚构作品栏目,而有些评论刊物则开设了非虚构作品评论专栏,等等。对于对传统的文体分类构成解构性意味的“非虚构”概念而言,其实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具备绝对的封闭性,甚至是被视为不具备文体分类意义上的规范性,中国原有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口述实录体写作等,似乎都能够被涵盖进去。
如果在叙事散文之外,将非虚构的筐子里,装进的全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传统层面已有的文体,甚至因为过于追求客观真实性而将非虚构与近乎新闻深度报道式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完全划上等号,忘记文学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失却艺术真实性的坚持和追求——因为只要是文学的某个类别,哪怕是非虚构写作也不应该忘记对艺术真实性的追求。一旦忘却这一点,恐怕就是对虚构小说的“失真”予以纠偏得有些矫枉过正了。非虚构写作,强调写作者的介入性姿态、写作的亲历性和现场感,但是否就应该丢弃艺术真实性的追求呢?是否非虚构写作就不具备艺术虚构性了呢?恐怕不能这么决然和泾渭分明地对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予以划分,更不能因为追求“客观真实”而丢弃对文学本质特征之一的“艺术真实”的坚持和探索。非虚构写作在文体规定上的宽泛和与虚构文学之间并不是决然对垒、界限分明,也让很多研究者意识到这个概念的不明确和不很确切的方面,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似乎也都很值得商榷。所以大家也几乎都意识到了非虚构写作固然对于虚构小说“虚构”过度的现状,乃至当代文学写作传统、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审美维度等,都有其挑战、解构、重塑和再塑的意味,但是,谁又能够否认呢?这的确是一个存在着“文体边界和价值隐忧”[2]的方兴未艾的文类。
陈涛的《在群山之间》,在具备非虚构写作浓厚的亲历性、现场感和介入性写作姿态等特征之外,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与见惯了的非虚构写作或者是扶贫文学面孔不大相像的气息。《在群山之间》是作者陈涛对自己挂职甘南冶力关镇当“第一书记”的二十四个月(两年)的非虚构书写。但这本书打开来,不是压抑和迫在眉睫的所谓的客观真实,而是如水墨山水的封面下面,甘南的层峦梯田,白云朵朵,镶着金边的晚霞掩映下的山坡上,是自在惬意地吃着草、仰望着远方的牛只……《在群山之间》的封面上,这样诗意哲思的话成为全书的楔子和题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有无数个决定/但总会有那么几个决定,将你引向难以预知却又充满独特魅力的旅途。”这些话,充满诗意,暗蕴哲思,是作家在甘南两年扶贫的写照,也可以视作人生路途上的一种抉择与省思。
而壮烈秀美的风景画片多帧,一下子让全书带上了一种旷远和诗意的意味。壮美的蓝天白云远山层叠梯田图片上,也铭记下了作者的心语:“我时常站在高高的山顶/长久地向群山以及山下望去/那大团大团的白云,层层叠叠的梯田/展示着一份壮美一丝忧愁”。与金色满天的晚霞、斜坡上驻足的牦牛图片相应和的,是作家自诉的心语:“从未有过一次旅行是这般的漫不经心,/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随心随性,不克制也不壓抑自己的内心/我可能知道我下一步的目的地,/可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个确切的时间以怎样的方式到达。”这些句子是诗,但绝非硬作诗意呈现的诗语,它们其实真实地记录了作家挂职做“第一书记”两年的心路历程。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怀,其实是来自细碎繁复的扶贫履历和扶贫经历,而挂职、扶贫,通常会呈现一种令读者觉得近乎紧张感的现场感、太贴近原生态的生活真实而难免显得有些审美粗砺,或者呈现为往往是一种过于拘泥于生活真实、客观真实感的现实生活照录。
《在群山之间》本身就是一种非虚构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它又是如何在客观真实和呈现生活真实之外,葆有文学的艺术性审美性和保持着文学应该有的审美趣味的呢?与疏于艺术真实性追求的那种非虚构作品不同的是,《在群山之间》首先叩动读者心怀的,可能是这本书的写作所自带的诗意和别具能够吸引读者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审美趣味。
《在群山之间》的开篇很难让人把阅读对象,与传统和通常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以及扶贫作品联系起来。在充满诗性和散文意境美的情境与意境里面,作家将自己虽则当下已经离开甘南,但是却多次梦回自己曾经挂职扶贫过的甘南小镇,梦境里“我”与小镇街头和居住住所以及作品里反复提到的核桃树相遇,在对甘南冶力关小镇的一种如诗如画厚思深念的眷念当中,两年的扶贫经历与从自己可谓是扶贫日志的笔记里面择取而出、写作而成的篇章,就自然而然进入了我们的阅读视野。文学性、艺术性和诗性暗蕴成为整部作品的底子和底色,文学性和掩抑不住的诗性自如流淌,随着我们的阅读映入眼帘,隐现在字里行间。在读者读作品这整个阅读交流过程当中,不会有太过贴近现实而觉文学性与艺术性审美欠缺和粗砺的感受,也不会有觉得作者化生活的能力不够或者是欠缺而导致阅读与作品文本本身审美维度缺失的感受,亦不曾感觉到有过于自然主义的书写乃至有通常扶贫作品难以避免的记笔记、记账式或者作总结式地对扶贫工作经历的记录和照录。可以说,作品完全不会有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或者是工作总结之类凡此种种的担虑和嫌疑。
《在群山之间》这部书记录了作家陈涛下基层挂职两年扶贫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种种细碎琐碎的日常。看似所写皆系庸常、日常的碎片化生活,却在细碎琐碎、碎片化的生活之上,提供了一部陈涛式的“扶贫文学志”书写——既提供了一部甘南冶力关镇的关及历史、地理、人物、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的地方志书,又远非“地方志书”的称谓和归类可以定义和涵括。《在群山之间》是可以当作诗歌、当作抒情与叙事散文来阅读的特殊的文学样本——称其为“一部非虚构的扶贫文学志书”,或许是较为恰当的。
二、兼容并包的文体:兼具诗性和求真尚情的叙事散文及纪实类写作文体特征
陈涛的《在群山之间》,毫无疑问是非虚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又处处散发着诗意盎然的情怀,把它当作作家精心择取自己在扶贫工作和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和所想所思,写作并存在自己的“扶贫日志”里的篇章,经过沉积萃取,缀连在一起形成的崭新篇章,似乎再合适不过了。陈涛的笔下,是甘南冶力关镇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女孩儿晶晶会跑来送“我”六颗核桃,并嘱“我”一次吃完,“我”却要一天只吃一颗,把这美好的感觉持续很多天。甘南缺少青菜、绿叶菜,想吃绿叶菜,要通过三鲜馅儿饺子里那星星点点的青菜达成心愿。这里的青年人,朴实无华,不用下酒菜,就可以把家中自酿的青稞酒一杯杯喝个不停歇,浑然无觉中直到把所有的酒都喝光。留守儿童拿到外面捐赠的书籍和毛绒玩具,各个小脸儿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大地上的孩子》一篇,不可避免让人一下子想到了阿城的小说《孩子王》,而根据小说《孩子王》改编而成的电影的画面,仿佛就和甘南的孩子们隔代遥相应和。读到《在群山之间》里这些记事、场景和画面,再次感受到陈涛的作品生动地给我们展开了如那部电影《孩子王》中一般的画面……
《在群山之间》作为非虚构扶贫文学作品,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是作家在追求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时候,非常“尚情”。作家情怀绵密,这情怀,有对家国的,有对甘南村村镇镇山山水水的,有对冶力关镇的男女老幼父老乡亲的,有对女儿那爱入肺腑牵肠挂肚的惦记与思念……这么说吧,把纪实类作品《在群山之间》当成情思迸发的叙事散文来读,也未尝不可。
非虚构作品唯其“情真”(真情实感、情怀的真)才能打动人,但这“情真”,真归真,还不能过于峻切,亦即绝非作家本人跳入作品构建的事件现场、过多地去发出作者自己的声音,而是须将作家主体和介入性主体姿态适度后撤,用身在现场的“我”的眼睛去看,用“我”的耳朵去听,尽量与所写的人与事的立场保持同一性,能够踩在所写作对象——每个人物自己的鞋子里,用他们自己的眼光、视角来叙述事件现场所发生的一切,作家只说符合人物角色身份和世界观、价值观“视点”的话,只发出人物自己的声音。比如红霞和燕子去往高山村,向那个作者并没有写出名字的乡村女人索要她偷偷拿走的红霞的六百元钱。作家并没有用自己在场或者亲历的第一人称叙述,而是用了红霞和燕子的眼光来看周遭的一切:那在一处高地上,独门独户的女人的家,裸露着灰色的外墙,内里也空空荡荡,全是用贸然造访的红霞和燕子的眼光来看取的。女人没名没姓,但却被作家写得生动形象,很像鲁迅《故乡》里那个叉着腰,张着两脚,被鲁迅称为“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似的杨二嫂。偷拿走红霞六百元钱的女人,无名无姓,却让人印象深刻。这段情景现场的复现,不是作者急切地诉述和宣泄自己的价值判断来呈现的。这里的“真”已经远非仅仅是客观真实,还具备了艺术真实性。这里面,除了作家写作手法的巧妙运用,更多的,还是作家将一部非虚构作品的“情真”控制在了合适的度,没有妄加和过多增加作家个人的主观性价值判断。《在群山之间》是一部很打动人的情真之作、意真之作,是一部感人的作品,这与该作在非虚构作品通常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基础之上,所呈显的艺术真实和文学性息息相关。
虽则是一种介入性写作,但作家陈涛的表现,较之一般的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颇为有所不同。作家在主观性介入作品叙事方面,是很有节制的,不会过于宣泄自己个人的主观的声音,不会过多地代冶力关镇那里的人说话,冶力关镇的人们,口里说着的是他们自己的话,人物發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这就让《在群山之间》与一般的纪实类写作已然有所区分,那种过于新闻文体式地记录事件和场景的写作方式,很难在陈涛的笔下见到。作者不见得是有意,可能就是在无意当中,让自己写作兼容纪实类报告文学文体特征之余,多了一些诗性、情性和艺术性与文学性。作家没有把无比贴近现实地去摹写现实和近乎自然主义的书写方式,作为写作的终极追求,没有过于放大纪实类报告文学文体里面常常罹患“纪实性”过强、新闻深度报道特征过于明显的情况。
《在群山之间》是扶贫作品,又是非虚构写作,既具有一般的扶贫作品和非虚构写作的纪实类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纪实性较强,却又有效避免了扶贫报告文学的作者通常难以祛除的方面——作者容易自带一种“任务”意识来写作。陈涛在这本书里没有明显的预设的写作框架,虽则记录了在冶力关镇扶贫的日常和很多细节,但看不出有向组织、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意味或者是预设的功利性目的的写作意图。像《四十盏路灯》一节,不仅是以“是谁/从蓝天上扯下一抹白云/挂在了我们的脖子上/成了一条雪白的哈达/……”这样的小诗,开始了全篇的叙事,而且是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自己任职的村子的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有关自然环境描述的文字,直让人疑惑,你是否正在读一部扶贫作品?抑或真的是在读一部非虚构作品吗?读者似乎会忘记这本书所带有的——扶贫作品和非虚构作品这两个要素。这样的不急促、不紧张,不具明显“功利性”特征的叙事和叙述,自然而然带出当地村镇到了五月时节了仍有凉意的地方特色。这里的“雨”“雪”等都是实景,也是意象,是散文尤其是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常常会有的“意象”。须知,“意象”是文学作品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通常会被认为是诗人或者作家“心物交融”的产物。貌似实景的描写,却不是过于急切和峻切的叙述,这里的“雨”与“雪”,都是作家陈涛的内心与所扶贫工作之地的“物”彼此交融的产物。已经脱离实地实物和单纯的现实表象,是经过了作家陈涛内心重新营构之象,是陈涛在内心对当时路上情景和在扶贫之地冶力关镇累积的当地生活经验的重现,然后又将自己的心性和内心的所思所想与情愫,反过来融入到了“雨”“雪”以及这里的地面、太阳如何等客观的景物当中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涛《在群山之间》不仅是非虚构扶贫作品,还是极好的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具备叙事散文与抒情散文的文体特征。读者可以在阅读中有着非常舒宜的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感,这是一般的纪实类报告文学往往很难具有的文体特质,充分体现了陈涛无形中是将纪实类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与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的文体特征,作了不露声色有机的融合。需要注意的是,这几种文体类别如果硬要拼接在一起,是不行的,过下无痕恰恰显示了作家的功力。这是这本书颇为难得和难能可贵的地方之一。
陈涛在这本书里,所体现的“情真”,还表现在作家并没有刻意遮蔽和掩盖扶贫作品所选取的素材里那些不好的、并不光鲜亮丽的方面。像前文所举例,作为工作人员的红霞和燕子两个年轻姑娘去农户家里,要回被女人偷偷拿走的红霞的六百元钱,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像“我”需要坐车前往各个村子扶贫,有一次因公差和公务所搭的汽车,司机是当地的一个青年人,开车车速太快,又故意炫车技,在需要谨慎驾驶的崎岖山路上,车速快到什么程度?这辆车在山路拐弯处,从抛锚停在路边的车旁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不仅如此,这位司机根本不专注于开车,各种尬聊神聊,见自己不被乘客搭理,又给“我”讲述了他的朋友与一群人酒后驾车狂飙,导致车内六人除了司机全部死亡的故事,“我”禁不住愤怒地戳穿他话里的关键点:他的司机朋友之所以活下来了,是他的这位朋友开车时怀里坐着自己的女朋友,从而给他形成了缓冲,而女朋友却白白丢掉了性命——这位司机嘴里讲出的这本不该发生的车祸悲剧,作者很明晰地加进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却没有展开长篇累牍的说教,反而是叙事紧凑,现场感很强,情景还原得很真实,这样的叙事段落可读性强,却也将这里民风的彪悍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思想的落后、对生命逝去持有一种无所谓的心理状态——这样一些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光明”一面的选材自然而然给书写了出来,同时也没有流于峻切的批判。
如果是自帶“任务”意识写作的作家,可能会自觉规避这些方面。《芒拉乡死亡事件》一节里,羊得才夫妇把老母亲分户出去,不给饭吃甚至传说可能是媳妇给老人下了毒,夫妇二人故意在低保调整时期,将快要不行了的老人拉到乡上去,在羊得才夫妇看来这是一举三得:第一,没了母亲,减轻了生活压力;第二,母亲的丧事可以换来乡上和村里的帮忙,自己省钱又省力;三是,借机可以获得低保名额,每月领到补助。即使对于扶贫干部而言,面对这样的“风土物事”,作者也是无计可施。
《在群山之间》当中,这种没有功利性目的的合目的性与艺术性,或者是作家自带的文人气质,是挥之不去,萦绕其间的。“我”会有迷惘,会有无奈,会有觉得身处和陷入困境的时候……“我”并非一位高高在上,自觉无所不能或者是被赋予超强能量的“外来人”形象,“我”亦有喜怒哀乐、迷惘困惑与忧思烦扰的平常人心理和情思,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格外敏感善察一些。《小镇青年、酒及酒事》里,作者与小镇青年一起欢笑和迷惘,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和体味他们的忧愁。因升职进步不顺而黯然神伤的小尤,能够向“我”吐露他的心里话;喝酒豪爽的小武,酒量本就不大,多饮几杯之后,小武情绪失控发酒疯所说的牢骚,其实道出了他自己兢兢业业多年,一直事业第一,家庭第二的内心的愧疚之情……第二天,面对来向“我”为自己前一天酒后失态道歉的小武,“我”没有苛责他,反而反复宽慰他,还让他把剩下的酒带走,这不停地挠着头的淳朴的青年人,逃一般地走了。作家陈涛也完全不避讳地真情书写自己对于家人对于女儿的想念之情,完全不弃人间烟火气地直言女儿出生时,自己的第一眼,就已经认定女儿将是自己一生的软肋,自己在深夜给女儿写就的那一篇长长的情真意切的书信……陈涛这位扶贫甘南的“第一书记”,在他扶贫的地方——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践行着行前领导的嘱托:“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并且是发自内心地与当地人分享喜乐哀愁,也与他们同样承受种种束手无策,而且就像笔者在阅读当中真切感受到的,这本书完全不是单纯的工作记录、思想汇报类的写作,陈涛在后记里明确说:“从我写下第一个字时,我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于环境与工作的记录,我试图去穿透生活的表面,在展示不同群体的形象以及努力中思考复杂的人性,揭示永恒的困境。”[3]陈涛直言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他能够看到当地人的良善朴实上进等优点,也能够尝试去理解其自身的不足,在扶贫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也深切感受到需要一代代人持续不断地付出,才能真正让这个地方发生改变和焕然一新。陈涛从来不会无视和忽视自己心里的“迷惘”,不讳忌生活中那些看起来不很光鲜亮丽的方面,他对承受工作和升迁压力的青年人,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与其同喜同忧。作品没有经过“去芜存菁”地人为设计和刻意择取的选材,让《在群山之间》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加贴近真实的人生,也更能触动读者的感怀和缅想。
陈涛为冶力关镇这里的人们,写作了属于他们的小人物传记——野生民间人物杂传,散落在《在群山之间》里面。近年有研究中已经条分缕析了“为民间人物立传”和“民间世界的野生人物立传”的小说写作倾向[4]。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陈涛的《在群山之间》里,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民间小人物:养蜂人龙聃,牛人何暖阳,等等。除了这些原生民间的小人物,“我”在冶力关镇挂职结识的几位与“我”相类似情形的、挂职于此的朋友,也带着一种当地原生风物与外来者新鲜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彼此交融的气息,让人印象深刻。
具有艺术真实性和文学性追求的陈涛,所写作的《在群山之间》给人的鲜明感受就是,作者是为自己写作的,是为可以令自己倾吐心声的读者们而写作的。作家无目的地开始了写作,反而让作品格外有“情”,格外在日常生活的、寻常的点点滴滴中动人心怀。这或许无意中应了那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艺术追求。也正因为作者带着一颗朴拙的赤子之心写作,扶贫日常工作中那些再平常不过的琐事,自带了一种平淡之中悠然不尽的意味和情味、人情味,文学旨趣也因之氤氲而出。
三、非虚构写作的叙事探索及无限可能性
《在群山之间》立足非虚构,有效打通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文体界限。非虚构的客观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与作家陈涛完全投身甘南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和对于虚构小说、虚构作品所具有的虚构性手法的有效借用与汲取,两者兼取并生,催生出了《在群山之间》的独具特色的艺术真实性和能够感动人打动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正是由于文体边界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文学批评业已意识到了“非虚构写作”属实不能在强调“非虚构”和介入性写作姿态的同时,过于强调和夸大了非虚构写作的“非文学”和“反文学”的一面。在有的论者看来:第一,原初的、贴近原生态生活的“第一自然形态”的真人真事,需要进行题材和选材的择取,不能什么都写;第二,需要写的,又需“增删隐显”“贬褒臧否”,需要写作者具备识见和魄力,写什么和怎么写,被认为背后其实隐藏着妙不可言的“文学问题”[5]。
比如,非虚构、扶贫作品容易出现客观真实性过剩而艺术性、文学性相对不足的情况,稍不注意,这类作品中概括性叙述就占了上风。而《在群山之间》中,概括性叙述所占比例就极少,全书主要是一种呈现型叙述。作家意在对于人与事和场景的展示,不去充当和承担全知的、高高在上的叙述人角色,尽量避免能够俯瞰全局和对于事件、人物、场景等全知悉的无所不能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不知道陈涛是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从《在群山之间》里《甘南漫行》一节中透露出了他在写作上的有意或者无意的旨趣与文学追求,契合陈涛在《在群山之间》当中的叙事探索和文体意识。他没有将自己的写作,套上“非虚构”与“扶贫文学”的俗见的枷锁。他的写作是没有带上功利性写作的镣铐的,《甘南漫行》中这段心得,看似是对他一次漫行在自己挂职扶贫地区的山水间的所思所想、心得体会,实际上也暗合和契合了他在这部《在群山之间》当中所作的叙事探索和所持有的叙述观念。陈涛放弃了非虚构写作常常具有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也不是传统叙事散文、抒情散文的概括型叙述,他采用了“呈现型叙述”的叙述观念。陈涛似乎在有意让自己所写的对象,挣脱既定的写作理念缰绳的束缚,不要受自己太多的控制和牵制,他给了他写作的对象——甘南这里的风物人情更多的自由和可以信马由缰。在一种更加接近现场的呈现型叙述中,让自己所写的对象与自己一起去“面对那些未知的可能”。作家自带了一种充分享受自己的写作历程、写作旅程的心态和心理,不去“明晰那些所谓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反而让他的写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度,并能够真正地在写作上心態松弛下来,从而让《在群山之间》收获了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并且是与其他同类非虚构写作或者是扶贫文学作品有着明显不同的较为明晰的标识度。
一直以来,非虚构写作是作为对虚构过度的小说写作的反拨和批判的姿态,出现并存在着的。但问题是,非虚构写作自身概念内涵和外延就不是严格限定、界限明晰的。不同文体的概念区分与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几乎不存在与其他文体样式可以截然分开、完全不借用其他文体形式和叙述方式的单一性的文体样式。哪怕是在写作上呈现状态系最为信马由缰,与现实和客观真实都相去甚远的武侠小说、玄幻网文小说和科幻小说等,都不可能做到纯粹和完全建基于虚构和想象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和客观真实性原则。如果作品纯系虚构,假若完全没有客观真实性的细节化叙述的存在,没有与生活和现实吻合、接近的细节与场景等,这些作品本身就无法具有可信性,无法勾起读者在少量和部分的“已知”当中,去追索“未知”的渴求和阅读欲望。这样过于地脱离现实甚至毫无现实质素可言的作品,是否还具有可读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反之,如果非虚构在纪实与客观真实性叙述基础之上,完全不借鉴和采纳虚构小说的写作手法和叙述手法,恐怕也会大大折损和失去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以及事件所关及的人、物,作者恐怕不可能仅仅是充当一名对新闻事件或者是故事素材予以客观记录的记录者、新闻纪实性记事者的角色。能对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和人与事等,巧用虚构小说的一些叙事手法,予以符合艺术真实性的还原和呈现,是作家陈涛于《在群山之间》当中所作的有益的叙事探索和写作尝试。
前文已经述及的,作家陈涛在这样一部介入性写作姿态非常强烈和浓烈的作品里面,却在叙事上很有节制,不让作家主体过多地作主观介入性叙事,不大喜欢采用或者是有意放弃了新闻报道、深度报道、纪实类报告文学等常常采用的全知视角,作家并不过多发出作者自己的主观的声音,让笔下的人物说着他们自己口中的话,冶力关镇的人们发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作家可能只是意在“呈现”这里的人与事,而不是将这里的人与事概括和总结给读者或者是有关部门以及上级的领导。
介入性写作姿态的非虚构写作,强调在场性和亲历性。写作者对于写作对象而言,始终在场,他自己要亲自参与和见证着所发生的一切和一桩桩事件,并且全程参与其中,真实记录着所发生的一切,故也被称为“行走”着的文学。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与事件和人与事的强关联性以及在场性、亲历性、介入性等写作姿态,导致作家的视角天生就已经出现在了每一个叙述场景当中,无法回避;但也不能让作者的视角权限过大,作者视角过于侵入叙述,就会让原本有限的叙事资源更加地捉襟见肘,更加地被拽向现实的地面,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羽翼更加被折断或者是受到伤害。而且既然在场、亲历,作家就不可避免要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这所思所感写好了,会锦上添花,写不好,会让读者读来味同嚼蜡。
而陈涛《在群山之间》非常打动人的一面,就在于他的所思所感真切感人,能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陈涛反复书写的镇政府院子里的两棵核桃树,为读者所瞩目。陈涛在对核桃树的书写中,其实寄寓了他的所思所感所想。这所思所感所想,由于作者在叙述上的巧妙剪裁和用心、用情,文字上的取舍合理,格外动人和感染人。作者在透出的是对自己待了两年、工作并生活过的地方的自然、真实和淳朴的感情。但是伴随月亮升起来的,竟然还有自己心里的一份“平静的难过”,看来作者寄寓在这里的感情是平静居多,难过仅占一分,虽则仅占一分,却不是没有。这“一分”,或许是想念家中的妻子女儿,或许是日常扶贫工作中的种种甘苦琐碎辛劳……作家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情感过多地渲染和宣泄,却是在自然环境和核桃树、白云、远山、天空、月亮等的自然景色当中,寄寓了自己真实而感人的情感与情思。在《另一种生活》这一节标题下,在形式上差不多是作为该节题记出现的小诗:“在生活严格训练下,/紧绷的身体,费力攥紧的拳头,/以为已然抓住,殊不知松开之后才是真正的拥有。”这些诗性的语音,哲思满蕴,实际上是作家陈涛基于自己身在现场的生活体验,加上自己的文学素养和修养,加以重新建构而成的文学的审美空间。这个审美空间的维度是丰富而丰赡的,引人遐想乃至深思。
阅读《在群山之间》,如上这样的诗性语言处处皆是,一点都不稀奇。而这部书别具特色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叙述上独具一些优势和专长。作品叙述节奏自然流畅,很少用长句,多是高低错落的短句,将汉语古雅有韵味的一面融入现代汉语的剪辑和叙述当中,去除了白话文尤其是非虚构作品容易罹患文字和语言表达不够优美的弊病,在对事件的叙述上又能够充分调动身在现场的“我”的眼耳口鼻等各种器官和感官的动能,形成一种比较快的叙述节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如果是在叙述一个故事、事件,就会充分调动读者的各种感官、感觉和感知能力,去体会和捕捉在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让人产生如在现场的艺术真实性的感受。这在非虚构作品尤其扶贫类非虚构作品普遍缺乏惊心动魄的戏剧化冲突的场景和事件的还原与叙述当中,让作品能够有效借鉴虚构小说的一些虚构性叙述的手法,有效弥补和完善了非虚构作品在叙述与文体上的局限性及不足之处。作家陈涛从来也没有想代冶力关镇这里的人物说话,但他却把这些人物活生生、栩栩如生地带给了我们。
陈涛的《在群山之间》,图文并茂,其中的摄影作品也是令这部书得以增色之处。在叙述和文本呈现上,二者形成“互文”的效果,摄影作品还可以被视为是文字内容的“补白”或者“画外音”。在叙述学家看来,作品的文本形式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文本(物质)形式,它是作品叙事的有机构成部分。如果有有心者,或可以对《在群山之间》当中的摄影作品乃至包括题记小诗等,都加以考虑和研究。陈涛以“情真”的写作,给予了我們《在群山之间》这样一部感人的非虚构的“扶贫文学志书”;不仅如此,《在群山之间》所开启的——对于非虚构写作所应该持有的文体开放态度,对于非虚构作品所应该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叙事探索,等等——都给予了非虚构类写作本身以有益的思考和启迪。
[注释]
[1] 陈竞:《文学的求真与行动——文学报专访李敬泽》,《文学报》,2010年12月9日。
[2]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谈起》,《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3]陈涛:《在群山之间》,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页。
[4] 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1—262页。
[5] 吴秀明主编:《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