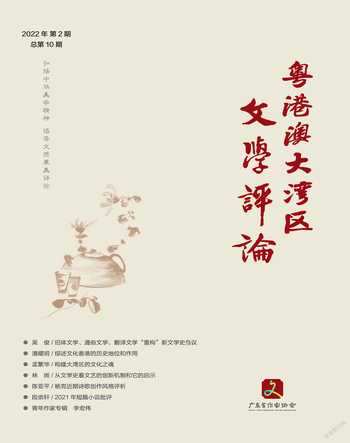少数族裔的原乡想象与文化对话
龙扬志 唐明映
摘要:作为一位游牧于母族文化、汉文化、西方文化交错地带的白族诗人,冯娜的诗歌体现出鲜明的跨族裔文化特征。当她将本民族文化弱势转化为德勒兹所说的“一种光荣”与主流诗歌对话,也构建了自我与自我的内在对话。诗人通过不断回溯自我精心搭建的“原乡神话”追寻民族文化血统的核心,地方经验既体现出主体的再造,也彰显了诗人作为少数族裔面临现代性语境的文化身份。由民族文化遭遇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撤退与融合,折射出少数族裔原乡书写持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冯娜;族裔;游牧;原乡;身份
于云南丽江藏族聚居、多民族杂居的群落出生,又在沿海现代大都会求学、生活,白族青年诗人冯娜选择用汉语书写神秘的原乡,這一抉择作为飞散视角的彰显,无不体现出“抵制文化上的同化,而以跨民族的眼光和文化翻译的艺术进行新的文化实验和实践”[1],形象地反映出冯娜诗歌创作的吊诡之处。
作为上帝放逐犹太人的隐喻,“离散”在当下文化语境里泛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2],根据美国人类学家阿帕杜莱的说法,跟随社会革命进程跨入现代社会并逐渐“文化混血”的少数民族群体,某种程度上也是家园的失落者和文化的流散者。审视当下边缘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故乡”这一“折射某一历史情境中人事杂错的又一焦点符号”[3],更深刻地触及了历史的沉痛与复杂。正如王德威所说:“‘故乡的人事风华,不论悲欢美丑,毕竟透露出作者寻找乌托邦式的寄托,也难逃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意识形态兴味。与其说原乡作品是要重现另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不如说它展现了‘时空交错(chronotopical)的复杂人文关系。”[4]
作为一个游牧于母族文化、汉文化、西方文化交错地带的少数民族诗人,冯娜的汉语诗歌创作可以视作拨亮自己执掌于大地的灯芯,引领读者与其一同梦回南诏的招魂式书写。冯娜将本民族的文化弱势转化为德勒兹所说的“一种光荣”,在构建与主流诗歌对话的同时,也构建了自我与自我的内在对话,她不断反诘自己精心搭建的“原乡神话”,由此折射出少数族裔原乡书写的复杂景观与文化困境。
一、异域的“寻鹤人”
彩云之南的丽江怀抱苍山洱海,背靠澜沧江和金沙江,诸多少数民族群聚于此,东巴、藏传佛教、本主崇拜、道教等宗教信仰相互生发,民族文化自独立又相互交错,造就了一片令人目眩的神巫之地。对汉语作家而言,异域书写可能无法避免中原文化中心对“他者”的猎奇,而将藏区塑造成一片天涯海角式的神圣“乐土”,[5]对于生活于其内部的诗人,文学已是与母土血脉、族群记忆天然契合的灵魂歌唱。冯娜曾如是谈及自己的写作:“丰饶的大自然和边地人情风俗所赠予我的想象也好、幻术也好,已经成为我心性的一部分,它们在书写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浮现和托付,就像山涧飘落的马缨花,我只需要倾身为一条清冽的河就可以承载它们。”[6]
冯娜想象幻术里自然浮出的原乡,和汉语主流诗歌显然保持着某种不可跨越的距离:“在云南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让它顺从于井水”(《云南的声响》)、“七月初七我们把山峦还给大地/把豹子还给深山/再把无端的爱和怨和还给菩萨”(《流水向东》)、“被他抚摸过的鹤,都必将在夜里归巢”(《寻鹤》)。“菌子”“大象”“豹子”“山峦”“鹤”与“菩萨”,这个我们既亲且疏的云南显然不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云南,而是“带翅膀的云南”,既有一个山地民族与自然相契合的野性想象,又有人与神灵的感应,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气质,又撇去了汉语诗歌90年代以来的日益空洞和琐屑。这想象的原乡,如王德威所言,内蕴着“一种偷天换日式的异乡情调”[7]。冯娜已然走出了象征女性被围困的黑夜意识,她不断潜入自己编织的原乡,向外界展示那个既辽阔深沉又神秘多情的神秘村落,同时尝试以诗歌承载整个族群的生存图景和历史记忆。比如:诗人写居住的村落和生活:“他们被云埋葬悄悄地度过了这一生”(《云中村落》)、“捡拾菌子要持续几个月,雨水好的年份/从江边开始,向深山慢慢推移”(《采菌时节》);写群落的婚丧嫁娶:“走到石榴树下/向从未谋面的神灵/说出婚俗中不会有的那部分”(《婚俗》)、“春天盛大旁若无人/多么的喧嚣的葬礼只有一个人不再听见”(《春天的葬礼》);也写族群与大地的神性交融,一场雨能写得惊心动魄,庄严神圣:“先知们打开伞状的感应/漂浮的生灵和魂魄呼啸着扑进大地的身体”(《大地丰沛如容器》)。大地上的粮食和人事,熟悉事物的来临与远去,冯娜迥异于吉狄马加、阿来等作家在男性视野下展开的粗粝广阔的书写,而是以女性自有的细腻再现族群在大地上的生活,看似柔弱无骨,却余味悠长,自有一种逆水回流的力量。冯娜采摘云南大地的心脏,恰如一只纤柔蝴蝶飞过沧海的姿态。
在关于“水”的“御风术”里,冯娜这种直抵民族文化血统核心的能力或许得以淋漓尽致的彰显。众所周知,白族对“水”的崇拜由来已久,作为一个逐水而居的民族,白族的本主神话[8]保存了大量涉及水神崇拜的篇章。无论是龙神锁洪,还是平民求得龙神降雨而被奉为本主,抑或段思平父子制服恶龙的英雄事略,都蕴含着白族先民对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的复杂体认,也是白族文化极具生命力的文化源头。这些曾在白族先锋诗人栗原小狄的诗歌写作中绽放异彩的意象群,也构建了冯娜“原乡神话”中内涵深邃的主题,比如生与死,爱与轮回。《金沙江》《流水向东》《沿着高原的河流》《龙山坝的夜》《夜过凉水河》《他留河》《洱海》等诗歌,仅考察其标题,冯娜对“水”的迷恋在“原乡书写”中的分量就可窥见。“她爱她漂流/她殉情”(《龙山的女儿》)、“你是我爱美的姐姐描完尘缘左边的眉棱/飘向下游去做河伯的新娘”(《画眉》),冯娜多次以近乎唯美的痴情,痛苦追忆殉情于金沙江的姐姐,由此缅怀那些站成了水中礁石的“女人”,“金沙江”的“水声呜咽”与“河伯的新娘”让“水”与人的生死纠缠在诗歌中被表述得既沉痛又凄美;而《澜沧江》里,这种沉痛被更为有力的声音代替:“仿佛一万年前我的心被这一江水啄空/在此后心痛的岁月里缓缓返还”(《澜沧江》),带走了“远方的婆姨”“近处的娃娃鱼”,“啄空”了“我的心”,却又在轮回里寻回救赎,“此后心痛的岁月慢慢返还”。看似简练的语言中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与族群记忆,让整首诗的情感几乎满溢:这并非对时间循环、命运轮回的简单体认,内中的慈悲与救赎,来自对族群文化的认同和传承,也来自其对自己民族文化矿藏的深入挖掘。白族的本主崇拜,东巴教的自然崇拜,佛教的定命运轮回,相互渗透,彼此兼容,这些早已化作了一种文化潜意识,渗透到诗人的血脉之中。换一个更具体的表述,即“我体内的一斛酒取它的上游”,故“我要喝光这下游的孤独与慈悲”(《夜过凉水河》)。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冯娜不自觉地幻化成她笔下的“寻鹤人”,而云贵高原上所拥有的一切,亦成为冯娜一次次回返精神原乡的理由。她一次次抚摸这些族群文化的魂器,以求它们“在夜里归巢”。事实上,类似“世间的猛兽良禽虫豸/还有会唱歌的他留人老死时/会和植物一样/只靠水带来干净的音讯”(《他留人牧歌》)式人与大地共同呼吸,轮回流转的和谐之境从来都是人类的幻想,在如今的后现代社会,更近乎一种乌托邦的梦境。冯娜的“故乡”作为“被看者”对主流汉语诗歌的回应,因而构成了一种货真价实的“异域情调”:她让祖先在纸上凝视守望,如澜沧江亘古不歇的轮回。
二、游牧者的跨民族书写
如果将冯娜的“原鄉”书写仅仅视作一种有关文化乌托邦的建构,恐怕低估了冯娜原乡叙写的复杂性。冯娜的书写并不局限于一种固定的单一视野,她试图寻求“完整地拥有这座山”的“好姻缘”(《良辰》)。正如童明所言:“流散者并非纯正地保持他家园的文化传统,而是将家园的历史文化在跨民族的语境中加以翻译,形成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更丰富的语言(greater language)”[9]笔者所关注的是,居住于文化夹缝间的游牧者,“更丰富的语言”是如何参与到冯娜的“原乡世界”的建构中来,并构建一种多元互补的声音。霍俊明认为,冯娜诗歌有地方空间和曾经生活片段的放大性撷取,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人事、场景和细节都被情绪和知性过滤化了。[10]换句话说,冯娜对于地方经验的描述充满了强烈的主体再造意味,契合了她作为一个少数族裔观看/凝视现代世界的方式。
考察冯娜近些年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其诗歌所依存的三个地域版图:首先是作为母土的云南,其次是广阔的西部藏区与其他少数民族群落,然后才是“除此之外”的现代世界。有意思的是,漫漫十年的在外游历并没有让现代感思在冯娜的诗歌中占有多少分量,甚至作为“第二故乡”的岭南之地,也并非诗人着意建造的自足世界,充其量只是原乡世界的某种对照,但它确实构建了一种中心——边缘的对话关系。
这种对照被她内置于诗歌中,组成一种诗性的时空关系:“一日千里,浩浩汤汤/日头还来不及落下,你的爱就越来越短”(《速朽时代》)、“这一趟小旅行芒果树和小三角洲/帽子插满风和野花的日历/一页被火车带走了,发出轰隆隆的回声/一页在日光里变质”(《火车向东》)、“要不是路过这里/去向哪里已不再重要”(《车过增城》)。我们也发现,在为数不多的诗歌中,岭南始终是一个永远行进在路上、即将抵达却永不抵达的地方,内中的疏离之意并不难领会。
相似的境况也出现在她游学京城的作品里(她曾以驻校诗人身份入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比如《陪母亲去故宫》一诗,冯娜将滇西与北京的关系喻为“尽管门敞开着,钥匙在拧别处的钥匙”。北京作为某种权力中心的象征,在冯娜的诗中散发着一种困惑的犹疑:“不知这里的鸟是否飞出过紫禁城/不知鸟儿可否转述我们那儿的风声”。在冯娜最近的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中,“雾中的北方”被用作其中一辑的命名,显得意味深长。事实上,“雾中的北方”作为南方的参照,尤其作为诗人所着意搭建的远离于现代生活的原乡世界的对照,“大雾就是全部的北方/即使在创伤中也只能试探他的边沿”(《雾中北方》),更多强化了诗人家园失落的撕裂和对故土的坚守,“一个观光客手中的礁石长不出稻谷、土豆、耐涝的食粮”(《在外过冬》),以至于连梦中也要哽咽出“南方口音”。这样一种缺乏认同的异域感知,深刻地反映出背后的文化疏离。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冯娜对少数族裔怀着别样的亲善,因此不少藏族、彝族、维吾尔族人不断进入其视野,她曾说:“我对云南、西藏、新疆等遥远的边地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血脉中相通,这不需要有意识地强调;这些地域的风无声无息但一直吹拂和贯穿在我的写作当中,它将成为一种内心世界的风声,而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11]边缘与边缘的对话构成了与中心—边缘对话外的另一重声音。“我们用汉话划拳/血淌进斗碗里”,“大儿子上前斟酒没人教会他栗木火的曲子”(《与彝族人喝酒》),“我是未成熟的青稞地孤独匍匐”(《青海》),“年少的僧侣疾步走向经堂/他们红色袍子扫过高高的台阶/石阶沁凉/坐在上面像另一个朝代的遗民”(《晚课》),同样的“失语”姿态,同样游离于中心之外,关于这些边地的书写与冯娜的云南原乡构成一种互文。事实上,丽江白族与纳西、彝、藏、傈僳、普米等族同属藏缅语族族群,长期群聚于同一区域,并与西北的氐羌族群书渊源不浅,算得上是同源异流[12]。某种意义上书写这些边缘少数民族也就是书写自我。就此层面,冯娜的书写验证了德勒兹关于弱势文学的观点:“如果作家身处他自己的脆弱的社会群体的边缘甚至置身其外,那么这一局面反而更有利于他表达另一潜在的群体,锻造为另一意识和另一敏感性所需的手段”[13]。可以说,这是冯娜继栗原小狄之后给当代诗坛提供的白族文学新视野。
三、“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惟有这样的人可以返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乡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返乡时得以有足够的丰富体悟和阅历”,[14]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如是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然而在今时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中,尽管冯娜在诗歌以“异域情调”幻化一个神秘的原乡,那么“还乡”是否意味着流寓于现代性境遇时实现自我救赎的一种可能?
冯娜在诗歌中不断追叙其家世,“曾祖父以前的亲人都埋在异乡……他站在高高的石碑后面说话/石头吸附了他一部分声音:不要在意家世里失传的部分——/如果死后能在这里埋骨”(《家世》),“颠西北的云是粉红色的/是我流着泪的母亲送走她的父亲时未落下的夕阳”(《云上的夜晚》),当冯娜把云川的山川风物编成最柔软的诗句时,这些追忆家世迁徙流离的句子也就构成了对“原乡”的自我反诘。在她的诗歌中,还乡被处理为一种未完成时态:“如果能在这里埋骨”“我的祖辈怀揣许多迁徙流离的故事,有些故事充满盛衰的悲辛,但会让人感到一种诗意,以至于我觉得祖辈骨子里携带着一种‘诗人的基因。”[15]而充满盛衰的生命个体构建的家族记忆,事实上也就纳入到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冯娜对家族历史的追溯,远溯初唐以来千年间的王朝交替,在族谱失散、记忆失据的总体背景中,这一点尤显意图深远。少数民族在贵州西部汉族政权的不断干涉引导下,南迁鹤庆、丽江以求繁衍。因此,对这一充满流徙历史的尝试性建构,冯娜的书写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后现代语境下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的重构。
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体验过浮世变换的流散者,当诗人回返那个“豺狼”、“松茸菌”、“不懂汉话”都需要假设存在的故土,失乡之痛也成为唤醒书写欲望的重要理由。当一个白族人在祝酒词里悲叹:“我不知道你们在他耳普子山活了多少世/我也活成了一只没有故乡的猛禽大地上的囚徒”(《一个白族人的祝酒词》),“命运拿走的,他留河会全部还给我们”的祝酒词也就成了这酒所制造的幻觉。“回不到的故乡”是诗人刺痛心扉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全球化语境下,不管是否愿意,所谓边地也早已不得不席卷进这汹涌而来的现代潮水,哪还有一片千年如旧的土地,当诗人们千辛万苦跋涉于回乡道路的同时,民族内部也早已遭遇不可回避的某种颠覆和拆解。以技术为支点的现代性是如此无孔不入,已经没有一个静态不变的故乡,不论主动还是被动,民族文化注定处于一种与外界对话、寻求新变的状态。正如故乡在跋涉还乡的路上不断被自己的想象美化、虚构,当它成为精神层面的“原乡”,已经不可避免沾上了某种镜花水月的气息。“回不去时回到故乡”(杨炼)正是所有游离于故土之外的流散者面临的命运。
事实上,当诗人写下“山上若还有不懂汉语的人请他饮酒”,他已经洞悉了“金沙江无人听懂”的秘密。语言作为存在的家,也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关键要素。当“土话”“失传”,失语的焦虑注定成为少数族裔发声者无法绕开的困境。少数族裔依托汉语进行原乡书写也构成了“回不去的故乡”的表征。在冯娜的诗歌中,“异乡人”一直是其重点着墨的部分。比如:“我以为我会遇见一个远游的人/ 听他说起长路或者他乡/此生——仍深陷于坝子的腹部”(《龙山坝的夜》)、“我们把豆子抛洒在返家的小路上/一个人蹲下来:他是真的走不动了……”(《一位朋友客死在异乡》)。“永无归依”如“沱沱河的鱼群”,构成了冯娜关于异乡人的凄凄想象。“我离开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出生地》)式的体悟将诗人捏合成一个出门寻找故乡的人。这看似悖论,但却隐含着一种原乡失落的焦虑。那些用无数想象搭建的“带翅膀的云南”成为“面目全非的云南”。冯娜诗歌写作的行程,也是漂泊者告别母语、穿越汉语的矿藏重新踏上寻找文化之根的旅程。彝族学者阿库乌雾曾说:“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书写形态的被颠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而以汉语书写作为语言策略,实际上意味着“必须以自觉体验、颠覆母语文学传统,甚至颠覆母语文化传统的精神失落感为前提,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对民族文化传统母语文化‘元叙述方式加以全面背叛”[16]。
德勒兹在《卡夫卡》中曾言及弱势文学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主要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17],它寄居于多数族裔文学内部,开辟自身的言说空间,在面对汉语压迫性的主流地位时,与汉语进行文化混血的少数族裔诗人,如何在文化翻译中寻求对自己民族文学差异性的保存,而不至于“失语”并锻造自己民族文学新的血脉,正是冯娜在诗歌中不自觉地承担的一种使命。当然,如何在这种对话中通过容纳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美学追求建构言说的主体身份,恐怕不仅是这位“80后”诗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少数民族诗人在文化身份和民族性建构过程中必须持续面对的挑战。
结语
不管自觉与否,冯娜在诗歌中精心搭建的原乡神话,实际上构建了一种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的对话,并在自我的不断反诘中折射出少数族裔原乡书写的可能。德勒兹说:“对于这种文学来说,弱势乃是一种光荣,因为弱势对于任何文学都意味着革命。”[18],对于冯娜这样一位年轻诗人而言,尽管她在阅读中西诗歌并有着广泛游历的经验,其诗艺无疑还存在广阔的进步空间,也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也不能再歌唱回不到的故乡”,原乡或许应当成为策动再次出发的精神驿站,把自己置入更为开阔的文化空间,在不断自我诘问中,深化文化关怀和语言命运之思考。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她的游牧书写能让自己成为自己语言中的吉卜赛人。或许,卡夫卡给出的答案能满足我们全部的期待:“把婴儿从摇篮里偷走,在垂直的绳子上面起舞。”尽管这看起来困难重重,却值得不断尝试。
[注释]
[1][2] [9]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分散视角》,《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3][4] [7] [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页。
[5] 可参看支教藏区的诗人的《雪山短歌》,虽然马骅极力在诗歌中隐去中原文化的中心姿态,但支教背后的隐居姿态,仍未能完全抹去汉语诗歌对藏区的乐土想象。
[6] [11] [15]冯娜、王威廉:《诗歌和生命的“御风术”——冯娜访谈》,《山花》,2014年第9期。
[8]本主,又叫本主神。白语称之为武增、武增尼、增尼、本任尼、老谷、老太、东波、吾白害等, 意为我们的主人。汉语中的本主一词,早期记载为本境土主、本境恩主、本境福王、本郡之主、眾姓之主、一方之主等,本主一词是简称。参见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0] 霍俊明:《黄昏中摁下世界的开关》,载《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冯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12] 参见杨文顺《丽江白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初探》的论述,文中还提到据纳西族东巴经《创世经》记载,人祖崇忍利恩与天女衬红褒白命成婚后,生下3个儿子,但长大后不会说话,后派蝙蝠上天侦知,诚心祭天可使儿子说出话。果然,祭天之后一个早晨, 3个儿子来到门口蔓莆田里玩,突然跑来1匹马,拼命吃蔓莆,3个儿子着了急。老大用藏语叫:“达尼芋,玛早” (马吃蔓菁了)!”老二用纳西话: “软尼阿肯开(马吃蔓菁了)!”第三用白语讲:“满尼左各由(马吃蔓菁了)!”于是一母之子变成了3个民族。这个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3个兄弟的传说反映了丽江白族与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25卷第3期。
[13] [17][18][法]吉尔·德勒兹 、[法]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组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第47页、第47页。
[14]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页。
[16]罗庆春(阿库乌雾):《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3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华商务贸易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