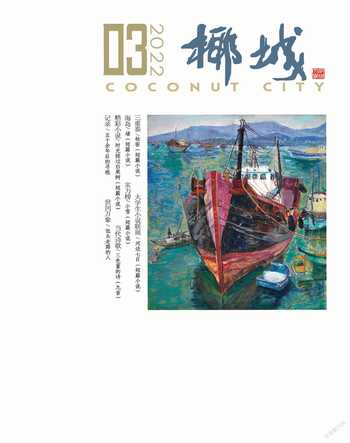低头走路的人
◎马卫巍
姥爷活着的时候,曾是个极度吝啬的人。其实,“吝啬”一词从我这里表述出来不一定准确,况且词汇运用也不一定到位,他应该比吝啬还要严重。这种吝啬与他的外表呈现出格格不入的对比,换作其他人表述,绝对不这么认为。在其他人眼中,姥爷却表现出一种波澜不惊的独特智慧。
他的吝啬是我强加给他的。他不会准备花生、瓜子和糖果招待我,最多买几根已近干涸的甘蔗,长短大小不齐,应该是在卖甘蔗处剩下的残次品。若碰上他大方地拿出几块糖来,准是这块糖快要融化,用以包裹的糖纸已全部粘住了,需要很费劲地舔下来。他也会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几块麻酥,那么你要小心了,它们的坚硬程度堪比石块,会冷不丁地崩掉半颗牙齿。
在我的印象里,他喜欢低头走路,倒背双手,上身前倾,像有心事般缓慢而行。他已经在三年前故去了,要不然他会一言不发地用眼神和我对质。他的眼睛已经太过浑浊了,并无波澜也不清澈。眼球上面罩着一层暗黄色的薄膜,薄膜后面是无数个关于他的故事。他把故事装进心底,不愿意和其他人分享,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波澜不惊的处事风格,很容易伪装成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在他的视力范围之内,不一定看清我在哪个方位。我尴尬地咳嗽一声,他才慢慢转回头,暗灰色的眼神游离了过来,眼神是柔和的、模糊的、流动的,让人稍感安慰。
若他活着的时候对着一棵树、一盆花或者一只猫久久凝视,那么请你放一百个心,他针对你的眼神已在这种凝视中消散了。他的思绪慢慢飘动,撞开心扉抵达远方。他会用眼神长久地答复你——然后低下头走了。
他是荒原乡村中非常普通的退伍机枪手、杀猪人和老木匠。这些身份集于一身也并未给他带来特殊光环,芸芸众生中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舅舅家的表弟和我讲,小时候跟着姥爷赶集,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钻进人群消失不见了。表弟到处寻找他,炸油条处、卖烧饼处、卖花生瓜子处、卖烤地瓜处、卖糖果处……这些地方都没有他的身影。表弟像一条受了委屈的小狗,在人群缝隙里钻来钻去,赶集的乐趣变得索然无味,就连通过变戏法卖肥皂的表演也没心思观看,只好低头耷脑地返回家了。表弟怀疑他是否来过集市:来的时候,明明拽着他的衣角来着,却转眼不见了踪影,连个脚印都没留下。这种情形像被冬天的风雪掩盖住了。雪花之下,脚印与大地还能分辨出来吗?两者之间貌似没有直接的关联,大地承受了他,却也遗失了他。
表弟回家之后,却发现姥爷早已回家,并且正收拾一挂猪肠子、半个猪头或是已经有些烂兮兮的小青鱼。他坐在院子里,脸上并未因舍弃我的表弟而感到不好意思,反而招呼他赶紧帮忙。
他有各式各样的刀具,尖的、圆的,长的、短的,宽的、瘦的,这些刀具被他整齐地叠放在一起,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他十分熟练地将猪头分割,耳朵、口条以及猪脸儿;他给小青鱼开膛破肚,把已经发黑的五脏六腑收拾干净,用清水泡了;只用一根筷子就能快速地把肠子翻过来,洗净上面黏糊糊的粪便。他对这些事情乐此不疲,并用盐水、碱面、白酒等,消除掉令人作呕的腥臭。等这些事情做完,阳光已经跳到墙头的另一边去了。他泡一壶浓茶,看着眼前的一切,兀自笑了。
我曾见过姥爷的刀具:一把扁长的剔骨刀,还有一把宽绰的大砍刀。它们早已失去昔日神采,被扔在炕头下一处破洞里。刀身锈迹斑斑,并不尖锐和锋利,岁月把它们侵蚀得不成样子,灰头土脸毫无精神,如一头受伤的老狼,在昏暗的巢穴里独自寂寥,回忆旧时光,熬过风烛残年。
关于姥爷年轻时杀猪的经历,我听舅舅说起过。这并不是他的专业,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那时,荒原上的杀猪人是一种职业。他们与猪肉商贩不同,只有碰到哪家过寿、娶妻或添子添孙,才会被请去杀猪取肉用以招待客人。杀猪人往往不收取费用,杀完猪脱了毛将肉分解后挑半挂下水算是报偿。姥爷经常拿回一只猪耳朵、半边肺叶和肝叶、一只猪心和半挂大小肠,足以让家人兴奋不已。舅舅说,可别小瞧这半挂下水,在那个年代可是最美佳肴,清苦人家能吃上这些已经不错了。有时为熟人杀猪,姥爷表现出特有的矜持,只拿回四只猪蹄子。
有回,我在姥爷家住宿,他弄回一个猪头来。他耐心细致地刮着尚未褪掉的猪毛,动作比绣花还要仔细。他的手顺着猪头的顶部缓缓向下,绕过耳根,然后在两只眼睛处用食指和拇指把稍微硬长的毛发拔下来。他的眼睛已经花掉了,只能时不时地把猪头举起来,对着阳光的缝隙找寻尚未拔掉的硬毛。他长久地与一个猪头对视,让我生出莫名其妙的幽默感。他把猪头揽过来,自己的脸差点碰到猪耳朵或者猪嘴唇了,依然没找到那根刺刺的长毛。对于猪头上面的硬毛,他有着近乎疯狂的密集症隐患。他架起火堆,用一根铁钩子挂着这颗硕大的猪头熏烤,火烧毛发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让我的心脏都跟着缩紧。这种声音像硬铁相互碰撞发出的尖锐的呼啸,貌似要把耳膜刺破。
我不敢与这颗猪头对视,它紧闭着的双眼会在烟火的熏烤下突然睁开,冒出一道道灰沉沉的暗光。它的耳朵随着火苗的大小上下摆动,好像一对翅膀要带着这颗头颅飞起来一样。姥爷可不管这些,猪眼睁开后,他会用刀子迅速在这四周刮上几遍,那对眼睛只能不甘心地重新闭合了。
熏烤不过半刻钟时间,姥爷把猪头弄下来,然后烧化一锅浓稠的松香。松香块呈现出一种暗金色,迎着阳光时,更像一块巨大的钻石,光线被它不规则的棱角切割得零零散散了。开始时,松香的味道奇特无比,像小松鼠嚼了松果,弥漫着松林中的静谧气息,可松香彻底融化沸腾后,却有一种腥臭焦糊的味道,让人干呕。他把猪头放在松香中轻轻转动,确保每个部位都能粘上这些稠糊糊的东西。多年之后,我还能记起那种味道,顺着心底丝丝游离起来,然后涌入鼻腔。不过,那种味道已被岁月消磨掉了,继而变得软润起来。我觉得自己的胆量还可以,不至于被一个裹满松香的猪头吓到。松香冷却后没有了晶莹的微黄色光芒,它色如沥青,在猪头上面炸开一道道干涸的裂口,狰狞如头困兽。姥爷粗暴地把松香撕下来,随着松香片的脱落,撕裂下更为纤细的绒毛。他在做这些事情时,我总感觉脸上也糊了一层厚厚的松香,每脱落一片,脸上也跟着火辣辣地疼痛。这个过程尚未完成,我已经捂着脸快速逃离了。
松香全部被撕裂下来后,整颗猪头突然变成了洁白如绸的艺术品,即便火熏之下的灼黄色也有些柔软色泽了。两只眼睛里的暗灰此刻如玻璃般晶莹透彻,似有水流。姥爷沉浸在自己做成的艺术品中不能自拔,翻来覆去不断观看,直到心满意足地下锅煮熟。我惊奇于所有变化,缓慢之间,姥爷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他这般操作一气呵成,从未拖泥带水,每一道工序细致而又粗暴,最终使这颗猪头完成了华丽转身。此刻,所有的焦糊味道已飘无痕迹,香气在铁锅中旋转、激荡、漂浮,整个院子都充满了迷人的肉香。
我犹记儿时与表兄弟们捉迷藏,会经常藏在他打造的橱子或箱子里,印象最深的则是躲藏在他打造的棺材中,或躺着、或蹲着、或倚在一角看外面的动静。我在姥爷家最常见到的是凿子、刨子、锤子、锯子以及大大小小的钉子。他年轻时曾走街串巷打过家具,包括橱子、桌子、椅子、凳子,至于打造棺材则是顺手的活计。
荒原上的老人多有临终前置办寿材的习惯,自己出木头,然后把姥爷请了去。主家烫一壶老酒,烧两个小菜,算是开工大吉的仪式。主家多准备柏木、松木或者榆木作为原材,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则选择保存长久不易腐烂的柳木。姥爷和舅舅两个人配合,用两到三天时间完成了这项最为朴质的手艺。姥爷从一名操作者俨然成了指挥者,他只打量一眼主家的身高便知道打造棺材的具体尺寸,然后指挥舅舅解木、打线、做好标记。他目测好木板长短之后,墨斗中的线便从这边直直抽了出去。他伸出的指头有点像戏曲里的兰花指,轻扬之间便把墨线弹好了。墨线撞击木板,上面的油墨精准无误地打下来。两者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一条笔直的黑线映入眼帘,墨线撞击木板抖落的碎点,像银河里的繁星。棺材做成的那一刻,从主家的眼神中能看出满意之色。他们的赞美之词让姥爷沉醉,会用剩下的边角料做一两个小凳子,抬抬手的事,用不了多少工夫。
我不理解姥爷为什么会对木匠的身份如此偏爱,但他又不得已放弃了打造桌椅板凳的活计,从而专注于打造棺材。桌椅板凳已由传统的手工制作转为机械化批量生产,这对于作为荒原老木匠的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无法逆转潮流,只能默默承受。好在打造棺材的时候,他还能找到手握刨子、凿子和锯子的快感。他年迈不堪了,舅舅则成了他的精神支柱。这还不成,他又把我的小姨夫叫了过来,并郑重其事地递给他一个使用多年的老墨斗。我能准确地回忆起小姨夫接过墨斗的样子:简直诚惶诚恐,受宠若惊。捧着这么一个脏兮兮黑乎乎的东西,内心到底起了什么波澜?这不是黄金疙瘩,也不是手雷炸弹,却有沉甸甸的分量。这个墨斗让我小姨夫过早地佝偻了脊背,他的头发也在四十岁之前变得花白了。
姥爷喜欢坐在一旁看两人做活,还时不时指点一番。木屑中漂浮着令人沉迷的味道,而这些碎屑又像冬日里激扬起来的雪花。雪花落到头上,散发着下午茶里的晶莹。姥爷迷恋这种感觉,他用最为原始的手艺致敬亡灵。在荒原,老人们告别人世最好的方式就是挑选一口上乘的棺材,尘归尘土归土,到头来这才是最好的归宿。老人过世后的操办程度,不仅仅考验子孙是否孝敬,还考验着家境是否殷实。孝顺的定义,荒原上每个人的心里自有定论,但总有那么几家装装样子,想在葬礼上挣一回死者的面子——而棺材的好坏自然牵扯到最后的面子。这给姥爷带来了挑战:最为廉价的木材怎么能做出不失面子的棺材呢?
舅舅购进一批木材厂废弃掉的松木,它们已然在风雨中浸泡得不成样子了,千疮百孔,腐朽不堪。这种木材做出来的棺材可想而知,稍不注意极有可能支离破碎。我一直替他担心,这种脆弱不堪的棺材能够承受身体的重量?要是漏了底可怎么办呢?
我的忧虑最终没有发生。姥爷用他特有的智慧使棺材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辉,他让松木化腐朽成神奇。他会打一盆薄薄的浆糊,把早就筛好的沙土放在里面搅拌,形成类似于水泥般的涂料。在每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手拿刮刀在棺材上层层涂抹,就像往墙上刮腻子一样,精心细致、一丝不苟。对他而言,这简直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细沙把所有的窟窿填充,整块木板光滑而又平整。我总觉得,这哪里是在打造棺材,分明是在造一座宫殿。等沙土晾干之后,刷一层大红油漆——这口棺材就获得了新生。
我在捉迷藏的时候,会冷不丁地听到棺材咔咔作响,木头与木头之间的那种脆裂、厚重乃至让人窒息的闷响。姥爷告诉我,这是荒原上某个人死去了,他的亡灵提前过来挑选心仪的棺材。我被他的讲解吓得汗毛竖立,像只野兔子从存放棺材的屋子里窜了出去。姥爷面无波澜,找块布料重新把它擦拭一遍,然后找个角落泡壶热茶静静地等待。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人来把它拉走了。
我想再告诉你另一件关于他的故事。这个故事需要往回追溯六十年,所以,请你不要着急。那时他刚刚结婚,一直想盖座像样的房子。在荒原上,泥土脱坯砌墙不是问题,树木做成房梁也不是问题,最为重要的是需要支撑顶棚的芦苇。他对建房的各个工序都了如指掌——这也是所有荒原男人所必备的技能之一。他独自一人施工,挖土、脱坯、砌墙、选木、造梁和椽子,但遮盖房屋的芦苇何处而来呢?这让他犯了难。若到集市上购买,他却舍不得花这份钱,无奈之下,他拉着平板车下了东洼。
你可不要小瞧这个“东洼”,它是靠海之地,盛产芦苇,而东洼距离荒原近一百五十公里,只有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能够到达。他拉着车在荒原上行进,并未感觉到因劳累带给他的寂寞和孤独。没人陪他说话,更没人关注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但他确实走到了东洼,看到了芦苇成片的壮观景象。他并无心思观看芦苇中惊起的白鹭,无心留意横冲直撞的野兔和惊慌失措的鹌鹑,只休息片刻便把镰刀抡开了。或许平板车装满的那一刻,他才感觉到困倦,只好倚在芦苇旁眯了一会儿。然后干啃几块窝头,喝几口凉水,趁着月光尚未升起来的时候返程。
我不敢想象那是怎样一个行程,他拉着装满芦苇的平板车缓慢地行进在乡间土路上,路旁的榆树和槐树如孤零零的鬼魂,而不远处的坟头上却飘荡着一层层磷火。月光照在路面上,洒下一层盐碱白,被拉长了的身影恍惚间变成移动的沙丘。他渺小如同蝼蚁,却有移动大象的气力。荒野上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他脚踏泥土的铿锵作响和芦苇哗啦啦的声响,他能听到自己粗壮的喘息声和收缩扩张的心跳声。他低着头一路向前,终于走到了荒原。而这种一天一夜的行程,他却来来回回地走了三趟。
在这之前,我还要叙述另外一个故事。他十八岁当兵,几乎在奔跑中度过。他到过四川、湖北和云南。在这些地方辗转,仅靠了两条腿的测量。及至后来,我看到他双腿上凝成的一团团乌黑色的疙瘩,这些疙瘩扭曲、狰狞甚至恐怖,经脉扩张引发的暗疾使他后半生处于缓慢的疼痛中,从未停歇过。他身上的疤痕触目惊心,他从未在外人面前光过肩膀——他隐瞒了自己的种种过往。
所以,你能猜到他到底走了多少路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有在年老之后的梦境里偶尔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地名。在他弥留之际的前几天,他忽地说了几句话,但我们都不知道具体内容。我的舅舅、母亲,还有二姨和小姨,在点点滴滴中追溯这几句话的源头,都无从考证,毫无结果。不过,舅舅在他零散的语句里拼凑出了一句话:低头走路。
是啊,他走了很多路!但荒原上每个人不都走了同样多的路吗?若人生还有另一个世界的话,他极有可能重见当年亲手打造的橱子、柜子、桌子、椅子、凳子,也会再做几回香气扑鼻的猪头肉。他的脚步不会停歇,低着头在荒原上行进,如一条缓慢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