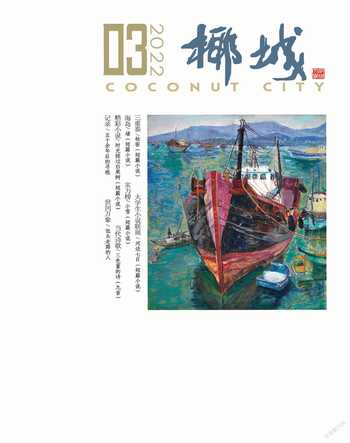河边七日
萧然
他从河中爬起,筏子像顽固的龟壳,托着某个剩余的废墟。從废墟中一跃而出,他的脚第一次有了触水感,这是一种微凉的透明物,使他的前行受阻。岸上的泥土吸引了他的脚,他有一种迫切地站立上去的欲望。于是他踢开发亮的水,把自己立在这片松软的土地上。
这里四处是高大的树,每一株都长势相同,如经由神祇的仪式复制而成。他察觉到的惶惑,与盲目的龟类以背壳朝向鹰时相似。按理说,他不应该莽撞地登岛。但泥土的诱惑对一连划楫多日的双臂而言,致命无比。他简直是轻松乃至草率地弃掉了舟楫,如解去倒悬之苦的安泰俄斯,在泥土温热而不乏预谋的召唤中,再次成为它的儿子。
为摆脱那些长相一致的树带与他的惶惑,他只得快速奔跑起来。他湿润的脚印是一串护身符,将引他辨认来时的路。周围始终只有树,因此他不间断地奔跑,指望闯破树的无心围裹,或只是寻觅到一棵与众不同的树。那或将是他的安身之所,内心的预兆告诉他。但周围始终只有树。起初耗去大量膂力的奔跑使他想起名为菲迪皮茨的先祖,先民为示纪念,在茴香之地发明了马拉松。旋即他遗忘了先祖复杂的名字,随之是茴香星状的外形,最后连茴香浓烈的气味也遗忘掉了。他畏惧地不去想自己的名字,音素的组合逐渐丢失。
很快,他失去对方向的掌控。他乞求他的脚印们将他带回去,但泥土早已远离河边水汽的侵袭,转为坚硬牢固,他赤裸的双足竟早已不能在泥土上留下凹陷。水迹也早已干燥,遗弃了他。他找不到来时的路。天色渐渐低下来,连一声鸟叫都没有,这对密林而言非同寻常。他不出声地小跑着,恐惧像只有力的手扼住他的咽喉。他以充分的虔诚向水祈祷,并恍惚记得祖先也这样祈祷过,但他已忘却祖先拜水时的仪态与例语。
再三祈求后,水准允了他的归附。前面露出一个浅浅的滩,他认出这就是自己上岸之所,两行脚印还软绵绵地印在泥上。但是,他以视线的筛网徒劳搜寻,筏子不见了。
他在原地迸出一声大吼。作为呼应的鸟叫声,没有。作为使者的风声,也没有。他认出这些长相一致的高树的叶子都一动不动。那么多叶子,密密麻麻,像山峦聚在大地上一样聚在枝桠上,也像山峦一样沉稳不动。这些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既出于失望、愤慨,也出于密度过高的恐惧,他迈开双足,沿着河边的空地向前奔去。
这次他先行择出一条存有秩序的路。沿水而行,河边的空地始终和树林平行,如棕色的粗笔镶边勒住绿色的钻。他好似被一只指针拴着,以树林中心为轴,用两脚划过边缘。时间不存在于钟表中,但自上俯瞰,他存在于这面巨大的表盘上。在弧形的奔跑中,树木不断重复,脚印不断重重印在泥土上。但他不觉得疲乏,只是在往前跑,仿佛有什么捏着他的腿,喝退了本应发生的抽搐。
于是在棕与绿之间,第三种剔透的颜色出现了。那是一株乳白色的植物。三瓣细而薄的椭圆形长片,均匀地向三个方向伸展开。它长在一株树的树干上,体积极小,却被奔跑中的他一眼发现。他几乎在刹时就对它产生好感。他无法辨别这朵花的品种,只莫名觉得眼熟,且想要贴近。他早已疲惫不堪,在发现这朵花后,一片巨大的安宁降落在他的双肩上,使他放松关节,旋即全身的关节被传染,结缔组织放弃了对骨的制约,他不再坚持人类独有的骄傲的直立姿态,而是平躺在树下。那安宁如一只无形的动物,以柔软的腹部围裹他双肩后,伸出毛茸茸的掌垫抚平他的眼皮。在这座岛上,无食物、无覆盖织物、无蔽身之所却睡着,他血管中先祖的警惕心并不准许他这样做。但与名为安宁的动物的搏斗很快以失利告终,他腿中占众数的酸涩首先告饶,随后是眼皮,最后是先祖的心。
次日,他在酣睡中醒来,晨光射过万千片叶子,似被孔隙过滤,只留下如水的光。在满天潭水中有一朵影子在轻轻摇晃,那种力度顿时使他想起在摇篮中被妈妈轻轻摇晃的样子,水波在摇篮中溅开,妈妈嘴唇翕张,歌声没入水波,弹出几个由小及大的涟漪,最终像一串水消失在水里。他茫然地睁开眼,再次看见那朵白色的花。
那朵白花在柔和的白光中端庄地舒展着,像鸽子挺起它的尾羽。
他双目迸出热烈的光,局促不安地绕着它走了几圈,强忍住跪伏的冲动,夏夜风中的燥热从他舌头中醒过来,散尾葵的涩味轻轻敲击舌苔,他口干舌燥,不得不抿了抿嘴唇。几乎在瞬间,他已确认:他爱它。
他反复地围绕它兜圈,却又不敢靠近,它太纤弱,他深知任何一个莽撞的动作都将使它无法承受,一种纯粹的物质上的触碰并不可取。他转而寻求那些原本寄身于物质却又全然超出的形式,声带的摩擦,薄膜的扇动,笛孔中被压成或瘦或壮的风,它们组成了声音,后者又分身出语言,语言中美妙的诗:正在开放的神性的花蕊,光的铰链。他默念着,祈求这屡经折转的形式将使他的狂热如同改道数次的河水,削去过分危险的流速。这祈求却也失败了。声带的摩擦愈发激烈,那休止原先存在于由他发出的每两个音节之间,愈发短暂,直至消失。最后他重复着一段早已失去原状的诗句,或者说重复着一串费解的声音。
诵读失效了。他几乎是自暴自弃地将手探向那朵花,试图摘下。将要触及的刹那,来自地心而非地表的震颤精确地叩击了他的灵魂暗室,他得以止住那伸得笔挺的、将每一根皱褶都拉直的指尖。他一阵后怕,倒退了一尺又一尺,直至需五步才能触及那朵花,这才稍稍松弛。可他仍要发狂,时间像两只靴子,一左一右地踢在他的太阳穴上,使他疼痛、使他双目发赤。时间越过去,痛楚越深,他想将它抓在手中,哪怕把它碾得粉碎。可那白色一映入眼帘便击碎他的狂热,转为一种崇敬的圣洁。他平复下来,想温柔地对它说话,却只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他这才惊觉他已忘记任何一种语言。
他低低地哭起来,用他仅掌握的音节,如以“啊”示懊恼,“哦”示意志,“呜”示绵长的悲痛,“噫”示短暂的叹惋,最后他连绵长的音节与短暂的寓意也忘却了,只发出断断续续的啊哦声。这次哭泣反而使他发赤的双目褪去岩浆般的颜色,转为与摩根石相似的淡粉,那是泪水而非欲望的结果。得此启发,他决心用另一种生理攻势来消弭自己后果可怖的狂热,那就是奔跑。他绕树而奔,如抡圆的钟摆,却只追逐自己。gzslib202204051136这一天他精疲力尽,由狂热拧成的绳索将他双脚系牢,一次一次砸向地面,直至绳索断裂,他踉跄摔在地上,因万斤重的疲倦而睡着。
第三日,他在浑身的酸涩中醒来,四肢几近不能动弹,五官却分外灵敏。他发觉那朵花似乎长大。他用目光制成的尺只稍稍一量,便证实了这种猜想。那三瓣细长而薄的椭圆形慷慨地延展了自己的长轴与短轴,匆匆行过的吉普赛人或将忽视这微妙变化,但昨日视之万次的他精确地区分了毫厘。此外,那朵花分泌出从未闻过的香味,如果不是昨日反复跑动的身体最大限度地拧松了理性的束带,使感官坦然大敞,他未必能够嗅出。生物经由激素调节自体,植物遵循同样的公理。但他已忘记激素的写法或读法,脑中只浮现出一团面目不分明的黏糊糊的物质。他可笃信的,是那朵花与他诞出同样的欣悦,它释这欣悦以力所能及的法子,如形体的伸展与前所未有的异香。毋庸置疑,他视此举为它对他的回应。
他因过度喜悦而手足战栗,但早已无法以语言述出,甚至遗忘了那指向花的音节。于是他向水边行出十余步,脚印中囤积着不舍。他在郁郁的芦苇丛中折下一枝,小心翼翼地递入口中,随后惊喜地发觉,自己借由这植物吹出了呜呜的哨声。他采来满怀的一大束,快步回到树下,坐在那朵花的正下方,不时吹起来。兴奋时,拿起长而细的一根,迸出高亢的尖鸣。由于他忘我地吹着,耳朵调聚了他的精魄,得以怠工的眼睛并不能准确地捕捉到那朵花的反应。偶尔他瞥到一抹急驰的影子,但对那是花瓣的跌扬还是树叶对太阳光的捉弄无法断言。有时,他甚至看见一队空气与另一队空气的交替,但拿不准那是花动的缘故或是远处风动的缘故。
因无应答而低落时,他的哨声也随之低落,由于这哨声并非赞美而是怨怼,他对芦苇管也生起气来,将它拦腰折断。到黄昏时,因这种缘故而折断的芦苇成了高耸的一堆。他又饥又累,已忘了自己有多少日未进食,但嘴部的酸涩使他对寻些食物来咀嚼失去兴致,况且岛上未必寻得到食物。他只草草地将那堆芦苇摊平,钻入其中,又拢起一些盖在自己的腹部,以此抵御夜间可能到来的寒冷。忍受着嘴唇因芦苇持久摩擦而造成的疼痛,他在围裹中满足地睡去。
第四日下起大雨。起初,雨唤醒他的听觉,他并不很情愿地醒来,因接纳雨水而色泽深邃的泥土进入他惺忪的眼。他立即挺起身,去看那朵花,所幸巨大的树冠如厚实的帆布抗击着雨水,花安然无恙,他自己也未曾沾染。水幕渐厚如一堵环形墙,树冠却像是严丝合缝的屋顶,他托腮观看那朵花,不禁在脑中诞出“家”的概念。由于他已忘记任何一种语言,他决心镌刻一枚符号来凝聚此时的无限沉着与狂喜。他挑挑拣拣,拾起一根完好的芦管,小心翼翼地拨动它脆弱的身躯,在泥土上留下一横,以此象征头顶的树冠,随后用三條端点相同、分别向外探伸出的短线象征那朵花,又用一道圆圈象征自己。他志得意满,创作的自豪使他反复向那朵花展示自己发明的图案,那涵盖了它与他与寄身之所的图案。
微凉的透明物袭击了他抬着的额头,他不无后怕,但欣慰地发现那只是水。旋即他觉得不妙,连忙将手掌盖在那朵花上方十五厘米处,形成结实小巧的穹拱,不多时,他的手背湿漉漉。雨水同样轻松地攻略了他的头发与后背的干燥地带,一部分经由衣袖巧夺胸腹。寒意并非不能忍受,但高举过肩的酸涩使他手掌一寸寸下移,险些当头拍到那朵花。他简直说不清,这下移是由于肌肉的羸弱,还是自己隐秘的欲望。他不得已撤下一只手,稍作歇息后,换上这只,将那只替下来,两只手交相蜷在那朵花上,直至两块肩胛骨都发出凄厉的呻吟声,不愿配合他举起的任何一只。他采取最后的胜利姿态,即将头抵在树上,用颈窝捍卫那朵花。踮起的双脚也渐渐失去知觉,他以面孔支撑身体,脸上被刮出与树皮一致的褐色纹路。当雨在黄昏时分止住时,他已如歪斜着的梯子,长在了树上。
他费力地将自己从树皮上剥离,面孔布满卵石似的疼痛。他跌跌撞撞地走去河边,掬水洗去血迹与树皮的分泌物。在水中,他瞧见了自己的脸,瘦削而铁青,眼睛因臃肿的狂热被撑得巨大,不像人形。他这才忆起他已经四日、十四日或四十日未进食。他仓惶地离开水面,甚至怨憎起自己的影子,怀疑它背地里已腐烂。他决心带那朵花离去。
第五日,他在前所未有的清明中醒过来,散发着两点之间的直线一样笃定的气息,过去他从那些伟大的人物身上嗅到过这种味道。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出发前,他凝神端详那朵花,在它的纹路里,猜测沙漠的布局。道别如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道别一般不舍。他来到河边,沿水逆时针步行,企图辨认出自己的上岸之处,寻觅那条筏子的线索。他警惕又不无耐心地叩问他光临过的泥土,但没有一块土地敢于向它诉说自己的与众不同。出于不被告知的理由,那些泥土狡黠地将自己隐入宽厚的大地。他自觉足够缓慢,仍然在太阳还瞩目地悬挂穹顶时就回到了那朵花旁边。他意识到这岛呈环形,出于先前习得却又遗忘的本领,他再次赞美了直线,从毗邻的树身费力折下一段还算长的树枝,粗细也合宜,不会轻易折损。他握着这段树枝,一边向密林中精准地走去,一边在身后留下拖痕,果然顺利穿过了整座岛,再次来到水边,但也沮丧地、害怕地意识到,岛上除了树与泥土空无一物,甚至没有一只吵嚷的鸟。沿树枝的拖痕走回去,已进入又一个夜晚,他择来一束新的芦苇,不再折断,但吹出的只是一些低低的呜咽。
第六日,他醒来时已很迟。无限的燥热迁居到额头,那正是水给他的惩罚,如牲畜被滚烫的烙铁咬过,冒出白烟。鸟群在他脑袋里飞窜,那些掉落的尾羽,每一根都如此清晰。他看到那朵花便恢复镇定,但只消一闭眼,鸟群的盘旋又无法终止。在此期间,他看到许多未来的景象,河流的头衔着河流的尾,城镇被装上卡车运走。他明白自己发起了迟来的高烧,由于他对那朵花的觊觎,水以自己的手段惩罚他,如带走筏子和降下雨水。他苦闷地设想远离这朵花以后的日子,但巨大的失落空虚像失去心的树皮一样干瘪,扫走了他的念头。器官的剧痛使他畏惧,他想要逃离,只能带那朵花一起。他迫切地,迫切地需要抓住那朵花。但他发着烧的身体软绵绵的,并不能站起。他默默等候体力的恢复。小憩与清醒的交替后,有一次他感觉自己积攒出一些气力,便挣扎着坐起来,倚着树休息了一会儿,竟然成功地四肢并用爬起身。他试探性地向花发起冲锋,但手指距它三厘米便落荒而逃。理性使他缩回,此时的身体并不能支撑他带它逃走。渴望却使他探出,离花越近,那清凉越使他灼热的面颊舒适。他再次细细端详那朵几日来他望过无数次的花,它已长至先前的两倍,原本动人的弧线如今更为饱满,像少女柔软的腰肢,他简直不能相信它只是一朵花。
这夜他没有入睡,而是以充分的耐心维持清醒。
第七日的天明到来时,那水波般的晨光再次打在他和它身上,一块金黄欣然做了它的衣裙。它轻轻摇曳,上下点头,仿佛在催促他的行动。他等候这刻已经一夜,果敢地伸出手。
那朵花顺利地被他拿在手中。他原以为将生出异象,但万籁都隐去,万物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