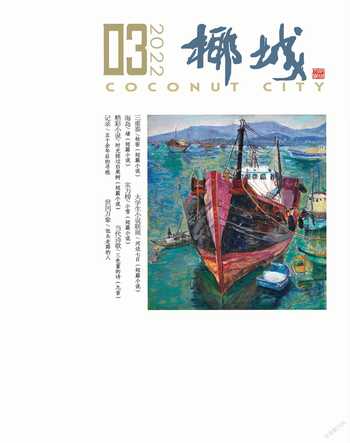生命结缘,无限担当(评论)
◎阿 探
王闷闷在90后作家里,无疑是一个把叙事长句玩出异质味道的人,作为读者,总能从那些崎岖嶙峋的字句里准确感知人物的心灵动影。与更多沉溺于细微触觉式叙事,几乎抛弃了叙事速率的同龄作家相较,他的叙事显然是专注而不断跃进的,他将较大跨度的时空转换融入叙事,常常以某些不变去直面去捕捉那些潜藏着烈度动量的不断的变化。他把对小说的认知化作了人物某一时点的精神内质的动荡,短篇小说《枯窑》就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文本大篇幅的叙事几乎与“枯窑”不相干,作为短篇小说的题目,它只是临近完结才浮现出来。或许这是更多的年轻作家小说创作的一种惯性思维的延宕,但在王闷闷这里却有了更多的文本承载意义:小说最终的核心表达,是一种基于大爱的灵魂担当,“枯窑”则更是文本情节所赋予的实体担当,它同时又成为闵娃的养父精神担负的象征性意象,托举起对结缘生命的无限担当与希望。“枯窑”无疑是他与同病相怜的瘸子可以开掘出莫大希望的精神富矿,是生命洞穿无限悲哀不竭的原动力。
小说开篇给予读者一幅夜已深沉,主人公因精神背负着无限的重压而无法入睡,无以排解无限愁绪的画面。“窗外的静寂在层层浸漫,依凭常年的感觉,夜已经深到低谷,接下来便会缓缓爬升,直至山后新阳散射出尖刺的光芒。烟抽到半夜才躺下,睡意全无,频繁的辗转反侧是内心焦躁的外现,清醒的意识难以用最能营造困倦的夜色遮蔽,假装哄骗全被内心了然。”这段关于夜与主人公的描写,似乎与这“夜”与主人公“他”无丝毫关联,而是独属于王闷闷的叙事方式,亦是赋予读者渐次展开的心灵序曲,使小说人物精神担负的质地可触可感。叙事轻盈地转入白天晌午,却并不直接切入关于闵娃的言语,而是细致入微地表述“他”吃馍馍与喝水的相关细节及人生认知,使小说人物丰富的精神气质跃然纸上。“他”心疼的人儿闵娃出现,她对“他”的关爱之外,所带来的却是令主人公“他”难以承接与承受的二十五六万债务。“他”无疑是痛心的,但痛心的不是巨额债务,而是不是女儿胜似女儿无助的自己看着长大的闵娃。尽管这个世界并未准许“他”以任何舒服的姿势坐卧与行走,但“他”没有抱怨女儿,只怨自己没有给予她良好的家庭环境,怨自己背锅无能力的给予。睡意起时,“他”却不得不去扫街道,生活不容“他”有丝毫的喘息,甚至为了多挣几个钱,“他”冒着生命风险去扩大自己的负责区域。
小说紧接着以时间倏然过隙之感叹,倒叙到数十年前,表述了“他”与生俱来的驼背,与外面世界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无缘介入。33岁的“他”因背痛去医院看病,在厕所里怜惜被遗弃的生命而拾回幼小的闵娃。因着天生的罗锅,原本一个人的生活已经十分不易,抚养一个弃婴又将是何等艰难?幸亏有邻居老婆婆多年的帮衬,闵娃还算顺利地去镇上读书。闵娃小学升初中未考好,心理压力巨大,“他”穷尽了一个因身体畸形而深有自卑感之人前所未有的勇气,给中学校领导送上礼品与红包,终于让闵娃上了理想的学校。照料闵娃的老婆婆去了,闵娃的生身父母来了,“他”所能给予孩子的太少太少,因此陷入了新的纠结。最终,“他”顺其自然,默许了闵娃与父母的相认。闵娃顺利成长,她高三放弃学业,去工作并很快恋爱。面对女儿带来的陌生男人,“他内心装有莫名其妙的慌乱,但面对恋人的黏腻相爱又不能说出,世间太多事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发生,难以提前制止,就算提前言说制止,到头来也会发现,其实那根本就不是本质上的阻止挽救。可等事情真的发生了,又会后悔当初没有劝阻,人就是这样,矛盾不已。”这对于“他”几乎是一种真实的宿命式的表述,对于闵娃又何尝不是这样?情爱的黏腻与轻率的结婚,或许正是日后离婚与冷漠的一种注定。这一段的叙事速率有着阿乙式的高速推进,从一个女婴到人妇,王闷闷对叙事有着高超而笃定的掌控。最后一节,文本叙事回到小说的现在时空,回溯了闵娃离婚的起因和最终无可挽回的结果:“李明转身从门里出去,顺着坡道下去,路过家户院子,狗听见人声,咬吠得震天动地。”这不仅仅是李明的一种坚定与决绝的姿态描述,更是婚变在主人公“他”内心所激荡起的巨大震动。甚至可以说,这个闵娃或许是“他”前世的冤家,今生带给“他”不断的承受。即便如此,他依旧以一个父亲的伟岸灵魂去直面这个生命的一切赋予。
王闷闷随即将叙事转入正在进行时,“他”作为环卫工人的扫街不再是扫街,而是实质性的一种人生庄严的“盘算”:“他没有什么不可付出的,这把岁数的人,随时等待死亡的降临,与其等死不如去用残喘的余生做些事情,换得钱帮衬闵娃。去哪里挣钱?”闵娃对“他”言说,意味着“他”永远是她最忠实最可靠的肩膀,“他”必须托举起原本属于她个人的重压。“他”僵化的大脑在突如其来的重击之下竟突然变得灵动起来,几乎拥有了“哈式急智”,“他”很快想到了应对危局的办法,尽管是十分冒险之举。“他”立即行动,去找瘸子,立即和他一起去废弃的枯窑查看,“……夜已浓郁深邃,两个干瘪的生命依凭着最后的气力游动于世,边走边观察计划挖出煤怎么运送出来,现在的路能不能满足,多年前的枯窑了,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如意的煤量,让牵心的人儿度过难关,至于往后再有什么,两个气喘吁吁的老人已然难以顾虑到。”被废弃已久的枯窑,在人声静寂中,早已腾升为背负人世责任的两个身体畸形老人对结缘生命的全部热望与无限担当。
“他”是一个无名者,却依旧拥有着伟岸父亲的崇高灵魂。小说构建思路清晰,叙事因时空及跨度而游弋多姿,拥有了较高的完成度,轻盈地完成了灵魂的冒险与抵达。王闷闷的短篇小说《枯窑》,既有属于自己的长句叙事语言特质,又有着年轻一代作品的共性:时空游刃,精细精准,碎片叙事,凝聚于人之瞬间心灵力量的攒聚与爆发。小说之道,大体须有,定体则无,艺术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