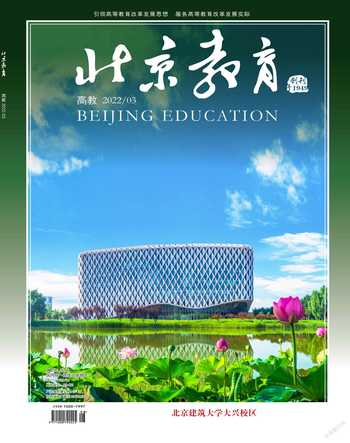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逻辑与路径
朱贺玲 郝晓晶
摘 要:从同僚治理、教授治校走向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调、彼此制衡的共同治理,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应然方向。在中国情境下,从决策权力的纵向分配来看,中国大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倒金字塔”式治理结构,决策权力大多集中于学校高层,院系缺乏自主权。从决策权力的横向分配来看,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仍居主导地位,学术权力虽逐渐受到政策文本和大学改革实践的重视,但教师等学术人员参与治理的机会仍然有限,且往往沦为形式,并未实质性影响决策结果。
关键词:治理;大学治理;共同治理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以来,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结构,厘清大学各决策机构或个人的权力关系,完善权力机构间的合作与制约机制成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本研究详细梳理治理与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及范式演变,并从纵向、横向两个视角,对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以期为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实践参考。
治理与大学治理:概念界定及范式演变
治理(Governance)在较长时间内与政府(Government)同义,指涉国家的正式机构及其对于合法的强制性权力的垄断,主要特点为有能力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1]。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对于“政府失灵”的诘问,在此背景下,治理转而强调突破以政府为主的框架,主张国家和社会共同治理。相较于政府,治理涉及更多的权力主体,除公共部门外,私立部门、志愿部门同时参与决策过程,而且治理不再强调界限清晰的权力结构,而是注重权力主体间彼此协商、相互合作的互动过程[2]。
大学治理概念较为复杂,外部治理侧重大学与政府、市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内部治理则通常指涉决策(Decision-making)的结构和过程[3]。正式结构是大学治理以及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形成与互动的基础,规限了各决策主体的权力边界;决策过程则侧重探讨大学内部各权力主体间彼此协调、相互制约的过程,往往涉及权力的安排、资源的分配、利益的平衡等诸多议题。相较于治理,管理(Management)和行政(Administration)通常强调决策后,藉由责任和资源的分配,或业已授权之程序的实施,达成既定的决策结果[4][5]。
传统的大学,尤其是存活于王权、教權、城市自治权“夹缝”间的中世纪大学认为学术自由作为学术人员应该坚决捍卫的内在价值,神圣且不可侵犯,国家或政府应保障大学作为学术社群的福祉与自由[6]。学术自由需要内部治理结构的支撑,同僚治理(Collegial governance)、教授治校因而成为经典的大学治理模式,强调掌握专业知识、共享相同价值和理念的教师群体组成学者社群,在相互信任和道德约束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决策过程,决策结果旨在达成专业共识[7]。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大学职能的拓展,传统的以经验或专业知识为决策基础的同僚治理、教授治校难以应对逐渐升级的治理挑战,在此背景下,科层治理模式被引入大学。科层制强调自上而下垂直分工、界限清晰的权力结构,同时设置明确的规则和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过程。在科层制的影响下,大学行政管理系统得以迅速壮大,校长、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的权力日益集中,而且学科知识的发展与分化,使得教师等学术群体难以兼顾繁杂的行政事务,专业管理人员开始形成,大学治理呈现“以行政管理系统”为基础的科层治理模式,与“以院系学术管理为基础”的专业组织治理并行的格局[8],如何平衡两类组织的利益冲突和理念分歧也成为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挑战。
为协调和明确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力边界和作用空间,美国大学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共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过程,旨在保证治理结构的平衡以及有效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共同治理最早见于美国1966年发表的《学院与大学治理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该声明提出,重大事件的决策需要机构全体人员的参与,各群体发言权的权重因其在具体事务中所负责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共同治理的理念下,美国大学内部参与决策过程的机构和组织较多,其中,董事会、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层、代表教师利益的学术评议会是最为主要的治理机构,《联合声明》明确了三者在大学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并尤为扩大了教师的决策领域。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引发问责与竞争的强化,一方面,政府、市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纷纷借由董事会参与大学治理过程;另一方面,速度成为大学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市场导向的治理模式受到大学的关注。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被认为是大学在知识经济和商业化时代成功的必要条件,校长等管理层的决策权应该在较大程度上扩大,以改善大学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有鉴于此,各国大学纷纷精简决策程序。集中决策权力,校长、院长等领导在决策中的作用得到强化。
进入21世纪,“多元化巨型大学”不断涌现,除规模急剧膨胀、学科愈发庞杂、功能更加多元等内部变化外,外部环境也在较大程度上冲击着现代大学的治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职业化的行政机构对于大学的高效运作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国家学术自治的领域不断萎缩,但仍未忽视对传统学术自由理念的坚守,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依然能够监督甚至制衡迅速扩张的行政权力。
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现状及问题
从国际视野来看,随着大学组织以及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内部治理面临的挑战成倍增加,以学术共同体为核心,强调学术权力的同僚治理、教授治校日渐式微,主张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的共同治理受到广泛关注。另外,在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下,各国纷纷精简决策程序、集中决策权力,旨在形成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层以加快决策速度,但以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力量依然可见较强影响力。
在中国情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多以计划调控和行政命令直接干预大学具体运作。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实施一系列还权、放权政策,大学渐次获得招生、学科建设和调整、教学、科研、学术交流、教师队伍建设、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人员配备、经费管理及使用等系列自主权。然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逐级下放的权力多数集中于以党委、校长为中心的学校行政管理层,学院自治空间有限,学术权力也并未凸显。下文依次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剖析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其中,纵向治理结构主要指涉学校与院系等教学科研单位在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横向治理结构涉及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分野与职能范围。
1.治理过程中的校、院互动:决策权力的纵向分配
關于治理过程中大学与学院的互动,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大学决策机构与学院的互动;其二,学校行政部门与学院的互动。依据相关学术讨论,大学决策机构与学院的互动存在“行政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9],行政的逻辑强调自上而下的服从,大学与院系之间呈现科层组织的层级关系,与之相对应,学术的逻辑更倾向于相对平等、自主的决策方式,注重教师或学术性委员会基于专业权威的协商和沟通过程。
在现行治理体系下,中国大学通常依据“行政的逻辑”实行科层式决策,学校掌握着包括经费在内的各种资源分配的权力,使得学院或系所对学校形成依赖[10]。有学者调研后发现:91%的大学教师认为大学的决策权力主要集中于学校层面[11]。具体来说,大学层级的决策权主要由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党委会)施行。周本贞(2013年)等学者进一步指出,关乎大学发展和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决策,往往直接由学校党委会与校长办公会“拍板”,甚至仅仅通过党委会与校长办公会下属的行政职能部门简单提议后,便形成一项决策或规章制度,进而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直接发布[12]。
关于学院与行政部门的互动,西方国家大学的行政部门通常为决策执行机构,并不介入治理过程,而在中国,大学行政部门亦存在干预学院决策的情形。以教师招聘为例,学校人事处等行政部门通常依据院系的面试或试讲评价意见,同时参考应聘者的科研成果、教育背景等,最终确定录取结果,或者将录用意见上报校长,由校长办公室决定是否录用[13]。具体而言,人事处等行政部门在最后决策阶段,一般存在两种情形,其一,充分尊重院系的意见;其二,基于行政部门自身的考虑,决定是否录用应聘者,后者在中国大学更为常见[14]。事实上,学校行政部门与院系对于应聘者的要求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院系可能更为看重应聘者的科研能力和潜质,行政部门则倾向于依据教育背景、科研成果等硬性标准决定录用结果。
2.政治、行政与学术:决策权力的横向分配
从决策权力的横向分配来看,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仍居主导地位,但学术权力也逐渐受到国家政策文本和大学改革实践的重视。以往政策文本大多强调教师的福利、权益以及学术事务中的讨论、监督、审议、咨询权,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授治学”的概念,强调应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2014年,《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首次明确了教师在学术事务中的决策权。
在实践层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学治理形式几经改革,但大多围绕学校党委与校行政职权如何划分而展开。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大学先后经历了“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新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阶段[15]。不过,教师虽然并未享有学校层级的决策权,但在学院或学系层级,却可以通过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切实地发挥影响力[16]。与此同时,大学章程也为相关学术组织在大学层级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搭建了平台。
不过,教师享有决策权并不仅仅意味着大学设立相关的学术性委员会或教师有机会参与学术性会议,而是强调教师真正参与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结果。在中国情境下,一方面,学术性委员会成员以院长、系主任等学术领导为主,有学者调查中国近百所大学各类学术机构成员的背景后发现,大学学术机构成员资格的获得与其拥有的行政职务高度相关,即使是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权力也并无强势表现[17]。另一方面,教师参与学术性会议通常仅为程序需要,作用仅限于集中表决由领导事先拟定的方案,缺乏深入的沟通与讨论[18]。而且,教师参与决策往往被异化为承担具体的、常规性的行政杂务。
结语
传统西方大学强调学术和机构自治,认为大学有权在资深教授的指导和监督下,对内部事务独立做出决策,同僚治理、教授治校因此成为经典的治理模式。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大学组织以及外部环境日益复杂,政府、市场逐渐介入大学的内部治理活动,强调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的共同治理,以及主张精简决策程序,集中决策权力,形成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层以加快决策速度的企业化治理迅速受到广泛关注。不过,以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力量依然可见较强影响力。
从共同治理的视角来看,大学与学院的多主体参与,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相互协调与制衡,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应然方向。在中国情境下,一方面,中国大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倒金字塔”式治理结构,决策权力大多集中于学校高层,院系缺乏自主权[19],而且,由于学校掌握资源分配等权力,院系多对其形成依赖,依据校领导决策意图执行相关决议被视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在大学和院系层面,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仍居主导地位,学术权力虽逐渐受到政策文本和大学改革实践的重视,但教师等学术人员参与治理的机会仍然有限,且往往沦为形式,并未实质性影响决策结果。
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关键,在于依托大学章程明确内部权力结构,为各决策主体设定权力边界和行为规范。从决策权力的纵向分配来看,学校应适当下放权力,使学院成为课程、招生、教师招聘、职称评定等学术事务的决策主体。当然,院系层级的决策过程及结果,尤其是招生、招聘等事务,可能更容易受到人情与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但此类现象不应成为学校回收权力的借口,或可考虑在院系层级的决策过程中,引入、强化监督和惩罚机制,引导讨论程序、表决规则以及决策标准的制度化。
从决策权力的横向分配来看,宜进一步明确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职能边界,尤其凸显教师等学术人员在学术事务中的决策权。具体来说,可在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机构增加不同职称的教师比例,尤其是无行政职务的教授以及青年教师的比例,打破各级领导对于决策资源的垄断。另外,给予并尊重普通教师的讨论及投票权,而非表决由相关领导“内定”的决策结果,或仅承担低层次的行政杂务。
从理论到实践,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治理结构,只有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院校规模、性质、历史使命相契合的“适合”的治理体系。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院校的治理结构往往针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回应和调整,并无固定和统一的标准。因此,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大学传统理念,适合大学实际处境,并受到多数领导、教师、学生、校友等群体理解与认可的治理结构。
本文系2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世界一流大学治理改革研究:基于案例分析的视角”(项目编号:18YJC880154)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STOKER G.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55): 17-28.
[2] 朱贺玲,梁雪琴. 大学治理的经典模式与特征解析[J]. 高教探索, 2021 (7): 19-26.
[3]KEZAR A J,ECKEL P D. Meeting today’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examination of a future agenda for scholarship [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4, 75(4): 371-399.
[4]MIDDLEHURST R. Changing internal governance: are leadership roles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in United Kingdom universities fit for the future?[J].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2013, 67(3): 275-294.
[5] 朱贺玲,黎万红. 从共同管治看中国内地大学教授治学的现状与发展[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14 (3): 91-106.
[6] BRAUN D,MERRIEN F X,MCNAY I. Towards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for Universities?— A Comparative View[M].London & Philadelphia: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1999: 11.
[7]OLSSEN M. The neo-liberal appropri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 policy in New Zealand: Accountability, research and academic freedom [R]. “State-of-the-Art” Monograph No. 8.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02:1-20.
[8] [19]周光禮. 从管理到治理:大学章程再定位[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4, 13(2): 71-77.
[9] 陈霜叶. 中国大学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互动类型[J]. 高校教育管理, 2013,7(2): 20-32.
[10][15][16]张斌贤.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变迁[J]. 教育学报, 2005(1): 36-42.
[11]林炊利. 核心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办高校内部决策的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2] 周本贞,陆选荣,王飞. 多元共治视阈中大学内部四大管理主体的问题及消解[J]. 高校教育管理, 2013, 7(1): 21-26.
[13]李军,阳渝,伍珂霞.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我国高校教师招聘 [J]. 当代教育论坛, 2006 (19): 81-82.
[14] 胡先锋. 论高等学校的教师招聘[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2005 (1): 50-53.
[17] 李海萍. 高校学术权力运行现状的实证研究[J]. 教育研究, 2011,32(10): 49-53.
[18] 屈代洲, 鄢明明. 教授治学的实现路径探析—以 H 大学教授委员会为例[J]. 中国高校科技, 2013(12): 8-11.
(作者单位:朱贺玲,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首都工程教育发展研究基地;郝晓晶,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
jscpu20220323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