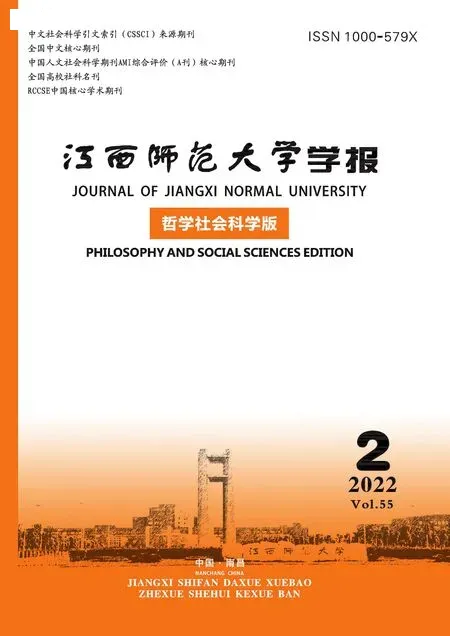度量衡与中国早期哲学
闫月珍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关于中国早期器物与制度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器物与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一定探讨(1)如阎步克探讨了器物与制度史的关系,“爵”是饮酒器的通称,同时又是古代一种最重要的品位序列之称,从周代到清末,历代都有封爵。“尊”则是盛酒器的通称,它也成了最重要的身份用词,与“卑”相对。这样两个身份用语“爵”与“尊”,同时又是酒器之称,由此启迪了一个推想:萌生期的爵制,曾存身于一种物化的、可视化的形态之中。爵、尊又作身份之辞,就是这种“原生态”的爵制遗留下来的历史胎记,而且与饮酒礼息息相关,见《制度史视角中的酒爵酒尊——周代爵制的可视化形态》一文,收录于《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相对而言,对器物功能与制度话语之间的关联,尚缺乏一定的探讨。中国早期哲学的言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隐喻得以实现。其中,关于道德和法度的描述,主要通过作为器物的度量衡得以实现(2)关于法度的隐喻,学术界已有一定探讨。其一是作为自然物的水,早期的中国哲人对法的思考并不借助于概念和逻辑,而是来自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由水所提供的意象成为中国法思想的一个原型,参见王人博《水:中国法思想的本喻》,《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其二是作为器物的律,律是自然的根本法则;此外,典、彝、则、宪、刑等也都与法、律有相通之处,参见曾宪义、马小红《中国传统法的结构与基本概念辨正——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本文主要探讨作为器物的度量衡在中国早期哲学建构过程中的意义。。这是因为道德和法度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甚至是人类社会的集体规定,而不同于自然物之不赖于人工、不假于人为。
度量衡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计量层面,即用数量对事物的描述;二是技艺层面,是用工艺对器物的制作;三是制度层面,是用政令对文化和经济的规约,这三者往往达到数量、技艺和制度的统一。但在思想领域,度量衡的意义超越了上述层面,构成了一个新的境域和系统。在中国早期哲学建构过程中,作为器物的度量衡成了各个学派立论的元素。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和从技术进展所获得的名词相平行发展,器物的制作技术和使用功能塑造了关于制度和秩序的话语,这为探讨制度背后的语言逻辑,提供了线索。
一、度、量:技艺与制作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定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1](p203)。西周春秋时期,检校制度得以创立,当时国家设有专职官吏来管理度量衡事宜。战国早中期,诸侯国普遍铸造了一批标准器。战国晚期,各国常派专门官吏对度量衡器物进行统一检校。秦汉延续了战国时期的度量衡制,并进一步加以检校。在此一过程中,度量衡成了经济生活中的实物,更成了政治生活中的隐喻。人们以度量衡为言说方式,对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了描述。
度指计量长短的标准,单位是丈、尺、寸、分(2)陈梦家发现秦始皇统一前的列国度量衡标准大致上是相近似而稳定的,差异和变化都不很大,汉代的度量衡也承袭秦制,相差很小。参见陈梦家:《战国度量衡略说》,《考古》1964年第6期。。《汉书·律历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2](p966)关于长度的测量,一是取人体为标准,在周代,寸、尺、咫、寻、常、仭皆以人之体为法。寸法人手之寸口,咫法中妇人手长八寸,仭法伸臂一寻。皆于手取法,故从又。二是取自然量和器物为标准,人们以黄钟律管长为准,以累黍为法确定标准。采用律管作用检验长度的原器,是因为如果用中等大小的黍子去测量黄钟律管的长度,恰好等于总共九十颗黍子的长度。每颗黍子的宽度就相当于标准尺的一分,所以律管之长是九寸。《说文解字》:“度,法制也。”就是指长度的测量取法于特定的参照物,由此确立特定的规范。
量指计量物体体积的容器,单位是石、斛、斗、升、合。《汉书·律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67页。按照《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律管上包含了度、量、衡三者的基本单元。但孙机认为黄钟律管对于计量器来说,除了校准长度外,在校准容积方面已没有意义。参见孙机:《汉代黄钟律管和量制的关系》,《考古》1991年第5期。制作的核心是对数量的考察。制作器物前,需要对长度、体积等数量关系进行考察。没有数量的关系和比例,就不可能做出器物。同理,在制定政令前,需要对形势、风俗等社会情况进行考察。没有这一考察,就不能实现社会的治理。“制度”一词的意义就来源于“度量衡”,《周易·节卦》:“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3](p240)《周易·节卦》:“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3](p240)数度指礼数法度。君子效法《节》象,制定礼法作为“节制”的准则,又评议人的德行优劣以期任用得宜。
度量衡是一个政体确立的重要表征。在中国计量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度量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政权的更迭往往体现于度量衡的确定。《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4](p1001)圣人治理天下,需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如同考订历法,变革服饰、徽号、器械一样,这都是可与民众一起变革的。而血缘、级别关系等,则是不能变革的。《礼记·王制》:“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4](p435)有关饮食、衣服、技艺、器物品类、长度、容量、计数、规格这八个方面的规定,称之为八政。秦朝建立后,统一了度量衡,《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5](p239)总之,度量衡不仅是一个经济流通行为,还是一个政治规定。
在器物的制作、都城的建造过程中,数量的大小须符合爵位的序列。《左传·隐公元年》:“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6](p51-53)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非法制所许。《周礼·夏官司马·量人》:“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7](p791)通过量人掌控丈量、营造和祭献之数,实质是以官职的方式将建制统一起来。
《考工记》记录了器物制作的规范。《考工记》提到车轮的检测,包括以下六道工序。即规、万、水、县、量、权[8](p23)。“规”是用来检测车轮、车轴圆度的工具;“万”即矩,是检测角度的工具;“县”即悬,检测车辐直度的工具;“水”是指测量将车轮放入水中,若下沉的深度一样,则车轮取材一致;“量”指测量各部分的长度和深度;“权”是测车轮重量平衡的方法。《考工记》还说明了栗氏制造量器的材料、标准和功能,“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8](p55)可见,量器的制作要使用去除杂质的铜和锡,鬴、豆和升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嘉量用于校准量器而非收税,它被颁示四方作为执行的法则。栗氏量“将长度、容积、重量三个量的标准量值集于一件器物之上,即可用一器来传递度量衡三者的量值,这种设计思想是很科学也是很巧妙的”[9](p220)。
在儒家看来,不仅器物的制作需要度量,制度的实施也需要度量。《荀子·富国》:“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10](p194)没有度量衡,人们会以利为驱动而失却义,故荀子主张以利律己,以利待民,这是因为民富则国富。《周礼·地官司徒·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郑玄注:“量,豆、区、斗、斛之属。度,丈尺也。”[7](p366)即在行政上通过量度来确定价格,以实现货物的流通。《大戴礼记·盛德》:“凡民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量也。”[11](p143)无度量实质是无德法。可见,在儒家看来,民是利之基础,以礼作为调节的手段,则可实现社会的治理。
在法家看来,度量是社会法规的核心,需要人们加以遵循。《韩非子·用人》: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12](p205)
如果抛弃檃栝、规矩、度量之器,即使造车的名匠奚仲连一个轮都造不成。同理,若没有功、刑、法的诱导和威逼,就无法治理社会。国家必须“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12](p441),法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统治者应设置法度以统一民众的行为,信赖赏罚以发挥民众的才能,公开赞誉和毁谤以阻止恶行。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治理之“势”。而若没有度量,则会被虚妄之言行所蒙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冶又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12](p267)《韩非子·守道》:“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12](p203)君王是利的主导者,君王以法、术和势进行硬性的强制,才可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商君书·君臣》:“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13](p130)百姓众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故创立法度和标准来禁止这些行为。法制严明、刑赏得当,才会使“军士死节”“农民不偷”。
二、权、衡、准:平衡与治理
权、衡和准,都通过平衡关系测量物体的重量和水平。权是秤锤,用以测定物体重量。重量的单位有石、钧、斤、两、铢。《汉书·律历志》:“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2](p969)又:“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2](p969)璇玑是北斗魁的第一星至第四星,即枢﹑璇﹑玑﹑权;建是北斗的斗柄所指;七政指日、月和五星;玉衡指北斗七星之第五星。北斗四星作为斗柄,一年之中,斗柄旋转而依次指向不同方向,月份的更替由此确定。通过衡权和星象的类比,这里将天文和人文统一了起来。
国家的治理有着可以依据的标准,儒家将度量衡视为政体实现的必需。人们通过制度和权力,可实现对国家和文化的控制。《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14](p266)这里从君王的角度,论圣人之道可以垂训来者,认为百姓之过,其根本在于君王的政令是否通达。君王宽厚、示信、敏速、公平,则民心归之。在荀子看来,礼需要通过外在的权力和法度得以实现,《荀子·解蔽》:“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10](p394)人主不公,人臣不忠。荀子将礼比之于权衡、绳墨和规矩,人心往往蔽于好恶而缺乏公正,礼则具有公平和正义性质。出于性恶论,荀子主张以外在的规范而非内在的心术调整和约束民众,如《荀子·性恶》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10](p435)孟子也强调法度之重要,主张以权、度实现对人心的揣测,《孟子·梁惠王上》:“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15](p21)出于性善论,孟子主张修养应该“反身而诚”。[15](p353)总之,儒家对权衡的看法,主要以礼和德为宗旨,《荀子·大略》:“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10](p495)儒家以德为主,将德、礼和法融为了一体。
法家认为权力的控制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故比其他各家更多地讲到了权。一方面,权是君王守持之柄,是控制社会力量的手段。《韩非子·有度》:
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12](p38)
有了规矩、绳线、水准、权衡、斗石,就可以使不确定的因素变得平衡。韩非子强调法之客观性和必要性。君王掌握了权,也就掌握了社会。
基于此,一方面,管子主张权度应该公正,得信于众,而非偏于私心。《管子·君臣上》:“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修义者惑。”[16](p545)《管子·君臣上》:“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16](p546)作为官职的吏啬夫全面掌握计量规章和事务法律,在审理刑法、重量、容积、弹劾案件时,就可以不徇私情而实现事务的公正。另一方面,管子认为持权是掌握社会形势的治术。《管子》的《权修》《山权》《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等章,均是从度量衡出发论国家治理的。《管子·权修》:“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淩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16](p53)关于《权修》,黎翔凤注曰:“权者,所以知轻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轻重,然后国可为,故须修权。”[16](p47)朝廷不整肃,贵贱地区分,长幼不分明,制度不清晰,服饰无等级,上下超越界限,而求百姓尊重君主之政令,是不可实现的。《商君书·修权》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13](p82)《商君子》认为治国有三个要素,第一是法度,第二是信用,第三是权柄。法度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柄是君王独掌的。《商君子·修权》: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13](p83)(4)《墨子·大取》:“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掔,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吴毓江:《墨子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11页)
古代帝王制造了秤和尺,就是因为其分量明确。而没有这些器物,则失去了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因此,法度是国家的权衡。背弃法度而听信私议,就不知事类。因此,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主张通过集权将刑罚公之于天下,这就克服了德、礼对法的约束。
而在道家看来,法治是人为的戕害,并不能实现社会的完善。度量所体现的计算思维,甚至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庄子·胠箧》: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17](p350)
如果掊斗折衡,则民众就不会争斗。《庄子·天道》:
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17](p467-468)
军事、赏罚、形名和法度只是末技,没有大道作为根基,就无法管理好社会。故庄子主张不治而治。道家思想的实质是去除德、礼和法,以顺应自然而实现社会的无为而治。
以工匠的技艺特别是度量衡进行言说,墨子倾向于将法度普泛化为天志(5)《尚书·舜典》:“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在时节变化的过程中,协调时令和人事,统一计量器物。李约瑟发现“道家和墨家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并指出阴阳家“发展了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哲学”。(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法律自然主义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典型表征是:把“天”或“天道”当成立法的根据,此谓“则天立法”。把四季变化和自然灾异当成执行刑罚的前提,此谓“顺天行罚”。参见崔永东:《论中国古代的法律自然主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编,《比较法律文化论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183页。。《墨子·法仪》提出了“五法”: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18](p29)
法就像百工所用的工具,能防止治国没有依据而偏离公正(6)《墨子·天志上》:“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吴毓江:《墨子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96页)。墨子以“兼爱”精神为旨归,以顺应“天志”为原则,强调天具有立法和监督的功能(7)“‘礼’所概括起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并不单纯是我们经验中所发现为中国人感受到的与‘普天之下’对正义的本能感觉相一致的那些东西;它们还被认为是与上天的‘意志’相一致、而且确实还是与宇宙的结构相一致的东西;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人们就无法体会‘礼’字的全部力量。因此,犯罪或者甚至于争执,都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重大的不安,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扰乱了自然界的秩序。”(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59—560页)。
准是测量水平的仪器。《说文解字》:“准,平也。”段玉裁注:“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水平谓之准。因之制平物之器亦谓之准。”[19](p560)《汉书·律历志》:“准者,所以揆平取正是也。”[2](p970)《考工记》:“准之然后量之。”[8](p55)所以,准具有效法之意,《周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3](p266)《管子·水地》:“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16](p814)以水为准,在法度观念的确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说文解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从字面意义上看,灋是用刑来处罚有错之人,公平如水(8)刘丰发现中国古代的法,从时间顺序来看,一般而言,在三代是刑,春秋战国是法,秦以后则一直称为律。从本质上来说,三者是一致的,核心是刑。在三代社会中,刑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法的观念当中,并没有相对应的权利观念。中国古代的法,基本都是‘公法’”。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页。。段注:“刑者,罚罪也。易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法的含义与模、范、型一样,都是需要遵照的硬性规范。
人们还将度量衡与时令结合起来,用以解释自然现象,赋予社会现象以合法性。《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4](p475)周代定期检查度量衡,每年进行两次。春分和秋分昼夜被均匀平分,蕴涵有天地公平的内在含义,这就将度量衡与天地和四时联系起来。《淮南子》更将上述观念细化,将度量衡器物与天地和四时分别进行了组合,《淮南子·时则训》:“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20](p439)
三、表、律:月令与候气
圭表是用以测量日影的器物。它由座、圭和表三部分组成。圭是平卧在石座上指示南北方向的尺,表(也称臬或槷)是直立的标杆。圭和表下方有座,圭和表交叉于座中。人们根据日影的变化确实方向和节令,并由此制定历法和确定疆土。这是因为一天内正午时的表影投向正北,一年内夏至日表影最短,冬至日表影最长。东汉的铜圭表是目前出土最早的一件天文仪器[21]。仪也指测量日影的器物,并引申出法度之意,《荀子·君道》:“仪正则景正。”《说文解字》:“仪,度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7](p250-253)这里提到了用土圭测日影之法测量土地四方的远近。由此,土圭引申为出标准和法度之意。关于立表测定方向的方法,《周髀算经》记载:“其术曰:立正勾定之,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指表者,正南北也。”[22](p91)确定方向之法:日出时刻立表而在表影顶端之处的地面做标记;日入时也同样对表影顶端做标记。在这两处标记之间以直线相连,则此直线即为正东西方向;将此直线的中点与表相连,则连线所指为正南北方向。《淮南子·天文训》用四表测东西南北:“欲知东西、南北广袤之数者,立四表以为方一里歫,先春分若秋分十余日,从歫北表参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应,相应则此与日直也。辄以南表参望之,以入前表数为法,除举广,除立表袤,以知从此东西之数也。”[20](p290-291)计算东西和南北的距离,可树立四个圭表,形成边长一里的正方形。在离春分和秋分十多天的日子里,从北两表参望初升之日,当两表与日共处于一条直线上时,再从南两表参望它,查看这时日与西南表的连线离东南表多远,再以此法去除立表的长宽乘积,就可以知道东西的距离了。
表之于日影,如仪之于德,它们都是事物本质的呈现,《墨子》:“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由圭表引申出了道德意义。一是中正和中庸[23](p166)。首先,是方向之中正。例如陶寺中期王墓IIM22:43漆杆的功能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史前时期至殷商时期被称为“中”,西周时期称为“圭”[24]。因表测影需居于祖槷之中。何弩发现:“‘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们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最大特征。”[25](p116-117)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诸侯,人主赐各诸侯以长条形的上尖下方的玉器作为凭证,令其前往指定地区规划土地,建立邦国。《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注:“土其地,犹言度其地。”[7](p254)二是忠信,表意味着将内在德行表明彰显出来——槷表将每天的日光变化表现为具体时间,将混沌的时间概念转换为守信如时的道德体悟,而君子则通过外在的仪表、举止显现自己内心的道德修养。所以,人们认为最能体现诚信的莫过于时间。而槷表作为测量时间的器物,具有了信义与准则之意。以槷喻德的本质在于由时间引申出的忠信思想,其实这是人们修德所奉之圭臬。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男子执槷以表对君主忠信不欺之臣德,女子执槷以示对丈夫有专一守节之妇德,邦国间的外交和结盟则往往以圭来表达诚信[23](p153-155)。由表的器物功能引申出道德意义,这其实是表被赋予社会意义的过程。
“表”还进入文体领域,臣子陈情表意、表达内心忠信之德的文体,乃为表。《文心雕龙·章表》曰:“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26](p44)这里以作为器物的表,喻表这一文体。臣下呈献天子的文体,有章、奏、表和议四种。章用以感谢恩赐,奏以弹劾罪行,表以叙述请求,议以坚持异见。《文心雕龙·史传》:“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26](p32)这里的表征,原意指测量日影的表所显示出来的征象。史传记载历史,有显示历史盛衰的功能。
律是测量音准和检验度量衡的器物。丘光明发现律管频率与声波的波长成反比,理论上闭口管空气柱基波的波长等于管长的四倍。因此,如果管的口径不变,那么频率与管长的四倍成反比。律管的频率定下来,它的长度也就可以求出。故用黄钟来校正尺度是符合科学原理的[27],古人“认识到音律的高低与管的长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有固定音高的律管,其长度是不变的。从而采用这‘万世不变’的律管作了检验尺度的标准”[28]。除此之外,人们还以律管作为检验容积和重量的标准。如新莽铜嘉量既采用了黄钟律来统一度量衡,又将度量衡三种标准附于一器之上。相传黄帝命伶伦造律之尺,一黍之纵长,命为一分,九分为一寸,共计八十一分为一尺,是为律尺。以黍粒横排,则百粒为一尺,相当于纵黍八十一粒。在律管上,从低音管算起,成奇数的六个管即阳六叫作“律”;成偶数的六个管即阴六叫作“吕”,合称“律吕”。律管在考古发掘中已屡屡出现。迄今发现最古老的律管是出土于江陵雨台山2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竹律管[29]。《汉书·律历志》记载律按节气分为十二音,称为十二律[2](p958)。十二律的名称,据《礼记·月令》记载是黄钟、太族、姑洗、蕤宾、夷则、亡射、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其相应的节气为“孟春之月,律中大簇”;二月“仲春之月,律中夹钟”;三月“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四月“孟夏之月,律中中吕”;五月“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六月“季夏之月,律中林钟”;七月“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八月“仲秋之月,律中南吕”;九月“季秋之月,律中无射”;十月“孟冬之月,律中应钟。十二月“仲冬之月,律中黄钟”;十二月“季冬之月,律中大吕”。[4](p470-497)这就将节气与音律对应起来,音律具有了自然法则的意味。《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大蔟。”郑玄注:“律,候气之管,以铜为之。”[4](p448)《周礼·春官宗伯·典同》:“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7](p622)凡制造乐器,以十二律来确实其度数,对照十二病钟的声音来校正大小容量。调整旧乐器也以此为标准。
《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30](p108-109)钧为度量钟音律度大小之器,以七尺之木,系之以弦,击弦所发之音,以定钟音之律度。比之今日之乐器,“钧”即今之“标音”,以此定乐器律度之高低。“大不出钧,重不过石”,谓音律度之大者不得超过钧所发之音,钟之重不得超过百二十斤[31](p280)。在单穆公看来,先王制钟有着特定的规格,律、长度、容量、重量都因此确定。如果声音无法被听到,形制不符合规定,钟声不和谐,规格上无法成为标准,那就无益于乐而浪费民财。
由音乐的声律到社会的法则,实现了意义的引申。律是月令变化的秩序,用律管测量时令、节气的变化,即所谓“候气法”,这体现了乐律统帅着历法与度量衡(9)参见戴念祖、王洪见:《论乐律与历法、度量衡相和合的古代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关于候气法之科学性的争议,参见黄一农、张志诚:《中国传统候气说的演进与衰颓》,《清华学报》(新竹)1993年第2期。。在律的基础上衍生出法则、法令的意义。《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4](p1459)自秦汉后,制乐者都标榜以西周初年的古黄钟律为典则,同时也常用来作为制定度量衡的标准。由古黄钟律来制定的乐,代表了西周的“雅乐”。司马迁这样解释人类法度与乐律之间的关系:“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5](p1239)律既具有自然法则的意义,也具有人间法则的意义[32]。
《尔雅·释诂》:“律,[……]法也。”[33](p15)“‘律’作为法律、法令的意义出现,最晚不会迟于商。”[32]如前所述,《汉书·律历志》记载中国古代度量衡的观念皆起源于黄钟律管。古人以黄钟律管的长度为“度”,以其管孔容积为“量”,以其质量的九分之一为“衡”[34]。“律”本身是确定度量衡的器物,律管还具有确定月令的功能,这引申出了规范和标准之意。根据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制定政令对国家政治和经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政权因度量衡标准的制定而得到巩固和加强,经济贸易则因有了统一的标准而能顺利交易,音乐因有律而和谐,可以成教化、助人伦,整个社会都因有律而秩序井然。
在中国早期哲学中,“律”成了万物所由出的根本的自然法则。李约瑟发现了“律”字作为法律和律管之同的关联,即它联系着非人类现象和人类的法律两个领域。在李约瑟看来,“在协调的思维中,各种概念不是在相互之间进行归类,而是并列在一种模式之中。而且,事物的相互影响不是由于机械原因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ance)。”[35](p304)由这种感应产生了宇宙类比,即人事和天地之间的对应。
四、结语
哲学的言说,本质上是一个隐喻的系统。在度量衡用语转变为哲学话语的过程中,计量之原意被淹没和混合到了新的概念模式,在对社会的阐释、比较和评价的过程中起到了表述的作用。这些隐喻并不是偶发的,而是取鉴于其计算长度、容积、重量,以及测量月令的物理功能。它们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延续性,生发出了思想构成的元素。
度量衡的功能体现为数量的确定和使用。一方面,对数量的掌握是人生修养的必需。《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载保氏以“六艺”教育贵族子弟,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指“九数”。东汉的郑玄引郑司农所言:“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7](p353)《管子·七法》说:“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16](p106)另一方面,对数量的掌握是探寻天地规律的条件。《汉书·律历志》:“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2](p956)这里列备数为第一,也说明了数是度量衡的共用之处。《后汉书·律历志》:“夫一、十、百、千、万,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历,其别用也。”[36](p2999)这里将数量之用与度、量、权衡和律之实统一起来。
但是,在取用度量衡的社会意义时,人们注重的不是数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类比,而是物理功能与社会意义的类比。一是度量衡用以喻道,即以数量关系实现对天道的呈现;二是度量衡用以比德,即由度量衡的测量意义引申出道德意义;三是度量衡用以喻法,体现为法度观念的确立。这就将天、人和器统一起来,以器象天、以器藏礼、以器比德、以器喻法成了一个有机的序列。在此一序列中,“法”的意义多取自具有规范意义的器物。其中,度量衡类器物是最为主要的。如《管子·七法》提出了“六法说”: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16](p106)
《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16](p998)法令是君臣共同设立的,也是官吏和百姓行为的准则,而权势却是君王独揽的。《汉书·律历志》进一步说明了“五则”之间的关系:
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2](p970)
由权到衡、规矩、绳、准的过程,是一个由前生后的序列,上述五种器物与阴阳、宇宙、天地和政治之间有着关联,这就建立了一个天、地和人合一的系统。
由制作和技艺而来的度量衡,引申出了道、德和法的意义,这就溢出了其原始的计量功能。以度量衡器物来诠释礼、法、德,尽管各家的倾向有异,但论域是相同的。在此一过程中,度量衡的意义主要体现于道德和法度观念的确立。如“科”的本义是“度量衡”的总称。《说文解字》:“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科”是会意字,从禾从斗,字形意是用斗测量粮食(10)中国现代“科学”一词属于外来词,对应于英文的science。而在西方,科学的本义是关于测量自然的学问。吴国盛认为西方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前一个传统是大传统,后一个是小传统;前一个是西方区别于非西方文化的大传统,后一个是西方现代区别于西方古代的小传统。吴国盛:《“科学”的辞源及其演变》,《科学》2015年第6期。。关于程,《荀子·致士》:“程者,物之准也。”[10](p262)可见,程也是度量衡的总名。《说文解字》:“规,规矩,有法度也。”段注:“法者,刑也。度者,法制也。规矩者,有法度之谓也。”[19](p499)从科、规、矩的原意看,其计量功能是基础的,其道德和法度意义是衍生出来的。这说明观念的建构元素是概念,而概念有着生成的机制。人们惯于通过有形、可感的事物,来说明无形、抽象的意义。
总之,在政治和伦理领域,度量衡被用以为社会规范制名(11)中国早期的“制名”活动,受“远取诸物”思维方式的影响,存在着以器物为话语制名的现象,参见闫月珍:《作为仪式的器物——以中国早期文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此外,模、范、型和则也被用以为社会规范制名。模、范和型都是制器的模型,分别为木、竹和土所作。《说文解字·木部》:“模者,法也”;《说文解字·竹部》:“范者,法也”;《说文解字·土部》:“型者,铸器之法也”;则也具有法度之意,《说文解字·木部》:“则,等画物也。”则是一个会意字,指用刀在模、范上刻画图案或文字,其本意为“制模器样”,由此引申出了制器模型之意[37](p94),如《诗经·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就是这个含义。在探寻社会秩序话语的过程中,人们参照了度量衡的物理功能,引申出了社会意义,由此确立了道德和法度领域的基本表述方式。
从中国早期计量方式,可以发现制度话语的产生,固然出于人为的设定,但与器物和技术的关系更为直接。马凌诺斯基说:“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12)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页。马凌诺夫斯基主张探讨物质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他将文化分成四个方面:物质、精神、语言和社会组织,“物质文化”是其中的实体,而具有观念性的精神和社会性的制度是文化的真正要素。物质和文化往往直接关联,他发现“高度的物质繁荣的时期,往往在精神上是堕落的。当文化的物质方面过于发达的时候,当运输和破坏的方法,以及大量生产和广告,支配着一个国家的生活的时候,整个社区便充满着穷奢极欲式的虚假和妄狂的需要的满足,到这时,整个的文明都大堪忧虑。人类历史上的现今这时代便是一例”,参见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物质文化往往产生了与其相配的语言和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度量衡与中国早期哲学的建构,也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之中。在度量衡与中国早期哲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器物和技术促成了制度和观念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