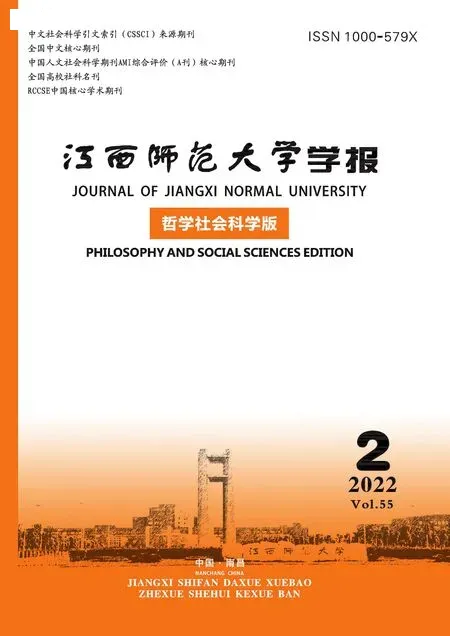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现代性隐痛
——以贾平凹《暂坐》为中心的考察
马建珠
(1.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井冈山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西 吉安 343009)
新时期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方面,贾平凹的态度可谓犹疑而迷茫。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的封闭、落后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但情感上对传统的风俗人文不由自主地产生迷恋;另一方面,他对现代文明导致的人性迷失感到无比痛心,但理智上他却深知现代文明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这种既坚守又批判、既摈弃又迷恋的矛盾与痛苦,可以说是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而产生现代性精神之痛。这种现代性精神之痛本质上就是对传统价值的艰难决裂与对新价值的犹疑认可。因为“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1](p15)。贾平凹在这现代性的痛苦漩涡中难以自拔,他曾多次提到:“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2](p450)这种犹疑的精神之痛,与贾平凹阴柔的美学追求以及简约的叙事风格,形成了一种隐痛叙事的美学特质。分析和理解贾平凹的这种隐痛美学,对于贴切把握作者的文化心态,以及其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一、都市女性主体性的隐性缺失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男女有别”,《周易·系辞上传》中有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3](p531)当男女社会地位以“天尊地卑”的方式来引证的时候,“男尊女卑”便有一种天地之道般的伦理合法性。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以此来规范人伦秩序,这种“男尊女卑”的伦理传统便逐渐内化为中国文化基因并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女性的独立与解放之路也就注定要走得颇为艰难。“五四”以来,启蒙者将女性解放上升到人的解放的高度,也仍然避免不了其先验式的文化宿命。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即使凭借爱情的力量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最终也无法走出脱离“父权”陷入“夫权”的命运怪圈。庐隐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茅盾笔下的都市新女性,丁玲笔下的反传统女性,她们同样都致力自身的个性独立与命运解放,但也走不出男权中心话语所建构的生存空间。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体性意识随着人道主义的倡导又得以高度张扬。张洁《爱,是不能被忘记的》、张抗抗《爱的权利》、王安忆《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池莉《不谈爱情》、铁凝《麦秸垛》等,以爱情为主题,不仅表达出个体的生命意识,更彰显出女性的身份意识与主体意识。林白、陈染、卫慧与棉棉等作家对女性的主体性似乎表现得尤为极致,她们在自我封闭的情感空间中审视自我最潜在的生命欲求,甚至直接以个人欲望的大胆呈现而彰显出对男权中心话语的抵制与消解。女性作家文本中这种强烈的女权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男权中心文化所造成的性别冲突。
在男权中心话语中,“文学”可以说就是一种男权文化的延伸。所以在男性作家中,他们并不像女性作家那样以鲜明的性别冲突意识去彰显女性主体性,而更多的是以其潜在的男权中心话语去塑造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从而达到对男权秩序的建构与巩固。莫言《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蛙》中的姑姑,她们敢爱敢恨、性格果敢坚毅,具有一种女性阳刚化的审美特质。莫言以一种“原始生命力反抗”般的生命张力完成对理想女性的审美建构,从而形塑中华民族坚毅的女性形象。贾平凹小说的女性更多体现为一种阴柔之美。这些女性有传统之美如“菩萨”、宽厚质朴如“地母”,她们身上更多体现出作者心中理想女性的审美特质。即使现代气质如“女妖”,或妖艳妩媚如“欲女”,她们身上也不具有那种强烈的性别冲突意识与女性主体意识,但这些女性最终也难免“放弃成为主权主体的权利要求”[4](p774),而表现出对男权中心文化的主动迎合与臣服。
贾平凹《暂坐》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较他以往的小说似乎有更多的突破。从小说人物构成来看,《暂坐》塑造了十几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而男性人物如羿光却退居为从属地位,这在贾平凹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从小说主题来看,这是贾平凹第一部以女性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小说。他以聚焦性的叙述方式,集中叙写了都市女性日常的生命情态;从女性人物精神气质来看,小说中的十多位女性经济富足、气质高雅,而且时尚靓丽、个性张扬。同时,她们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经济独立,思想开放,甚至对有违一般世俗伦理的同性相恋,也不是讳莫如深,而是有一定的包容性。另外,她们经常用染奶奶灰、讨论苹果肌下垂、购买名牌包包等各种现代都市女性的文化消费符号标榜自己的个性与独立性,俨然深具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气质。这些都是贾平凹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突破。
关于理想女性,贾平凹曾这样说道:“以你所言的‘女菩萨’式和‘女妖’式的女性,我喜欢的,两种特性能结合起来最好。”[5](p218-219)也就是说,贾平凹最理想的女性就是既具传统美德,又具现代性气质,是传统与现代的两者融合。《暂坐》中的海若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贾平凹对女性形象的理想建构。海若情感细腻,关爱姐妹,又懂经营、善管理,遇事沉稳、行事有章,同时又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她的形象集中体现男权中心话语下对女性人物的理想建构。但正是这样一位理想的现代女性,其实也隐含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层隐忧。因为她貌似独立实则对权力有严重的依附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权力的依附无疑就是对男权文化的屈从与认同。海若商业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富足,完全是她依靠对男性权力的经营与利用,她时尚现代的表象掩盖的是依附权力关系的实质。相对海若而言,严念初人物的设置不仅体现了对其主体性的精神审视,更着重于她的人格审视。严念初开名车住别墅打高尔夫球,在众多姐妹中似乎完全实现了经济独立与精神自由。事实上,她表象的富有也是靠她精于官场规则、甚至不顾伦理底线地对男性的巧取豪夺而获得。她不惜违背自己的本心,在没有任何情感基础的情况下嫁给痴迷藏玉的阚教授,怀上了他人的孩子后又通过离婚获得了巨额家产。为了能中标医院的医疗器械业务,严念初在王院长面前极尽讨好与奉承之能事,甚至不顾廉耻地对王院长以各种性暗示,这些行为显示了她毫无人格底线的人格特征。另外,为了巴结讨好王院长,她与王院长一起联合算计朋友应丽后,致其本金回收无望。严念初表面的风光完全是依靠对男性的取悦与依附而获得。诚如波伏娃所言:“如果要成功地过女人的生活,她就只能取悦于男人。”[4](p773)严念初充分利用其年轻貌美的资本,臣服于男权话语下的建构规范,完全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这方面,严念初可谓达到了极致。而辛起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惜放弃自己的老公,甚至通过做“缩阴术”取悦一位七十多岁的香港老板。当被抛弃后,又想骗取香港老板的精液而去做试管婴儿,并试图以此作为要挟而获取财富。这种极端的方式无疑体现出一种“前现代”的、丛林法则式的生存方式。另外,无论从出身、职业、地位,还是生存环境与精神气质,辛起都与海若、希立水等姊妹完全格格不入。而作者将她与众姊妹置放在一起,其实就是为了让她与众姊妹形成对照性审视,从而将辛起的个人命运引申到对整个女性命运的追问与思考。
主体性本质上就是主体之所以为主体的一种质的规定性,它是一种建立在非异化主体上面的个人审视,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是保持自我生命主体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当以性别角色去审视这些时尚女性的主体性精神时,不仅海若、严念初、辛起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其他女性人物也同样缺少真正的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徐栖敏感而又自卑的城乡意识,陆以可以算卦的方式决定生意上的决策。她们又似乎与三十年前《废都》中的唐宛儿、柳月其实并无二致。甚至作为外来者的伊娃,也完全中国化的心理思维,缺少作为外来者所应具有的一种异质性。这些女性身着“现代”性的外衣,包裹的却是“前现代”的灵魂。她们的行为主体逻辑仍然是以男权中心文化为主导,这也就决定了她们从根本上无法摆脱被男权中心文化所同化的命运。
中国女性命运的坎坷除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因袭外,还有男性作家对理想女性的审美建构无形中又参与并强化了对女性的规训。诚如一位女性主义者所言:“男人写的所有有关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4](p17)贾平凹一方面以男性的视角表达出对女性生存境遇的隐忧,另一方面,贾平凹又以男权中心话语完成对理想女性的塑造,这在无意中又强化了对女性的文化规训。另外,男女的先天性差异也同样造成了女性命运改变的艰难性。因为“男性呢就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的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6](p221),这种差异性导致女性要取得自主的胜利就必须牺牲女性气质,也就是说女性唯有遵从男权话语下的“他者”建构规范,放弃自身的主体性权益,降格为男人的客体性存在,才有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即使“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4](p773)。这似乎注定了女性的主体性命运的解放就永远是一个无解的悖论性与先验性存在。
《暂坐》中女性人物所体现出分裂的人格特征恰是贾平凹犹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性症候。一方面,贾平凹以现代性元素描绘出当下都市女性的生命情态;另一方面,他又以“前现代”女性的思维特征无意地消解了她们身上的主体性,构成对这些女性的精神审视。贾平凹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既建构又解构的叙事姿态表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关怀与深切隐忧。但这些女性的人格特质,也表现出贾平凹难以彻底决裂于历史传统,以致缺乏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视野,从而难以对这些女性进行超越性的精神审视,使得这些女性都表现出一种外在时尚内在传统的双重文化人格特征,从而缺少一种真正的现代性女性人格特质。
二、知识分子现代性人格的缺乏
贾平凹虽然一再强调其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并坚持采用一种底层叙事的姿态,书写其个体的生存经验。但他也跟鲁迅一样,在“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7](p272)。因而,知识分子也是其小说创作中重要的书写对象。无论是《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还是《高老庄》中的子路、《秦腔》中的夏风,这些人物形象都缺少知识分子现代性人格特质,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旧式的文人姿态,凸显一种潜在的男权中心意识,而且他们在文本中总是与女性人物形成一种“男主女仆”式的文化结构。这基本上构成了贾平凹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类型。
《暂坐》中的羿光在精神气质上与《废都》中的庄之蝶最为接近,两部小说又同样是以西京都市生活为背景,有学者认为《暂坐》与《废都》“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西京遥相呼应的‘两都赋’”[8]。因而,将羿光与庄之蝶进行比较分析,能更深入地把握住羿光的精神特质。
《废都》可以说是一部承载作者生命苦难经验并蘸着他血泪的心灵之作,也是一首无家可归的生命挽歌。这部作品最具文学史意义的地方,就是写出了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积淀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那压抑无奈而又迷茫无力的心路历程,并形塑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塑像。然而,小说中的庄之蝶摆脱不了其旧文人的气息,他爱好文物字画,自命不凡又自我封闭,对待女性也完全是旧文人的那种狎妓的心态,没有对女性所应具有的尊重,缺乏现代性的平等意识。同时,还以神秘的定数论阐释世间的因果关系,消解了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理性意识。
如果说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废都》中庄之蝶的塑造还缺少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视野,那么,在历经30余年后,《暂坐》中的羿光同样表现出浓重的旧式文人趣味,仍然看不到贾平凹在羿光身上所赋予的新的人格特质。小说中的羿光跟庄之蝶一样爱好文物字画,讲究文人的风雅趣味。虽然与众多的女性保持着一种亲密的知己关系,同时,还总是以救赎者的姿态表达他的人生智慧与生存感悟。但他与庄之蝶一样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命不凡,从骨子里都缺少对这些女性真正的尊重。尤其是羿光跟伊娃在拾云堂亲密的一幕,更是显示出他“文人无行”的一面。
羿光与庄之蝶虽然同样具有内在心灵之痛。但是,相比于庄之蝶的落寞茫然、阴郁颓唐,羿光则以一种外在的旷达与闲适遮蔽其内在的隐痛。所以羿光既能与众姊妹打笑取乐、与朋友玩牌休闲,也能给身边朋友讲禅论道,缓解人生苦闷,完全是一幅融入俗世的闲适图景。同时,他又能痴迷于收藏、赏玩古物,表现出一副大隐隐于市的旧式文人姿态。然而,如果仅此认定这是羿光的全部精神人格特征,则显然没有穿透其闲适旷达的表象,审视其作为知识分子最为内在的心灵之痛。那么羿光在貌似旷达的背后,又具有什么样的隐痛呢?羿光与伊娃在拾云堂亲密的一幕可以视为把握羿光内在心灵之痛的关键。当羿光正好与伊娃作画调情并极度放松的时候,一个代表官场权力的电话立马让他正襟危坐。我们首先看他在权力面前的屈从:“嗯,嗯。我听着的。我和他是熟的,也仅仅是给他汇报过工作的熟,他也是以示关心作作秀么,当然要划清界限。呃。呃。是明天的会吗?这我宜不宜参加?哎呀,约好了医生去看病的,能不能不参加呢?嗯,嗯。那好吧。我听你的,那就参加。还必须有个表态发言?这该说什么呢?好吧,好吧。”[9](p172)羿光这种唯唯诺诺的恭顺态度与他日常落拓不羁的样子判若两人,这也许是羿光的一种言辞应对策略,但无疑显示出他对权力的屈从;再看权力对他的身心影响:“伊娃倒觉得羿光像变了个人似的,声音一惊一乍,表情也极其丰富,她忍不住要说你这是在表演吗,但看着羿光的脸色,却没有敢开口。”[9](p172)从羿光接电话声音的“一惊一乍”与丰富多变的表情,体现出羿光对权力话语的附和。同时,当他与所喜爱的伊娃性爱时,表现得颓唐不堪,以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都体现出权力对羿光的身心影响。最后羿光在此情境下的内心感慨最能表达出知识分子的精神隐痛:“我现在能做什么呢,无非是避免着中于机辟,死于罔罟,安时处顺地写写文章,再作些书画,纯粹是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但往往还不行。”[9](p75)这是小说中最具叙述情感显现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羿光内在精神的地方。羿光的感慨诉尽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秩序面前的各种无力与无奈。
羿光的这种精神隐痛与他日常的闲适旷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忽视贾平凹小说中这种精神隐痛,则很难理解其小说的深层意蕴。王尧曾就有些批评者误读或根本读不出文中深潜着的痛苦提问贾平凹,贾平凹则认为:“特别激愤的东西他们能够看到,但激愤有好多种,它转化以后,埋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拿苏东坡来讲,苏东坡一生遭遇也特别多,他也有激愤的东西,但是他把它化解成一种很旷达的东西。旷达这个东西比较闲适,它也比较消沉,实际上旷达就是一种彷徨苦闷又无奈,但是又放松自己的一种追求。”[5](p133-134)这种愤激的情感经过内在转化后表现出外在的闲适旷达,其实就是一种难言的内在隐痛。
然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挠现状的人”[10](p2)。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10](p6)。如果我们将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特质的参照,那么羿光的所谓“闲适”“旷达”除了具有内在的心灵之痛外,更具有羿光对现实的无力反抗与无奈屈从的实质。知识分子作为代表社会的责任与良知,却在面对权力时表现得唯唯诺诺,更何况说要向社会发声,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议。羿光这种对权力与现实的屈从无疑喻示着知识分子的一种失语与失职。所谓失语,借用冯友兰的话就是“一个人在说了很多话之后的静默”[11](p252)。这种静默与知识分子应为公共事务“发声”形成鲜明对照,彰显知识分子“妥协”与“退却”的入世姿态。一方面,羿光仍然保留了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作为众姊妹的精神导师,他身上延续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职能。在价值失落的现实处境中,他也能寄情于书画、赏玩古物,以一种超然于世的姿态悬置自我,并以此标榜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另一方面,他又精明务实,精于世故。在现实中也只求能“避免着中于机辟,死于罔罟”,完全是一副明哲保身的生活姿态。所以他才会在卧室门口置一对天聋地哑的石雕童子,并以“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说的不要说”作为警示自己的处世箴言。对照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职能,羿光无疑是对自我责任与使命的主动放弃,是一种可悲的“现场逃遁”与“失职”。羿光这个人物形象,喻示着知识分子已从致力终极价值的追寻蜕变到安然现实秩序的犬儒主义者。这种角色使命的退化隐含着贾平凹对知识分子人格异化的深切忧虑。
在贾平凹三十余年小说创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塑造,《暂坐》中的羿光在精神底色上与《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高老庄》中的子路等知识分子形象并无二致。首先是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那浓郁的旧式文人情怀,他们都迷恋于传统,但又都缺少一种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所应具有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人格特征。其次是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浓郁的男权意识,缺少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平等观念。无论是《暂坐》中的羿光与海若、伊娃,还是《废都》中的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白夜》中的夜郎与虞白,《高老庄》中的子路与菊娃、西夏,《秦腔》中的夏风与白雪等,这些男女关系都具有一种潜在的“男主女仆”式的结构模式,女性主要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即使笨拙、内向执拗的子路、夏风,他们身上仍然显示出浓厚的男权中心意识,这无疑表征出贾平凹潜藏在骨子里的浓厚的传统宗法意识。贾平凹自己也曾表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身上传统的成分更多一些[5](p127)。贾平凹的这种偏向传统的文化视野导致其“现代性”不足的病症,决定了他难以像鲁迅一样以现代性的视野进行超越性的审视与批判,达到“对进化既深信又深疑、对启蒙既倡导又警惕”的尖锐深刻,从而形成一种“忧愤深广”美学特质。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贾平凹对《暂坐》中羿光的人物塑造仍然没有跳出其惯有的文化视野。
三、隐痛的叙事美学及其叙事的悖离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不仅仅体现在小说人物的传统型人格方面,也体现在叙事方面。他认为:“整个中国人的思维认识,中国哲学和美学呈现一种阴柔的东西。……所以阴柔的东西最容易幻想、浪漫、抒情,也最容易咏叹人生,也最容易表现日常、也最容易表现悲剧。缺点是和西方相比,写得很不极端,容易流于软和模糊。”[12](p111)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决定了贾平凹小说具有一种阴柔的美学特质。另外,贾平凹是一位极为注重小说文体的作家,他还从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传奇体与笔记体中吸取叙事经验。胡应麟曾“将‘传奇’看作是古代小说在唐代的重大发展”[13],认为“传奇”讲述的多是一些荒诞奇异的故事。笔记体小说则可追溯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多以人物趣闻轶事为题材,具有写人粗疏、叙事简约的特点。相对传奇体的荒诞奇异,笔记体小说在书写人物日常轶事时,更为注重叙事的简约节制、平缓自然,不作惊人之笔。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既有传奇体小说以非常之事传达非常之情的荒诞性与奇异性,也有笔记体小说叙事简约的叙述特点。
《暂坐》中的叙事风格,颇合笔记体小说的叙事品质,这表现在其冲淡简约之美方面。小说采用散点透视的写法,将西京城各种世情与人情以生活原生样态的方式呈现。小说没有铺陈、夸张之笔,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刻意的叙述痕迹,一切显得自然而然,仿佛就是日常生活的再现。然而,小说叙述情感的克制与内敛,并不意味着对情感的排斥。《暂坐》虽然以平淡自然的叙事笔调展开叙述,但其中却呈现了茶庄由盛到衰过程,尤其是茶庄爆炸后众姐妹的离散,更是显露出世情的凉薄,隐含着作者强烈的情感。有学者认为《暂坐》在人物气质与叙事结构方面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也是对《废都》的延续和改写[14]。其实,小说中隐藏的悲痛的意味也与《红楼梦》《废都》构成了内在的同质性。因而,《暂坐》文本的叙事内核,并不像外在一样平淡自然,而是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愤激的悲痛之情。他将这种强烈、愤激的情绪加以克制与内敛,并将其融于一种极为平淡的日常化叙事中,从而达到一种“更多混茫,更多蕴藉”[15](p3)的叙事效果。这种隐匿的精神之痛与阴柔的美学追求、以及简淡自然的叙事风格形成了具有贾平凹特质的“隐痛”叙事美学。
有学者认为贾平凹“隐痛”美学中这种含混、暧昧的叙事特质,是其思想混乱与理想性匮乏的表现。这种评论固然抓住了贾平凹创作中的某些症结,但无疑也是对贾平凹迷茫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文化心态的忽略,也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价值冲突导致的多元性、复杂性的忽视。贾平凹也曾认为有些研究者只习惯于那种激烈的、极端的,而对于那种中庸的、中和的东西容易忽略。如海若人物身上的“中和”性就将我们导向一个伦理判断的尴尬境地。我们既不能简单地遵从道德伦理将其奉为“菩萨”,也不能草率地遵从商业伦理将其贬为“女妖”,更不能片面地认同她现实的生存伦理视其为“地母”。执其一端固然会明朗深刻,但往往也会造成对多元性与复杂性的遮蔽。而将其“中和”则反而让人物最为接近本相的生存状态。所以贾平凹文本中潜在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多种情感的交织与中和,是一种“冷漠中的温暖,坚硬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16](p90)。《暂坐》中伦理判断的尴尬不是贾平凹思想的混乱,也不是其理想性的匮乏,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带来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呈现。贾平凹正是以这种现代性的精神“隐痛”表征出转型社会所具有的驳杂与混沌。
然而,贾平凹似乎也在为其隐痛美学所带来的含混、模糊而作出调整。他一方面将自我的精神之痛隐匿在日常化的情境细节中,通过简朴的、传神的言语表达情境细节,并以琐碎的、反戏剧化的叙事,描摹出原生态的“生活本质”;另一方面,贾平凹又具有一种克制不住地对生活进行“理念”诠释的冲动,他总是通过设置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或借某个人物之口,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造成对叙事的干预。这种“情感”的隐匿与“理念”的呈现,既形成了贾平凹小说中潜在的叙述结构与张力,也导致了文本中“情”与“理”的疏离。在贾平凹的早期小说《土门》中,他以感伤的叙述笔调与切近社会现实的叙事姿态,书写了社会变革时代城乡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其中,无论是城乡交接处“仁厚村”的空间设置,还是成义、云林爷等人物设置,甚至“明王阵鼓乐”的魔幻化出演,这些情境细节都显示出作者对城乡关系一种二元对立式的理念化图解。在贾平凹的其他小说中,如《废都》中的收破烂老人、《极花》中的“老老爷”、《山本》中的陈先生与宽展师傅等,这些“超现实”的人物几乎都是以“智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像“先知”一样深不可测,也像个道德神话符号一样隐喻某种永恒。他们在文本中几乎都承担着一种“理念”诠释的功能。然而,这种“理念”又往往疏离于文本中的审美情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作者自身的情感和思考,往往大于作品的生活图景和艺术形象……作家自己对作品的诠释,不知不觉地超出了作品自身。”[17]贾平凹的这种叙事弊病又与其隐痛的叙事美学构成了分裂与悖离。
贾平凹的这种叙事的分裂与悖离,在《暂坐》中同样存在。贺绍俊认为《暂坐》是作者以散文化的方式抒发人生感慨[18]。这无疑指出贾平凹在文本中对人生经验做智慧性总结,尤其是在年近七旬,他这种叙事倾向更为明显。小说中所聚集的女性人物,完全不同于那种农业文明时代的保守与贫困,她们都是社会的中产阶层,女性中的精英,引领着都市社会的某种风尚。然而,她们虽然外表时尚光鲜,但她们内心又各有各自的隐匿的痛楚。于是,羿光等人物关于人性救赎的各种言论,都成为贾平凹对人生感慨的一种“理念”性总结。小说中,某个人物会时不时地冒出一段有违小说情境与人物性格逻辑的言论。如果说羿光是一位“启蒙者”,理念性的言论是他的一种话语方式。海若或冯迎也因为具有一定的文艺素养,她们的一些形而上的言论也还符合人物性格逻辑,那么,作为红木家具的老板司一楠,竟由日常生活中的涂脂抹粉的化妆,引申一番关于人性褪色说的言论:“临潼的兵马俑原本是有色彩的,但一挖掘出来就褪色了。西京城春夏秋冬不分明了,该冷时不冷,该热时不热,到处是灯光,白天没了怎么的白,黑夜没了怎么的黑。人也在褪色啊,美丽容颜一日不复一日,对新鲜的事物不再惊奇,对丑恶的东西不再憎恨,干活没了热情……是什么让我们褪色呢,是贪婪?是嫉妒?是对财富和权力的获取与追求?”[9](p89)这番言论明显溢出了小说的情境逻辑与人物的性格逻辑,具有明显的叙述干预性。贾平凹这种总结人生智慧的创作意图,既有他随着年岁的增长与人生阅历的丰富所导致创作心境的变化的影响,也有他对日常化叙事中的情感或理念不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担忧,所以他就通过设置特殊的人物形象或借某个人物之口,传达出他对生活的理解与诠释。丁帆也曾在品读《废都》时,认为“许多人看不到这心灵悲剧后面隐匿着的作者真情表达”[19]。所以贾平凹在文本中不仅有细节的委婉暗示,还有通过叙述代言人的设置来直接表达他的真实意图。但总体而言,《废都》与《秦腔》这两部作品是一种传奇体小说的叙事风格,具有一定的情节性与传奇性,并且融入了其切身的生命体验,有着强烈的内在情感作支撑,所以这两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能承载他的某些理性思考。相对而言,其文本中的“情”与“理”还能做到浑然一体。而《暂坐》主要是一种笔记体小说的叙事风格,淡化情节,行文简约,情感克制,因而“情”就难以承载过多“理念”表述,以致最终走向了一种“情”与“理”的分裂与疏离。
贾平凹小说中偏好对“理念”的诠释,显示他在叙事中追求一种形而上的叙事意图。但前提是应具有厚重的生活底蕴作为支撑,不能让“理念”的呈现虚浮于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所以这个“理”必须有丰厚饱满的艺术形象作为载体,做到“融情入理”,因为“情乃理之根”。否则,必将显得宽泛与空洞。另外,贾平凹在美学上既想追求一种生活的厚重与韵味的绵长,又想对生活作出理念性阐释,从而形成对文本的超越性文学意义。这在文本中既构成了一种叙述张力,也导致了一定的叙述失衡,从而造成了一定的美学缺失。
四、结语
贾平凹在《暂坐》后记中写道:“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就试着来做撑杆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9](p276)这无疑是贾平凹对自我创作突破意图的直接表述。但他又深陷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迷津,难以形成超越性的文化视野。这就决定了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看似极具现代性,但是这些人物内在的思想与思维仍然是以“前现代”的文化逻辑为主导。另外,贾平凹固有的创作理念,以及几乎每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高量产出,让他缺乏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有效提炼,以致难以将自己对生活的理性认识有机地融入日常化的生活叙事中,这就造成了他在小说创作中一些弊病的因袭重复。这些都决定了贾平凹难以对自我创作形成一种真正的突破。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