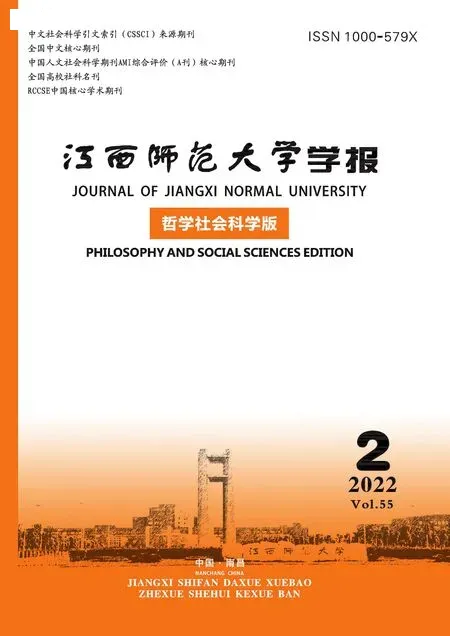从中国文学传统理解传统中国文学
——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的“中道”与建树
潘志刚, 陈文新
(1.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欧阳溥存(1884—?),字仲涛,江西丰城人,清末江西诗人欧阳熙之子。1894年,皮锡瑞(1850—1908)会试不中,南下江西,欧阳溥存在南昌拜其为师[1](p28)。1910年,与清末翰林黄大壎、留日学生汤本殷等人在南昌发起成立豫章法政公学学校(1)余洋,龚汝富:《近代江西法政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南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昌市志(五)》,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465页。。1911年,参加留学日本毕业生考试,取得优等,被授予法政科举人[2](p1109)。“中华民国”成立后,与孙雄(1866—1935)同在陆军第十九师师长兼江西庐山垦牧督办孙岳手下任职[3](p187),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内务部礼俗司司长一职,因祭孔肉糜烂一度被罢免[4](p486)。1915年至1916年,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声讨袁世凯倒行逆施、卖国求荣等行为。1919年,调任甘肃省泾原道尹[5](p403-404),1921年请从平凉四十里铺开挖渠道,得甘肃省政府批令就地筹款修建,事不成[6](p173)。20世纪20年代,先后在陆军总长张绍曾、军事总长何丰林等手下任职。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攻入北平后,辞官隐居。20世纪50年代初,从北京移家南昌,寄居其弟欧阳瀚存家,受聘江西文史馆名誉馆员职务(2)据欧阳溥存外孙肖云儒回忆,欧阳溥存民国年间住在北京,1951年左右移家南昌,1952年为抗美援朝捐款时,年68岁。参见肖云儒:《讲书堂笔记(三题)》,《海燕(都市美文)》2006年第9期。。欧阳溥存浸润中、西两种文明,极为留心文化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思想引进、泰戈尔介绍、中华大字典及中学教材编撰等方面贡献不俗(3)欧阳溥存编撰、出版的著作有《中华大字典》(1915)、《中华中学经济教科书》(1912)、《母道》(1914)、《新中学教科书经济学大意》(1925)、《中国文学史纲(中等以上学校用)》(1930)等。欧阳溥存文学创作多见于《大中华杂志》《东方杂志》《中华妇女界》等期刊,孙雄《旧京诗文存》亦有收录。1912年,欧阳溥存在《东方杂志》发表《社会主义》(第8卷第12号)、《社会主义商兑》(第9卷第2号);在《新世界》发表《驳社会主义商兑》(第8期)。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其与陆费逵等人编撰的《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万多个,影响巨大。1916年,在《大中华杂志》发文《介绍太阿儿》(第2期)。。
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是为中等以上学校编写的教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前后刊印达6次之多(4)此后1931年、1932年、1933年、1938年、1976年均有再版。除1976年版系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外,其他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年版标为“国难后第一版”,1933年版标为“国难后第二版”。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整理该著时发现,书中引文多有删节,且不乏文字上的瑕疵,为呈现原著面貌,本文所引该著凡有问题处,不做更定。。这部教材分上下两卷,共四编十九章:第一编“上古文学史”以秦为断,第二编“中古文学史”以隋为断,第三编“近古文学史”以明为断,第四编“近世文学史”专述清代。
1931年,金毓黻阅读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论道:“昨日阅市,得欧阳氏所撰《中国文学史纲》,书仅八万言,既具古今之要删,复极文学之能事,读之不忍释手,此亦可诵之名著也。……欧阳氏之作,视诸作为最后,而意不矜饰,语无支蔓,盖以简洁胜人,所谓后来居上,其此之谓乎!”[7](p2552)1944年,戴逸在常熟读高三时,学校增设了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教材即为欧阳溥存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正是这门课程帮助戴逸“奠定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8](p16)。这也许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史纲》是一部值得重温的文学史著作。
本文以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为讨论对象,旨在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化对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整体研究。
一、在“纯文学观”风行时期依然秉持中道
20世纪初,第一部本土“中国文学史”诞生,它是清末林传甲(1878—1922)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时撰写的讲义。随后,“中国文学史” 陆续撰写出版,至三十年代形成高潮。虽然都名为“中国文学史”,但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与早期文学史的面貌已大有不同,其显著特征是“纯文学观”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931年,胡云翼(1906—1965)在为他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所作的《自序》中就这一现象作了评述:“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如谢无量、曾毅、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著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9](p4)胡云翼把欧阳溥存列入“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其实就《中国文学史纲》的撰写出版时间而言,欧阳溥存与胡云翼属于同一年代。
胡云翼的评述是在“纯文学观”渐次风行的背景下做出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文学史”中“纯文学”的比重逐渐加大,最终成为“文学史”的主体。1935年出版的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甚至明确以“纯文学”作为书名。以“纯文学观”选择文学史研究对象,其特点是强调诗、文、小说、戏曲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不过传统的古文因其偏于载道而被入了另册;文学史要以“纯文学”文体为主要的叙述对象。符合“纯文学”观念的古代文体被划分到相应的领域,如诗、词、散曲属诗歌,古文、骈文、小品文属散文,等等。后来,“纯文学观”与“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结合,《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得到格外重视。
欧阳溥存对于“纯文学观”是了解的,也大致认同,他在《绪论》中明确指出,文学史“组织之要素固存夫集部”[10](绪论,p1)。中国传统的知识门类,以经史子集为基本框架。比照现代的学科建制,子部与哲学较多对应,史部与史学较多对应,集部与文学较多对应;经部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类,而是意识形态地位的标志,所包括的作品可以分别划入哲学、史学或者文学,如《春秋》可划入历史,《诗经》可划入文学,《易经》可划入哲学。欧阳溥存以集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赞赏昭明太子《文选》、姚鼐《古文辞类纂》等选集不收录经、子、史部的作品。他认为,相较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归为“文学文章”,《文选》《古文辞类纂》的选文更为允当。此外,欧阳溥存在第十七章“元文学”设置了“南北曲章回体小说”一节,第十八章“明文学”设置了“戏曲”一节,第十九章“清文学”设置了“词曲小说”一节,显示出自觉与“纯文学观”衔接的理念,这说明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理念上他都不应该被划入“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
与胡云翼、刘经庵等有所不同的是,欧阳溥存虽然了解并认同“纯文学观”,但能秉持中道,致力于从中国文学传统理解传统中国文学。刘勰《文心雕龙》、颜之推《颜氏家训》有文学“出于经”的说法(5)刘勰《文心雕龙》有《原道》《征圣》《宗经》等篇章,颜之推《颜氏家训》有《文章》等篇章,均将文学的源头推至儒家经典。,但现代学者通常视之为一种虚与委蛇的门面话,或者视之为一种陈腐观念的延续。其实,这句在中国古代习以为常的话,确实说出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核心部分,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政治、社会生活,也深刻影响了古代作家的人生和创作,构成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有机而重要的部分。子史的影响虽然不那么大,却也不能忽视。欧阳溥存对这一事实深有体察,所以他赞许“文学源自儒家经典”的观点,说文学史“不能置经、子、史于不谈”[10](p1)。这一理念,与原生态的杂文学观已有所不同:不是对作为理论的“纯文学观”的否定,而是对具体文学史研究中已产生偏差的“纯文学观”的矫正。例如,《中国文学史纲》设有“两汉文学起源及其流变”“经术及玄学”“诗文体格之变迁及各种学术之发达”“道学与文学之关系”“宋人征实之学”“清代文学昌盛之由”“考证及翻译”等小节,并非为了附和“文以载道之说”,盖欧阳溥存明确说过,他对“文以载道之说,深所弗取”[10](编辑大意,p2),而是为了揭示影响文学发展的文化因素或文学生态。
欧阳溥存在《中国文学史纲》中安排了他认为不可忽略的“文字”知识。他提出,“言中国文学,略应析为三事:其一曰文字,考求形声、训诂之本原;其二曰文法,指示安章宅句之程式;其三曰文学史,叙述历代文章体制之变迁,而评骘其异同得失。”[10](绪论,p1)文字、文法、文学史这三大知识板块涉及现代学科中的文字学、文章学和文学史等诸多门类。作为中国文学的文化基础,欧阳溥存确信有讲述的必要。
欧阳溥存对唐以后的文学进程“多依当世文章体制为别”[10](编辑大意,p1),以“诗歌”“散文”“小说”“词”“戏曲”作为小节标题,与唐以前的章节设置迥然有别。唐以前的讲述,如第一编有“儒家之文学”“道家之文学”“法家之文学”“名家墨家之文学”“纵横家词赋家之文学”“杂家之文学”“兵家之文学”;第二编有“传注之文”,第三编有“注疏之文”“佛教之文”,等等;上编第四章以“孔子文学”为题,下分“易之文学”“书之文学”“诗之文学”“礼之文学”“春秋之文学”“余经之文学”“孔门弟子之文学”“纬书之文学”等小节。这种体例上的前后差异,显示欧阳溥存对实际文学发展状况的尊重,他不想让事实迁就一刀切的所谓“纯文学观”。
二、在写法上有述有作,述作并重
欧阳溥存“编辑大意”指出,“以八万言叙论中国四千年文学,稍欲求备,则满纸皆人名书目,将令读者了无所得。”[10](编辑大意,p1)如何用不足九万字的篇幅展现中国几千年文学的面貌,做到既不罗列篇目、跑马观花,又让中等学校以上的学子开卷有益?欧阳溥存的办法是:“提纲挈领,其为一代精神所表现、后来著作之渊源者,特加详述,余从简略。”[10](编辑大意,p1)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详略有度、言之有物,在于他灵活运用了有述有作、述作并重的写法。
在文学史写作对象的选择上,欧阳溥存以传统史志、书目为依据,努力将“一代精神所表现、后来著作之渊源者”纳入教材,抉择审慎。欧阳溥存认为:“今世所谓文学史者,比况旧籍,其范围视《唐书·艺文志》所列文史为广,其性质与后汉以来《文苑传》略同。”[10](绪论,p2)他把中国文学史取材的对象大体划定在史志、图书目录、总集、选集等所覆盖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史书和图书书目所覆盖的范围之内,使用最多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史志之外,《七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四库简明目录》等图书书目,以及《文选》《唐诗纪事》《唐宋八大家文钞》《唐贤三昧集》《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十八家诗钞》等总集或选集也多所参证。凭借这些著作,加上他的中西教育背景,他对历朝历代文学面貌的把握,基本达到了他所认为的“提纲挈领”的要求。
例如欧阳溥存对“文苑传”的倚重。历代正史的“文苑传”,本是史书“列传”体例下的一个门类,与“儒林传”“列女传”等并列。自从曹丕倡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1](p313),专以文章名世的才俊开始受到史家的关注,范晔撰《后汉书》,专设“文苑传”,并为后世史家递相沿袭。“文苑传”与“文学史”的区别当然不少,比如,“文学史”重视历代作家之间的纵向联系,注重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与启示,以及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创新,而“文苑传”只是作为一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部分,注重的是历史人物之间的横向联系;“文学史”以展示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为中心,重在演绎某种“规律”统领下的文学发展进程,而“文苑传”则以排列传主关乎天下治化的生平行事为主,秉笔“实录”,并不在意所谓“规律”的统领作用;“文学史”通常对不同文体、不同作家、不同作品按文学成就的高下排出先后,安排篇幅大小,文学之外的生平事迹以及那些被确定为文学成就不高的文体、作家、作品,只是与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状况一起作为背景被提及,那些与文学成就较为疏远的内容则被消解,而“文苑传”则按史家的标准而非文学的标准进行安排,所著录的文章与传主生平事迹之间也没有主体与背景的分别(6)参见陈文新、甘宏伟:《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但总体看来,“文学史”写作借鉴“文苑传”,确实是现代中国文学史著述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以唐代散文部分为例,欧阳溥存抓住“燕许大手笔”这一枢纽,不仅介绍了苏颋、张说的大致情况,而且分别附录了两篇文章。不是说欧阳溥存偏爱苏、张二人,而是说他们两人在当时的确具有很大影响,如此取材,理据充分,足以显示其时的文坛风尚。
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欧阳溥存主要依据史书记载和古代的诗文评,与胡适等人的“重新评价”迥然异趋。如关于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的叙述,几乎全部来自《史记》《汉书》。这里摘录苏洵部分为例:
《宋史》: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辙、轼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宰相韩琦善之,奏于朝,遂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
《嘉祐集》十六卷,《谥法》四卷,均传于今。老苏所著《权书》《衡论》,最为世所称。本传载其《心术》《远虑》二篇。《易》《书》诸论,笔势雄畅。《名二子说》,虽寥寥三数行,而深远可味。其论文自比贾谊,而评者谓其得力于《孟子》,用笔纵横矫变,而字句简峻。曾南丰称之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10](p162-163)
以上内容是欧阳溥存对苏洵的完整叙述。比照相关记载可知,第一段文字录自《宋史·苏洵传》,第二段“《嘉祐集》十六卷”至“本传载其《心术》《远虑》二篇”也主要来自《苏洵传》,仅“《易》《书》诸论”以下文字来自他处。对苏洵文风的评价则引自曾巩的《苏明允哀词》。作为编著者的欧阳溥存,他本人的议论极少。这不是说他没有见解,而是说,他的见解是经由材料的选择而表达出来的。
中国古代本有“抄书为学”的传统。梁启超指出,古人为学,“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12](p62)。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均是集腋成裘,通过记录平时所见所闻而成的书。清人将这种学术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清初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中期的乾嘉学派,无不如此。今人张舜徽的《清人笔记条辨》、来新夏的《清人笔记随录》等,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样的“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既显示了对前贤的尊重,也避免了信口开河的发挥。
一方面以述为作,另一方面自抒心得,构成了欧阳溥存这部文学史教材的特色。他本人也承认:“书中评论,其为编者自抒心得者,亦复不少,阅者审之。”[10](编辑大意,p1)
《中国文学史纲》单列《八股文》一节,与唐诗、宋词、元曲并举,予以高度推崇:“八股文,明人为之最工,几如唐人之诗,元人之曲。”[10](p211)这个论断,揭示了明代八股文繁盛的事实,也彰显了欧阳溥存的学术个性。“作为文体,八股文兼具策、论等源于子部的作品和诗、赋等集部作品的某些属性。其体制主要有两方面的要求:代圣贤立言;体用排偶。‘代圣贤立言’具有论的意味,即传统所说的‘义理’,不过并非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用圣贤的口气表达圣贤的思想。‘体用排偶’则是继承了诗、赋、骈文的修辞技巧,包括词句、辞藻、历史故事和典故的运用等,即传统所说的‘词章’和‘考据’。”[13](p161)与清人经常鄙薄八股文不同,明人倒是不乏喝彩之声,晚明文化名人李贽、袁宏道等,都曾豪迈地以八股文作为明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明清人对于八股文的这种态度差异,除了清人的“弑父”情节、凡事爱与明人唱反调的原因之外,也与明人的八股文写得足够精彩有关。一种新兴的文体,在其成熟之初,可以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极大,因而也格外动人。这也是唐诗、宋词、元曲成为“一代文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八股文成为明代的代表文体,也与这一原因密切相关。
欧阳溥存在评价《颜氏家训》时指出:“之推著《归心篇》,盖亦自命为杂家,然则清《四库书目》从儒家迁《颜氏家训》于杂家中,名为退抑,实深知之也。”[10](p114)颜之推《家训》,《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新、旧《唐书》均归入子部儒家类,而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代《文渊阁书目》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均划入子部杂家类。欧阳溥存确认《颜氏家训》实属杂家,故并不认为将其剔出儒家类别是贬斥,反而强调这是对颜之推的理解和尊重。
清代乾嘉学派常指责宋人征实之学荒疏,欧阳溥存则专设《宋人征实之学》一节,罗列了宋人的小学著作如邢昺《尔雅疏》、陆佃《埤雅》,考证著作如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史家著作如《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目录学著作如《通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总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等,得出了“宋人征实之学,当时亦颇发达”[10](p154)的结论。这些地方,都足以见出欧阳溥存的个性与学养。
欧阳溥存也不免有其偏见,这跟他的个人趣味有关。如《孔雀东南飞》一诗,欧阳溥存说,该诗“絮絮至一千七百四十五字,为古今最长之诗,读之莫不倦而欲寐”[10](p66)。在他看来,好诗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尚简练,黜冗长,乃文词公例”[10](p66-67)。甚至在将《孔雀东南飞》与唐初永嘉禅师的《证道歌》比较时,对后者的评价也高于前者。
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兴起较晚,数量也少。《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灵台》《大明》《文王有声》等,朴实简略,不成规模。汉代乐府诗中的《陌上桑》《羽林郎》《东门行》《病妇行》《上山采蘼芜》以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等,才终于撑起了叙事诗的门面[14](p225)。对于这一脉来自民间、以叙述故事为特点的作品,不少文化精英是看不起的,例如世人所熟知的王夫之。他在《古诗评选》卷一中说:“自‘庐江小吏’一种赝作流传不息,而后元、白踵承,潦倒拖沓之词繁,………彼‘庐江小吏’诸篇,自是古人里巷所唱盲词白话,正如今市井间刊行《何文秀》《玉堂春》一类耳。稍有愧心者,忍辱吾神明以求其形似哉。”[15](p22)王夫之鄙夷这一类作品的“市井趣味”和叙事的琐细,当然是一种偏见,欧阳溥存也保留了这一偏见。
三、在内容上重视“私德”培育
在知识传递之外,《中国文学史纲》也极为重视学生的“私德”培育。
“中华民国”最初的二十年间,中小学的德育导向较为混乱。晚清政府建立新式学校之后,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德育观念[16](p187),其培育方式是读经和研习儒家言论。1909年,顾实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谴责要求小学生读经的做法(7)顾实:《论小学堂读经之谬》,《教育杂志》1909年第4期。,缪文功也就修身课程专讲儒家言论作了批评(8)缪文功:《论修身教授不可专用儒家言》,《教育杂志》1909年第12期。。民国政府在西方平等、博爱等理念基础上,提倡“爱国、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也未能得到一致认可。在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建立之前,国内各种思想碰撞,运动迭起,德育导向呈现众声喧哗的状态。一方面,传统的忠君、忠父、忠夫观念在蔡元培改革、新文化运动等冲击下,处于崩溃边缘,另一方面,各种舶来的思想主义也让青少年无所适从。
欧阳溥存一向重视青少年的培养。1914年,欧阳溥存编译了《母道》一书,较早从科学角度解释母亲道德的必要性、以及母亲道德如何培育等内容。该书一共十五章:《妇人之本分》《母氏当如何尽其天职》《母当如何养成儿童从顺之美德》《母当如何养成诚实之美德》《母当如何养成廉正之美德》《母当如何养成儿童之自信力及自觉心》《母当如何养成勉励与秩序之精神》《母当如何养成勤俭之精神》《母当如何养成礼让之观念》《母当如何养成爱及同情之观念》《母当如何养成美及清洁之习惯》《母当如何赏罚儿童》《母氏对于儿童交游当如何注意》《母当如何处置儿童轻微之过失》《母氏管理不逊儿童之法》;附录列举了24种母亲不当的行为。该书虽名为《母道》,但欧阳溥存说其主旨实在于“述养成儿童道德之教育方法以飨世之为人母者”[17](序,p1),最终指向的是儿童的培养。
欧阳溥存对“私德”的偏重,也与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有关。1921年,元尚仁翻译、出版了杜威的《教育上的道德原理》(中文译名《德育原理》,中华书局1921年版),其“译者小言”说道:“道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说来是平常得很的。他就是一种完全生活的法则,一种做人的法则;并不是什么‘四勿’‘三从’一类的消极的防范,和那些足以斫伤性灵的道德的毒药。这个界说关系儿童的一生一世,我们不但要自己记牢,而且还要劝告人家去了解。”[18](p315)欧阳溥存赞同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等命题(9)参见吴健敏:《杜威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评论》2001年第6期。。作为新旧时代的跨越者,亲历了旧式道德崩溃与民国新式道德体系建构的变迁,他既认同传统中国的“私德”观念,也接受西方现代的“公德”思想。
欧阳溥存在《中国文学史纲》“编辑大意”第六条中说:“本书于历代作家行事足资法戒者,时加取录,冀于德育有少助焉。”[10](编辑大意,p2)也就是说,教材中既有可资效法的榜样,也有可引以为戒的负面例证。
杜甫是欧阳溥存高度赞美的榜样之一:“诗人不得志于时,辄用没世名称,矜傲当代。而甫不然也,其《梦李白诗》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醉时歌》云:‘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论者谓王维学佛,李白学仙,甫则崇笃儒术。实则甫识旷通,非暖暖姝姝专以儒为悦者。故曰:‘儒术于我何有哉,孔邱盗跖俱尘埃。’”[10](p142)“诗人每悉心于吟风弄月,叹老嗟卑,即白之使酒学仙,亦只求一己之解放,而甫则平生歌哭,多为民众呼吁。”[10](p141)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圣”,他曾经满怀热情与理想,生活的磨难让他将热情变为思考,将目光投向现实,由关心个人转向关注社会民生。《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的问世,标志着杜甫诗风的转变和人格的提升。如果说《从军行》反映的多是赏罚不公、战事残酷和士兵埋骨荒野的命运,杜甫则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战争,将战争与统治者的政策、百姓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之所以能“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19](p111),固然与其儒家信仰有着重要关系,但表达得如此深切,正在于他能由己及人,从自身的不幸看到了时代的苦难。这是杜甫的特点,也是其伟大之处。欧阳溥存对杜甫的推重,既在其诗,更在其人。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与李商隐有关。李商隐写了一些无题诗,风格“艳冶”,很多人因而揣测李商隐人品不端。欧阳溥存节录了李商隐的《上河东公启》:“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伎,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10](p146)李商隐借柳下惠和阮籍的例子说明自己不是一个风流浪子,他在丧偶之际拒绝了河东公将乐籍美人张懿仙送给他的好意,足以证明其人格品性。欧阳溥存将李商隐和温庭筠、杜牧等人进行比较,结论是:“商隐为人,与温庭筠、杜牧殊异。”[10](p146)他为李商隐洗刷污名,也着眼于对“私德”的重视。
欧阳溥存极其厌恶“文人无行之弊”[10](编辑大意,p2)。其《对于建安文人之批评》一节,最后一段几乎指斥了建安时代所有成就较高的文人:
建安文家,寿算多促,比方两汉,其贾生、王子山之俦欤。其人器质,大都不甚闳厚。《颜氏家训》尝历数之曰:“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又云魏太祖、文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10](p75-76)
北齐颜之推(531—约591)《颜氏家训》二十篇,聚焦于立身治家之道,不论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抑或位至帝王的曹操、曹丕,都未能逃过他的批评。欧阳溥存完整引用颜之推的话,说明他的“私德”观与之一脉相承。
又如,关于谢朓,欧阳溥存详细叙述了其屡屡告发亲朋好友、不得好死的下场:“朓尝为宣城太守,建武四年,告王敬则反。敬则诛,朓迁尚书吏部郎。敬则,朓妻父也,其妻常怀刀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为吏部郎,沈昭略为朓曰:‘卿人地之美,无忝此职,但恨刑于寡妻。’明年,朓以江祏等谋废立告人,反为祏等构奏,下狱死,年三十六。”[10](p101)这一类记叙,意在告诫学生,千万不能做道德败坏的小人。这样的内容,在其他文学史著作中,虽也偶有涉及,但如此自觉地加以突出,却极为少见。把人格培养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欧阳溥存的做法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
欧阳溥存是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跨世纪学人,却并没有放弃经史子集乃是“文学”的底色,其深厚的国学基础促使他秉持“中道”,致力于从中国文学传统理解传统中国文学。其留学的背景让他具有“他者”视角,强化了其从中国文学传统理解传统中国文学的学术个性,最终呈现出一部有述有作、述作并重,并且一以贯之重视道德培育的文学史著作。在建构中国文学史话语的道路上,以及中国文学史教学科学化的范式上,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的价值,颇值得重视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