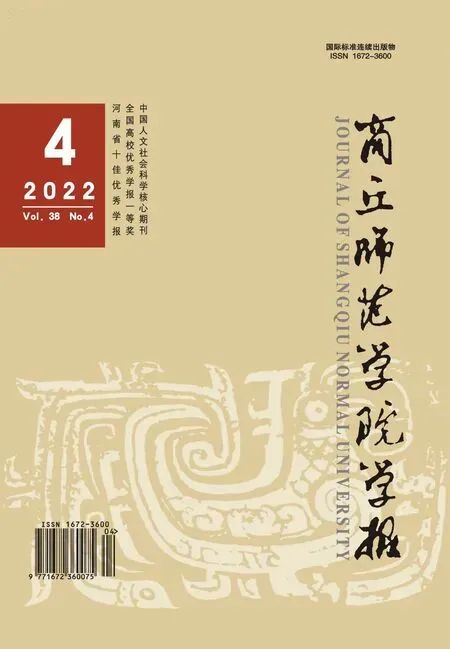试析王夫之视阈下的司马氏形象
——兼论南明士绅对亡国的认识
王 浩 淼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两晋宗室虽然被认为是亡国的祸首,但是他们的许多行为也时刻影响社会的发展,如过继的泛滥、出镇制度的施行和执政体制的参与等对该制度的成型起了关键性作用。学界对于两晋宗室的认识多停留在八王对国家政治的影响(1)关于西晋诸王封国的论著有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7—43页)。关于八王之乱评析的文章较多,有辻正博《西晋的诸王封建与出镇》(《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李晓光《对“八王之乱”的再认识》(《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0年第2期)等。关于对两晋宗室的群体制度研究有张兴成《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阅江学刊》2013年第5期)、张兴成《两晋宗室始封爵考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张兴成《两晋宗室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上,忽视了宗室群体对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的作用,而王夫之恰是最早全面分析了司马氏在国家机制运转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多含贬义,但不失为认识司马氏群体的崭新视角。笔者根据《读通鉴论》中对司马氏行为的评论以探求王夫之的宗室思想,如有不确,望方家予以批评斧正。
一、司马氏选嗣不力说
宗法制是帝制时代维护贵族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各个中原王朝为了巩固政权永传万世,往往奉守周代所施行的宗法制。宗法制的存在确实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各支裔争夺爵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嫡长子为维护对象的宗法制并不能每每保证继承者都是贤良端正。继周朝以后,晋朝和明朝恰恰是固守宗法制最极端的时代,这也就说明了晋、明朝皇帝有很大可能性是昏庸的,只是偶尔在转点时期出现一丝曙光,由于晋朝与明朝在遵守宗法制上十分接近,无怪乎王夫之会猛烈抨击晋朝的宗法制度。
晋朝在君统上始终奉行宗法制,晋武帝虽曾怀疑太子的愚笨,但经不起杨氏、贾氏的迷惑[1]2618,晋孝武帝时期,君臣并不关注太子的贤愚,晋朝如此坚持遵行以嫡长择嗣的行为引起了王夫之的困惑。王夫之认为,“惠帝,必不可为天子者也;武帝护之而不易储,武帝病矣”,该观点起自于对西晋灭亡原因的分析。在“晋武帝一”条,王夫之探寻了晋、宋的灭亡原因,他认为八王之祸不能直接归咎于晋文、昭、武帝没有实行裂土而封的方针,“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贤于无法,亦规诸至仁大义之原而已”[2]308,法律是治国的基本,至于如何守法,还需要贤人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管理、引导人们,晋惠帝、安帝皆“不慧”“行尸视肉,口不知味、耳不知声”最终造成了晋怀、愍、恭帝的“不足以图存”。王夫之甚至从假设的角度论证国君贤愚与否的重要性,他在“晋武帝十五”条提及司马攸的影响时称,“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故举朝争之,争晋存亡之介也”[2]321,如果司马攸取代了司马衷的位置,在王夫之看来,杨氏、贾氏、八王会收敛,君主的“贤能”可以在清除奸臣、稳定社会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这充分体现了王夫之的选贤制胜过于宗法制,在王夫之所在的时段,宗室选贤开始兴起,但事实证明,选贤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而且极容易引起旁支的介入,这也是南北朝时期部分叛乱的源头(2)该原因造成的叛乱有南朝宋谢晦废营阳王而激起宋文帝杀三臣、宋文帝宠爱刘子鸾而引发太子刘劭弑父,等。。
王夫之认为,如果无子,可以选择养子作为后继者,一可以立嗣于政,二可以选贤于德,三可以豫教于治,但是必须保证豫教在继承以前,如此嗣子能掌握主动权,权臣无法实施篡弑[2]292。这就隐喻了晋惠帝和晋安帝不仅自己昏庸,甚至择嗣不明,违背了“无子而非有嫡长之不可易也,宗室之子,唯其所择以为后”和豫教于治的原则。晋惠帝长子愍怀太子司马遹十分聪明,但秉性刚毅,深受贾氏厌恶,被陷害而死,三子也惨遭囚禁。此后赵王讨灭贾氏,自称皇帝,六王相继加入纷争序列,虽立有皇太子,但都任凭执政的意愿而随意被兴废,更谈不上豫教了,因此晋惠帝死后西晋名存实亡的根本所在就是立嗣不正。晋安帝无子,在权臣的控制和宗法制的贯彻下,没有选择嗣子,更没有采取“豫教”的措施,这不仅表现出其本身的无能,也表明东晋按武陵王、会稽王、琅琊王、皇太子至君主的爵位阶梯化过继模式是存在弊端的(3)东晋继续采取封藩的策略,在晋元帝本支设置琅琊王爵位,不仅在于奉祀,而且作为世子的继承者,随着支系的兴替,琅琊王之下有会稽王和武陵王,依次作为前者的人选来源。。晋安帝的继承者晋恭帝尽管有清醒的头脑,其登基原因有可靠的血缘依托,但是缺乏“豫教于治”的管理,缺乏统治的主动权,不得不依托于权臣,因此无法延缓刘裕篡位的步伐,成就刘裕快速篡位的先机在于安帝没有率先采取选贤、立嗣和豫教的措施而拥有立帝的功劳。晋惠、安帝二人都陷于囹圄,又无政治治理能力,因此并不会认识到嗣子的重要性,造就了执政权力日益兴盛。另一方面,两宋皇帝之所以能够立嗣明确,除了对宗室管控和职官分工明确外,过继体制已经十分完善,而且两个案例的过继子都是疏宗,血缘十分疏远,保证了养子与被过继子之间的情感沟通,杜绝了他人的觊觎之心,王夫之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评价北魏宗爱弑君事件中,认为宋高宗内禅成功的原因是得时得人,“时”是高宗年老而早坐正位,“人”是孝宗的血缘较为疏远[2]464,这在宗支脆弱、矛盾激烈、皇帝寿命较为短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南燕慕容备德在本国有旁支的前提下仍然坚持派人前往秦国找寻亲侄慕容超[1]3688—3689,慕容超即位后大肆屠杀旁支[1]3692,这标志着这一时期王位争夺会持续演进,只是表象不同。
惠帝死后,怀帝被迎立,在西晋政治过继频繁的时代,过继于皇太孙司马尚的襄阳王司马范当最有资格被选为继承者,然而司马越仍然扶持弱小的怀帝,目的在于能更好地控制朝局。王夫之认为由于无法激发各州牧的卫国积极性,司马越将怀帝禁锢于洛阳——有部分原因在于怀帝本身的柔弱——是造成西晋不能御狄于都门之外、辑抚骄镇的根本原因[2]337。
明末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面对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帝否决了以太子监国于南京的决策,采取“天子守国门”的方针。借怀帝的案例,王夫之认为,君主应该被置于危地,否则不仅被敌人孤立,甚至会被自己的天下所孤立,“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于膜外,虽猎卫主之名,亦将焉用此哉”[2]337。即将天下与国君存亡的重要性进行了罗列,肯定了国君为天下死社稷的做法,这是南明士人对思宗自缢做法的肯定。与此同时,南明鲁王、唐王始终将自己置于战场最前线,如唐王曾多次自请北伐,深得士绅的爱戴,鲁王在钱塘江也是亲临前线。其次南明福王、唐王都没有过早设置继承者,因此无法摆脱权臣。晋惠、安帝的昏庸也隐刺弘光政府,黄宗羲曾谈论:“称弘光宽仁而虚己,然则晋惠东昏,皆足以当之。”[3]336南明士绅甚至曾认为如果以崇祯太子朱慈烺监国南京,名正言顺,有很强的响应力[4]117,更不会出现日后的三大案,酿成左军内侵的悲剧。
旁支的嗣疏远的嗣子可以保证感情的重组,而且更能保证在传位过程中不断吸入“贤”的成分,王夫之等人十分支持不要过分依赖宗法制,这是吸收明朝诸帝传位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所得到的深刻认识。晋与明相比又有稍许不同,晋群臣争相违背宗法制而君主不从,明群臣争相遵从宗法制而君主不愿。北京陷没后,东林党-复社成员坚持反对崇祯帝堂兄福王即位,其中吕大器等甚至列举了福王“七不可立”的条款,认为应该按照“选贤”与“宗法”相结合的方式迎立潞王朱常淓。事实证明,潞王并不比福王好很多,而且按宗法制确定皇位继承人并不能保证君主的贤明,顾诚也认为不管是福王还是潞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东林人士没有当机立断扶持某位宗王登基,使拥立功劳白白让予马士英和江北勋将[5]52。与二者相比,唐王和潞王作为疏宗,不管是在号召吏民抗清还是内政方面都有很好的作为。桂王的嗣立不仅有唐王的口头诏谕以及唐王宠臣何吾驺的说辞,而且按伦叙也是合理的,而唐王弟朱聿反而被排斥为伪政权,王夫之用了一个“叛”字说明了自己的立场。由此可见,王夫之等人并不反对宗法制,但是在没有选明继承者时,选贤择嗣是主要手段。
二、司马楚之北投说
王夫之是明末大儒,他猛烈抨击司马国璠,称:“国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璠兄弟始。”受刘裕逼侵晋室诸王,司马国璠被迫北走,此后司马休之在荆州不敌下游诸军,寄身于后秦姚氏,司马楚之从竟陵北走,在长社一带栖身谋求反攻,北魏在吞并河南地区时,司马楚之也被迫接受北魏的控制,授爵享禄。《魏书》特开一卷讲明司马休之等人入魏后的活动[6]853—864,一面交代了拓跋氏入主中原后的一系列重用汉人等的统治方针,体现了拓跋氏一视同仁的态度;一面提高了鲜卑拓跋氏的文化地位,政治上接纳了故国后人,从法理上阐释了拓跋氏解救江南的司马氏,在政权交替时提高了本身的正统性。宋以前,中原政权多渗入胡人的因子,如北魏、北周为鲜卑人,北齐是鲜卑化的汉人,隋、唐统治者都与胡人有姻亲关系,文化程度更有包容度,五代中原正统王朝除了后梁和后周,后唐、后晋、后汉都是以沙陀为核心的政权,辽人多次南侵,两度参与或主导推翻中原政权的活动,中原政权由胡夷主政,北部的契丹也是胡人政权,因此中原官吏对于仕华仕夷的选择意识已经麻木了。然而华夷之辨在宋朝儒治理念的引导下不断升华,儒学家开始反思如何提升以汉人文化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因此投敌者尤其曾是朝廷官员将受到笔伐。明朝的儒治理念更为深刻,在少数民族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之际,士人往往借助于华夷之辩来讨论国家主权。女真崛起至进入北京,其机构的核心成员是明朝缙绅,这尤其受到南明士人的鄙夷,因此王夫之的目的在于嘲讽当时的“礼崩乐坏”。
王夫之多次痛斥借敌兵以讨本土者。早在司马楚之北投以前,王夫之就已痛斥奔敌卖国者,曹魏时期,诸葛诞不满于司马氏的篡权,承鉴王凌、毌丘俭被诛,以讨司马昭为旗号奔吴。王夫之认为:“魏而亡,亡于司马,亡于吴,无以异也,吴岂为魏惜君臣之义,诛权奸以安其宗社者哉?”[2]301退一步讲,晋篡魏犹能保护魏宗坛,注重禅位的合理性,保存魏国君主,而吴国是敌国,投吴就是叛国。在当时司马氏篡国未显露,对于时人而言叛国的罪过更大,不仅自己的忠心被过激行为所埋没,甚至给予司马氏讨叛、篡国的口实。吴国即使肯相助,也不会行君臣礼、保存魏国礼仪、宗社、君主,只会以战胜者的姿态抢夺战利品。与此相似的还有投奔蜀国的夏侯霸。王夫之接着评论,诸葛诞等人“借敌兵以讨贼者之亡人家国也,快一朝之忿而流祸无穷”,并成为后来司马楚之、刘昶、萧宝寅、元彧等宗室效仿的对象[2]301。
前燕也发生了两例“投敌击己”的事件。慕容翰不为其嫡弟慕容皝所容,奔段氏,并成为攻击柳城的重要将领之一;慕容垂受慕容评的排挤逃往前秦。他们都不希望本国灭亡,只是寄希望于时间的冲淡或者外部的重压来改变本国对自己的想法,灭国改嗣不是这些慕容氏的初衷,所以不管是慕容翰还是慕容垂,最终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国家。王夫之对慕容翰有深层次的心理分析,他认为慕容翰的间谍行为并不仁道,逃离本国并不为了背叛,而是为以后邀功创造可能,但是却背叛了接纳自己的敌国,最终通过“伏不测之机以窥之”的方式回到了本国,慕容皝的猜忌是慕容翰被诛的次要原因,而慕容翰本身狡诈的性格才是首因。
慕容仁则不同,作为同时出逃的慕容仁采纳了季弟慕容昭的意见,“男子举事,不克则死,不能效建威偷生异域也”。慕容仁等认为慕容翰“偷生异域”,实则表露出鲜卑人的普遍桀骜不驯的性格,在他们看来不存在苟且性命,生与死本来就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们的身份并不低微,燕国的王位继承权应该有他们一份,因此慕容仁和慕容昭等采取了独立方式对抗慕容皝,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背叛燕国,与各朝觊觎皇位的诸王性质相同。这也是王夫之没有特意指明慕容仁的重要原因,另一项原因是王夫之的政权中心观起了主导作用,他在评论慕容超时称:“超之窃据一隅而自帝,非天命也;慕容氏乘乱而世济其凶,非大统也。”即慕容氏不能成为正统,也就无须发自内心感到惋惜。
太和三年,前秦君主苻坚待遇宗族过厚,引起宗人对苻坚非法夺位的不满和对王位的觊觎,一系列的叛逆事件也引起苻坚亲兄弟的恐慌,魏公苻廋甚至怂恿燕军尽快入关。尽管如此,前燕和前秦都没有直接受宗室投敌的影响使本国陷于危机,相反使本国调整宗室政策而获得更好发展,因此也就不符合王夫之从当时的社会危机出发所提出的“惧内逼而逃之夷”的理论。
事实上,不管是曹魏的夏侯霸,还是前燕的慕容翰等,他们都不满足以汉资夷的特点,姑且不说夏侯霸是否属于曹魏宗室(4)朱子彦反对夏侯氏与曹氏为族姓关系,认为他们是姻亲关系。参见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385-396页。,其投降蜀汉在正统观念上也是名正言顺的,而慕容翰等本身就是夷狄,“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2]337,黄宗羲也提到“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7]517,这是因为明朝长期受蒙古、女真等威胁所升华的理念[8],根本不用为助夷灭夷辩解,相反可能对于汉人政权而言是一件幸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自始至终都把正统观放在南朝,至于北方各个政权乃至北魏,他有如此论断:“自拓跋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2]325拓跋氏尚是“假中国之礼乐”,那么石氏、刘氏、苻氏、慕容氏等也是得势窃权之外族姓氏了,这些胡人政权之衰,尤其北周的灭亡作为暂时的终结,“故杨氏之篡,君子不得谓之贼,于宇文氏则逆,于中国则顺;非杨氏之能以中国为心,而天下之戴杨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移之也”[2]366。正是如此,王夫之认为,王猛投秦而不归晋是智略短浅的结果[2]386。在谈到司马国璠无法通过自己力量讨伐刘裕而选择北走,王夫之认为,司马国璠兄弟、司马楚之、休之相继投奔后秦,以后各朝每有变事,宗室中总不乏有人效法司马国璠等北投敌甘作南方罪人,“于家为败类,于国为匪人,于物类为禽虫”[2]414。王夫之甚至认为,这些宗室自号恢复故国、驱除族属的共同罪人仅仅是苟且的借口,“偷视息于人闲,恣其忿戾以侥幸,分豺虎之余食,而犹自号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2]414。这类宗人本已根基于南方,遭受一定变乱后不但不为家、为国、为本土效忠,却为了苟且偷生而引导夷人南侵。王夫之的内心认为,尽管受到宗国的排挤而离开,“身之所托,心之所依,不与谋倾覆宗国之事”尚可以得到原谅,这是本国不可抗拒的力量所致,可以不能为国尽忠,但坚决不能荼毒本国,这是不仁不忠的表现,完全是为了达到私心的目的[2]472。
然而自晋室开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除了贵族与庶民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外,民族冲突也逐渐成为主要矛盾,自晋朝以后,陷没并投降于夷的现象在西晋已广为出现,那么为什么王夫之独醉心于指责司马国璠等人呢?这与王夫之的思想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王夫之处于明末,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思想,但仍然是以传统儒学为基调,因此不可能超脱“君主”二字,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的昏庸并非单纯是自己的问题,国家设置百僚的目的在于辅政,让官吏秉承上意各司其职,从而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9],宗法制的传袭过程中不能绝对保证君主继承者是明智的,因此宰辅的职责就要充分发挥。怀、愍二帝本身的软弱与个人无关,却与八王之乱直接相联系,尽管此时还未直接出现主动投敌的司马氏,但是宗室已然成了主要关注对象,并成为东晋亡国的间接责任人。王夫之从各朝禅让制的不同点入手阐述了自己对司马氏北投敌不认同的观点:禅让制自古至南朝宋未有中断,新朝、曹魏、晋朝都采取这种较为和平的方式建立政权,这种政权的特点在于注重维护新朝正统性的过程,因此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同时不能采取极端的行为,“丕之篡,刘氏之族全,炎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阳,陈留令终而不逢刀鸩”[2]414。禅让制不仅让本朝获得了正统性的巩固,而且故国君主宗室也得以保禄终身。刘裕采取禅让制的方式夺得政权,尽管较为仓促,但是他仍然做足了准备,在所有禅位案例中,王夫之认为“刘宋之功伟于曹魏”,而李唐之“名逆,其情未诈,君子恶其名而已”[2]532,可见王夫之认可刘裕在禅让之前的贡献,对其禅让行为进行了表面美饰。与以往禅让不同的是,刘裕弑杀晋恭帝为后世所不解,王夫之对此辩解称,是司马国璠等北投夷狄并引兵侵华夏的行径给予了刘裕以“彼将引封豕长蛇以蔑我冠裳者也”的借口[2]414。
从社会环境角度看,可试将东晋末年与明朝末年进行比较。第一,司马楚之和王夫之都处在朝代变更之际,也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更为雄厚的转折点,司马国璠等北逃不久刘裕即篡国,王夫之从南明政权脱离后不久,清朝即一统全国,而北魏和清朝又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压迫是诸多南人所恐惧的,侵占汉土、“假中国之礼乐文章”,因此王夫之实际是借司马国璠和北魏来痛斥南明降清者和清朝。第二,司马楚之是东晋宗室中具有杰出品质的一员,在东晋,谯王司马承殉国于长沙为后人所熟识,此后也有宗王出镇重地,但是自谯王司马尚之、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殉国后,真正掌握军权并成为帝派的军事核心力量只有宗室后起之秀司马休之和司马楚之,尽管二人确实在抗争刘裕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努力,但没有为此殉节,通过资敌助虏给予刘裕镇压司马氏的口实,晋恭帝被弑、司马氏几无噍类的首要因素在于“司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其次才是“刘裕之穷凶以推刃”[2]414。
王夫之在批评诸葛诞的行径也在批评投清者,尽管并不指向于明朝宗室,但清朝三藩,尤其是故平西伯吴三桂等的助纣行为激起了南明当世的愤慨。明末士大夫对于假和议之名的边将已有所排斥,土木堡之变,明朝吏民对少数民族深恶痛疾,汉族官吏甚至对有少数民族血缘的将领有所抵触,明末边疆治理逐渐成为重要的议案之一,女真崛起后,多数督臣、阁臣多赞成与蒙古议和,而对女真采取抵制措施,他们认为“借资二虏(蒙古)以养我全力,持之用之,奴不敢西向”[10]15。女真作为公开反叛的民族,明朝官员深受宋朝的前鉴,担心与女真议和会使其更加轻视本朝,而且极易加重蒙古的离心[11]408。因此袁崇焕从民族角度出发打算缓和京城危机而两次力图建议与女真议和,反而受到重重阻难,甚至被扣上叛国的帽子。明末士大夫在不断加深对议和投敌的厌恶,一方面使思宗不能公开关于议和的提议,加深了对文臣谏官的猜忌,另一方面加快了被士林抨击的武将及投降农民军的明朝官员降清的步伐。明朝官吏不思报效国家,不以投虏为耻,使得明王朝一败再败,失去了原有的根基,甚至连禅位的资格也失去了。而南明官员尽管昏庸,仍然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家,投清尽管能够保全生命和财产利禄,但是国家宗社、文化已经被破坏了,以“忠”为核心的儒家体制已然不存,因此他在《永历实录》中大为歌颂瞿式耜和张同敞的悲壮殉节、严起恒的清正高重来讽喻降清者。清朝统一全国后,缙绅喜于大国再盛而歌颂满人,王夫之不屑于此,正如他本人对司马氏的看法,“中夏之士,亦不为之抱愤以兴矣”,真正有家国情怀的士人绝不会为此沾沾自喜[2]414。
三、宗室不能屏藩说
王夫之在否定晋惠帝后,时常发出“司马氏之子孙,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的声音,他先从晋武帝授兵开始,认为授兵给孺子是亡国的开始[2]335,这些孺子都是纨绔子弟,只知道竞争,不识军练之事,一味向外族夸耀军容而没有实战经验,同时向朝廷索要更多的军事权力和封赏,最终造成相互残杀。由于宗室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纵横之术不断被使用,以至于“不得竞而欲相竞,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强”[2]335,这也是传统对八王乱国和夷狄南侵直接原因的共识。
王夫之又从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司马颙角逐的角度入手,认为司马伦虽然妄图称尊,但没有弑君的计划,此后司马颙、司马颖也仅仅是挟持君主,而司马越弑君,司马模等居然袖手旁观,任由局势变坏,以至于“惠帝死,而乱犹甚,国犹亡;惠帝不死,则琅琊虽欲存一线于江东也,不可得矣”[2]333。在这一看法中,王夫之一再强调君主的重要性,君主即使再昏庸,辅臣、宗室的辅佐则可以避免国运衰败,然而西晋宗室不仅不辅助君主,蛮横和无能到了极点,惠帝时期诸王相争,怀帝时期司马越垄断朝局,愍帝时期坐据秦州、扬州等地的司马氏竟“视君父之危若罔闻”[2]345。但王夫之并不批评琅琊王司马睿,相反他指责愍帝无能力指挥南阳、琅琊二王,所颁发的勤王诏是“戏”诏,直接指责愍帝“之于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统,义不足以相长,道不足以相君”,而且贾疋等才是长安陷没的罪魁祸首,愍帝之立并不是诸王推戴的结果,因此他不可能存在合法性,长安城内诸大臣在王夫之眼中是“愚以躁者,乃挟天子为孤注,而诮人畏沮丧,不量力,不度势”[2]344,“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必然失败。元帝是诸王、大臣所共立,但大臣也多是贪佐之人,尤其是王氏家族无法承担辅助的重任,“王敦称兵犯阙,王导荏苒无所匡正”[2]357,“盖导者,以庇其宗族为重,而累其名节者也。王氏之族,自导而外,未有贤者,而骄横不轨之徒则多有之”。这并不影响元帝足以“相统”“相长”“相君”的地位[2]355。由此可见,愍帝和怀帝虽然都由贪佐大臣所拥立,怀帝甚至在血统上远不如愍帝,但是在王夫之看来,诸王的响应和君主本身的期待决定了他的正统性,而这正是为南明诸帝的合法性创造了历史理论依据。
与晋愍帝不受诸王所共戴不同的是,王夫之在极力推崇南明唐王和桂王,他借用晋愍帝的非合法性和琅琊王司马睿南渡的案例说明了南明时期唐、桂王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唐、桂二王一直致力于提高个人在诸王中的威望,诸王相继以福州、肇庆为核心展开复明活动,大部分藩王在地方无立足之地后,纷纷融入两个政权,并以殉难来表达对监国者的认可,一切都说明了王夫之所处的政权是合乎正统的。对于唐王,正如黄道周所认为的那样,“在昔琅琊,先讨石勒,后渡五马之江,暨于宛叶,初会平林,遂发昆阳之绩。以今揆古,易世同符”[12]377。南明士人将隆武帝比作司马睿、光武帝,将其作为复辟的希望。王夫之在评价司马睿时提及“承八王之后,幸不为伦、颖、颙、越之争”,同于黄道周讽谏鲁王朱以海时所说的“昔晋室以八王贾乱,琅琊鉴之,遂克中兴”[12]364,张家玉认为唐王在身世、即位时间和起兵目的“常变又相准”“今天子大度远过光武”[13]86,正是表明了唐、桂王虽然在血统上仅次于福、惠王,但是并未直接参与和弘光政权的斗争,相反福王渴望拥有权力,潞、惠王则极力降清,唯独唐、桂王是群臣和诸王共同推戴的结果,而且嗣大统不久即得人心,恰与司马睿相似,这是鲁王、唐王之弟无法比拟的特点。
此外王夫之着重强调了晋惠、怀、愍帝时期辅臣中的“躁者”,所谓“躁者”,指迫切渴望获得权力而无视君主存在的权臣。他认为,晋惠帝时期之所以出权臣,在于“扶弱图存”,利用庸主来达到“无天子之世”。在这一时期,“有天子而无之,人欲为天子而不相下,群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无天子者”,以至于贤人“蹇裳而急去之”,中者多死于难,剩下的人仅仅寄命、纳身于水火中,造成这种状况的罪人就是这些“躁者”[2]329。其中八王是宗室躁者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东海王司马越鸩杀惠帝,对于躁者而言,庸主就是掌权的绊脚石,不能废,不能杀,因此王夫之讽刺司马越的同时甚至带有一丝惋惜,“不得已而听人之毙之,越之情亦苦矣”[2]334。王夫之所处时代恰也是充满“躁者”的时代,弘光时期,辅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侵害正士,勋镇也都秉持着“扶弱图存”的目的。隆武时期,郑氏作为功臣拥有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却并不思考如何拯救危亡的明王朝,当清军进入福建,郑芝龙立刻投降,这正是晋朝卖主求荣者索綝的形象。王夫之在《永历实录》极力贬低推戴朱由榔的大臣王化澄、吴炳等人,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也提及辅臣的贪婪,可见王夫之虽然以桂王为正统,但在分析桂王失败的原因上则强调了辅臣的不作为。永历时期,吴楚之争十分激烈,在王夫之看来,永历帝虽然昏庸,可以依靠阁臣谏官来规避“不贤”,所谓“人之贤不肖,铨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王夫之深恶除堵胤锡以外的吴党人士,并在著作中大力贬低他们的作为(5)关于王夫之对吴党主要人士吴贞毓、万翱等的评论,见《永历实录》卷20《童郭吴万程鲁列传》,第175-181页。。吴党人士多是朝中阁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处打击异己人士,最终招徕孙可望,是亡国的刽子手,“争于其流,则议论繁而朋党兴。贞邪利害,各从其私意,辨言邪说,将自此以起”。此外王夫之是十分赞同土官世袭和“以骁悍为我立功”的方针的[2]402,这与楚党的主张不谋而合。
从国家政策来看两朝宗室无法承担屏藩的重责。晋朝惩魏之宗室孤僻,大封宗室。而明朝对宗室方针恰接近于曹魏,即“疑同姓”,具体表现有削军权、禁止进入士农工商行列、严格实行封藩制,禁止随意出城和越关、禁止非法奏讦,不许随意进京,正德以后乱伦者处死,严格实行宗法制,郡王冒袭者废爵。明朝在政治、经济上优崇上级宗室,下级宗室的生活遭到残酷打击,与曹魏都有食邑(或食禄)而无实权相似,而曹魏宗室只有少数成员深得君主信赖,甚至可以担任权臣。南明隆武帝曾经为祖父所软禁,袭唐王爵后又禁锢于南京,因此时人对于明朝宗藩的残酷境遇感到惋惜,有识之士请求增加宗室谋生的渠道。明朝宗室中富者日夜游玩,贫者为食宿而烦恼,晋朝宗室则忙碌于权力的争夺,两者都遭到了现实的打击而无力屏藩,正所谓“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2]315,这是从国家政策出发论证了晋、明两朝宗室都很难有屏藩的表现。
晋室司马氏热衷于追逐权力,尤其是懿亲者,君主如简文帝与权臣共同谋逆,诸王如会稽王司马道子“僭帝制以浊乱”,因此王夫之强烈认为晋朝宗室“无可托之人,所任者适足以相挠,固不如妇人之易制也”[2]391。从君主角度出发,晋室宗室一旦获得权势则破坏制度,无法承担屏藩重责,因此不值得托付重任。有志之士虽然有救国的办法,如王豹等,但这些救国并非长远之计,仅仅只是避免宗室交讧而已,他们的救国之术起于老、庄“处乱世而思济”。王夫之认为自古以来有三大害,老庄第一,浮屠第二,申韩之术第三,他并不看好老庄所说的“静”为主因,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不能忽略外间的大事,这实际也在批评王守仁的渐悟之道,认为王学并不能经世致用,败坏了儒学的风气。其次老庄之术可以“息烦苛”,但不足以“兴王道”,尤其是魏晋后期巫术往往借助于老庄术紊乱国家[2]516-517,朝内有方士乱政,朝外有教徒横行。唐宋以来,各种学术结合道学、佛学,造成“无善无恶、销人伦、灭天理者,谓之良知”,在王夫之看来,必须由行得知,不能空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明后期的心学之风[14]。王夫之对于当时心学弊病的认知与黄道周不谋而合,他们都肯定了环境造就下的心学,同时提出对于学术的评价不能只看理论,而应该看重能否拯救当时的社会文化弊病[12]27,由此对王学发展有了纠正作用。王夫之总结称:“此(老庄之术)以处争乱云扰之日而姑试可也;既安既定而犹用之,则不足以有为而成德业。(琅琊)王与(王)导终始以之,斯又晋之所以绝望于中原也。”[2]333这也是他从学术角度出发对于南明各政权君主存在意义的认可和对未来展望充满忧虑的原因所在。
四、结论
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宗室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司马氏在帝位传袭过程中过于依赖传统的宗法制,以至于不管在国家治理、用人方面和选择继承者方面都不能有很好的表现。第二,尽管前朝有多起宗室投敌、引敌现象,但司马国璠、司马楚之是首例投夷事件,并继而造成南朝被北朝压制的格局。第三,两晋宗室并不能做到屏藩的责任,在宽纵的国初政策引导下,他们为了私欲不顾君主的权威互相攀比竞争权力,当君主的权威受到挑战时又沉默不言,甚至竞相效仿夺权行径。王夫之评论司马氏多基于自己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识。首先,王夫之以南明士绅的角度肯定了崇祯帝自缢和唐王北伐的政策,从而否定了司马越未将怀帝置于危地以鼓励士众的做法。其次,王夫之借反对司马国璠等北投资敌的行迹认为降清者引敌入寇是造成南明局势日渐衰弱的主因。最后,王夫之认为当国家没有法定继承者,由大臣和诸王共同推戴的人员才具有即位合法性,因此琅琊王司马睿并未奉诏北援恰是图存的表现,这一看法是为明朝唐、桂王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尽管王夫之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并未完全依据于史实,或者说是具备浓厚时代性的主观思想,这是因为这些思想基于对当时环境的认识并掺入对历史的评论中。
—— 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