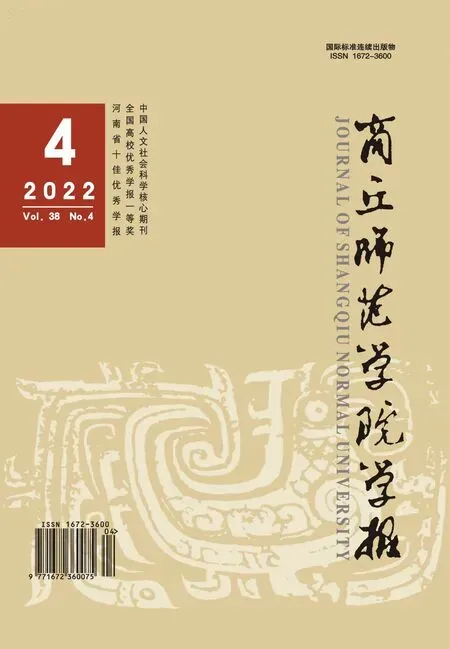当代诗歌的历史诗学研究
——以咏史怀古诗为视角
苗 霞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阅读当代诗歌,不难发现:总有部分诗人心揣历史,正如他们怀揣诗歌一样,总是跨越时空的暌隔,一再向久逝的过去招魂,与古人进行一场场千古旷世的会谈。这样就产生出了当代的咏史怀古诗。从题材内容上看,咏史怀古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可以把它细分为两类:“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1]239确切地说,咏史类是翻阅旧书,检点旧说,针对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陈述自己的见地或抒发一己情怀;怀古类是登临古地游览凭吊古迹,追念往事抒发感慨。在诗歌最初的源头,分别能看到它们的萌芽、产生,譬如,《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便是一部从周民族的诞生直至文、武开疆称王的民族史诗,完全可以看成是咏史诗。《诗经》中的《黍离》又被称为怀古之祖,《毛诗序》云:“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2]330在后来古典诗词发展过程中,咏史怀古诗更是涌现出了许多垂式千秋的不朽之作,如左思的《咏史》、陶渊明的《咏荆轲》、鲍照的《芜城赋》、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杜甫的《咏怀古迹》、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长平箭头歌》、李商隐的《隋宫》和《贾生》、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和《金陵五题》、杜牧的《赤壁》《题乌江亭》和《过华清宫》、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袁枚的《马嵬》等,不胜枚举。这种咏史吊古的抒情模式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已形成自身独特的一套历史诗学和创作规则:“诗”“史”结合,用典互文;“史”“志”结合,借古讽今;“古”“今”结合,对比反衬。
犹如历史延伸而来的地平线一般,出于对这种诗歌类别的继承和发展,当代诗人也做出了向着纵深发展的不懈努力。余光中写有《草堂祭杜甫》和《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林莽有《暮色中登君山眺望洞庭》《西行琐记》,西川有《李白》和《杜甫》,钟鸣有《与阮籍对刺》,柏桦有《李后主》《在清朝》,肖开愚有《向杜甫致敬》,任洪渊有《高渐离》《聂政》《伍子胥》《项羽》《司马迁》,黄灿然有《杜甫》,古马有《过华清宫》《赤壁》和《杜甫草堂》,李少君有《敬亭山记》《桃花潭》,陈先发有《中年读王维》和《敬亭假托兼怀谢朓九章》,陈陟云有《王的盛宴》《英雄项羽》之组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当代诗歌表现出一种寻根问祖的历史动感,是对古典诗歌遥远的膜拜和致敬。
对古典咏史怀古诗而言,当代咏史怀古诗既有对之的继承传续,又有超越性的时代发展。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对传统的继承是借助于何种方式实现的?并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发展又创造出哪些方面的新质?当代咏史怀古诗又居于一个什么样的美学地位?拥有什么样的历史诗学特征?这些,都有不少可供掂量、切磋、伸展的话题。接下来,笔者从当代咏史怀古诗对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阐释其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
一、传统的继承:用典的修辞和吊古的模式
在当代咏史怀古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各个分散、点点闪烁的古典灵光,这些灵光的色调甚不一样,形态颇有差别,情致各有千秋,然而综合起来就会使历史以及由其包孕着的往昔岁月和传统文化变成一种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存在。那么,所谓的古典灵光,其中的“古”和“史”是借助于什么样的言说方式表述出来的?当代诗人介入方式和责任承当会因历史的包容性和结构性呈现出怎样的形态?这应当从当代咏史怀古诗的修辞学所传承并遵循着的两个原则说起:一是用典的文字语法:把历史事实或历史文本作为典故加以化合妙用;二是吊古的抒情模式。“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当代诗人在历史场景中悉心地寻找深度与启示。正是这样的措辞特性和运思向度使当代诗歌频频闪烁着传统的吉光片羽,发散出浓郁的古典韵味。
用典,是在诗文中援引历史事实或历史文本来表情达意的艺术手法。古典诗歌中的典故,按来源可分为事典和语典。“事典”是“举乎故事”;语典是“引乎成辞”。用典作为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特色之一,在当代诗歌中也屡屡出现。
余光中的《草堂祭杜甫》吟咏的是杜甫48岁自秦州、同谷等地艰难赴蜀至59岁流寓湘江病逝的后半生,其中贯穿着杜甫夔州离乱的艰难岁月。在此期间杜甫写下了大量的不朽诗篇,真切深入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今天的诗人余光中在吊祭杜甫时,所用语言的某些局部如词语组合、从句、修辞术等,则采用、化合杜甫此阶段诗篇中的语言、意境。余诗中出现的“饮中八仙”“浣花溪”“曲江”“高楼”“茅屋”“白帝”等都曾是杜甫诗中的显词。其“家书无影,弟妹失踪”,更是直接把读者的审美视线指向“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更呢喃燕子,回翔白鸥”引向“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任孤舟载着老病”引向“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 引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杜甫的声音就这样在余诗中不绝如缕地幽鸣着。大量的语典使用形成了余诗语言这根线条充满张力的两头,一为语言的生产者,一为语言的使用者,其内部形成余光中和杜甫两个主体的对话。当然这并不是说二者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因余光中对杜甫在情感与思想上介入得极其深刻,二者是有相互渗透的地带,界限含混不清,总是缺少某种东西使读者作出明确的区分,这种语言的双重性是一种奇特的联盟,可以看出是今人对古人的一种深情探询、致意和拥抱。
与此相似的还有古马的《杜甫草堂》,该诗起首显然是有前文本互文反衬的,前文本即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草堂居住三年期间所写的一系列歌颂田园风光的佳章,如《绝句四首》(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那首)《水槛遣心》《江畔独步寻花》《江村》等,而古马诗最有具体指向的就是《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在该诗中,杜甫用欣快明朗的笔调抒写了一幅花蝶娇莺闹春图。而古马今天的“蝴蝶捧杯,娇莺夸口”,无疑是对一千多年前这首诗的巧妙回应和化用。对于以诗名世的大诗人杜甫来说,诗作是他的遗泽余香,供后人学习敬仰,后人用他的诗作和语言来纪念缅怀他是最自然不过了,由此一来也自然形成诗歌的语典。
《与阮籍对刺》是钟鸣的“典籍”之作。该诗把阮籍称为“大人先生”,抒情主体“我”与“你”即“大人先生”进行一场砥砺心志的思想冲刺。熟悉古典文学之人皆知,阮籍曾写过一篇奇文《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道家最高的理想境界和人格类型:“乘物以游心”“齐万物,一死生”的“大人先生”。“大人先生”秉着人性的自由发展对帝王“宰割天下以其私”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是社会的本质,所以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后世有人视“大人先生”为阮籍的自我写照。在钟鸣诗中,此是一语典,另有几处“事典”:其中之一是“一只白眼烈日,一只青眼豆火”,使人必然联想到它的出典——《晋书》上“籍又能为青白眼”。“大人先生”是阮籍的艺术创造物,“青白眼”是阮籍的历史事实,语典和事典一并运用,虚构和写实杂糅在一起。钟鸣就以这样的方式与历史上的阮籍进行思想对刺,对刺使双方都去掉无聊的浮浪和虚伪的粉饰,裸露出纯粹和本质,从而帮助抒情主体完成真正人格的塑形。
由上述可见,从形式上,“用典”是一种引用互文法,前文本被引入到新文本中来,其方式有缩略、概要、暗示、转移等诸多方法,语言修辞上既雅驯精致又冷峻含蓄。从内容上看,“用典”还是一种语义考古,它表明:先辈的意念仍在今人血脉中流淌,这种以历史固有典范来定义自己价值的倾向,是对传统价值传承的重要过程与表现。正是经由“用典”的记忆密码,当代诗歌与过去的时空血脉相连,灵魂的碰撞和精神的拥抱使得当代诗歌具有某种与古典诗词相重叠的性质。
历史的遗迹和特征既存在于由文本记录的时间长河中,又存在于广袤无边的空间地域中。地球的空间上铭刻着人类太多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文化是由累世文人浓墨重彩层层涂覆上去的。试问:如果没有白居易的“江南好,最忆是杭州”,没有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没有杨万里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没有历代文人诗词歌赋的言饰,杭州会不会如此地像现在闻名遐迩,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实难说!所以林莽在《肩水金关》中怅然叹惜:
在金塔城以北
曾与玉门齐名的一座汉代的雄关
因一万多枚汉简面世而浮出了历史
但因缺少了诗人王之涣
始终沉寂于平沙茫茫的戈壁滩上
一片片地域空间成为名胜古迹后,负载着大量人类文化学的深厚含义,变成质感化的记忆。比如扬州,在诗人的笔下,既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销金窟,又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锦绣地,还是“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的温柔乡。地域空间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色彩,总是引领登临游览的诗人们心生悠然之思,追忆渺远的历史情形。一如李少君在《我总是遇见苏东坡》中所道:“我总是遇见苏东坡/在杭州,在惠州,在眉州,在儋州/天涯孤旅中,我们曾互相慰藉/这次,在黄州,赤壁之下,你我月夜泛舟高歌。”
吊古的抒情模式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已形成自身独特的一套创作规则:先交代景物与时令,然后用典以示对历史当年情形的追忆,最后归结到自己的身世之感或天下兴亡的浩叹。运用这套吊古的抒情模式,当代诗人把笔触探伸到亘古的土壤中去,重新钩沉打捞出历史的骨骸并放置在今日的光线之下。且看古马的《赤壁》,历史上的赤壁之战被无数次地铭写,被众多的文牍和档案包围,被纷繁的言辞和书籍追逐,赤壁这个地方就成了一部有形的历史。它身上镌刻的名字太多太多。在数不清文人骚客的创作中,最有名的恐要数苏轼浩叹历史兴亡的传世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今天的诗人古马登临赤壁时,首先响在耳边的是历史上苏轼音律流畅,机锋凌厉的声音:“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所以该诗起首“清风周郎衣袖/水月苏子额头”呼唤的正是那种清越壮丽的历史情境。敬亭山是安徽宣城的一处名迹,是历史上南朝齐诗人谢朓吟诗的地方,“一生俯首谢宣城”的李白曾在此吟成著名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敬亭山这个地方因这些人、这些诗而获得了深沉的人类含义,变得质腻切实。当代诗人李少君登临此山时首要表达的就是对李白的敬意: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李白斗酒写下的诗篇
它使我们在此相聚畅饮长啸
忘却了古今之异
消泯于山水之间
(李少君:《敬亭山记》)
在《桃花潭》中,李少君接着向李白致敬。该诗分为三小节:第一节是阅桃花潭,看古木翠竹、青苔浅草、流云雾霭,一幅古色古香的青花瓷;第二节是品桃花潭,“桃花潭是封存千年的一坛好酒”,今天的我们“喝着这一坛李白未来得及喝完就已醉倒的美酒”而诗酒风流;第三节是听桃花潭,听百鸟啾啾,牛羊哞哞,桨声悠悠,鱼群泼剌的钧乐。感人显著,莫过于色;感人精微,莫过于声。声、色,这首诗都做到了,营构出一场视听盛宴。桃花潭的声色音尘酿就的这坛美酒至今使诗人啜饮不已。可是,最使诗人沉醉不已的还是李白千古传诵的《赠汪伦》之类的诗章吧!
用典的修辞方式和吊古的思维模式使当代诗歌文本中潜存有大量的“隐性本文”,如:余光中的《草堂祭杜甫》中有杜甫的《月夜忆舍弟》《登岳阳楼》《江村》《蜀相》;古马的《杜甫草堂》中有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赤壁》中有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钟鸣的《与阮籍对刺》中有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李少君的《敬亭山记》中有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桃花潭》中有李白的《赠汪伦》……。它们之间的呼应与对话,是古今灵魂的碰撞和精神的拥抱。显而易见,古典诗词是当下诗人不断返回和重新书写的隐性文本,当代诗歌常常以追寻、重访、钩沉为载体,一次又一次地重构或重述出古典史籍来,致使古典诗歌的某些元素在21世纪的背景下再次焕发出多彩多姿的青春。当然,重构或重述远非目的,目的是令之重生。当代咏史怀古诗毕竟不会重蹈古典咏史怀古诗的旧辙,它的诗学要求乃至历史学特征都呈现出一种当代性。何谓当代性?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智慧、当代的精神和当代的哲学理念。“如果‘当代’要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它就必须意味着为我们定义或聚焦了时间的某种东西,这东西似乎塑造了我们时代的面目,或者形成了这时代了解自身的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3]15当代咏史怀古诗不独追求对历史的立体复现,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诗学的拓展深化和现代性场景、经验的呈现。也许后者才是这部分诗篇存在的最大美学价值。
二、现代性发展:抒情主体新质自我的产生和现代场景经验的呈现
当代咏史怀古诗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进行着若干超越传统的创新努力,表现出不类从前的新特征,具体有二:
一是新质自我的抒情主体产生。分析诗歌的主导方法向来是集中研究说话人态度的错综性,研究一首诗如何使你所重建的说话人的思想感情戏剧化[4]79-81。套用这样的分析手段,可以发现:当代咏史怀古诗的抒情主体呈现出当代性的新质特征。
在古典诗中,古,大抵是用来喻今讽今的,以历史故事比况自己或当前所经验的事,说明自己的志向态度,小至托喻身世之感,大至寄慨白云苍狗的天下兴亡之叹。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思不多。诗人咏史怀古并不会被“史” “古”所湮没,有诗为证:“不恨我不见古人,但恨古人不见我”;“乃知古诗人,亦有如我者?”当代咏史怀古诗同样也是如此,引用典故以成吾意,加以个性化理解和创造性运用,典故有寄托、有深意,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彰显出强烈的现代主体的自觉角色意识。借用诗人们的诗句可以更好地来理解这一点——
历史典籍让人们朝云暮雾
心的秋水烟波微茫
时光往复 我行走于其中仿佛是另一个生灵
我不是李白 不是杜甫 不是范仲淹
更不是娥皇 女英 仰天长啸的三闾大夫
我只是秋天里的一株芦草
摇曳于岁月的某一阵风中
白了头
(林莽《暮色中登君山眺望洞庭》)
今夜,站在城墙上看月的那个人
不是王维,不是岑参
也不是高适
——是我。
(李少君《凉州月》)
这里,诗人们都突出强调了主体性介入,这种强烈的主体性光照总想洞察历史的迷雾叠嶂,发现其隐匿不彰的意义和踪迹,使之重置于现代性视阈中。在《暴雨洗过敬亭山》中,陈先发就极力想要代替古人说出他们未曾说出的一切,表达出历史“埋不掉的东西。是死者要将喉中/无法完成之物送回地面”。但是,“让我陷入绝境的/是我自己的语言//面对众人我无法说出的话/在此刻这幽独中仍难表达”。所以,这种表达的痛苦也即表达的期盼“遍及我周身。遍及我痛苦阅历中的/每一行脚印,每一个字”。
古今咏史怀古诗都有着鲜明的主体性,但我们明白,主体性是根植于时代的沃土之中的。时代不同,主体性的内涵和外延则不会相同。古典诗的抒情主体重胸怀而轻反省,呈现出的都是一个个天下皆醉我独醒的孤高自许,一幅幅对“历史救赎”洞若观火的刚愎自信。而现当代诗歌则不然,偏重于历史个体生活状态的反省,极力回复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可以说,对历史个体生活状态的反省与否,是古今咏史怀古诗抒情主体的泾渭间隔,唯有后者,才使历史和主体双向打开。
正是21世纪的主体性使诗人们不是匍匐在历史上爬行,而是与之对视对刺,在对视对刺处不断产生着新的碰撞与交锋,一次次碰撞与交锋,又都预示着一种种思想或情感情景的可能性展开,而这种展开无疑是一种当代话语逻辑和识见判断。在《杜甫》一诗中,西川和前辈诗人杜甫进行的思想碰撞即见一斑。杜甫的历史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前史,他的故事今天还在上演,只不过出现于新的光线之下。因为在岁月流逝之中,时代语境的基础已经转变。今天的诗人西川在当代的话语场域中试图和杜甫进行一场饶有意味的对话。这种对话性首先体现在形式上,西川在杜甫的煌煌诗章中撷取一句“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作为题首,以此来概称杜甫“深仁大爱”的人格,及由此带来的博大堂奥的艺术特征。从形式上该卷首引语的功能是对话性质的。前文本中的他人话语以卷首引语的形式转化为现文本的有机构成,双重意义上的存在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对话性。这样,利用卷首语引文的首要位置,发挥题旨的结构作用,以十分明显的对话姿态,导入正题,引出下文。
西川认为,杜甫的诗发出的是一种磅礴、结实又沉稳的声音,“在一个晦暗的时代”,这种声音成了“唯一的灵魂”。杜甫出生在世代“奉儒为官”的家庭,自幼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和熏陶,一心想走“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但是在当权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生活的磨炼中,杜甫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这样的认知,我国文学史上不少诗人也曾达到过。但“杜甫杰出的地方在于他突破了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始终采取面对现实,投身政治的积极态度,而把个人的穷达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5]181。所以杜甫在诗中频频表达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悯情怀,立志于“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切以现代视角观之,杜甫诗虽有经世致用之志,但在昏庸的统治者、暴烈的军队和强大的刀枪面前,它却无经世致用之力,一个豺狼横行的艰难世事里,诗人何为?所以西川质疑道:“伟大的艺术不是刀枪/ 它出于善 趋向于纯粹”。但西川的思索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接着往深层推进:即使你杜甫一介文人实现了文学的经国之大业,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又如何?
你比我们更清楚
所谓未来 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 不过是命运
(西川:《杜甫》)
与其说这是一千多年前杜甫的识见判断,不如说是来自21世纪的西川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与深度体味。在此,西川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引发人们对历史作再度思考,产生出的也就是一种立足于当代性高度的史识。新的史识使抒情主人公成为新质自我。这个新质自我与古典诗人的对话,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之一,也是他生命的一种另样形态。
可以看出,强大的主体性使当代诗人对视古典诗人进行着深层次的对话交流,对视,并不是取其反,而是综合性思辨——不是不同视点并置的结果,而是不同视点综合的结果,是它们融合为一体的结果。即是说,在交流的问题上当今诗人不是无条件顺应与古人方向一致的平行状态,也不是由于冲突而将之泯灭抵消,而是辩证性取舍发展。所以余光中企图在杜甫“无所不化的洪炉里/我怎能炼一丸新丹”(《草堂祭杜甫》)。古马在《赤壁》中,“我”没有看到“火的阴谋”“月光的字迹”,而是“空明”“净了”。这些都是抒情主体辩证思考古今的结果。
二是现代性场域、经验的展现和现代性视角的批判。强大的抒情主体是立足于现代性境遇经验之中的。身处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现代性经验的书写,具体地呈现出完整的时代与体验的内在的真实图景,是诗人无法回避的主题。即使是咏史怀古诗,诗人也不可能不顾现代性场域而一味沉溺于历史场域被历史同化。由于古今的差异,诗人最后还得从历史镜像中清醒过来。如柏桦的《李后主》一诗,诗中虽然部分放弃了20世纪当代人物的反观视角,在977年的语境里直接展示当时的历史场景,但情感抒发的现代性视角并未丧失。其《在清朝》亦复如此,整个诗篇用“在清朝”作为引子,串连起那个时代特有的事象和物象:科举、谷物、茶叶、山水画、庙宇,伴随那种散淡和缓的叙述的还有现代性批判。
正是由于现代性视角的烛照,当代咏史怀古诗有不同于古典咏史怀古诗的史识和洞见。同是吟咏项羽,古典诗歌杜牧的《题乌江亭》、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王安石的《题乌江项王庙诗》和当代诗人任洪渊的《项羽》、陈陟云的《英雄项羽》自是不同。杜牧、李清照、王安石对项羽的褒贬纵使不一,但其着眼点都在封建帝王们的成就霸业上,借对其歌咏以实现豪情慷慨的千古文人英雄梦。当代诗人任洪渊和陈陟云吟咏项羽或许是看到了现代社会勇侠精神不可挽回的没落,固然不能“起而行侠”,但完全可以“坐而论侠”,在现时代的语境中重铸另一种“英雄主义”。任洪渊的《项羽》起句就定下了雄浑悲壮的调子,项羽砍掉自己的头,发出的竟是“落日的响亮”,落日熔金,满目堂皇,橙色的光芒覆盖天宇,当落日遽然飞遁时有一刹那极其绚烂的展开。项羽自杀时诗人给他配置出了这幅壮景,何等壮丽、肃穆!头是砍掉了,心却被保全了下来,这颗心无疑是项羽尚勇尚侠精神的体现。如果该诗仅此而已,那它不过是重弹了千古文人英雄梦的老调,其奇拔警彻、峭然孤出之处在于:
心安放在任何空间都是自由的
安放在人的兽的神的魔的一个胸膛
温暖得颤栗
可以长出百家的头
却只有一颗心
(任洪渊:《项羽》)
诗人借咏项羽弘扬的是一种不拘形迹、不限格式的自由,褪除外界的人兽神魔的强制标签,不拘褒贬臧否的众说纷纭,只追求一种自由的心——独立苍茫,傲视千古,注重个人意志,追求个性舒展。非胸中有大丘壑,焉能想到这里!
陈陟云在《英雄项羽》中引领项羽及八百骠骑、江东子弟重新上路,不回江东,不到楚地,不入咸阳,要去哪里呢?诗人如是回答:
今夜,我用合掌的十指
引领你们
重新上路
从地平线背后的维度
看到一片澄明
(陈陟云:《英雄项羽之江东子弟》)
对项羽的当代性呼唤不是为了赞颂成就霸业的逞勇嗜杀,而是引领他们进入一片澄明境界,没有名利的杀戮、没有权欲的掳掠,有的是澄怀观道虚怀观物,以天地之心为心,自然小我扩大,其中不乏慈悲仁善之念,传达作者对于宇宙与人生的超然态度和达观意绪,道家禅趣意味很浓,澄明了英雄被遮蔽的另一种意义:庄子式的英雄。在当今欲望横流的现实无疑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或许我们可以迂回思辨一下,当代诗人咏史怀古的激发点或触媒很可能是现代性的弊端诱发的。在《醉后自谢朓楼往敬亭山途中怀古》中,诗人陈先发一开始就为时代的症候下了定义:“我以为能匹配这个时代的唯有/精雕细琢的躯壳”,在当今烦琐的物质主义时代,人们一味沉溺于口鼻耳目的感官享受而丧失了诗意的感受,缺乏诗意是物质时代人的显著性格特征,而缺乏诗意的时代显然又是一个人性堕落的时代。诗人厌倦了无休无止地与商品和物质碎片累积的世界奋战,因此决定选择另外一个方式——到大自然中去,在那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人的精神更需要原始和自然的庇护,所以陈先发呼唤着历史上的山水诗人谢朓——“所以谢朓到来”。在《枯树赋》中,陈先发仍然呼唤着谢朓。一棵枯树“在满目青翠中”却“一身苍翠地死去”,在它身上,诗人读出了谢朓的名字:
我们也可用时代的满目疮痍加上
这棵枯树再构出谢朓的心跳
而忘了有一种拒绝从
他空空的名字秘密地遗传至今
(陈先发:《枯树赋》)
诗人正是立足于现实的不足和缺失才呼唤着深远的历史性,想在时代空洞的精神里面注入一种坚实的内容。无论是从现代性视角审视历史抑或以历史来匡正补足现代性弊端,古今两重世界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微妙的隐喻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镜像”关系,彼此映照,互为隐喻。当下的现实场景始终为浓厚的历史所笼罩,反之,那些历史性又是当代诗人从当代性语境、高度、立场上对历史的新理解、新运用,是一种“去蔽”和重新呈现的行为。当代咏史怀古诗保持着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纷繁复杂的对位,开启现实世界与历史境域的比例关系。二者的镜像关系和对话性处于一定的震荡之中,由此建构起多重意义和价值对比之间的对话,形成双重主体,即如陈先发有句,“曾经我是两只蜂鸟中的一只/此刻我同时是这相互追逐的两只”。(陈先发:《醉后自谢朓楼往敬亭山途中怀古》)
现代性主体、现代性场景、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性视角是当代咏史怀古诗区别于古典咏史怀古诗最根本所在,是前者对后者最大的创新和发展。这里的现代性是从观念层面、精神层面来界定的,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美学气质,一种主体态度。
三、启示:继承和创新的新辩证关系
当代咏史怀古诗对古典咏史怀古诗既有继承,又有当代性的创新发展。继承体现在用典的修辞方式和吊古的运思向度上,创新体现在抒情主体的新质自我的产生和现代性场景、经验的呈现和现代性视角的批判上。继承多从语言修辞、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多从主体性和时代精神等方面开拓。二者的恰切熨帖表明,现代理念和时代精神在传统的表达方式中也可能趋近于完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咏史怀古诗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结合了久远的古典诗歌的传统,又包涵了当前的现实状况,充分吸收历史和现实的文化信息,并恰当地完成对这些信息的融化和组合。
从当代咏史怀古诗对古典咏史怀古诗的继承和创新上可以烛照出当代诗歌关于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第一,创新是第一义、根本性的,继承是第二义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继承可以被有所偏废,二者是胶着的关系。如果当代诗只有继承,仅从表面的语言效果或诗歌体式上表现了向传统的模拟,那么其“已退到要对古汉诗进行意义翻版或同镜再构的地步”[6]27。有继承,当代咏史怀古诗又并不止于此,其继承活动在本质属性上是与创造性理解同时到来的,在继承的基础上使之再生。“所谓再生,首先是指精神实质和内在元素的再生,在此过程中必定会融入一系列新的异质因素。”[7]
第二,创新永远是在社会环境、时代语境中升发出来的,创新之上凝聚着丰富的时代感,时代感是一种流转起伏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精神,一种被时代所崇尚的社会气质与总体风貌。人常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实不能据此判定后来时代的文学一定优胜于早来时代的文学,但一时代文学自有一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诚然不假。关于继承和创新,还是让我们谨记刘勰的“通变”思想。通,是指文学发展中有一些基本的创作原则是历代都必须继承的;变,是指文学创作必须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而有新的发展与创造。
这些,或许是当代咏史怀古诗关于继承和创新富有启示性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