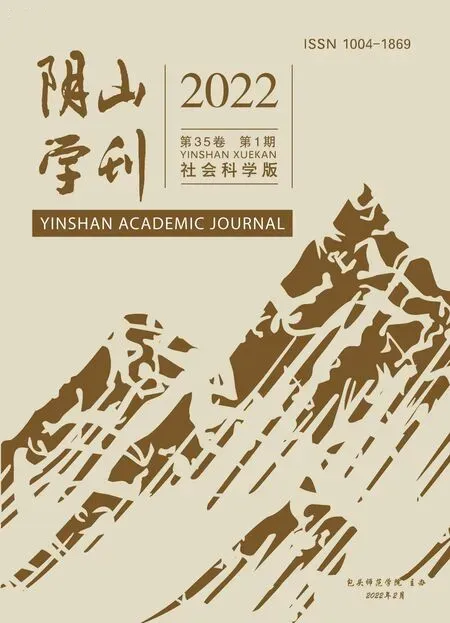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
高 雪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① 可参阅吴正南《“君子”考源》,《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第29-37页;池水涌、赵宗来《孔子之前的“君子”内涵》,《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25-129页;张贻珉《孔子君子观》,北方工业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页。
君子,是中国古代仁人志士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成为君子,是无数文人墨客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儒家是君子人格的推崇者和发扬者。余英时先生曾言:“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1]。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也可以称之为君子之学,儒家实现平治天下的方式在于培养君子。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周文疲敝的社会现状,学术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纷纷著书立说以寻求重建秩序之道,儒家则是把重建秩序的可能寄希望于君子。《论语》《孟子》《荀子》几乎章章言及君子,对君子的重视不言而喻。
先秦时期是君子思想的奠基期,君子思想的发展路向呈现出道德性和政治性两个维度。君子一词由来已久,西周时期便已十分常见。学界通过字源考证和对中华元典中君子概念的分析,普遍认为君子最初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贵族阶级的统称,并无道德伦理含义①。春秋末期,孔子赋予了君子道德内涵,彰显了君子的道德性之维,奠定了儒家君子思想的基础;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之维,从内圣的维度进一步提升了君子的道德内涵;荀子在继承孔孟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同时,从外王的角度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凸显了君子思想的政治性之维。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君子思想的政治性维度并非由荀子所开创,早在西周时期君子便指“在位者”,孔子讲君子为政以德、爱民惠民,孟子言君子有仁心行仁政,都是在政治维度下对君子的言说。与荀子不同的是,他们虽也涉及了君子的政治性维度,但对君子人格政治性维度的阐发也主要体现在道德层面,主要讲德性君子对社会政治的参与和影响。至于直接从政治立场出发对礼法君子的言说和重视主要是荀子,与孔孟不同,他主要从礼法的外王路径拓展和深化了儒家君子思想的政治性维度。
一、孔子与儒家君子思想的奠基
孔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守护者,他一生以恢复周礼为目标,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明了他的文化追求。面对“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社会现实,他述而有作,在继承发展礼乐文化的同时,开创了仁的思想学说,创立了以“仁礼合一”为主要内核的儒学思想。孔子所言说的君子,正是“仁礼合一”精神的化身,他既具备仁的内在自觉,又注重礼的外在约束,“既是道德修养的楷模,亦是政治治人的主体与承担者”[2]。前者主要体现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而后者更多地展现了孔子君子思想的政治性维度。当然,相较于君子思想的政治性维度,孔子对于儒家君子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对君子人格道德性维度的彰显。关于君子人格的道德性内涵,孔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刻画:
(一)穷且益坚——困境中的君子形象
君子最早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是贵族阶级的代名词。春秋时期,分封制逐渐瓦解,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贵族阶层受到冲击,君子不再是高枕无忧的统治阶层。孔子赋予君子新的内涵,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理想人格典范,君子可能不再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甚至会穷困潦倒,但有着穷且益坚的优秀品格。所以当孔子与弟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时,子路很不高兴地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来回应他[3]159。孔子认为,君子也有穷困之时,但可以坚守道义原则,不会像小人一样“穷则滥溢为非”。正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3]35。可见,孔子对于君子形象的界定已经侧重于其道德精神追求,而非止于位的拥有。
(二)仁义智勇——君子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仁、义、智、勇等优秀品格的具备,是孔子赋予君子的道德修养要求。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其君子思想中的重要道德内容,他将仁看作君子行道所必须具备的品德之一。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3]35。在孔子看来,没有仁德,君子是无法成就其声名的,君子不论外界环境如何,无时无刻不在践行仁。由此可见仁对于君子的重要性,仁是所有美好品德的基础,君子拥有仁,便具备了最重要的美德,便不会产生忧愁,可以达到“仁者不忧”的境界。那么,君子应该如何行仁呢?这就需做到孝敬父母,宽待亲友,以身垂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3]77,在上位的君子应该以身垂范,做好榜样作用,对亲人和故旧宽厚,这样百姓便也能拥有仁。所以当宰我对孔子抱怨“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时[3]186,孔子应对说:“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3]186他严厉斥责宰我:“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3]186。孔子弟子有子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2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3]130,都主张以孝敬父母、宽待亲友来实现仁。
义是孔子思想的道德范畴之一,也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孔子所言义,具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适宜、合宜,“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3]164“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3]36“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3]188此处的“义”都是强调适宜、合宜的重要性。对于天下之事,君子应以合宜为原则。二是指与利相对的概念范畴,侧重于道德性的内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8,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君子是重义的,可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69“君子达于德义,小人达于财利”[4]195。
智和勇亦是君子所具备的道德品格。孔子言君子道者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3]153,君子不仅要有仁,还得具备智与勇。君子有仁者之心,但并不鲁莽盲从,拥有智慧而不被迷惑。所以当宰我问孔子“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时,孔子回之“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3]62,即可以做到“知者不惑”。勇是指勇气,但孔子强调的君子之勇并非是鲁莽冲动的勇往直前,而是兼具义和礼之勇,“勇而无礼则乱,”[3]77“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3]188可见君子不仅要有勇,更要有礼的约束和义的规范。
除了对君子人格道德性内涵的凸显,孔子也注意到了君子人格的政治性功用。一般说来,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德政和礼法。孔子则主要阐发了德政君子的一面,主张君子应行德政,强调君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君子在政治生活中应起到榜样作用,以身垂范。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孔子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127,“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回之[3]127,可见孔子十分重视君子以身垂范之作用,君子在政治生活中能够以身正己,百姓则能够安定顺从。在用人方面,君子应该做到“取其善节也”[4]214,即“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3]164。
其次,孔子主张身居上位之君子应该惠民爱民。孔子认为君子为政,可以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3]208。具体说来,便是能够做到与民以利而自己无所耗费,在百姓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让百姓去劳动,从而不招致怨恨,想要仁德就能得到仁德而不贪求其他,不以人多人少和势力大小去怠慢他人,这样便可以做到安泰矜持而不骄傲,君子穿戴整齐、目不斜视,庄严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从而做到威严却不凶猛。
由此可见,孔子对君子提出了道德修养上的基本要求。面对困境君子应该有穷且益坚的高尚品质,同时,君子也应具备仁、义、礼、智等优秀品行。由此可以说,孔子主要从君子自身道德修养的角度彰显了君子的道德性之维,赋予君子以德性修养的内涵。当然,孔子也注意到了君子的政治功用,他从有德君子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强调有德君子应有“学而优则仕”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从政过程中他们应自觉端正自身、以身垂范,通过上行下效在社会上形成良好道德风尚。此外,有德君子从政还应行德政,积极实施惠民举措以安百姓。概言之,孔子对儒家君子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贡献是给君子注入了德性修养的内涵,彰显了君子思想的道德意蕴,肯定了有德君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奠定了儒家君子思想的基本理论基础。
二、孟子对孔子君子思想的内圣化发展
孟子在继承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的基础上,对其君子思想进行了内圣(1)梁启超曾言: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此处的内圣以及第三部分的外王便是基于此义而言的。化的发展,从性善论出发进一步对君子人格的德性修养要求做了深入阐发。如果说孔子主要彰显了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赋予了君子以具体的道德修养要求的话,那么,孟子则更加侧重于主体的道德自觉,对君子何以能够具备高尚德行进行了阐发。
孟子对君子思想内圣化的阐释是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5]280。“性善论”是孟子“向人的生命深处追寻善的依据”的理论成果[6]82,是他“发挥孔子仁学的主体精神,强调道德价值内在于吾人的生命之中”而确立起来的本体论主张[6]82,它为“儒家的修身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7],也为君子的内圣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前提。性善论言人有四心、四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由仁义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等主张,认为人们生而具有善端,不必外求,只需保持善端并将其发展为善行即可。由此,孟子解释了人何以能够有善行善的问题,彰显了人具有道德自觉的深层依据。而孟子更是将这种道德自觉视为君子之特性,也是君子与常人不同之所在: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5]210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5]218
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一点点,一般人都丢弃它,而君子能够保存它,所以君子能够明于庶物人伦,内心具备仁义然后将其外化于行动。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存心”的不同,君子会以仁与礼存养本心。人人都有善端,但君子能够将善端化为善行的原因是君子能修己,做到了“扩而充之”(2)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此外,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君子也与常人一样,拥有不忍人之心,所以君子远庖厨,“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5]16君子拥有与常人一样的本心,却更加的仁慈,无外乎是做到了“以仁存心”“由仁义行”。
对于修己,君子还表现在对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追求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耳、目、口、鼻以及躯体的享受,君子认为能否得到属于命,并不强求。而对于仁、义、礼、智等美好的道德,君子认为应该竭尽所能,努力修己以拥有: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5]375
孟子认为君子是不可以拿钱收买的,“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5]99对于钱财君子是淡然的,但君子很注重仁、义、礼、诚的拥有,所以孟子讲: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5]314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5]274
君子不亮,恶乎执?[5]327
可见,君子对于道德素养有着很高的追求。
君子之性也是基于性善论而言的,君子通过修己能够将善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5]344。此外,君子比较注重内心的真实,而不在意徒有虚表的形式,故“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5]356。以上都体现了君子的主体意识和道德自觉。
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85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统治者将仁心推及政治层面,便可以实现仁政。“孟子仁政论政治哲学的思想根基在‘心’论上,孟子讨论王道仁政的实现也多着眼于从君主的‘仁心之发动’开始。”[8]65而君子则是由仁心实现仁政的主体,作为拥有道德自觉之人,对于社会治理君子亦会自觉承担起责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孟子也看到了君子于国家社会的作用,言“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5]352。君子除了自身要修己拥有道德外,也要向政治、社会延伸:
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381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5]202
由此可见,在性善论这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孟子主要从内圣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孔子的君子思想,在孔子所理解的有德君子的基础上对其何以能够具备高尚道德人格进行了阐发。与孔子一样,孟子虽也积极肯定君子的政治功用,但他主要强调仁心对于仁政的基础作用,以性善论为理论依据将仁心善心推及政治层面,而君子则是由仁心推及仁政的自觉承担者。可以说,在理论特点上,孟子君子思想“实际上是走了一条由内而外、由政治而道德的道路”[7]。可见,儒家君子思想中礼法君子的这一重要政治之维,从政治而非道德立场出发讲君子,至孟子也并未清楚而自觉地表达出来,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荀子来推动完成。
三、荀子对孔子君子思想的外王化发展
孔子彰显了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孟子则从内圣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到荀子时,儒家所理解的君子已经是指具备仁、义、礼、智、信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荀子对孔孟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是继承的也是发展的。从《荀子》中我们可以窥见,荀子所理解的君子具备仁、义、礼、智、勇、诚等道德品格,俨然已是一个具有极高道德修养的楷模。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对孔子君子思想进行了外王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从政治角度而非道德角度出发凸显了君子的政治性维度,他不仅注重有德君子参与社会治理之功用,更强调礼法君子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前者是对孔孟那种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有德君子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后者则是荀子从其所处之时代语境出发而对礼法君子的期许与凸显。由此,荀子所理解的君子不仅是道德楷模,更是一个治世的政治人才。正如东方朔所言:“在荀子思想中,作为政治之理想人格的君子既是道德的楷模,也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和公道世界的设计者、承担者和完成者。”[9]
荀子直承孔孟,对其君子思想中有德君子之面向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有学者称:“君子,作为政治人格,体现在官制中的德位合一”[10],荀子便承袭了孔孟之君子“德位合一”的内涵。那么在荀子看来君子怎样在政治生活中做到“德位合一”呢?这可以结合《荀子》文本进行分析。
荀子言:“君子者,治之原也。”[11]228即君子是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源头,又言:“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11]228,可以说君子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以身垂范的表率作用,表率作用示范得好,便会上行下效,整个政治风气和氛围都会变好。这与孔孟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荀子还有言:“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11]492即君子入仕可以为君主增光、为百姓减忧,能够很好地发挥治理作用。那君子应该如何发挥其“治之原”的角色呢?
首先,君子应该做到诚,“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11]45-46,做到至诚的方法则是守仁行义,“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11]46。
君子至德,嘿然而喻,……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11]46-48
荀子将诚视为可以感化万物、教化万民、懂得尊卑亲疏等的必要条件,是君子的操守,视为“政事之本”。而要达到真诚,则需守仁行义,这正是对孔孟君子人格之继承与发展的表现。荀子认为君子做到至诚,便可以感化万物万民,使百姓不返恶的本性,从而维护政治秩序。
其次,君子自身要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以从政安民。君子要依靠德行来实现社会的治理,做到治民有术,从而更好地实现德位合一。荀子讲:“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少者以长,老者以养。”[11]179-180有德行的君子通过治理,可以役使百姓的体力劳动,可以使百姓的群居生活和谐、财务有所积聚、地位能够安稳、寿命可以长久,使父子亲密、兄弟和顺、夫妇欢乐,少有所依、老有所养。
君子还可以凭借聪明才智使百姓归服,治天下之众。荀子言:“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11]212也就是说,睿智的君子善于使众人敬佩,众望所归以取势,行事轻而易举且会有赫赫之功,容易相处且乐观。而那些身居高位的君子能够不出内室厅堂却知晓天下情况,是因为治民有术。“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11]48-49此之谓也。
此外,君子应该行德政,使庶民安政、国家富足,如此君子才能安其位。《荀子》言: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犹将无益也。[11]151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11]175
实现“庶民安政”,君子应行德政,选拔德才兼备的贤良之士,帮助孤寡贫穷之人,做到“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要使国家富足,则需“节用裕民”,如此君子方可安其位,实现德位合一。
无论是君子守仁行义以达到至诚或是凭借其自身道德以从政安民,还是君子实行德政之策,都是从君子自身修己修德积极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而言的,这与孔孟之君子人格的政治表现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荀子对德政君子的阐发是对孔孟君子人格政治表现的肯定和认可。
当然,荀子虽从德政君子的角度发展了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但其对于儒家君子思想发展的贡献,最主要的还是从外王的角度凸显了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面对天下即将定于一的历史大势,荀子以儒学为宗,整合诸子思想资源而形成极具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为重建秩序设计了一套治理方案。荀子开出的治理之方主要有两点,一是礼义,二是法度。在此基础上荀子凸显了礼法君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关于君子在礼法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荀子说:
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11]161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11]226
礼义是治理之本,而君子是礼义之本;法度是治理之端,而君子是法度“之原”。可见,礼义法度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虽十分重要,但君子是礼义与法度得以实施的主体,在礼法的实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荀子为什么如此重视礼义法度,礼义法度的实施又为何依靠君子?
荀子将君子当作“治之原”,将重建秩序的使命寄托于君子身上。他重视礼法君子的原因在于礼义法度的作用符合了君子修己安人的品质。首先,践行礼法能够修身正己,如果没有礼法是寸步难行的。荀子言:“礼者,所以正身也。”[11]34“无礼何以正身,”[11]34“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11]142“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11]347“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11]480“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11]479其次,礼法的践行能够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11]206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11]275
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11]477
可见,礼对于国家社会而言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起到约束和规范之效,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措施。“隆礼至法则国有常”[11]234,荀子在隆礼的同时,也注重法的作用,“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11]320,刑罚等法度的正确实施,能够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反之社会便会混乱。礼法之用是荀子构建礼法君子来治理社会的直接原因。
荀子凸显礼法君子的深层原因则追溯到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主张[11]420,这也是荀子隆礼重法、构建礼法君子的逻辑起点。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11]337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埶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11]70
荀子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生而有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追求,如此便可能导致争夺、祸乱乃至会使人陷入秩序崩溃的困境。高贵的身份和富裕的生活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但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欲望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所以古之圣王面对由人的本性而引发的无序局面采取的治理措施便是“制礼义以分之”,这便是礼的起源,用礼义来明分使群,使人们有所差别,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实现“群居和一”。可以说礼义是由圣人制定的,它能够起到分和安民治乱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圣人与常人的本性一样都是恶的,他之所以能够制礼义是因为圣人做到了化性起伪。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11]423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11]423
圣人能够深思熟虑,通过人为的努力克制自身的欲望,对于人们的欲望能够做出合理的安排以分,于是产生了礼义。所以说礼义并非产生于圣人的本性,而是生于“圣人之伪”,“伪”即人为(3)杨倞注:“伪,为也,矫也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可参阅廖名春《由〈荀子〉“伪”字义论其有关篇章的作者与时代》,载于《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可见,“伪”在礼义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能够由性恶到拥有礼义的重要环节,强调了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也赋予了君子及常人可以通过化性起伪以掌握礼义的可能性。“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11]425,礼义对于社会治乱具有重要的作用。荀子通过圣人的化性起伪、制定礼义让人看到礼义对于安定社会之用,也使人看到人性虽恶,但善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获得,人生来虽不会拥有礼义,但君子作为“治之原”却能够化性起伪,学习并通晓礼义。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11]425
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11]427
故荀子基于人性恶的理论突出了礼义的明分使群的作用,又指出礼义来自圣人的化性起伪,强调后天努力的作用,赋予了君子能够通晓礼义的前提。然礼义并不会自己实行,必须要有通晓礼义并能够有效实行的君子参与。“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11]162没有君子,便无法治理天地、统摄礼义,纲常伦理就会混乱。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11]44
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11]255
君子施政,礼义得到遵行就是治,礼义遭到破坏就是乱;礼义完备会吸引君子归附,有了礼便会使人品行优秀,有了义便会使国政清明,与积礼义的君子共同为政便可以称王于天下,“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11]205正如彭岁枫先生认为的,礼义是社会和谐之根本和前提,圣人发现了礼义,而君子宣扬和传播了礼义,没有君子就没有礼义的宣扬和传播[12]。所以荀子讲“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君子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亦会向其理想目标即圣人学习,主动地化性起伪以通晓礼义,君子能够通晓礼义便可以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由此荀子凸显了礼义君子的必要。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11]423,法度同样是圣人为了改变人恶的本性化性起伪而制定的,圣人制礼义后,随之也建立起法度来矫正、引导人们的性情,使人们都能够遵守社会秩序,合乎道德原则。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11]421
可以说,法度是伴随着礼义而生的。礼义与法度都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与礼义不同的是,法度有着具体的行为规范,更具有强制性,通常用刑罚与明令禁止的准则条例来实现社会治理。荀子言:“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11]425可见,礼义主要是教化之用,法度有治理之效,刑罚起到禁止之功,运用得当,便能天下大治。
可见,法度同礼义一样,也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荀子讲“法者,治之端也”。但是法度同样也不会自己实行,也不会灵活变通,法度制定后如果不能灵活的实施,那么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就容易出现问题:“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11]150只有君子才能够做到对于法度灵活变通实行,使各项工作不失误,“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11]150故君子在法度实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11]226
荀子认为法度是“治之端”,而君子则是“法之原”,是法度施行的主体。君子懂得法度的道理,无论法律简单与否,都能够应对自如,处理得当。荀子还认为“有治人,无治法”[11]226,法度的实行必须要靠君子来实施,君子是正确的原则和法度的总要,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人物,健全的法度不一定能够保证国家平安无虞,但君子的存在却可以使之免于危乱。正所谓:
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11]256
可见,荀子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强调法度之于社会治理的功效及作用,所以荀子才讲“法者,治之端也”,法律制度毕竟是刻板僵硬的,其灵活运用和正确实施离不开旨在正理平治以安人的君子的参与,所以荀子讲“君子者,法之原也”。由此,荀子从人性论这一角度凸显了法度君子的必要。至此,礼法君子在荀子的君子思想中凸显开来,荀子凸显了儒家君子思想的政治性维度。君子作为礼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主体,又是怎样利用它们来进行社会治理的呢?
首先,君子对于礼义应该学习研究、熟悉贯通、积累并且爱好,这是做君子最先要做的事情。所以荀子讲:“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11]161
其次,君子通晓礼义,对于礼义是敬重且遵守的,并能够将之贯彻到为人处世之中。
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故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并遇变态而不穷,审之礼也。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居乡里也,容而不乱。[11]228-229
再者,荀子认为礼是严谨地处理生和死,君子对于生死之礼,是十分慎重的。君子能够严肃对待人的出生即人生的开始,也能慎重地对待人的死亡即人生的终结,对于生死都能同等重视,这是君子的原则,也是礼义的具体规则,故荀子言:“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11]349
此外,君子对于礼义的实行把握适中,行之有度。“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骛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坛宇宫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11]348
对于法度,君子是爱好的,并会意志坚定地去践行,所谓“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11]33“少言而法,君子也。”[11]97
君子能够践行法度,行为能够合乎礼义。而那些肆意放荡违反礼义的人,则是小人,所谓“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11]421也正是因为小人的存在,更需要通晓、践行礼法的君子存在,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法度的约束,那么社会就会混乱。如果君子有权势去统治他们,那就能够教化和约束百姓。所谓“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埶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11]64君子守礼义,尊法度,教化百姓,明德慎罚,便可实现国家治理,“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11]445。故君子在礼义与法度作用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荀子从德政君子和礼法君子两个维度凸显了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前者是对孔孟君子思想中有德君子面向的继承与发展;而后者则是从政治立场、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强调了礼法君子的必要,由此实现了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外王化发展。对德政君子的强调,体现了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对礼法君子的彰显,则体现了战国晚期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荀子君子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相较于德政君子对于国家治理的贡献,荀子更注重礼法君子的作用和影响。他主要从政治而非道德的立场出发来讲君子的必要性,由此深化和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之维。荀子对君子人格政治表现的阐释,丰富了儒家君子思想的内涵,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追求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结语
先秦儒学大师孔子、孟子、荀子对君子的阐释确立了儒家君子思想的主要内容,使君子成了道德要求与政治要求兼备的理想人格。具体说来,孔子奠定了儒家君子思想的基础,彰显了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孟子对孔子君子思想作了道德精神下内圣化的发展;至荀子时君子的道德人格已十分完备,荀子在此基础上又从政治的外王立场出发凸显了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需要注意的是,在荀子以前,孔子主张君子行德政,孟子主张君子行仁政,两者都已注意到了君子的政治功用,肯定君子对社会政治的积极影响,但这都是从有德君子参与社会政治的角度而言的,并非直接从政治立场出发而对君子进行理解和说明。由于时代语境的转变,荀子对儒家君子人格的阐发呈现出政治现实主义的色彩,主张君子守礼义、行法度,从政治立场即外王角度凸显了礼法君子的政治功用。孔子、孟子、荀子对于君子的塑造,奠定了儒家君子内圣外王的基本要求。孔子确立了儒家君子的道德精神,孟子在继承孔子君子思想的基础上作了内圣化的发展,而荀子对孔子君子思想则作了外王化的凸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治国方略。荀子从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对德政君子与礼法君子的推崇便很好地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思路。在荀子看来,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有美好德性的礼法君子来引领,而现代社会治理其实还是需要荀子所看重的这种君子,他们不仅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还在法治建设上有所贡献。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不意味着两者居于平等并列的地位。两者相比,前者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向,而后者则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补充”[8]128。所以,具备优秀道德品质的治理人才固然重要,但拥有法律意识和法治才能的治理人才于现代国家治理来讲或许更为重要。这或许正是荀子君子思想留给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点启示。因此,我们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可以以史为鉴,“从民族传统社会治理思想中汲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慧和灵感”[8]133。从孔子、孟子、荀子的君子思想及其比较和嬗变来看,他们留给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历史借鉴或许在于: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我们虽然需要孔孟塑造的具备高尚道德品质和注重内在道德自觉的君子作为榜样,但更需要荀子塑造的兼具优良政治品格和注重外在规范约束的君子作为楷模。当然,仅就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而言,这对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政治人才的培养尤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对我们自身的修身养德和建功立业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