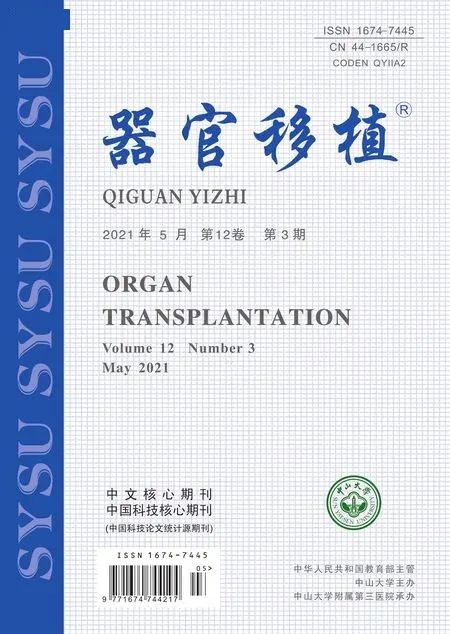贝拉西普
——抗排斥反应战场上的新武器
孙赫 孙旖旎 程颖
器官移植是临床上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重要手段,也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医学成就之一。绝大多数器官移植受者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术后终身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目前常规的免疫抑制方案为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类药物联合吗替麦考酚酯,有时还需联合糖皮质激素[1]。现有的免疫抑制方案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近期疗效,但远期疗效仍不理想[2-3]。
以CNI类药物为基础的二联或三联免疫抑制方案可以有效地预防移植受者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但因其作用靶点广泛,而并非特异性、精准性地针对免疫系统,同时也给受者带来了很多不利的脱靶效应,如肾毒性、神经毒性、高血压病、代谢性并发症(移植后糖尿病、高脂血症等)[4-10]。鉴于此,移植免疫工作者开始不断探索新的特异性针对免疫细胞的药物来取代CNI类药物,于是共刺激阻滞剂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贝拉西普是世界范围内第1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用于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治疗的共刺激阻滞剂,本文对其临床疗效及临床应用做一综述,旨在为优化临床免疫抑制方案提供参考。
1 共刺激阻滞剂的问世
T细胞的活化至少需要2个独立信号的刺激[11-12]。第一信号来自于T细胞表面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和CD4或CD8分子同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提呈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肽复合物的结合;第二信号来自于T细胞和APC表面的共刺激分子的相互作用。而共刺激阻滞剂的原理则是通过特异性阻断T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抑制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从而达到预防排斥反应发生的目的[13]。
T细胞表面可以表达不计其数的共刺激或共抑制分子,最先受到关注的是其中最经典的、也是在T细胞免疫应答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共刺激分子——CD28[14-15]。最初人们发现针对CD28受体的直接阻滞剂可以显著抑制T细胞的增殖,但是传统的抗CD28抗体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定的激动活性[16-17],这也大大阻碍了CD28受体直接阻滞剂的临床应用,并迫使人们将目光转移到了针对CD28受体的间接阻滞剂——贝拉西普(belatacept)。贝拉西普是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CTLA)-4免疫球蛋白融合蛋白,它并不是一种抗体,而是CTLA-4分子的类似物,它的作用原理是选择性地与CD28和CTLA-4分子的共同配体CD80(B7-1)、CD86(B7-2)结合,从而达到阻断CD28受体的目的[13]。贝拉西普也是临床上另一种CTLA-4免疫球蛋白融合蛋白药物——阿巴西普(abatacept)的升级产品,比阿巴西普具有更强的CD80和CD86结合力。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同时发现,贝拉西普可显著地提高同种异体移植物的存活率[18-19],因此贝拉西普很快于2011年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批准,成为世界范围内第1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用于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治疗的共刺激阻滞剂,现已在欧美国家广泛使用。略为遗憾的是,贝拉西普尚未在我国被批准使用,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2 贝拉西普的临床疗效
2.1 贝拉西普的有效性
对于贝拉西普的临床疗效评价,世界范围内已开展了多项临床试验。首先是Vincenti等[20]在著名综合类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的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Ⅱ期临床试验研究。该试验比较了以贝拉西普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和以CNI类药物中的代表药物——环孢素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的临床疗效差异。结果发现,在肾移植术后12个月内,贝拉西普组受者的移植物功能[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显著优于环孢素组,同时慢性移植肾肾病(chronic allograft nephropathy,CAN)的发生率显著低于环孢素组。
鉴于这项Ⅱ期临床试验令人鼓舞的结果,一项名为“贝拉西普作为一线免疫抑制剂的肾脏保护及临床疗效评估试验”(Belatacept Evaluation of Nephroprotection and Efficacy as Firstline Immunosuppression Trial,BENEFIT)的临床试验研究迅速开展起来[21]。这是一项由世界范围内100多个移植中心参与的多中心、单盲、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研究。该研究的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接受活体供肾肾移植或标准尸体供肾肾移植的受者。排除标准为:供者年龄≥60岁,或供者年龄≥50岁并同时合并以下至少2项危险因素[脑卒中、高血压病、血清肌酐>132.6 μmol/L(1.5 mg/dL)];冷缺血时间≥24 h;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纳入的肾移植受者被随机分配到3组:高剂量贝拉西普组、低剂量贝拉西普组、环孢素组,每组受者均同时接受巴利昔单抗免疫诱导治疗以及吗替麦考酚酯和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治疗。该试验最终共入组666例受者,其肾移植术后1、3、5、7年的随访结果,分别在《美国移植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报道[21-24]。结果显示,肾移植术后7年,贝拉西普组受者死亡或移植物失功的发生率较环孢素组下降约43%[24]。在移植肾功能保护方面,肾移植术后1年和3年,高剂量和低剂量贝拉西普组受者的GFR均明显高于环孢素组[21-22];术后5年和7年,贝拉西普组受者的GFR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而环孢素组则呈持续性下降趋势[23-24]。但同时令人遗憾的是,贝拉西普组受者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更高,且排斥反应病理学分级较环孢素组更为严重。该研究同时发现,贝拉西普组急性排斥反应多发生于肾移植术后1年以内,高剂量贝拉西普组、低剂量贝拉西普组、环孢素组术后1年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2%、17%、7%[21]。术后2~3年,贝拉西普组无新发排斥反应,环孢素组有1例新发排斥反应[22]。术后5年,低剂量贝拉西普组和环孢素组各有1例新发排斥反应[23]。术后7年,只有环孢素组有1例新发排斥反应[24]。
与此同时,另一项针对扩大标准供者应用贝拉西普临床疗效评价的多中心、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BENEFIT-EXTended criteria donors,BENEFITEXT)也在进行[25-28]。该临床研究同样比较了高剂量贝拉西普组、低剂量贝拉西普组和环孢素组的临床疗效,试验分组及用药方案与BENEFIT试验一致。结果显示,术后1年和5年,贝拉西普组受者的肾功能均优于环孢素组(P=0.008 3、P<0.000 1)[25,27],术后3年和7年,贝拉西普组受者的肾功能略优于环孢素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28]。而在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受者生存率及移植肾存活率方面,各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为了进一步比较贝拉西普与他克莫司的临床疗效,de Graav等[29]开展了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该研究共纳入了40例肾移植受者,随机分配至贝拉西普组和他克莫司组。结果显示,贝拉西普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高于他克莫司组(P=0.006)。同时贝拉西普组受者中3例出现了术后移植物失功,且均为急性排斥反应所致。
随后,美国Emory大学移植中心Adams等[30]对745例肾移植受者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比较贝拉西普和他克莫司免疫抑制治疗的临床疗效。同样发现,贝拉西普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高于他克莫司组(50.5%比20.5%,P<0.001);且贝拉西普组排斥反应病理学分级也更高。在肾移植术后4年内,贝拉西普组受者较他克莫司组表现出更好的肾功能水平(GFR 63.8 mL/min 比 46.2 mL/min,P<0.000 1)。而两组在严重感染(巨细胞病毒、BK病毒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是肾移植术后移植物失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现有的免疫抑制方案并不能很好地抑制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产生,因此贝拉西普是否可以有效降低DSA水平便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BENEFIT及BENEFIT-EXT试验同样对3种免疫抑制方案在抑制DSA产生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令人鼓舞的是,在BENEFIT试验中,贝拉西普组较环孢素组能更有效地降低新生DSA和移植前预存DSA的水平[31-32]。对于扩大标准供者供肾肾移植,贝拉西普组受者新生DSA和移植前预存DSA的水平显著低于环孢素组[31-32],说明贝拉西普对于扩大标准供者供肾肾移植术后的DSA水平有良好的调控能力。另一项研究进一步对BENEFIT及BENEFIT-EXT试验中不同类型的DSA进行分析发现,贝拉西普组和环孢素组受者的DSA IgM阳性率接近,但环孢素组受者的DSA IgG阳性率显著高于贝拉西普组,表明贝拉西普较环孢素能更有效地抑制DSA IgM向DSA IgG的转化[33]。鉴于单纯DSA IgM阳性已被证实并不影响移植肾受者的远期预后[34],因此贝拉西普可抑制DSA IgM向DSA IgG转化,可能是其发挥更好的移植肾功能保护作用的潜在机制之一。贝拉西普调控DSA水平的可能机制,首先在动物移植模型中被证实,研究发现贝拉西普可有效调控CD95+GL7+生发中心B细胞和供体特异性滤泡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Tfh)[35-36]。而在临床试验中同样证实,贝拉西普通过细胞内源性途径调控浆母细胞的分化和功能,调节B细胞表面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并破坏Tfh与B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37]。
2.2 贝拉西普的安全性
BENEFIT临床试验提示,高剂量贝拉西普组、低剂量贝拉西普组、环孢素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70.8%、68.6%、76.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4],其中最常见的严重不良事件为严重感染,每百人每年分别发生10.6、10.7、13.3次。而各组在术后7年后由于不良事件而调整免疫抑制方案的受者比例为5%~6%。
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尤其是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PTLD)的发生风险,一直是临床上应用贝拉西普时令人担忧的问题。BENEFIT临床试验同样提示,高剂量贝拉西普组、低剂量贝拉西普组、环孢素组肾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每百人每年分别发生2.1、1.8、2.6次[24]。术后7年,贝拉西普组有5例受者发生PTLD(低剂量组2例,高剂量组3例),环孢素组有2例受者发生PTLD。贝拉西普组发生PTLD的5例受者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率较高(2/5);除1例受者外,其余受者PTLD均发生于术后2年内。目前,临床上为了避免应用贝拉西普引起的PTLD,通常不建议应用于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血清学阴性的受者[38-39],但也有研究认为EBV血清学状态和贝拉西普剂量与PTLD的发生率并无明显相关性[40]。
肾移植术后高血压和高脂血症是造成受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及影响移植物功能的重要危险因素。BENEFIT和BENEFIT-EXT临床试验均提示,即使环孢素组受者于术后接受了更大剂量的降压药和调脂药物治疗,贝拉西普组受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及血脂水平仍低于环孢素组[20,24,28,39]。
以上临床试验表明,贝拉西普较CNI类药物可明显减少药物不良反应,提高移植物功能和存活率,并有效抑制DSA的生成。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因而限制了贝拉西普的临床应用。鉴于贝拉西普药物的优势和劣势,笔者认为贝拉西普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抗排斥反应战场上的新武器,服务于广大移植受者。
3 贝拉西普的临床应用
3.1 贝拉西普在肾移植中的临床应用
基于贝拉西普组受者术后1年内排斥反应发生率较高,部分移植中心开始尝试利用贝拉西普联合他克莫司的过渡治疗方案。Adams等[30]研究报道,肾移植术后6个月内联合应用贝拉西普和他克莫司,适当减少贝拉西普用量,并维持他克莫司于目标血药浓度范围内,在术后3个月内排斥反应发生率控制良好,联合用药组排斥反应发生率与他克莫司组接近;但联合用药组停用他克莫司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仍高于他克莫司组(33.3% 比20.5%,P=0.046)。之后,该研究团队将方案调整为联合用药时间延长至术后1年,调整后联合用药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与他克莫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0%比20.5%,P=0.900),且比他克莫司组能提供更好的肾脏保护作用。
同时,一些移植中心开始尝试调整肾移植术后接受CNI类药物治疗且免疫状态稳定受者的免疫抑制方案,以避免长期使用CNI类药物所造成的不良反应。一项Ⅱ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在肾移植术后3年内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方面,贝拉西普联合CNI组略高于单纯CNI组,但贝拉西普联合CNI治疗同时可以提供更好的肾脏保护作用[41-43]。此外,还有一些移植中心也在尝试由CNI类药物向贝拉西普转化的方案,均取得了不错的临床疗效[44-46]。
3.2 贝拉西普在其他器官移植中的临床应用
贝拉西普在肝移植受者中的应用首先由Klintmalm等[47]报道,其Ⅱ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经过1年的随访发现贝拉西普并不能使肝移植受者获益。鉴于此,移植免疫工作者普遍认为贝拉西普不适合应用于肝移植受者。之后,LaMattina等[48]发现,对于丙型病毒性肝炎合并围手术期肾功能不全的肝移植受者,应用贝拉西普比CNI类药物更能使受者获益。同时,Schwarz等[49]同样发现贝拉西普可以使肝移植受者获益。总体来说,对于肝移植受者,贝拉西普不失为一种对CNI类药物不耐受受者的理想选择。
至于贝拉西普在心脏移植、肺移植、胰腺移植、儿童器官移植领域的应用,目前尚停留于个案报道阶段,有待于多中心临床试验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进一步证实。
4 引起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元凶”
某些记忆性T细胞被认为可以不依赖于CD28受体而自行活化和增殖。如前所述,CD28受体是T细胞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第二信号之一。在人类刚出生时所有的T细胞均表达CD28受体;到了成人阶段,绝大多数的T细胞仍恒定地表达CD28受体,但有一些T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受慢性病毒感染、炎症等的刺激而失去CD28受体,成为CD28nullT细胞,而这些CD28nullT细胞的特点是多为记忆性T细胞,且可不依赖于CD28受体而自行活化增殖[50-52]。鉴于贝拉西普是针对共刺激分子CD28的免疫抑制剂,起初移植学者普遍认为CD28nullT细胞是导致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元凶”[53-55]。但令人意外的是,Mathews等[56]利用恒河猴同种异体肾移植模型,发现CD8+CD28+再次表达CD45RA的效应记忆性T细胞(terminally differentiated effector memory T cell reexpressing CD45RA,TEMRA)是导致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可能原因,而并非CD8+CD28nullT细胞。不久,Cortes-Cerisuelo等[57]又进一步通过分析应用贝拉西普的肾移植受者的免疫状态发现,发生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受者术前存在更多的CD28+效应记忆性T细胞(effector memory T cell,TEM)和TEMRA,而这些CD28+TEM和CD28+TEMRA可以分泌更多的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一种T细胞活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细胞因子,进而导致肾移植术后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发生,而这一发现也进一步明确了引起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可能“元凶”。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CD4+CD57+PD-1-T细胞在发生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受者中明显增高,并通过分析其增殖、活化等功能,判断其很可能也是引起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危险细胞群[58]。但至于究竟以上哪一群记忆性T细胞是造成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主要原因,还有待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除了以上记忆性T细胞,鉴于CD4+T细胞的高度异质性,还有学者比较了贝拉西普对辅助性T细胞(helper T cell,Th)1和Th17的抑制作用,并发现贝拉西普能很好地抑制Th1,但对Th17的抑制作用欠佳,并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Th17可能也是引起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原因之一[59-60]。同时,也有学者发现贝拉西普通过抑制CD28受体,从而影响了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而这也可能是导致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原因之一[61-62]。
总之,这些高度可疑的引起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细胞群,让我们在术前能更精准地选择适合应用贝拉西普的受者,并能预测贝拉西普耐药性排斥反应的发生。同时,也驱使我们去寻找新的共刺激及共抑制分子靶点,来联合或取代贝拉西普用于排斥反应的治疗,为广大移植受者提供新的希望。
5 展 望
诚然,贝拉西普的问世已经为无数移植受者带来了较为满意的疗效,并弥补了CNI类药物对肾功能保护方面的不足。但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高仍严重限制了其广泛的临床应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刺激阻滞剂为广大移植免疫工作者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共刺激阻滞剂作为特异性抑制T细胞活化的免疫抑制剂,凭借其更好的肾脏保护作用和更低的不良反应正逐渐被广大移植受者所接受并使用;同时更激励器官移植工作者去寻找新的共刺激或共抑制分子靶点,从而为更多的移植受者提供更加优化的免疫抑制方案,来达到降低排斥反应发生的目的,延长移植受者的生存期并改善其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