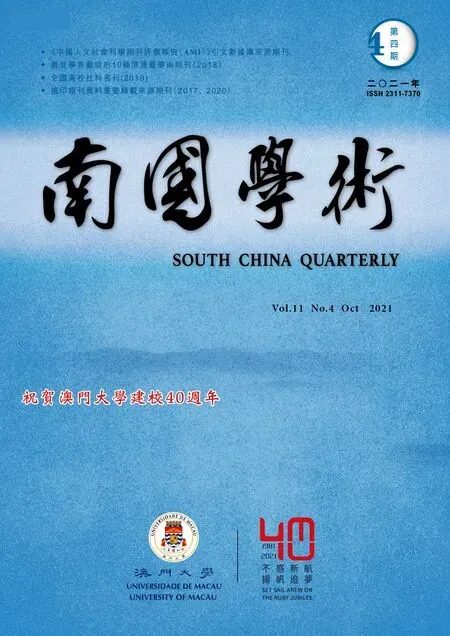三皇五帝的文化
黃開國
[關鍵詞]三皇 五帝 文化
三皇五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远古時代”。由於歷史的起點也是文化的起點,因此,三皇五帝文化作爲中國文化的基始,當今許多觀念都可以從中找到影子。當然,儘管三皇五帝在諸多古籍中有所論及,但多缺乏可信的文物佐證,並且異說紛呈,所以,後世不可能對他們作出完全準確的說明,衹能運用反溯的方法,即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進程,可從春秋以來中國人相傳不息的文化觀念來追溯歷史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文化。這些歷史文化印迹,是通過一代代中國人潛移默化的傳承,被逐漸固化爲中國文化的基本觀念,而成爲中國文化發展基因的。
一 重視道德的理念
中國古代文化最重名號,名號中最有政治意義、文化意義的莫過於諡號,被視爲對其一生功過的蓋棺論定。《白虎通》引用的《禮記》有《謚法》篇,《世本》的《秦嘉謨輯補本》《雷學淇校輯本》也有《諡法》篇,《逸周書· 諡法解》有周公製諡之說。根據王國維等人的研究,諡法形成於周恭王、周懿王之時,而皇帝的名號、三皇五帝名号都出於戰國之後,皆帶有諡號的性質。
《白虎通· 號· 皇帝之號》說:“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春秋文耀鉤》說:三皇“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曰皇”;又說:“皇者,含弘履中,開陰佈綱……指天畫地,神化潛通。”《帝王世纪》載:“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古人惟天爲大,故在這些涉及“皇”的名號解釋中,無一不是從天的高度來界定皇的道德,並由天引申出“美大”“神化”等品性,以說明皇的道德是至高無上、完美無缺的天德,而且達到神化的境界。《風俗通義· 三皇》對此作了最集中的說明:“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佈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可以說,皇的名號最根本的含義就在於具有與天媲美的道德。正是這種德性,三皇纔能處處合於道德,神化萬物,光輝不可度量。
《世本》關於帝的諡號的規定是:“德象天地曰帝。”①宋衷註、秦嘉謨 等輯:《世本八種· 秦嘉謨輯補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第285頁。這一說法最早可追溯到孔子,《論語· 泰伯》載孔子語:“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就是稱譽堯的德行以天爲法。而堯爲五帝之一,所以,這也可以視爲對五帝德行的說明。《白虎通· 號· 皇帝之號》正是這樣說的:“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並引《禮記· 謚法》:“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在稱王。”但今本《禮記》與《大戴禮記》皆無《諡法》,而衹是在《逸周書》的《諡法解》有十分類似的說法:“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白虎通》所引《諡法》很可能出於《逸周書》。《易緯坤靈圖》的說法最爲精審:“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不僅指出了帝的屬性是德配天地,而且進一步點明了德配天地的要義在於不以公權謀私利。無論是象、合、配,都是表示帝的德行可與天地媲美。司馬遷在《史記· 太史公自序》說:“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以五帝的道德皆爲法天則地的最高德行。“皇”“帝”的名號雖異,但在具有與天相配的最高德行方面完全一致。
道家的莊子也有相近的說法。《莊子· 天道》說:“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下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莊子所說的無爲的帝王,皆指三代以前的古帝王,如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等,儘管都是清靜、恬淡、無爲的聖王,帶有道家色彩,但也明確說到他們具有以天地、道德爲宗,德行配天地的特性。特別是“帝王之德配天地”一語,如果不是出自《莊子》的明文,人們一定會認爲出自某個儒學家所言。這也說明,儒道有對立爭論,也有契合處。皇帝是道德的至高人格,具有與天地相配的德行,乃是儒道共同的觀念。而從天的高度來讚美五帝的至德,是三皇五帝的文化印迹在後人思想中的再現。
皇帝的這種最高的德行,《淮南子》相關篇章稱爲“至德”。《覽冥訓》說:“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俶真訓》說:“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遇唐、虞之時。”這兩段話一段講伏羲、女媧將至德遺留後世,一段講堯、舜的時代是至德之世,都是以三皇五帝爲至德的說明。這種至德,常常被稱爲聖德。例如,說伏羲得名在於“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①〔唐〕孔穎達:“尚書序”,《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2),上冊,第113頁。,堯“聖德之遠著”②《尚書正義· 堯典》,收入《十三經註疏》,上冊,第118頁。,甚至直接說黃帝“有聖德”③《竹書紀年》(上海: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卷上。、神農“有聖德”④〔宋〕張杲:《醫說》(上海: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卷1。,等等。“聖德”與“至德”詞語不同,意義卻是相通的,但“聖德”更能表明皇帝的德性至高無上,而成爲後來儒學的常用詞。所以,自漢以來,以“聖”來稱譽三皇五帝的德性就流行於學界。
在三皇五帝的德性中,後人最推崇仁與孝。郭店楚簡的《唐虞之道》說:“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禪而不傳,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賢仁聖者如此。身窮不貪,沒而弗利,窮仁矣。……六帝興於古,咸由此也。”六帝具體爲誰,文中沒有明說,但可以肯定主要是指堯舜爲代表的三皇五帝。《唐虞之道》的中心是稱頌堯舜的禪讓,而禪讓之所以被稱頌,是因爲它是一種最高的仁德,能夠實行禪讓的帝王都是具有仁德的聖王。這裏的“仁之至”“窮仁”之說,都是說明堯舜爲代表的三皇五帝具有最高的仁德。《史記· 五帝本紀》講堯“其仁如天”,《諡法》以舜的諡號“仁聖盛明”可爲旁證。《新書· 修政語上》:“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大戴禮記· 五帝德》《史記· 五帝本紀》講帝嚳都用“仁而威”一詞,邵雍有“三皇同仁而異化”⑤〔宋〕邵雍:《皇極經世》,收入《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23册,第423b頁。之說。從這些追述中可見,三皇五帝都被視爲具有最高仁德的聖王。但在《尚書》的《堯典》《舜典》中,還沒有“仁”觀念的出現,堯舜是三皇五帝中最後的人物,他們之前的帝王更不可能有“仁”觀念。“仁”觀念出現在春秋時期,作爲最根本的道德觀念是由孔子所確立的,後人以仁德爲三皇五帝最重要的德性,雖然查無實據,但這一說法,卻是對三皇五帝是孔子思想淵源的追認,是中國文化延續性的有力說明。
“孝”爲三皇五帝另一重要的德行,集中體現在舜的大孝形象上。在《尚書· 堯典》以及先秦西漢的《孟子》《中庸》《大戴禮記》《史記》等許多著作中,都有舜孝順父母的傳說。當堯向四嶽徵詢繼承人時,四嶽一致推薦舜,理由就在舜的大孝:“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⑥《尚書正義· 舜典》,收入《十三經註疏》,上冊,第123頁。面對頑囂桀驁的父母弟弟,舜卻能以孝悌而帶來全家的和諧。《禮記·五帝德》借孔子之口說:“舜之少也,惡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舜不僅在青年時代就以孝行名滿天下,更爲可貴的是他的孝行不是一時,而是自始至終,從無懈怠。孟子還認爲,大孝是舜能夠成功治理天下的根本:“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⑦《孟子註疏· 離婁上》,收入《十三經註疏》,下冊,第2723頁。後來形成的“二十四孝”,也以舜排列首位。舜被譽爲聖人、成爲帝,皆源於大孝的大德。而唯有孝的大德,纔能夠受命於天,成爲人民真正擁戴的聖王。
人類社會自出現以來,血緣關係就一直是最重要的社會關係。處理血緣聯繫的人際關係,成爲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倫常道德的所有觀念,皆由此而產生。人類之初,其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族群的繁衍。族群繁衍的維繫,需要人們一代一代的延續不絕。爲保證族群的代代相傳,而形成了維繫這些血緣關係的倫常觀念。作爲維繫父輩與後代聯繫的孝觀念,無疑是最早出現也是最根本的觀念。通過舜所集中表現出來的孝道,《尚書》等以大孝對舜帝的稱頌,說明孝觀念是中國文化最早形成的倫常觀念,而不能僅僅視爲東夷部落獨有的①孟祥才:《齊魯思想文化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第25頁。,應是當時各部族至少是多數部族持有的觀念。由於舜的大孝不過是三皇五帝重德的集中表現,所以,《呂氏春秋·孝行》說:“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三皇五帝都是孝德的踐行者,也是他們能夠取得政治成功的根本保障。這種對孝的極端推崇所反映出的對血緣關係的極度重視,是中國遠古社會能夠不斷發展的最重要文化根基。
二 民爲 中心的理念
三皇五帝不僅是道德的最高表率,也是爲民建功立業、抵禦大災大難、勤勞付出的偉大英雄。從戰國開始的各種著作,如《世本》《管子》《尸子》《逸周書》《呂氏春秋》《風俗通》《帝王世紀》《古史考》《拾遺記》以及各種緯書在論及三皇五帝時,無不將他們看作是爲民建功立業的英雄人物。從用於民生的大到房屋、車船、紡車,小到衣、服、甑、竈、鼎、碗、杯、盆、罐、甕等,用於生產的鏟、錛、犁、鑿等,到用於戰爭的弓、箭、刀、劍、矛、盾等各種武器,用於音樂的鐘、瑟、簫、簧等各類樂器,以及精神文化的八卦、文字、圖書、數學、音樂等,舉凡有關人類生存的方方面面,無不出自三皇五帝或是他們領導下的臣屬,其中最著名的如燧人對火的發明,伏羲的畫八卦、馴服牲畜,神農對農業、醫藥的發明等,最爲後人所稱道。黃帝的各種發明尤爲顯赫,被康有爲稱爲“萬王民功之魁”②康有爲:《康有爲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集,第70頁。。1886年,康有爲著《民功篇》,搜羅各種經史子集的著述,甚至讖緯道教的著作,對從伏羲到大禹以來歷代帝王的各種發明創造做了詳盡的說明。他以《民功篇》作爲篇名,就是取義於三皇五帝爲代表的古帝王爲人民立下了豐功偉績。
從中國考古學來看,三皇五帝主要處於新石器時代的父系氏族社會的歷史階段,有的還處於舊石器時代末期的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從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相關出土文物可知,這個時期衹有石製的斧、刀、鏟、錛、犁、鑿、紡輪等生產工具,以及甑、竈、鼎、碗、杯、盆、罐、甕等各種日用陶器,這與當時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是相應的。處於這個歷史階段的中華先民,面對強大自然的寒暑風霜、地震洪水等災難,以及野獸的侵害等,各種發明創造對維護人類生存發展具有緊迫而重大的意義。正是這些偉大的創造發明,爲中國人的生存發展建立了物質與精神的保障。三皇五帝被後世尊爲聖王,就在於他們都是爲民謀福的英雄,是爲民創立物質財富、抵禦災害的偉人。
中國古代最重祭祀,而各種祭祀對象不是爲民立功的英雄,就是爲民抵禦災難、勤勞付出的英雄。《國語· 魯語上》說:
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在《國語》成書的年代,雖然還沒有三皇五帝的說法,但敍及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就是後來的五帝;西漢之後,烈山氏炎帝與神農合一,成爲三皇之一,所以,這一段祭祀所講的對象主要就是後來所說的三皇五帝爲代表的古帝王。而三皇五帝之所以被民衆一直祭祀,就在於他們能夠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這段話也表明,中國遠古的祭祀,並不完全是巫術的神靈崇拜,而是必須有功於國人的生存發展。《禮記· 祭法》有一段關於“聖王之制祭祀”的論述,對這一觀念有更詳細的說明。可見,這一觀念在先秦絕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流行的。
從這一觀念可以看出,人們對三皇五帝崇敬,最根本的原因在以民爲中心。《論語· 雍也》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子還說:“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①《論語註疏· 憲問》,收入《十三經註疏》,下冊,第2514頁。在孔子眼裏,使百姓安居樂業是聖王的最高境界,衹有做到博施於民纔能夠配稱聖王。孔子在論述堯、舜、禹的禪讓時認爲,他们三人重在“民、食、喪、祭”②《論語註疏· 堯曰》,收入《十三經註疏》,下冊,第2535頁。,民被排在第一位。陸賈敍三皇五帝,總是以天下人民開始,再敍述三皇五帝的偉大功績,如敍神農:“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敍黃帝:“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③〔漢〕陸賈:《新語· 道基》(北京:中華書局,1954),第1頁。這種敍述格式表明,人民的需求是三皇五帝建功立業的出發點,滿足他们的需求是三皇五帝爲政的目的。其他古籍敍及三皇五帝時,也常常以人民爲說,如《禮記· 五帝德》載孔子說黃帝:“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史記· 五帝本紀》說帝嚳“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帝堯“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三皇五帝之所以能夠成爲遠古人民崇拜的領袖,就在於他們都是爲民謀福利的大英雄。這一以民爲中心的三皇五帝崇拜,不僅是後來中國文化“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的最古老根源,而且也是中國文化沒有成爲宗教爲主導的人文文化的重要根基。
在世界各國的石器時代及其稍後一段時間,都有所謂的英雄崇拜,但西方的英雄崇拜缺乏以人民爲出發點與目的的精神,所以,導致了神學佔據統治地位的中世紀。而中國三皇五帝崇拜中的以民爲中心的精神,則引導中國從春秋時期開始就步入以人爲中心的發展大道。
三 禪讓的尊賢理念
孔子論“大同”“小康”,與他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夏商周以來的“小康”是家天下,堯舜的“大同”是天下爲公。而大同的天下爲公的制度保障,就是“選賢與能”,由賢人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政權的轉移實行禪讓制。所謂禪讓,是指在位帝王通過和平的方式將權力轉讓給經過考驗的賢人的王權過渡制度。這在《尚書· 堯典》中有相關的記載。
對於《堯典》是否可信?蘇秉琦有一段話可作爲參考:
《堯典》係後人追述,難免有記不準確而把作者當時的某些情況附麗增錦進去的地方,但也不會是向壁虛構。衹要看看龍山時代已有很大的城(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城內面積就達20多萬平方米),就知當時一定有了城鄉的分化,有了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兩槨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貴族,製銅、製玉和蛋殼黑陶等當時的高技術產業很可能有工官管理。①蘇秉琦:“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史學史研究》3(1991):9。
堯舜的時代還沒有文字發明,現存《堯典》衹能出於後人追記,但結合考古成果,《尚書》關於堯舜時代的追敍,並非“向壁虛構”,而是某些歷史印迹的再現。具体到堯舜的禪讓說,徐中舒指出:“堯、舜、禹的禪讓傳說,實際就是依據唐、虞、夏的部落聯盟時代的歷史而傳播下來的。”②徐中舒:《先秦史論稿》(成都:巴蜀書社,1992),第29頁。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也認爲,禪讓制反映的是部落聯盟之民主選舉制度。禪讓不是無中生有,而是中國遠古社會確實存在的權力更替的制度。這一制度,與財產共有、還沒有階級和國家的社會發展狀況是相應的。
堯舜禪讓不僅在《尚書· 堯典》《禮記· 禮運》中有記敍,在《論語· 堯曰》中也有明確記載:“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墨子· 尚賢上》也記述道:“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儒墨爲春秋末期顯學,皆有禪讓之說,說明禪讓非一家之言。而春秋是與遠古最接近的時代,對遠古歷史的敍說可信度高於後來的文獻。
在戰國文獻中,除儒墨之外,道、法各派的論著中也有禪讓說。在出土竹簡中,尤以儒家的論說最多。這集中見於郭店楚簡的《唐虞之道》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容成氏》《子羔》三篇文獻。《唐虞之道》開篇即稱:“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禪而不傳,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賢仁聖者如此。……故唐虞之道,禪也。”“堯舜之行,愛親尊賢。愛親故孝,尊賢故禪。孝之施,愛天下之民。禪之傳,世亡隱德。孝,仁之冕也。禪,義之至也。六帝興於古,皆由此也。”“禪也者,上德授賢之謂也。上德則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賢則民舉效而化乎道。不禪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容成氏》說:“(尊)盧氏、赫胃氏、喬結氏、倉頗氏、軒轅氏、神農氏、椲鳦氏、壚蹕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子羔》載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與善相授也,故能治天下,平萬邦,使無有小大,使皆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吾聞夫舜其幼也,敏以學詩……堯之取舜也,從諸草茅之中,與之言禮,說博……而和。故夫舜之德其誠賢也,由諸畎畝之中而使君天下而稱。”③裘錫圭:“談談上博簡《子羔》篇的簡序”,朱淵清、廖名春 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第8—9頁。這表明,禪讓制是戰國時儒家最爲讚頌的政治制度。在戰國儒家看來,禪讓不僅是堯舜實行的制度,也是古代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頊、帝嚳等帝王通行的制度。禪讓的特點是與賢不與子,核心本質在於尊賢。而賢的標準衹有一個,就是與天地媲美的德行,而不在身份血緣。衹要具有最高的德行,即使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也可以成爲人民擁護的君王。著名的堯舜禪讓,就是因爲舜的大孝聞名天下,而得以從草茅畎畝的民間直接接替堯的帝位。禪讓制得到儒家的極端推崇,被認爲是一種利於天下而不謀一己的美好制度,是使天下人民獲得幸福的根本保障。
戰國禪讓學說的這些理念,顯然是針對夏商周以來的“家天下”所帶來的政治弊端而發。自夏代以來,父傳子的家天下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在權力集中於一人的政治語境下,很難保證天子一定是賢人。歷史已經證明,歷代王朝除了開國的君主外,後來繼任的君王極少賢明者,絕大多數不是庸才就是驕奢淫逸的殘暴巨魁,他們衹知道無底綫地享樂腐化,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正是爲了矯正現實政治的這一弊端,所以,戰國的儒家借三皇五帝以尊賢爲內在精神的禪讓制,呼喚時代對賢人的尊重,希望賢人政治能夠在現實中得以實現。儘管這一呼喚在古代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實現,但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藉堯舜禪讓呼籲賢人政治,是三皇五帝對中國文化的重要影響之一。
四 神人相分的理念
三皇五帝時出現民神異業之說,表現出神人相分的理念,這是古代天人哲學的肇端。在三皇五帝各種創造發明中,最具有哲學意義的莫過於伏羲畫八卦說。《周易· 繫辭下》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本自然,這個自然體現在中國文化中,不是獨立於人之外的物自體,而是與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相通的,與人生的價值追求息息相關。所以,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不衹是以天地爲觀察對象,同時帶有以天地精神爲人生價值的意義。
伏羲畫八卦,儘管缺乏可靠的依據,但在五帝時期,天人關係已經成爲社會最關注的問題卻是可信的史實,許多古籍中“絕地天通”的傳說就是證明。這一記載最早見於《尚書· 呂刑》:“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呂刑》的得名,是周穆王用呂侯之言,追敍夏禹贖刑之法,並佈告天下。全篇圍繞刑法爲說,反對蚩尤、苗民的五虐之刑,主張“敬五刑,成三德”,以德爲歸。《墨子·非攻下》《隨巢子》也有類似記載,都以九黎或蚩尤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而有重黎的“絕地天通”,但這些著作中都没有“絕地天通”具體含義的說明。
對“絕地天通”的詳細解說,見於《國語·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從《國語》的解釋可知,所謂“絕地天通”就是改變九黎破壞造成的“家爲巫史”的“民神雜糅”普遍迷信,而回到原先“民神異業”的天人相分狀態。這裏的“民神雜糅”與“民神異業”實際上說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狀況:一種是人人爲巫的全社會信神的原始迷信;另一種是人神分離的理性文明。依照社會發展的歷史順序,應是先有原始迷信,後有人神分離的出現。美國學者克雷默(S.N.Kramer, 1897—1990)說:“認爲天地相通,人與神的相聯繫曾成爲可能,後來天地纔隔離開,這樣的觀念在許多文化中屢屢看到。”①[美]塞· 諾· 克雷默:《世界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第365頁。《國語》的說法在時序上不合歷史的實際,而“家爲巫史”的原始迷信也不是所謂九黎亂德造成的,而是存在遠古中國各部落氏族的普遍現象。
如何理解“絕地天通”的含義,不少論著多從巫的視角來解釋。這有一定道理,因爲“絕地天通”不過是“民神異業”的實現,所要改變的則是“民神雜糅”,二者都涉及神,而古代巫以通神爲業。但是,“絕地天通”的所謂神,並不僅僅是指神靈,而是指人之外的自然。以自然爲神,是古人普遍的觀念。所以,“絕地天通”最大的文化意義是改變了人對自然(神)的原始迷信,社會不再通行“民神雜糅”,而是通過“民神異業”的神人之分開啓了人對自然的理性認識。
人與自然的關係,從遠古以來一直是人類認識的基本問題。這個基本問題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發生從迷信到理性的演進。古代以自然萬物皆有神,神不過是自然的異化。在遠古的初民那裏,民神混沌不分,隨着人的智力的發展以及社會實踐的逐步深入,人就會擺脫與自然的混沌不分而獨立開來。“絕地天通”實際上就是遠古中國人這一認識的變化,通過顓頊的傳說而表現出來。所以,“絕地天通”的神人分離觀念,實際上反映古代中國人在長期的農業生產發展中,對天地自然自覺認識的大飛躍。司馬遷在《史記· 曆書》中早有揭示:
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災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這裏講到顓頊命重黎云云,儘管無“絕地天通”之語,但很明顯主要是採自《國語》關於顓頊“絕地天通”的記敍。“絕地天通”的人神不雜,使人從完全屈服自然(神)變爲獨立於自然(神)之外的相對主體,這纔爲人們認識自然創造了前提條件。在遠古時代,農業生產狀況關係到社會存亡與興衰,所以,天文曆法成爲最重視的問題。神人相分帶來的最早發展也最發達的成果衹能是天文曆法,而“絕地天通”的最大成果與最早成果無疑是天文曆法的成就。所以,司馬遷在這段話中以“天之厤數”爲“王者所重”,可以說是對“絕地天通”文化意義最深刻的說明。
“絕地天通”記載於顓頊時,是有原因的。根據相關文獻與考古材料,中國古代各處都有農業活動的遺迹,到顓頊時代,農業生產活動已有相当大的發展。但農業收成的好壞取決於兩個重要因素,即天時與地宜。爲了處理好這兩個問題,就萌生出專門的職業,重黎就是這方面的職官。顓頊以前的人們沒有“絕地天通”的發生,與那時人們還沒有发展到能够自覺認識天地有直接關係,顓頊時因農業發展引起對天地認識的進步,而有重黎“絕地天通”的出現。古代曆法中所謂《顓頊曆》,未必出自顓頊時或顓頊之手,但依託顓頊這一現象的背後,說明顓頊時中國人對天地的認識確有巨大的飛躍,至少是一較爲可信的歷史印迹。正是在有了“絕地天通”的“民神異業”、神人相分,纔可出現對認識自然的天文曆法等科學成果,與仰觀俯察而形成的八卦等觀念及其相關的人文學說。
綜上所述,重視道德、民爲中心、尊重賢才、神人相分這四個理念,構成了三皇五帝文化最重要的內容。這些理念通過春秋時期的文化傳承,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然,由於古人視三皇五帝爲聖王,文獻中敍三皇五帝常常多溢美之詞。但是,如果離開這些溢美記載,那就無法研究三皇五帝。所以,本文從四個方面說明三皇五帝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相互聯繫,衹能是探索性質的討論,相信它對認識中國文化的延續性還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