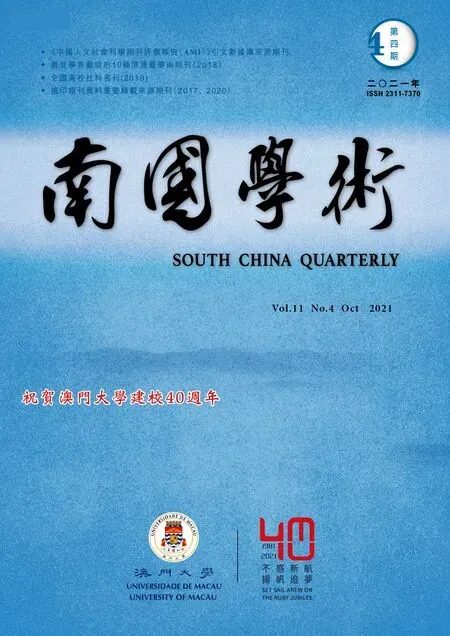讀者解放:從文本閱讀到文本能力的轉向
盧德平
[關鍵詞]開放文本 文本能力 讀者解放 意義
自文字産生之後,語言又增加了書寫方式,不僅從口語交流的情景性中獨立出來,成爲對生活規則的記載,而且所形成的文本形態,成爲了思想的載體,以更高的知識容量,獲得神聖化的評價;同時,創作和閱讀的價值與困難,都促成了書寫文本的神聖化。在現當代,隨着對主體性的高揚,“讓我們的思想尋求明晰性,讓我們的表達具有邏輯性,讓我們的討論更具說服力的精神力量”①江怡:“卷首語”,《中國分析哲學(2012)》(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第2頁。,使得讀者解放,重新規定讀者、作者、文本三者的關係,成爲時代的命題。讀者的解放,意味着破除文本神聖化,形成符合時代意義創新需要的文本能力。由此,反思和批判順從文本規則,以理解文本爲主要閱讀任務的閱讀傳統,就成爲革新閱讀和讀者解放的目標。
一 “開放文本”的悖論
讀者解放,需要重新審視文本與讀者的關係。“解放”不是對文本的破壞性革命,而是要聚焦文本如何向讀者開放,讀者如何走進文本並走出文本、返回自我的問題。文本向讀者開放多少——是無條件的絕對開放,還是有制約的相對開放?艾柯(U.Eco,1932—2016)提出的“文本開放性封閉”“文本封閉性開放”②U.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問題,反映了圍繞文本形成的作者與讀者之間糾葛不清的關係。作者可以通過元語言手段,對文本閱讀設置一些引導性規範,或交由讀者研讀、發現文本迷宮的編織紋路。但是,文本脫稿於作者之後,就進入到流通領域,如何開放——是開放性封閉,還是封閉性開放,主導權已經從作者移位到讀者——是讀者的閱讀條件、閱讀目的、閱讀能力在對作品開放程度加以分類。走進文本,走出文本,並且返回自我、移步社會,其節奏和幅度與讀者的個體化差異存在着因果聯繫。這些因素,使得閱讀與文本在對應關係上發生齟齬。在文本的開放性上,産生了究竟是文本問題還是讀者問題或者是二者關係問題的困惑。
儘管從作者脫稿後,文本的作者已是讀者的想象而非經驗意義上的舉證,但是,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存在着天平向兩端傾斜的偏向:一端是以作者爲重心,對文本如何理解和解釋,取決於作者的權威性規定,甚至這種規定被納入文本的構成規則;一端是以讀者爲重心,強調讀者理解和解釋的自由,甚至提倡需要對作者進行解構,宣佈“作者已死”③8-10.。這裏出現的問題是,文本的控制,其合理性取決於作者還是讀者(因爲,對文本的控制,既包括作者對文本規則的設置,也包括讀者對文本規則的遵循或挑戰,以及讀者將現有文本解構爲自己所用等方面)?處置文本,是爲了與作者的意向實現統一,還是爲了與讀者自己的文本資源實現連接,從而擴容閱讀的興趣?這些問題其實是老問題,之所以重新提出來,旨在從文本能力的角度提出“閱讀社會人”概念,將圍繞文本問題的爭論引向一個離開文本、走向社會的方向。
可以看出,艾柯提出的“開放文本”命題,是一個悖論性問題。“開放”屬於受規則限制、有路徑准入的文本“封閉”策略:“作爲結構性策略的組成部分,開放文本勾畫的是面向模範讀者的‘封閉’計劃。”④R.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London:Fontana Press, 1977), 142-148, 156-158.U.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10, 8.而“封閉”的文本則又屬於面向所有可能解讀的絕對開放:“向所有可能的解釋無節制‘開放’的文本屬於封閉文本。”⑤R.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London:Fontana Press, 1977), 142-148, 156-158.U.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10, 8.這個悖論的提出,涉及作品與文本的區分問題⑥8-10.,也涉及作品與文本的再生產問題,還涉及讀者與作者的角色關係問題。
如果區分開作品與文本,劃分出作品的再生産與文本的再生産,揭示出讀者對作品理解的有限自由性與對文本解釋的無限自由性,那麽,就可以消除這一悖論。去除悖論之後,“開放的文本”命題,將有助於指向這樣的方向:文本是文化的表徵、思想的容器、生活的承載,而文本活動,促成了文本鏈的構成,解釋了知識生産和傳播的基本規律。從這一意義上說,文本的開放,意味着社會全體成員都擁有文本可及性,而非單純服務於作者所規定的“模範讀者”①U.Eco,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5-88.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7-11.。
對於文本的閱讀,“並不意味着要從根本上回溯過去,而是要介入當下已言說的內容”②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Continuum, 2004), 393.。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事實上隨着閱讀的開啓,就轉換爲文本與讀者的關係。那麽,“模範讀者”的合理性,就無法從作者那裏尋找,而衹能從文本中定位。也就是說,“模範讀者”並非作者所能規定,對於“模範讀者”角色的認定,並非作者的特權,而是交由從作品分離出來的文本本身。不可否認,文本藉助“連貫性”這一基本特性③M.A.K.Halliday & R.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Longman Group Ltd, 1976), 1-30.,分化出文本的規則體系和符號細節,調適着讀者的閱讀過程,使之在以下條件下成爲文本的僕從:讀者一定要閱讀出作者的“命意”,一定要對文本的特性進行複製,一定要看懂文本提供的各種符號細節,並自願承受其“觸媒”的影響。④R.Barthes, Image Music Text.Trans, 79-124.讀者在成爲文本僕從之後,演變爲作者的僕從,“模範讀者”成爲現實。這是“模範讀者”命題成立的一個悲劇性條件。
文本的命運在於流通。這一特徵說明,任何一個讀者閱讀一部文本,都擁有先前或同步流動着的文本資源,構成其閱讀的基礎和坐標。從這一意義上說,文本置身於社會時間和空間中,完成知識和文化的傳遞,離不開讀者。文本的作者以讀者爲前提。因爲存在着閱讀文本的需求,文本的生產纔成爲對意義的生產,纔成爲讀者走進文本、穿越文本、體驗意義的供給。
文本的閱讀指向了讀者的創造。與其選擇對文本規則和細節的遵循,自覺歸順作者的“命意”,成爲文本的模範考生(極端化的“模範讀者”),不如結合自己的需求,進行爲我所用的閱讀。讀者的閱讀選擇,以及對閱讀自由的追求,從魯迅對《紅樓夢》的解釋中可以獲得印證。《紅樓夢》作者在“模範讀者”前提下設定的“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⑤〔清〕曹雪芹、高鶚:《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第2頁。的主導性“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⑥魯迅:“《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8卷,第179頁。
文本需要閱讀,正是在閱讀之中,讀者把握到呈現於文本之中的作者的內在經驗。文本的理解就是對作者經驗的想象性揣摩,但文本理解是手段而非目的。在理解的同時,讀者不斷走出文本,産生與其自我興趣的關聯,形成“道學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等方面的多元聯繫。這種關聯,是社會角色影響閱讀角色的證明。正如伽達默爾(H-G.Gadamer,1900—2002)所揭示的,文本閱讀存在理解和解釋兩個維度⑦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Continuum, 2004), 393.。讀者的社會角色必然要求其結合自身的旨趣,在理解文本的基礎上,通過創新性解釋,走出文本,從讀者狀態恢復其社會人的身份。《紅樓夢》規定出一種主導性“命意”,無論“道學家”“才子”,還是“革命家”“流言家”,在文本閱讀過程中,都能理解這一主導性“命意”,也都臨時充當起“模範讀者”的角色。但“道學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都不願成爲《紅樓夢》文本的僕從,而是要擔當解釋的主人,從閱讀《紅樓夢》出發,走向各自的社會角色。這裏,文本的理解依附於文本的解釋,文本的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獲得實現。
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存在着責任歸屬,也正因爲承擔着責任,作者纔獲得文本權威的桂冠。但是,這種因生產責任而獲得的桂冠,無法通過把讀者限定於對文本的理解而犧牲其文本解釋的自主性。作者對文本負有生產責任,而讀者似乎無需承擔閱讀的責任。在文本閱讀和傳播的過程中,或者說,當文本一旦離開作者的筆端,進入流通,作者的權威性桂冠就已經褪色爲文本的署名。署名的符號性在於標記出作品的終結和文本的開始。署名的存在本身,僅僅是作品桂冠的末梢性閃爍,以及對文本、讀者行使理解霸權的最終機會。
例如,羅蘭· 巴特(R.Barthes,1915—1980)對文本與作品分離以及作者之死問題的論時代問題論爭述,就預測到文本在理解和解釋上的分化,以及告別作品、進入社會的意義:
作品是物質片段,佔有圖書的空間(如圖書館),文本則是方法論的場域……作品是可以看到的(例如,在書店、圖書目錄、考試大綱裏),而文本則屬於一個證明的過程,它依據一定的規則(或反對一定的規則)而言說。作品是拿在手中的,而文本則盛放在語言之中,衹存在於話語的運行過程(或毋寧說文本成其爲文本的理由就在文本自身)。文本不是對作品的肢解,相反作品則是文本的想象性末梢。或者說,文本衹能在生産活動中體驗到。文本不會停留(如書架上),其構成成分屬於穿越性運動。①R.Barthes, Image Music Text.Trans, 156-157.
隨着文本從作品中脫胎而出,文本由過程轉爲結果②M.A.K.Halliday & R.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12.。文本從作者的主觀表達轉變爲一種客觀的標記,文本成爲標記性符號,而不再是作者的表達性手段。③E.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 Vol 1, 183-186.也就是說,作者退出了文本。文本的作者名,成爲客觀文本符號與作者主觀表達之間的連接。其符號性提示,使得讀者與作者産生了想象性關係。文本的意義,不單純是作者的意向或“命意”,而是讀者在想象的基礎上實施的添加。作者與讀者的關係,逐步演變爲文本與文本、讀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互文性”概念④J.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anguage and Ar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其價值就在於說明文本閱讀、流通之後産生了新的文本間、讀者間的意義。
由於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邊界,因此,在文本理解上,作者構造的文本,以文本的內在“連貫性”以及遍佈文本的催化性符號,吸引讀者走進文本,使之獲得閱讀的陶醉。但是,文本無法一直扣留讀者,在讀者的遵循中蕩漾“文本的快樂”,並滿足作者對文本的霸權,因爲讀者通過對文本的解釋,開啓了離開文本的旅程,其回歸社會的動力以及社會對文本的要求,是任何文本結構、任何文本作者所無法阻攔的。當然,可以通過忠實於文本的考試制度,來維持文本的傳統和作者的神聖;但讀者對文本的學習和超越,成爲現代社會知識創新的主題,以實踐價值超越着對文本的閱讀和理解,並清晰化作者與讀者的界限,實現了作者、文本、讀者的社會分工。
所謂“模範讀者”,其範疇指向的是將文本意義定位於作者意向,而非社會構成意義上的“理想型”⑤36-68.M.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6-22.讀者。倘若賦予“模範讀者”以理解與解釋的雙重職能,將忠實性文本理解與自主性解釋結合起來,那麽“模範讀者”的內涵將獲得社會意義。這樣重新界定“模範讀者”的含義,可以使艾柯提出的文本概念獲得時代的新生。這樣的內涵更新,解決了因設定理想的“模範讀者”而帶來的“開放文本”的悖論。
解決開放文本的悖論,意味着將文本的理解和解釋界定爲文本閱讀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側面。作者在文本中設置了規範性或引導性手段,說明作者爲文本的理解提供了路徑,體現了文本規則性的開放特徵,即艾柯所說的針對“模範讀者”的“開放中的封閉”。同時,艾柯所說的另一種“封閉中的開放”,則屬於這樣的情況:讀者在文本的理解上完全任性,對文本形成了“六經註我”式的解釋。既不考慮文本的題材類型,任意再生産,也不在閱讀上實現與作者的想象性連接。無論是“模範讀者”還是“六經註我式讀者”,在規則和自由的維度上都存在着絕對化的問題。因此,開放的文本應該滿足三個條件,這也是構建文本的社會、文化意義所必須遵循的步驟:(1)需要理解文本的主導性“命意”,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理解作者的符號設定。但這僅僅是文本接觸的初始狀態。(2)作者的“命意”不能成爲約束讀者解釋自由的控制性原則,文本內的各種符號設定不應成爲約束性指標。(3)面向文本能力的文本閱讀,必然要求文本的理解和解釋構成文本成立的充分條件。對文本理解的強調,僅僅是文本閱讀的必要條件,也是艾柯提出的“模範讀者”的落腳點。讀者携帶其閱讀經驗、知識背景,需要在走進文本之後走出文本、返回社會、加以解釋,這構成了文本閱讀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文本閱讀需要關聯到閱讀者的個人旨趣、知識擴容、社會行動等多個方面,纔能體現出文本閱讀的意義。
簡言之,當作者無法將讀者扣留於文本之內,當讀者的閱讀動機超越了文本本身,或者說,當讀者將文本的閱讀服務於自我的興趣或功用時,“模範讀者”命題就需要從作者對文本的立法轉向讀者對文本的實踐。文本實踐不僅僅是閱讀,而且包括知識的連接,以及包括從文本理解出發,與社會性自我關聯,對文本做出創造性的解釋。如果考慮不到這些問題,那麽,“模範讀者”或以此爲依據提出的“開放的封閉”“封閉的開放”等命題,就失去了經驗基礎,成爲單純的文本學術語。
二 文本開放與文本能力
文本牽涉到絕大部分社會活動的符號性再現,其功能恰恰在於以語言等符號手段再生產各種社會活動,並通過閱讀實現知識的傳播,獲得文本的公共化。無論共時的生產還是歷時的再生產,文本始終置於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之中。一方面,傳統文本的再生産,由於當下的閱讀,歷史的知識與當下的知識實現了匯通,使時間失去了延滯①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Continuum, 1975), 393-404.,歷時轉變爲共時;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的文本再生産,形成文本鏈,包裹於文字、語音以及電子等可傳播介質,獲得流通,從而解決了空間阻隔的問題。
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上看,讀者閱讀文本,其閱讀行動是走進文本與走出文本的結合,其閱讀過程承擔着理解與解釋的雙重任務。對於文本的理解,實質上是讀者走進文本、滯留於文本的過程。同時,對文本的解釋,則是讀者走出文本、回歸社會和文化的過程。讀者文本能力的形成不能脫離開這兩個過程。文本呈現於讀者,是結果。讀者走進文本,實現與文本的意義互動,同時走出文本、回歸社會,文本又是過程。讀者的文本實踐是文本能力的現實化,而文本能力又不單純是關於文本的知識。閱讀是活動,是依據規則的實踐。文本能力不是對文本知識的轉述,而是通過閱讀,在理解和解釋中完成對既有文本知識的吸納,與讀者已有知識匯通,從而形成新的文本,或超越原始文本,走向不同知識場域的互文。
文本的閱讀,是一種理解和解釋活動,而不是對原始文本規則的記憶。同時,文本的理解又不是讀者任性的“六經註我”式的發揮。形成和發展文本能力,需要開放的文本;而文本的開放性,就其合理性而言,涉及上文所提出的文本開放三條件。這三個條件,可以視爲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語言能力學說的借鑒②N.Chomsky,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4,,也可視爲對海姆斯(D.H.Hymes,1927—2009)交流能力理論的繼承③4-131.D.H.Hymes,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ciolinguistics.Selected Readings (London:Penguin, 1972), 269-293.。
喬姆斯基將語言能力限定於語法規則的知識,而語言表現是語言能力的自動生成,從而激發起對於語言能力“初始狀態”的探尋。④N.Chomsky,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4,生成出來的結果,即語言表現,距離語言能力的規則有偏差,體現出相對於穩定性規則的隨機性、偶發性。能力成爲完美的內核。與此不同的是,海姆斯強調了語言能力存在於交流過程,交流過程中的語言表現本身就隱藏着規則。在海姆斯看來,語言能力並非像喬姆斯基所說的需要與語言表現分離開來,而是相反,二者緊密結合,互爲條件。
受喬姆斯基和海姆斯的啓發,本文所說的文本能力,不是要向作者那裏尋求“初始狀態”,而是要立足於文本與讀者的關係,根植於讀者的閱讀過程,聚焦於讀者與文本的對話,從文本爲我所用的動機來分析文本的解釋過程,以及面向社會文化的互文遷移。同時,由於文本與作品分離,文本能力是基於文本結果的過程化能力,其關注的重點不是作者,而是讀者。需要說明的是,文本能力不同於言者對語言的生成能力,也不是關於交流主體的行動能力,而是需要轉向文本接受者即讀者的過程化實踐能力。
就文本的理解而言,文本能力一方面表現爲文本的閱讀可及性,另一方面又體現爲對文本內在統一性的把握。文本存在於語言之中,語言活動構成了文本符號的內涵。文本以語言的樣態呈現於讀者,走進文本,起始於對文本語言符號的解碼。然而,語言樣態依然是文本的外衣,閱讀從解碼語言符號開始,就是要去除語言外衣,把握文本意義。面對結果性文本,讀者對文本的可及,意味着讀者有能力從文本的語言符號去推斷文本的內涵。文本可及,反映了讀者對文本符號擁有信念。讀者認爲,可以從能夠閱讀並且熟悉的文本符號,去推斷那些非字面閱讀可知或不熟悉的文本內容。如果字面閱讀可知,那麽文本就衹是符號的外衣,而與內容無關。文本閱讀的價值在於新鮮,而非熟悉。文本的可及性能力,既包括讀者從熟悉的文本符號出發到達陌生的文本內容的過程,也包括讀者在進入文本之後,通過文本符號的各種組合關係,通向文本“命意”,提取知識元素,定位文本風格,形成自我連接的文本行動。其中,自我連接是文本閱讀走向社會實踐的節點。
文本行動是一種旅程。如果讀者穿越文本符號,到達文本的主導性“命意”,就會沉浸於文本,忘卻了自主性,那麽,“文本自足性”①M.Riffaterre, “The self-sufficient text”, Diacritics 3(1973):39-45.就成爲文本霸權的代名詞,降服了讀者。文本的開放,並非要通過對讀者持續的扣留來實現文本的吸引力,而是要將文本的內涵以通俗可及的語言表述出來,呈現於不同的層次,使讀者可以止步於第一層次,也可以從第二、第三層次返回其社會角色。不一口氣讀完就無法理解的文本,就屬於極端化“文本自足性”的負擔性文本。有助於文本能力發展的“文本自足性”,目的在於給讀者留下喘息的時間,就此止步“且聽下回分解”,但這並非段落、章節等文本處置手段可以簡單實現的。
文本能力落實於讀者,但並非與文本自身無關。文本的規則,是之於閱讀的規則,而非局限於文本構造的規則。對比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學說和海姆斯的交流能力理論,無論是“文本自足性”概念還是“文本開放性”概念,都體現出以文本爲中心的思路。即使考慮到讀者,這些概念也僅僅是以文本理解爲目的,其出發點是以對讀者的限制性閱讀來提高文本的完美準則性。
文本能力的形成,出發點不是要幫助作者創造文本,而是要幫助讀者理解和解釋文本。文本既已創制,作者無需幫助。從生產角度看,文本是結果,而非過程。但從閱讀角度看,文本是過程,而非結果。文本一旦從作者手中分離,離開了寫作,就進入了社會流通體系,一切交給了讀者。對於作者的任何文本學幫助,實質上就是對作者脫手文本的否定。對於理想文本規則的呼喚,就性質而言,是從文本向手稿的回歸,成爲一種文本編輯技術。相反,之於讀者的文本學,因服務於文本能力,而承擔了社會責任。從讀者出發,文本的規則在性質上轉變爲,針對讀者的閱讀、理解而形成文本的語法規則。文本規則的生產,不是由作者一人埋頭完成,而是需要在事實的作者與想象的讀者的對話中完成,並在事實的讀者與想象的作者的閱讀關係中加以驗證。
從這一角度說,韓禮德(M.A.K.Halliday,1925—2018)提出的“參照”(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連接”(conjunction)等文本規則②M.A.K.Halliday & R.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一方面服務於文本自身的“連貫性”需要,另一方面體現出對讀者閱讀需求的滿足。人稱代詞指代對象、話題、事件,旨在減少重複,降低文本的熟悉性,調動讀者的想象性連接。或者說,是在替代性指涉中,向讀者陳述着同一事物的不同視角。讀者在替代性指代中,獲得符號的啓示,理解了文本不是在重複製造,而是在提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說法。讀者在閱讀中,結合文本的語法策略,用自己的知識想象,尋求文本的陌生意義,客觀上實現了與文本語言的對接。文本的“省略”手段同樣體現了對讀者閱讀時間的考慮。其功能並不在於單純服從文本的結構需要,也不是爲了追求文本的句法平衡,而是隱含着讀者指向。“省略”的文本意義在於,重複且沒有新意的表述,將終止讀者對文本的旅行,是非連貫性文本形式驅趕了讀者,使文本賦予的意義無法通過讀者加以實現。
文本是賦予意義的符號,而讀者的閱讀則是實現意義。文本分離於作品,文本成爲作者的痕迹。如果作者掙扎於文本,則使賦予文本意義成为再現作者的意圖。文本提供的一些看似供讀者窺視的元語言性質的符號,實質是作者對作品霸權的殘留。文本能力是要形成“智慧的讀者”,幫助讀者建立“批評話語分析”能力①N.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London:Routledge, 2010).。對於文本的批評能力是文本能力的倫理維度,也是文本通向道德、訴諸閱讀的標準,是區分好文本與壞文本的依據。
“智慧的讀者”需要通過理解,與文本的意義實現統一。文本的符號在於賦予意義,讀者藉助自己的文本資源,參照流通於社會的文本鏈,與自己的意義儲備形成橋接。文本構成於語言,閱讀是語言活動,文本與讀者的橋接是語言的對接,文本的“連貫性”②M.A.K.Halliday & R.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1-18.提供了對接的結構保障。文本的“連貫性”需要文本提供各種文本手段,如指涉、替代、省略等,加以維護。連貫的文本,是爲了保證文本意義獲得邏輯性的設置。相應的文本手段,成爲文本的語法符號,供讀者索引和遵循。讀者與文本的意義對接,走在規則的軌道上。一部文本,正是由於這些可遵循、可索引的規則,纔成爲多數讀者而非怪異看客的閱讀文本。索引文本規則是文本能力的重要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讀者通過閱讀所要實現的與文本意義的統一,並非爲了對文本意義進行考古學的復原,不是爲了刻板複製隱身作者的意義,而是爲了從事一種有價值的閱讀活動。文本的語言符號依據社會公約,其能指和所指的關聯取決於包括讀者在內的社會成員。就文本字面而言,在文本與讀者之間實現意義的統一,是先決的;同時,讀者在閱讀之前,虽然通過其他文本形成一定的文本能力,但相對於所要閱讀的文本,仍然存在一定的距離。这就解釋了文本閱讀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建立意義的統一,形成閱讀的文本與讀者文本資源庫的橋接,需要讀者做出調適,形成適應性文本能力。
文本能力的複雜構成,對文本的開放性提出了更高標準。文本的開放性,無法通過禁止閱讀流通中的文本加以遏制,也無法通過更改文本的字面秩序來阻止讀者對文本意義的探尋。文本的開放性規則,及其提供的文本連貫性手段,區別開“文本”與“非文本”③Y.M.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London:I.B.Tauris & Co.Ltd, 1990), 218-243.,屬於文本構造的基礎條件。文本的開放程度,取決於讀者的文本能力。也就是說,對於文本的開放性,需要以文本能力的形成和發展爲前提。文本能力的倫理條件,以及對文本規則的索引性,對文本意義的統一性連接,連接過程中的適應性等等,都是不可迴避的問題。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四原則:
其一,文本能力從文本的可及性開始,涉及對文本所提供規則的掌握能力。但是,對文本規則的掌握,是爲了“文本爲我所用”,而非以掌握和理解文本規則爲目標。
其二,文本能力不是文本的製作能力,而是文本的接受、解釋、創新能力。因此,創作論對作者的倚重,文本論對文本結構的倚重,都難以活化文本,而活化文本的方法是閱讀。文本提供的閱讀路徑,以及相應的文本手段,服務於讀者的文本能力。
其三,文本能力簡單說是一種符號能力,是關於活化文本的符號能力。將文本能力視爲符號能力,旨在界定文本的符號性和意義指向性。文本閱讀就是憑藉文本符號邁向文本意義的過程。
其四,文本能力是索引文本規則、連接讀者需求、從文本意義向社會意義關聯的過程。文本是結果,但閱讀文本是過程。文本能力是從文本結果出發,面向社會,指向讀者的意義資源發展的能力。考察文本符號之於讀者産生的言語行爲效果①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可以將文本能力清晰化爲語用能力。
三 當代文本連接的轉向
文本能力的基礎是語言能力,對語言能力的超越是探討文本能力的價值所在。在新世紀,隨着全球化的深化,通訊技術日新月異,語言活動也發生着深刻變化。以書面閱讀爲基本特徵的傳統文本能力範疇,不僅難以解釋單語碼書面文本與現代多模態電子文本之間的關係,也難以涵蓋二者。故此,克拉姆希(Claire J.Kramsch)從應用語言學界提出了“符號能力”概念②C.Kramsch & A.Whiteside, “Language ecology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towards a theory of symbolic competence”, Applied Linguistics 4(2008):645-671.,布隆瑪特(J.Blommaert,1961—2021)等從社會語言學界提出“超級多樣性”概念③J.Blommaert, B.Rampton, “Language and superdiversity”, Language and Superdiversity, Rampton (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 2016), 21-48.,這就牽涉到當代文本能力的範式轉換問題。
傳統的單語碼文本是思維的邏輯性轉寫,其中包含的知識價值已經獲得充分的論證。而與此相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語、多模態文本正在成爲“新常態”。無論是面對面的口頭交流,還是單語碼文本閱讀,都在銳減。一些社會群體,不斷用多語、多模態交流替代面對面語言交流;一些社會場域,傳統的文本體裁,正在被難以名曰的文本形態所替代,“體裁期待”④趙毅衡:“文本如何引導解釋:一個符號學分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14):121—125。M.Bakhtin,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6), 60-102.的文本規律普遍受到忽視。
當代的多模態電子文本,究竟應看作是從傳統文本出發進行的延伸,還是應看作傳統文本的終結?是不是意味着語言本身發生了質的變化?或者說,意味着正在敲響單語碼文本傳統範式的喪鐘?或者,是不是單語碼文本仍將是文本的主導範式,傳統意義上的文本能力仍將是時代的主題,是對多語碼、多模態文本傾向的糾偏?這是面向當代文本能力建設需要回答的問題。
就表現形態而言,可以歸結於文本的連接問題。但是,這種文本連接與依據文本內在意義的互文連接,並不完全一致。可以看到,作爲“初級體裁”的日常會話,與作爲“次級體裁”的具體社會場域的行業性語言交流⑤,在社交軟件文本上形成了重叠、混合。不同體裁的語言交流相對於社會空間的不同語境條件,在社交軟件文本上被壓縮爲同一語境下的共用狀態。通過當代通信技術,虛擬的空間對現實的空間實施了積極的作用,改變了空間之於語言交流的關係。置身於虛擬交流空間的電子文本,不是對現實空間中的語言交流活動的刻板模擬,而是通過多模態手段,如表情包、錄音留言等非文字方式,編寫着可供即時交流的文本,口語交流與書面語交流產生重叠。在二者重叠的基礎上,不同於口語交流、書面語交流在語音和文字上的區分性,當代社交軟件文本連接口語文本、書面語文本,並且藉助技術條件以及其他非語言符號手段形成了第三種文本。這第三種文本屬於相對於口語文本、書面語文本的時代文本範疇。
全球化背景下的超級多樣性語言條件,呼喚了第三種文本的出現。超級多樣性不僅表現爲人口流動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表現爲超級多樣性人群對第三種文本的需求。就現代互聯網聯絡的任何一個國家、地區、城市而言,無論是流動人口還是常住人口,都在呼喚語言交流方式的超級多樣性。第三種文本是對時代的超級多樣性條件的符號化表現,其文本的視聽不同於傳統文字文本的閱讀,而是口頭交際、書面閱讀、面部表情、情緒態度的綜合體,需要訴諸多模態的手段纔能滿足視聽的需求。
傳統文字文本側重命題信息的傳遞,去除了口頭交際中的情境性、情緒性、生動性,獲得了抽象性,從而形成了書面閱讀所造就的交際模式。當然,這種抽象性是對語言交流中共性的提煉,利於要點的把握以及核心信息的傳播和接受。但是,爲了滿足語言交流的豐富性、生動性、情境性,需要從文本閱讀轉移到面對面的口語交流。
書面語與口語的關係,並不單純在於前者是後者的轉錄,而在於書面語删除了口語的情景性、生動性,以及口語和其他非語詞符號並置的可能性,成爲一種淨化過的獨立文本。這種文本從功能上看,衹有通過閱讀行爲纔能實現。閱讀所帶來的作者、文本、讀者的關係問題,與閱讀過程中讀者對文本情景的想象性恢復,對作者製作文本意向性的揣摩,都存在着深層次的關聯。生活於口語交流世界的讀者,對交流者的面部表情、身體的姿態、語音發送過程中的情感細節,都有着切實的把握,在分享語言交流意義的同時,領悟到對方的性格、心理、情緒等多個方面。讀者對作者的揣摩,很大程度上是處於口語交流世界的讀者,在向書面文本轉移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實施着口語文本和書面文本的匯通。
同時,對於傳統書面文本閱讀過程體現的互文關係,不僅在於書面文本與其他書面文本之間的引用、借鑒,而且在於閱讀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啓動着自身擁有的書面文本知識資源,以及來自日常生活的“初級體裁”對話資源,使得書面文本在閱讀過程中呈現出很多被遮蔽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可以看出,在通信技術的推動下,第三種文本的出現具有書面文本與口頭文本匯通的規律性基礎;同時,也反映了“初級體裁”日常會話覆蓋語言交流全域,“次級體裁”交流是“初級體裁”的分支性産物這一規律。
超級多樣性條件下的第三種文本,表現爲社交軟件文本交流,集成了口語交流中的非語詞多模態符號和書面文字,並以即時通訊方式,實施着對日常會話交流的模擬性語言實踐。但是,這種文本又不同於日常會話交流,它以視覺而非聽覺,與閱讀者發生着不同於口語交流的書面性關聯。同時,它也不像書面文本那樣排除掉口語交流的情景性、生動性,而是將口語交流中不可分節的面部表情、情感態度等符號加以分節性處理,開發出表情包、繪文字等技術工具,爲當代超級多樣性條件下的社會人提供了雜糅口語與書面、匯通思想與情感的交流手段,构建了以第三種文本爲代表的交流宇宙。從人際交流的角度看,第三種文本交流宇宙是集成了“初級體裁”“次級體裁”交流風格,並穿越二者,由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人實施的語言交流。
不僅如此,超級多樣性條件下的第三種文本,還出現在現實的空間中。跨國人口流動,使得同一現實空間中匯聚了不同區域、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群,其間的語言交流突破了以往那種以地理位置、交流密度形成的“言語共同體”概念,多語交流成爲同一社會空間中的現實。這種多語交流,往往又不是以學會“他者”的語言爲前提,而是以代碼轉換,以不成句、不合語法、頻繁借用詞彙的“跨語言”方式①O.Garcia & Li Wei, Translanguaging:Languag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2014).,實施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語言交流活動,達成着相互理解和共享。
這種“跨語言”的口語交流,呈現出類似社交軟件文本的雜糅性特徵。它不僅表現爲不同語言之間的臨時性、隨意性轉換,以及對同一語句實施的異質語碼配置,而且表現爲非語詞多模態符號對口頭語言的超載性滲透。這種交流形態,顛覆了句法的統一性條件。同時,超級多樣性條件下的雜糅性語言交流形態,往往藉助社交軟件文本補充了口語交流的不足。就第三種文本的類型而言,多語條件下的“跨語言”交流口頭文本與社交軟件文本形成了共振關係,爲全球化背景下的流動人口提供了口頭、書面以及兩者相互補充的文本格局。
從當代文本格局的變化態勢判斷,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1895—1975)所提出的“初級體裁”語言交流方式,即日常生活會話,已經轉變爲當代社會的多語碼、多模態、口語書面交叉、時空高度壓縮的第三種文本的“初級體裁”,同樣在功能上覆蓋着絕大多數社會生活場域。因此,當代意義上的文本能力,除了要掌握第一種口語文本、第二種書面文本之外,尚需掌握第三種文本。問題在於,是否在掌握了第三種文本之後,就可以弱化甚至拋棄口頭文本和書面文本呢?
在歷史的延續之中,可能會出現事件的斷裂,但歷史的延續性本身是通過話語實現的①M.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Routledge, 1972).,而文本則是福柯(M.Foucault,1926—1984)“話語”的同義詞。在疏浚人類知識長河的過程中,文本履行了主要功能。無論是“初級體裁”的口語文本,還是通過文字轉化而成的書面文本,抑或當代超級多樣性背景下的第三種文本,都是知識積累、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撇開前一種文本,就不可能出現第二種文本,也不可能出現第三種文本。後續的文本並非是對前一類文本的替換,而是功能的增補,是對新的社會條件下增加的社會交流功能的回應。舊文本承載的文本功能仍在延續,新文本採取一些技術手段打破了時空的制約,強化了這種功能的接受方式,但這並不等於可以否定既有的文本功能,更談不上可以拋棄第一文本、第二文本。但是,也要看到,隨着文本類型的增加,人們一方面獲得了文本利用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文本負擔。面對文本負擔,人們在獲得更多文本選擇自由的同時,産生了簡化口語交流、減少書面閱讀、單純利用社交軟件開展交流的惰性。滿足人的發展的豐富性而非簡化性的文本能力,就是要幫助人形成縱向貫穿文本歷史、橫向選擇多種文本的能力和優勢。
如同書面文本對口語文本形成了補充,成爲獨立類型的文本,承載了人類創造的知識,當代社交軟件文本、多語“跨語言”文本則是適應全球化人口流動背景,應對超級多樣性交流條件的産物。文本能力,不是局限於讀者的概念,而是要密切聯繫到依託於社會發展條件的社會人。本文提出文本能力在於讀者走出文本、返回社會的命題,就是要說明,社會人不僅要在社會發展的大潮中處理文本、利用文本,而且要學會文本。文本能力是一種社會學習。文本能力不是從文本外化出來,單純落實於文本的接受者,而是要考慮到,社會人在利用文本的同時,在創造着文本,創造着以文本承載的知識。承載的方式,不僅包括傳統的書面文本,也包括口頭文本,還包括集成了書面文本和口語文本的第三種超級多樣性文本。回首看,超級多樣性文本本身不僅是知識的産品,也是服務於當代社會人的一種交流方式。時代爲文本能力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