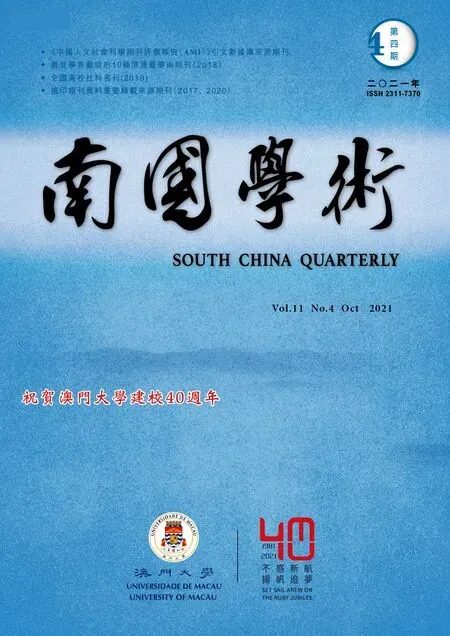從以“名”言道到“體”道
——《老子》對“名”“言”之域的拓展
貢華南
[關鍵詞]《老子》 名 言 正言 體道
任何言說都有限度,或者說,在特定歷史時期,哲學總有“說不得”階段。春秋時期,廣義的形名思潮興起,以分限清晰、確定爲特徵的“形名”佔據主導地位。以“形名”說是形式地說,用以辨別事物更清晰、更方便。但是,對於無形無分者,“形名”卻顯得無能爲力。對無形無分而說不得者,《老子》積極地嘗試用“體名”(即“聲名”“觸”“味名”等),以及“希言”“建言”“信言”等肯定性的“正言”來“說”。“體名”“正言”開啓了道說的新境域,並促成了中國思想的“體道”傳統。《老子》的說不得者之說,對檢討中國近現代以來佔主導地位的“邏輯地說”具有重要意義,對當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探索也具有啓示價值。
一 名與言
“名”的本義是命名,即依據物的獨特性給予其名,以區別他物。“名”體現的是物的獨特性,對他物而言,此特徵即爲可辨別的個性。有了可辨別的個性(“名”),物就從幽冥之處現身。對人來說也是如此,人的“名”是個人的獨特特徵。人有了“名”,也就可從衆人之中凸顯出來,爲人知曉。《說文解字》對“名”的解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強調“名”的聽覺(聲音)基礎,這當然是漢代人的觀念。但是,讓有名者從幽冥處(不相見)凸顯出來,人得以相見,這則是先秦時期“名”的古義。
“言”既需用“名”,也可用“字”。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女子十五歲行及笄禮或許嫁)時,師友爲其取字,供家人之外的人稱呼,以示尊敬。“字”中包含着言說者的態度。《老子》所推崇的“道”就是“字”。例如,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王弼註:“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有形纔有其名,大道本身沒有確定的形,人們無法對其命名,而衹能“字”①《韓非子·解老》混“字”與“名”爲一,認爲“道”既然無形可“名”,也就不可“字”。他堅持“强爲之字”,即“字”與“名”一樣都是勉强爲之。。王弼這個說法深明古義。依此,“道”是人們對那“獨立而不改”的生生之母的讚賞性稱謂(“稱可”)。
《老子》對“言”有豐富的論說。隨着言說者目的、對象的不同,“言”呈現出不同的內涵。比如,以“言”自我表達(看法、情感、態度),或以帶有力量(如權力、具有感染力的情感等)的“言”命令或勸導(他人)以達到某種效果,等等。聖人對天下人(百姓)“言”,“言”就是命令②按照J.L.奧斯汀的理論,語言不僅具有對世界的描述功能,同時也是人類的一種行動方式。這種行動會對聽者産生某些影響,奧斯汀稱之爲“話語施效行爲”〔J.L.奧斯汀:《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哈佛大學威廉· 詹姆斯講座》(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第96頁〕。《老子》無疑也注意到了“名”“言”對人的情感、思想、行動的影響力。;知者對芸芸衆生“言”,“言”就帶有勸導意味;得道者之“言”,“言”是淡而無味的道言。據此看,傳統註家將第二章“聖人處不言之教”之“言”解釋爲“政令”不無道理。“政令”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即將在上者的目的、意志、慾望施加於在下者,以此影響、改變他人的思想、態度、行爲,達到屈人以就己的目的。對《老子》來說,百姓素樸之性是完美的,對素樸之性的增益或減損都是對其性的傷害。因此,不以政令擾民(“不言”)是最好的選擇。同時,發佈政令的“言者”因其期待特定效果,自我會隨着政令而逐物在外,自身素樸之性也會相應迷失,故曰“多言數窮”①《老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五章。。《老子》斷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②《老子》,第五十六章。無疑有其道理。
“不言”是拒絕向他人發佈政令,即拒絕將自己的目的、意志、慾望施加於他人。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老子》拒絕一切形式的“言”。得道者要救人、救物,同樣需要以“言”達“道”,以“道”之“言”引人從道等等。簡言之,“言”於《老子》有其必要性。
二 “見而名”與“無名”
春秋時期,以齊桓公、管仲爲代表的形名事功思潮興起。他們爲追求效率、功利,在“名實”關係上主張“循名責實”,並以客觀、確定的“形”作爲“實”的本質,遂將“形”“名”貫通,“名形”關係由此成爲“名實”關係的新形態。以“形”作爲“名”的根據,被視爲理所當然。例如,《管子· 心術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又如,《孫臏兵法· 奇正》:“有形之徒,莫不可名……分定則有形矣,形定則有名[矣]。”所謂“形”,乃視覺要素,以“形”爲根據的“名”乃視覺化、形式性語詞。狹義的“形”指刑律,廣義則指一般的形式化規定。其特徵是,有分限(“分”)、確定(“定”),客觀,清楚明白,容易把握。這是形名事功思潮將“名”“形”相互貫通的原因。“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既指明了“名”的根據,也透露了“名”的邊界——有“形”。這種命名方式可以簡單稱之爲“見而名”。
形名事功思潮的氾濫是《老子》思想展開的重要背景。不過,《老子》對此思潮充滿疑慮。有形之徒皆可名,對於無形者怎麽辦呢?《老子》最感興趣的“道”恰恰無形又無名,道所創生的人、物亦不以“形”爲本質。“名”有兩種功能:摹寫與規範。確定且有分限的形名無法摹寫混成之“道”,若硬以形名規範“道”,則道被納入分限之中而失去自身。人們可以形名摹寫萬物,以獲取關於對象的確定性知識。不過,規範與摹寫同時同在,以形名規範萬物,素樸的萬物也就被塑造成分化了的存在者。進而,人們根據形名來控制、聚集萬物——把萬物從其自在的天地中拔出,轉變爲“爲我之物”。以形名摹寫與規範人,使人成爲心智分化、魂魄分離的俗人。約言之,以形名言道,則道隱無名;以形名言萬物,則萬物遠離素樸而淪落爲器;以形名言人,人亦失去其素樸之性。因此,被形名事功思潮視爲根基的“形”“名”自然被《老子》所拒斥。《老子》第一章對“名”表達出明確的拒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一般解爲“言說”,即當時流行的視覺—形名言說方式。③貢華南:“中國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與認知”,《中國社會科學》3(2016):42—61。“道”非確定性、外在性、形式性、客觀性所能描述或把握。道恒無名,確定性、外在性、形式性、客觀性之名僅僅是“有名”的具體形態。對視覺性的“名”的反思,這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對“名”的第一次自覺。
“可名”之“名”即用視覺性方式去命名,命名的結果就是對象被賦予“形名”。在《老子》看來,這樣的“(形)名”並不是“常名”。也就是說,視覺性的“名”並不配“道”之“名”。基於此,《老子》屢將“道”與“無名”關聯。例如,第三十二章“道常無名”、第四十一章“道隱無名”等。由此似乎可以說,“道”與“名”無涉。但是,在《老子》第二十一章中,“道”又實有其“名”:“道之爲物,唯恍唯惚。……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對於這裏的“名”,各註家分歧較大。蔣錫昌認爲:“此‘其’字爲上文‘道’之代名詞。‘名’非空名,乃指其所以名之爲道之功用而言。道名不去,猶言道之功用不絕。……故道之一名,可謂常在不去也。”④蔣錫昌:《老子校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第148頁。照此說,這裏的“名”是道之“名”,但並未指出是何種“名”。張松如坐實其說,將“其名不去”解釋爲“它的功德不能廢除”⑤張松如:《老子說解》(濟南:齊魯書社,1998),第123頁。。李零將“其名”釋爲“萬物之名”,並指出“名”是“形名”。但是,萬物之形名何以能夠“自古及今”?李零又說:“從現在往古代追,大家都知道它的名,這個總名就是道。萬物有形,我們怎麽知道萬物是怎麽來的?是靠‘衆父’給它們起的名。‘衆父’也是道的別名。”①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83、82頁。這裏“其名”又被解釋成了“道”之“名”。爲什麽註家會有此含混?根本原因是對《老子》中“名”的理解僅限於“形名”,而“形名”又不足以解釋《老子》的命名問題。
打破將“名”等同於“形名”的陳詞,將“名”由“形名”擴展開,那麽,“其名不去”就不會如此繚繞了。這裏的“名”確實不是“空名”,但也不是“形名”,而是“聲名”,即蔣錫昌所說的“道的功用”、張松如所說的“道的功德”。以“道的功用不窮”“道的功德不能廢除”等解釋“其名不去”就能夠說得通了。
三 “不見而名”與“強爲 之名”
“形名”既不能傳達“道”及“道”的思想系統,《老子》衹能尋求“形名”之外的“名”來“言”。“有名”之“名”當然不是“形名”。此“名”究竟是“何名”?《老子》第二十五章有所提示,即強爲之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強爲之名”可以理解爲《老子》在通常命名方法——以形作爲命名的唯一根據之外,探求新的命名方法之嘗試。通常意義上的“大”與空間相關,但這裏的“大”既涉及空間的延展,也涉及時間的綿延。具體說,“大”指無限的延展與綿延,它與“逝”“遠”“反”的內在關聯就表明了這一點。聯繫道的“混成”“寂寥”“獨立不改”等特性看,“大”首先不是“形名”,天地間無“形”與之對應。它的內涵“混成”“寂寥”“獨立不改”“逝”“遠”“反”等,也非“形”所能“定”。嚴格說,這裏的“大”主要表達的是無形的“體”或“質”②《莊子· 則陽》進一步區分了形式的“大”與質料的“大”:“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孟子· 盡心下》也有類似區分:“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爲“質”,“光輝”爲“文”(形),“大”是兩者之統一。。故《老子》說“吾不知其名”。“強爲之名”的“名”以“體”或“質”爲根據,參照“形名”,不妨稱之爲“體名”。學者們不理解此命名法,無法理解“強爲之名”含義,便對此“名”作文章。比如,高亨認爲,這裏的“名”應是“容”,所謂“名、容形近,且涉上文而訛”。③高亨:《老子正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第43頁。事實上,帛書本、竹簡本都是“強爲之名”而不是“強爲之容”。這說明,以“容”解“名”缺乏根據。劉笑敢則認爲,爲什麽衹能勉強名之曰大,是因爲,“‘道’是宇宙萬物根本之‘大’,是超出我們個體、乃至全人類的認知能力的。老子對它的認識是模糊的”④劉笑敢:《老子古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295頁。。將“強爲之名”歸結爲人類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甚至斷言老子對道的認識是模糊的,這種說法不能令人信服。這恰恰表明,“形—名”命名法在世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在第四十七章,《老子》直接否定了形名——以“形”爲“名”之根據的觀念,提出“不見而名”: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帛書乙、河上公、王弼皆作“不見而名”,《韓非子· 喻老》作“不見而明”。“不見而名”意思是說,不依靠視覺對“形”來命名。由於韓非自覺繼承齊桓公、管仲開創的形名事功思潮,在根底上與《老子》異趣,當然不會讚同《老子》提出的新命名方式“不見而名”。他遵從形名之說,支持“見而名”。因此可以理解,在引用中,韓非子有意無意地將“不見而名”改爲了“不見而明”。
“不見而名”這一新的命名方式同樣見於《老子》其他章。例如,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帛書本爲‘微’);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帛書本爲‘夷’)。”道不可辨別,故不可以視覺性的“形”爲根據來命名。《老子》在這裏屢屢以“名曰”的方式展示了新的命名方式——“不見而名”。“夷”又見於第五十三章:“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作爲道的基本特徵,“夷”通常被訓解爲“平”,指的是消除一切凸顯之態。“希”又見於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第四十一章“大音希聲”,指的是聲音(及內涵)未分化(成可辨別的宮、商、角、徵、羽等)之態。“微”則見於第十五章“微妙玄通”,指的是幽杳不顯之態。這三個概念與“寂”“寥”一樣,都具有消除具體分化(“形”)並導入混成之體的功能①如同“無形”“無聲”“無味”等概念,一方面具有否定“形”“聲”“味”的意思,另一方面還具有精神指引功能,即通過具體的“無”而導向“無”本身。。常人的官覺對應的是對象分化之態,“夷”“希”“微”三名都表達未分化的整全(“混而爲一”),因此,常人官覺無法辨別。未分化的整全無“形”而有“體”(非“形體”之“體”,而是“實有”之“體”),以“夷”“希”“微”言,即是以“體名”言。顯然,“夷”“希”“微”之“名”依據的不是可見之形,甚至不是可區分的感性特徵。
那麽,《老子》以什麽作爲命名根據呢?第三十四章透露出一些信息:“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慾,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小”“大”並不是依據可把握的客觀形式(比如,空間延展)來命名,而依據的是實質性內涵——“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慾”與“萬物歸焉而不爲主”。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二“名”爲同一對象——“道”。或者說,同一對象,儘管其“形”爲“一”,但依據其所呈現出的不同內涵可以給出不同的“名”。通過內涵的轉換,原本表達空間延展的“大”“小”等“形名”,也被轉換成表達內在特質的“體名”。
與對“大”“小”命名類似的還有“多”“少”等語詞。《老子》用“多”“少”來表達人的生存狀況。例如,第二十二章:“少則得,多則惑。”人得“一”(“少”)以生,本性完美;不斷以名利(“多”)增益其身,則本性被移易。第十二章“五色”“五音”“五味”之“五”,既標誌着對原本處於獨立之“一”狀態之物被人爲聚集,也標誌着人心智分化至於紛亂自傷地步(“目盲”“耳聾”“口爽”)。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一”“二”“三”則分別指存在的整全、存在的初步分化與存在的進一步分化。可以看出,原本用來表達數量的“多”“少”“一”“二”“三”“五”等都被轉換成表達存在的內在情態之“體名”。
“道”以“生”爲其基本特性,其所生者亦秉此特性,如“一”“二”“三”皆以“生”爲其基本特徵。“道”之所生的“有”“無”等語詞也如此。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是“道”之“有”,“無”是“道”之“無”。“有”“無”以創生(“生”)爲基本特性。“無”可生“有”,“有”可生“萬物”。簡單說,富有“創生”之性的“有”“無”都不是純粹的形式規定,不是“形名”,而是無形式的、內含創生之性的“體名”。撇開道,“有”“無”成爲空頭無據之“有”“無”,亦成寂滅之“有”“無”。“以無爲本”,以“無”自立門戶,多流於“空無”,而非道之“無”。
與將“形名”轉換成“體名”相對應,《老子》還使用了視覺語詞之外的大量聽覺語詞、味覺語詞、觸覺語詞來通達“道”之“體”。
由於《老子》中的“道”是本原性的存在法則與存在方式,而本原性表現爲無限性,但此無限性並不是與天地人物無涉、純粹客觀的無限性。“道”是天地人物的存在法則與存在方式,人可“法道”②《老子》,第二十五章。,依照“道”生存,並展示出對天地萬物相應的態度。而“道”可“法”,表明“道”並不拒絕人的接近;或者說,“道”可以爲人知,也可以爲人得。知“道”、得“道”的方式決定了表達“道”的方式。
以第十章爲例:“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其中,“載營魄抱一”之“營魄”即魂魄——精神與形體。“一”通常解釋爲道。“抱”是將事物收於懷中,使之緊貼於身,唯恐其失。抱“道”,即將道向自身拉近,緊貼,人與道盡可能親密交融。第二十二章的“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內涵同此。“無離”即超越、避免內在精神的分化、分離、分裂。“專氣致柔”之“專”,帛書乙本寫作“摶”。“摶氣”“專氣”意義有差別。“專氣”是使氣專一、不分散;“摶氣”即使分散的氣重新聚成一個整體。“致柔”即到達柔弱、柔和的狀態或境界。“玄覽”即“玄鑒”,這裏指心靈。“疵”是雜滓,即摻雜在素樸之性中的多餘者。鏡子上有灰塵,會影響鏡子的功能;心靈上有灰塵、污垢,也會影響人們看世界。“滌除”是清洗、去除污垢,即把大道之外的知、慾種種雜念清除掉。清除摻雜在本性中的污垢纔能保持自身之純粹、精神清明。可以看出,得道需要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準備:身心之氣凝聚不分化(“專氣”),去除身心被摻雜的異質(“滌除玄覽”),並且始終讓道與人親密交融(“抱一”)。
人通過身心修煉而得“道”,同時也需要“守”的精神纔能使“道”不失去。第三十七章“侯王若能守之”的“之”與第五十二章“守其母”的“母”同指“道”。“守其母”之“守”,表達的也是自覺靠近、緊挨其母,惟恐其失之態。自覺靠近顯示出對對象的親近、認同、與之一體等義。因此,可以進一步引申爲守護、守衛。“母”帶着“子”,保護着“子”,爲“子”提供方向與歸宿;“子”遵照“母”的方向與原則展開自身,也就有了終極歸宿。夫物芸芸,逐物會失去自身之性,衹有守住大道,方可不爲物累。此謂“沒身不殆”。第十六章“守靜篤”、第二十八章“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則可視爲“守道”的具體表述。“守靜篤”,竹簡本爲“守中,篤也”。“中”或解爲“沖”,即“虛”。“守中”即“守沖”“守虛”。“雌”“黑”“辱”乃《老子》追求的生存姿態。作爲生存姿態,“雌”展示爲自身收攝、凝聚,不凸顯自身,不揚己抑人,以及謙讓、包容他人他物等義。“黑”對自己意味着停留在自身,對他人爲不顯露,不爲人矚目。自覺守“黑”,意味着自覺地停留在自身,不刺激他者。這樣,物我之間不會互相強加、互相損害,由是各自的本性得以保全,等等。
當然,對“道”還需要發自內心的認同與自覺的追隨,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①《老子》,第十四章。。首尾是有限者的品格,道無始無終,無首無尾,但修道之人可迎之、隨之。“迎”“隨”是兩種對道的態度與姿態。“迎”是主動敞開自身去接納,“隨”是自覺放棄自我去追隨。“迎之”“隨之”,道就會綿綿不絕地呈現。人不能用人爲化的感官去通達大道,不能用物性思維試圖把握道,而衹能用“迎”“隨”等情感態度、姿態對待、呈現道。“迎”“隨”的態度包含着高度肯定、虔誠相信、自覺認同之義。有了迎之、隨之的情感態度與姿態,人們纔有“得道”之可能。“執道”亦是“得道”之意。“執”是觸覺語詞,即親熱地、堅定地握拿。類似於《詩經· 邶風· 擊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之“執”,即親熱拉着,堅定不離。《老子》第三十五章“執大象”之“執”同此,引申爲自覺而堅定地與道契應、與道爲一。
“道”可“抱”、可“守”、可“執”,同時,也可“聞”。“聞”的意思是“聽進去”,即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聞道,會自覺而堅定地將“道”化到自己生命,並在生命展開過程中隨時踐行“道”。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能高度認同並隨時踐行“道”。“道”進入“中士”生命,但他們時信時疑,時而“存道”,時而“亡道”。對“下士”來說,他既不認同“道”,或有所聞,卻隨時拒斥、疏遠之。所以,在《老子》,“聞道”——聽進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相信、認同、踐行道,纔能使道與生命融而爲一。
“道”亦可“味”,如第六十三章“味無味”。聯繫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可知“無味”指“道”對人的意味,而“知道”“得道”的方式就是“味”。視覺活動(“見”)的展開,對象與人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但聽覺活動(“聞”)的展開,對象始與人有距離,終至距離消失。與視覺活動、聽覺活動不同的是,味覺活動(“味”)的展開,對象與人之間始終無距離。作爲通達“道”的具體方式,“味”包含着與“道”親密共在的情感態度與姿態。
道可抱、可守、可迎、可隨、可執、可聞、可味,人們通過這些方式知道、得道,進而抱道、法道、行道。基於抱、守、迎、隨、執、聞、味等方式所得之道,展現爲系列充滿“道味”的語詞,如“無”“有”“樸”“素”“弱”“柔”“雌”“清”“靜”“淡”“沖”“虛”“淵”“湛”“夷”“希”“微”“妙”“玄”等。這些語詞是對所抱、所守、所執、所聞、所味的表達,它們屬聽覺、觸覺、味覺,但卻與視覺無涉①不少學者根據《老子》第五十四章斷言視覺活動(“觀”)也是《老子》認知的基礎,但這裏的“觀”不同於第一章“觀其妙”之“觀”,也不同於第十六章“觀復”之“觀”。首先,“以身觀身”之“觀”是“知”的方式,而主要不是爲了欣賞。其次,這裏的“觀”不是“客觀”(無成見但有態度)之“觀”,而是帶着理想的尺度——素樸的身、家、國、天下——去衡量現實的身、家、國、天下。觀的結果無非兩種:合乎理想的尺度與不合乎理想的尺度,而這就是“知”。這樣的“天下”不可見(目光向外投射以知對象之實然)而可“觀”(所知是對象之應然)。所觀不是對象外在、客觀的“形”,主要是內在的素樸之質。值得注意的是,“道”不可見,《老子》也不說觀道。依照“以天下觀天下”句式,或可說,“以道觀道”。“觀道”的前提是“以道”,也就是知“道”。由此前提,也就不必再去“觀”。所以,對於“道”,純粹視覺是無法觸及的。。
從道的層面看,“(體)名”是必要的。道創生萬物,作爲個體存在(“一”)的萬物各有其“個”,各有其“德”。其“個”“德”獨立且獨特,讓其“個”“德”由幽冥處呈現出來需要“(體)名”來標識。換言之,“名”之於物的必要性在於:“名”標誌着道的創生,以及萬物之爲萬物的個體化的獨立之性(“德”)之確立。在此意義上,《老子》第一章纔會說“有名,萬物之母”。對於人群來說,一方面,有“名”是其生存的前提:知物之“名”,掌握物的特性可以使人辨別利害,以資其生;確定人之“名”,有助於維護人群秩序。因此,“名”不可無。另一方面,“名”又是人之製作,哪怕是“體名”,亦屬人爲。過分依賴“名”意味着遠離人、物素樸之性,也背離了“道”的精神。解決這種衝突的辦法有兩條:第一,製作“名”要有限度:“始製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②《老子》,第三十二章。對萬物來說,有了可辨別的“名”,也就從萬物之中被人挑揀出來,成爲“爲人之物”而失去素樸的自在性。對民來說,有“名”意味着在人群中有了確定的位置、位分,以及與位分對應的責任、義務。責任、義務的實質是強制性的規範,也就是命令(“令”)。有“名”則有“令”,“名”“令”滋長,人、物失真。因此,要隨時停止“製名”。第二,要不斷淡化“名”的屬人特性。“名”雖不可無,但卻不可以“名”爲天造地設之物而過分倚重。人不得已而製名,又不可以“名”自限,而應當以“無”爲根本。對於已經製作之“名”,不能熱衷於此,而要用“道”的精神淡化其對人與物的控制與命令(“令”)。
四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在《老子》看来,道無名,對道卻不能無言。言道不能以“形名”,衹能用“體名”。言道之言合道,卻淡乎其無味。
世俗之人以自我爲中心,而與他人、萬物对峙。世俗之言隨之在善惡、美惡、有無之間無端翻滾。世俗之言的實質是自己的目的、意志、慾望之溢出。言爲自身之所出,對於他人他物爲“外”。將一己之目的、意志、慾望施加於他人或萬物,一方面減損自身素樸之性而增益他人或萬物之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減損他人或萬物之性。於己,世俗之言意味着素樸多失,生機多出。生機多出則自身註定窮竭(“數窮”),故不能“多言”。天地之言亦然。飄風驟雨乃天地之言,“飄風終日”“驟雨終朝”爲“多言”。天地“希言”——“飄風不終日”“驟雨不終朝”,故能不窮。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希言”側重的是言者之“不能久”,也就是強調“言”對“言者”的意味——言爲自身之所出,所出者是對素樸之性的減損。“不言”側重的是“言”對他者之意味——施加而增益其性,也是對他者的傷害。“希言”“不言”皆“信言”,而非“無言”。
世人習慣物性思維,往往會以物性思維來思考“道”。但“道”與“物”不同,《老子》不斷申說此意,如第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道”與天地間的“物”不同類,故“道”與萬物皆不相似(“不肖”)。具體說,“物”有形、有色、有聲、有質,“道”無形、無色、無聲、無質。道以“無”的方式呈現,常人的官覺並不能觸及“無”,尤其是被世俗觀念改造過的官覺無法觸及“無”。道之“無”又非純粹的“虛無”。爲避免這一誤解,《老子》不斷嘗試用不同的“體名”來言“道”,如第二十一章:“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象”本來的含義是大象,後演變爲富有力度的生命體。相較於“形”,“象”以內在生命之體爲特徵。“物”的甲骨文意思是“牛”①《說文解字》:“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從牛。”王國維《釋物篇》進一步說:“物,本雜色牛之名。”〔《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8卷,第188頁。〕。“牛”與“象”一樣,其內涵指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存在。就形態說,“精”深藏不顯,不過,同樣以源源不絕的“生”爲其基本特性②“精”在古代思想中意蘊玄妙。《管子· 內業》說,“精”能“下生五穀,上爲列星”,其特質是能够“生”天地萬物。人之“精”也具有“生”的特性,如《黃帝內經· 素問· 金匱真言論》:“夫精者,生之本也。”“精”有時又被稱作“精氣”,如《周易· 繫辭上》“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黃帝內經· 素問· 古天真論》“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泄,陰陽和,故能有子”。“精氣”最大的功能就是“生”物、“生”人,儘管是以潜能形式存在。。較之“夷”“希”“微”之混整,“象”“物”“精”之“形”遞次弱化,直至消隱。它們皆以內在充盈的生機爲特徵,可謂“體名”。“象”“物”“精”都是道之創生,也都分有了道的創生品格。道就在“象”“物”“精”之中(而不在其“後”,或其“上”),由“象”“物”“精”也可知“道”之實有。與“夷”“希”“微”一樣,“象”“物”“精”拒絕了常人的官覺,但卻在修道者的真實體驗中呈現。
修道者以“道”爲“法”,唯道是從。“道”混全不分化,修道者亦混全爲一。第十五章“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即其成身、成德之態。“微妙玄通”拒絕明確、限定、有限、不通的狀態,既能“獨”(立)又能“通”。“微”“妙”“玄”“通”不是外在的、客觀的形式,而是內在深厚的生機與盎然的生命境界。因此,用形名無法言說它(“深不可識”)。《老子》進而用“豫”“猶”“儼”“渙”“敦”“曠”“混”等語詞描述得道境界,如第十五章:“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冬涉川”“畏四鄰”是敬小慎微之態,“客”指嚴整收斂之態,“冰之將釋”則是欲融未融之態,“清”是本性不被摻雜,最終則“生”機慢慢顯露。“豫”“猶”“儼”“渙”“敦”“曠”“混”等描述得道境界與姿態的語詞內含着不斷流動轉化之幾,它們皆非“形名”,而是“體名”。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③《老子》,第四十章。作爲“道”最直接的展示,“反”“弱”是理解“道”的關鍵。“反”既源源不斷地返回“道”。“道”與“俗”對立,“反”又有“反俗”之意。“弱”與“強”對立,指不炫示、不強加、不威脅他者。在《老子》中,“弱”與“柔”意義接近,有時二者連在一起用。
“柔”是一個觸覺性概念。“柔”是柔軟,指與他者接觸時展示出來的性質:觸之而避、而退、而隱。“柔者”以“虛”“無”姿態與他者接觸,接受、容納他者,自身卻不會爲所容納物而改變。能虛、能無、能容者纔能“柔”,因此,“柔”是一種精神品質與自覺追求的在世姿態,即第十章“專氣致柔”、第五十二章“守柔曰強”是也。對於“柔”的力量,第四十三章有充分的估量:“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是“柔”的極致,也就是“道”“無”精神之極致所展示出來的最強大的“柔”。“至柔”無所不包、無所不容,而物我皆能各遂其性。“至柔者”不會改變自身,恰恰可以最完整地保持自身。“馳騁”描述的是“至柔者”創生的展開無所阻礙之態。即使所遇爲“至堅者”,即隨時向他者示強、意圖改變他人他物者,至柔者亦無往不利。“天下之至堅”是堅的極致。對他者來說,“至堅”意味着攻擊、威脅、破壞、損害,但遇至柔者,則無所阻礙,無從攻擊、威脅、破壞、損害。以“柔”在世,自身始終保持“無”“虛”,也就保住了自身之“生機”。對萬物“柔”,亦可使萬物保持生機。因此,《老子》第七十六章用“柔弱”來刻畫“生”,用“堅強”來刻畫“死”:“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弱”通向生生不已這樣一條道路,而“堅強”表達的是失去活路或者說是沒有空間和前途、希望之路。
“柔”是“道”與得道者的展開方式,“淡”則是得道者在世的基本態度。《老子》第三十一章展示出對特定事物“兵”的態度:“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它有兩個功能:自衛與勝人。兩者都可能傷人,故老子認爲“兵”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不崇尚暴力,不追求暴力,亦不決絕拒斥暴力,而是採取恬淡的態度。“恬淡者”既不“溫熱”(熱衷於),也不“寒凉”(斷然拒絕)。對於以“爲腹不爲目”①《老子》,第十二章。爲待物自處基本原則的修道者來說,自足於內,無待於外,他們不僅對“兵”要“恬淡”,對世間萬物也同樣淡然處之。
“淡”也是道言的基本特徵:“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樂與餌”刺激人、吸引人,也傷害人。以刺激人的厚味多加於人,而致使人的味覺被移易、改變,此即“五味令人口爽”②《老子》,第十二章。。“道”聚集萬物,但不會刺激人的慾望。“道之出口”,以“淡”“無味”爲特徵。“淡”即“無味”,乃道言的基本特徵。味覺活動的基本特徵是物我距離之消弭,可使物我交融,但距離之消弭並不意味着彼此失去自身。對於《老子》來說,萬物的到來,我以柔待之,隱退自身而給萬物提供其自由展開的空間。雖爲零距離,卻能彼此包容——我不加於物,同時不爲物所加,物我各全其身。以道言言,善救人而無棄人,善救物而無棄物,可謂“善言”③《老子》,第二十七章。。對於無味——淡,《老子》第六十三章主張“味無味”,即自覺以味覺(這裏主要指精神性味覺)來品味無味——淡。
可以看出,這些基於聽覺、觸覺、味覺的“體名”都有相應的聽覺、觸覺、味覺經驗支撐,可謂是“經驗之談”。比如,“無”有“無爲”“無知”“無慾”等生命經驗支撐。“虛”有“致虛極”精神境界支持。作爲“道”之“用”的“弱”與生機直接體現的“柔”,以及作爲理想生命的“樸”“素”“清”“靜”“淡”,作爲得道直接體現的“微”“妙”“玄”“通”等語詞,無不以具體的“德”爲根據與表現方式。真實的生命經驗與精神境界賦予“道”系統中的這些語詞以真實而充盈的意義。
五 雖若反﹐實正言
唯道是從者清靜自正,獨立不改,不自生、不自見、不自是、不自戕、不自矜、不自貴,其言乃自身之自然涌現,此即“信言”。此“言”或涉及自身之外,但卻不會擾物生事,而是自覺呈露大道,以“道”主“言”,即第七十章“言有宗”是也。所“言”皆實有,皆可見於行,即第八章所謂“言善信”也。善信之言,“實”而“不虛”。不過,“信言”淡然無味,人不可得而親疏貴賤,於他人並無吸引力,故第八十一章說“信言不美”。曲意取悅他者之言爲“美言”,取悅他者是爲了換取利益,即第六十二章所謂“美言可以市”。爲利益取悅他者而失去素樸之性,他者之身、自身被移易而失“信”,即八十一章所謂“美言不信”。言“美言”者爲“俗人”,言“信言”者有“真我”。“信言”與其人爲一,往往被世俗之人當作離“身”而“若反”之“虛言”,故第五十六章有“知者不言”之說。誠然,撇開“聞道”“體道”之身,“言”成“虛言”,“言者”實“不知”也。
道言恬淡,理解道言需要真實的生命經驗與精神境界支撐,這就大大增加了理解道言的難度。對於信奉賢能堅強、習慣物性思維的世人來說,這些道言莫名其妙,似是而非。老子洞悉世態,深知其言之效,如第四十一章“下士聞道,大笑之”,故有“正言若反”之嘆。其言雖若反,實正言。《老子》由形名走向體名,同時,用“言”含攝“名”,也以“字”言“道”。道無名,但對道不能無言。斷言《老子》“超名言”或“反名言”①伍至學:《老子反名言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鄧立光,“概念與語言名相的局限在於無法直接展示天道的內涵。……道的內容可意會而不可言詮”〔《老子新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7頁〕。,完全背離了《老子》精神。
“正言”是積極的、肯定的表述,但是,近現代學者立足近現代歐美哲學,以理性—非理性、理性—直覺、理性—神秘等二分架構看待這些“正言”。例如,由於無法用客觀的、形式化的、確定概念理解“正言”,有學者就將它們歸於非理性、神秘②錢鍾書認爲,“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乃神秘家之句勢語式,“正”爲“反反以成正之正”〔《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第463—464頁〕。、直覺等;也有學者認爲《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是“直覺主義的認識方法”③劉笑敢:《老子古今》,第475頁。;還有學者認爲這是片面誇大理性認識,相對貶低感性認識④張松如:《老子說解》,第271頁。。按照《老子》的思路,“知天下”並不是知天下之“有”,“見天道”也不是見天道之“有”。“無”乃“天下”“天道”的實質與真實顯現,而出戶、窺牗衹能見到室外的這這那那、形形色色、事事物物,並不能窮盡作爲存在者整體的“天下”,也不能見作爲存在根據的“天道”。⑤《老子》第五十四章將“以天下觀天下”作爲“知天下”的方法,其“觀”以“天下”之“名”作爲根據,並非純粹視覺活動——“看”。“見天道”之“見”,也不是通常所說的肉眼“看見”之“見”。在此意義上,向外追尋得到的是更多的“有”,同時也錯失本質性的“無”。故可說“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那麽,在戶牖之內如何知天下、見天道的問題就成了如何發現“無”、把握“無”的問題。由於“不見而名”針對的是“見而名”,《老子》不再將命名的根據放在視覺性的“見”—“形”之上,而是依照對象的內在之體命名。內在之體,包括道、無的內在之體,都“可聞”“可抱”“可迎”“可隨”“可執”。通過回到自己身心,如無爲、無事,人們就能發現“無”、把握“無”,也就能執道、抱道了。這些接近道的方式與人之在特別是人的思想境界難以分離,但卻不是與理性對立的“直覺”,說其“片面誇大理性認識,相對貶低感性認識”亦是牽強。
事實上,理性—非理性、理性—直覺、理性—神秘之對立乃西方哲學的內在邏輯,也是視覺中心主義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在此觀念下,理性概念乃視覺性的形式化語詞,這是西方哲學的秘密所在。當然,西方也一直在探索視覺語詞的邊界,能說得清楚的是視覺語詞邊界之內,一旦超出此邊界,節制者打住(如維特根斯坦),庸俗者強爲之說,高明者則積極探究視覺之外的語詞(如海德格爾嘗試聽覺,阿倫特嘗試味覺⑥判斷力正是以“味覺”作爲其心理判斷的基礎。阿倫特(H.Arendt,1906—1975)以疑問的方式指出:“爲什麽味覺應該提高到和成爲心理判斷能力的手段?而判斷力爲什麽應該基於這種感覺?”〔[德]漢娜· 阿倫特:《精神生活· 意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姜志輝譯,第264—265頁。〕阿倫特曾計劃寫作《精神生活· 判斷力》,但最終並沒有完成,僅留下一點筆記。)。如果意識不到這個問題,盲目追隨西方,註定無法理解“正言”⑦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西方的近現代思想家樂於把《老子》中的“無爲”等語詞當作“正言”。例如,法國經濟學家魁奈(F.Quesnay,1694—1774)吸取了老子的“無爲”,提出“自由放任”思想,並以老子“自然”概念爲基礎創建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羅素(B.A.W.Russell,1872—1970)在《自由之路》卷首題有《老子》第二章“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並認爲抑制自我與調和的精神爲核心的中國思想將救贖西方文明。哈耶克(F.A.Hayek,1899—1992)則將《老子》第五十七章“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看作是對自發秩序理論最經典的描述。這些正面闡釋讓《老子》在現代不斷煥發出新的生機。張申府曾試圖從“科學”視域來理解《道德經》:“古云:‘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我嘗說,爲學亦日損。證之最近科學之所趨,可以益信。斯皆‘歐坎剃刀’之利用,明着或暗地。”〔《張申府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第364頁。)所謂“歐坎剃刀”即最簡原則。作爲思想方法,“歐坎剃刀”在科學、哲學都有表現,以此詮釋“爲道日損”,《老子》有走向科學的可能性。可惜,張申府對從科學來理解《道德經》的理路並未進一步發揮,新文化運動中的其他思想家也未響應之。。
“正言若反”出現在第七十八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五章通常被當作“正言若反”的典型: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與第七十八章一樣,《老子》的表述涉及道與俗等不同層次。“明道”“進道”“夷道”“上德”“大白”“廣德”“建德”“質真”“大方”“大器”“大音”“大象”“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等屬“道”思想系統的語詞;“若退”“若纇”“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若渝”“無隅”“晚成”“希聲”“無形”“無名”“若缺”“若沖”“若屈”“若拙”“若訥”是“道”呈現於“俗”之態。“道”及其在“俗”之中的對立源於“道”與“俗”之間深刻地對立。事實上,對於“聖人”或“上士”來說,“明道”“進道”“夷道”“上德”“大白”“廣德”“建德”“質真”“大方”“大器”“大音”“大象”“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乃“道”的直接呈現,而不是“若……”或“無……”。這些都是《老子》積極確立的“正名”“正言”,也是《老子》稱之爲“建言”的原因。“正言若反”,但“正言”既非“反言”,也非“反語”。
傳統註家大都將“正言若反”落實於“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句,認爲這是合道之言,但世俗之人無法理解,將其理解爲“反言”。①例如,河上公,“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298頁);蘇轍,“正言合道而反俗”〔《道德真經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89頁)。現代學人往往將“正言若反”視爲《老子》的基本表達方式,並以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正、反、合”釋之,認爲“正言若反”是“否定”思維。例如,馮契說:“要如實地表達‘反者道之動’,衹有採取‘正言若反’的方式。……表達了對事物的肯定的認識中包含着對它的否定。”②馮契:《馮契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第4卷,第111—112頁。將“正言若反”視爲“反者道之動”原理的名言表達,這無疑是深刻的。但是,一旦停留於“否定性”,其結論往往會將《老子》推向純粹的“虛無”。比如,勞思光認爲,“反”是“道”的內容,《老子》言“反”以狀道,其主旨是:“每一事物或性質皆可變至其反面。”基於此推導出“萬物芸芸,悉在變逝之中,每一事物皆無實性。”③勞思光:《中國哲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第177—178頁。“反”被理解爲“相反”,理解爲單純的“否定”,那麽,推論出萬物無常、皆無自性這樣奇怪的觀點也就不足爲奇了。還有學者基於“否定性”,認爲《老子》“始終不願從正面的角度對道作肯定性的界說,而衹從負面對道作否定性的描述”④朱曉鵬:《老子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第111頁。還有學者細緻區分“否定性”的四種情况,“第一,用否定性的術語來表達肯定性的內涵。第二,用否定性的術語提醒人們防止好事變成壞事。第三,用否定性的術語提醒人們由反入正。第四,用否定性的術語提醒人們要解决矛盾必須超出矛盾”〔牟鐘鑒:《老子新說》(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第247—248頁〕。。這就將“若反”坐實爲“反”,而無視“正言”之爲“正言”。
誠然,以道主言,道索言者修行態度與工夫。確切說,“正言”以相應的境界與工夫爲前提而發。它們是得道者素樸本性中自然涌現之言,是有德之言。“正言”即“信言”,非實有此境界與工夫者不能理解。換言之,相應境界與工夫之缺失使得俗人必然不能信“信言”,也必然會視“正言”爲“反言”。“信言”出於自身,是自身真實體驗、境界之表達,以“信言”言道意味着道與人之在難以分離。
六 體名與體道傳統之生成
道與人之在的融合,決定了通達道的路徑。從語言層面說,連接着道與人的“體名”也構成了認識道之基本階梯。沿着《老子》開闢的道路,以“體名”言“道”逐漸形成了中國思想中的體道傳統。
老子“聞道”思想在道家後續發展中得到進一步展開,例如,《莊子· 人間世》:“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這裏區分了三種聽:“聽之以耳”“聽之以心”“聽之以氣”。以耳聽易爲耳——生理結構所限:每個人的聽力有限(“耳”);以心聽易爲心——一己之成見所限:僅能聽到自己可以理解者(“符”)。超越耳聽、心聽之限,也就是以氣聽——虛而待物,這也就是以道聽。以道聽任事物自由呈現,纔能聽出事物之本質。
《文子· 道德》同樣發展了“聞道”思想:“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非學不知,非精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疑則有問,聽則須審,亦猶撞鐘,聲不虛應,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玄覽無遺。中學以心聽,或存或亡。下學以耳聽。瞥若風過。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學”不止是理智的瞭解,而且是境界的提升。“以耳聽”“以心聽”“以神聽”所獲得的“皮膚”“肌肉”“骨髓”分別指向生命與學識的交融程度。“學在骨髓”表達出“道”與“生命”高度交融的智慧之境。
老子“抱一”“執大象”“迎”“隨”“守”等觸覺性方法則被《莊子》《文子》《韓非子》發展爲“體道”說。例如,《莊子· 知北遊》: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
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體道”不同於“論道”。在後者,“道”是“人”的對象;在前者,“道”在人生命中。以人的身心承載、支撐並顯示道,而把道從自身推開,使之成爲與自己有距離的對象,則道纔會隱而不彰。《文子· 守易》則對“體道”做了更細緻的描述:
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體道”內在要求爲道者之情性、心術和諧寧靜,情感上高度認同、滿足“道”。同時,不屈物從己,淡然自適,和愉靜漠。節制慾望與心意,以生命持存爲度,養生抱德,以終天年。這些精神態度構成了“體道”的基本精神準備。
韓非子的精神氣質雖迥異於《老子》,但他也能理解“體道”之妙用:“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①《韓非子· 解老》(北京:中華書局,2007)。在這裏,韓非子把“體道”理解爲保身、有國的精神前提。由“體道”而智深,由智深而會遠,由此達到保身、有國目標。
老子“味無味”思想在漢魏晉發展出“味道”概念。例如,“(班固《答賓戲》)委命共己,味道之腴”②〔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4231頁。;“申屠蟠……安貧樂潛,味道守真”③〔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1751頁。;“蓨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④〔漢〕曹操:“爵封田疇令”,《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39頁。;“原憲味道,財寡義豐”⑤〔三国· 曹魏〕嵇康:《嵇康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658頁。;“味道忘貧”⑥〔晉〕葛洪:《抱樸子· 外篇》(北京:中華書局,1991),上冊,第414頁。,等等。“味道”之“味”意爲“嘗味”“體味”“玩味”,也就是以自己的生命自覺與道交融,並在個體的生命中呈現出“道”。“味道”概念的普遍使用,標誌着漢魏“味名”之自覺與味覺思想的完成⑦貢華南:“從形名、聲名到味名:中國古典思想‘名’之演變脈絡”,《哲學研究》4(2019):52—61;“中國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與認知”,《中國社會科學》3(2016):42—61。。
“聞道”“體道”“味道”構成了中國思想通達“道”的基本路徑。這表明,《老子》以來超越客觀性、確定性、形式性的思想趨向得到自覺的延續與強化,而身心參與到對象的呈現之思想道路在思想史中得以確立與成型。
自從《老子》將“形名”拓展到“聲名”“觸名”“味名”,並以這些“體名”來言說對“形名”說不得者之後,這個思路就被後世繼承並充分發展。漢代思想家總結出“造字”之“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①〔漢〕班固:《漢書》,第1720頁,唐人顔師古註。“象形”即以“形”爲根據造字,相當於“形名”;“象聲”以“聲”爲根據造字,相當於“聲名”;“象意”以“意(主要是意味)”爲根據造字,相當於“味名”。“形”“聲”“意”被當作並行不悖的造字根據,與《老子》拓展名言的思路大體一致。在中國現代哲學中,金岳霖提出“本然陳述”理論,試圖解決如何說那說不得者。②金岳霖:《金岳霖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2卷,第359—374頁。金岳霖以本然陳述積極表達可感而不可說的具有實質、活動特徵的“能”,由邏輯名言拓展到本然陳述,其拓展說不得者之言說的努力也貫徹了由形式性的名言(廣義的“形名”)到實質性的名言(廣義的“體名”)之思路。可以看出,《老子》拓展名言的思路在歷史中一直不乏同道。對於當代中國哲學來說,學會“邏輯地說”(以“形名”說的新形態),以增強“言說”的“可信性”“普遍性”固然重要,但是,積極探索“說不得者如何說”,卻決定着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的廣度與深度。《老子》自覺超越“形名”,而嘗試以“體名”(包括“聲名”“觸名”“味名”)來說“說不得”者,其對說不得者積極的言說開啓了中國“名”“言”智慧更豐富的可能性,也爲當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探索、建構提供了積極的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