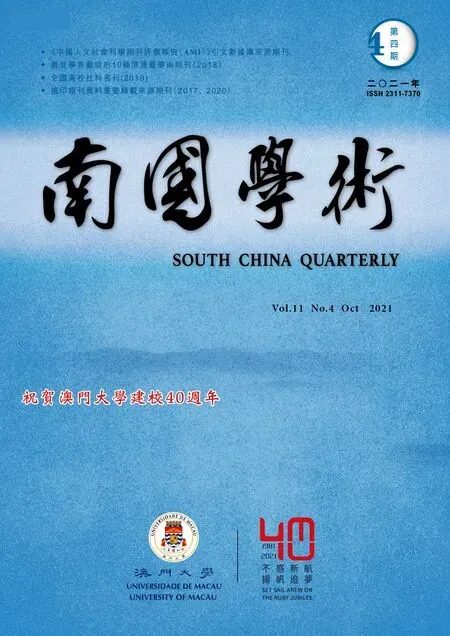北京毛家灣明代瓷器坑的歷史真相
——兼論正嘉之際中外關係轉折與文化變遷
萬明
[關鍵詞]毛家灣 出土瓷器坑 明武宗 豹房 政局更迭 雙重閉關
2005年,在北京市毛家灣,考古發現了一個明代百萬餘片的瓷器坑,這成爲新時期明史研究的一大謎團。因爲,考古學者通過對坑中大量瓷片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形成於明代正德年間的垃圾場;但是,歷史學者卻對此產生了諸多疑問:第一,正德年間爲何會形成這樣一個垃圾場?第二,異常的大型瓷器坑的出現,究竟在訴說什麽?本文擬立足於全球視野,從明代瓷器坑歷史遺存的探源出發,來揭示明代正德、嘉靖之際所顯示的中外關係的重大變化及其深刻的文化變遷。
一 北京毛家灣發現的明代大型瓷器坑
根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西城區文物管理所《北京毛家灣明代瓷器坑發掘簡報》顯示,毛家灣明代瓷器坑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前毛家灣1號院內,北距地安門西大街約356米,東距西黃城根北街約185米。2005年7—8月,進行了考古發掘,清理了1個瓷器坑和3個灰坑,出土了瓷器殘片約一百萬餘片。大部分是明代中期的産品,也有少量唐、遼、金、元時期的瓷器殘片。景德鎮瓷器數量最多,器形有碗、盤、杯、罐、壺等,以碗、盤爲大宗;磁州窑瓷器的數量僅次於景德鎮瓷器;也有少量龍泉窑、鈞窑和北京龍泉務窑、雲南玉溪窑等其他窑口瓷器。這批出土瓷器的年代跨度較大,窑口衆多,釉色品種豐富,並且普遍有使用痕迹。考古學者認爲:“上述現象表明,該瓷器坑爲二次堆積而成,不具有窖藏性質……我們認爲,這種坑是以填埋廢棄瓷片爲主的垃圾坑。並根據年代最晚的‘正德年製’款,確定該瓷器坑形成於明正德年間。”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西城區文物管理所:“北京毛家灣明代瓷器坑發掘簡報”,《文物》4(2008):51—61。
考古發掘無疑爲瓷器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此外,其重要的研究價值還遠不止於此。例如,如此多的瓷片從何而來?這是帶來困惑而需要追蹤探索的基本問題。考古學者進行了多方面探索,做出種種推測,意見不盡相同,大致有四種說法。②根據中央電視台《走進科學》編輯部編《瓷器中國》(成都:巴蜀書社,2016)對參與發掘毛家灣瓷器坑的韓鴻業、李永强采訪論述整理。又見,李永强:“北京毛家灣瓷器坑那些事”,《大衆考古》9(2015)。
1.窑址說。衹有燒製瓷器窑址,纔有可能出現如此多的瓷片,而燒造瓷器的慣例是,將不合格的打碎掩埋。但是,毛家灣這塊地方靠近皇城,沒有記載,也不可能是窑址所在。大量的青花瓷片來自明正德年間的景德鎮窑,但又不衹來自景德鎮窑,還來自龍泉窑、鈞窑、定窑等九處窑口,是多地窑口出産,不是一個窑址出産。
2.漕運說。從地理上看,毛家灣東邊是皇城,北邊是太平倉,西邊是吉慶坊、民意坊,南邊是紅羅場,處於城區中心。有猜想或與京城漕運相聯繫,與碼頭沉船有關。但是,這種猜想隨即被否定了,因爲明代毛家灣這一帶並非漕運碼頭。不僅沒有漕運碼頭,而且大量瓷器有使用過的痕迹,也不可能在運輸過程中形成。
3.庫房說。文獻證明,瓷器坑鄰近明朝庫房集中地,後來這一區域得名西什庫。然而,那些庫房無一是儲藏瓷器的,大量有着使用痕迹的破碎瓷片,也不可能出自明朝庫房的儲藏。
4.地震說。有人提出地震說,根據記載,明代一共發生過37次地震。但是,具體到正德、嘉靖之際,並無直接證據。
2007年出版的《毛家灣:明代瓷器坑考古發掘報告》,作者分析了毛家灣胡同的歷史沿革和明代其周圍的環境,並充分注意到了瓷器坑的瓷片堆積非原生堆積而是二次堆積,和出土瓷片普遍帶有明顯的使用痕迹等重要迹象,得出如下結論:“毛家灣瓷器坑形成於明代正德嘉靖之際,它不具有窖藏性質,而是以填埋廢棄瓷片爲主的一種較爲特殊的垃圾坑。坑內大量的明代中期的瓷件,直接來源於當時周邊人群生活中的破損瓷器。數量驚人的瓷件在填埋之前,被分散丟棄堆積在若干處地方,因爲城市擴建等原因,被清掃集中,就近填埋在當時的垃圾場——現在的前毛家灣1號院。”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編著:《毛家灣:明代瓷器坑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第315頁。
表面上看,該報告對坑內大量瓷器殘片的歸屬給了一個合理的推論,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對於考古學者認爲是一個“垃圾場”,歷史學者應當納入歷史研究的領域,接着追問和探索,這個“垃圾場”的性質與背後形成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二 毛家灣明代大型瓷器坑探源
北京城區出現如此大型的瓷片垃圾場,雖然可能是二次累積形成,但有如此規模,顯然不太正常。從瓷片看,年代不同,包括唐、宋、遼、金、元到明朝前期的瓷片,最晚是在正德年間(1506—1521),陶瓷專家耿寶昌判斷:“時代下限應爲正德朝末嘉靖朝初。”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編著:《毛家灣出土瓷器· 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如此說來,雖然存在以往城市廢棄的成分,但最終的廢棄形成於正(德)嘉(靖)之際。
由於大量瓷片有使用過的痕迹,而正德年間是形成大瓷器坑的關節點,說明當時是由一個相當龐大的消費群體大規模廢棄而形成的。而這樣規模的廢棄物,沒有出現在明代其他時期,考古學者所謂“城市擴建的需要”恐難令人信服。因爲,即使在明代興建北京城的時候,也沒有出現這樣大的瓷片坑。而且如此多的瓷器被打碎,顯然具有非正常的廢棄因素。聯想到明武宗是一個離經叛道的皇帝,死後無子嗣,明世宗由外藩繼位,正嘉之際政局更迭,出現革除武宗朝弊政、嘉靖大禮儀以及人事大變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從而在北京形成一個非正常的人口大變動時期,因此,瓷器坑的形成當與政局更迭時期北京不同尋常的社會人口大變動有所關聯。追根尋源,還要從明武宗的弊政談起。
(一)明武宗弊政的四方面問題
其一,建立豹房建築群——另一皇家權力中心。
正德二年(1507),明武宗開始建立豹房,稱“豹房公廨”。《明實錄· 武宗》記載:“蓋造豹房公廨,前後廳房,並左右厢房、歇房。時上爲群奸蠱惑,朝夕處此,不復入大內矣。”到正德六年(1511),部分建築還未完工。工部上奏:“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費價銀已二十四萬餘兩,今又添修房屋二百餘間。”更重要的是,武宗不在乾清宮而在豹房內長達十五年之久,至死沒有回歸宮內。一個由皇帝、宦官、親信邊將等新貴結成的最高權力中心在豹房形成。《武宗外紀》載:
乃大起營建,興造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又別構院御,築宮殿數層,而造密室於兩厢,勾連櫛列,名曰豹房。初,日幸其處,既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見幸者,皆集於此。
正德九年(1514)十月,刑部主事李中上言,歷數西內豹房之地建立佛寺,廢弛政事:
蓋陛下之心惑於異端也。夫以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於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住番僧,日與親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則用捨之顛倒,舉錯之乖方,政務之廢弛,豈不宜哉!②《明實錄· 武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正德九年十月甲午”。
不僅如此,還是軍事演習之所:
上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於禁中,視團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未幾,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爲義子,四鎮兵號外四家,(江)彬統之。上又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操練,呼噪火礮之聲,達於九門。③《明實錄· 武宗》“正德十一年二月壬申”
所謂豹房“新宅”,最主要的還是遊樂之地:
上稱豹房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工愬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令,獨居京者承應不均;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送教坊承應。於是,有司遣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皆乘傳給食。及到京,留其技精者給與口糧,敕工部相地給房,室大小有差。①〔清〕毛奇齡:“武宗外紀”,《明太祖平胡錄(外七種)》(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第78頁。
以上說明,豹房“新宅”並非武宗所建的一兩個宮殿,而是武宗建立的另一皇家權力中心。它既包括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軍事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大學士梁儲等云:“日者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茫不與聞。”②《明實錄· 武宗》“正德十六年六月辛未”。由此可見,作爲皇帝“新宅”,不僅在西苑,而且也在西安門外,所以,應是一個分散於宮城內外的豹房建築群概念。其中,不僅有“豹房公廨”,是武宗處理公務的地方,而且在經濟上有皇店開設,軍事上有官廳與教場,文化上有寺院與各種聲伎會演之所。武宗皇帝建立的,是一個脫離皇城文武百官正統體制的另類皇家多元權力中心。
其二,圍繞豹房形成的四類群體。
明武宗以個人偏好在豹房形成新的權力中心,“文武群臣茫不與聞”。在豹房,圍繞在他身邊的,主要有這樣四類人群:
一是宦官群體。大凡豹房事務,皇帝起居諸事,都由宦官掌管;國家軍政大事,也都有宦官參與。他們不僅有軍權、監察權,更有批紅權,淩駕於外廷文官之上。至於豹房宦官人數,史無記載,圍繞皇帝的宦官人數衆多,參與豹房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的活動。
二是邊將軍士群體,代表是江彬。江彬,宣府人,原爲大同遊擊,善騎射。邊兵入衛,賄賂武宗佞幸錢寧,引入豹房,得到武宗賞識,升爲左都督,收爲義子,賜姓朱,出入豹房,甚受武宗寵幸。他誘導武宗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號“外四家”,統領西官廳、威武團練營、鎮國公府,史載“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③〔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江彬奸佞》(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722頁。。
除了明武宗寵信的宦官外,豹房中人數最多的是“豹房官軍”——扈從聖駕的官軍勇士,懸帶銅牌出入,牌背面鐫文:“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同罪。”④于力凡:“明代隨駕銅牌及相關問題考略”,《首都博物館論叢》(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25輯。他們名爲隨駕養豹,兼有馴豹和携豹出獵職責,同時還是豹房護衛。關於豹房官軍的人數,不見記載。《殊域周諮錄· 吐蕃》載嘉靖七年(1528)提督豹房太監李寬奏:“正德等年間,原喂養土豹九十餘隻。”《萬曆野獲編· 內府蓄豹》云:“嘉靖十年,兵部覆(豹房)勇士張異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隻,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歲糜二千八百石,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據此估計,豹房官軍勇士約二百多人。以豹房爲中心聚集的軍事力量,根據李洵研究,基本上是三支隊伍:一是舊有“侍衛上直軍”,包括“錦衣衛”在內的御林軍,約有萬人上下。二是武宗時調集的邊軍。本來,根據明朝“祖制”,京軍不能調外,邊軍不能調內,可是武宗不遵祖宗章法,將四鎮邊兵調入了京師,稱“外四家”,約六千五百人。三是由內廷太監組成的“內操軍”,估計一兩千人,在豹房召集“大內團操”,接受武宗檢閱。⑤李洵:《正德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第76頁。值得注意的是,豹房勇士有很多是西域人,王世貞《正德宮詞》中所云“回鶻隊”⑥〔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 正德宮詞》(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第2400—2401頁。,就是指稱來自西域。
三是僧人群體。明武宗崇信佛教,特別是藏傳佛教,達到明朝的一個高峰時期。《名山藏·王享記》云:“武宗習僧門,自號大慶法王,被服如番僧,建僧寺於西華門內。”《殊域周諮錄· 吐蕃》載:“西僧行秘術者夤緣而進居其中,勸上遣中使偕其徒至烏斯藏迎異僧。”武宗還大量頒賜度牒,正德八年(1513),“賜大慶法王領占班丹番行童度牒三千,聽自收度”。此前曾下旨“度番漢僧行、道士四萬人”,由於多冒名者,爲禮部所阻,故有此令。⑦顧祖成、王觀容 等編:《明實錄藏族史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第2集,第920頁。
四是役使群體。這一群體不僅規模龐大,而且成分複雜,有工匠、聲伎、美女、奴僕、市井無賴等。錢寧因騎射得到武宗賞識,被賜姓朱,稱朱寧,掌錦衣衛事,他一度總管豹房日常事務,引進番僧,教武宗御女術,將各種聲伎、美女藏入其中玩樂,其中不乏從絲綢之路供奉而來。一時無法召幸的女子,被安排在浣衣局寄養,以備武宗宣召。據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初一工部上報云:“浣衣局寄養幼女甚衆,歲用柴炭至十六萬斤。”①《明實錄·武宗》“正德十五年正月戊寅”。如此看來,數目驚人。
李洵特別指出,在豹房中還有一些爲武宗日常荒誕生活服務的“小人物”,其中三個姓于的比較典型。(1)于永,色目人,在豹房當供奉,擅長“房中術”,因此得到武宗的寵愛。他曾將“回女善西域舞者”十六人送入豹房,供皇帝玩樂;②《明實錄·武宗》“正德二年十二月辛卯”。(2)于經,原是一名太監,善於理財,爲武宗管理“各處皇店”,在張家灣徵收來往舟車稅;③《明實錄·武宗》“正德九年九月甲子”。(3)于喜,在豹房的軍事遊戲中得勝而得寵於武宗。④李洵:《正德皇帝大傳》,第80—82頁。
總之,豹房中都是明武宗的親信及其役使之人,人員龐雜,其中不乏色目人、外來僧人、西域美女等,而且武宗的皇店由宦官直接經營貿易,與絲綢之路中外貿易也有直接關聯。還有,明武宗廣收義子,正德七年(1512)九月二十四日,一次宣佈賜給國姓“朱”的義子名單就多達127人。⑤《明實錄·武宗》“正德七年九月丙申”。在這批賜姓義子中,有一些與宦官有親屬關係、或與豹房中人有特殊關係而得到武宗寵信,有的出身奴僕,有的本是市井無賴等。
其三,豹宮廷文化的流變。
蓄養和携豹狩獵的外來文明風習,可以遠溯至唐朝。⑥張廣達:“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唐研究》7(2001):177—204。自古以來,通過絲綢之路作爲貿易之路和民族遷徙交流的通道,中國宮廷中不乏異域文明的蹤迹:既有異域的物産,也有異域的文化。自明王朝建立、永樂帝遷都北京後,憑藉遼闊的版圖和強盛的國力,絲綢之路大開,對外交流規模擴大,外來的物産、宗教、習俗、建築、音樂、舞蹈、繪畫等,被明朝宮廷廣爲吸納和融合,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又一個高峰。今見繆荃孫抄《永樂大典》的《順天府志· 土産》記述獸之品,在獅、象之後有“豹,金錢毛色,甚雄偉……隨牽至靼靼山田……遇獸無有不獲”,比之其後晚出的記述更爲珍貴。
豹在明朝宮廷早有故事。嘉靖七年,提督豹房太監李寬統計了歷朝養豹數量上報:
永樂、宣德年間舊額原養金錢豹、土豹數多,成化間養土豹三十餘隻,弘治間原養金錢一隻、土豹二十餘隻。正德等年間原諉養土豹九十餘隻。嘉靖年原養土豹七隻,舊額設立奉命採取,及各處內外守臣進貢豹隻給予本房諉養,自立國以來,已經百餘十年,非今日之設,非係無益之物。⑦〔明〕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吐蕃》(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377頁。
不僅豹大多來自異域,而且異域伴送豹來華之人和明宮中的養豹之人也往往以“回回”稱。永樂七年(1409),明太宗自南京北上途中在德州狩獵,被胡廣記入詩中:“紫髯胡兒飼玄豹,攫拿捷疾好牙爪。”⑧〔明〕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德州隨駕觀獵》,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集部,第29册,第168頁。其中的“紫髯胡兒”,無疑是來自陸上絲綢之路。
1516年,波斯商人賽義德· 阿里· 阿克伯· 契達伊的《中國志》第十五章《赴中國去的人員》,較爲詳細記載了明武宗時來自異域的人群以及獅子、豹、猞猁。這裏特將相關記述轉錄於下,以見中國陸上絲綢之路貿易交往之活躍:
自陸路入華的使節——商人爲中國人帶來的“貢品”是用於交換其他商品或“恩賜物”的,他們的貢品主要和首先是波斯馬,餘者按照其分量多少依次爲粗羊毛、被稱爲“埃斯卡拉特”的羊毛呢(以用於製造短大衣)、玉石料塊、金剛石、銀幣、珊瑚(出自希臘和意大利),最後是獅子、獵豹和猞猁猻等(經馴服後用作狩獵)。
這就是中國人經常作爲“貢物”而接受的物品。
獅子比馬匹有權擁有十倍的榮耀和豪華。獵豹和做狩獵用的猞猁猻各自有權獲得用於獅子的一半榮耀和豪華排場。如此一支非常很好的伴送隊伍把他們從中國邊陲一直護送到北京……至於中國人的“慷慨恩賜”或納付的價格,一頭獅子值三十箱商品,而每隻箱子中都裝有一百種不同的商品:綢緞、緞紋布、拜-貝賴克帛(可能指絲綢)、馬鐙、鎧甲、剪刀、小刀、鋼針等。每種商品單獨成包,每隻箱子中共包括一千包,也就是共有一千種商品。爲了交換一頭獅子,他們花銷這樣的三十箱商品,而爲了交換一隻獵豹或一隻猞猁猻則要十五箱。爲了交換一匹馬,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比交換一頭獅子少十分之一。至於使節團的成員,他們每人獲得八套綢緞衣服的衣料及襯裡布,外加三件套穿的色布袍,其衣料如此之大,以至於每塊可供兩人而不是一個人穿。他們此外還可以獲得一塊寬一個古拉吉(約爲180厘米)的平紋布以及高腰皮靴等。這完全是他們奉送給這些人的賞賜物,因爲貢品的物價還要單獨付償。這就是中國皇帝對任何一名穆斯林的賞賜。①[法]阿里·瑪札海里:《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耿昇 譯,第321—322頁。
養豹、獵豹是古代國際性的宮廷風尚,本是中亞、西亞、南亞乃至歐洲各國王公貴族的習尚,而養豹狩獵也本是明宮故事,並非明武宗開創。例如,南海子是明朝皇帝遊幸狩獵的園囿場所,沿自“元舊也”,“設海戶千人守視”,“永樂中,歲獵以時,講武也”。②〔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城南內外·南海子》(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34頁。武宗繼位後,曾數幸南海子狩獵。正德元年(1506),“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③〔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中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1789頁。由於武宗的狂熱偏好,融合外來生活方式和氣氛充斥明朝宮廷,更出現了變奏——豹房公廨,這是史無前例的,也自然爲明朝傳統典制所不容。
明武宗不僅在北京建立豹房,還在江彬的導引下,大肆遊獵,出嘉峪關,三幸宣府,並在宣府建立了第二豹房。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第一次到宣府,“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名義調發各處軍馬錢糧;至大同,發生“應州之戰”。次年,明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要往征“遼東、宣大、延寧、甘肅等處”,再次巡邊到宣府、大同,並渡過黃河,來到九邊重鎮之一、延綏鎮的榆林衛。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由太原出發,回到宣府,結束了長達半年之久的巡邊,成爲明朝皇帝最後的巡幸北邊。在這一年,以寧王反叛爲由,他又開始了南征。
其四,明武宗年間的特殊外來人員。
一是葡萄牙使節來華,曾納賄于江彬。明武宗年間,是東西方交匯的特殊時刻。他在南京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葡萄牙使臣到南京等待接見。伴隨葡萄牙海外擴張的浪潮,托梅·皮雷斯(T.Pires,1465—1540)成爲葡萄牙派往中國的第一任使節,也是歐洲派到明朝的第一位使節。他所肩負的使命是,到中國覲見皇帝,要求與中國建立通商貿易關係。④萬明:“明代中葡兩國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中國史研究》2(1997):129—139。《明實錄· 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有如下記載:
佛郎機國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並給勘合。廣東鎮撫等官以海南諸番無謂佛郎機者,況使者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請。下禮部議處。得旨:“令諭還國,其方物給與之。”
在廣州,皮雷斯讓通事火者亞三賄賂“鎮守中貴”寧誠,得以進入南京。時值寧王宸濠在南昌發動叛亂,明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立意南巡,於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520年1月16日)抵達南京,直至十五年閏八月十二日(1520年9月23日)啓程返回北京。但是,因無意在南京接見使團,皮雷斯等人衹得繼續北上,前往北京等候。此間,火者亞三又賄賂明武宗的寵臣江彬,自己先見到了明武宗,向喜玩樂的武宗以“能通番漢”的火者亞三說話有趣,“時學其語以爲樂”①〔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滿剌加》(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第6216、6217頁。。
但是,武宗並未接見皮雷斯。根據《朝鮮王朝實錄· 中宗》記載,正德十五年(1520),朝鮮通事寫給國內的報告稱:“佛郎機國爲滿剌國所遮攔,自大明開運以來,不通中國。今者滅滿剌加國來求封,禮部議云:‘擅滅朝廷所封之國,不可許也。’不許朝見。”由於明武宗對待葡人“無異於他國”,並且,“皇帝凡出遊時,如韃靼、回回、佛朗機、占城、剌麻等國之使,各擇二三人,使之扈從。或習其言語,或觀其技藝焉”。正德十六年(1521),朝鮮國王問及葡萄牙使節在北京的情況,朝臣申鏛回答:“其初入貢,以玉河館爲陋,多有不遜之語。禮部惡其無禮,至今三年不爲接待矣。其人多賫金銀以來,凡所貿用皆以金銀。臣等往見其館,皆以色布爲圍帳,四面列置椅子,分東西而坐,中置椅子一坐,蓋之紅氈。曰:‘此皇帝臨幸所坐之處。’蓋以入貢之時,皇帝路逢,往見其館故也。中原亦言,皇帝還京,必往見之。”②《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第16册,第14頁。武宗經常出入會同館,也可於朝鮮使臣報告中得知一二:“與靼子、回回等諸酋相戲,使回回具饌物,帝自嘗之。”甚至有時“或着夷服,以習其俗,出幸無常”。③《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實錄》,第15册,第568頁。據此,武宗出入會同館時,曾過葡使所居,也未可知,衹是無其他史料證實。
葡使在京期間,被中國史籍記載的重要事件是,通事火者亞三驕橫不法,與哈密首領寫亦虎仙“或馳馬於市”,在會同館見到明朝禮部主事梁焯不行跪拜禮,“且詐稱滿剌加國使臣,朝見欲位諸夷上”,惹得梁焯大怒,“執問杖之”。④〔明〕嚴從簡:《殊域周諮錄·佛郎機》,第320頁。江彬得知此事後,反怒而言道:“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耶?”⑤〔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滿剌加》(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第6216、6217頁。揚言要奏報武宗。恰值武宗之死,梁焯得以幸免。
武宗死後次日,明朝即下令:“進貢夷人俱給賞,令回國。”⑥《明實錄·武宗》“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佛郎機即葡萄牙使臣也列於其中。明廷在清除武宗佞臣江彬後,還處死了倚仗江彬勢力的葡萄牙使團通事火者亞三,並頒旨將葡使一行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此後,葡使皮雷斯在廣東淪爲階下囚,病故於中國。
二是哈密首領寫亦虎仙在京,與豹房關聯。明初,設哈密衛,封哈密忠順王。正德三年(1508)四月,忠順王拜牙即繼位,派遣寫亦虎仙等人爲使者,到北京進貢方物。寫亦虎仙在京逗留半年有餘,售賣夾帶私貨和朝廷賞賜之物被揭發:“哈密使臣寫亦虎仙等來貢,夾帶私物,虛糜供給,所賜盡於京師鬻之,其屬留邊者俱未霑及,宜加禁治。”⑦《明實錄·武宗》“正德三年十月甲戌”。可見,他一直利用哈密做中轉站,活躍於絲綢之路貿易以獲取財富。無論是吐魯番速檀滿速兒多次侵佔哈密,還是多年侵擾河西走廊的重鎮肅州、甘州,寫亦虎仙都參與了。但由於寫亦虎仙以西域珍寶、女子納賄於豹房錢寧,逃脫了罪責;並得到明武宗青睞,供奉於會同館,還誘引武宗時時遊幸會同館。由武宗賜以朱姓,“傳陞錦衣指揮”。⑧〔明〕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哈密》,第419—420頁。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叛,明武宗率軍親征,寫亦虎仙父子和女婿與幸臣江彬隨行。
嘉靖皇帝即位後,即下詔:“回夷寫亦虎仙交通吐魯番,興兵構亂,攪亂地方,以致哈密累世受害,罪惡深重,曾經科道鎮巡官勘問明白。既而夤緣脫免,錦衣衛還拿送法司,查照原擬,問奏定奪。”⑨《明實錄·世宗》“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寫亦虎仙瘐斃獄中,其子米兒馬黑木、女婿火者馬黑木、侄婿米兒馬黑麻皆於嘉靖二年(1523)五月斬首於市。
(二)毛家灣大瓷器坑是正嘉之際新政的見證
首先,時間上的關聯:正嘉之際,清除武宗弊政。
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死於豹房。內閣首輔楊廷和在太后首肯下,迎接孝宗之弟興獻王之子朱厚熜入京即帝位,後世稱爲明世宗。而在朱厚熜入京前的四十多天裏,楊廷和果斷地開始對武宗時圍繞豹房形成的幾類人群徹底清理,這成爲大瓷器坑形成的基本真相。
在武宗暴亡當日,楊廷和即擬旨解散豹房官軍:“命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命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營操練;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管事;原調各邊並保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於本鎮,人賞銀三兩;命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揀選團營官軍分佈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①〔明〕楊廷和:《楊文忠三錄·視草餘錄》卷4,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當時,邊兵也就是“外四家”被及時遣散出京,是極爲重要的一步棋,涉及的人員不在少數。
楊廷和革除武宗弊政,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罷威武團練營,其中的官軍還營,各邊和保定的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並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自還衛,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遣出;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處置哈密寫亦虎仙,哈密與吐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人等俱給賞,令還國。以上各項,均涉及武宗時的大批人員離京。武宗死後第三天,便頒佈楊廷和草擬的武宗遺詔,除宣佈“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外,具體內容是:
京城九門、皇城四門,務要嚴謹防守。威武團練營官軍,已回原營。勇士並四衛營官軍,各回原營,照舊操練。原領兵將官,隨宜委用各邊。放回官軍,每人賞銀二兩,就於本處管糧官處給與。宣府糧草缺乏,戶部速與處置。各衙門見監囚犯,除與逆賊宸濠事情有干,凡南征逮繫來京,原無重情者,俱送法司,查審明白,釋放原籍。各處取來婦女,見在內府者,司禮監查放還家,務令得所。各處工程,除營建大工外,其餘盡皆停止。但凡抄沒犯人財物,及宣府收貯銀兩等項,俱明白開具簿籍,收貯內庫,以備接濟邊儲及賞賜等項應用。②《明實錄·武宗》“正德十六年三月戊辰”。
同時,大量裁革武宗時期通過傳陞、乞陞、冒籍等方式形成的冗官冗役,這其中包括武職官員、京衛軍校、各監局內使、軍人舍人、冒功軍官、義子等,人數很多,故在楊廷和擬嘉靖《即位詔》中頒佈了裁革冗官冗役的條款,清理工作按部就班進行。據《明實錄· 武宗》記載,正德十六年六月,“查革錦衣衛冒濫旗校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八名”;七月,“命革錦衣衛等八十衛所及監局寺廠司庫諸衙門旗校勇士、軍匠人役,凡投充新設者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一人。敢有違明詔,影射存留、冒支倉糧者,罪如律”。《玉堂叢語· 政事》云:“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盡……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幸得官者殆盡。”其人數,來源於嘉靖帝即位詔書。田澍認爲:“這一數目基本上反映了正德年間以上機構冒濫的嚴重情況,但是,它衹是被初步估計的裁革人數,而不是已經被裁革了的人數,況且還不包括此前和此後裁革的其他機構的數目。”③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禮儀”與嘉隆萬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145頁。
具體而言,新皇帝繼位後的幾個月內,一是將“谷鎧、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中官張永、魏彬、張忠等九人,蔭授弟侄等錦衣衛官”全部革除;二是應吏部疏請,將正德年間傳陞乞陞中書科、鴻臚寺、欽天監、太臣院少卿等官127員,分別予以“罷黜停降”的處理;三是下令裁革僧錄司左善世文明等182員,道錄司真人高士柏等77員,教坊司官俳奉鑾等官蘇祥等106員,總共365名官員的職位;四是裁革五府所屬京衛並親軍衛分大小官員、旗尉共3199名。④林延春:《嘉靖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第50頁。五是革除冒濫工役旗校等,即上引的148700餘人。《明史· 楊廷和傳》載,由於大規模地裁革冗官冗役,“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每年可節省漕糧153.2萬餘石。這確實是一個龐大的消費人群在北京的消失。這些被裁革的官役人等,將大量日常用品遺棄在北京,所使用過的瓷器,成爲當時瓷片坑的主要來源。
不僅武宗身邊的大量宦官被清理,調集入京的邊軍被調出北京,還有大量寺院的毀棄和僧人的驅逐。嘉靖元年(1522),禮部郎中發檄:“遍查京師諸淫祠,悉拆毀之。”①〔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世宗崇道教》,第783頁。嘉靖六年(1528)十二月,僅京師即毀尼姑庵寺六百餘所②〔明〕霍韜:《霍文敏公全集·石頭錄》(寧海:石頭書院,清同治元年,1862),卷3。。同時,還驅逐豹房番僧人等,以及大量樂工、歌姬等人員。更有南海子淨身之人的驅逐,如嘉靖元年“原充南海子海戶淨身男子龔應哲等萬余人詣闕自陳”③《明實錄·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己巳”。,嘉靖五年(1526)“南海戶淨身男子九百七十餘人復乞收入,上怒,命錦衣衛逐還原籍,爲首者杖之”④〔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中官考》,第1881頁。。經嘉靖初年的清理,到隆慶二年(1568)三月,穆宗以“左右盛稱海子”,欲幸駕那裏,至則以“榛莽沮洳,宮帷不治”還駕。⑤〔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城南內外·南海子》,第134頁。這是武宗之後南海子宦官遣散的一個例證。
值得關注的,還有在嘉靖初年對皇莊、皇店、皇鹽、勛貴莊田的清理與退還。明武宗時,創建皇莊七處,又大建皇店,內自京城九門,外至張家灣、河西務等地。嘉靖二年初,夏言《查勘莊田疏》云:“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假之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⑥〔明〕徐學聚:《國朝典·莊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19。請求查勘“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佔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民”⑦〔明〕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3,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5冊。。二月,帝詔令廢皇莊改官地⑧《明實錄·世宗》“嘉靖二年二月乙亥”。。皇莊管理人員主要是宦官,大都是由武宗親信管理,進行了大量調整。
明武宗的豹房被全面清算,史稱“更化改元”,構成武宗朝特權集團及其相關人員的大量處置,這些人數加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數目。此外,世宗初年興大禮議,最終藉嘉靖三年(1524)七月左順門哭諫之事,盡逐廷臣。所以,如果再加上嘉靖初因大禮議而被清除的大量官員,那就更不可計數了。正是正嘉之際政局更迭出現的北京人口非正常大變動,成爲大瓷器坑出現的主要原因。它見證了武宗朝豹房特權集團及其相關人員一個龐大的多元群體的消失過程。作爲曾經在北京生活的外來人員,在他們非正常地離開北京甚至離世以後,其日常的瓷器用品被大量廢棄是可以想見的。因爲,瓷器不像細軟可以帶走,而且大量被打碎的瓷器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些瓷器的主人很可能是非正常離開的。如將正嘉之際這場大規模革除武宗豹房弊政及其所涉人員,以及嘉靖初以大禮議清除的官員人等的人數統而計之,粗估可達二十萬;如果每人所用瓷器即使以一件計,也有二十萬件;如果均被打成碎片,以一件爲五片計,即可達到一百萬片的數字了。
其次,空間的界定:毛家灣與豹房建築群的位置。
美國學者蓋傑民(J.Geiss,1950—2000)認爲,畜豹的豹房,與殿宇衆多而有“新宅”之稱的豹房各爲一地,而此兩地的距離並不甚遠,並圖畫豹房公廨的位置:在騰禧宮以北,贓罰庫以南,蓄豹房與百獸房以西,皇城西墻西安門之十庫以東一帶。⑨[美]蓋傑民:“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3(1988):13。但他對文獻的利用還不夠充分,因此,位置的考察尚有空間。
《明實錄· 世宗》卷一載楊廷和擬世宗即位詔云:“一內府禁密之地,不許蓋造離宮別殿,載在祖訓,萬世當遵。近年以來,節被左右近倖之人獻媚希恩,在內填蓋新宅、佛寺、神廟、總督府、神武宮、香房、酒店之類,在外添蓋鎮國府、總督府、老兒院、玄明宮、教坊司新宅、石經山祠廟、店房等項,使着內官監、工部、錦衣衛、科道官逐一查勘,但有不係舊規者,或拆毀改正,或存留別用,或變賣還官,官匠人等有因蓋造陞官者,亦就查革改正。在外者聽撫按官一體查勘改正,變賣還官,不許隱匿。”這基本上將武宗時在宮城內外的所有建築都點到了。因此,武宗弊政是以豹房新宅爲中心,在宮廷內外均有大量營建,形成了一個建築群,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廣泛領域,使宮廷與城市社會生活從未有如此緊密的聯繫,也給京城百姓造成了莫大影響。
西苑是明代重要的皇家園林,主體位置在宮城西墻和皇城西墻之間,西至西安門。西苑設有豹房,是養豹之房,與豹房公廨是兩回事,這一點蓋傑民所說無誤。但是,此前的研究沒有分清蓄養豹房與武宗豹房的本質區別在哪裏,而反復爭議武宗豹房有沒有豹、有幾隻豹,其實沒有意義。孫承澤《春明夢餘錄· 宮闕》記載:皇城外圍墻3225丈餘,有6個門,西安門是其一。西苑蓄養豹房與豹房公廨新宅均在西苑,而豹房公廨新宅還延伸到了西安門外的皇城西北角,所以他纔認爲是有乖舊典,是逾制不道。下面作具體考察:
——毛家灣鄰近太平倉。查閱嘉靖三十九年(1560)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下簡稱《胡同集》)書前之圖:皇城西安門外有安富坊、積慶坊、鳴玉坊。書中“積慶坊· 四鋪”記有西四牌樓東北、陳皇親宅、紅羅廠、太平倉、皇墻西北角、甲乙丙丁戊字庫、司鑰庫、贓罰庫、鷹房蟲蟻房、鴿子房、東花房、西花房、羊房、豹房、經廠、果園廠等地名。其中,將西苑的羊房、豹房、經廠、果園廠也列入。但其中的西四牌樓東北、陳皇親宅、紅羅廠、太平倉、皇墻西北角等地名,極具價值。以此比對今毛家灣位置圖,可以發現,毛家灣就在太平倉南,紅羅廠北。①北京文物研究所 編著:《毛家灣:明代瓷器坑考古發掘報告·毛家灣位置示意圖》,第3頁。再查清代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下簡稱《志稿》),西安門外大街有四個連在一起的地名:“太平倉、前毛家灣、中毛家灣、後毛家灣。”並引《明史· 外戚傳》云,陳萬言是嘉靖肅皇后之父,“嘉靖二年,詔營第西安門外,費帑數十萬”。由此,毛家灣與《胡同集》中積慶坊陳皇親宅、紅羅廠、太平倉可以組成一個鏈條,得出的結論是:發現大瓷器坑的毛家灣,與太平倉在同一個區域內。
——太平倉即鎮國府。太平倉本身有故事。本是元代永昌寺,正德五年(1510)改建爲倉,賜名太平倉;八年三月,改太平倉爲鎮國府,②《明實錄·武宗》“正德八年三月戊子”。進而成爲一個新的政治軍事中心。《明實錄· 武宗》記載:正德九年八月,“太監韋霦傳旨,鎮國府千總都指揮宋贇、楊玉,京營千總都指揮左欽、湛臣,俱充參將。贇領春班官軍,玉、臣領秋班官軍。”明代朱茂曙《兩京求舊錄》記載:“康陵先立鎮國府,後乃自封鎮國公,府在鳴玉坊,嘉靖初仍改太平倉矣。都人至今猶呼西帥府胡同也。”康陵是明武宗的陵墓,這裏作爲他的代稱;而武宗確實是先建鎮國府,後於正德十三年九月自封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而且其死後,嘉靖元年五月,改鎮國府仍爲太平倉,命總督倉場官管理。這裏出現的問題是“府在鳴玉坊”,《胡同集》記鳴玉坊三牌十四鋪,有“四牌樓西北西帥府胡同”,以武宗在此建立鎮國府而得名。因此,太平倉在鳴玉坊還是積慶坊,記載有出入。無論如何,記載印證了豹房建築群擴展到積慶坊、鳴玉坊一帶,而毛家灣鄰近當年的太平倉,也就是當年的鎮國府。
——積慶、鳴玉二坊的西市皇店、義子府、教場。明朝西四牌樓大街也稱西大市街,是北京商業街之一,就在安富坊、積慶坊、鳴玉坊、咸宜坊交接處。永樂年間,宛平縣蓋十六間半“召商居住”的廊房③〔明〕沈榜:《宛署雜記·河字·廊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第58頁。,也就在西四牌樓,靠近皇城西安門。據鄭克晟考證,武宗皇店的設立始於正德八年④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4),第327頁。。《明實錄· 武宗》載:“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刑科給事中徐之鸞上言:邇者都民爭言京師西角頭新設茶酒店房,或云車駕將幸其間,或云朝廷實收其利。”這裏揭示了京西建立皇店的事實。次年四月,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等言:“近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有言欲造皇店、酒館,有言欲營義子府第,有言欲開設教場者,老稚轉徙,哀號垂涕。夫開設皇店數年於此,商賈苦科索,閭閻艱貿易,朝廷得利甚微;而下同壟斷,不罷即已,復增設之,則非恩也……伏賜停罷。不報。”①〔明〕何喬遠:《名山藏·典謨記》,第1209—1210頁。由此可知,當時皇店開設在積慶、鳴玉二坊已有數年,此時又準備在二坊之地擴建皇店,建義子府邸,開設教場,這片地方在明朝皇城西北角的西安門外,而這些建築在性質上屬武宗豹房建築群的擴展部分。
——毛家灣位於“西安門外第一區”。嘉靖初年清算武宗建築群時,肅皇后之父陳萬言對原賜第處不滿,於是,皇帝“命工部改給西安門外第一區”。②《明實錄·世宗》“嘉靖二年三月庚戌”。這就是出現在嘉靖三十九年《胡同集》中的“陳皇親宅”,它與太平倉、紅羅廠羅一起列名;而後清代《志稿》出現的毛家灣,則與太平倉一起處於“西安門外第一區”的地理位置。正德、嘉靖年間,這一帶先是拆毀民居建豹房擴展的新宅,後又作爲弊政加以清算,建築的主人換了一批又一批,産生了大量瓷器碎片,就近處理在毛家灣,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明武宗死後,在西安門外所建部分豹房建築群,以奸人名義全部被清算。刑科左給事中許復禮言:“頃者逆彬於西安門外立鎮國府,於西市建新房,奪民居以圖市利,百姓怨恨,痛入骨髓。又宣府行殿鄰於北虜,巍峨燦爛,恐生戎心,皆宜亟毀,以安衆心。”③《明實錄·世宗》“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這是將營建鎮國府、西市新房奪民居圖利等都算在了江彬身上。
綜上,毛家灣位置鄰近武宗豹房建築群,正是就近處理廢棄物的合理安排。大瓷器坑的出現凸顯了雙重見證:一是正嘉之際政局更迭清除武宗弊政的見證;二是武宗豹房建築群毀棄的見證。
三 毛家灣明代大瓷器坑的延伸解讀
以往對明武宗的評價,均以弊政做出定性判斷,而將革除弊政稱爲“嘉靖革新”,如果僅從政治史視角來看是有道理的,因此,嘉靖新政長期以來得到普遍好評。然而,既然豹與獵豹是一種古代中西宮廷的風尚,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交流實例,那麽,作爲16世紀全球化開端關鍵的中外關係史交匯點的正嘉之際,就應該置於更廣闊的全球視野來思考與研究。
在瓷器坑中,有不少是武宗時生産的青花梵文紋碗、青花梵文紋杯、青花梵文紋盤的瓷器碎片,明顯帶有外來文化元素。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編著:《毛家灣:明代瓷器坑考古發掘報告》,第17、22、23、28頁。陶瓷學界專家認爲:“正德青花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喜歡將文字,包括漢字,少數民族文字如藏文、維吾爾文,外域文字如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作爲裝飾,甚至作爲裝飾中心,別有一番情趣。”⑤李知宴:《陶瓷發展的歷史和辨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4),第378頁。雖然大瓷器坑以民窑生産的瓷器爲主,似乎沒有武宗時官窑生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青花瓷片出土,但大量存在於中外博物館的正德年製青花瓷,帶有外來文化元素的特徵也不勝枚舉。由此提醒人們:瓷器坑的出現,或可證明是中外文化正面交鋒後矛盾升級的一個結果,凸顯的也是文化的衝突。
揆諸歷史,如果從全球視野出發,將正嘉之際對外交往事件相互聯繫作一綜合考察,就會發現,正當16世紀全球化開端的關鍵節點,嘉靖初年對陸海絲綢之路實行雙重閉關,這意味着中外貿易與文化聯繫的一度中斷,形成了中外關係的一大轉折:
一是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閉關。由於驅逐葡使和處置葡萄牙通事火者亞三,明廷頒旨:“自今海外諸番及期入貢者,抽分如例,或不賚勘合及非期而以貨至者,皆絕之。”⑥《明實錄·世宗》“正德十六年七月戊寅”。原在正德初年已經開始放寬的對海外各國來華貿易活動的貢期和勘合要求,此時完全收緊。⑦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第193—194頁。
二是對陸上絲綢之路的閉關。哈密是明朝“扼西域之咽喉,當中西之孔道者”。永樂年間於哈密設衛,從此哈密承擔起陸上絲綢之路對外交往的樞紐作用。①蒿峰:“明失哈密述論”,《山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84):45—50。革除武宗弊政,與葡使通事一並處置的包括哈密首領寫亦虎仙及其親屬群體。張璁曾論及嘉靖三年五月處決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八月土魯番大舉入寇甘州,“誠未必無所由也”。②〔明〕張璁:《張璁集·論邊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71頁。他直接提出殺寫亦虎仙等人之“誤”,與嘉靖三年嘉峪關閉關事件的關聯。
以上事實說明,正嘉之際的政局更迭,對絲綢之路的影響是雙重的,既包括陸上絲綢之路,也包括了海上絲綢之路。明朝史無前例的陸海絲綢之路的雙重閉關,形成中外關係至關重要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明代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大轉折點。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一點被遮蔽了。
明成祖遷都北京,奠定了絲綢之路新的起點與交匯點,將古代絲綢之路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對外海陸並舉,特別是航海外交從海上貫通了陸海絲綢之路,在人類文明共同體互動層次上有了新的提升,形成了東西方文明交融的大格局,重構了絲路輝煌。③萬明:“全球視野下的明代北京鼎建”,《史學集刊》4(2021):29—40。雖然鄭和下西洋以後,海上絲綢之路貫通了陸地與海洋,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降至其次,但是,明武宗正德年間是一個東西方交匯的重要節點:一方面,武宗建立豹房、寺院,任用邊將、巡幸西北,這些所謂弊政現象,大多隱含着永樂遷都北京以後,明朝宮廷濃重的絲綢之路多元文化混雜融合的影子,可以說陸上絲綢之路外來影響在明武宗朝達到了一個高潮;另一方面,從海路西方葡萄牙使節首次來到中國宮廷,中西發生了直接交往與衝突,陸海絲綢之路上的來客,在明朝宮廷集結,成爲一個史無前例的彙聚時刻。明武宗的行爲觸碰了王朝開放的底綫,嘉靖朝君臣與之在政治文化上具有高度分歧,在政治上清除武宗弊政後,出現的是一個文化轉向內斂的進程,使得絲綢之路對明朝宮廷的影響一蹶不振,遭遇閉關後的中外關係進入深度的緊張狀態。
進一步剖析武宗弊政中來自絲綢之路的外來因素,政治變局中的文化衝突浮出水面。16世紀全球化開端之時的中國一幕導致了絲綢之路大變局,中外文化交流的轉折鮮明地表現在明朝宮廷文化上。豹及豹獵文化的傳播,是絲綢之路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武宗的豹房是多元文化混雜交融的産物,而革除武宗弊政後的明朝宮廷則完全轉換了一種文化,因此,政局更迭也意味着文化史的改寫。在正嘉之際,豹和獵豹不僅提供了中西文化傳播的實例,而且也彰顯了中外文化的衝突,在深層次上透露出明朝內部文化取向的重大分歧。武宗對中外文化融合採取開放的態度,其宮廷呈現出多元文化薈萃的特徵,足以證明明初與帖木兒帝國的交往過後,雖然中亞地區陷入分裂割據局面,但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並沒有停滯,仍然發揮着重要的中外交流紐帶作用,乃至出現了一個高潮期。前引武宗時期來華波斯商人的《中國志》就是最好的證明。以往史學界有明朝遷都是內向的看法,然而從全球視野看,遷都北京恰恰是繼承了漢唐長安的傳統。而正嘉之際,在武宗弊政被革除後,實際上意味着永樂遷都以後明朝開放的宮廷時尚達於頂峰而被扭轉,纔是明朝轉向內斂的標誌。
瓷片坑是考古重大發現,與它聯繫在一起的,是歷史發生突變的背景及其內涵。正嘉之際政治風雲突變,事態紛紜,向深層次探索,可以發現世宗朝轉向內斂的層面有二:政治與文化。在顯現新的政治格局同時,也昭示明朝做出了新的文化抉擇。相對正德時期,嘉靖時期的宮廷文化已是一種全新的格調,影響了其後一百多年的明朝歷史。換言之,正嘉之際成爲中外關係的一大轉折,也成爲明朝宮廷文化的分水嶺——排除外來文化,復興傳統中土文化,形成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明朝皇帝尚武的歷史至此結束,明宮狩獵、尚武的生活方式告終,後來的明朝皇帝再也沒有一位對軍事有興趣並且有能力統率軍事,而是更加重文輕武,武臣也從此再沒有力量與文臣抗衡,重振明朝武力之想在明朝宮廷中蕩然無存。
作爲南方藩王入主北京的嘉靖皇帝,意欲全面復興中國禮樂文明傳統,崇奉中國本土的道教,排斥外來宗教和文化,其內斂的文化取向極爲明顯。他生長在南方,又體弱多病,一反武宗對狩獵、豹、武夫、軍事以及尚武生活方式的偏好,而是對狩獵、武事完全沒有興趣。由此,明朝宮廷文化格調爲之一變。終明世,早年的尚武傳統再也沒有恢復。嘉靖朝,御苑禽獸由二萬上下漸減至二千,或放或殺的獸類中,包括了明武宗所畜的豹、獵犬、獵鷹在內。嘉靖七年,提督豹房太監奏稱:“奉命採取及各處內外守臣進貢豹隻給與本房喂養,自立國以來已經百餘十年,非今日之設,非係無益之物,今衹有玉豹一隻”,奏請嘉靖帝勿負“祖宗成憲”。嘉靖皇帝詔書則云:“豹房所奏,其意導君好尚之意,法當治罪。如曰祖宗成憲,不知此成憲載在何典?”下令:“這豹且留,今後再不許進收。”①〔明〕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吐蕃》,第15頁。他在位的幾十年裏,崇信中國本土的道教,長生不老是他的畢生追求,宮廷成爲一個修煉場所,一個提煉丹藥的實驗場。一反明武宗自稱大寶法王稱號的做法,他自擬的道號長達幾十個字:“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②〔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世宗崇道教》,第791頁。爲滿足修道與淫樂,他多次遴選民女入宮,每次達數百名。命令宮女們清晨採集甘露兌服參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宮女病懨,更導致以楊金英爲首的宮女們起而反抗,發動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壬寅宮變”。③〔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宮婢肆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94—396頁。
至嘉靖初,永樂遷都北京後特有的文化多元化與開拓活力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復興傳統禮樂文明的內斂取向,隱含文化的轉型。就此而言,北京毛家灣大瓷器坑不僅揭示了正嘉之際非正常的人口大流動,也見證了一種文化全新格局的拉開。尤其是閉關的出現,促成其後明朝宮廷的注意力全面轉向傳統,不再有興趣向外廣納新觀念。由此,毛家灣大瓷器坑所見證的歷史信息極爲豐富:16世紀初年中國宮廷的一場權力更迭,其影響絕不僅是政治震蕩,而且波及了中外關係與文化走向的重大問題。
綜上所述,瓷器坑是歷史遺存,以往對毛家灣明代大瓷器坑定義爲“垃圾場”,顯然低估了這一瓷器坑承載的歷史信息。它形成的主因是正嘉之際發生的政局更迭人事變動,引發了一場北京人口大變動;次因是它與武宗豹房的宮外建築群在同一區域內,明顯具有就近填埋的因素。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大瓷器坑也包含此前北京的廢棄瓷器而形成,不排除其中有京城居民日常毀壞瓷器的二次集中堆放。如果進一步延展解讀,正嘉之際不僅發生了政局更迭,在清除武宗朝弊政的同時,還發生了文化變遷,更發生了久被忽視的阻滯陸海絲綢之路的中外關係一大轉折。從嘉靖皇帝的視角來看,明武宗的尚武、崇佛、狩獵、玩樂、放蕩、經商都是一回事,都與外來風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他繼位以後,使宮中風尚大改,篤信道教的世宗轉向了內在,回歸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