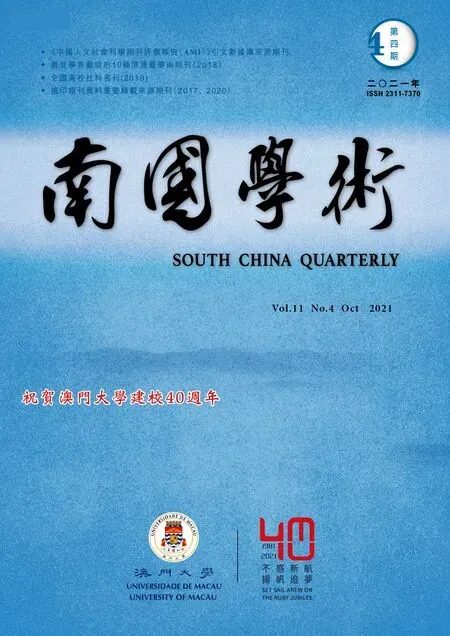中西學術書寫倫理中“抄襲”的演化
江寶釵
[關鍵詞]學術倫理 “抄襲”認知 印刷現代性
在古代中國,“學術”意謂着一種研究學問的方法與水平;在現代,由於全球學術模式爲歐美國家所主導,“學術”被用來指涉高等教育和研究,即其專業極細膩分科後形成的系統化、領域化的學問。而有心追求知識、累積學問以進行研究或從事高等教育的殿堂,被稱之爲“學術界”或“學府”。於是,學術成爲一公共領域,以“原創性”爲前提的論文書寫則是其主要呈現。人文學科較之於其他學科,學術成果更常見的是,以前人的成就及成果爲基礎,再加上自己的一點貢獻與創見。①黃銘傑:“著作權法與學術倫理面面觀”,《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011):4。因此,論文書寫除了個人的投入外,還存在着與他人交往的學術群體。爲了維護學術工作的合理性,持守研究者彼此的信賴,在是否具原創性的判斷上,必須建立一些客觀的準則,以共同遵循。非一己的原創性論述或創作,如果有所援用,就要作必須性的說明、引註;若未能遵循,便需要予以懲戒。這便是當代學術規範、倫理的概念。近一二十年來,全球高等教育出現了巨大變化:一方面,大學數量增多,教師與研究生群體增大,以計劃的形式鼓勵研究和教學,使得論文數量與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如升遷、經費、聲望等)相關聯,導致學術共同體成員間的競爭愈趨激烈;另一方面,電腦與手機網絡的出現,使得文獻複製容易,論文的生產量大增,有關學術規範和倫理的事件、爭議屢見不鮮,群體間的攻訐加劇,人際關係緊張。然而,人們常常會發現,每當事件發生之後,對於處理結果所涉及的學術倫理判例,當事者雙方或旁觀者的認知會出現巨大差異。這就需要站在求真除僞的立場,思考何以如此的關鍵所在。從人文學科、中文書寫的學術倫理看,之所以產生爭議,其根源在於,這一套創新知識生產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在很多地方忽略了中文書寫的傳統形式。
一 “抄襲”的本義與轉譯
(一)“抄襲”的本義
查閱中國古代文獻,“抄”在早期衹是單語,作“鈔”。最早接近“抄襲”概念的應爲《禮記· 曲禮上》:“毋勦說,毋雷同。”東漢鄭玄註:“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然而,接下來的《曲禮》又說:“必則古昔,稱先王。”意思是說,在與人應對進退的禮節中,應當引用先聖前賢之語作爲依據,而不是將之當作自己的話語,也不要每個人的回答都一樣。雖然“竊取他人的著作”這一點上似乎與現代“抄襲”概念相同,但《禮記· 曲禮上》指的是在言談之內的規矩,而非指將他人作品據爲自身的著作。唐朝玄應大師謂:“古文‘抄’‘勦’二形,今作‘鈔’,同。……字書:抄,掠也。《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言強奪取物也。”②〔唐〕元(玄)應:《一切經音義》,收入《佛學工具書集成》(北京:中國書店,2009),第1冊,第51—52頁。可見,“勦”“剿”“掠”“抄”屬於同樣的概念,意同“剽竊”、侵佔他人的物品以爲己有。③“剽竊舊人文章而竄首易尾者,亦云‘畫眉濶’。”〔宋〕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068冊,第57頁。而“鈔襲”“勦襲”一詞,最早出現於南宋;雖是沿用至今的語彙,但最初的意思卻是包抄、襲擊、突擊。④“抄襲”一詞,宋人吳潛在《奉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中云:“水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沂流淺澁,人有沿岸抄襲之患,一難也。”這裏指的是從側面的突擊。一直到清末民初,“抄襲”一語依然有包抄、突襲之意,與今日使用的概念有別。〔宋〕吳潛:“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75冊,第106頁。抄襲的本義還可以從以下三種衍派去理解其內涵。
1.科舉制度。由於時文(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需要博學的人才,因此,對於經傳典籍的熟記是基本的要求。例如,李燾記載宋哲宗年間的科舉亂象:“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剿襲,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⑤〔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0冊,第337頁。又如,清代戴名世謂:“時文之徒,未聞有廓然遠見、卓然獨立者也。即其所習之文,不過記誦熟爛之辭,互相鈔襲,恬不爲恥。”⑥〔清〕戴名世:《南山集· 與白藍生書》,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第39輯,第445頁。兩者所謂的剿襲、鈔襲,意味着在科舉作文當中,僅知背誦而不解音義,甚至引用前賢經典卻不知聖人之道者。重點在批評時文之徒不知會通。
2.創作傳統。在中文創作過程中,模擬仿作被當作是學習的一個過程。沿襲仿作,自六朝以來,蔚爲風氣,韓愈所謂:“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盗。”①〔唐〕韓愈:“薦士”,《韓愈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第73—74頁。鍾嶸亦云:“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②〔梁〕鍾嶸:《詩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8冊,第200頁。楊倫更言:“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爲可厭。”③〔清〕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25頁。也有對這個創作形態的批評,如“人想要做杜,斷無鈔襲杜字句,而能爲杜者”④〔清〕傅山:“杜遇餘論”,《霜紅龕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第833頁。;“詩不易作者五言古,尤不易作者古樂府。然樂府貴得其意,不得其意,雖極意臨摹,終篇勦襲,一字失之,猶爲千里”⑤〔明〕胡應麟:“詩藪”,《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第2502頁。。儘管有貶抑,卻都呈現了中國創作形態中的“沿襲”傳統。及至宋代的江西詩派、明代前後七子的擬古復古主張,以仿擬爲當行本色,皆屬於這個傳統的顯化。以上可見,模擬、仿古、復古之間的創襲關係錯綜複雜。由是可知,模擬、仿作在中國傳統中與現代意義上的“創作”關係不僅不是截然二分的,反而在意識形態上呈現出更深層的聯結,使得創作與抄襲的區界曖昧不清。⑥江寶釵:“中西書寫倫理的差異與衝突——以宋代爲中心的考察”,《南國學術》2(2020):216—229。
3.集註傳統。承孔子“述而不作”的“述學體”傳統而來,對經典的註解一直都是中國學術的形態。由於這些經典的註解必須保存且承襲前人的說法,不免被視爲一種“鈔襲”:
顧今經生家言,月異歲殊,或多堆鑿,或多鈔襲,作者心苦而讀者不能無生厭。惟輪山之文,類抒寫其胸中所自得者,雖言人人殊,而新新不已,無堆鑿鈔襲之弊。⑦〔明〕蔡獻臣:“輪山課士錄序”,《清白堂稿》(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第340頁。
在這個意義下,“堆鑿”與“鈔襲”同樣指涉輯錄前人的說法。雖然集註儘量避免堆鑿抄襲、令人生厭,然而,於解經註疏,累積前人知識本是必要的步驟之一。中國古籍經典的集註,雖也會有引爲“某曰”,但並未像現代一樣需要清楚標示書名、頁數,幾乎都憑印象寫下,誇示自身的博學。集註裏,所謂的“胸中自得”“新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來自前人的說法:
《周禮》自漢儒訓釋,至於今日,不下百家……但名物器數與非大義所關者,亦不能一一出自己見爲解,摘採前人與己說合會而成一家之言。
可見註疏之中,必須是不斷透過“摘採前人與己說合會”方能“成一家之言”。而堆鑿、鈔襲前人的字句與思想,正是所謂“博雅”的學術形態的一部分。若依照現代學術倫理觀之,將別人之說法與己見融合而成一家之言,已是當代定義下的“抄襲”。⑧〔明〕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6冊,第507頁。
(二)“抄襲”的轉譯
很多人看到“抄襲”這個詞時,都以爲明白這個概念,很少人去考察其定義的源頭。西文的“plagiarism”(抄襲)這個詞源於拉丁文“plagiarius”,字面意思是綁架者、小偷、誘拐者。英文詞“plagiarism”是1661年纔出現的,在18世紀被廣爲運用。最早使用“plagiarism”一詞的是公元1世紀的古羅馬詩人馬提亞爾(M.V.Martialis,40—104),用來指稱那些複製他的作品當成自己作品而廣爲流傳的人綁架了他的詩作。⑨Bill Marsh, Plagiarism:alchemy and remedy in higher education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e Press, 2007), 31.因此,“plagiarism”在字源上即隱含着道德判斷——“綁架”意味着將他人的物品佔爲己有,牽涉到物品的所有權問題。但是,當“plagiarism”這個詞被譯爲中文“抄襲”時,不管是單字的“抄”“襲”,或者是相結合的詞“抄襲”,都沒有任何與“plagiarism”相似的內涵。這就如同西方的術語,如“Philosophy”(被譯爲“哲學”),發源於古希臘,就詞源而言是“愛智”的意思,指稱對客觀世界的抽象邏輯思維,中國思想中能夠與之對應的是“名學”一支,而作爲中國思想主流的儒道兩家都是以主體實踐爲思想核心的,與西方“哲學”截然異趣;又如“epic”(被譯爲“史詩”),原本指的是盲詩人口唱的神話傳說或英雄故事,但中國文學傳統中所稱的史詩是以詠史事或時事爲主,兩者皆有不同的意指;再如“novel”(被譯爲“小說”),原本指某一位作者通過口語虛構長篇的故事情節,描寫具體的時空環境,塑造形形色色的平凡人物,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是由18世紀笛福(D.Defoe,1660—1731)、理查遜(S.Richardson,1689—1761)、菲爾丁(H.Fielding,1707—1754)開始的,而在中國,“小說”在漢代已出現,用來指稱街談巷語①“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參見〔漢〕班固:《漢書· 藝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9冊,第817頁。,後來纔演變成今日一種文學類型的代稱。
有趣的是,“抄襲”除了前面所列舉的範疇外,這兩個字的中文字源另有經典化的意涵,使人在遇到“抄襲”的意指時,更加感到困惑。在佛教中,抄經如同誦經,是一種不能不落實的修身養性方式,通過注意力集中,使人的內心世界無妄想雜念、更加澄淨清明,其終極目的則在萬緣放下,達到戒、定、慧的境界。在文學中,“抄”指涉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如《海洋詩抄》指的是在諸多海洋主題的書寫裏挑出具代表性的作品,《十八家詩抄》是從無數詩家裏選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衹是宗教要求抄經,文學需要抄寫,書法、繪畫也都需要抄練。這些抄,有的是講摹習,有的是講經典,有的是講淨心,都具有高向度的正面意義與價值。而“襲”是一個形聲字,它從衣、從“龍”,本義是死者所穿開襟在左邊的衣服;至於“因襲”的意義,指的是依照舊傳統辦理,亦與剽竊、侵佔、盜取毫無關係。
如此看來,將中文語境中的“抄襲”與西文的“plagiarism”相對應,可以說是跨文化翻譯下一個與本義相矛盾的最佳案例。其表意的結果,本身會產生許多誤會。這就如同以一個新的箍,紮在一個舊的桶上,尺寸大小、形狀樣式完全不合適。
“plagiarism”在西方被廣爲運用的時間是18世紀,工業革命與浪漫主義相繼發生,創新見解被高度強調,小說創作大受歡迎,印刷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經濟利益被推向了另一個高峰。
浪漫主義時代是西方的“創襲”概念發生質變的轉折點。在這個時代,人們視“原創性”爲作者的美德,主張個人的創造不應與其他人相同,強調知識所有權。“原創性”不僅僅意味着文學或知識的生產是創造前所未有事物的手段,更要避免抄襲。所謂“作者”,不再是在前人遺留下來的結構上繼續建置自己的作品,而是自行打造與衆不同的特色作品,建立藝術的原理。②Robert Macfarlane, Original Copy:Plagiarism and Origin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
浪漫主義對於原創性的認知,並不是影響西方抄襲觀念發展的唯一因素,經濟因素是另一個關鍵。由於知識生產成爲經濟累積中的重要一環,而且互爲影響,於是,著作權、版權與專利一樣都成爲個人或特定公司資產的一部分,受到嚴格的保護。托馬斯· 馬倫(Thomas Mallon)對此總結道,對作者而言,衹有在意識到他們的作品可以賣錢時,抄襲纔成爲問題;因盜印而產生的損失,意味着危及金錢,對書商和作者都是不利的,故而開始了對“版權”的講求;而引述前人說法固然是註記別人的貢獻,但引註有如書刊廣告,可爲出版商獲得利益,其後演變成“著作權”。③Thomas Mallon, Stolen Words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1989), 38-40.
18世紀的工業革命,也推動了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崛起。資本家爲了將印刷品的銷售量增加到最大限度,改用本地語言出版書刊,取代了過去像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之類的書面語言。其結果是,使用各地方言的讀者得以理解與他使用同一地方語的人,共同論述因而浮現地表。資本主義、印刷術、方言這三者的互動,產生了民族國家的共同想象。歐洲民族國家於是從它們的印刷語言的周邊形成,包括英格蘭、蘇格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丹麥、瑞典爲代表。幾乎是同一時期,新興的民族國家挾其白人殖民主義,結合透過地理的大發現,藉由實際的航海、宗教宣傳、貿易經商、戰爭征伐,歐洲開始蒐集並編纂非歐洲語言的辭典,打造出另一個更龐大的印刷資本市場。①[美]班納迪克·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0),吳叡人 譯,第81—90頁。
在此還要特別指出的是,現代西方重視新創發明,批判因襲守故,使得人們誤以爲西方的述作書寫都是重“原創”的。事實不然。西方對“原創”觀念的探索是歷經一段頗長的時間,纔形成今日樣貌的。
二 學術倫理與中文書寫傳統
在人文科學領域,幾乎每一位述作者都要繼承前人或他人的學術與文化成果,那麽,雷同到怎樣的程度是傳承?怎樣的程度是抄襲?這實際上涉及三個層面的書寫規範問題:其一,創作、研究該如何進行纔是原創性的作爲。其二,如何區別其創新、沿襲與剽竊,即如何分辨哪些文學創作或學術研究是原創者的貢獻,並予以適當標識。其三,若未能如此做而違背了這一規範,即應視爲剽竊、抄襲。簡言之,所謂書寫規範,就是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規範和倫理。儘管“抄襲”與“原創”的意義與價值在古代中國學術中另有看法,然而在“學術倫理”這一範疇內,現代中國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的傳播。而這個現象是一個漸變的結果,需要從近代檢視歷史的發展。
作爲西方知識體系的產物,學術倫理被中國接受要從1860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也稱“自強運動”)說起。面對兩次鴉片戰爭失敗造成的前所未有的變局,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自強之道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伴隨着自強運動出現的“同文館”“總理衙門”,提供了中國在學術與思想向西方學習的基礎。“戊戌變法”導致新式學校的出現,建立新學制成爲吸收新知識的方法,進而奠定了中國現代學校的根基。爲了改革維新,知識分子開始提倡白話文作爲利於傳播與推廣的語言,這加速了報刊媒體的興起與發展。而隨着思想與語言的改變,新文化運動便高舉以白話文來推倒文言文,甚至主張中國語的歐化,廢除漢語,改用世界語。在一次次的求新求變中,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不斷被重新定位,學術形態上的西化趨勢已成事實。
從清末到民初,西方思想夾帶着新語言、新名詞進入中國,迫使中國的學術模式與形態走出傳統經史子集的舊學而邁向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學術範式被歸結爲:“走出經學時代,顛覆儒學中心,標舉啓蒙主義,提倡科學方法,學術分途發展,中西融會貫通。”②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爲中心》(臺北:麥田出版,2000),第16頁。隨之而來的影響,就是西式大學教育取代了原有的“師門”與“家法”的中國學術形態。從這個時期開始,在西化最徹底的大學教育中,開始以西方的標準與體系重新評定中國學術思想。直到當代,這個標準與體系仍然在不同層面(如知識分科、學術倫理)發揮效用。然而,向西方學習是一回事,以西方的標準來重估中國學術的價值又是另一回事。不論是強以西方學術範式套加在中國學術上,或是將中國學術掐頭去尾以適合西方學術的標準,兩者產生的問題並不是“全盤西化”就可以解決的,也並非因此即能產生新知。
在語言的層面上,明末清初,對漢語的反思已散見於傳教士跨文化語言的研究中。漢語的特性是一個字即可表示一個意義,單音節,字的書寫順序與意義的變化有關。從清朝到民國,越來越多的跨國接觸與交流使得翻譯的需求日新月異,開始注意到漢語更深層的語法問題,馬建忠撰述的《馬氏文通》是第一部闡述漢語語法的著作,系統性揭示古漢語的語法特色,特別是虛詞和語序的作用,其意義在啓發中國人對漢語語法的思考。民國以後,瞿秋白③“中國的現代白話——普通話(以及各地方的主要方言),應當採取拼音制度,用羅馬字母拼音,制定一種新的中國文,完全廢除漢字。”參見瞿秋白:“羅馬字的中國文還是肉麻字中國文?”,《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第3卷,第229頁。、魯迅④“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爲好奇,乃是爲了必要。”參見魯迅:“玩笑衹當牠玩笑(上)”,《魯迅全集》(臺北:唐山出版社,1989),第7卷,第107頁。、茅盾⑤“我們應當先問歐化的文法是否較本國舊有的文法好些,如果確是好些,便當用盡力去傳播,不能因爲一般人暫時不懂便棄卻。所以,對於採用西洋文法的語體我是贊成的。”參見茅盾:“語體文歐化之我見”,《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第18卷,第110頁。等人不僅提倡白話文,甚至推廣漢語歐化(拉丁文化),說明了白話文的歐化是有目共睹的文化現象,而語言的變革又影響了思維方式乃至思想的形構,“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則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①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102頁。。正是在這裏,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從語言、文法到學術形態的不同。在中國書寫與學術形態削足適履的過程中,學術界理應從扞格處重新思考更符合中國學術的倫理規範。
中文所謂的述作——“著書立言”,其中很大一部分意謂着沿襲與傳承,與西方要求學術的“原創性”相去甚遠。②“其時新遭秦火,儒家唯以保殘守缺爲事,其爲諸子之學者,亦但守其師說,無創作之思想,學界稍稍停滯矣。”參見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學術經典集(上)》,第96頁。“孔子以後的儒家,也多採取述而不作的態度,祖述六經、宗師仲尼,一切意見,均以闡述經典或註釋經典的方式來表達。”參見龔鵬程:《文化符號學》(臺北:學生書局,2003),第20頁。20世紀初期以來,在進步現代性的要求下,學術論文全面取代了中文述作傳統,學界、知識界幾乎全盤接受西方的學術形態與書寫模式,棄守了中文書寫的主體性,忽略了中文書寫所使用的語言必然而且依然蘊含着豐富的歷史內涵,特別是在人文學科領域,這個內涵又屬於一個講求沿襲、繼承的傳統,甚至也不乏一模一樣的複製案例,而所謂的抄襲往往就是其文化薪傳的奧義所在。這種與西方迥異的基本特質,使得全盤西化的學術倫理的接受在當代中文書寫中產生無比的困難。
在中國,將經典文獻刻版印刷,從唐代就開始了。然而版權的概念始自宋代:“書籍翻板,宋以來即有禁例……《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錄後有長方牌記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③葉德輝:“翻板有禁例始於宋人”,《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第91、91—92頁。但如何上報管理單位,上報的文又是什麽格式,一概不清楚;覆板印刷會有甚麽懲罰,也不知道。當然,版權的概念是隨着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翻印所造成的損失不僅直接關係到原出版商的資本,也關係到原作者因出版而產生獲利,以及著作被隨意割裂曲解:“今雕板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④葉德輝:“翻板有禁例始於宋人”,《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第91、91—92頁。版權、印刷術、資本主義,是同時興起的。在這個意義上,中文的“抄襲”意指翻印。⑤“《四書》義句句有刻,公相抄襲而已。”參見〔明〕方弘靜:《千一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26冊,第343頁。“皆翻弄坊間近科程墨,竊其唾餘,不免雷同抄襲。”參見〔明〕王在晉:《越鐫· 重實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104冊,第444頁。翻印會使得原來的排版者、出版者的利益被淡化,甚至到了明代,爲了大量快速獲取利益,“明人刻書有一種惡習,往往刻一書而改頭換面,節刪易名”⑥葉德輝:“明人刻書改換名目之謬”,《書林清話》,第365頁。,“朱明一朝,刻書非仿宋刻本,往往羼雜己註,或竄亂原文”⑦葉德輝:“明人不知刻書”,《書林清話》,第364頁。。這些現象都表明,版權問題衹有在資本主義下的印刷術中纔會出現,作爲中國最具資本主義時代的明代,版權與翻印的問題也就最明顯。然而,中國卻一直要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頒布的《報律》纔立法保障版權:“第三十八條:凡論說紀事,確係該報創有者,得註明不許轉登字樣,他報即不得互相鈔襲。第三十九條:凡報中附刋之作,他日足以成書者,得享有版權之保護。”⑧“報律”,《申報》1908-03-24,第2張第2版。儘管是立法,依然沒有處罰的規定,要到1914年的《報紙條例》中,纔出現相關的罰則。⑨《申報》1910年10月15日第2張第2版《民政部修正報律案理由書》中說:“原律第三十八條既有禁止鈔襲之規定,即應有違犯此項規定之制裁,若無處分明文,則該條規定便同虛設。”因此,也就有《申報》1914年4月7日第11版的《報紙條例之公佈》所規定的罰則。這可以看到中國落後的印刷現代性。
三 抄襲的規範化
一些語言修辭、創新觀念的“類似”被定義爲“抄襲”,是因爲竊佔了他人的作品以爲己有,並用於中文書寫,不僅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權,甚至還損害了出版商的版權利益。
與著作權相比,學術倫理的要求更爲嚴格,因爲它代表着所有參與研究的人員對研究誠信的承諾,而著作權屬於知識產權下的一環。立法者的目的,主要是爲了保障著作人的著作權益,保障文化創作的“原創性”。在其中,“原創性”意指原始性和創作性,“原創性部分強調作品是來自於自己,而非抄襲他人;創作性則要求最低程度的創意”①楊智傑:《著作權法判決與評論》(臺北:新學林,2012),第16頁。。因而,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是該著作的表達,並非思想、概念、原理、發現等。問題在於,哪一部分屬於表達?哪一部分屬於思想、概念?
學術倫理不同於著作權法,它牽涉到從事學術研究的群體在創新知識競爭中的公平性。對學術而言,特定思想或觀念是由何人所出至關重要,故採用他人的觀念或思想進而表達自己的創作時,須明白標示,否則就屬於抄襲。可見,學術倫理較著作權法嚴格得多。例如,“自我抄襲”就不存在著作權法的問題,但卻違反了學術倫理。
研究者的“原創”觀念公之於衆後,他人對這種“原創”無論是部分還是全部複製利用,均須作適當說明,將之歸功於原創者,如果未能做到,即屬“抄襲”。
在1950年代以前,西方對“抄襲”的觀念並未作明確的規範,仍然維持着早期模糊的看法。一直到1952年,林迪(A.Lindey, 1896—1981)寫下他對抄襲/原創的看法後,這種情形纔有所改變。在他的認知裏,“抄襲”是這樣的:
抄襲是文學、藝術或音樂性的偷竊,是冒充著作者的不當行爲,將他人心智的產物虛假地當作自身的作品呈現出來。僅僅是原封不動地複製其他人的故事、劇本或是歌曲,或加入一些無足輕重的改變,並在成果中附上自己的姓名,即構成了抄襲。②Alexander Lindey, Plagiarism and Origi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2), 2, 60.
他還警告說,人們一定要小心,千萬不要混淆“借用”與“竊盜”。“借用”是將前人著作中的幾個片段挪爲己用,“竊盜”則是佔據別人的作品冠上自己的名字,原封不動或略作改變。林迪還認爲,有些觀點過於狹獈,僅僅注意兩個作品之間的雷同;其實,判斷抄襲要看整片樹林,而不是兩棵樹:“抄襲最嚴酷的考驗是,一定要閱讀全文。”③Alexander Lindey, Plagiarism and Origi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2), 2, 60.
林迪的說法,爲人們判斷什麽程度的“借用”會被視爲“抄襲”提供了反思的視角:在引用他人的說法時標示其人,而不加註腳、不引出處(無論有意或無意),在學術規範上應屬於“借用”,是不嚴謹的;而要達到“抄襲”的判定,應從全體而非片段來做評斷。
儘管林迪的意見是中肯的,他也警告在先,但“抄襲”觀念持續發展到今天,被廣爲認可並正在使用的卻正是林迪認爲不當的標準——聚焦於作品中比較孤立的相似性,而非作品的整體性。例如,《MLA論文寫作手冊》中的定義:
最明目張膽的剽竊(plagiarism)就是拿別人的報告或論文當作自己的作品交上去。其他較不明顯的剽竊包括:摘錄或轉述他人的文句卻沒有註明出處,引用特別巧妙的詞句而未註明作者,轉述他人的論點或理念卻未聲明作者是誰。④書林編輯部 編譯:《MLA論文寫作手冊》(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第58頁。
該定義明顯擴大了“剽竊”的適用範圍,將它延伸於詞語、思考的過程。然而,每個人都是從傳統中承襲某些想法和觀念的。它們通過記誦而經典化,成爲記誦者認知、描述、敍述其周遭世界的基礎材料,它既是人類的“經驗樣態總體”,也是彼此溝通言說可以理解、同情而共享的內容,其構成與呈現亦具有表層語言的統一性。在這個階段裏,“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與“非共同知識”(uncommon knowledge)、人與我是不易分開的。“即使沒有普希金這個人,普希金的《歐根· 奧涅金》也會被寫出來。”⑤[英]特雷· 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伍曉明 譯,第3頁。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引的這句話,提供了一種人與人的想象有可能近似的証明。實際的例子如,華萊士(A.R.Wallace,1823—1913)、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幾乎在同時意識到“進化論”的存在;其後,達爾文將其發展爲影響全球的重要學說,華萊士反遭受遺忘。①王道還:“華萊士與達爾文”,《科學發展》444(2009):46—51。又如,《三國演義》中,吳、蜀陣營在赤壁之戰前,面對曹操號稱的百萬雄師,如何破敵?周瑜與諸葛亮同時在掌上寫“火”,不過是同一情境所激發的結果。如何將此一種可能性有效排除在抄襲之外,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原創與抄襲其實是一體兩面,二者相刃相靡。在經過長期的討論之後,如今不僅把應遵循的倫理規範條規化,而且對論文的寫作格式、引用方式等也作了明確的規定,如美國現代語言學會逐年出版的《MLA 論文寫作手冊》(MLA Handbook),及各式各樣的《論文書寫指南》等。
這些“論文寫作指南”定義下的抄襲,大致牽涉到兩個層面:一是觀念、創意層面,二是語言層面。先看第一層面,例如:“狄金森最強而有力的詩表達了她堅定抱持的信念:無法了解死亡,就不能充分理解生命。”如果有人把上面這段話改成:“狄金森堅信,除非我們了解死亡,否則無法充分了解生命。”②書林編輯部 編譯:《MLA論文寫作手冊》,第58頁。這兩個句子的原文分別是:“Some of Dickinson’s most powerful poems express her firmly held conviction that life cannot be fully comprehended 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death”;“Emily Dickinson strongly believed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life fully unless we also comprehend death”。兩者論述的對象,都是詩人對死亡的感受可能會對讀者產生什麽樣的影響,所使用的語言不同,但觀念一致,這就被視爲觀念上的抄襲了。
再看第二層面,舉一個以論述對象爲事物、而又不同來源的例子:“人人都使用語言以及文化。‘語言—文化’這個詞提醒了人們兩者之間必然的關聯。”如果這句話被論者陳述爲:“在語言與文化的接榫點上存在着一個我們稱之爲‘語言—文化’的概念。”③書林編輯部 編譯:《MLA論文寫作手冊》,第58—59頁。這兩個句子的原文分別是:“Everyone uses the word language and everybody these days talks about culture……‘Languaculture’is a reminder, I hope, of the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its two parts”;“At the intersec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ies a concept that we might call ‘Languaculture’”。除了“語言—文化”一詞的使用屬語言形式被視爲抄襲外,這句話也涉及語言、文化兩者之關係的觀念。
以上兩個例子反映出,這一類的“論文寫作指南”無非是要學生養成規訓的習慣,避免他們在知識生產中發生謬誤,導致不可收拾的結果,但這樣的準則是否適用於中文書寫?又該如何與中文書寫的傳統文化對接,乃至內化爲當代中文書寫者的認知?恐怕就不能採用簡單化的“拿來主義”,而是應建立一套適合中文學術書寫並具文化主體性的倫理規範。
综上所述,“抄襲”這個詞譯自英文“plagiarism”,其本意爲拉丁文的“綁架者”。從綁架到盜竊、抄襲,乃至對原創性的高度要求、版權的出現等等,都與西方國家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而今日規範下的所謂抄襲,是指在觀念的“創意”、語言的“修辭”兩個層面不當地取用他人,與之雷同。“抄襲”在學術倫理中隱含的脈絡是在一個學術共同體中發生,以此獲得學術名譽的增長與學術資源的分配。若此一原創是得自將別人的貢獻據爲己有,即違反學術倫理規範,將會帶來學術聲譽與資源上的懲罰。這些因人暨利益而建立的“準則”,在不同的時代、社會裏難免有所變遷,在不同領域、學科將產生迥異的需求,在不同文化語境下更會出現參差的認知。由是必然導致建立共識的困難,衍生出諸多的爭議。關鍵是:書寫相同到怎樣的境況纔是抄襲?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它涉及的層面有一部分與文化背景高度相關,而不得不回溯學術倫理及其同義詞“抄襲”概念的演化過程。無論在中國學術傳統中,還是中文“抄襲”一詞的概念,都與現代學術倫理頗有差異。現代學術的引註,一方面具有查證的功用,一方面也是學術共同體互相交流、書籍產銷宣傳的方式之一。對照中國解經的引註,其目的較接近宣示自身的“博雅”。由於中西學術傳統、規範、典律、模式等自古以來不同,經由跨文化傳播,進入華人社會,漢語轉譯爲“抄襲”這個用詞與英文“plagiarism”本義也不盡相同,進而引發了中文書寫者的種種不適應。這些不適應如何妥善解決,需要當代學林重視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