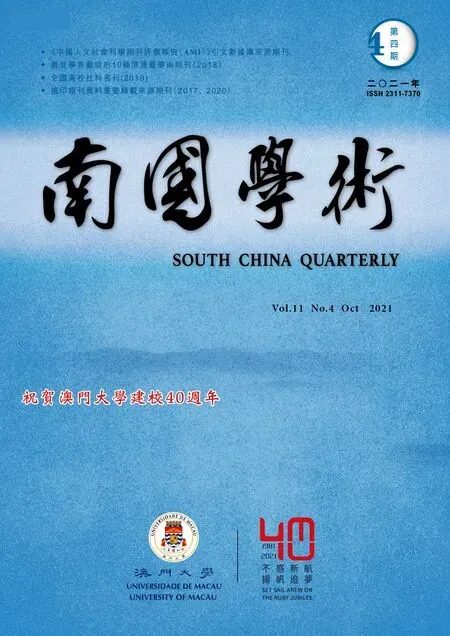規約與突破:恩德文化中的中國文學主題
楊春時
[關鍵詞]中國文化 恩德 中國文學 主題
關於中國文化中的報恩思想以及中國文學的報恩主題,學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是,這些研究還存在三點不足:一是主要在狹義上理解報恩觀念和報恩主題,即研究直接的施恩、報恩行爲,而沒有把施恩、報恩作爲一種社會關係的法則和基本的倫理規範即“恩德”(包括家族領域的“孝”、社會領域的“義”、政治領域的“忠”等)加以研究,因此,相關的文學研究也局限於具體的施恩、報恩故事,而沒有從文學的基本主題着眼。二是衹把報恩觀念作爲中國文化的一個側面,而沒有把恩德作爲中國文化的核心;衹把報恩作爲中國文學的主題之一,而沒有把恩德作爲中國文學的基本主題。三是把儒家的恩德、佛教的恩報、墨家的俠義混爲一談;三者雖然有聯繫,甚至互相滲透,但本質不同。儒家的恩德是一種身份倫理,是不同社會角色的責任;佛家的恩報不是一種自覺的倫理選擇,而是宿命論的因果報應;墨家的俠義不是一種施恩、報恩行爲,不具有支配性和依附性,而是平等的“兼愛”。衹有儒家的恩德,纔是中國文化的主導觀念,也是文學的基本主題。故此,本文擬從闡釋中國文化的恩德本質開始,進而考察中國文學的基本主題。
一 中國恩德文化對文學主題的規定
關於中國文化的性質,爭議頗多。從總體上說,中國文化具有倫理中心和泛倫理的性質,“倫理”主導並覆蓋了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而中國倫理的基本內涵是恩德,即它以施恩和報恩的責任規定了基本的社會關係和倫理原則。因此,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恩德,也可以稱爲恩德文化。①關於中國恩德文化的論述,參閱楊春時:“中國恩情文化批判”,《東南學術》1(2014):75—82;“恩德文化:中國禮物文化在後宗法社會的變異”,《南國學術》3(2020):494—507。
中國恩德文化可以溯源於周代,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確立於漢代以後。周代建立了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度,確立了民本理念,扭轉了殷商時期的神本主義。其時對神的崇拜消退,祖先崇拜增長,爲神恩向人恩轉化做了準備。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轉型,等級制度瓦解,貴族社會轉化爲平民社會,家國一體的封建制度崩潰,貴族文化瓦解,此即所謂“禮崩樂壞”。平民社會形成了新的社會關係和倫理規範,就是以家族關係和家族倫理爲原型,建立了家國同構的制度和文化,即把家族關係和家族倫理推廣爲社會關係和社會倫理,建構起新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倫理規範;再推廣爲政治關係和政治倫理,建構起新的政治關係和政治倫理規範。在這個過程中,儒家把商周社會的神恩轉化爲人恩,對家族倫理及整個倫理體系做了恩德化的闡釋,以施恩、報恩來規定社會關係和倫理原則。也就是說,家族關係中的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孝)、兄與弟的關係(悌)、夫與妻的關係被闡釋爲施恩與報恩的關係,父(母)施恩於子(女),兄(姐)施恩於弟(妹),夫施恩於妻;同時,子(女)要報恩於父(母),弟(妹)要報恩於兄(姐),妻要報恩於夫。中國文化認爲,社會關係是家族關係的延伸,社會倫理是家族倫理的延伸,因此,人際關係是一種恩德關係,社會倫理也是恩德的體現。鄉鄰、朋友、師長之間的關係等同於父子關係或者兄弟關係,是孝悌倫理的延伸,也具有施恩與報恩的性質,即長者施恩於幼者,尊者施恩於卑者,師長施恩於弟子;反過來,就是幼者報恩於長者,卑者報恩於尊者,弟子報恩於師長,從而形成了尊卑長幼有序的社會關係和敬老扶幼、抑強扶弱、尊敬師長的社會倫理。國家領域的關係也是家族關係和家族倫理的延伸,如君臣關係和官民關係等同於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即所謂“君父”“父母官”與“子民”的關係;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也等同於父子關係。於是,君主施恩於臣民,官吏施恩於百姓,宗主國施恩於藩屬國;而臣民報恩於君主,百姓報恩於官吏,藩屬國報恩於宗主國。由此形成了忠君愛民、官良民順、夷夏一體的政治倫理。總之,恩德文化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係之上,形成了倫理觀念與社會關係的一體化。經過春秋戰國以後的社會演化和儒家的倡導,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恩德文化得以正式確立,成爲中國文化的主體。
恩德文化具有多重屬性。其一,恩德具有愛的屬性,施恩表達了對他人的愛,報恩也表達了對這個愛的回應,也是一種愛,它們構成了儒家所謂的“仁”。無論是家族倫理、社會倫理還是政治倫理,都體現了仁愛——以“孝”爲核心範疇的家庭倫理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間的仁愛;以“義”爲核心範疇的社會倫理是社會人群包括鄰里、鄉黨、國人、天下人之間的仁愛;以“忠”爲核心範疇的政治倫理是君主與臣民之間的仁愛。恩德以仁愛把整個社會的人都聯繫在一起,取消了獨立的個體,排除了契約關係,形成了一個互相施恩、報恩的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化是仁愛的文化。
其二,恩德建立的仁愛是恩愛。它雖然也是一種愛,但不等同於現代的愛。由於恩德與社會關係捆綁在一起,也就是規定了人在家族、社會、國家領域的角色(君、臣、父、子),因此,恩愛權力化,具有支配性和不平等性。施恩者具有了支配受恩者的權力,受恩者負有了服從施恩者的責任。在家庭領域,以施恩的名義,父母、丈夫、兄姐可以支配子女、妻子、弟妹;而以報恩的名義,後者要服從、依附前者。在社會領域,以施恩的名義,長者可以支配幼者、尊者可以支配卑者,師長可以支配弟子等;而以報恩的名義,後者要服從、依附前者。在國家領域,以施恩的名義,君主、官吏可以支配臣民、百姓;而以報恩的名義,後者要服從、依附於前者。這種關係說明,施恩不僅僅是一種愛,也是權力的建構,是愛的權力化。因此,後來形成了所謂“天地君親師”五尊,作爲絕對的施恩者,也是絕對的報恩對象,擁有支配性的權力;也形成了三綱,即“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爲臣綱”,體現了施恩者(父、夫、君)支配受恩者(子、妻、臣),受恩者要服從施恩者的權力關係。
其三,恩德不是普遍理性,而是身份倫理,産生了恩愛的差等性。依據恩德的法則,恩情是恩德的基礎,因此所施予的恩惠多,恩愛就大,而施予的恩惠少,恩愛就小。恩德文化雖然也強調一體之仁,但推己及人的結果就産生了差等。中國傳統社會是家族爲基本單位的後宗法社會,家族關係具有優先性,其他社會關係就相對疏遠。在恩德中,血緣關係承載了更多的恩情,如父子、兄弟關係,而其他社會關係承載的恩情相對稀少,故形成的恩愛依據親疏遠近不同而有別。因此,孝悌就具有元初的地位,而恩愛向非直系親屬、師友、鄉鄰、國人、天下人等依次推廣,越近越濃厚,越遠越稀薄,故孟子說愛有差等,從而形成了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這樣恩愛就不是普遍、平等的愛,而是有限的、有差別的愛。
其四,恩德不是絕對理性,而是相對理性。它依據具體的施恩、報恩行爲,使情與理沒有充分分化,而是具有情理一體性,也就是恩情與恩義的統一。恩情是恩德的基礎,離開了恩情,恩德就難以存在,如孝作爲道德責任要依託父母的慈愛,忠作爲政治責任要依託君主的信用,否則就失去效力。這裏也存在着情與理即恩情與恩義的衝突,使得恩德具有了相對性。
其五,恩德具有對應性和不對等性。所謂對應性,是說施恩與報恩的義務是雙向而不是單向的,各方都對對方負有責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賢、君明臣忠、官良民順,雙方互相施愛,互相約束,缺一不可。但是,施恩與報恩雙方的責任又是不對等的。由於施報責任與社會身份相關聯,所以,施恩方支配報恩方,報恩方依從施恩方。由於報恩方的弱勢和被動性,對報恩方的約束力更強,因此纔有“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之說,也纔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可以不明,臣不可以不忠”之說。
中國恩德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它決定了中國文學的品格:一是鮮明的倫理性,懲惡揚善,是非分明,而相對不強調文學的真實性。二是強烈的社會性,注重抒發家國情懷,而相對不注重表達個體生存體驗。三是厚重的現實關懷,關注此世的生存,而相對不注重靈魂的安頓。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文學的恩德主題,也就是施恩和報恩的主題。這個主題,貫穿於家庭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領域。
在西方,文學的基本主題是愛與死。愛的主題包括愛情主題與反面的復仇主題,這與其個體獨立和契約關係有關,也與西方文化的一般理性有關。古希臘史詩是歐洲文化的源泉,其中《奧德修斯》是復仇主題,《伊利亞特》是愛的主題與復仇主題的交織,以後形成了愛情主題傳統如《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復仇主題傳統如《哈姆雷特》等。死亡的主題滲透着形而上的思考,即對生存意義的追尋,這個主題的代表有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和《浮士德》以及現代文學經典,體現了西方文學的超越性品格。
在中國,愛情主題、復仇主題之所以不多,主要是因爲中國社會個體不獨立,捆綁於各種恩情關係(包括家庭、社會、國家)之中,人作爲恩德的載體成爲施恩和報恩的角色,於是,愛和恨都不是個體行爲,而是一個恩德行爲,所以,少有獨立的愛情,衹有被規定的恩愛;少有個體的仇恨,衹有被規定的恩仇(家仇、國仇)。同時,恩德不強調仇恨,而注重恩愛,故中國文學淡化復仇,而突出施恩和報恩。在中國古代神話中,神祇成爲爲民造福的聖人,如女媧造人、后羿射日、鯀竊息壤、大禹治水、精衛填海等故事,都體現了神靈祖先對世人的恩情以及世人的報恩精神。中國漢族沒有長篇史詩,但《詩經》中的短篇史詩如《公劉》《生民》等記載了周民族祖先的偉大功績,帶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成爲恩德文化的源頭。後世的文學也集中在孝順父母、行俠仗義、忠君愛國的內容,形成了孝、義、忠三個大的主題。所謂孝,就是孝順父母,報父母的恩,並且衍生出兄弟、夫妻之恩愛,屬於家族領域的恩德主題。所謂義,就是行俠仗義,施恩或報恩於朋友、師長等,屬於社會領域的恩德主題。所謂忠,就是忠君愛國,報君主的恩,屬於國家領域的恩德主題。其中,家庭領域的孝悌主題相對薄弱,是因爲傳統社會的家庭生活比較狹窄、簡單,故事性不強,不容易成爲文學描寫的對象;衹是在傳統社會後期纔有《金瓶梅》《紅樓夢》等專門描寫家庭生活的作品,但它們不是正面謳歌孝悌,而是暴露和批判家庭倫理的潰敗、瓦解。此外,由於恩德文化的世俗性制約,“未知生,焉知死”①《論語· 先進》(北京:中華書局,2007)。,中國文學也缺少死亡主題,較少思考人生的意義,而聚焦於善惡衝突之中。
恩德文化對文學主題的影響有三個途徑:(1)社會生活的影響。從家族到社會、國家,貫穿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都體現着恩德。在家族中行孝,在社會中行義,爲國家盡忠,是傳統社會生活的主旋律。而且,人們也以恩德觀念解釋社會現象,評價社會現象。文學是社會生活的産物,是社會生活的藝術提煉,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恩德文化的烙印。因此,作家在觀察、選取、提煉社會生活現象,形成文學題材和內容時,就不可避免地採取了恩德視角,選取施恩、報恩題材,表達恩德觀念,從而形成了恩德主題。(2)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就是儒家的禮法道德,它也被概括爲“道”或“理”,而恩德是其核心範疇。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也是受這個意識形態規定的,因此提出了“文以載道”的原則,而這個“道”就是忠孝之道。中國文學在這一文學理論指導下,必然以肯定恩德爲宗旨。如《文心雕龍· 原道》就說:“文之爲德也大矣”,“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這個“文以明道”的思想體現在文學創作中,就形成恩德主題。這種文學觀念強調文學的教化作用,把小說作用“歸於令人爲忠臣、爲孝子、爲賢牧、爲良友、爲義夫、爲節婦、爲樹德之士、爲積善之家”②〔明〕無礙居士:“《警世通言》敍”,《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第1頁。。(3)歷史記述的影響。由於神話、史詩傳統薄弱,中國敍事文學主要脫胎於史傳,題材首先從史傳中選取。《左傳》《戰國策》《史記》《三國志》等史書記載了大量歷史故事,特別是一些紀傳體史書的一些人物故事具有傳奇性,這些故事後來演化爲文學作品。在這些歷史傳記中,體現了鮮明的恩德內涵,也形成了文學的主題。例如,荊軻爲報答燕太子丹的恩情而捨身刺秦王的故事,馮驩爲報孟嘗君之恩而爲其解困的故事,韓信以千金報漂母“一飯之恩”的故事,劉、關、張結義的故事,諸葛亮爲報“三顧茅廬”之恩而鞠躬盡瘁的事迹,岳飛精忠報國的事迹,等等。這些歷史事迹後來都成爲文學題材。儘管近代新的文學創造擺脫了歷史題材的限制,取材於現實生活,但仍然繼承了恩德主題。
二 中國文學恩德主題的呈現
中國恩德文化可以劃分爲家族、社會、國家三個領域,形成了以孝爲核心的家族倫理、以義爲核心的社會倫理、以忠爲核心的政治倫理;同時,文學的主題也相應劃分爲家族領域的孝悌主題、社會領域的義俠主題、國家領域的忠良主題,這些主題合成爲“恩德”這個基本主題。
由於中國恩德文化發源於家族倫理,因此,中國文學的主題也首先圍繞着孝悌展開。中國家族關係是以父子關係爲中心的,而夫妻關係、兄弟關係附屬於父子關係,因此,孝成爲家族倫理的基本範疇,展開爲悌、節等倫理範疇,理想模式是父慈子孝、夫德妻賢、兄友弟恭。儘管中國文化強調孝悌爲基本倫理範疇,即所謂“夫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①〔宋〕汪晫 編:《曾子全書· 子思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但在文學題材方面,孝悌主題並不突出,甚至顯得薄弱,因爲固化的家族倫理給文學描寫留下的空間有限,人的真實情感被家族關係和家族倫理所束縛,難以充分地展開爲感人的情節。所以,孝的思想更多地表現在抒情詩和敍事文學的非主題性情節之中。表達孝的思想的抒情詩如孟郊《遊子吟》:“慈母手中綫,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在敍事文學中,《三國演義》中寫徐庶爲了盡孝,不得不離開劉備而跟隨曹操;《水滸傳》中寫宋江之孝、李逵之孝,都是次要情節,沒有成爲主題。當然,也有以孝爲主題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志怪小說、話本、雜劇中。例如,《搜神記》中的《干將莫邪》,以爲父報仇的故事體現了孝的主題。又如,宋代話本小說《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寫汪信之被誣謀反,家人被捕;汪信之投案自首,被處斬,而全家得救。再如,元雜劇有劉唐卿的《降桑椹蔡順救母》,寫蔡順爲侍奉雙親放棄求取功名,隆冬時節,母親不思飲食而衹想吃桑椹,蔡順設香禱告天神,孝心感動天神,化雪降雨,令桑樹長滿桑椹,救活母親。明清小說中也有行孝的內容,但多不是主要情節,少有孝的主題。
中國文學中婚姻生活的題材也體現着恩德主題。在文學作品中,正面表現愛情主題的不多,多是通過對夫德妻賢的家庭生活描寫,來表達夫妻之間的恩愛。在抒情文學領域,有一些悼亡詩,表達了夫妻之間的恩情。這種恩情不同於西方的愛情,主要是一種親情,帶有更多的倫理性。悼亡詩的內容,主要是丈夫書寫妻子之賢淑品德以及與其相濡以沫的經歷,表達懷念之情。例如,蘇軾悼念亡妻的《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凉。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再如,清人納蘭性德的《青衫濕遍· 悼亡》:
青衫濕遍,憑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頭扶病,剪刀聲、猶共銀釭。憶生來、小膽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冷冥冥、盡意凄凉。願指魂兮識路,教尋夢也回廊。 咫尺玉鈎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陽。判把長眠滴醒,和清淚、攪入椒漿。怕幽泉、還爲我神傷。道書生薄命宜將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圓密誓,難禁寸裂柔腸。
由於婚姻衹是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産物,即使有和諧的婚姻,也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很多詩作歌頌了“婦德”,如孟郊的古詩《列女操》就謳歌了女子爲丈夫殉節:“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殉夫,捨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由於夫妻生活遵循恩德,少有故事性可言,故敍事文學的婚姻生活題材比較薄弱,但仍有一些婚姻題材的作品體現了恩德主題。例如,《搜神記》中的《韓憑夫婦》謳歌了不畏強暴、忠於婚姻的韓憑夫婦;《喻世明言· 窮馬周遭際賣䭔媼》中,賣䭔媼對馬周有收留、引薦之恩,馬周在發迹後不顧對方的低下地位和寡婦身份,毅然娶其爲妻作爲報答;《醒世恒言· 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爲了報答秦重的關愛之情和救助之恩,莘瑤琴不顧其家境貧寒,毅然嫁給了他。
戲曲中也有夫妻情義的主題。《永樂大典》收錄的戲文《張協狀元》寫張協中狀元後忘恩負義、拋棄前妻,後迫於情勢復合的故事,表現了“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夫妻之義,而這個義並不是以愛爲前提的。明代戲曲《琵琶記》寫張伯喈中狀元後,被逼入贅宰相家,不得與妻子團圓、盡孝父母,後歷經坎坷終於團圓,並且被皇帝旌表。這個故事也表達了對夫妻之義和孝道的宣揚。《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寫夫妻離散,屢遭磨難,終於團圓的故事,彰顯了夫妻情義。這些劇目並不強調夫妻的愛情,而是強調夫妻間的責任、名分,就是夫妻之間的恩義,即使無愛,也要遵守夫妻之義。
此外,還有許多故事是受恩者與恩人結成兒女親家,以此報恩。例如,《兒女英雄傳》主要圍繞報恩展開,十三妹搭救安公子與張金鳳,於是二人就設計報恩,最後將十三妹嫁與安驥,婚姻圓滿。後來,十三妹也知恩圖報,激勵安驥苦讀,後中探花。還有一些鬼狐化身爲美女報恩的故事,也體現出了婚姻關係中的恩德。例如,《聊齋志異· 花姑子》中,安幼輿五年前放生獵獐,其女深感救父之恩,爲其獻身生子, 而且不顧“業行已損其七”、百年不得飛仙的代價, 救活恩主。在元雜劇中,婚姻報恩主題也不少。除了人們熟知的《洞庭湖柳毅傳書》外,在《山神廟裴度還帶》中,裴度撿到了瓊英救父的玉帶,使得瓊英的父親得救,瓊英的母親爲報恩將瓊英許給裴度,裴度考中狀元,與瓊英完婚。一些民間故事和取材於民間的戲曲也體現了婚配的恩德主題。例如,黃梅戲《天仙配》原本是東漢董永遇仙故事,元代編成雜劇,明代以後出現多種劇本。該故事原本寫書生董永賣身葬父,孝行感天,玉帝命七仙女下凡與其結爲百日夫妻;七仙女憑勞作成果爲董永贖身後,告知實情,並贈送寶物給董永,重返天庭;董永進貢七仙女所贈之寶而得官,歸途遇七仙女送子下凡,後董永娶傅員外之女爲妻。這裏的夫妻之義是爲了報償孝道,而夫妻之愛是附屬性的。
從反面書寫夫妻恩德主題即描寫違背夫婦之德受到懲罰的作品較多。例如,“三言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描寫了違背夫德、忘恩負義而受到懲罰的故事,典型者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借金玉奴之手懲罰了負心薄幸的莫稽。又如,根據明代《包龍圖百家公案》《三俠五義》《續七俠五義》改編的戲曲《鍘美案》,寫了陳世美背棄夫妻之義被懲處的故事,“陳世美”遂成爲負心漢的代名詞。再如,《水滸傳》中宋江殺閻婆惜、武松殺潘金蓮和西門慶、石秀殺潘巧雲和裴如海等,都是懲罰淫夫淫婦的故事。這裏譴責的主要不是對愛的背叛,而是對夫妻責任的背叛。
直接體現兄弟之恩情(悌)主題的作品也不多,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這類詩作相對於描寫朋友之情的詩作顯然少多了。在敍事文學方面。悌的主題相對於社會題材中的結義兄弟故事,就顯得薄弱了。其原因也是兄友弟恭的關係束縛了真實的人情,也很難形成文學故事。當然,也有少量作品體現了這個主題。例如,明代戲曲《殺狗記》,寫因奸人挑撥,兄弟失和,最終得釋前嫌而和好的故事,宣揚了兄弟情義。
社會倫理規範着家族以外的社會領域中人與人的關係。在傳統社會中,社會倫理仿照家族倫理,人與人之間負有了施恩和報恩的責任。一般把這種類似於孝悌的社會倫理範疇稱爲“義”。在中國,由於商品經濟不發達,在家族與國家中間,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領域,社會領域主要是依附家族或者國家,邊界比較模糊。傳統社會有兩種形態:一是鄉土社會,屬於地理上接近、由若干家族組成的共同體,其間的人際關係是家族關係的擴大。另外一種是江湖社會,主要由遊民和社會邊緣人群(失業者、流動職業者、僧道、民間會社、盜賊、流寇等)構成,其人際關係具有不固定性、偶然性。中國文學在社會領域的恩德主題,主要體現爲對義俠思想的宣揚。義俠主題可以分爲“義”“俠”兩個具體的主題,它們有異也有同:同者在於,都是家族以外的社會倫理關係,是對他人的善行。異者在於,俠是江湖世界的倫理規範,俠的主體是體制外的獨立個體,強調自由意志,施恩不求報,有墨家文化的淵源;而義是主流社會的倫理規範,其主體是體制內的角色,強調其社會責任,多表現爲朋友、師徒、鄉里之間的施恩、報恩,屬儒家文化的範圍。但是,二者之間也互相滲透,往往混雜在一起。
關於俠的主題,形成了俠客文學。遊士在戰國時期興起,是舊的貴族等級制度崩壞後,流落在社會邊緣的人群。墨家群體爲遊士的源頭,後來産生了依附於貴族大家的遊士,他們繼承了墨家的行俠仗義精神。《韓非子· 八說》:“棄官寵交謂之有俠”,“有俠者,官職曠也”。俠是體制外的角色,對廟堂秩序構成威脅、破壞。秦漢之際,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而“俠以武犯禁”,遭到統治者的打壓、禁止,遊俠逐漸消失。但由於人們對社會正義的追求不能在體制內得到實現,故嚮往俠客和俠義精神,這種想象産生了俠客文學。司馬遷的《史記》有《遊俠列傳》,後來以此爲母本,形成遊俠文學。詩歌也有歌頌俠義之風的,如李白的一些詩作。俠義主題更多的則體現在敍事文學作品中。遊俠文學虛構了一個王法之外的江湖世界,描寫俠客不受禮法約束,快意恩仇,除暴安良,施恩不求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①〔唐〕李白:“俠客行”,《唐詩一萬首》(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第199頁。。這種源於墨家的思想,對恩德主題有所偏離。如元雜劇《趙氏孤兒》寫了程嬰捨棄自己的兒子搭救被殘殺的趙盾的後代,韓厥、公孫杵臼也爲此獻出性命。這個故事的思想內涵,不僅有儒家的社會正義,更有墨家的俠義精神。那些犧牲者與趙氏及其孤兒並無直接關係,衹是打抱不平,爲伸張正義而付出了生命和後代。清代成書的《綠野仙蹤》屬神怪奇幻小說,但具有俠義文學的特質。它描寫社會黑暗,惡勢力橫行,而冷於冰修得法術,斬妖除魔,扶危濟困,最後以俠義行爲被上帝垂青,得道成仙。
但遊俠文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約和影響,後期遊俠文學中的俠客也失去了獨立性,而成爲明君、忠臣的奴僕。遊俠文學的代表作有明代的《爭春園》、清代的《綠牡丹》《永慶昇平全傳》《萬年青》《七劍十三俠》等。這些作品中的俠客雖然在體制之外,但都是依託官府,爲國爲民除害。後來遊俠文學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也變成了恩德主題的一種,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及其續書,把俠客變成了體制內執法的衙役、捕快,其主題也成爲一種報皇恩、官恩之義。
“義”在恩德文化中的本義是倫理責任,後來專門指民間所說的義氣,即在社會領域人際關係中的恩德規範,體現了朋友、師生、鄰里之間的恩愛。義的主題多表現朋友之間的情義,而在恩德文化中,朋友是等同於兄弟的,彼此之間負有了施恩和報恩的責任。在抒情文學中,多有歌頌友情之作,表達了朋友之義,如李白的《贈汪倫》:“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在敍事文學中,朋友之義的主題也很多。例如,“三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羊角哀捨命全交》等。又如,《聊齋志異· 田七郎》寫貧窮獵戶田七郎秉性正直,富家公子武承休羡慕其人品而欲與之結交,多有饋贈,田七郎拒絕接受。後田七郎因誤傷人命而吃官司,武承休出重金買通官府和苦主將他解救出來。後來,武承休因縣官徇情枉法獲罪,田七郎殺死了叛主的惡僕、武承休的仇家和徇情枉法的縣官,自己也自刎而死。人們熟知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主題(或主題之一)就是寫朋友之義。《三國演義》寫了劉備對漢室之忠、諸葛亮對蜀漢之忠,這是忠的主題;同時也重點寫了劉關張之間的義氣。三國題材的戲曲也多歌頌忠義主題,如元雜劇《單刀會》歌頌了關羽的忠勇義氣。《水滸傳》也有忠義主題,故有《忠義水滸傳》之名。忠的主題表現爲宋江等聚義梁山是爲了“替天行道”,待機受招安,報效朝廷;義的主題是寫群雄聚義,互相依靠,同生共死。該書寫朋友之義比寫對國家之忠要生動得多,故主要體現爲義的主題——朋友之間的恩愛、情義,所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書中故事,生動體現了朋友之義的恩德本性。例如,宋江對李逵有恩,李逵尊宋江爲大哥,死心塌地追隨宋江,隨他上梁山,爲他劫法場,跟他受招安;宋江被奸臣下毒,臨死前爲了不讓李逵報仇造反,壞了自己的名聲,給李逵服毒,李逵知情後,竟然甘願與大哥同死。這裏體現了朋友之間的恩德帶有支配性和依附性。
國家領域的恩德主題體現爲忠君愛民思想。中國抒情文學中也有憂國憂民的主題,如《離騷》就表達了屈原對故國、君王的恩愛和憂思。歷代詩人多有憂國憂民的詩作,即所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如杜甫在安史之亂中寫了許多憂國憂民的詩篇,著名的有“三吏”“三別”等;辛棄疾的詞作,體現了以身許國的豪情壯志;其他一些詩人感懷身世的詩詞,也多抒發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憤懣哀思。敍事文學中的恩德主題有幾個具體的類型。其一是忠奸鬥爭題材,塑造捨生取義的忠臣形象。忠臣愛國救民,奸臣誤國害民,他們的鬥爭體現了善惡的對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故事中的君主往往是昏聵的,結局也多有悲劇性。這個題材的代表作有元代戲曲《東窗事犯》,寫奸臣秦檜陷害愛國將領岳飛的故事,譴責了奸臣誤國的罪行;還有歌頌忠臣海瑞的《海公大紅袍全傳》等。明清之際李玉的戲曲作品《清忠譜》,取材於明末蘇州市民反抗閹黨的事迹,謳歌了堅守正義、反抗奸黨的忠臣周順昌以及衆多市民的形象,宣揚了爲國爲民獻身的忠義精神。其二是忠臣良將報國題材,寫抵抗敵國的鬥爭,塑造愛國英雄形象,其間往往也交織了忠奸鬥爭。典型如《楊家府演義》《說岳全傳》等,寫楊家將滿門忠烈和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其間也雜有忠奸鬥爭故事。元代戲曲《牧羊記》寫漢代蘇武牧羊的故事,歌頌了對國家的忠誠。其三是清官愛民題材,寫清官懲治貪官、爲民除害的故事,也往往表現了社會的黑暗不公。例如,歌頌包拯的《龍圖公案》以及《蝴蝶夢》《魯齋郎》等包公戲,寫包公不畏權貴,敢於拿觸犯國法的皇親國戚開刀問斬。這裏很少正面表現君主對臣民的慈愛和恩惠,主要寫臣民的忠君愛國,說明了政治領域的恩德也是偏於報恩的,君主施恩往往是虛擬的。
《西遊記》是神話小說,其主題多有爭議。其實,它的主題是寫人的歸化的,也就是寫孫悟空接受了恩德教化,從化外之猴歸化爲人間角色,盡忠行義,最終成佛的過程。孫悟空是從石頭中生出的石猴,這個身份的寓意是,非爲人類,無父無母,沒有社會關係,不尊倫理規範,是化外之“人”。他作爲一個個人主義者任意而行,佔據花果山爲王,到東海龍王處搶來鎮海神針,下地獄塗掉生死簿,大鬧天宮,打敗天兵天將,逼玉皇大帝封“齊天大聖”,簡直無法無天。孫悟空戰敗被壓在五行山下,被唐僧救出,孫悟空感恩而拜唐僧爲師,許以護送西天取經,建立了師徒之義。同時,孫悟空又入了佛門,要遵從佛祖旨意,行佛法,這是一種“忠”(實際上是世俗社會對帝王的忠的宗教化體現)。取經成功後,唐僧弟子都封了佛界神職,悟空被封了“鬥戰勝佛”,功德圓滿。這體現了孫悟空被恩德教化,接受忠義,從化外之猴轉化爲化內之人的過程。
三 恩德的多重結構與文學主題的多重性
文學多重主題的衝突,是恩德文化的差等性導致的。恩德文化以家族倫理推廣爲社會倫理、政治倫理,而恩愛也由孝推廣爲義和忠,其間就産生了“差序格局”。文學所展現的社會生活,必然涉及家庭、社會和國家領域,也必然體現家族倫理、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文學故事中往往交織着多個領域的恩德規範,因此其思想綫索也往往是多元複合的,包括孝悌、俠義、忠良等主題。這些主題之間往往發生矛盾,從而就産生了文學多重主題之間的衝突。
首先是家族倫理內部的衝突,也就是家族成員之間不同恩德的衝突。家族倫理包括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其倫理範疇是孝;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其倫理範疇是悌;夫妻關係,其倫理範疇是節(主要對妻子的約束)。由於家長制,家族倫理以孝爲首要範疇。也就是說,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基本的、首要的,制約和規定着其他家族關係。這些家族關係,與倫理範疇之間必然會産生矛盾,如中國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婆媳矛盾,就隱含着夫妻關係與父母關係的衝突。在文學主題中,這種矛盾也體現出來,典型的是長篇敍事詩《孔雀東南飛》,體現了夫妻恩愛與對母親的孝的衝突。詩歌講述了焦仲卿、劉蘭芝夫婦恩愛有加,但由於婆婆不喜歡劉蘭芝,逼迫兒子休妻,兒子被迫聽從。休妻後,劉蘭芝投水自盡,焦仲卿也上吊身亡。按照恩德文化觀念,孝大於夫妻之恩愛,兒子必須爲孝犧牲自己的夫妻情義。但夫妻恩愛是真摯的,這種犧牲是不合理的,也是難以承受的,故焦仲卿因休妻而自盡的行爲也是對孝道的抗議。這個故事說明了家族中恩德的不合理性。
其次是家國之間的衝突在文學主題中的顯現。恩德文化以家族倫理爲基礎,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是其推廣形式,因此,家族倫理在邏輯上先於、重於社會和政治倫理,即“百善孝爲先”。但在國家領域,君主是更大的君父,並且握有強權,於是“國恩”“君恩”就事實上高於“家恩”。家與國的責任、倫理有時一致,有時又會發生衝突。在先秦,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家國一體,故儒家重孝道,爲了盡孝可以不盡忠。秦以後,大一統形成,家國一體分離,國就重於家,強調“移孝作忠”。文學作品也體現了這個矛盾,如元雜劇《伍員吹簫》就是寫伍子胥(伍員)以報家仇(建立在報家恩基礎上)廢棄對國家君主的報恩責任(以楚王不仁爲前提)。但隨着君權的加強,就不再肯定這種行爲了,對君主的報恩具有了絕對性。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之間的糾葛、衝突,也體現在一些文藝作品中。例如,流傳既久而定型於清朝道光年間的戲曲《四郎探母》,寫四郎楊延輝被遼國俘虜,召爲駙馬。他思念母親,不得成行,乞求公主幫忙。公主從蕭太后手裏騙得令箭,楊四郎得以出逃,到宋營見了母親、兄弟。爲報答蕭太后和公主的恩情,四郎又返回遼國,蕭太后問罪楊四郎,欲將其斬首,公主以死相逼,迫使蕭太后赦免了楊四郎。於是,舉家和睦如初。這個故事表達了楊四郎對故國的忠、對母親的孝,也表達了他與公主的夫妻之情、對蕭太后的感恩之情。這些恩情互相衝突,體現了恩德作爲身份倫理的內在矛盾,即家恩與國恩、夫妻之恩與母子之恩的衝突。該劇雖以大團圓結局,以報答公主和蕭太后的恩情掩蓋了對故國、家庭的背恩,但實際上並未解决這些矛盾。
再者,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之間也會發生矛盾,即社會領域的恩德與國家領域的恩德的衝突。這種衝突在文學中的體現,就是“忠”“義”之間的衝突。忠義往往是一體的,但也有區別甚至衝突。例如,《西遊記》的主題交織着忠與義,孫悟空爲了取經,降妖驅魔,是對佛祖的“忠”(這是世俗忠君的宗教體現);他保護師父,愛敬師父,又是“義”,這裏的忠、義是一體化的,孫悟空就是在忠和義的雙重倫理責任之下一路前行的。但從藝術描寫上看,義勝於忠,孫悟空對師父的愛和敬主導了其行爲,纔一路上與妖魔鬥爭,保護師父。在“三打白骨精”中,師父誤會悟空殺人,將其逐出佛門,斷絕師徒關係,孫悟空不禁灑淚而別;回到花果山後,聽到師父有難,就立刻前往解救,並且歸隊,體現出悟空對師父的情義。但對於佛祖特別是玉帝等統治者,悟空並無敬愛之心,也小有違抗、調侃,衹是不得不敬奉而已。這表明,忠的主題是虛寫的,而義的主題是實寫的。
《三國演義》中的忠義之間基本統一,如劉、關、張的結義與匡扶漢室(忠)的政治目標是一致的;劉備與關羽、張飛既是兄弟關係,也是君臣關係。但是,忠與義也有矛盾。例如,關羽被俘後,得到曹操厚待,最後放還,這是朋友之恩。後來曹操赤壁大戰敗北,被關羽截在華容道上,但出於報恩,關羽放了曹操。這就是取朋友之義(對曹操的報恩)而背國家之忠(對蜀漢的忠)。劉備與關羽是結義兄弟,情同手足;同時也是君臣關係,這種忠、義關係由於關羽的死而發生衝突。關羽被殺,劉備爲了報仇,不顧國家利益,興兵伐吳,導致兵敗身死,也是取朋友之義而背國家之忠。可以看出,在忠義矛盾中,《三國演義》認爲義要服從於忠、忠是高於義的,不讚成以朋友之義壓倒國家之忠。
《水滸傳》從另一個角度展示了忠義矛盾,通過忠對義的否定和義對忠的犧牲的描寫,有肯定義的傾向,對忠則有所否定。本來,群雄聚義,是爲了替天行道,即義是爲了忠,但梁山聚義本身,還是由於君主重用奸臣,天下無道,逼上梁山,故義的合理性不在於忠,而在義自身。作品寫梁山弟兄的義氣,體現出兄弟友愛,這已經打破了招安的合理性。由於忠高於義,故宋江一味要接受招安,但招安後,由於奸臣的陷害,卻導致結義兄弟死的死、殘的殘、流亡的流亡、出家的出家,多不得善終。宋江自己也被奸臣毒死,造成了悲劇結局。特別是宋江臨死毒死李逵,更表明了宋江棄義而就忠的悲劇性。這個結局表明了個體情義與國家責任之間的衝突。小說雖然宣揚忠義,但人物的悲劇命運卻導致了對義的肯定和對忠的否定。
四 中國文學對恩德主題的突破
中國文化把人置於無所不在的恩德體系之中,導致個體的獨立性被取消,人成爲施恩或報恩的主體和對象。恩德的實踐,往往需要人犧牲自己的某些權利和自由。孝要求爲長者奉獻,義要求爲他人奉獻,忠要求爲君主做出奉獻。而這種犧牲,正是恩德主題文學歌頌的對象。但恩德對人的壓制,必然引起反抗,從而導致對文學的恩德主題的反撥。
首先,感性慾望的反抗突破了恩德规范。恩德是由理性(恩義)主導的,對人的感性慾望是一種壓制,此即所謂“以理制慾”;但理性的壓制必然帶來感性的反抗,這種反抗也體現在文學之中。性慾是人的最強烈的慾望,但中國文化對性慾衹是有限的肯定並有所限制——既肯定“食、色,性也”①《孟子· 告子上》(北京:中華書局,2007)。,又把慾望置於理性之下,即《詩經· 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儀”。這個“禮儀”,就是恩德規範,不可逾越。體現在中國文學,一方面反對誨淫誨盜,另一方面也難以根除慾望書寫,因爲慾望畢竟存在於深層心理結構之中,越壓迫、禁止,就越強烈地表現出來。因此,一些作品就會産生明暗兩個主題,一個是表面上符合理性的道德主題,一個是潛在的違背理性的慾望主題。道德主題雖然冠冕堂皇,但缺乏人性的內涵,而慾望主題雖然不登大雅,但卻符合人性而富有吸引力。早期詩歌如《詩經》以及後世的民歌,多不避感性,甚至有一些赤裸裸的慾望書寫。到傳統社會末期,慾望膨脹,衝破倫理束縛,一些作品力圖以報恩爲名使得慾望合法化。例如,《喻世明言》中,《閑雲庵阮三償冤債》寫閨閣小姐陳玉蘭向阮三郎報恩酬情,《衆名妓春風吊柳七》寫名妓謝玉英向詞人柳永報恩酬情;《警世通言》中,《錢舍人題詩燕子樓》寫歌妓關盼盼向禮部尚書張建封報恩酬情;《醒世恒言》中,《賣油郎獨佔花魁》寫花魁娘子莘瑤琴向賣油郎秦重報恩酬情。這些故事雖然符合了報恩倫理,但不符合正統的男女關係規範,實際上把慾望合法化了;有不少還涉及狎邪、冶遊,更越出了禮教規範。還有一些故事,如《聊齋志異》寫善良的妖魅化身美女與男人發生性愛,本來是違反倫理的,屬於宣淫,但由於女主角非爲人類,就避免了直接觸犯道德規範,而滿足了讀者的感性慾望。還有才子佳人小說,往往寫郎才女貌、因緣巧合而結良緣,實際上是在禮教框架內滿足人的潛在的性愛慾望,因此也屬於慾望主題。這個類型的小說有《玉嬌梨》《平山冷燕》《好逑傳》《金雲翹傳》《定情人》《雪月梅傳》《駐春園小史》《鐵花仙史》等。
還有一些作品,是以道德主題掩飾慾望主題,以《金瓶梅》最爲著名。表面上看,該書具有道德主題,作者開宗明義寫了抨擊“酒色財氣”的《四貪詞》,勸誡世人遵守道德,其對西門慶縱慾身亡的描寫,也似乎意在暴露和批判淫邪行爲,提倡貞潔自律;但是,其繪聲繪色的性愛描寫,透露出作者的真實趣味就是渲染性放縱的快樂。該書之所以難以禁絕,也在於其巨大的感性魅力,它帶來了假想的性滿足。感性的快樂衝破了書中的道德教化,從而也就解構了道德主題。西門慶與潘金蓮等人的淫亂,完全違反了夫妻恩義,慾望衝破了恩德,形成了一個隱性的慾望主題。類似作品還有“三言二拍”等,其中一些故事津津樂道地描寫不倫的性愛故事,末尾再予以譴責,而且多以惡報結尾。然而,這些理性批判不能掩蓋其感性吸引力,反而被其解構。更有甚者,幾乎完全拋開理性,赤裸裸地進行慾望書寫,如《肉蒲團》《綉榻野史》《燈草和尚》《品花寶鑒》《鬧花叢》《株林野史》等誨淫誨盜的色情文學作品,都是以慾望主題來解構恩德主題的。
由於明代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形成,倫理觀念也有所改變,體現在兩性關係方面,就是對性愛的寬容和對貞節規範的突破。《喻世明言》中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寫蔣興哥對出軌的妻子的寬容,離婚後復合的故事。它沒有把王三巧兒寫作潘金蓮一類人物,而是作爲正面人物予以理解、同情;蔣興哥也是寬容大度,不忘舊情,最終夫妻團圓。這就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婚外情,破除了夫婦恩德的禁忌。
其次,是文學的社會批判主題否定了恩德文化。儘管恩德文化是主流,統治了人們的思想,恩德也成爲文學的基本主題,但由於恩德文化本身的缺陷,以及社會生活的潰敗,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在文學中揭露、抨擊社會的黑暗和道德的淪喪,從而産生了社會批判主題。這些文學作品通過社會批判,也暴露了恩德文化的虛假和不人道,從而否定了恩德文化,如宋元話本小說《錯斬崔寧》《簡帖和尚》《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抨擊社會黑暗,元雜劇《竇娥冤》暴露社會黑暗、司法不公,明清小說“三言二拍”、《聊齋志異》《鏡花緣》也有不少揭露和批判社會黑暗、人性墮落等內容。尤其是《聊齋志異》中的《促織》《席方平》《紅玉》《商三官》《向杲》等篇,書寫了世間的黑暗和主角的反抗,多以悲劇結尾,從而揭穿了傳統價值的虛僞。具有社會批判主題的典範作品是《儒林外史》,它深刻批判了科舉制度對士人的束縛、腐蝕,對士林的腐敗做了揭露,例如周進、范進等的仕途悲劇,遽駪夫、匡超人、馬二先生等人格的毀滅,還有婁四、杜慎卿等假名士的沽名釣譽,從而否定了所謂報國恩、君恩的仕進之路的合理性,揭露了恩德文化虛假性。此外,該書還揭露了恩德文化“以理殺人”的本性,如鼓勵女兒殉夫的王玉輝,就是中了貞節觀念的毒,而喪失了親情、人性。
以理想化的烏托邦世界對抗現實世界的作品,也體現了對恩德文化的消極反抗。例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搜神後記》中的《桃花源》《韶舞》《袁相根碩》《穴中仙館》,《幽明錄》中的《劉晨阮肇》《黃原》等,寫了超然世外、沒有王法管制的世外桃源,表達了對恩德文化的逃避心態。
此外,還有一些發興亡感慨的史詩性的作品,體現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也溢出了忠的主題,如《三國演義》《桃花扇》等。按照傳統觀念,國家的命運是由天命決定的,而天命體現爲民心,即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①《尚書· 泰誓》(北京:中華書局,2007)。,因此,忠君愛民就是天道的體現,也就會得到天下。但是,在《三國演義》中,雖然以君明臣忠的蜀漢政權爲正統,但最後的結局卻是蜀國、吳國失敗,曹魏一統天下,最後政權歸於司馬氏。這個結局就在人道(忠義)主題之上確立了天道主題,否定了有德者得天下的觀念,體現了天命無常、人事無功的思想,從而否定了天恩、人恩的歷史合法性。《桃花扇》描寫了朝代的更替,通過興亡之思,表達了對家國命運的思考:“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②〔清〕孔尚任:《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第1頁。,其中包含着對忠君、愛國的失望。
最後,是文學的審美意義對恩德主題的超越和批判。恩德建立在恩情、恩愛的基礎上,但恩愛並不是純粹的愛,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愛;恩義作爲倫理責任束縛、壓抑了愛的感情。人不是倫理性的實體,而是追求自由的生物,有愛的要求。他雖然不得不依存於社會關係和倫理體系中,但這種不可遏制的自由和愛的要求一定會表現出來;它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但在文學藝術中可以伸張。文學不僅有現實層面,也有審美層面。文學的現實層面體現着特定的倫理觀念,因此,中國文學有恩德主題。同時,文學的審美層面體現着自由和愛的要求,它超越意識形態,突破恩德主題,恢復了人的自由天性。中國文學雖然被恩德主題主導,但優秀的作品仍然突破恩德主題,體現了審美價值也就是人的價值。這樣,就在恩德主題之外,産生了超越恩德的審美主題。審美主題多以純真的愛來衝破恩德,體現着人性的光輝。它區別於慾望書寫,升華爲超理性的自由精神,從而在恩德主題之上産生了審美意義。
一些帶有神話色彩的志怪小說,以超現實的筆法表達了對自由的愛的嚮往和對恩德文化的反抗。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寫了人與神、人與鬼之愛,這種愛戀不受禮法約束,體現了自由的理想,如《搜神記》中的《紫玉韓重》《天上玉女》等,《幽明錄》中的《賣胡粉女子》《旁阿》等。唐代和宋金元的志怪小說中也有愛情主題的作品,如沈既濟的《任氏傳》、陳玄佑的《離魂記》、李朝威的《柳毅傳》等。《聊齋志異》繼承和發展了志怪傳統,寫了許多愛情主題的作品,其中《阿寶》《連城》《瑞雲》《喬女》《白秋練》《連瑣》《晚霞》《嬰寧》《小翠》《狐諧》等,謳歌了人鬼、人狐之間的美好愛情,描寫了一些善良、熱情的女性形象,突破了恩德文化中的女德桎梏。
傳奇小說則以浪漫的精神書寫了愛情主題,突破了禮法限制和束縛。唐傳奇如蔣防的《霍小玉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元稹的《鶯鶯傳》,宋傳奇如《嬌紅記》寫自由的愛情追求與現實的衝突所造成的悲劇,明傳奇中大量的愛情題材作品均謳歌了大膽、熱烈、執著的愛情。
話本小說源自民間,更大膽地突出了愛情主題。宋元話本小說《碾玉觀音》《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等寫了自主愛情的悲劇,《快嘴李翠蓮記》則寫了個性鮮明的女子與家庭禮教衝突産生的悲劇。明代的“三言二拍”體現了市民階層的愛情觀,進一步打破了傳統禮教。如“三言”中的《賣油郎獨佔花魁》《玉堂春落難逢夫》《宋小官團圓破氈笠》《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二拍”中的《通閨闥堅心燈火》《李將軍錯認舅》《莽兒郎驚散新鶯燕》等。此外,還有《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謳歌了妓女杜十娘追求愛情受騙的悲劇。
詩詞、戲曲也多有愛情主題。唐代白居易的《長恨歌》與元雜劇《梧桐雨》、清戲曲《長生殿》出自同一題材,都有雙重主題——“愛情”與“忠”。前者是對唐明皇與楊貴妃愛情的謳歌:兩人的愛,體現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的真情,令人同情、惋惜。後者是對君主負有的國家責任的強調,對唐明皇因私情誤國誤民的譴責。這種互相矛盾的主題,體現了恩德(國家責任)與愛的衝突。元雜劇《西厢記》也寫了張君瑞與崔鶯鶯自由戀愛的故事。由於私定終身,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違背倫理,不具有合法性,於是作者就以另外一種恩德爲其開脫,建立合法性,這就是張生救了崔鶯鶯一家,對崔家有恩,而且獲得了許婚的諾言。但這個理由仍然不夠,於是又有了高中狀元,奉旨完姻,就彌補了私通的道德缺失,而具有了充分的合法性。由於用了這些曲筆,表達了對男女自由結合的肯定和謳歌,從而破除了恩德主題,而建立了愛和自由的主題。此外,元雜劇《墻頭馬上》也正面描寫了“淫奔”故事,謳歌了愛情的真摯,突破了傳統禮法道德。《倩女離魂》寫痴心女鬼魂與心上人“私奔”,終於還魂成親的故事,歌頌了對愛情的執著。《牡丹亭》寫杜麗娘的愛情覺醒,與柳夢梅夢中相戀,死而復生,最終團圓的故事,謳歌了真摯的愛情。明代高濓的戲曲作品《玉簪記》寫亂世中書生潘必正與尼姑陳妙常自行結合,最終潘復試得官,迎娶陳妙常。孟稱舜的《嬌紅記》寫王嬌娘與“同心子”申純正相愛,雙雙殉情的故事,堪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清代黃圖珌的《雷峰塔傳奇》寫蛇精白娘子化身爲人與許宣相戀,後被法海識破,把白娘子鎮壓在雷峰塔下,許宣削髮爲僧。這個故事體現了情與法理的衝突,法海代表的法理摧毀了真實的愛情。
具有審美主題的典範性著作是《紅樓夢》。它的主題不是傳統文學的恩德,而是自由和愛,因此魯迅纔說:“总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①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國小說史略》(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第206頁。《紅樓夢》也寫了恩德,如賈母對寶玉、黛玉的恩愛,賈政對寶玉的嚴厲管束也是出於恩愛;在這種恩愛的基礎上,寶玉就承擔了對家族盡孝的責任,如走“仕途經濟”之路,聽從家長安排的婚姻等。但作者並不認同這個恩德,而是描寫了與此相背離的真愛和自由追求。寶玉出自自由和愛的天性,不滿足於家族給予的富貴生活,也不接受長輩安排的仕進之路和金玉良緣,而是追求自由的人生和真實的愛情,爲此背棄了父母之恩、孝順之義也在所不惜。所以,《紅樓夢》樹立了一個空前的主題,就是自由和愛的主題。這個主題完全背離了恩德主題。表面上看,它寫了三個綫索,一個是寶黛愛情的綫索,一個是大觀園女性命運的綫索,一個是大家族興衰的綫索,這三個綫索構成了一個社會人生的大悲劇。一是愛情追求與家族責任的衝突導致的悲劇。寶玉不顧一切地愛上了黛玉,但黛玉不符合傳統的賢妻良母的標準,因此,愛情不能實現,黛玉含恨而亡,寶玉出家。二是恩德文化下婦女命運的悲劇。大觀園女性雖然個個花容月貌,心地單純,是“水做的骨肉”,但在傳統社會和恩德文化之下,衹能以身報家族之恩,於是衆芳零落,成爲宗法禮教的犧牲品。這個悲劇,體現了作者對被壓迫女性的同情,譴責了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禮法。三是恩德文化下大家族的命運悲劇。榮寧二府雖然依靠元妃帶來的皇恩鼎盛一時,但最後仍然因腐化而敗落,因失寵而被抄家,由此揭示了恩德文化的虛僞、腐朽和傳統社會的黑暗、沒落。總之,小說書寫了傳統社會末世的新人追求和悲劇,表明了對傳統人生道路的批判。“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個以佛學的“空”概括的人生悲劇,表達了作者的悲憫之情,是一種大愛的主題。可以說,《紅樓夢》書寫的是自由和愛的追求與恩德文化的衝突,最徹底而決絕地確立了自由和愛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