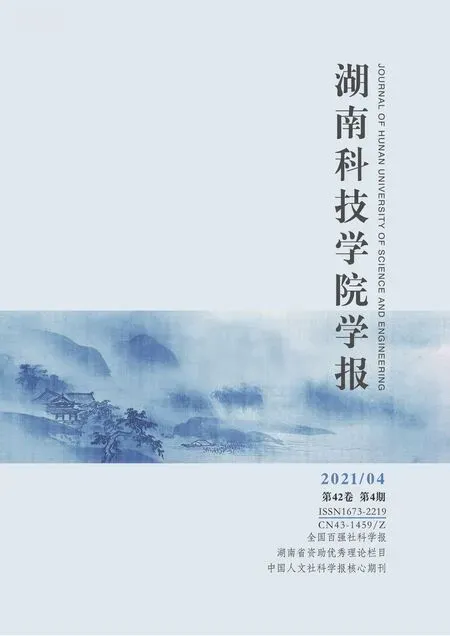论史蒂文森情感表达主义与道德分歧问题的解决
陈子衿
论史蒂文森情感表达主义与道德分歧问题的解决
陈子衿
(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情感表达主义是当代西方元伦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其对于道德判断的非理性因素的阐说,挑战了理性主义传统支配的思维,极大地丰富了元伦理学思想体系。但从创立以来,情感表达主义一直难以摆脱有关道德实践方面的诸多质疑,其中亟待解决的便是道德分歧问题的挑战。文章介绍了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思想与对道德分歧问题的论述,并从理论联系实际,解释了当今社会解决道德分歧问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反思了情感表达主义与道德分歧问题对当下道德教育的启示。
情感表达主义;道德分歧;道德共识;道德教育
一 道德分歧问题的由来——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
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一直是困扰着西方哲学界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世纪,休谟在《人性论》中就对“实是”(is)如何推导出“应是”(ought),价值判断如何从事实判断中推出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质疑。不同于事实判断,道德判断长期因缺乏科学、理性的方法而难以得到确证,甚至被质疑作为知识的可靠性与合法性。美国哲学家查尔斯·史蒂文森(Charles Stevenson)在一文中开篇便提出疑问:“当人们对某个事物的价值出现分歧(一个认为它是好的或正当的,而另一个认为它是坏的或错误的)之时,他们的分歧通过何种论证或研究的方法可以得到解决?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将其解决,或者还需要其他别的方法,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合理的解答?”[1]史蒂文森认为,要想寻找科学的理性的解决道德分歧(实现道德共识)的方法,首先必须阐明道德分歧的性质。而为了回答“有无科学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道德分歧问题”之问,史蒂文森改进了传统的情感表达主义理论。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是一种基于道德语言实际用法语义分析的道德语义学理论,继承了艾耶尔非认知主义的情感表达主义理论,对道德语言中非理性部分的肯定,并主张道德分歧的解决必须通过弄清道德论说的意义入手。根据史蒂文森,伦理学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的部分原因便在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想探寻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甚至在不知道“针”为何物的情况下还在问“海底有针吗”。
根据陈真教授的观点,西方哲学传统上将一个词的意义看成是它的所指。但这种意义理论只能解释语言的命题意义,无法解释语言的祈使或情感表达等其他的意义[2]。而对于道德语言而言,这种传统的意义理论显然是不够的。根据艾耶尔此前的研究,道德语言中具有非理性的、情绪的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非理性部分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除了语词的静态意义,即记录并传达信念之外,史蒂文森还划分出了语词的动态意义,即发泄情绪或影响他人这两个可相互叠加的层次。对于一个道德判断的两层意义的分歧,都有可能导致道德分歧的出现。考察下列两组分歧:
A1:甲认为丙乱扔垃圾。
A2:乙认为丙没有乱扔垃圾。
B1:甲认为丙乱扔垃圾是不道德的。
B2:乙认为丙乱扔垃圾是道德的。
史蒂文森认为,这两组分歧的不同之处在于,A组代表的是信念分歧,基于双方对某一客观事实的不同认知。B组代表的是态度分歧,基于双方对某一客观事实的不同感性态度。即使两人对“丙乱扔垃圾”的事实认知是统一的,但由于两人对于道德与否的标准不一,仍可能造成态度上的分歧。
道德分歧中既包含了信念分歧,也包含了态度分歧。我们对于某一道德事件态度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对该事件具备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基础上,即使我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这种了解可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另一方面,态度分歧的解决是道德论辩的终点,一切道德论辩的目的都是说服对方转变其道德态度。纠正其道德信念虽然是一个重要方法,但并非最终目的。换言之,即使双方抱有不同的道德信念,也有达成道德态度统一的可能。就举例而言,在上文提到的分歧中,甲乙就丙是否乱扔垃圾,以及乱扔垃圾是否道德的问题产生了分歧。甲若要说服乙,首先可以通过现场录像等方式,证明丙确实有乱扔垃圾的行为,从而解决信念分歧。再通过道德论辩,说服乙相信乱扔垃圾是不道德的。而另一方面,即使乙不相信丙乱扔垃圾的事实,与乙接受“乱扔垃圾是不道德的”的道德态度并不冲突。
因此,信念和态度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态度分歧是道德分歧的主要方面与常见表现形式。也正是态度分歧的存在,才使得伦理问题有别于科学问题,无法使用实验方法解决。人们对于重力的认知可以通过斜塔铁球实验形成无可辩驳的共识,但人们的道德分歧(尤其是态度分歧)绝对不可能通过一次真实的“电车实验”达成统一——更何况很多伦理学的思想实验本身也无法在现实中操作。
因此解决道德分歧需要从信念分歧与态度分歧两个方面,尤其是态度分歧方面入手。史蒂文森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科学方法依然可以在解决道德分歧方面发挥作用。根据道德分歧的三种不同情况,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道德分歧:
第一,对于争论一方的立场中包含逻辑上的不自洽所引起的道德分歧,可以采取理性的非心理的逻辑方法加以解决。这种不自洽往往是争论者根本的道德态度与其具体道德态度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不自洽,或在应用根本性的价值原则时出现逻辑的不自洽。例如某人主张功利主义原则,却又在电车难题中反对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又如某人主张环保主义,却又对乱扔垃圾的行为熟视无睹,便是逻辑上的不自洽。此时只需指出对方的逻辑错误,便可以使对方转变道德态度。
第二,对于争论一方事实信念的分歧所引起的道德分歧,可以采取理性的心理方法解决这类仅因事实分歧所产生的态度分歧。如上文所述,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可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而这种片面错误的信念往往带来错误的道德态度。因此,当我们进行道德论辩的时候,我们应该考察导致对方道德立场的信念(事实经验)是否是正确且全面的。例如新疆棉事件,部分国外媒体在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便对新疆所谓“强制劳动”进行道义上的抨击。无论对方出于恶意还是无知,针对此类道德分歧,最好的解决方式是阐明不存在“强制劳动”的事实,所谓道义上的指责也就失去了事实承载。对于一个拥有理性的论辩者而言,如果意识到自身信念的错误,会对其道德态度的转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三,对于根本态度的分歧所引起的道德分歧,即争论双方即使在所有相关的事实问题上达成了信念共识,但依然无法说服对方改变自己的态度导致的分歧,史蒂文森认为,无法通过理性的方法——逻辑或经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因而只能采取非理性的纯心理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利用人们的移情心,依靠语言的情绪力量直接去打动对方。换言之,前两种方法属于“晓之以理”,而此方法属于“动之以情”。
史蒂文森的理论在注重道德判断非理性因素的优点的基础上,加入了科学理性方法对解决道德分歧问题可能性的探索,较好地解释了部分道德分歧解决的可能性,也承认了部分道德分歧解决的困难。可以认为是一种改良的、温和的情感表达主义(Emotivism)。
二 道德分歧解决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人们对于道德的理解与感悟,往往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其所处的纵向历史阶段、横向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也包括人自身的性格、信仰、成长经历、受到的教育等具体的个人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影响共同作用,才形成了千人千面一般,每个人独具特性的道德心理。就如同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相貌,每个人也具备独特的道德心理。这种道德心理的特殊性体现在对各种道德情景作出的不一而足的道德判断。例如:伦理学中经典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牺牲一个人的性命来拯救五个人是否道德?这一问题争论至今,却仍然没有一种通行的“标准答案”可以说服所有的人。而我们生活中面对的具体道德问题,更是比抽象的思想实验复杂得多。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针对某一涉及道德或者价值问题的社会事件或者日常琐事,出于各具缘由的道德心理,论辩双方针锋相对,似乎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正因如此,有以英国哲学家艾耶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道德分歧是不可能通过科学、理性的方法解决的。“某事是道德的”与“某事是不道德的”本质上并无对错之分,都只不过是论辩双方的道德立场的情绪化表达。艾耶尔更是形象地将这种论辩形容为“谩骂(abuse)”,以描绘出这种论辩的非理性本质。
但是,我们对于伦理学的期待不应只是对现实的观照。伦理学作为一门有引导和教育意义的社会科学,更应该起到教人向好向善的作用,承担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与生活幸福感的重要责任。换言之,伦理学应当具有现实意义之上的价值意义。道德分歧的解决,或者说道德共识的实现与积累,是凝聚社会的共同价值,构建社会整体道德观念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无法达成任何道德共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都是自我、独断的,那么整个社会也将宛如一盘散沙,社会凝聚力与“核心价值观”也无从谈起。因此,即使在现实层面,道德共识的实现似乎是困难重重的,我们也应当努力追寻其实现的可能。
另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道德共识的实现虽困难,但并非绝无可能。人类在道德共识的达成问题上绝非一无所成。小到以“不应杀人”“不应偷窃”等具体独立的道德共识,大到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以笃信、仁爱为核心的基督教伦理思想等等,历经漫长的考验而熠熠生辉至今。虽然随着时代变化,这些思想精神的具体外延也产生了诸多变迁,但是其核心骨干部分依然被主流大众所接受。因此,我们对于道德共识的预期,不是事无巨细的,在任何细节琐屑的问题上统一道德判断;也不是一个不差的,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统一道德思想。而是在尊重个性化差异化的道德心理的前提下,对于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问题,例如尊重生命、尊重自由等问题,凝结人们普遍认同的正向的社会道德共识。这一伦理学的基本任务,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三 情感表达主义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显然,能否很好地凝聚道德共识,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前文所述,道德共识的实现与积累,是凝聚社会的共同价值,构建社会整体道德观念的必要条件。社会道德教育的本质,即是引导公民个人的道德观念向优秀道德观念学习,与社会核心道德观念达成共识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于情感表达主义、对道德分歧问题的研究,并非纸上谈兵的空洞文字游戏。而是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社会意义的哲学反思。
从道德教育受众的角度,我们可以将目前的道德教育分为两类:针对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道德观念的成人的道德教育,以及针对尚处于道德懵懂时期的孩童的道德教育。两者分别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现在与将来,因此针对两者的道德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前者的重点在于“理性纠正”,后者的重点在于“感性塑造”。一般来说,前者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具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也因此更容易陷入柏拉图的“囚徒困境”,将一些自身的经验总结奉为真理,对于自己形成的“印象”坚信不疑。因此,对于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应该主要通过非心理的逻辑方法以及理性的心理方法等理性方法,通过揭露其逻辑上的矛盾,丰富其对事实的认知,纠正其信念中的错误,引导其自然地矫正不正确的道德态度。而对于孩童的道德教育,则应该把握其心智尚未成熟的特点,运用非理性的纯心理方法,注重优秀道德观念的整体塑造。由于认识能力尚且不足,应当主要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培养其道德观:即使孩童对于何为“诚实”“正义”“友善”等概念的理解尚且模糊粗浅,也应当使其相信这些美德是“好”的,在感性态度上倾向于这些美德以及拥有这些美德的人,并认识到自己应该努力获取这些美德。
另一方面,应当意识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一些具有道德性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论辩,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共识达成的过程,以及社会道德观念自我运动自我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这些论辩的过程也会对我们的道德观念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来自于信念的丰富,也来自于态度的移情作用。例如对污蔑国家形象的言论的批评,可以增进我们的爱国情怀;对抗疫工作者先进事迹的歌颂,可以增进我们的奉献精神等等。尤其在社交网络发达便捷的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是发声者与倾听者。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对他人的道德观念产生影响,也时刻受到他人的影响。作为发声者,应当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保证传播的事实的真实性并避免情绪的不当宣泄;作为倾听者,则应当提升自身的识别能力,明辨是非善恶,在众说纷纭中依旧保持自身清醒的判断,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一些道德问题上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谩骂”的状态。因此,应当区分道德问题的“硬核”与“保护带”,对于核心的道德问题,如涉及人的生存、自由、尊严等基本问题,应当设立坚固的城墙保护,即凝聚统一而不可逾越的社会道德共识;而对于繁多的难以统一的“道德难题”,则应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既尊重社会的道德传统,也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与道德的动态更新;既尊重多数人的道德心理,也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倾轧。
[1]Charles Stevenson.Facts and Values: Studies in Ethical Ana- lysi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1.
[2]陈真.事实与价值之间:论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J].哲学研究,2011(6).
2021-01-22
陈子衿(1997-),男,湖南长沙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
B822
A
1673-2219(2021)04-0070-03
(责任编校:呙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