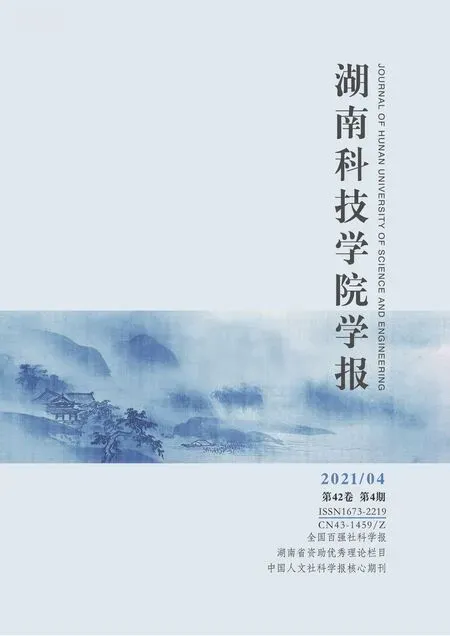君子何以解“困”兼论唐宋诗歌风格成因——以魏了翁、柳宗元为中心
黄科程 胡悦玥
君子何以解“困”兼论唐宋诗歌风格成因——以魏了翁、柳宗元为中心
黄科程 胡悦玥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君子以“修身治天下”为己任,其实践之路却往往有不少波折,贬谪于穷苦之地更是时有发生。面对此番 “困”境,作为贤人和圣人的两种君子人格有着上升式分别的解脱之道,通过以南宋魏了翁和唐朝柳宗元在“困”境中所作的诗歌为中心,来一窥两种贤人路数的超脱“困”境之道。而这两种路数在作为圣人的孔子处则是将其肯定之后再否定,以此得到最高的天人境界。同时两种贤人的解“困”之道变化也与唐宋诗歌风格转变的内在路数相契合,深植于人如何处世的两种“气质性”的存在。
柳宗元;魏了翁;主客体;诗歌;君子品格
君子之“困”是古代知识分子常有发生的生活境遇,古人仕宦于天子难免会因为各种缘由而被贬谪至穷苦之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古籍的训习之中从一开始就对人生走向有了一个大致的脉络把握,“达”与“穷”不过是一段直线上的两个点所构成的不同线段,以天下与此身为体,以“兼济”“独善”为用,看似因时而变的不同人生际遇实则是体用一源的整体。问题是在于当心志、筋骨、体肤及其所为在接受人生的磨练之时,体用之间在感官上感受到明显的割裂之时,主客体之间看似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与柳宗元同为八司马之一的凌准便在被贬为连州司马之后,又逢至亲不断离其而去,最后双目失明终老于桂阳佛寺,此番际遇不可不畏凄惨。如此这般饱受打击的人生际遇即便是圣人也难以避免,这是不可抉择的。孔夫子虽没有被贬谪,但几十载颠沛流离,周游列国被人嘲笑如丧家之犬,晚年其子孔鲤,其徒子路、颜回都先后离其而去,先后失去至亲之人、陪伴最久和最喜爱的徒弟,但夫子并未隳其志,没有如俗语那般“向生活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依然贯彻其在川上说的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管前方困境如何,处世之道依旧不偏不倚,秉持忠贞之志践行先圣之道便可“天不丧斯文”,但是贤人和圣人之间还是存有差别,尤其是在这困境之中更能一窥君子人格的两种不同解脱之道,呈现出不一般的精神际遇。
南宋魏了翁在理宗宝庆元年(1225),以“封章谤讪”“朋邪谤国”“欺世盗名”罪名,落职夺三秩,谪居靖州,于渠阳困境中作诗二十五首,其诗内容与唐朝贬谪之诗相比具有不同之处,本文试图通过援引唐朝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所作的贬谪诗与魏了翁《渠阳集》的诗歌进行比较,从主客体二者的对立之中阐发两种君子人格于困境中晕染出的生命色彩。
一 贤人之困:主体与客体的倾向性
(一)魏了翁:立足主体的消解之道
渠阳为宋时县名,“初为渠阳县,又为渠阳砦,又为渠阳军。北宋元丰四年,以贯保砦、托口砦、小由砦、丰山砦四砦设为渠阳县,六年,移诚州治所到渠阳县”[1]2。北宋年间,又将诚州改为我们现熟知的靖州。其自己描绘人口凋零的景象:“靖为郡百二十七年,布髽跣足之风,未之有改。城中不满四十家,气象萧条,盖可想见。”(《渠阳集·答苏伯起》)[1]42寥寥数文可见当时靖州的凄凉之景,况且当是时还有不少世居于此地的南蛮不断侵扰此地,以赵瞻、良肱、唐义问为首的大臣们更是屡议弃此地。“靖为天下穷处,其蕞陋又在峡郡下,而士风不恶,民俗亦淳,时和岁丰,则物贱如土”(《渠阳集·答任总干》)[1]14可以进行相参照。魏了翁(1178-1237),《宋史·儒林传》记载道其“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2]9507,可见此人年少时天赋甚高,卓越于众人,并且道学的影响在“庆元党禁”之后虽不能在官方背景下进行宣传,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思维生成,早已深入民间的道学也在慢慢汇聚为一股舆论武器,环境较之前已有所松动。“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授佥书剑南西川节度使判官厅公事,尽心职业。”[2]9508其进仕之心与一般儒生无异,可惜因在科举中谈及道学,本为殿试第一的他因此被波及为第三,由此可以看出魏了翁的风骨注定其既然坚定了道学为圣学所传,那必然会一往无前将其贯穿一生。魏了翁作为朱熹之后的一大儒,为道学在之后几百年的官方地位加上了重量级的砝码。嘉定八年(1215)时,魏了翁上书为四先生请谥,“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赐爵定谥,示学者趣向。朝论韪之,如其请。”[2]9509作为道学宗祖人物的北宋四子,官方的这一肯定行径,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对于魏了翁而言更可对道学尊统接续,一举奠定其在道学坐标系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早已在江湖之上享誉已久的道学至此可高居庙堂之上,这对于潜心于此学的广大学子而言,天人之间的隔阂方能被打破。但魏了翁被贬渠阳的罪名也与此有关。南宋的台谏大多是趋炎附势的当权者走狗。这帮人故技重施,攻击道学实为伪学,又借谐音,自娱自乐地称魏了翁为“伪君子”,与其并称的真德秀则为“真小人”。穷山恶水和诬告陷害是魏了翁所处“困”境之下的两大客观因素,作为贤人的君子品格便须在此设法解脱精神上的苦恼,不断修炼其身,以期日后方能“兼济天下”。诗歌作为古代知识分子抒发心中郁结之情的良药,最能在此时此地窥探贤人的精神际遇。
古时士人遭逢贬谪,比起对地方的振兴教化而言对他们的惩戒和政治斗争的意味更为浓郁。对于书生而言时间,是这段旅途最不确定的因素,如苏轼就死在从海南回京的路上。前路未卜和满腔抱负无处可施是被贬谪者精神世界的两条线索,但是从其对立面上来说远离庙堂之繁琐也更能发掘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魏了翁的诗歌中说:“蛮徭虎豹断行人,小市寒城净如水。驩传有客闯然来,㩜衣视之吾兄子。云从诸侯贡,往备天子使。来时吾父为我言,女之靖州问安否?靖州苦好修,女从得师友。世方白首声利场,父绍子承乃如此。柳阴花影春风香,喜极无言澹相对。家学既尔殊,天资亦云美。自淹寂寥无可赠,赠以中一言止。吾闻古之人,仕学皆为已。上不可欺其君,下不忍虚其类。此岂有为然,凡以自靖耳。我之行止命于天,上下四方难豫拟。且将自靖献于君,无限功夫归语尔”(《渠阳集·兄子髙斯得赴廷对》)[1]5。这首古体诗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直白易懂,没有太多意境供读者玩味,作为一首叙事说理诗简明的告诉你在这穷乡僻壤之中,他的兄弟履行公务途中来慰藉这一方灵魂,给予的主要是父子兄弟之情,离不开日用伦常,回应的主要是天道人伦,脱不得君臣大义。“说理”是宋诗的核心所在,即便是朱子的千古名句“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也谈不上是精神深处的意境,而是理性不断向周遭发问引发的思考。不断在活动的是人的理性思考,是人之作为主体的忧患意识,这是无源之水,可以说是继承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理念映射,但是两者之间也还是有差别,直白的道理和直观的生命从诗歌文字中带给人的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以柳宗元为中心论述的唐诗,则是另一种君子排解“困”境的路数。
(二)柳宗元:依托客体的排忧之法
相较于魏了翁而言,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声名更为远扬,其在永州时所面临的处境则更为险峻一些。首先永州此地在古时的险恶无须赘言,凡是完成了素质教育的学生对永州总能在眼前浮现那一句“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这得益于教科书将《捕蛇者说》收入其中。柳宗元被贬于此地则是因为投身于一场富有争议的政治运动。柳宗元(773-819),“其先盖河东人。从曾祖奭为中书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时。”[3]3736其父“佐郭子仪朔方府,三迁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贬夔州司马。还,终侍御史”[3]3736。虽然其祖辈曾位列相位,但到他父亲的时候已经是身处普通官僚家庭了,其所受的也是唐朝典型士大夫子弟教育,他自己的资质也不平常,新唐书说他“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3]3736对于柳宗元而言,在他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着重振家门的理想,而在他年纪尚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政治机会摆在了眼前。“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3]3736柳宗元结交了王叔文政治团体,较同辈而言以不够深厚的资历成为郎官,这是违背了当时官场秩序的,年轻气盛的人以一种在当时人看来显得急功近利的方式来施行自己“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可惜随着顺宗身体每况愈下,这场“永贞革新”运动也随之结束,柳宗元也成为了其对立面重点打击的对象,“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3]3736
相较于永州恶劣的生活环境而言,更让其揪心的是大量流言蜚语的攻击。他自己说“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移,嚣囂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雠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柳宗元集·与萧翰林俛书》)[4]798。但他又渴望从这囚牢中获得解脱,“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余润”(《柳宗元集·与萧翰林俛书》)[4]798,柳宗元从未放弃过自身的政治理想,可是又不得不在其认为复杂的环境中等待下去,这样的一种矛盾心理促使他投身于自然山水中,将主体的思想渗透进客体中,使客体绽放出高于现象界的审美情趣出来,这就是他的文字了。“南楚春侯早,馀寒已滋荣。土膏释原野,百蛰竟所营。缀景未及郊,穑人先耦耕。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农事城素务,羁囚阻平生。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柳宗元集·首春逢耕者》)[4]1212这首五言古诗也能让人一目了然,前一部分是倾情描绘南国早春时节一片天人祥和的景象,往后则是作者向一介农夫一吐心中不快,望能寄情于这之中忘却过往云烟,依赖于客体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事实上这也正是贤人的另一种解“困”之道,无论是立足于主体还是依赖于客体,只要将其发挥到极致后都会将人的生命力留存在历史长河中,但这两种方式以为对于君子的最高人格——圣人而言,都不能真正做到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各种苦难,于圣人言无主客之分,步入真正的自由世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
二 圣人之困:无问主客的天人境界
魏了翁和柳宗元所处的环境恶劣程度基本上可以判定是相差无几的,那么两者对待“困”境的态度是一样的吗?赋予这份“困”境的不是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的中无法逃避的“命运”,也不是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般看似逻辑严密的因果链条当中,他们所面对的就是“是非成败转头空”,也就是事物终究一直是变化的,追求这种存在是无意义的,也就是王朝更迭、人事沉浮这些都是不可选择的,不管做出哪种选择都有可能处在“困”境之中,唯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论语·子罕》中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5]105孔夫子认为自己承接了天命,既然文王传下来的天命还在我身上,那么证明上天还没有让其灭绝,天人之间不是一个割裂的状态,不是一个脱离了经验世界的实体状态。不用去理会上天的安排究竟怎样,人之为人就在于如何彰显这份生命力的高雅,是斯文而不是败类。困境是无法抉择的,但是斯文还是败类是可以抉择的,在困境之中,柳宗元所代表的那一类唐诗和魏了翁所代表的那一类宋诗都是斯文的体现。
魏了翁和柳宗元创作的诗歌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对于“美”的高度上,二者具有差距,但是在围绕“人与自然之中抉择何以可能”的命题上,生命力的彰显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所谓生命力的彰显就是各自的志向,理想的寄托。《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孔子的弟子各自谈论彼此志向的对话: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之能,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5]123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所说的就是与魏了翁一脉相承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人之生命抉择的道德意志倾向的主体体现。然后孔子又问曾点“尔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5]124孔子当众学生面表示愿跟曾点一样,但事实上孔子的实践之路果真如此吗?曾皙的志向倾向于和柳宗元一脉的人之生命抉择的自然意志,当然这须是上扬的自然生命力。得到老师表扬的曾皙等其余三人走后,忍不住问老师他与三名弟子的不同之处。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大哉夫子!这两种优雅的生命本就是存于体内的,将其表现出来不能用是非、高低、贵贱的标准进行判断。作为圣人的孔子一言以蔽之这种主客体倾向不同的志向在他这是并无什么不同,情趣审美上赞成曾点的路数,但用这一生来践行子路的路数。所以作为君子最高人格的圣人这里不存在自然与生命的倾向性解答,故不管遇到怎样的外在挫折,内心的煎熬之苦,只要安身立命之本不偏不倚,就可“从心所欲不逾矩”,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即藏”。
三 唐宋诗歌风格的转变:自然与生命的抉择
纵向上看与唐五代相比,北宋的诗歌创作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动,文学风气更多顺承于中唐“儒学复兴”思潮的延续,接续韩愈、柳宗元所开创的“古文”传统,然宋初文人在诗歌创作上推崇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尤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的影响颇为重大,词藻华丽、对偶工整、文风优美。“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欢笑。”[6]287西昆后学已无唐时那高昂的生命力,强作模效义山之诗便是穷途末路,无奈之下便只能直接窃用其语句引人发笑了。宋初诗歌这种吟风弄月、歌功颂德、无视现实状况、华而不实的文风直接导致了往后的创作越来越重视“文以载道”,南宋尤甚。唐朝诗歌创作的伟大就在于其毫无保留的恣意发挥人的自然生命,故有像李白、杜甫这样让人仰望的高山,人的高贵便是“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史便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是从人之生命力上扬上来看待的。宋儒所要反思的便是任由这种生命力发展所带来的另一种结果,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李杜的超凡之质,生命力还会有下坠的情况,其落到一定层面上在诗歌中就表现为急功近利、窃用其语句之流,所以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每个人无止境地、混乱地发挥便是政治史上的“安史之乱”,酿成“父死子笑”的人间炼狱。
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理学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点而往上翻,念兹在兹以理性来调护也即润泽我们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来调节润泽的,否则一旦生命干枯就会一无所有,就会爆炸”[7]19。北宋诗歌略显平淡、不以文采见长的风格似乎是唐朝华美之诗恣意生长的反思阶段,故其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道德生命对主体的把握,不再是生命力的那种美的体现,而是生命力在于生命本身的思考。魏了翁的《渠阳集》诗歌基本上将说理贯穿始终,尤其注重对于《易》理解和阐发,文中常见如“《易》终得未济,曹末观豳风。或嗟生处远,不近扶木东。谁知天然贵,正在阿堵中。喧寂四时耳,寒至窒斯穹。冷眼看千古,声色沈非熊。”[1]2(《渠阳集·次韵李肩吾读易亭山茶梅》)。其把“易”视作为最普遍的真理,处在万事万物之中,同时对于这个真理的追求是没有停顿的时刻,故其在诗歌上的最大特点是“说理”,有点像是现今电影中的“空镜头”,客体不是在作用层上展现美的意境,而是在存有层上由主体进行义理的思辨。与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集·江雪》)[4]1221相比,同样是对于一种“喧寂”状态的描述,诗歌的意境呈现出一种静态的“审美”意境,不再作为启动人的理性思考的离合器,而是一股直观的冲击,一种直觉认识。将两者并列来看,魏了翁面对“困境”时的精神活动更倾向于理性主导的思维运作模式之中,柳宗元则是感性驱使下的自然与人生结合的生命历程的遨游。当然无法凭借一两首诗,就将两者的诗都一概而论,但唐宋诗风格不小的转变是值得注意的,明显受到了“人如何能称之为人”这以哲学命题的影响。这种转变彰示了人的思维倾向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物质世界的变化会引导精神世界的反思,精神世界的反思又同样会改变物质世界的生活方式,两者的交替运行似乎如四时一般有规律可循,但又不能盲目跃进或停滞不前。事实上绝不可能说宋诗就没有展现自然生命之美了,只是过去作为主阵地的诗歌现在需要承担主体的理性思考,对于客体的倾尽的情思则转移到另一种文学体裁了。
[1]魏了翁.渠阳集[M].张京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2.
[2]脱脱.宋史[M].许嘉璐,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许嘉璐,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4]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6]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山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8]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蔡方鹿.魏了翁评传[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020-12-22
黄科程(1995-),男,湖南怀化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胡悦玥(1996-),女,硕士,湖南长沙人,湖南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I206
A
1673-2219(2021)04-0059-04
(责任编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