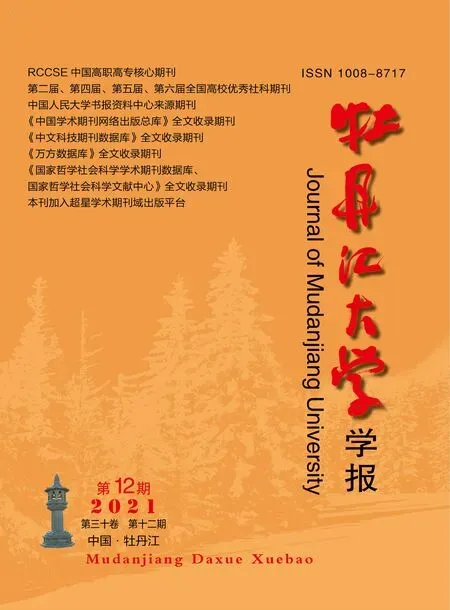浅论汉代经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于 萍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文心雕龙》一书,是产生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部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伟大作品,此书著作有着系统的理论、严密的结构、细致的论述。古往今来,影响着后人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对文章学和修辞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此书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于南朝齐和帝年间著成。《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或者说是“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宗经”为论著文章的基本思想, 《文心雕龙》的创作建立在吸纳汉代经学的精神思想上,汉代经学给予《文心雕龙》的创作很多的精神养料。《文心雕龙》理论系统的建构,从古往今来的学者研究成果来看,受到汉代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关于文学本体论,经学典籍《礼记》影响着《文心雕龙》的文学本体观。关于创作论,《周易》《乐记》的一些精神内涵对刘勰所揭示出的文学创作论(感物——情动——文见)有明显影响,刘勰提出的“质文相附”学说和“情经辞纬”学说,都逃不开经学的思想范畴。[1]对于文学发展论,《通变》篇则是对于《周易》中的论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的哲学思想的继承,《时序》一篇就是受到《乐记》《毛诗序》中关于诗乐发展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的影响,进而阐释了文学内在发展和外在发展的基本规律。关于文学功用论,以《文心雕龙》中篇章来看,“明道”“政化”“事绩”“修身”等功能,这些都明显地受到经学的影响,都逃不出经学的范畴。
一、经学之起源
什么是经学,首先就应该探讨一下。经学,是中国千年传统学术文化主题,自汉代年间形成以来,存在中国的历史足足有着差不多两千多年之久,经学的影响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代的儒家仕子以及经学的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也贯穿着中华文脉的始终。而何谓之经,又何谓之经学?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面说过,我们从他的语源学角度来看,“经”,常与作为织物的“纬”相对,后来引申出的意思与“天”有关,“经”就具有了和天一样的统摄地位和非凡的力量。古文中有“经纬天地曰文”等之语,从古汉语的语境中,可以看出经纬常常和天地相对比,经就和天有了一定的联系,故而在使用“经”这一术语的时候,就往往带有一种征服的意识。在汉武帝时期,由于经常与天相联系,就具有一种统摄万物征服世间的力量,经就具有了很高的地位,而有道德规劝功能的儒家诗学逐渐地与国家大一统社稷安稳的政治伦理相联系。于是结合天时地利人和,经就与儒家诗学相联系,就成为了所谓的经学。
因为儒家诗学固有的倡导建立功业,齐家治国的思想,和封建时期统治者需要的政治需求相吻合,儒家诗学其中的一些精神内涵就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满足现实的需求,于是儒家诗学就与国家的政治伦理相结合。而经学本身就具有的社会道德规劝的功能,这一种社会道德规劝的功能需要政治权力的加持,社会大众的认可,在汉代和皇权主流的结合就是一条比较方便达到其互相目的的路径。所以,加上正处于汉代君王有作为想寻求大一统局面的环境下,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抓住历史机遇,和政治伦理结合,然后经学不断发展,汲取有利于君王统治、社稷安稳以及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在汉代成为一种学术宗教而被确定下来,儒家经典于是就成为了统治者规定后代仕子学习的书籍。
又有说,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亡后,项羽火烧咸阳加上秦皇之时的焚书坑儒,导致六经除《易经》外皆无可幸免,汉朝从文帝景帝时期始,开始古籍的收集工作。到汉武帝即位后,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五经等篇章书籍就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形成了崇高的法定经典。汉代以后儒生因为各种原因,逐渐就以传习、解释五经经典为主业,自此经学开始形成。汉代经学,继承了先秦原初儒家学说的思想,同时又有结合时代的创新和发展。由于汉代经学的崇高地位,这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这也自然就包括《文心雕龙》,所以经学不可避免地对《文心雕龙》的创作产生影响。
二、从《宗经》论浅析汉代经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总论五篇,是全书理论的基础,为“文之枢纽”。第一篇为《原道》,开篇即是“文之为德也大矣”,进而论述“自然之道”,从世间的天地万物皆有文采说起,在论述人必然有“文”,所有的万物文采,又都不是人为的,外加的,而是客观事物自然形成的。然后《原道》的第二部分,开篇就是阐释人类之“文”的起源是起始于混沌之气。《原道》第三部分论“自然之道”和“圣”之间的关系。刘勰认为,古代圣人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著写文章,通过古代圣人的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原道》最后一段中说,自伏羲到孔夫子,远古的圣王伏羲创立章典,有王德而没有王位的孔夫子进行阐述和发挥,他们都推崇自然之道。刘勰通过论述例子,进而阐述自然之道是由圣人体现而为文章,圣人又是通过文章来解释自然之道。就像《易传》之中说的,章辞之所以能够写得优秀有感染力量,就是因为它符合自然之道。刘勰从《原道》出发,继续阐释他的思想,在《征圣》篇和《宗经》等篇都明显显现出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
从刘勰《为文心雕龙·宗经》篇来看,就明确提出了文必宗于经的思想。在《宗经》中, 刘勰首先是高度论述了经书的崇高地位和非凡的价值: “经也者, 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也。…… 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义既极乎性情, 辞亦匠于文理; 故能开学养正, 照明有融”。《宗经》篇直接宣言“文必宗于经”,全文为三部分,第一是为概述诸子经学的基本情况,以及诸子经学对人的感化教育作用的内容,第二部分则是专门介绍“五经”写作的不同的特点以及“五经”的成就;第三部分,是阐明文章为什么要宗于经,宗于经有什么意义。刘勰通过研读古今儒家经学典著,综其所究,认为经对各种文体都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要宗于经,好处有六种,能够文质皆美。能够宗经,就不会出现楚汉以后魏晋以来,文章都矫揉造作显现出一种浮夸文风的文学思潮,文学朝着追求绚烂的文字华丽的文采而忽略掉文章所要表达内在思想的方向发展的弊端。《宗经》开篇就向我们说明了什么是经学,即:阐明天、地、人三才者寻常道理的,这类书就叫做经书。所谓的“经”,也就是历经岁月不改的根本道理,不可改变的圣人教导。由此可见刘勰在这就把经书推崇到了一个高度,自然他的著作就离不开经学对他的影响。
《宗经》篇中认为儒家的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义既极乎性情, 辞亦匠于文理”,就是说,不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技巧,经典都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所以文章必须要宗经。 所以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出,《文心雕龙》的著作离不开汉代经学的影响。
《文心雕龙》中,除了文之枢纽之一的《宗经》一篇开头的直接宣言外,后文也继续说明了论、说、辞、序、诏、策等各种文体的类型,都来源于五经。五经作为“文章奥府”“群言之祖”,表明后世文体的创作就得学习经学,效仿经学的创作,以五经为文体创作的范文,足见经学对后世文体的影响。就本体论而言,刘勰在论述文学创作和作品产出的问题的时候,涉及到文学理论核心这一基本问题,而《文心雕龙》的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根源就在于经学。受经学元典中的《乐记》的影响,刘勰就提出了以“人心”为本的文学本体论。如:《乐记·乐本》篇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也就是说,只有人心生,才有作品出。刘勰对“乐由心生”这一命题的把握,不光是乐由心生,文自然也由心生,文学与艺术没有情由心生,是不会产出优秀打动人心的作品。以乐论来移植文论,文学理论从《乐记》中汲取营养,可见经学之一的《乐记》思想对其理论观念的影响。
三、从创作论浅析汉代经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从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情采》《体性》等篇来看,可以发现刘勰对文学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揭示,这个原理即是:感物——情动——文见。一说是世界万物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本源,先感物方能更好抒情,情才更好的由心而生。才可以“言形”来“吟志”,这就是刘勰“感物吟志”说。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主流就是抒情文学。刘勰的这种“感物吟志”说的观点自然源于经学,明显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经学元典《周易·咸挂·彖辞》中有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不从思想来看,《文心雕龙》中也有很多地方受《易经》的影响,从字面上看多处出现“两仪”“三才”“玄黄”“太极”,这些术语皆出于《易经》。而从思想高度来说,刘勰的“感物吟志”一说就受汉代经学《易经》的影响,受“感而化生”提出“感物斯惑”,之后其很多的篇章和理论也受这个影响。
《文心雕龙》也阐释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文学作品的审美理想等等。《文心雕龙·情采》中:“夫水性虚而沦漪结,……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认为作品的文质关系应是“文附质”和“质待文”,文质二者之间互相依赖,此论和经学中倡导的文质彬彬相切合。在刘勰之前,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也曾论述过“文质”的问题,曾提出:“文质两备,然后礼成”。汉代辞赋家扬子云,认为文章之“事”重于“辞”,质重于文。刘勰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思想,就形成了《文心雕龙》的“文质论”。经学家的基本观点是以质为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情经辞纬”论和“以质为先”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以刘勰的《风骨》一篇来论述,《风骨》篇总结了前人对“风骨”的研究和看法,也论述了刘勰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和基本要求。黄侃先生对刘勰的“风骨”说进行阐释,风即文意,骨为文辞。 二者在作品之间又都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因素。在文中,刘勰也相应举出不同的例子。就“风”而言,刘勰以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为例,而以“骨”来说,就是说,潘勖写就《册魏公九锡文》,企图学习经典的文辞,使别人都不敢下笔。同时,“风骨”论的宗经倾向还体现在“风骨”作为一种诗学范畴,“风骨论”和儒家倡导的思想相契合。刘勰反对晋朝至南北朝以来的浮夸文风,所以《文心雕龙》就是针对晋朝以来社会犹重清谈的现象,文学作品中过分追求华而不实的文采,从而忽略文章真挚的思想内容的倾向而提出的,这种对社会没有裨益的文章不为所喜,于是刘勰倡导文章需要有风骨,“情与气偕,辞共体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刘勰强调的“风骨”和儒家思想中所奉行的“刚而无虐”的精神内涵相符合,同时,也可以说刘勰的“风骨”也被经学所儒化了。
四、从发展论浅析汉代经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文心雕龙》中的《通变》和《时序》两篇,较为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的思想,以及对于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的认识。通,即是继承传统,也就是说古代现代文学有相通相承的一面。变,就是发展变化,也是古今文学之间有存在差异的一面。“通变”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周易》中有云:“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和“变”,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发展,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辩证范畴。刘勰受《周易》一书的影响,吸纳“通变”观念的精神内涵,在文学创作中,文学发展中,用通变来阐述文学批评的继承与革新之间的关系。 《文心雕龙·通变》中“通变”一词,就足足出现有七次。文中的一些原文,如:“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过原文和经学典籍的对照,可以看出,刘勰所论的通变与《易传》的渊源关系不浅。《周易》一书,其中蕴含的事物发展规律就是一个字“变”,变,才会有生机有新的方向。正所谓世间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变化,于是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位和永恒的标准,因此就有“唯变所适”,即是说要积极地适应,顺从事物的变化。《周易》中的“通变”思想,通过刘勰学习前人思想吸纳前人观念,继而又结合时代进行创新,富有创造性地将二者对举成文,进而就形成了一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文论范畴,用于阐述文学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通变观念与时序观念,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是关于文学的发展,文学与时代的两个主要概念。二者各有各的理论指向,同时又互相关联,但是就逻辑而言,通变所处的层面高于时序。
“时序”的观念源于经学典籍《乐记》,“时序”是阐述文学的外部发展规律,是论述文学的创作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总结了文学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迁,与时代息息相关。但由于古代的时候,诗乐一家,将《乐记》中论述“时序”和“乐”之间关系的思想移植至文学的创作。汉代《毛诗序》中就有此例,《毛诗序》中是将乐论用于诗论,而刘勰则是进一步吸纳《乐记》和《毛诗序》中的观点,联系当下社会的变迁来论述文学的发展,分析文学的变化。同时,无论是《乐记》还是《毛诗序》中有关诗乐与时序的探讨,都离不开经学的范畴。所以说,是刘勰运用汉代经学来阐释文学理论的实例,又是刘勰《文心雕龙》中受汉代经学影响的实例。
总体而言,《文心雕龙》在建构其理论系统上受到经学影响,而且在字词的运用,句法的表达,术语的引用上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见经学对其也有影响。《文心雕龙》中常用的范畴术语,从《原道》到《序志》来看,每一篇都有明显的出自经学的范畴术语,如:两仪,三才,文质,言,意,象,养心,通变,这些范畴术语皆出自于经学。《文心雕龙》中的这些范畴术语,对刘勰的思想理论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有着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地位。同样,汉代经学对《文心雕龙》的创作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从汉代经学来研究《文心雕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析了解龙学的学术特色和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