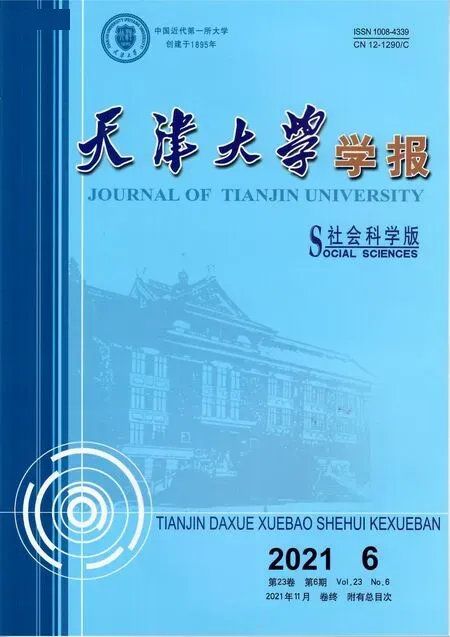王鸣盛“学宋”与乾嘉诗坛趋势关系考论
龙 野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南昌 330031)
王鸣盛(1722—1797)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诗人,以诗歌受知于沈德潜,列“吴中七子”之首。他中年后致力于经史考据之学,得享盛名,以致后世对其诗学不够重视。实则王鸣盛一直未放弃对诗歌的热爱,《听雨斋诗集序》云:“予三十余年以来,闭户一室,苦吟独赏,不与人相酬和,人以为予用意在穷经考史,而不知所深好者惟诗。”[1]可见诗歌是王鸣盛一生喜爱并看重的。从清代中后期诗坛的实际情况来看,他颇受时人重视,在《乾嘉诗坛点将录》的一个版本中他被列为“芒砀山旧头领”[2]之一,地位较高。王鸣盛在格调派诗学的传承与发展上有较重要的意义,“对新格调诗观有着深刻的领会和新的拓展”[3],是值得重视的一位诗人。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学界对王鸣盛的诗学研究不多,特别是对其中年的学宋诗经历还缺乏详细深入的论述①。实际上,这是后期格调派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王鸣盛在“吴中七子”中沾染宋调最深,他作为沈德潜的弟子而有这种诗学变化,本身就有研究的意义。因此,梳理其诗学取向的变化过程对于我们深入细致地考察沈德潜之后的格调派,把握乾嘉诗坛的走向均有助益。
一、 王鸣盛诗学取向的变化过程
考察王鸣盛诗学取向的变化过程,有必要从“吴中七子”说起。“吴中七子”同学诗于沈德潜,虽然创作风貌和诗学趣味有明显差别[4],但在提倡温柔敦厚与雅正的诗学取向上均受到沈德潜的影响,与沈氏保持一致。当然,他们的具体诗学取法对象与沈德潜存在一些差异。在乾嘉诗学背景下,他们都对宋调有明显的采纳,取径比沈德潜显得更为宏通。如王昶编《湖海诗传》对宋调诗作了有限的采纳[5],创作上也对苏轼、陆游等有取法。曹仁虎“诗宗三唐,而神明变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格律醇雅,酝酿深厚”[6],但其中年以后的诗歌沾染苏轼。吴泰来的诗学瓣香王士禛,“作诗大旨,一本渔洋”[7],以“神韵说”为宗,中年后对苏轼、黄庭坚、陆游均有取法。赵文哲早年论诗以汉魏三唐为宗,服膺王士禛,基本上是“神韵说”的“诠释与引伸”[8],但中年后兼取韩、苏雄奇一派,分体裁论诗,能认识到宋诗的价值。如认为欧阳修、王安石的七言古诗堪称大家,苏轼“尤变化不可方物”[2]1818即体现出对宋诗,尤其是苏轼七言古体诗的接受。在“吴中七子”中,对宋调的接受最为突出的是王鸣盛,他甚至一度有倡导宋诗的经历。
王鸣盛的诗学存在着三个阶段,较完整提到王鸣盛诗学变化的是其友人王昶。《王鸣盛传》云:“鸣盛为诗,少宗汉魏盛唐,排律则仿元、白、皮、陆。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后悔,复操前说。”[9]指出了王鸣盛诗学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以汉魏盛唐为宗,排律兼采中晚唐名家;进京应试与为官后,因与钱载、蒋士铨等宗宋诗人交往颇密,一度对宋诗兴趣盎然;晚年对曾经提倡宋诗的做法表示出悔意,并重返唐音。这样的看法,王昶还在晚年编订《湖海诗传》时提及:“(鸣盛)诗兼综三唐,初为沈文悫公入室弟子,既而旁涉宋人,归田后,复守前说。”[7]613也指出王鸣盛作为沈德潜入室弟子论诗兼宗三唐,在京师时有过旁涉宋人,晚年复守唐音的诗学经历。王昶还特意提及选入《湖海诗传》中的王鸣盛的诗歌是其晚年订正写寄,大概是据此以表明王鸣盛晚年诗学重返唐音的转变。这种看法是王昶对王鸣盛诗歌取向的定评,大体上符合其诗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当然,也有意忽略了王鸣盛早年不法唐宋,主张表现自我的诗学经历。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王鸣盛的诗主要保存在《西庄始存稿》(诗十五卷)及《西沚居士集》(诗二十三卷)中,是其诗学理念“重返唐音”后进行编定的,有过删改。从现存的诗歌来看,王鸣盛早年的诗歌创作如《曲台丛稿》(含《竹素园诗》三卷、《日下集》一卷,分别是其早年在吴地及入京应试时所写作品。)注重格调,词旨迢远,是典型的学汉魏三唐诗风格;但他在论诗方面又显示出与格调派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呈现出较复杂的面向,即论诗上对模拟唐宋的摒弃及对自我精神的重视与肯定。《题庆孝廉璞斋试卷即送之金陵六首》其三“学宋学唐都是假,但须学我自然佳”句小注云:“予昔游武昌,楚中名士毕集,一客问:‘诗当学唐耶?学宋耶?’予曰:‘皆不足学。’客大骇,曰:‘究当谁学?’予徐曰:‘学我而已’。”[10]在王鸣盛看来,唐宋皆不足学,而应学自己,即诗歌模拟唐宋并不足取,只有表现出自我真实的性情,才能写出好诗。其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持论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这种对诗歌中自我意识的强调远超沈德潜②。王鸣盛结识沈德潜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游楚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这意味着在追随沈氏两年后,他对诗歌仍存有自己的看法。他不主张诗歌刻意学唐或学宋,明确提出应当学自己,与康熙间诗论家叶燮等人接近,并世诗人中则接近薛雪、袁枚的主张③。当然,从王鸣盛现存的诗集及沈德潜编选的《七子诗选》中的诗歌作品来看,王鸣盛的诗歌创作是以唐为宗的。
随着交游的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京师与宗宋诗人群体的频繁交往,王鸣盛的诗学观念更加认同宋诗。乾隆十九年(1754),王鸣盛进士及第,开启了其京师为官生涯。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蒋士铨,与先前相识的友人钱载的交往也更紧密,这使得他深入接触到京师学宋诗的交游圈,并参与其中。蒋士铨《寿萱堂诗钞》(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寄答王凤喈同年鸣盛》其一有句“受铭蘀石偕康古,鼎足鸳湖振后尘。都道君才倍曹丕,汝推吾派异居仁。”其中提及王又曾、钱载、汪孟鋗等人鼎足于秀水诗坛,“振后尘”似指振起于朱彝尊之后。他们推崇王鸣盛的才华超过曹丕,而王鸣盛常在友朋间推崇蒋士铨与王又曾、钱载、汪孟鋗等人,显然是注意到了他们学黄庭坚诗取法江西诗派的现象,但与吕本中标举江西诗派并学山谷诗不同,王鸣盛推许蒋士铨等学江西诗派,自己却不学山谷诗而学杨万里。其三有句:“年来事事厌形摹,只觉前贤此意孤。……试看纷纷谈李杜,不知谁可见黄苏。”[11]其中蒋士铨道出了厌恶摹拟前人诗歌的做法,也指出了诗坛大多都效法李杜,未能真正见及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艺术成就。这是蒋士铨在有意提倡宋诗,主张兼容唐宋。在与蒋士铨论诗中大多以宋诗及江西诗派为中心话题,可见“宋诗”此时已经成为王鸣盛诗学中的重要一环。
与蒋士铨偏爱黄庭坚不同,王鸣盛在宋代诗人中最喜欢杨万里。《蒋清容先生手书诗稿》中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六月初一日王鸣盛题诗,第八首云:“尔学涪翁大是佳,瓣香我独奉诚斋。何时打破同床梦,费尽功夫踏铁鞋”[12]。诗中指出了蒋士铨诗歌学黄庭坚,自己诗歌瓣香杨万里的事实。这一段时期,王鸣盛居住在北京宣武坊,与蒋士铨等过从紧密。蒋士铨学黄庭坚诗的瘦硬拗折,王鸣盛则主要学杨万里诗的外表平淡与内在深隽,情韵兼长。我们知道,杨万里早年从江西诗派尤其是黄庭坚入手学杜,清新刻露而特为生拗;后期转向“活法”,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具有新、奇、活、快、风趣幽默的特点。杨万里论诗不肯寄人篱下,其诗学在重视与强调“自我”方面影响了清代的査慎行、袁枚等人。王鸣盛不学唐、不学宋,而强调“学我”,形成自己风格的主张与杨万里重独创接近,可能与诚斋有一定的关系。
乾隆二十五年(1760),王鸣盛在为《媕雅堂诗集》作序时,肯定赵文哲胸中“无唐无宋”,笔下诗歌“有唐有宋”。序中说“世人之论诗,或夸唐调,或持宋体,依门傍径,各仞其说而不能相下。夫诗则何唐、宋之有哉?唐人集其成,宋人极其变,异流而同源,其精神标格,各有千古者存焉。”[13]结合明清诗坛的情况来看,序中所谓“或夸唐调”可能是指明代的格调派及清初的宗唐派诗人,而“或持宋体”则可能是指清初的黄宗羲、吴之振等人及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以钱载等为代表的秀水派。王鸣盛认为这种将诗歌分为唐宋两派的门户之见是不正确的,唐诗与宋诗各有其特色,异流同源,各有其足以流传千古的精神在。只有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性情与体验,不去考虑是否与唐宋诗人的“离”与“合”,诗歌才能追配古人。在这种理念下,其诗“中年稍变化,出入香山、东坡”[6]739也就好理解了,是合乎逻辑的变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冬,王鸣盛有《冬夜读梅圣俞诗》,其中有句“滑口读不下,滑眼看不入。高峭带平淡,瘦硬兼酸涩。……前蹑郊岛步,后顾黄陈揖”[14]指出了梅圣俞诗高峭平淡、瘦硬酸涩的特点和上继郊、岛,下启黄、陈的地位。这表明此段时间王鸣盛在有意识地读宋人的诗篇。我们知道,清代诗坛从康熙年间起就形成了热衷于学苏轼的氛围,甚至一度流行为东坡做生日的雅集活动④,用苏轼诗韵作诗,是清人接受东坡文化精神的体现。尽管对苏诗用韵之谬颇存不满(见《蛾术编》卷七十八说集四“东坡用韵”条),王鸣盛的创作中仍数次用到苏轼诗韵,如《谢陈句山前辈饷酒用东坡监试呈诸试官韵》《试院用东坡煎茶韵呈钱坤一卢绍弓梁元颖诸前辈》等便是,体现出王鸣盛对苏诗的接受。此外,王鸣盛与友人论诗,曾提及江西诗派,如《顾学逊家条山并示新作因相与极论诗法并及西江派五叠前韵赠二子》有句“汉上喜看襟并接,豫章相约派求生。兔鱼得后筌蹄弃,扫却形模唐宋明”[14]170是着眼于“变”的角度,主张要告别机械摹拟,学习江西诗派生新的理念,形成自己的风格。乾隆三十五年(1770)王鸣盛的女婿姚壎与友人合选《宋诗略》,强调宋诗与唐诗异流同源,肯定宋诗价值,不分唐宋门户。在署名为王鸣盛实际由其弟王鸣韶代笔的《宋诗略序》中,赞扬该选能“使天下后世考见宋人之真诗”⑤,是对宋诗价值的一种肯定。此序虽然是代笔,但应该经过了王鸣盛的首肯,代表了他当时对宋诗的真实态度。
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鸣盛丁母忧返乡,不复出仕。在这一段时间内,虽然他对宋诗也较为优容,但其诗学取向又逐步回到了以唐为宗。在所编选的诗歌选本中更强调注重雅正,与其师沈德潜的选诗标准接近。其所编选的《练川十二家诗钞》《江左十子诗钞》等诗学选本大多贯彻了这种理念。王鸣盛晚年诗学对盛唐、中唐、晚唐均有取法,对唐代诗人杜甫、韩愈、李贺及李商隐、温庭筠均致力学习,而其中尤其偏好李商隐。《跋玉溪生诗笺注二》云:“然予近日颇爱李义山、高季迪两家诗,因季迪诗太亮,必以义山之行曲者参之也。”(转引自陈鸿森《王鸣盛年谱》下)王鸣盛在翰林院时受业于李商隐研究专家冯浩门下,当时并未刻意学习西昆诗风,晚年方喜好上李商隐诗歌,是清代中期学李商隐诗歌的重要代表。吴云《西沚居士集后跋》记载鸣盛晚年云:“诗以李义山为最,将尽改生平所作,效其体制。”[15]实际上,这种尝试并未真正实行。王鸣盛诗风格与李商隐不同,之所以有此言论,大概是他晚年意识到了从李商隐上窥杜诗的路径才是正途。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卷十三转引《怀旧集》云王鸣盛“晚岁务为绵密,时近西昆”[16]隐约逗露出这层信息。这种变化既是王鸣盛晚年诗律日益精细后的感悟,大概也与乾嘉诗坛的现实有关。
二、 王鸣盛中途学宋诗的原因
上文我们对王鸣盛的诗学变化进行了梳理,指出其诗学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虽然有过重视自我,不学唐与宋的主张,但追随沈德潜后,论诗大体以汉魏盛唐为宗;进京任职后,与京师学宋诗人群体相交游,沾染宋调;晚年复返唐音,由李商隐上窥杜甫。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他中途学宋的这一段经历。梳理其原因,并将其置于乾嘉诗学演进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那么,王鸣盛中年学宋的原因有哪些呢?概括而言,我们以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乾嘉诗坛唐宋兼取诗学背景之熏染;其二,京师诗坛以秀水派诗人为核心的宗宋派的影响;其三,王鸣盛诗学求新的自我诉求。以下一一进行梳理。
1.乾嘉诗坛唐宋兼取背景之熏染
从明代起,诗坛就存在唐宋诗之争。明末清初,钱谦益等有鉴于前后七子复古派摹拟盛唐的流弊,开始提倡宋诗,以救正诗坛的摹拟之风,并在康熙初年形成了一个学宋诗的高潮,王士禛、汪琬等名家均参与其中。随着吴之振《宋诗钞》等的风行,诗坛又出现了摹拟宋诗的弊病,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后来,因王士禛等人的推动,康熙诗坛的主流重新回到宗唐——尽管一些地区如江南一带仍有学苏、陆的风气,但总体而言,诗坛又出现了被唐诗笼罩的现象。从乾隆初年起,沈德潜宗唐的“格调说”流播诗坛,成为具有官方色彩的诗学思想。这时浙江一带虽然有厉鹗等提倡宋诗,但无法与“格调说”相抗衡。乾隆十五年(1750),具有官方指导意义的《唐宋诗醇》刊刻出版,其中收苏轼、陆游两家,表明官方对宋诗的价值已有认识。此书出版后立即颁行,成为各地书院生员学子诗歌写作的指导性教材。在此背景下,诗坛关注宋诗的风气也渐趋形成,并成为一种新的导向。这正是沈德潜离开京师告老还乡之后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到了乾隆中期后,诗坛出现了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以及其他诗人群体,这些诗人或主张诗歌不分唐、宋,或主张以唐为宗,唐、宋兼取,出入唐宋大家[17],或主张学宋诗。诗坛还出现了按诗歌体裁来选择优秀诗人诗歌作为学习对象的现象——如翁方纲《志言集》及《续集》对苏、黄七古的认同,对虞集、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等人诗歌的接受等,反映出当时宋调诗及宋以后优秀诗人的佳作日益被接受,人们在诗歌取法对象上不再简单地以时代来划分优劣,而是分体学习前代优秀诗人,这逐步成为诗坛的普遍现象。在这种诗学演进背景下,包括王鸣盛在内的“吴中七子”的诗学选择也与时代推移,浸染宋调。如前揭赵文哲《媕雅堂诗话》认为七言古诗当以盛唐人为极则,极其尽变而至宋代,变而不失其正,欧阳修、王安石皆称大家,苏轼的七古艺术成就尤高;他还分别评价了明代高启、袁凯、前后七子、清初王士禛等名家各体诗的优点与不足。这表明在后期格调派成员内部出现了对宋诗价值认识的诉求。我们打开沈德潜弟子及再传弟子等后期格调派成员的诗集,大多都能发现他们用东坡、山谷、放翁、诚斋诗集中韵作诗或效其体的诗作,本身就能反映出这一趋势。
2.宗宋派的影响与对格调派的调整
除了诗坛总体环境因素的影响外,王鸣盛沾染宋调还受到与钱载、蒋士铨等人具体交游圈的小环境因素的影响。《御选唐宋诗醇》的刊刻表明宋诗受到最高统治者乾隆的关注。虽然《御选唐宋诗醇》并未选入黄庭坚的诗,但并不代表其“瘦硬险涩”的诗风在诗坛无人追慕。乾隆十四年(1749)沈德潜致仕离京,翁方纲等人尚未走到诗坛的最前沿,京师诗坛出现了暂时缺乏领袖的真空期。这种真空期的出现,为诗坛风气出现变化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京师诗坛颇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一个以在京秀水籍诗人为核心的学宋诗的群体,他们早年在秀水从事诗歌创作时就提倡杜、韩、苏、黄,尤其是倡导学习黄庭坚的诗。金蓉镜《读豫章集赋呈乙公》“先公所师妙有绪”句下有小注云:“《桧门诗存》多学山谷,同时萚石、又辛继之,遂别衍为秀水派。”[18]随着主要人物相继进京应试、游幕、为官,这种诗风也被他们带到了京师诗坛。从现有的材料看,至迟在乾隆十九年(1754)左右这个群体就已经活跃在京师诗坛,其核心人物是金德瑛,重要诗人有钱载、蒋士铨、王又曾、汪孟鋗等人。在乾隆二十年左右,京师诗坛主要被秀水派诗人所主导。王昶进京时也与金德瑛、蒋士铨等交往颇密,注意到了他们学黄的倾向,《与彭芝庭少司马》云:“诗道沦胥,往往以枯硬为能,以险涩为巧,心知其误而不敢为之附和。”[19]就是王昶与彭启丰谈及他于乾隆十九年左右,在京师见到诗坛刻意学宋诗,尤其是学黄庭坚瘦硬枯涩的风气。王昶对这种学山谷诗的倾向表示出警惕,并不认同,但王鸣盛是主动融入其中。在京师诗坛宗宋风气日益兴盛的氛围里,王鸣盛与友人一起探讨宋诗的价值,他取法杨万里清雅一派风格,不刻意学黄庭坚,这种追求新变、重视自我的探索是在诗坛对宋诗价值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其次,王鸣盛取法宋诗可能还与格调派的不足有关。沈德潜在诗坛倡导“格调说”,虽然说自己不排斥宋诗,比前后七子来说也更圆融,但过于严格的取法也使得格调派诗人创作容易流于模拟,空有格调架子,多虚响而缺乏真情实感,流于另一种“不切”,因而招来其他诗学流派的批评。即使是格调派内部的一些成员,也认为拘泥于学唐诗,容易限制住诗人才情的拓展。因此,在格调派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在坚持雅正的前提下,适度向宋诗学习,能够更畅达的表现出诗人的真情实感。也就是说,无论是格调派内部出于自我拓展,还是其他诗学流派的外在批评都使后期格调派有完善自我诗学的诉求。王鸣盛在结识沈德潜之前,已经形成自己的诗学观,追随沈德潜宗唐诗学后,对诗坛的现状及格调派内部的不足无疑是深有体会的。面对诗坛日趋兴盛的宗宋氛围和其他流派对格调派不足的批评,王鸣盛选择了学习杨万里等人求新的诗学路径,大概也有融合唐宋,修正格调派诗学不足的考量。
3. 王鸣盛自我诗学求新的诉求
当然,王鸣盛学习宋诗也有拓宽自我诗学的因素。从晚明清初以来,诗坛一直存在着一股重视自我的意识,或显或隐,绵延不断⑥。如前所述,在拜沈德潜为师前,王鸣盛受诗坛具体环境的影响而主张不学唐宋,而应该“学我”。这种精神与宋诗求新求变的内在诉求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自我求新的主张为其稍后受容宋诗提供了基础。乾隆十九年(1754)王鸣盛入京后,与宗宋诗人密切交往,开始仿效宋诗。他学宋诗主要是着眼于能够写出自我精神的诗歌,而不是流于摹拟。宋人坚持“求新”,在唐诗的艺术高峰之后开拓出一条新的颇具特色的诗学道路,以形成与唐人不同的艺术风格。江西诗派黄庭坚、杨万里等人“求新”的特点尤为明显,成为乾嘉诗人追求诗歌多样化的学习对象。在京师诗坛“学宋”风气高涨的背景下,王鸣盛开始了拓展其诗学取法的尝试,他选择的学习对象是杨万里。宋代诗人中,黄庭坚注重在诗歌形式方面求新,杨万里主要是在诗意方面追求突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其三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20]。明显表示出绝去依傍,抒写真我的自觉意识,是对务去陈言、形成自我风格的追求。王鸣盛对杨万里的喜好主要就是着眼于此,即能够告别机械摹拟、门户意识,融合唐宋之长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清初以来的浙西诗家诸如查慎行等均有这种追求,王鸣盛对此颇为赞赏。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在《静退斋诗集序》中云:“近日诗家麻列,鄙趣顾独喜浙西诸公多酸甜风味,不屑掇拾人牙后慧”[21]。强调浙西诗人戴文灯的诗能够写出自己的特色,不拾人牙慧,取法于苏轼、陈师道、陈与义、范成大等,而能务去陈言,情韵独绝。王鸣盛喜欢浙西诗人这种诗风,是因为浙西诗人能够取法宋诗,在人人摹拟盛唐的背景下另辟蹊径,呈现出自己的诗歌风貌。这实际上是对宋诗具备新奇的特点的喜好。他还在《树萱诗草序》中提及近代以诗称名者大多是“或剽儗唐人之形模,或剿取宋人之膏沈,大约惟涂泽掇拾之是尚,袭其貌而遗其神,师其辞而失其意”[15]462,他并不赞同这种片面模拟唐宋的做法,因为这些摹拟之作取貌遗神,并不具备自我风貌。王鸣盛对诗坛弊病的这种批评也是从求新的角度来着眼的。当然,王鸣盛对宋诗的偏好也与他入京后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关。前文已述及王鸣盛在入京后曾受命编纂《续宋文鉴》,接触到大量的宋人诗文集,他在此过程中无疑会对宋诗有深入的研究与体认。
此外,王鸣盛论诗提倡学问,与诗坛学宋潮流相近。提倡学问与用典是宋诗一大特色,王鸣盛对引用严羽“诗有别材,非关学也”来论诗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吴诗集览序》云:“杜陵千古诗圣,其言下笔有神,必以读书万卷为本,然则性灵虽妙,非书卷不足以发之,彼谓诗有别才,非关学问者,聊饰词以文俭腹耳。故予论诗,必以多读书为胜。”[22]在他看来,有学问才能驱使性灵,这种重视学问在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念,实际上也是乾嘉时期学者型诗论家的主流看法。在注重学问这一方面,王鸣盛的主张与乾嘉诗坛走向宗宋大体是一致的。
三、 王鸣盛诗学变化与乾嘉诗坛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王鸣盛的诗学早年、中年及晚年存在着明显的变化。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鸣盛丁母忧返回江南后,其诗学逐渐复归于唐。其中途学宋与晚年复返唐音的诗学取向,对于我们认识乾嘉诗学演进趋势颇有意义。特别是他作为“格调派”领袖沈德潜的弟子而有此行为,更值得注意。袁枚就敏锐地发现了王鸣盛等人诗学变化的事实。《再答李少鹤》云:“当归愚极盛时,宗之者止吴门七子耳,不过一时借以成名,而随后旋即叛去。”[23]在袁枚看来,“吴中七子”早期从沈德潜学诗,是出于借以成名的考虑,当成名之后,就不再严格遵守沈德潜宗汉魏盛唐的诗学,降而取法宋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王鸣盛中进士后在京师期间的“学宋”经历呢?袁枚的看法符合实际吗?实际上,我们以为袁枚的看法并不完整。王鸣盛入京后与钱载、蒋士铨等人学宋诗,并不是“背叛”沈德潜,而是从诗坛唐宋元明并取的现状出发对格调派诗学进行的一种调整,也是对自我诗学的拓展,是当时诗坛唐宋并取背景下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学习宋代以降的优秀诗人有利于拓展其诗学取法的对象,使其诗歌能够在格调派的基础上拓展才情,体现自我精神与风格,弥补格调派过于刻板、流于模拟的不足——这正是当时诗坛对格调派批评的核心所在。从客观上看,王鸣盛对宋诗的推崇促进了诗坛对宋诗价值的接受,对于宋诗典范地位的确立具有意义。而他晚年并不如早年那样提倡宋诗,大概同样与乾嘉诗坛的现实状况有关。
据王昶所言,王鸣盛归田后,对自己中途学宋的一段经历颇为后悔,他晚年转而回归唐音,亲自写定寄给王昶编入《湖海诗传》的诗歌纯然唐音。他的诗集中学宋诗风格的作品大量被删汰,仅有一些痕迹可寻。那么王鸣盛为何在晚年会重返唐音?这应该是他从诗坛现状出发进行考量的结果,有现实针对性。王鸣盛作于暮年的《听雨斋诗集序》指出了乾嘉诗坛普遍存在骋才的弊病,认为这种风气不为好学深思的人所认同,因为骋才容易“其意尽也,词熟也,味短也,调雷同也,径直而无回曲也,繁杀嘈杂而感人浅也”[1]5。虽然未直接点明所批评的对象,但从语意上可以看出这是针对学宋诗而言的。宋诗不像唐诗那样注重比兴,而是以赋的方式写诗,其不足之处是容易意尽,因此,王鸣盛晚年重视提倡李商隐比兴蕴藉的诗风。因为李诗绵密精工,可补救粗涩,能避免黄庭坚等从形式上学杜带来的粗放之弊——刻意学黄庭坚,或者说经黄庭坚上窥杜甫是乾嘉诗坛的一股显流,其弊端主要表现为秀水派诗人的生涩,成为诗坛一大问题。其次,性灵派的诗人学杨万里等人而过于俚俗直露,缺乏比兴深致,同样成为乾嘉诗坛的一大弊病。秀水派与性灵派等学宋流于枯涩或俚俗,导致诗坛创作比兴缺失,这与儒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的诗教的宗旨相悖。或许正是看到了诗坛的弊病,王鸣盛、纪昀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李商隐诗歌绵密精工的优点恰可成为治病之药方,因而颇为留意。因此,王鸣盛在《听雨斋诗集序》中的主张,与其师沈德潜“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24]的观点颇为接近,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在王鸣盛看来,过分驰骋才情使诗歌一览无余,没有含蓄蕴藉的美感,无一唱三叹之妙,不能感人至深。王鸣盛曾主张诗歌不学唐宋,而应表现自我,在京师为官期间提倡宋诗,但在目睹了诗坛片面提倡宋诗的现实弊病后,对此有了切身体悟,他意识到雅正与比兴对于纠正当时诗坛弊病的重要性,因而晚年适时调整其诗学选择,重新回归到唐音的传统上。
王鸣盛晚年复返唐音的做法,可能还与当时诗坛未处理好雅正与新变的关系有关。王鸣盛辞官后致力于经史之学,并主讲丽泽书院。虽然精力不专于诗文,但作为“吴中七子”的一员,他必须关注江南诗坛的动态。大约乾隆二十年起,处在南京的袁枚开始在江浙一带提倡“性灵说”,对沈德潜的“格调说”带来了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去世后,格调派的势力很快就无法与袁枚抗衡。此时,王昶尚未显贵,担当格调派诗学领军重任的是王鸣盛。在沈德潜去世前的几年里,王鸣盛相继选有《练川十二家诗钞》《江左十子诗钞》《江浙十二家诗钞》等选本,不排除有接过格调派领袖身份的意图。当时,袁枚的性灵派在江浙间影响颇大,他们追求自我意识,求新求变,引领了诗歌领域的革新。性灵派主张废弃唐人诗歌的创作轨范,刻意表现自我,这种诗歌创作方式给诗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25]。有鉴于此,王鸣盛重新回到沈德潜倡导的雅正诗学传统上来,“于明何景明、李攀龙、李梦阳、王世贞、陈子龙及国朝王士禛、朱彝尊之诗,服膺无间”[9]1082。他将这些大家的诗歌均视为典范,加以学习,坚持雅正传统,以纠正江南一带的诗学弊病。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云:“先生生平论诗,以风人为主,在唐,如玉溪、飞卿,不失温柔敦厚之恉,宋、元,古法渐失矣。先生诗,上者法六朝,次亦确守三唐规范,以视世之抱韩尊苏者,超然远焉。”[26]刻意略去了王鸣盛学宋的经历,强调其宗汉魏三唐的取向,并未完整展现出王氏诗学历程,但将其视作王氏晚年诗学定论是没有问题的。阮元特别提及王鸣盛论诗注重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寓有对其传承沈氏格调诗论的肯定。王鸣盛晚年颇为注意诗歌的教化作用,强调比兴传统、风人之旨,有扶持诗教趋于雅正的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鸣盛论诗重新回到宗唐的主张上来,与乾嘉诗坛创作的具体现实困境有关。
综上所述,王鸣盛的诗学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与诗坛现实相关。通过梳理王鸣盛诗学变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诗学流派主张的提出、某位诗坛主将诗学观念的前后变化往往与具体的诗坛风气紧密相关,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或是顺应诗坛风气变化而作出选择,或是对诗坛的现实弊病进行抨击而有所调整,或是为改变流派的不足进行自我完善。我们在研究古代诗学史与诗学批评史时,难免会对这一种现象作出简单片面的理解,结论往往会与真实的情况不符。譬如王士禛诗学经历过三次变化,他中途学宋是在钱谦益等人的影响下,通过提倡宋诗来补救明代复古派的不足,但后来认识到片面学宋的流弊更大,因而复返唐音。编选过《宋诗钞》的吴之振晚年见到诗坛学宋的流弊,也拟重新编选唐诗来救正这种倾向⑦。他们的诗学选择都具有明显的现实考量,不应被简单理解。
回到本文所关注的王鸣盛,他早年追随沈德潜,以汉魏三唐为宗,进京为官后沾染宋调,一方面是因为接触到宗宋的诗人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求新,告别摹拟涂泽的弊病,因而尝试学宋。辞官返回江南后,看到诗坛学宋的流弊,尤其是性灵派过分追求自我的弊病,他重拾沈德潜“格调说”的大旗,提倡雅正,以救正诗坛的流弊。无论是在京师的学宋,还是晚年复返唐音,王鸣盛的两种选择都有其现实的指向与诗学意义,我们应该在动态的诗坛演进过程中客观全面地看待它,庶几能更接近诗学史的真实面貌。
注 释:
① 有学者曾专门撰文论述王鸣盛诗学思想,虽然论及其中年诗学沾染宋调,但限于行文未深入展开探讨。相关论文参见:郗韬,《王鸣盛诗学思想管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郗韬,《聚合与疏离:王鸣盛诗歌与乾嘉主流诗风的关系》,《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等。
② 沈德潜论诗强调要讲“法”(《说诗晬语》卷上:“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在模拟基础上要表现出自己的真神理(“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理不存也”);王鸣盛重视“我”,而轻视学唐、宋的“法”,与沈德潜存在差异。
③ 按,乾隆九年(1744)秋王鸣盛参加江南乡试中副榜,袁枚为同考官。
④ 相关研究已较多,可参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与嘉道以降的宗宋诗风”;朱则杰,《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张莉,《清代寿苏会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衣若芬,《时间·物质·记忆——清代寿苏会之文化图景》,《长江学术》2016年第4期等。
⑤ 此序见于《宋诗略》卷首,又收入王鸣韶《鹤溪文稿》稿本中,湖南省图书馆藏。
⑥ 相关研究可参青木正儿撰,杨铁婴译,《清代文学评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⑦ 吴之振致宋荦书札谈到编选《宋诗钞》时说:“至振之选诗缘起,因牧斋先生以伪盛唐流弊,后人不可底止,属以选订宋诗救正俗学。不意近来学宋者传染讹谬,滋弊更甚,街谈巷语,堆垛遝絮,李老登诚斋之床,龙褒入山谷之室,遂令海内归咎于《诗钞》之滥觞。复欲辑选三唐之诗以救近日学宋诗者之弊。”书札展现出吴之振顺应诗坛现实变化而调整诗学的事实。该书札见于《宝鉴斋录存所藏宋牧仲存札》卷五,上海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