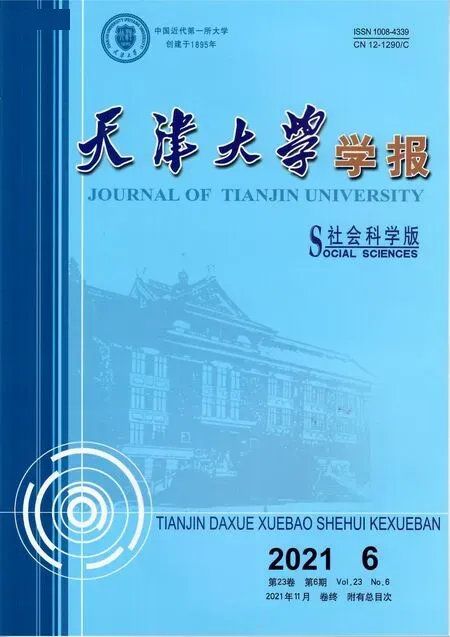论共有人给付之诉的诉讼形态
崔 斌
(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1)
一、 问题的提出
共有人给付之诉长期以来被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民诉解释》第7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与适用均将共有物受到侵害涉讼定为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1]。而实践中,共有人给付之诉类型并非只有一种。在共同共有的财产受到妨害等情形下,仅需要妨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情形下,共有人多数情况下不会一同起诉。
例1:林某为某市A区虹桥路小区5号房屋的产权人,章某某为其临近房屋的产权人,双方系邻居关系。林某购买房屋后,于其房屋左侧道路上搭建铁门一个、两栋别墅间围墙一堵。经交涉无效,章某某诉至法院,要求林某拆除其在5号房屋东侧公用通道上违章搭建的铁门和围墙①。
在例1的情形中,公用通道的所有权归属于全体业主,如果认为此种情形为必要共同诉讼,则需要全体业主一同参加诉讼。那么,便会使妨碍长期不能排除,也会大大增加维护共有利益的成本。由此可见,如对该条僵硬适用,则可能导致共有人在实体法上可以分别实施的权利被架空,而且不利于共有物的保护,此为本文的实践问题。其背后的制度问题是《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之“诉讼标的是共同的”的识别方法较为模糊,对其任意解释的空间较大,司法裁判也未形成一定之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些裁判中认为“请求必然同时影响其他主体”属于“诉讼标的共同”②,而在另一些裁判中则认为“诉讼标的存在牵连”的情形可认为系“诉讼标的共同”③,同时在一些裁判中强调“完全不可分”的情形方为“诉讼标的共同”④。《民诉意见》及《民诉解释》都相当程度上扩大化了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司法实务也基于防范矛盾判决、一次解决纠纷、方便审判等目的,泛化适用必要共同诉讼。但是,这种泛化适用带来了实体权能配置被漠视、权利保护落空、缺乏正当性等问题[2]。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共有人单一诉讼实施权松动的迹象。法院的态度则并无一般性的规律,有的法院认为涉及共有物的诉讼均为必要共同诉讼⑤;有的法院区分情形,认为排除妨害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损害赔偿属于必要共同诉讼⑥。基于这种变化,有学者对共同共有人涉诉的所有情形均纳入必要共同诉讼的做法提出了挑战,认为涉及共有物“持份权”的诉讼应归于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3]。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识别标准,则是“合一判决的必要”[4]。司法裁判也受此影响,出现了认为存在“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以及防止判决冲突、保护当事人利益等政策原因构成的必要共同诉讼”⑦的观点。此处的“合一判决”的必要,实际上是综合了防止矛盾判决、一次解决纠纷、纠纷解决实效等价值考量而作出的“结果论”意义上的结论[5]。这在学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一种只要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不甚合理,那么就归入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调和惯性”[6]。
因此,本文面对的理论问题是如何从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出发,确定共有人给付之诉的诉讼形态。具体的路径为:首先以普通共同诉讼为参照,厘清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基点,进而对其交叉地带进行研究;而后回归实体法,就“同一诉讼标的”语境下实体权利的不同形态进行类型化研究;最后,从诉讼标的、既判力、诉讼目的的视角,对共有人给付之诉的诉讼实施权进行解释论探讨。
二、 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基点
如前所述,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必要共同诉讼的识别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基于多重价值考量的。但其真正的立足点,还是要回到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基点,即回到其核心概念与要件上来。因此,本文将对必要共同诉讼及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基点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其存在模糊的交叉点,为下文讨论提供理论基础。
1. 核心属性:保护不可分割行使的权益
《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以“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标准确立的共同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以“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确立的共同诉讼为普通共同诉讼。任何制度的设置,其背后都有该制度设置的价值基础和目的,若无法将其价值基础和目的澄清,则难以对具体的制度进行研究,也就无法弄清“诉讼标的共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含义。
有学者在讨论共同诉讼的价值和目的时,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的目的均界定为避免矛盾判决、节约诉讼时间、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7]。这确实是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价值共享的部分,但实际上,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价值基础和目的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的制度差异设置的如此之大。我国主流的民事诉讼法教材对于为何设置必要共同诉讼的常见表述为“为了解决当事人共同的权利或共同的义务”[8],“必要共同诉讼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共同诉讼人之间诉讼标的的共同性”[9]等。作为共同诉讼制度源头的德国法,将普通共同诉讼⑧的价值基础界定为“简化程序的利益”,将必要共同诉讼的价值目的界定为“存在统一辩论和裁判”的法律必要性[10]。苏联民事诉讼法⑨也认为:“如果不能同时确定法律关系中其他主体的权利(或义务),就不能解决其中一个主体的权利(或义务)的问题。”[11]因此,从目的和价值基础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必要共同诉讼相较于普通共同诉讼,系基于利益的不可分性,亦即维护共同权利人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而非基于利益的衡量以及防止矛盾判决、纠纷一次性解决等诉讼法上的理由⑩。总结为一句话,即必要共同诉讼的核心属性为保护不可分割行使的权益,这既是必要共同诉讼最为核心的“基点”,也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价值基础和目的所呈现前述样态的根源。
2. 判断标准:诉讼标的不可分
如前所述,必要共同诉讼的核心属性为保护不可分割行使的权益。那么,对应到诉讼法上,即应为作为审理对象的诉讼标的不可分。
(1) 标准选择。明晰了必要共同诉讼的“核心基点”,若要对“诉讼标的不可分”进行解释,还必须明晰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在共同诉讼的识别领域,有学者主张按照二分支学说中的“案件事实”来判断共同诉讼的类型[12]。也有学者主张应该按照相对化的诉讼标的理论来确定共同诉讼的类型[13]。一方面,理论通说和司法实务的一般认识都是旧实体法说,除了德国司法实务界基本接受二分支学说⑪。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用“共同”和“同种类”界定两种类型的共同诉讼,是以“权利”为标准的[14]。同时,虽然我国立法将诉讼标的界定为“法律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按照“合同关系”“侵权关系”这样的“大法律关系”和主从合同等“中法律关系”对给付之诉进行判断均非主流⑫。因此,在给付之诉的语境之下,判断共同诉讼的类型,还应依照旧实体法说,亦即将“请求权”作为识别标准。
(2) “不可分”的一极。如前所述,对于“诉讼标的不可分”的判断标准应采旧实体法说,则典型的诉讼标的同一的情形即实体权利同一且其所有权能均不能分割行使的情形,可以将这类权利称为“不可分割行使型”实体权利。以共有权人涉讼为例,不论是物权法上的共有,还是基于对知识产权等财产权的准共有,共有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共有权。共有权在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情形下都属于同一权利。因此,因共有权而生的请求权,如因处分共有权而生的合同法上的请求权,均应属于全体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的请求权。
例2:甲、乙、丙三人共有一套房屋,甲以自己的名义与丁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丁支付购房款后,甲并未如期交房。丁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甲继续履行合同。此时,乙、丙的诉讼地位为何?
例2中,丁若胜诉,则共有物会归其所有,直接冲击了共有人的根本利益。这种类型的请求权由于关涉全体共有人可能争议的利益,所有权能均不可分割,应由全体共有人共同行使。与此相似的权利,还有以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提起的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⑬、继承人因继承权利涉讼等范围极其限缩的情形。此为共同权利因实体法原因必须共同实施而“不可分”的一极。
3. 作为参照的普通共同诉讼:权利基础或事实 同一
(1) 普通共同诉讼的司法价值考量属性。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通共同诉讼才是共同诉讼的“底色”,必要共同诉讼则为普通共同诉讼的例外⑭。也正是由于必要共同诉讼的例外属性,其保护对象十分清晰——不可分割的利益。这一保护对象的确定,是基于前述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属性——保护不可分割行使的实体权益。而对于普通共同诉讼而言,其并没有像必要共同诉讼那样清晰的核心属性,其存在主要基于司法上的价值考量。基于这种价值考量,《民事诉讼法》第52条将普通共同诉讼的构成核心要件界定为较为模糊的“诉讼标的同种类”⑮。而学界对于如此定义普通共同诉讼的核心要件多有批判,认为这一范围过于狭窄,是造成必要共同诉讼泛化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提出了“存在共同的事实问题”“同一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等标准。
本文认为,对于普通共同诉讼的构成要件中“诉讼标的同种类”不能仅作字面解释,而应探究普通共同诉讼之实质。普通共同诉讼的实质为诉的混合合并⑯,这种合并主要基于效率考量。由此可见,普通共同诉讼最为核心的识别标准是相互独立的诉是否可以合并审理,亦即两诉间是否具备牵连性。以旧实体法说为识别标准的规范出发型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实体权利,那么另一个诉要与其有牵连性,即与该权利有牵连性。如前所述,在给付之诉的语境下,构成诉讼标的的请求权由请求权基础和要件事实构成。那么,请求权基础或要件事实同一的独立的诉,显然具备牵连性,可以构成普通共同诉讼。同时,由于普通共同诉讼还有合并要件的制约,在诉讼标的的层面无需对其进行过于严格的限制。因此,前述“要件事实”可以放宽为生活事实同一即可。
(2) “完全可分”的一极。与必要共同诉讼判断标注下有诉讼标的完全不可分相称,普通共同诉讼也有“完全可分”的一极。“完全可分”的普通共同诉讼的常见类型有多个被害人向同一加害人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同一债权人对相互独立的复数债务人提起的诉讼等情形。《民诉解释》第221条规定之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法院起诉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基于前述判断标准,也属于普通共同诉讼,系“完全可分”的一极。
4. 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交叉地带”
如前所述,对复数权利人或义务人,存在实体权益完全不能分割行使的必要共同诉讼和权利完全独立的普通共同诉讼两极。但在这两极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地带”。
(1) “交叉地带”的具体类型。
例3: 谢某奇是某小区的业主,轩和公司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并利用小区公共区域建成停车位并收取停车费。该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谢某奇单独起诉要求轩和公司停止对公共区域的侵害[15]。
例4: 徐某雇佣刘某建房,2008年9月6日,刘某在施工中被倒塌的楼板砸伤,当天经抢救无效死亡。徐某建房使用的楼板为李某生产和销售,李某属无证经营,其生产的产品也未经安全、合格检验。经鉴定,楼板所含钢筋总量不符合省标规定(无国家统一标准),不当施工方法也是产生安全事故的重大隐患。刘某的父母、妻子及两子女起诉,要求徐某、李某承担赔偿责任。[16]
此处所谓“交叉”,主要指两种情形:一是实体权利常被识别为同一,但共同实施诉讼又因实体法允许部分权利人单独行使而违背处分原则或不利于实体权利保护的情形。如例1和例3,在共有人数量多、无权利代表组织的情形下,如果不允许部分共有人单独起诉,则共有人的共同利益可能受到较大损害,侵害行为也无法得到及时制止。二是实体权利并不同一,但合一作出判决被认为更合适,在我国实务上亦常被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这种情形包含连带责任之诉、不真正连带责任之诉等情形⑰。如例4,刘某死亡的结果是因为楼板质量不合格和施工方法不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共同侵权,两侵权人需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应识别为两个请求权,但实务一般认为基于查明事实需求、一次解决纠纷的考量,应一并审理。介于经典的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之间的“交叉地带”情形,是共同诉讼形态识别的难点。
(2) 基于结果论的“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对于这一交叉地带,理论界给出的主流解释方案为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具体而言,即在第一种情形下,为了权利行使的方便,赋予个别权利人诉讼实施权,但裁判需要合一确定,既判力及于其他权利人[17]。对于第二种情形,解释为基于防止矛盾判决,而有合一判决、既判力扩张及所有权利/义务人的必要。这部分学者认为,继续以实体法标准来界分共同诉讼类型,会直接导致目前被挞伐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泛化”。究其实质,“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之观点,实质上就是特定情形下既判力的扩张。
但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前述必要共同诉讼的价值基础和目的系实体法上维护权利人共同利益的需要,合一确定的必要实际上就是实体法上的必要。另一方面,从规范构成的基础理论来讲,不论实体还是程序规范,其基本模式均为“构成要件+法律效果”。 一个规范的构建和判断应当从体现其本质的构成要件出发,而不是从效果出发。而这部分学者所称之“程序标准”,并非必要共同诉讼的构成要件,实际上是必要共同诉讼的效果。在制度构建和解释的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不同于我国理论界不断扩张的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在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母国——德国,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十分狭窄、适用也十分慎重。具体而言,在德国判例上,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仅限于法律明确规定法律效力发生延伸的共同诉讼情形[18]。在学说上,充其量将争讼权利不可分的情形也纳入进来,如《德国民法典》第1011条规定的共有人可单独实施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19]。日本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也基本如此,覆盖法律规定既判力扩张和共同所有关系本身所涉单独诉讼实施权的情形[20]。
同时,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最为核心的效果即既判力及于未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那么,我国的既判力现状能否容许这种基于论理需求的、较为随意宽泛的既判力扩张?虽然司法解释已经尝试逐步构建我国的既判力规则,如《民诉解释》第247条明确规定了“一事不再理”的情形,第249条规定了诉讼承继情形下的既判力扩张规则。一方面,我国既判力理论尚不十分健全,既判力的相对性尚未为立法明定。另一方面,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破坏最基本的既判力相对性的情形。对既判力的随意破坏,导致我国裁判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受到严峻挑战,同时造成虚假诉讼等难题频出。因此,判断既判力是否扩张不应仅基于论理上的需求,仍应回到实体法的框架之内讨论。
综上所述,探讨必要共同诉讼的识别标准、厘清交叉地带的形态,仍然要回归实体,同时结合共同诉讼设置的价值基础和目的,从请求权的角度来看何谓“同一诉讼标的”。
三、 “交叉地带”语境下的请求权解析
如前所述,必要共同诉讼的基点为保护不可分割的利益,“诉讼标的不可分”语境下存在“完全不可分”的一极,普通共同诉讼存在“完全可分”的一极,二者存在两种情形的“交叉地带”。在这一“交叉地带”中,存在清偿目的同一型、基础权利同一型和请求权同一但无需共同主张型三种实体请求权的样态。
1. 清偿目的同一型
如前述例4,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常常被识别为“同一诉讼标的”,进而被认为是必要共同诉讼。对于连带责任而言,一方面是由于《民诉意见》《民诉解释》等规定扩大了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连带责任确实具有责任承担上的“共同性”。赔偿权利人虽然可以请求任一债务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但一旦一个或数个债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则免除其他义务人的赔偿责任[21],即清偿目的具备唯一性。法院出于防止矛盾判决和一次解决纠纷的目的,并基于清偿目的的唯一性而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程序。而《民法典》第178条第1款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首先,债权人有权请求全部或部分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说明债权人对各个债务人的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其次,请求权的核心是权利义务关系,在连带责任中,权利人的权利对应义务人的多个义务,应当认为权利人享有要求义务人分别履行义务的独立的请求权[22]。从请求权的构成——“权利基础+要件事实”来看,连带责任所涉请求权,请求权基础同一,但由于权利主体不一致,要件事实也当然不一致,故非同一请求权。不真正连带责任则更为明显,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如产品销售者和生产者的责任,以及可以被不真正连带责任涵括的补充责任、先付责任等,被侵权的民事主体有两个以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分别针对负有不同法律义务的侵权人[23]。由于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不同的法律义务,债权人享有的权利也不同,其请求权基础不同一,自然为非同一请求权。
由此可见,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之诉背后的请求权是完全独立的。这一“完全独立”,一方面在于其权利本身的独立,另一方面还在于其并未依托于其他权利而产生。《民诉解释》中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多数情形均属完全独立的请求权,如第58条规定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为共同被告;第66条规定的一般保证债务人和保证人为共同被告;第71条规定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为共同被告;第54条规定的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等。
对于我国《民法典》第307条规定之共有人因共有财产对外产生债务时,该债务为连带债务,债务人可请求任一共有人履行全部债务。共有人的权利一般被识别为同一权利,但立法者为了善意的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共有关系具体情况并不知晓的善意第三人,认为其可以向任一共有人主张部分或全部债权。因为对第三人而言,一般情况下难以获知共有人之间属于何种共有关系,只有使共有人之间承担连带债务,才能防止共有人之间互相推脱履行义务。民法学界也对这一观点表达了支持态度,认为这一安排符合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实际安排和民法原理[24]。因此,共有人因共有财产对外产生债务之情形下,债权人对各共有人享有独立的债权请求权。
2. 基础权利同一型
在实体法上,相互独立的请求权除了前述“完全独立的请求权”,还有基于同一基础性权利而相互独立的请求权(例1和例3所述情形)。《民法典》第302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该条赋予了按份共有人和共同共有人管理共有物的权利,但规定模糊,并未具体界分不同类型的管理行为的权利属性。民法学界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释,认为第三人妨害共有物时,所有物权人均享有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或消除危险的不作为请求权[25]。这种不作为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为全体共同共有人,其与“物权本权”紧密连结在一起,但并非所有权本身[26]。同时,这种请求权的行使,是因保障全体共同共有人的利益,无需其他共有人同意[27]。此为共有人各自享有对共有物为保存行为、改良行为和利用行为的权利[28]。另外,除了物权请求权中的不作为请求权,如果已经因侵害或妨害受到损失,共有人还可能基于《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结合该法第179条,享有侵权法上的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之不作为请求权⑱。通过《民法典》的现有规定和民法理论,可知共有人基于共同的所有权享有可单独行使的不作为请求权。那么,该不作为请求权是同一个请求权抑或相互独立的复数请求权呢?
如前所述,《民法典》将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管理权都一并规定在一条中。但实际上,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在共有物管理方面的原理是不同的。在按份共有中,按份共有人基于其享有的份额(部分所有权)而对共有物享有使用、管理的权利[29]。亦即,每个共有人基于其份额,均享有对共有物全部的独立的使用、管理的权利⑲。那么,由按份共有人独立的使用、管理的权利生发出来的维护共有物完满状态的不作为请求权,即属于独立的权利。而共同共有人的使用的权利是不可分的[30]。因此,共同共有人基于共同的使用、管理的权利而产生的不作为请求权应属于同一请求权。
3. 请求权同一但无需共同主张型
通过前述可知,在实体法上,请求权一般是被分别享有的。但在共有的情形之下,有诸多由各共有人共同享有的请求权。如前所述,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共有人的不作为请求权应属同一请求权。但是,基于及时保护共有物的考量,虽然《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其行使方式系单独行使抑或共同行使,基于及时保护共有物的需要,民法理论通说认为应当允许共同共有人单独行使之。除此之外,共有物返还也是一典型情形。
例5: 某房屋为甲之父母乙、丙在其婚前全款购买,不动产登记簿所载产权人为甲、乙、丙,房屋长期由甲及其妻丁居住。后甲与丁离婚,甲遂要求丁搬出房屋,丁拒不搬出。因此,甲向法院起诉请求丁于10日内搬出,将房屋归还三原告使用。那么,在乙、丙未参与的情况下,甲是否可以单独起诉?如果甲、乙、丙根据协议按份共有该房屋,甲是否可以单独起诉?⑳
如例5所示情形,除不作为请求权外,《民法典》第235条规定之返还原物请求权也属于同一请求权。且在按份共有的情形下,由于共有物在法律上归属于所有共有权人,因此共有物也要向全体共有人返还,而不能向自己返还[30]695。由此可见,共有权人返还共有物请求权在按份共有的情形下属于全体共有人共同享有。这一点在德国民法理论上也得到了印证,《德国民法典》第1011条规定的按份共有情形下对“整个共有物”返还请求权属于所有共有人基于所有权共同享有的请求权。但是,不论德国法、还是我国民法理论,均认为该请求权虽为全体共有人共同享有,但应允许个别按份共有人分别实施。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也有民法学者认为,共有物返还请求权可以由各共有人分别实施,而无需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26]243。有民法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共同共有人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形下,不得主张返还原物[30]693。本文认为,这一争议的核心是共有物不可分割,所有共有人应共同为受领㉑。在共同为受领这一点上来看,个别按份共有人主张共有物返还和个别共同共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可能产生的风险是一致的。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在理论上对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情形下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行使设置不同标准是不恰当的。因此,在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共有物返还请求权均为一个请求权,但实体法上允许各共有人主张向所有共有人返还。另外,前述共有人不作为请求权在两种共有的情形下均可由各共有人主张,那么在物权法上同属物权请求权的返还原物仅允许按份共有人主张,在体系上也是不合适的。
除此之外,因共有物而产生的债权㉒,被我国《民法典》第307条界定为“连带债权”。即任一共有人均可向债务人主张承担全部的给付,债务人给付后,则债权消灭。立法者对于将因共有物而生的债权界定为连带债权的理由与前述将因共有物而生之连带债务界定为共同债务一致,均为“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但前述共同债务确实可以起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作用,而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则不明显。由于单个还是复数的共有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对于债务人利益并无太大影响。因此,有民法学者认为,由于共有权人作为一个整体享有所有权,那么亦应作为一个整体享有债权,按份共有人对外享有的债权应为给付对象和权利行使主体均为全体的不可分之债,共同共有人是共同之债[31]。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符合共有的权利共同属性和维护共有人共同利益的,法国和德国的通说理论也认为,债是否可分取决于债的标的可否在复数债权人间分配[32]。但由于《民法典》沿袭《物权法》的规定,未对其进行修改,仍宜放在请求权同一但无需共同主张的类型中。
四、 共有人诉讼形态之识别
综上所述,在实体法上,加上没有争议属于典型必要共同诉讼的“请求权必须共同主张”,与共有人相关的请求权有四种样态。其中,清偿目的同一型中请求权完全独立;基础权利同一型中请求权生于同一权利但相互独立;请求权同一但无需共同主张型中请求权由权利人共同享有但可分别主张;请求权必须共同主张型中请求权为共同享有且不可分别行使。那么,在诉讼法上,与这四种类型相对应的共同诉讼类型为何,即需实体法与诉讼法有一“交割”。
1. 诉讼标的的检视
诉讼标的是与共同诉讼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层理论”[33],是必要共同诉讼判断的第一道“闸门”。对于诉讼标的并非“同一个”的诉讼,自然就并非必要共同诉讼。而如前所述,本文所采用的诉讼标的识别理论为旧实体法说,故应用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是否独立来检视前述四种样态是否对应同一个诉讼标的㉓。
对于第一种请求权样态范畴之内的对共有人债务之诉,由于债权人请求权完全独立,诉讼标的并非同一。故其不能纳入《民事诉讼法》第52条下的必要共同诉讼,应属普通共同诉讼。而第二种请求权样态范畴之内的按份共有人不作为之诉,其权利基础为同一,但本身并非同一的请求权。且由于各按份共有人分别享有请求权,因此其亦并非必要共同诉讼的涵射范围,应属普通共同诉讼。对于第三种请求权样态范畴之内的共同共有人不作为之诉、共有人对外连带债权之诉、共有物返还之诉而言,请求权为所有共有人共同享有,满足诉讼标的为同一个的要求,但实体法允许共有人单独主张。对于第四种请求权样态范畴之内的共有权相关诉讼,请求权性质和行使方式与共有权本身十分接近,属于同一诉讼标的,且实体法上没有赋予其各共有人分别实施的权能。
2. 共同处分或共同受领必要
对于涉及共有物增减变动的请求权,因其直接基于共有的所有权而发生,且在实体法上并未对应独立的实体实施权。在诉讼法上,也自不能为共有人设置单独诉讼实施权,故涉及共有权的请求权属于共有人给付之诉中最为典型的必要共同诉讼类型。此种情形下,主要涉及的是共有人共同对共有物为处分行为或效力相当的行为的情形,故在实体法上具有“共同处分的必要”。
(1) 既判力视角㉔。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请求权同一的情形下,判断各权利人是否可以单独提起诉讼,进而判断判决既判力是否可以及于所有共同诉讼人,不应仅基于论理上的需要,而要回到实体法的框架内。
先看共同共有人不作为之诉。如前所述,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同一个不作为请求权,但基于《民法典》第300条,民法学界的通说解释是该种情形下共同共有人可以独立行使该权利。同时,由于不作为请求权是要求债务人停止某种行为并在未来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请求权,其并无共同为受领之必要㉕。因此,对共同共有人不作为之诉而言,共同共有人享有独立的诉讼实施权,且无既判力扩张之必要。对于学者担心的因共有人各自享有诉讼实施权、判决效力不扩及所有共有人所可能造成的债务人反复被诉及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一方面,共有人不作为请求权是为了保护全体共有人利益而生,可推定提起不作为之诉的共有人是为维护全体共有人的利益,其他共有人多次起诉同一债务人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共有人,由于请求权系同一,共有人可以选择成为共同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也有第三人参加之诉等制度窗口,可以让其他共有人参与进来。同时,对于共有人胜诉的案件,因为同一权利已经得到了保护,则后诉不具备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即没有诉的利益㉖。对于共有人败诉的案件,纵使先前判决没有预决效力,但其具备证据能力,可以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因其诉讼标的同一,会对法官的心证产生相当影响,对债务人产生损害的可能性亦较小。因此,在共同共有人不作为请求权的情形下,各共有人应享有单独的诉讼实施权,且既判力无需发生扩张。
再看共有物返还之诉。不仅在我国,在比较法上,共有物返还之诉的诉讼形态分歧同样很大。有学者认为共有物返还之诉因诉讼标的同一,但实体法赋予共有人单独诉讼的权利,因此为程序法上的必要共同诉讼。还有学者认为,各共有人享有的是并存型诉讼实施权,分别享有为全体共有人实施诉讼的权能,应为普通共同诉讼。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普通诉讼说[34]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说两种观点。如前所述,在我国实体法的解释上,按份共有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实施权归属于各按份共有人,但必须向全体共有人为返还。共同共有人的物权返还请求权的实施权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无论从及时保护共有物的角度,还是从体系的角度,应该认为共同共有人的返还共有物请求权都是可以单独行使的,但同时也必须向全体共有人为返还。由此可知,一方面我国实体法解释一致认为应当向全体共有人为返还,在实体法上可以解释出为共同受领的必要,在诉讼法上若裁判可以分别作出,则会架空实体法上的“共同受领必要”。另一方面,相对于共有人不作为请求权而言,共有物返还请求权法院作出合一判决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损害都更大,共有人无法及时回复其共有权的根基——共有物,债务人将可能陷入被缠讼的境地。由此可见,共有物返还之诉中,各共有人均享有诉讼实施权,但基于实体法上“共同受领必要”,而需要合一判决。这一结论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论的判断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此处所述之“共同受领必要”来自实体法的安排,而非单纯的论理需要,因而不会对既判力相对性规则产生冲击。
最后看共有人对外“连带债权”之诉。如前所述,我国物权立法将共有人的对外债权界定为“连带债权”,但比较法上并没有将共有人享有的债权界定为连带债权的立法例,学界主流观点是将其废除[35]。在功能上,连带之债是为了使债权的主张和债务的清偿更为便利易行,不可分之债是为了确保给付的整体性,即以统一的行为进行履行[36]。由此可见,将共有人对外债权识别为不可分债权更符合其本质,且若为不可分债权,则必须共同主张,应属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但由于《民法典》沿袭《物权法》规定,其明定之“连带债权”也缺乏民法权威学者的挑战,故在解释论上不应突破其规定,仍应视其为债权人单独实施的共同债权。如此,即与上述共有物返还非常相似,共有人享有独立的诉讼实施权,但由于必须向全体共有人为给付,具有实体法上的“共同受领必要”,应合一判决。
(2) 诉讼目的视角。总结而言,前述既判力视角下,可以发现在同一诉讼标的语境下,不具有实体法上共同处分或受领必要的不作为之诉应属普通共同诉讼。具有共同受领必要的共有物返还之诉则对应既判力的扩张。共有人对外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之诉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典型的必要共同诉讼,但由于《民法典》的现行规定,应归入对应既判力扩张的必要共同诉讼。涉及共有权的请求权,属于必须共同行使的请求权,因此应归入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除了既判力的视角,作为程序法上非常特殊的诉讼类型,必要的共同诉讼的具体类型划分还要接受诉讼目的视角的检视。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必要共同诉讼设置的目的是基于实体法上维护权利人不可分割的利益之需要。实体法上共同处分的必要是共有所有权核心权能的体现,关涉共有关系中最为重大的利益,因此是必要共同诉讼设置所要保障的核心类型。共同受领是共有权的核心权能,且损害赔偿、返还原物等责任承担形式的受领人为谁关系利益重大,法律难以推定单一共有人可以完全代表全体利益,因此,共同受领的情形亦应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保护范围。但与此同时,实体法上对于共有物返还和共有人对外债权设定了各共有人单独实施的权利,诉讼法上直接剥夺其诉讼实施权是难以成立的。但由于其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范畴,且有导致既判力扩张的实体法基础,因此应归入目前探讨较多的“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情形,一旦诉讼系属或判决确定即不能再争讼。
3. 对《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的理解
经过从诉讼目的、诉讼标的理论选择到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类型化再到诉讼法上诉讼标的、既判力、诉讼目的三大理论层次的检视,让我们回到研究的起点——《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一般认为,该款前段规定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对应必要共同诉讼,后段规定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是普通共同诉讼。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前段“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在给付之诉中应该对应请求权同一的情形。但仅仅到这一步还不够,要结合实体法,判断这一共同享有的实体权利是否有共同处分或受领的必要。若无,则应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涵射范围,应归于普通共同诉讼。此时,可以理解为“诉讼标的同一”,但基于实体法的规定,并不“共同”。若有,则一般对应所有共同诉讼人必须共同参加诉讼,即《民事诉讼法》第132条上的规定之“必须共同进行诉讼”。但是,如果像本文分析之共有物返还请求权之诉和共有人对外债权请求权之诉那样,在实体权利层面,规定各权利人均享有独立的实体实施权。那么,就应当对该条规定之“为共同诉讼人”作出可以单独起诉,但判决既判力基于实体法的规定而扩张至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解释。在必要共同诉讼的范畴内,单独诉讼实施权是共同诉讼实施权的例外㉗。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可谓十分狭小,仅限于设置目的范围内维护权利人共同利益的需要,结合实体法具体而言,就是“同一诉讼标的+实体法上共同处分或共同受领”。如果实体法上例外的安排了独立的实体实施权,那么诉讼法上亦应当赋予其独立的诉讼实施权,但因其有实体法上的共同处分或受领必要,既判力应扩张及所有权利人。除此之外,均应属于普通共同诉讼。这一方面验证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之普通共同诉讼作为共同诉讼之底色,必要共同诉讼应为其例外;另一方面验证了不应采取先验的“判决需要合一确定”标准识别“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而应依循实体法-诉讼标的-既判力-诉讼目的的角度进行考量,应将扩张既判力的情形(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作为一般的必要共同诉讼的例外。
4. 如何看待《民诉解释》第72条的规定
前文我们提及《民诉解释》第72条将共有财产权受他人侵害所产生的诉讼界定为必要共同诉讼。但该条作为司法解释,其解释的对象是《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故在对法律的解释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对该条的解释亦应相应发生变化。
(1) 共有人不作为请求权之诉应排除适用。如前所述,必要共同诉讼的判断标准是“诉讼标的同一+实体法上共同处分或受领必要”。按份共有人的不作为请求权给付目的同一但完全独立,不满足“诉讼标的同一”的要求,自非必要共同诉讼。共同共有人的不作为请求权虽然系共有人共同享有的请求权,但实体法赋予了各共有人主张的权利,而且也没有共同处分或受领的必要,故非属必要共同诉讼的范畴。如果将这两种请求权所涉诉讼纳入该条规范范畴,那么该条规定就既包括了必要共同诉讼,也包括了普通共同诉讼。如此,该条就会变成《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的注意规定,且在前述对普通共同诉讼要件解释的语境之下,普通共同诉讼的覆盖范围已经足够广,司法解释再设这样语义模糊的规定实无意义。因此,共有人因共有物被侵害而产生的不作为请求权应该被排除出该条的适用范围。
(2) 解释“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经过检视,我们发现在共有人给付之诉中,返还原物和损害赔偿(共有人对外享有债权)之诉皆属允许部分共有人单独提起诉讼,但既判力扩张及全体共有人的情形。在对该条的官方理解与适用中,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表示“按份共有财产权受到侵害的,需要结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不同案情,来具体分析”,而且因“实践中的共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极为复杂”,故将1992年《民诉意见》第56条规定之“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删去。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该司法解释时,是预留了解释空间的。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此处“为共同诉讼人”应当被分解为:一是在共有物被侵害,且涉及共有权时,无论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都应当将所有共有人列为共同诉讼人;二是在共有物被侵害,但不涉及到共有权时,全体共有人仍为共同诉讼人,但无需一同为诉讼行为,也无需全部列为当事人。
注 释:
①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725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248号民事裁定书。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77号民事裁定书。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37号民事判决书。
⑤ 如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7891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686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绍民终字第108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再60号民事判决书。
⑦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辖终289号民事裁定书。
⑧ 在德国法上被称为“简单共同诉讼”。
⑨ 苏联立法对我国早期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影响很大,如苏联的二元诉权论在早期是我国的通说,参见张卫平的《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连接与统合:从民事诉讼法视角看民法典的编纂》,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⑩ 对于来源于德国法的“诉讼法上的必要共同诉讼”被我国和日本学者称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类型。由于在德国法上,其适用范围极其狭窄,只适用于诉讼法定有明文的既判力扩张类型。
⑪德国诉讼标的理论已经进一步发展,一分支说成为了理论通说,但司法实务界仍然坚持二分支说。
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78号裁定书。
⑬如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债务人和第三人应为共同被告。
⑭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通共同诉讼作为共同诉讼的一般形态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相关观点,参见三木浩一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共同诉讼制度及理论:兼与中国制度的比较》,张慧敏、臧晶译,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2期。
⑮其他要件还有当事人复数、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当事人同意合并审理。
⑯包含诉的客观合并与主客观合并。
⑰相关实体法内容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⑱有学者认为,不作为请求权等“绝对权请求权”不能为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一般侵权责任所容,应以物权法中的物权保全请求权规范为请求权基础。相关观点,参见崔建远《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⑲有民法学者已经对于《物权法》目前将按份共有人和共同共有人的管理、使用权利规定在同一条文中的立法模式进行了挑战,认为将二者置于一起规定,是将性质不同的两种权利放在了一起。
⑳参见(2018)沪0106民初1784号民事判决书。
㉑受领必要相关问题即与诉讼法上必要共同诉讼问题相衔接。
㉒如第三人侵害共有物导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㉓本文的论证也旨在证明,在不卷入诉讼标的识别学说的“混乱战场”的前提下,运用与司法实务和实体法最为贴近的旧说,也能达到限制必要共同诉讼过分扩张的作用。
㉔德国法称之为“程序法上的必要共同诉讼”。
㉕纵使涉及排除妨害中除去妨害物等作为内容,也不涉及向全部共有人为给付的情形。
㉖诉的利益是指对于具体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进行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权利已经消灭或得到了完全救济,又不属于既判力范围的,即属没有诉的利益。相关讨论参见张卫平《诉的利益:内涵、功用与制度设计》,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4期。
㉗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是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的例外,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