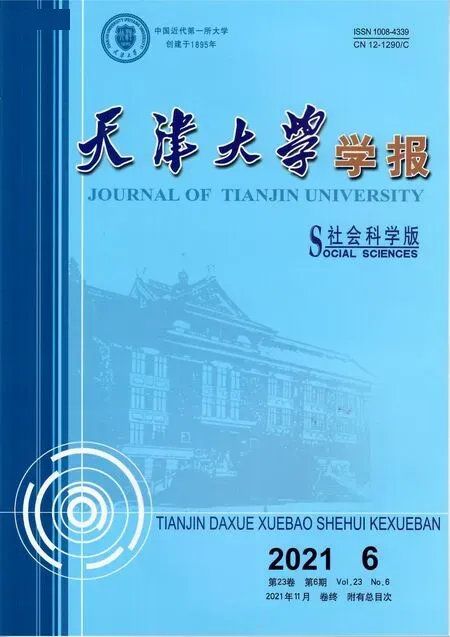青年的成长与历史的展开
——武歆小说的一个主题
艾 翔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革命历史题材为众多读者所熟知的特点之一,便是情感描写的矜持。自从早期的“革命小说”出现的“革命的浪漫蒂克”[1]弊端后,现实主义一直调整个中比例关系,加上对革命目标认识的逐渐规范化与范式化,感情便自然成了一件越来越自然的附属物。确切地说,感情的描写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与肯定,但由于革命任务更为宏大而迫切的特性,作为基本人性的感情变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在武歆最为引人注意的那些作品中,青年人及其感情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这并不妨碍一些重大历史、社会事件成为情节主干。
一、 革命与情感同频共振
武歆的创作还在继续,在已有的作品中,“红色爱情”系列尤为引人注目,关于这个系列的设计初衷,作家如此表述:“以爱情作为视角,表现普通中国青年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抗争、牺牲,表现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坚守,当然还有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内心情感。”[2]从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其小说承接的脉络,即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以及关于“人”和“人性”的理念。用革命的视角和立场写近现代历史重大事件,用艺术的形式解释革命的起源与发展,传达革命精神中体现出的价值理念,摒弃了宏大叙事的模式,将爱情置于显著地位,并且不以塑造改天换地的英雄为目的。武歆是一个非常重视多元文学资源的作家,完全可以妥帖地放置进文学史中,同时又能从文学史中脱颖而出,体现自己独特的创造力。如果按照阎浩岗对《红旗谱》“日常生活描写”[3]的贡献的界定,以及孙犁对人情人性美的诗意书写,可以见到武歆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但将革命日常化后依然保留革命的理念内核与外在气象,则是后者的推陈出新。
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之时,爱情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推崇,从此便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价值共识。后来不断有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各个角度论证爱情其实是一种并非真实存在的人造概念,希望人们不要片面追求这种激情状态而忽视生活乃至生命的本质。究其原因,大概与浪漫主义反抗中世纪宗教对人的束缚相关,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的自主,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爱情这一概念的充实无疑会对这一任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价值构筑整个文化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特征。在封建社会,人们的爱情观念是非常淡薄的,‘爱情’一词本身,也是20世纪受西方文化影响后才产生的。……恩格斯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明确了中西方文化这些基本差异,就不难理解何以爱情成为西方诗歌最核心的主题,……为何中国根深叶茂的诗歌之树上,情诗的硕果寥寥可数”。[4]但凡出现思想解放、文学繁荣的时候,大多有爱情受到高度张扬的现象。
武歆讲述革命历史的切入点在青年学生。既然是学生,自然就有一个逐渐成长的发展历程,从学生到革命者,但又有别于其他作为成长小说的同题材作品。在《延安爱情》中受老师关文波的影响,苏贞逐渐倾向革命,男主角彭登科投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苏贞的爱慕,最初做出的“英雄行为”也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王新语虽然没有如此冲动,但是却抱有相同的情愫。《天津爱情》中陶淑媛投身革命是出于对表兄潘翔升深沉的爱恋,王美生这个带有浓烈美式自由主义思想的海归被发展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同样也是因为与陶淑媛弄假成真的情感。武歆并未动摇传统现实主义革命叙事中“引路人-年轻一代”的结构模式,但真实诠释了青年学生群体的革命起源问题。作家并不急于让这些学生主角被带领快速变身为革命者,而是用大量丰厚的生活细节暴露他们的青涩、莽撞、冲动。王新语站在精英立场表达对农民的不理解,彭登科随工作队下乡与村民产生矛盾、与上级发生直接冲突,北平行动中苏贞在得知彭登科准备暴露身份以确保任务完成后一反常日的冷静,颇为激动地要求方义提供支援。陶淑媛因为对表兄的情感波动,多次直接扰乱了与王美生假扮情侣以刺探情报的任务,王美生同样数次麻痹大意。
通过对相关小说的研究,有学者确认了《红旗谱》中贾湘农一类“代父”形象,充当成长过程中的“引导者”角色。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文艺摒弃了“成长”过程,“代父”形象也随之消失[5]。曾经有一个共识,就是革命时代的人早慧早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做经天纬地的大事,但武歆以为这种观念因为缺乏细节支撑造成了一定误会,青年的成长节奏与是否身处大时代并非绝对对应,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自古皆然,过去与当下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代青年完全可以与当时的青年做比照。作为成长小说重要结构支点的“代父”角色也因此恢复,仔细品味不难再次发现,如苏贞和王美生大约生于1919年,彭登科生于1920年,陶淑媛生于1922年,朱小米大约出生于1923年,许坤善生于1913年,潘翔升生于1918年,陈黛林生于1913年,即使是作为战斗英雄的路大勇也是生于1918年。这些人物的年龄差不超过10岁,基本可以算一代人。也就是说,是一群青年相互扶助着克服困难、摸索前行,过去“红色经典”系列中的革命前辈被淡化。在成长的过程中,“代父”的直接指导也并非多数,主要是青涩的学生们依靠自己的勇气寻求经验。其中,情感占据了重要位置。青年们在追求爱情、经营友情、处理接收到的情感信号的过程中,激发出了血性,学会了欣赏、沉着、冷静、理智以及人际交往所需要的情商,并积极从“代父”对情感的指点中总结经验用于革命实践。在这里,革命与情感实现了本质交流、经验共享,表面上有人还存在“谈情有碍革命”的意识,但实际上正是在这反复来回的交往中自行走向了成熟,完成了学生到革命者的演变。同时也说明,革命与日常并非完全冲突,与情感更不存在矛盾,正因为如此,革命实践才会是符合人性而非反人性的,如此便能解释星星之火何以燎原,这也正是刘卫东所断言:“武歆想建立的,是一个以‘爱情’为中心的‘革命发生学’。”[6]
二、 时空与命运的紧密关联
《延安爱情》带着漫游的色彩,彭登科、苏贞在北平走上街头后,到了西安办事处,彭登科私自决定自己行动,被山中土匪掳去,巧遇李政委和纪排长被营救回延安,后来组织工作队到了临近的李家堡,又随独立团到了山西前线,接到紧急任务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故事后段,彭登科选择留在延安钻研纺织技术。由于感情问题发生思想变化的王新语和倪裴分别去了前线体验生活,又去了赵家窑等地调查水质。
这些年轻的学生不是引路人,只是庞大跟随者队伍中的一员,革命对他们而言是一套宏大的理念,他们是教育对象,无法决定革命的走向。青年学生们对于宏大话语及其实践的感知是通过接收指令,并将自己置身于特定时空环境中,借助外在力量推动自身的变化。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一种被动的而非想象中的主动改变,这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没有经验自然没有方向,青春本来就带有盲目性,有学者直接道明:“启蒙/成长就是不断的试错旅程,不完满,即是生生不息的未来。”[7]被动的过程很粗砺、很痛苦,却又无比深刻。在李家堡做群众工作时,彭登科表现出的冲动和蛮干令一心想着要顺利完成工作的纪队长产生了将其送回延安的念头,苏贞表示反对,认为送回延安反而回避了彭登科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就错失了改正的机会。当然,情感在其中更起了润滑剂的作用,彭登科进独立团是为了跟郑大龙较劲,最终被战斗英雄感染惺惺相惜。正是倪裴的陪伴让彭登科挺过了艰难的时段,令他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除了嘴上硬硬的髭须之外,目光中更有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坚定和成熟稳健。”[8]很难分清这种对信念的坚定和对理想的执着究竟多少来自革命实践,多少来自情感实践。王新语跟随采访队上前线是为了采访郑大龙,创作表现英雄的话剧以证明自己,也便于更了解倾慕的苏贞。
《天津爱情》与《延安爱情》恰好形成一个对比,《天津爱情》是一部仅限于特定城市的独幕剧,场景改变了,小说的面貌自然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作家求新求变的表现。然而变与不变之间也存在一个辩证法,那就是核心理念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是城市,而且是近代天津这样的开埠城市,自然就有不同租界以及老城区的分界,此外作家还特别突出了“书店”和“菜市场”两处“典型地点”。虽然相比《延安爱情》的“广阔天地”这里只能算是尺寸之地,却也人为划分出许多用于叙事的空间,人物同样有一种缩微景观式的漫游特点。当时,革命者从事实践的方式只能是地下工作,与上线沟通的情报传递是由经验更为丰富的潘翔升承担,相对初出茅庐的陶淑媛和王美生则以情侣身份刺探王父以及金融工作的相关消息。不过,即使有科学分工,当陶淑媛长时间与王美生进行零情感基础的情侣扮演时,加上朱小米的外在干扰,也时常出现情绪波动和行为失准,但出于对各自情感的顾忌和地下工作的特殊要求,二人在每次行动中都尽可能自我约束,为了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革命感情——不断屈从,不断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作风,开始理性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而这恰恰又是个体性格成熟的标志。可以说,正是由于敌占区地下工作的训练,实现了人物服务大局与个体发展的统一,而地下工作开展的起点又恰恰是年轻人最绕不开的情感问题。
这部小说有多重阅读角度,最直观的是那个时代的青年革命者从事革命实践的历史叙述,同样也是个体成长的真实记录。因为题为“爱情”,自然也可视为两位主人公从互相抵触到默契直至相互依恋的情感史。在后记中,武歆回忆了写作“前史”,即关于老天津的系列散文,以及作为准备阅读的大量地方文史资料,这些材料成就了《天津爱情》的独特风貌。跟随主人公的视角,不断插入叙事者关于地方史详略得当的解说,包括劝业场、青木公馆、平安电影院、东浮桥菜市场、联青社、祥德斋糕点、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华北证券交易所、西营门外烈士陵园等,这些特殊的空间概念将小说锚定,与特定历史阶段一起营造出强烈的画面感,成为了解天津以及天津为代表的近代开埠城市的窗口。城市的性格,城市的特殊斗争方式,就这样深刻影响了在这里的年轻人,最终携手走向最初厌恶的、富于象征意味的菜市场。与其他小说不同,《天津爱情》除了表达武歆对信念、人性、感情的珍视之外,还传递出了他对这座城市的认同与情感。
到了《归故乡》,作家的视野更为开阔,表面是一个返乡再离乡的故事,其实包含了五层叙述空间:除去钟叶、艾瑞克夫妇从巴黎回到故乡赣南参加祖父祭奠仪式的当下时态,首先是作为双主线叙事的另一支由祖父钟谭林引出的赣南革命史;其次是艾瑞克祖辈(包括祖父和外公)在法德两国抵抗纳粹法西斯的往事,然后是附着在两条主线之下的关于赣南地区的地方史与民俗考察,还有对欧洲冷战时期与当下的描述。在与陈曦的交谈中,武歆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眼中当下年轻人的问题:“我的小孩跟你的年龄接近,我的感触就是他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跟外界的对话和交流几乎没有。而且他的天地非常狭小,只是在意自己很窄小的这么一个范围。其他事都不关心,……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跟他交流沟通。”[9]从中可见他的小说创作有最实际的期待。
三、 女性问题与革命遗产
在《归故乡》一书中,男女主角被设计成跨国婚姻,一方面是为了放大当下青年的情感及婚姻困惑而不至于因夸张导致失真变形,另一方面则暗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视野,即这种困惑不只存在于中国的年轻人中。同时,这种设计容纳了多层次的中国:祖父之前、大量民俗及地方史描写中的传统中国,祖父代表的革命中国,钟叶代表全球化的中国。他们的对立面则是艾瑞克代表的西方世界及背后的世界观,钟叶远涉重洋嫁到法国,也是现代中国进入西方秩序和视野的象征,二人之间的矛盾既是性别差异导致的婚姻矛盾,也是中西崭新全球格局的表现。艾瑞克对这几种视角的态度有所区别,首先,传统文化颇受其倾心,司机小蔡的讲解一度缓和了他与妻子的冷漠关系。赣南传统建筑风格与“风水”概念甚至帮助他突破了设计瓶颈,实现了事业提速,但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表示出极大的不理解,这也体现出欧洲对殖民史的反思还很不够。对于十分欧化且学习比较文学的妻子的行为处处表示不解,二人的关系以冷漠和争辩为主。对于中国,艾瑞克起初了解很少,后来被钟谭林家信中的故事吸引,并同科隆的舅舅开始进行交流,逐渐找到了两国、两个家族以及夫妻二人之间共同的命运,这当然是作家设计的“无巧不成书”。
视野拓展了,热衷爱情故事的武歆仍初心不改。虽然《归故乡》与“红色爱情”系列体现出了明显的变化,但仍然可以归结为自成一体的“红色爱情”系列:赣南爱情、法国爱情与中法爱情。中法之间现实层面的交叠自然是钟叶、艾瑞克的结合,历史层面是二人的祖辈二战期间在中国的接触,同时他们的情感也彼此呼应。艾瑞克祖父曾经的女友艾玛同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后因刺探情报走近了一个德军少校,最后却被同胞处死。与之相似,钟谭林三段婚姻与情感伴侣都是被本地反共武装杀害。可见,女性在历史中受到的戕害之深无关国界。小说丰富的民俗陈列中,作家毫不隐讳旧礼教对妇女的伤害,这正是革命的目的之一。然而革命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牵连到女性,被包办婚姻的刘氏固然是愚昧导致的悲剧,但革命者钟谭林也痛苦地自省,自己的革命是否对刘氏太过不公。至于同为革命同盟的涂彩花和余翠娇都是为保护钟谭林而牺牲,只有享受到革命红利的钟叶才能对丈夫任性地“一半烈焰,一半柔水”。
从刘氏、涂彩花、余翠娇到钟叶之间,发生了什么,令女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答案就在“红色爱情”中。在《天津爱情》中,陶淑媛不满假扮情侣的安排,认为这种不顾真实情感伪造情感的行为没有考虑她的感受,她只是做了一枚棋子。固然这是尚未分清革命工作与现实的区别,但也说明女主角的主体意识已经形成,并且被作者给予了特别关注。如前文所述,对“爱情”的提升与对“人”尤其是女人的提升本是互为表里。随着对时空化的革命的深入体验,陶淑媛不但是个重视情感、表达与交流的独立女性,更认识到革命与爱情中的激情不是常态,平静长情的日常才是最终目的。与陶淑媛、王美生携手走向菜市场的场景相似,彭登科在多次被苏贞拒绝,被磨练得成熟稳重以后,二人终于平静如水地走到了一起。而作为“完美女性”的许坤善不但有高超的马术技能,抹平了同男人的性别差距,在对待与关文波的感情时同样也是波澜不惊,柔情而坚韧,她在工作上体现出的温柔、仔细、沉稳的做事风格,同严冬山的粗暴、急躁、严厉、多次导致失误形成鲜明反差。这正是许坤善成为众多男女青年的精神支柱的原因。事实上,苏贞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这种“完美女性”的色彩:具有领袖气质、成绩优异、枪法卓越、容貌出众、工作能力全面,她还是掌握交际舞、拉丁舞和秧歌的“陕西舞王”,受到很多人爱慕,但依然保持情感自主、人格独立,但毕竟还是青年人,相比许大姐仍显不足。可见,武歆对革命化的“女性特质”格外青睐,并且未将女性塑造陷入“女性化”的泥潭。同青年问题一样,女性问题同革命也无法分离。
审视革命议题,就要落实革命叙述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延安爱情》用绵密的叙事铺展了从1937—1946年的漫长岁月,结尾简略概述了20世纪50年代和新世纪,让一生的革命奋斗历史有了完整的交代。《天津爱情》采用跳跃式的叙述方式,分别讲述了抗战中后期、内战前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直到80年代的往事,节奏短促而快速。在《归故乡》中,钟谭林的家信截止于崇义县解放后不久,尽力还原真实性也是武歆着力的方向之一,扑面而来的真实历史细节不胜枚举,如对延安民风的描摹、初到延安的文人与民众的隔阂、信任瓦解带来的精神崩溃、军队与农民最初的小摩擦、租界内无害无聊的有闲阶级、年轻人玩闹式革命、特殊时空下的人性表演、中西方的矛盾与差异,等等。
经过认真梳理之后,武歆将对革命的理解、接受与传承摆在每个读者面前,或者说是革命遗产问题。其重要性在读过《归故乡》后都会清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当钟叶与艾瑞克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却在赣南重温革命往事时一度得到大大缓和,而家族祭祀活动后又重新陷入激烈纷争。直至最后,科隆的德共党员波尔舅舅动情地讲述了父亲即艾瑞克外公的革命往事,令钟叶感同身受。波尔意图帮助年轻一辈挽救婚姻,通过讲述革命往事表达了诸如不能放弃感情,革命是“为了日常”而非“就是日常本身”、打开自身格局便能更好地理解和融入世界,突破时代局限性保持本心等理念。也就是说,革命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记录,也不仅仅是当下之果的前因,更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当下的生活。跨越历史与国界的爱情故事充分说明,左翼革命对全人类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到最后的终结,应该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如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米兰·昆德拉、赫塔·米勒等人,对欧洲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过一些表达,有过反省和检讨。”[10]今天,“‘根’与超越了狭隘的血缘观的‘祖’相对应,而‘祭’却又包含了两重意义,祭奠和重寻。作为小说的线索情节,祭祖本身就隐喻着我们该如何在信仰逐渐消退、现代性与物质对人们不断挤压的大环境中生存和抗衡。而这种抗衡的突出表现,无疑就是与焦虑的不断角力”[11]。通过叙事方式的不断调整,武歆一直在积极寻找与年轻人交流历史的方式,并试图让他们知道,无论是青年时的问题、女性身份或是各种社会症结,都需要直面历史,用真诚沟通的方式去面对和解决。钟叶最终跳出感情的困境,憧憬“无国界文化”行动,从而走向广阔世界,不正是一种赓续祖父革命精神的“精神还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