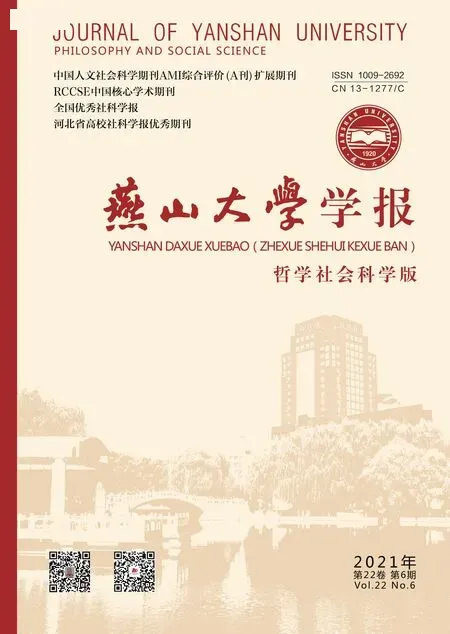黄道周《洪范明义》对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许 卉, 贡 淼
(1.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2.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洪范》是今文《尚书》中的一篇,它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关于古代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首次系统阐述了古代帝王治国应遵循的“大经大法”,“自今天看来,它也确实是一部最系统最完整并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的政治哲学著作。”[1]135黄道周对《洪范》进行诠释,撰成《洪范明义》一书,系统阐述“尧舜之道”“神禹之学”,即传统帝国政治的大纲大法。此书受到其门生的推崇,称《洪范明义》“盖王者性命建极之书也”[2]345。近代大儒马一浮认为:“自来说《尚书》以《洪范》最为难明,汉董生及刘氏向歆父子之徒专推《春秋》灾异,宋后诸儒又多泥于象数,虽各有所明,皆不能无执滞,学者苦之。朱子颇称苏子瞻、曾子固二家,其疏解文字简而能晰,于义则犹有阙。自九峰蔡氏《传》外,独明儒石斋黄氏《明义》特为精醇。”[3]328可以说,在马一浮眼中,《洪范明义》一书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本文通过对其进行剖析,来挖掘和阐发黄道周政治哲学特别是政治合法性思想,以窥其对晚明政治秩序和君权的思考。
一、 明末的政治危机
反思明代之亡,崇祯虽自称非“亡国之君”,但作为政治和君权的最高代表,难辞其咎。孟森先生曾评价:“综帝之世,庙堂所任,以奸谀险谄为多且久,文武忠干之臣,务催折戮辱,或迫使阵亡,或为敌所禽。至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入。而当可以恤民时,君臣锐意刻剥,至临殉难之日,乃叹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为辨别用人之准,则救亡犹有望,乃有几微大柄在手,即不肯发是心,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4]371概言之,孟氏认为崇祯其咎有三:所用非人、专倚内侍、不念民,诸弊端不仅是崇祯一朝的弊病,亦是整个晚明政治窳败之因。
首先,诸弊端破坏了政治体制,影响其正常运行,使得政治体制的运行出现停滞、迟缓状态,产生滥权、腐败、怠工、不作为和胡作为等情况。如宦官专权、滥权,直接破坏了政治制度,且严重影响了其正常运作,带来朝廷上下官员的怠政、不作为,如武宗之时,诸臣“自刘瑾摧折而后,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5]152。就“所用非人”而言,黄道周在崇祯朝深有体会,他称:“自臣入都来,所见诸大臣,举无远猷,动成苛细。治朝著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不经;谈刀笔簿书,则以为知务。片言可折,则藤葛终年;一语相违,则株连四起。”[5]176黄氏之语皆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惜崇祯不悟,仍亲信二人,待之甚厚。尤其温体仁作为内阁首辅,于国事治理上几乎无所作为,重一己之利,“怀私植党,误国覆邦”[6]7905。可见,“所用非人”直接是在日益衰弱的明王朝的心脏上又插了一把利刃。反过来,政治体制运行的不通畅,加剧了诸多弊端丛集。
其次,诸弊端带来政治意识形态危机。程朱理学作为国家权威意识形态,在明末出现淡薄之态,“今天子庶人,一切以仁义尧舜为邪说,则人心败坏何所底止!”[5]733不仅社会群体对于传统儒家思想出现“误解”,且作为显贵群体和精英分子对于儒家经典也持有“非议”态度,“夫仁义、志气、政刑、德礼,此皆天下易解之言;尧、舜、禹、汤、周、孔、孟、程,此非天下难解之姓字也。而达官显人引为怪说,至云通篇无一语可解者。夫使载籍所陈,贤哲所道,止此数字,已自不解;即今士大夫所解者,当为何事乎?”[5]168传统儒家经典作为古典政治的根基,它的动摇直接导致后者处于不稳固的状态,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
概言之,明代晚期所爆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危机,直接导致传统帝国的政治体制构架、王权专制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的挑战与质疑,如“东林的追随者们期望实现皇帝与宫廷权力的下移,这样不仅可以将皇帝的官僚系统完全组织成为六部,而且也可以使地方官员们分享到那些能够影响国家命运的决定权”[7]371。这种期望是企图解构君主的独断权力,同时取消内阁,分权六部,以六部为行政中枢,使得六部能够真正成为权力行使部门。这种想法甚至在身为阁臣的大臣也有出现,如曾任首辅的叶向高在给申时行信中称:“高皇帝罢中书省,分置六部,是明以六部为相也。阁臣无相之实而虚被相之名,所以其害一至于此。今惟遵高皇帝旧制,仍裁阁臣,而以天下事仍责之六部,彼六部操柄在手,事有分属,犹可支持,其与阁臣张空拳,丛群责而徒愤闷以死也,不大相绝哉?”[8]5051虽然是抱怨之语,但可见其对于时存政治运行体制的质疑。
对于君权的合法性问题,有大臣尖锐指出这种合法性并非牢不可破,人君若不念民,则有可能不被民众所接受。“人主能为万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若夫休戚不关,威力是凭,窃夺之己耳!斩刈之己耳!……今乃驱之使乱,臣惧万姓不肯为朝廷屈也。”[8]1014-1015
概言之,传统帝国的政治秩序与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在明末遭到严重的危机,政治体制危机、运行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等,重重迭起、互现。明代政治危机和政治弊端胶葛一起,互为因果,合力动摇了明代的政治大厦。如何加固朱明王朝的统治,对此,怀有强烈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的黄道周力图借助重新阐发儒家经典的方式挖掘和复兴儒家政治哲学的合法性理论,修复和拓展帝国秩序与王权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回应当时在政治危机、社会转型环境、多元思潮下产生的问题与挑战。
二、 黄道周对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浦人,明末大儒,与刘宗周并称“二周”,在明代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洪范明义》一书集中体现了黄道周对政治秩序与君权合法性的思考。
纵观黄道周的《洪范明义》,其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从三个方面论证并回应:首先,通过论证《洪范》作为统治大法的合法性,来加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根基;其次,通过阐释“皇极”来说明统治中统治主体的权力以及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再次,通过论证“锡福天下”来证明统治中政治目的的合法性。通过层层论证,黄道周从理论上论证了儒家所设立的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秩序和王权的合法性。
(一) 统治大法的合法性
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来自于其统治所依赖的统治大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此,黄道周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洪范》所设立的大法的绝对性、不可置疑性,从根本上确立了建立在大法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首先,圣圣相传。圣圣相传保证了《洪范》的神圣性。《洪范》作为统治大法,其传授的过程保证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在《洪范》文本中,作为“天阴骘下民”的人间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的根本原理,是由上天赐予大禹,大禹后又传给后世圣王,至商殷则由箕子保存且陈述给周武王。这样一个神—圣相传的过程,在《洪范明义》中,黄道周以理性精神诠释了《洪范》的授受过程,将“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的天赐说改造为圣传说。他称:“羲易既营,禹畴乃作,咸稽天道,以赞图籙。文王演彖,与箕同时,洪范始著,为周公师。此五圣人,实明历数,爰本图书,以揆世度。”[5]854又称:“《洪范》一书,为尧舜所授于禹汤、周公所得于箕子者。”[10]798也就是说,《洪范》传授是一个圣圣相传的过程,是尧—舜—禹—汤—箕子—周公的过程。这样一个传授过程,褪去了神学色彩,以理性精神和道统权威保证了后世帝王以《洪范》作为统治原则的绝对性和神圣性。因而,他称:“后世圣人有志于尧舜之道、传神禹之学者,必在是篇焉。”[10]799
其次,天道垂象。天道内容保证了《洪范》的真理性。黄道周称:“《洪范》以天道治天下,俯而垂象。”[10]807又称:“古圣少言天道,其言天道者,惟《洪范》、《尧典》二篇,为千古历数之所从出,仲尼、子产未之谈也。”[10]810《洪范》九畴虽是一部关于君主如何治理天下的“统治大法”,但其根源在于天道,正是因为其根源于天道,所以能够成为流传百世的统治大法,他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道,百世所取法也。”[10]799《洪范》的根本是“天地之大道”或者说是“天道”,那么有两层涵义:首先,依照《洪范》而形成的人间政治秩序有着超越性的依据,它是天道在人间的投射;其次,《洪范》是天道的载体,作为统治大法,其具有普遍性、独立性、永恒性。其普遍性表现在它成为天子和庶民共同遵守的客观规则;其独立性表现在它不因某一政权的消亡而消失。最后,《洪范》和天道一样,具有永恒性,这种永恒性表现在它不因某一政权的取或者舍而失去其真理性。
第三,圣人叙布。圣人作为《洪范》的施行主体保证了《洪范》的权威性。《洪范》作为天道而成为人间统治大法,具有不可违背的权威性和绝对性。作为高悬的“道”,其必须向下运化与人贯通,在政治领域内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和力量。同样,作为天道的《洪范》只有和人密切发生关系,才能实现其作为大法的价值。
黄道周释“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彛伦攸叙”,称:“言上天静黙品骘下民,作君作师,以相助和,协其天下,必有常理叙布其间,循之者治,紊之者乱,是以天人感应百世不爽,是圣学之首务也。盖天以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形质不齐,因其生克以为伦叙,而人所受于天者,曰命曰性,性命之原,本于太极。至善不离,至一不二,阴阳五行以是分化,廸吉逆凶,是生治乱。众人皆知为善之得吉,为恶之得凶,而不知其条理伦次。毫发不爽,嘿操其柄,品骘于上,谓之帝天。精明其道,叙布于天下,谓之圣人。”[10]805
黄道周肯定天人之间存在感应,这种感应的基础是阴阳五行的运化,其运化而形成万物和人,此是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看待天人关系。同时,从本体论或者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万物和人之性、命皆本于太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运作形成“彛伦”,顺其则吉,违其则凶,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客观法则。这种客观法则“彛伦”是由圣人叙布于天下,“圣人观形以知理,观性以知命,观其生胜配合以知阴骘相协之意。故生者以协父子,胜者以协君臣,并者以协兄弟。因君臣以协夫妇,因兄弟以协朋友,智由此出,礼由此作,仁由此奋,义由此制,信由此立,腑脏官骸由此以理,道化政刑由此以设,于以制器利用,则大备矣。圣人虽不明著其事,而福殛之所由生,灿然可见。”[10]807圣人根据宇宙根本法则制定了人类政治秩序的法则,因而两者具有同一性,保证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二)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在君主统治中,君主即是政治权威的人格主体,其所施行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其德性、天道以及采用君、师相辅相成的统治法式。
1. 顺性立命:君权的德性根基
在君主统治的政体中,君主作为政治权威的人格主体,其权威的获得在汉唐经学体系中,多以“神授”“天命”的形式确定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洪范》中,开篇亦是以“天命”为君主的个人政治权威提供不可置疑的保障。在早期文明中,“天命”的转移、政治变迁和朝代更替是以“德”为标准,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成为上天检验一个统治者是否拥有统治权的合法性的内在素质。
至宋明,天理论取代天命论,在理学语境之下,合乎天理、顺乎天地之性成为君主受命的根据。在《洪范明义》中,黄道周以鲧和禹不同的结果来说明王者受命的根据在于是否“顺天地之性”。“在昔尧时,鲧恃其力,不率水性,陻塞洪水,乱五行之列。上帝乃震怒,不畀以洪范九畴,民既不得安居,彛伦亦以斁败。盖五行生人,水为之始,水既乱行,则土不稼穯,火不炎上,金木因之,不遂其性。盖天地之有五行,犹人之有五质,五质循叙,而后性命之理可求也。鲧恃其力以拂天地之性,其始以为物皆可以力争,其终至于败壊不可收拾。鲧则殛死,禹乃嗣兴。禹顺水性以修干蛊之业,不乐其有奇功而乐其有常理。上帝知禹不拂人性以汨天道,乃锡禹洪范九畴以骘下民,奠厥居而五常之理无复紊乱。是禹顺水性即所以顺天地之性,顺天地之性,即以立万民之命,其道不敝,其理一也。”[10]805禹因为不拂人性、不汩天道,顺天地之性,所以禹受九畴而王。可见,黄道周以理学化的领域内容,指出君主作为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在于其德性和德行是否合天理。
2. 天道皇极:君王统治的终极根据
具体来说,君主政治统治标准的正当性包括:一是君主建立统治标准的正当性,二是君主实施统治标准的合法性。前者在《洪范》的语境下,以“皇极”为名,后者则强调以“德”或者“纯德”为其本质。
《孔传》云:“皇,大; 极,中也”,“皇极”即“大中”。 朱熹释“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11]3453,将“皇极”解释为君主之标准。黄道周不同于汉儒、朱熹的解释。他释“皇”为“天”, 释“极”为“君”“至”“止”,称“极,君也”[10]807,“极者,至也,止也”[10]816,所以,“皇极”就是“天极”。
相比较而言,朱熹重视的是君主本身的政治权威的现实性问题,并使之成为天下人所遵循的规则,“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为天下至极之标准,则天下之事故莫不协于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观于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谓皇极者也。”[11]3454黄道周则是重视君主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在他看来,“皇极”并非是君主以身作则成为天下人的标准,而是天道或者说天之运行规律和原则。在他看来,“所谓‘五、皇极者’,乃皇天所建其自有之极,即北极也。二气五行,无此北极不能自立,人君虽尊,犹如帝星绕极而动,当思皇天所建之极以为极主。”[10]816他强调君主政治权威的建立是君主以天道为榜样,仿效天道而建立自己的标准。也就是说,天道是君主政治权威正当性的依据和来源,舍此无其他根据,“故上曰‘建用皇极’者,人君之事;此曰‘皇建其有极’者,上天之事也。八畴皆不言用,此独言建,以明君用之为天。体天之所建,即君之所树,人君舍天所建,必无复有以自树者。”[10]816
可见,黄道周并不认同朱子所言的“皇极”是君主自己建立标准以示天下。如果按照朱子的逻辑,“人君以身为表而布命于下,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11]3453,又称“其本皆在人君之心”[11]3458,“其实都在人君身上”[11]3458,虽然君主之为是循天理而为,但是,其为依旧是人之为,则君主既是政治权威的主体,亦是政治权威的来源,结果会导致政治权威无法得到外在客观的支撑和保障。黄道周看到了这个矛盾,他以“天极”诠解“皇极”,即天道的标准是皇极,“极者,天道之所会归也,惟皇作极,而天下会归”[10]819,从而保证皇极的绝对性和超越性。这样,“建用皇极”则是君主法天之标准而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即:“圣人本天以为体,本心以为用,建于不动,以为众动之枢。”[10]807
“皇极”的内容从朱子到黄道周有一个鲜明的提升和拔高,即从人为的准则提升为天道的原则,增强了皇极的天道本体涵义,也增强了政治权威根据的超越性。
在朱熹看来,“皇极”作为人君示以天下臣民的标准,其内在的道德精神是君之“纯德”所代表的道德精神。与朱子不同,黄道周将“皇极”作为天道本身之标准。“北极……皇皇在上,至精至微,至中至一。凡万物之所谓命、谓性、谓心,皆出于此也。自其分布流行、合理与气而言之,则为五行。自其运持推移、动静不分而言之,则谓皇极,《大学》之所谓至善,《中庸》之所谓独也。”[10]807天道、命、性、心、五行、皇极、至善、慎独皆是异名同质,在形而上层面和本体层面来论皇极,则皇极和儒家的至高道德、终极道德相通。因而,“至善”作为皇极的内在道德精神,由于其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因而保证了人君建立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天建有此至善以发皇其用,至于极广极大、极高极明,而皆不离此物。人君法之以建极于心。”[10]816
“皇极”至善的道德精神不仅源于天道,且这种至善的道德精神亦是人性,因而保证了皇极能够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按照皇极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标准由此也获得民众的自愿服从,“天子能建其极,则庶民咸受其福。考其微义,当以敬为建极之本。盖万物之生,非敬不聚,敬而后静,静而后一,一而后变化不测。故福虽有五,极一而已,畴虽有九,敬一而已。天以一极而敛五福,分畀庶民,使庶民共知其有君。君以一敬而敛五福,分畀庶民,使庶民共知其有天。于是庶民皆以君为极,愿保君为万年之主。盖天所锡民与民所锡君者,皆本于至善、纯一不二性命之故,还相与也。”[10]817
3. “道在箕子”:君、师相辅相成的统治法式
黄道周称:“惟有《洪范》一书,为尧舜所授于禹汤、周公所得于箕子者。《易》于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羲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10]798“《易》言‘箕子之明夷’,明禹汤之道在于箕子也。”[10]805既然道在箕子,也就是箕子是道统的传承者。箕子传《洪范》于武王,即是以“师”的身份传授天道,体现了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治统。黄道周认为,武王克商,既而访道于箕子,“道在箕子,则武王必就学于箕子,古称武王师于箕子。《大戴礼》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则访道之礼或当然也。孟子曰‘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汤于伊尹、武王于箕子,盖皆师也。”[10]805
“武王访道于箕子”在后世儒者的解读中,加入了道统和治统之间的张力,有研究者指出,《洪范》开篇武王向箕子访道的情节设置被很多儒家学者(如苏轼、张九成、赵善湘、黄道周等)赋予道统与治统并峙的意义。这些儒家认为,现实统治者并不天然地拥有大法的正当性根据,而是由箕子类型的素王掌握了儒家道统。它可以传授给政治权威,并且在后者悖离的情况下提出合法的批评与抗议。儒家理想的素王成为大法意识的公共人格化身,对现实政治权威持有规范制约的使命。[12]
在黄道周的解读中,除了道统、治统并峙、互掣外,理想的政治权威则是道统和治统的合一。黄道周认为,武王代表的治统和箕子代表的师道或者道统,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天下太平。黄道周称:“上天静默品骘下民,作君、作师,以相助和协其天下,必有常理叙布其间,循之者治,紊之者乱。”[10]805在他看来,“君”和“师”作为两种上天赋予的两种身份,可以统一于一人之身,也就是“圣王”,代表了道和势的完美结合。当然,这两种身份也可以分离,由不同的人分担,即是道和势的分离。分离并不代表着对立,两者亦可以相辅相成,而协和天下,即“天子有道,师保傅治之”[10]806,“天子有道,冢宰治之。”[10]807治统以道统为根据,道统和治统相结合,其实是从天道、真理的角度保证了政治统治标准稳定、有效地在社会中施行。
(三) 统治目的合法性的标准
君主制度下,政治活动目的的合法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由于皇极的道德精神与人性相贯通,因而政治活动目的的正当性衡量标准之一即为是否顺应这种普遍的道德精神,化民于至善之地。其次,政治权威主体的行为活动是否形成了一个道德、公义的政治环境;第三,是否“实现民众福祉”。
1. 代天而为,以至善立民之命
君主活动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亦表现在:由于民众的智慧和道德能力存在不足,所以需要君主引导,君主代天而为,而非师心自用,从而保证了政治活动的正当性。黄道周称:“凡人有私,不能鉴别贤否,惟天无私,居高视下,庶民贤否,贲如草木,善则畀福,不善则畀威。……民之有猷有为有守,此得于天性,天所钟美,以命于君,君则念之,君不敢自以为福。民之未有猷为操守,亦未有显过败类,此得于物命,天所泛爱,以寄于君,君虽不用,天则受之,君不敢自以为威。盖君虽有威福之柄,而皆命之于天,民虽有贤否之殊,亦皆受之于天。必如共、鲧、兜、苖,则与众弃之,谓是天之所不受也。此所谓以至善立民之命也。”[10]817
君主代天而为,并不是随意和主观的,君主的活动和行为都受道德辖制,以道德为根本。在黄道周看来,君主好德和无私的道德行为有助于营造一个公平、至善、和谐的公共政治环境,“贤愚有一定之性,贵贱有一定之命,为攸好以念贤才,而人不敢以为私,为皇受以宽中人,而人不敢以为纵,为时辜以恤下士,而人不敢自为贪,为用咎以儆无良,而人不敢自为竞。”[10]819
2. 帝天所好者,德耳
“帝天所好者,德耳。”[10]818好德作为上天的性质,对于君主具有道德他律的作用,君主应该积极不断地以此自律,以合天德,“天子好德,庶民亦好德”[10]821,形成清明的政治环境,亦保证政治权威的持久性。
王道本于天道①,天道无有好恶,无有偏侧,则君主和社会成员亦应遵循此道,形成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对于圣人来说,“圣人处心极虚极平,其取义极精,去利极微,上揆天心,下揆人性,因好恶之自然而一无所作焉。”[10]819且圣人之好恶本于天德,“好而知恶,恶而知美,利之所在,以义裁之,故正直而荡平。”[10]819对于常人来说,“人则有私,有私好而后作好,有私恶而后作恶,作好作恶而偏陂横生,皇途废塞矣。”[10]819且常人之好恶本于人欲,“好复作好,恶复作恶,道之所在,以意裁之,故偏党而反侧。”[10]819由于圣人和常人在道德上存在差异,所以君主需要如圣人般好恶本于自然,本于天道,以天理为根据,去除自身各种陷于私利的好恶意志,如此“上无作好作恶之君,则下无淫朋比德之民”[10]821,形成了一个合乎天道公义的道德共同体。这样的道德、公义的共同体保证了政治活动目的的正当性。
对于政治活动目的正当性的考察可以从人性实现和完成的角度入手。虽然“凡厥庶民受命于天”[10]817,每个人在本性上都具有超越的来源,体现为善良人性,但由于气质禀赋的清浊差异以及后天的习染,导致个体的性善之端不能充分发展,因此需要由君主权威建极来引导民众,实现和完成至善之性。黄道周称:“凡厥庶民受命于天,以天为极,即有淫比之心,以天示之,无不惕然敬念者。……君既建极以善与人,协于善者,君锡之福,虽五臣相推,十六族并举,不谓之淫朋;不协于善者,君示之威,虽共工滔天,伯鲧圯族,不谓之专德,犹之皇天为民作极,祸福善败一无所私,听民自取,民亦何私之有?惟环向归命于天而已。此所以至善立民之性也。”[10]817人君以天道为标注,其使命不仅在于以天之至善立民之性,亦在于帮助民众实现至善的本性,“凡以变其气质,成其德性,去偏即彛,归于至善之域而已。”[10]822“圣人以天为心,所好惟德。……圣人在上,与茕独者造命,则天下皆至命,与高明者治性,则天下皆至性。无他,诱之好德,以归于善,如是而已。”[10]818
3. 作民父母,锡福万众
君主权威本于为民,不为民则权威不存,“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不为民父母,则无以作天子。”[10]873“作民父母”之一,就是君主施布福祉给民众,民众得福。政治权威通过这种锡福的形式,为民众谋取物质和道德生活的幸福,从而得到民众对其权威的认可。
同时,君主锡福并非擅自而为,而是根据天道而来。“凡在天地之中,吉祥善事,皆敛聚于皇极之前。皇天用此敷锡庶民,庶民以此各正性命,环拱归向,无有违畔于极。人君深知此意,以此敛福敷锡天下,故声色不动而天下从之也。”[10]817“福威皆出于天,君之从天与臣之从君一也,君无好恶,以天为好恶,故好好德而恶不好德者,君无威福,以天为威福,故天之威福,君亦威福之。”[10]893君主根据天意而行使权力,确保了其政治活动目的正当性。
三、 余论
关于《洪范明义》,《四库提要》评介称:“道周兼采众说,参以已见,亦未见其必然。惟其论天人相应之理,意存鉴戒,较王安石之解《洪范》,以天变为无与于人事者,固为胜之,读者取其立言之大旨可也。”[13]798虽然四库馆臣由于学术立场和学风之因,对《洪范明义》评价不高,但是黄道周却很满意,认为自己在错简、讹字等方面的订正是发前人之未知,“皆伏晁之所不稽、郑孔所未说,宋元诸儒稍发其端,明兴诸贤未竟厥绪”[10]798。近人马一浮亦赞其精醇。无论褒贬,正如周中孚所认为的,黄道周作《洪范明义》“志在启其心,以沃君心,故不沾沾于比合经义也”。[14]165黄道周作《洪范明义》一方面论证统治原则的天道性、超越性,以儒家思想规训现实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在尊王的前提下,以天道来约束皇权,实现儒家政治理念和诉求。他对《洪范》政治哲学理论进行阐发,不仅为晚明帝国的政治秩序和统治合法性提供了经典支撑,且试图从儒家经典中找到解决当时政治危机与社会转型下产生的问题的办法。立足于此,即可看出他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反思和寻找解决途径的努力。
注释:
①黄道周释“王”为“天”,认为“遵王之义”,即是“遵天之义”。将王道改换为天道。同时,在《洪范明义》卷上之下《皇极章第七》中,对于“王道荡荡”,释“道”为“天”,则“王道荡荡”即是“王天荡荡”,亦以天道取代王道。见《洪范明义》卷下之中,《皇极章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