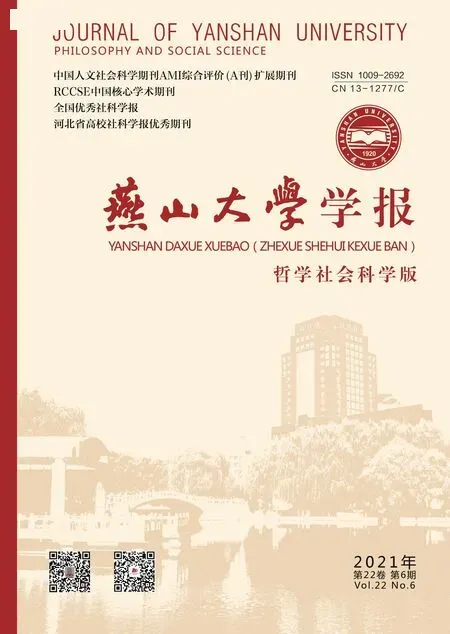郭象“性分”思想的三重解读
吴宁宁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06)
纵览魏晋玄学的学术宝地,郭象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通过对《庄子》的注解和诠释,形成一套他所独有的哲学思想,创立了在本质上崭新的哲学话语。在其众多思想中,“性分”思想是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成为他哲学问题的重要视域。迄今为止,学界对郭象“性分”思想不乏研究,如束际成的《郭象性分论》指出,郭象思想体系中的“性分”是标志不同物种间的种属差异性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的哲学范畴,并分别从生成论和认识论视角指出“性分”是由气化而自然生成,性分决定了人的认识能力的高低。[1]暴庆刚的《郭象的性分论及其理论吊诡》一文认为,郭象的性分论即是自性论,“虽然性分论是郭象哲学中独具特色的理论,但其本身并不圆融,而是内含着性分的先天决定与后天形成、性分与习学、仁义作为普遍之性与特殊之性的三大理论吊诡。”[2]梁涛的《郭象玄学化的“内圣外王”观》一文提出,从郭象的“本性性分论”思想,可以看出其将事物的本性看作是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和动力,而事物的性分则规定了个体的差异,进而确立了玄学的性本体论。[3]此外,王晓毅的《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汤一介的《郭象与魏晋玄学》等著作,也都对“性分”思想作了学理上的探讨。王晓毅认为,“性本体”才是玄学本体论的突出特点,郭象“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性’本体论哲学”。[4]汤一介先生指出,郭象将“理”与“性”进行了统一,认为“只有了解每个事物的‘性分’,才可以讨论每个事物的‘理’。”[5]343可以看出,上述现有的研究成果均主要围绕着“性分”的本体论维度展开思考,对“性分”的理解基本上是就“性分”思想而谈“性分”思想,虽具有哲学上的学理视域但却缺乏实践意义的延展。为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郭象“性分”本体论思想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实践向度的分析,进一步探究其“性分”思想中的实践哲学价值意蕴,以彰显出其“性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 “物之自然,各有性也”之“性”本体论
“性”的观点是郭象全部哲学建构的源泉。庄子认为,“性”是宇宙万物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内在本性。“性者,生之质也。”[6]473对于人而言,人性即是“天下有常然”[6]163,任人性之自然,即是圆满的人性,为此,庄子提倡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摆脱道德说教的束缚,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达到与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庄子对“人性”的探讨奠定了郭象对“人性”作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在庄子那里,虽然对“人性”的本源和境界(逍遥游)进行了描绘,但对于人性该如何实现,以及如何保持人的“本性”纯然并没有作出解答,这一问题在郭象这里得到了完善。
“性”究竟是什么?依郭象之意,“性”义主要有三。其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7]533在“性”的本质理解上,郭象与庄子的思想并无二致,郭象将“性”与“自然”相结合,认为“性”是“自然而然”而形成,“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7]694“性”是万物的天然素质,是天之授,万物具有不同的禀赋,皆是自然所致,万物之“性”天生如此,所以“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7]20,对于万物和人而言,“性”既是万物存在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是自然的本性。可以说,“所谓某一事物的‘性’(自性)、‘本性’、‘性分’等,在郭象和庄子看来都是指某一事物之所以为某一事物者,也就是某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素质(天然如此的素质)。”[5]268
其二,“性”之依据在于“自生”。不同于王弼“以无为本”的万物生成论哲学基础,郭象提出了“物各自生”的观点,“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身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7]50郭象认为,“无”即是“无”(意为没有,什么都不存在),“无”作为一种绝对的虚无,并不具备生成万物的机理,因此,“无”不能作为产生物的依据;而“有”又因为没被产生,所以“有”也不能生成物,现实物各自具有的“有”是所属物的独一无二的“有”,“不足以物众形”,是一种自有。“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7]111在郭象看来,无论是“无”还是“有”均不能成为万物产生的根据,万物生成的根据即在于自身。正因为此,万物能安于自然之性,使本性能无意识地自发存在,对事物自然而然地发挥着根本作用,可称为“本”,“以性言之,则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于本也。”[7]239
其三,“性各有极”“性各有分”,事物的本性具有分限和边界。郭象认为,每一事物之“性”均具有自身特定的分量和限度,称之为“性分”。“性分”是标志不同事物间的种属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哲学范畴。“性分”先天形成,既是万物存在差别的原因所在,也是万物所持有的最高确定性,万物必须在其“性分”的范围内活动,不可任意改变其性,“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7]59对于万物而言,“性分”的所得带有偶然性,但一旦“性分”落实到万物之中,与万物合一,就会使以此性为根据的物具有了必然性。正所谓“一物无性分之前,完全不受决定,一有性分,即绝对受决定”[8],表明了“性分”的绝对性。所以,“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也。”[7]128
为了进一步表达“性”的特质,郭象还将其与“德”相联系,并把这一状态上升到“理”的层面加以肯定。
对于“德”,郭象指出:“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谓之德也。”[7]215“德”就是事成、物和,是事业的成功,万物的融合。而“德则无不得”[7]90,对于万物来说,“得”与“德”是相连的,按照“德”方式去行为,万物总会有所“得”。正因为“德”“无不得”,所以“得”具有特定的获取方式,“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谓德也。”[7]425“得”不是一般意义所指的获得,而是一种自得,“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7]251“自得”即是“自然而得”,是指不借助于任何条件,自身成就自身。就万物来说,能根据自身的自然本性去“得”,顺从自身的本性而运作,就会实现“德”。可以说,通过把“得”“德”打通,在肯定“自得”的基础上,郭象赋予了人性自然以“德”。
“理”是对物性“自足”的概括和凝练,在郭象的《庄子注》中使用十分频繁,钱穆先生曾论述说:“王弼之后有嵇康,亦治庄老,而最善持论,其集中亦常言及理字,然尚可谓其乃自抒己见。至郭象注《庄子》,乃亦处处提及理字,一似弼之注《老易》,而犹有甚焉。”[9]据钱老考证,郭象注《庄子》内篇时用“理”字达七十处,而注《庄子》外杂篇时,用“理”字多达七十六处。郭象指出:“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也。”[7]71物的本性“自足”是至理尽德的根本体现,万物“自足”之性相异,所以“理”也相殊,但万物如果能在自己本性的轨道上依乎自然而实现本性“自足”的价值,就能达到道通为一的至高目标。在这里,郭象把人性“自足”看作是手段方式,“至理”则是目标终点,最终,“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7]631。
由于万物都具有“自得”“自足”的本性,因此郭象指出,在万物自身的体系里,只要满足自己的本性,就意味着保持了自身的自然。个体如果能够使自己的本性完全运作,并且最大限度地实现本性功能的话,社会就会达到理想的状态。“性各有极,苟足其极,则余天下之财也!”[7]25这样,郭象就从另一侧面肯定了个人“尽其性”的特殊价值和社会意义,把保持本性的“自得”“自足”看作是个体最佳价值的体现,是“性分”最理想方式。
二、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的“性分”“自为”实现论
由万物的视角切入,郭象借由性之“自然”“自生”以及“性各有分”建立了其“性”的本体论地位。在“性”本体论的基础上,基于对个体价值的肯定,郭象对人性的“性分”作了进一步地思考,并通过恰当的途径展开“性分”的“自为”之方。
在郭象之前很少有哲学家承认个体的存在价值。儒家、墨家等对于个人价值的思考多数是建立在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下,个人价值无法同社会、国家的整体价值进行平等对话。虽然在魏晋时期,个人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关注,但直到郭象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价值才受到重视,这种重视即是通过“性分”基础上的“自性”发挥来实现的。
如前所述,郭象认为每个个体以各自的“性”为依据而独立“自足”,但个体的“性”有其限定和范围(“性各有分”“性各有极”),在其限定和范围中充分发挥“自性”便是个体自我实现,在本性的范围内充分成就自我实现就是逍遥。[10]相比于庄子的“逍遥”,郭象根据其“性分”思想的需要,对其进行了“曲解”。[11]就庄子而言,其所谓的“逍遥”是一种“无待的逍遥”,亦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绝对自由境界,这种境界只有圣人、神人、至人等具备理想人格的人才能达到。而在郭象这里,“逍遥”则是立足于现实的性分或性命之中,是满足于现实、安于个体之性命[12],万物依其“性分”而“各适其性”,如此则得逍遥。“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大小虽殊,逍遥一也。”[7]9这种逍遥的境界就为个体在自身的“性分”内实现自我价值创设了必然前提。
在表达如何对待“性分”进行行为活动这一问题上,郭象提出了“自为”的观点,“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此无为之至易也。”[7]184郭象指出,“止于本性”的“为”(或适于本性的为)是“自为”,是个体在自身本性内的自生自得,丝毫不能超越“性分”所允许的范围去行为活动,“自为”可以看作是个体行为最理想的状态,能做到“自为”就是一种“无为”之至,而“不能止乎本性”的所作所为,都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不当,“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己。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7]88在郭象看来,世间真正理想的状态应是每个人都做到“自为”,这样就会使个人性情得到最大的发挥,完成个体自身的功用,达致人我和谐的理想状态。虽然郭象认可个人“性分”“自为”的发挥,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每个人“性分”的特殊性,即“素分”。“素分”是与个体俱存的本性天然客观限度,是最原初的本性要求,每个人由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素分”都是不同的。如果个人采用“性足”的方式,能够认知到自己的“分”并知其 “初极”,就会在自己“性分”的限度内发扬本性,进行活动,从而避免超出性的“素分”而使自身陷入困境。“聪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为有余,少方不为不足。……若乃忘其所贵而保其素分,则与性无多而异方俱全矣。”[7]313在这里,“本分”强调的是个体本性所持有的素质和能力,“本用”则是指本性所含有的完备功用。就个体而言,持有的“本分”和“本用”完全一致,有多大的“本分”,就会发挥出多大的“本用”,从而完成性“自为”的目的。
那么人当如何在“自为”基础上保持“性分”?郭象分别采用了“安”“守”“当”等方式来论说,这些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与“性分”合一的过程,进而也体现了如何“性分”的行为之方。
首先,“安”是指安然处之,在郭象看来,每一个个体的“性分”最主要的是是否适当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性分”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的差别。因此个人应安于自己的“本分”,满足于自己的“本分”。“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7]81“安分”不仅是实现自足、自生的条件,也是个体展开其生命价值的驱动轮,个体性能的最大发挥“莫若安于所受之分”。[7]571如果能做到“各安其分”,那么万物在相异系统中所存在的大小、多少的差别都会在个体自身系统的自足中得到消解[13],从而营造出一片万物和谐的图景。
其次,“守”是从安守、持守的角度指明的含义,其比“安分”要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古人不随无崖之知,守其分内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后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后归之如溪谷也。”[7]1095“守分”的意义在于能使人“全其性”,郭象认为,只有“性全”的人,才能达及天下,因此“守分”是与天下相一致的行为,“守分”是前提和保证,“及天下”则是追求的目标境界。同时,“守分”与保全性命还相属相连,如果个体认为自身的“性分”不完备而去追求完备进而破坏了“守分”,就会失去生存的依据,“不守其分而求备焉,所以恶分也……不反守其分内,则其死不久。”[7]798因此可知,“守分”是个体全其性和实现最大生命价值的前提,个体必须持守自身的“性分”,从而达到人与社会的自然安定。
最后,“当”是承当、担当。“当分”不同于“安分”和“守分”,它表明的是一种个体的主动性,客观上体现为每个人“各当其能”“各司其任”的分内职责。“夫臣妾但各当其分,未为不足以相治也。”[7]58“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7]465“当分”要求个人在“安分”“守分”基础上,主动与其“分”保持一致,既是一种行为的承担和履行,同时也是个体在自己本分内具有的角色意识,表明个体最大价值的体现。“对郭象来说,当分是检验安分和守分程度的标准,它体现着个体对自身本分的责任,它是安分和守分的归宿。”[14]285
郭象分别从“各安其分”“自守其分”“各当其分”的向度出发,论述了个体“性分”行为的当为之方,这些行为的方式依本性“自得”“自足”的特点而产生,它要求个体了解和重视本性中“分”的作用和价值,进而在个体“性分”的限度内,最大限度地实践自己的才能天赋,完成自己的本分职责。
三、 “群材各自得、万物各自为”的“性分”实践论
郭象的“性分”思想并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和实现的层面,而是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在社会层面予以实践论证,一方面将其作为社会统治者治世的基本遵循,要求君主将无为而治与民自治进行统一,实现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另一方面将其与圣人的理想人格进行统一,达致其从现实到理想的统一维度。
在仁义礼教君臣制度方面,庄子和郭象表现为不同的态度。庄子主张废止礼教和君主等级制度,回归到一种无君无臣、无上无下的玄同状态;郭象则认为仁义礼教等是属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内容之一,仁义礼教对人或人伦来说,不是外物使之为然,而是天然如此的“自然”,“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7]58因此社会上有君臣上下、尊卑先后的等级秩序具有相对合理性,是不可无的。郭象的这种观点无疑为君主实行名教统治提供了合乎人性的合理外衣。基于这一观点,郭象为君主设计了一个“无为而治”的理想统治模式。同个体“性分”采取“自为”相一致,郭象认为君主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应尊重个体“性分”本性的特点,采取“顺万物之自为,因万民之自性”的“无为”统治方式。在郭象看来,“因其性而任之则治,反其性而凌之则乱”[7]398,“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则大均也”[7]873对于统治者而言,能否依据人的本性特点来治理民众,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因此,在治理社会时君主应依据民众的本性来治世,使社会上的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自足”,个人才性得到最好的体现。
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上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在“性分”上不尽相同,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存在着与各自“性分”相匹配的社会分工,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君主能根据每个人“性分”的特殊性最大限度地辅助万民在本性之内各司其职。“夫无为之体大矣,天下何所为哉!故主上不为冢宰之任,则伊吕静而司尹矣;冢宰不为百官之所执,则百官静而御事矣;百官不为万民之所务,则万民静而安其业矣;万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则天下之彼我静而自得矣。”[7]461这里的“冢宰之任”“百官之所执”“万民之所务”“彼我之所能”显示的是不同的职业身份,这些职业身份均具有不同的职责和职能,理想社会应是每个人都能在符合自身“性”质的基础上,做到各司其职,各展其性,因此君主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对每个人的本性予以尊重和重视,任人唯贤,不一味地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个体的社会价值,而是要以是否尽到与自己“性分”相一致的社会责任为标准。作为社会治理者的君主应该知道,无论个体存有多大的差异性,其所起的社会效用和具有的社会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即“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7]7。如果君主能够让社会每个人“安其所司”,各尽其能,“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7]466。这就是郭象所设想的君主以“无为”治天下与万民“自性”统一的“性分”实践设想。
为了更好地凸显“性分”思想的实践价值,郭象还把遵循万民“性分”本性上的“自为”特征进一步发挥,体现在他的理想圣人人格中。
不同于儒家只注重现世“人事”的圣人人格和道家超脱现实的圣人设想,郭象把儒道相统一,认为圣人既身处“人事”,心又不执着于“人事”,而是游于玄外,在精神上逍遥自得,圣人“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7]268,是“外内相冥”合一的理想人格,这种“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7]28的圣人,无疑是整合道家出世和儒家入世为一体的思想结晶。郭象指出,圣人人格体现在“任世之自成”“任世之自得”[7]552的无为。“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7]369这里的“无为”就是因、顺、随、任万民的自为,是一种有限度的有为,“其相对于道家的无为是一种有为,相对于儒家的有为又是一种无为”[14],它不是儒家雕琢人性,化育万民的有为,而是因任民之自性的有为。对于治世的圣人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根据人的能力给予适当的任用,但在任用的过程中自己却不进行干预,其所要追求的客观效果就是要“乘万物御群材之所为,使群材各自得,万物各自为,则天下莫不逍遥矣”[7]594。圣人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圣人是了解自己、他人以及万物本性的人,在对待他人方面,能够同等地看待他人,同时能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合规律、自觉地去维护他们的自性,成就不同的人,“性之所能,不得不为;性所不能,不得强为。”[7]973因此说,“圣人无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圣也。圣能任世之自得耳。”[7]552而正是在圣人任“自成”“自得”的外化条件下,人乃至万物都能够按照各自的本性而自行、自为、自化,体现出遵循“性分”的实践价值。
四、 结论
不言而喻,郭象对人性及“性分”的思考,不仅深刻而且具体,其深刻性表现在从人性之自然和人性本质的视角来规定“性分”的本体问题,并以“安”“守”“当”作为实现人之本性的最佳方式;其具体性则见于对“性分”实践运作的设计,实现个人才性的最大发挥,二者的整合,构成了他关于“性分”的系统思想。当然,作为魏晋时期的时代产物,郭象“性分”思想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特点,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他在“性分”思想的思考上,体现出一种思想上的特殊性:如一方面郭象主张人的“性分”应是守其本然之性的一种天爵,应因人之本性;另一方面他又认可与其“分”保持一致的当其职分的人爵,进而使得郭象的思想中带有着维护现行秩序与体制的思想倾向。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的,郭象“在‘性分’之内实现‘能动性’的观点正是魏晋门阀等级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5]353,成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思想产物。
但不可否认的是,郭象对于“性分”的思考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价值,社会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开展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积累,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离不开对“人”的追求和完善,如何更好地发掘出人本身所具有的最大潜能,进而使这些潜能最大化地投入到社会的建设中是社会最需要解决和思考的问题。郭象“性分”思想所推重的个体具有的角色意识、尊重“本性”基础上的个体“自为”举措,以及社会治理者如何使万民“各司其任”的治理观点,不仅包含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如何展现自己才能的当为之方,而且也为社会治理者指明了实践向度,为理想社会的治理提供了诸多可以借鉴的现实价值。理想的治理应该如郭象所设想的“因任民之自性的有为”模式,也就是治理者在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实施方面认识到自身的职能所在,以成就不同的人在各自不同职位上发挥最佳才能为目标,尽全力为社会个人提供最为广阔的施展舞台,让社会成员都能找到最为适宜的发展模式,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