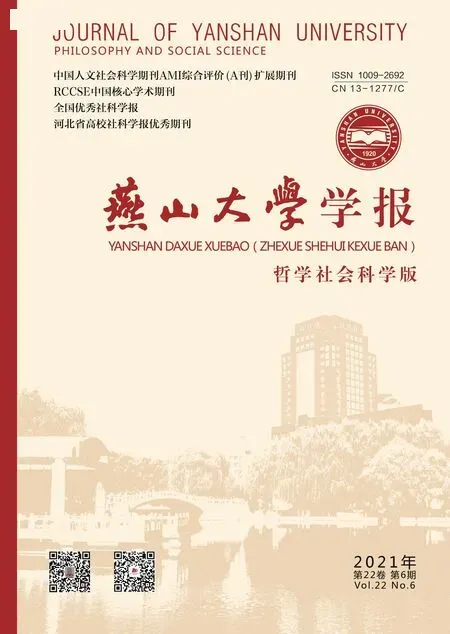20世纪域外杜甫英译专著之文化语境、诠释立场及影响
江 岚
(美国圣·彼得大学,新泽西州 泽西市 07306)
一、 引言
在域外唐诗英译的历史进程中,当西方世界开始尝试着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去了解中华文化精神,他们意识到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之经典,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之冠冕。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一类的介绍性文字,在介绍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的著述中并不鲜见。但真正涉及到唐诗作品译介,重李轻杜的现象长期存在。如知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完成了对中国文学史全景描绘,虽然他肯定杜甫的诗名“直追伟大的李白”,但他译出的杜甫作品总数也只是李白的二分之一。能够将李杜二人并列于同等重要位置上的,以首开唐诗专门译介先河的威廉姆·弗莱彻(W.J.B.Fletcher,1879—1933)为第一人。
弗莱彻曾经是英国政府驻华领事馆的职官,任满后留在广州,任中山大学英语教授,后来逝世于广州。他的《英译唐诗选》(GemsofChineseVerse,1919)和《英译唐诗选续集》(MoreGemsfromChinesePoetry,1925)这两本译著,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断代唐诗英译专书。两书都以弗莱彻“致敬李白和杜甫”的小诗开篇,编排体例统一:李白一卷,杜甫一卷,其他诗人合一卷。从译出作品的数量上来看,杜诗总数还比李诗多二十余首,这“应该是出于填补差距,想要西方读者多了解杜甫一点的理由,从他个人的角度,他对李杜的喜爱和推崇并没有高低上下的差别。”①
1929年,杜甫英译专著出现,英语世界的杜甫与杜诗专门译介研究从此开启,也带来一个在域外唐诗英译的领域里十分罕见又十分有趣的现象: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杜甫英译专著难以确认。因为杜甫专门译介的“开创性文本”一出现就是两部,同年同月出版发行。更有意思的是,两位如此推崇杜甫的译者,都不是经院派汉学家,又都是女性。
二、 杜诗英译的先驱译者
1. 艾斯珂夫人的杜甫译介
芙洛伦丝·艾斯珂(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1878—1942),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是在上海经商的加拿大人,母亲是美国人。芙洛伦丝在上海渡过了大部分童年岁月,十一岁回美国波士顿接受学校教育。在美国求学期间,她经常回上海探望父母,继续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大学毕业后,芙洛伦丝返回上海,一边进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工作,一边继续潜心学习汉语和中国古典诗歌。1897年,这个当时在上海洋行圈里有名的美才女嫁给了英国商人弗朗西斯艾斯珂(Francis Ayscough,1859—1933),成为艾斯珂夫人。1917年,艾斯珂夫人携带大量中国书画艺术私人藏品返回美国布展。为了能让观众既能欣赏到视觉效果的美感,又能理解书法内容的诗情,她将展品中的文字内容大致翻译成英文之后,请好友艾米·洛维尔 (Amy Lowell,1874—1925)帮忙润色。而后者,此时已是美国现代诗坛上声名鹊起的诗人兼诗歌评论家。中国书画作品在美国的此次大规模公开展出,轰动了当时一片东方热的文化界,出版商当场建议二人继续联手翻译更多中国古典诗歌,这就催生了《松花笺:中国诗歌选译》(Fir-FlowerTablets,1921)②一书。
《松花笺:中国诗歌选译》(以下简称《松花笺》)由艾斯珂夫人负责选诗、逐字翻译并给出必要的注解,洛维尔负责修改、润色。自出版之日起造成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堪为汉学家与名诗人合作向英语世界推介中国古典诗歌之经典成功案例。此书的长篇前言由艾斯珂夫人撰写,文中说明了她的三大选诗标准:其一,尽量避免典故;其二,尽量避免与此前他人选译的重复;其三,“从中国人的角度”选择。头两条很好理解,第三条的“中国人角度”是什么呢?
在艾斯珂夫人看来,此前西方译家选译中国古典诗歌,或出于译者个人喜好,或出于容易被目标读者接受的考量,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偏颇。那些以英语文学“Poetry”的概念简单套用于汉语“诗歌”范畴,把戏曲唱词或民间歌谣也选上的,又失于太宽泛。她所选的,是那些被历代中国人公认的“古典诗歌精华”。因此《松花笺》的内容以唐诗为主,在唐代众多诗人中,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中国人公认的三大家。三人之中,关于白居易,已有英国知名东方学家、翻译家兼诗人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的专门译介珠玉在前,因而遵循她的选诗标准二,她只选入一首白诗。在李、杜二人之间,尽管西方人一提到中国诗歌就会想到李太白,中国人却认为杜甫是一位“学者诗人”(poet of scholars),李白则只是一位“大众诗人”(people’s poet)。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学者”,包括官吏,才处于最受尊敬的上层。她坦承自己受中国老师楚能先生[音译,Mr.Nung Chu]影响,最为欣赏杜诗写景状物之绵丽,摹写现实生活之精确。接着翻译、引用了不少元稹、韩愈、陈正敏、胡应麟等人对李、杜的评价,让这些“渗透力(penetration)”足够惊人的诗论去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李、杜二人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仅从《松花笺》的内容来看,选译李诗数量多达83首,高居全书之冠,杜诗只有13首,表面上看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同期译本似乎并无不同。但艾斯珂夫人的这篇前言,是域外唐诗英译的历史进程中,首次提及重李轻杜这个问题并予以公开驳斥的文字。而且,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松花笺》之成书,先有出版社以市场营销为导向的策划,后有大诗人洛维尔的强势参与,选诗数量不见得能充分体现艾斯珂夫人的个人意愿。
事实上,艾斯珂夫人后来在《中国诗人杜甫传》(TuFu,TheAutobiographyofAChinesePoet)③的前言里提到过,最终确定《松花笺》的译文终稿之时,她和洛维尔的意见有不少出入。所以,在楚能先生帮助下,她参考清代杨伦的注本《杜诗镜铨》,独立完成了《中国诗人杜甫传》。此书以诗歌编年译本的体例,按照杜甫年谱顺序,译介了他童年到中年时期的一百多首作品,讲述他在公元712—759年的相关经历。艾斯珂夫人认为,此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介绍杜甫及其作品的专著。她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位杰出的美国作家兼翻译家,昂德伍夫人(Edna Worthley Underwood,1873—1961),译介杜甫的进度恰与她同步。
2. 昂德伍夫人的杜甫译介
昂德伍夫人原名Julia Edna Worthley,出生于美国缅因州一个英裔的世代书香家庭。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语言天赋极高,精通西班牙语、俄语、波西米亚语、克罗地亚语、波兰语、巴西语等至少五、六门语言。她的阅读广泛,数量巨大,令人刮目相看。她从十几岁起开始一边创作,一边尝试翻译其他语言的诗歌。因不大喜欢Julia 这个名字,发表作品的时候直接把自己的中间名(middle name)Edna放在前面,早年的小说创作曾轰动一时。24岁那年,她嫁给了堪萨斯城里一个珠宝商人Earl Underwood。婚后不久,她随丈夫的工作变动移居纽约,此后一边跟着丈夫到世界各地出差,给他当翻译,同时进入了她自己创作和翻译的旺盛期,成为美国文学界和诗歌翻译界鼎鼎有名的“Edna Worthley Underwood”,昂德伍夫人。1930年代以后,她越来越专注于翻译,先后因为译介拉丁语诗人、墨西哥诗人和海地诗人获得过很高的荣誉。④
昂德伍夫人并不懂中文,她也不是学者,她的“中国印象”和此前此后的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不同且十分奇特,其中只有一个如梦如幻又非梦非幻的“概念大唐诗国”:
“……(公元七世纪、八世纪)这一时期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因为满满一国的人们都是艺术家。波斯、阿拉伯、中国、印度,成为美之制造业的魔术师。在这片盛产亚洲天才的土地的中心区,杜甫诞生了。他的时代至关重要,那是一个思想强大,情感丰富的精神动荡时代。八世纪初,也就是杜甫的时代,一名使者从土耳其、波斯来到了中国。来自土耳其的这一位提出了要为王子建造一座宫殿的建议,中方表示愿意合作并提供帮助。拥有魔力的中国工匠们被派去从事这项工作,他们的唐代艺术理想随后向其他国家散播,抵达了波斯,又触及了南亚。这种罕见的,奇妙的,以艺术美感统治东方的现象,就像曾经的希腊以同等的视野、美、辩才和足够的技术力量统治西方一样……”⑤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昂德伍夫人之所以起意去译介唐诗,并专门译介杜甫,极可能是因为1919年前后,她译介日本诗歌时接触到的一批日本诗人。当她结识了朱其璜(Chi-Hwang Chu),便有了解决语言障碍的助力。1928年,昂德伍夫人和朱其璜合译出“TheBookofSevenSongsbyTuFu”,即杜甫的组诗《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次年,两人合译的《杜甫:神州月下的行吟诗人》(TuFu:WandererandMinstrelunderMoonsofCathay)⑥被隆重推出,不仅有普通版,还附带有两个小册子,即杜甫的《同谷七歌》和《三大中国名篇》(ThreeChineseMasterpieces)⑦,还有50册精装签名的限量收藏版。这个收藏版全部用日本精制仿皮纸印制,封面用中国丝绸和浮金花织锦缎,堪称豪华。可惜这个号称译介杜诗300余首的文本,内容杂乱,错漏到处都是。有些是同一首诗被重复翻译,以不同题目置于书中的不同位置且无说明;有的是截取不同篇章中的诗句拼凑而成;有的夹杂了大量昂德伍夫人自己的诗句;还有的根本不是杜诗原文的翻译,而是俞第德《白玉诗书》的转译。看来除了字词解释之外,朱其璜对这个译本的贡献很有限。
中国文学素养深厚的行家们对这样的译本自然不屑一顾,华裔史学大家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先生曾评价过,《神州月下》“完全没有任何编排原则”,乏善可陈。就连同样不大懂中文,以转译称雄汉诗英译界的前辈克莱默—班(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也在充分肯定昂德伍夫人“扫除西方偏见灰尘”的努力之后,认为这个译本展示的只是“昂德伍夫人亲切和蔼的个性,杜甫则远远站在画面的背景中”⑧。 除了译诗之外,克莱默—班也大力肯定昂德伍夫人为此书撰写的序言。这篇序言长达30多页,用散文诗的语言介绍杜甫生平和宋、元以来中国诗学界对杜甫的认识和评价,站在中西文化比较和世界文学的高度上描述杜甫及其作品,的确值得一读。序言之前,昂德伍夫人特地将《神州月下》标注为自己译出的第一本杜甫诗集,且称此书是“世界上第一本在中国之外出版的杜甫作品,大概也是第一本中国诗人的个人诗集”。这个自我定位显然过高了,《神州月下》肯定不是中国本土以外“第一本中国诗人的个人诗集”。至于“第一本域外英译杜甫诗集”的地位,也要和艾斯珂夫人的《中国诗人杜甫传》并列了。当然,即便如此,昂德伍夫人也依然是域外英译杜甫的先驱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
三、 英语世界的杜甫系统译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十数年间,杜诗专门译介的成果堪为域外唐诗译介领域最醒目的重大进展之一。这个过程中,艾斯珂夫人的贡献还是要比昂德伍夫人大得多。到1934年,她又出版了《一位中国诗人的游踪:江湖客杜甫》(TravelsofaChinesePoet:TuFu,GuestofRiversandLakes)⑨,译出了三百多首杜甫诗歌,主要涵盖公元759—770年间,杜甫老年和生病时期的经历。最后以杜甫生前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三十六韵 奉呈湖南亲友》收尾。两卷本加起来,艾斯珂夫人不仅译出了大量的杜甫作品,选译和编排方式也突出了杜诗的“诗史”特质。至此,艾斯珂夫人成为英语世界系统译介杜甫第一人。克莱默—班高度称扬她的译笔,认为这比此前几乎所有的杜诗译介都更能体现真正的杜甫:
“其他人,包括这篇评论的作者,试图把杜甫描绘成我们想象中的他,让他重新骑上他的马,或者呈现他扬帆漂流到他梦想之都(的样子)。但艾斯珂夫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比她的天才同事艾米·洛厄尔更聪明,比安德伍德夫人更聪明,比脱不了牛津学究气的阿瑟·韦利先生更聪明。‘当我们想象我们在描绘别人时,’正如Emile Hovelaque⑩所指出的,‘我们画的是我们自己的肖像’。而翻译,尤其是中文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和替代的努力……通过自我牺牲的行为,通过压制她的文学自我,艾斯珂夫人在翻译艺术上完成了一场革命。”
而且,和昂德伍夫人相比,艾斯珂夫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深入得多。她终身致力于向英语世界揭示中华风物真实的且在西方想象之外的广阔丰饶,还有《中国镜子:表象背后》(ChineseMirror:BeingReflectionsoftheRealityBehindAppearance,1925)、《关于远东的好书:中国历史概要》(FriendlyBooksonFarCathay:aSynopsisofChineseHistory,1929)和《鞭炮的国度:年轻读者的中国世界图说》(FirecrackerLand:PicturesoftheChineseWorldforYoungReaders,1932)等书籍早已出版,因图文并茂、故事性强,语言通俗易懂,而深为年轻一代读者所喜爱,且早就进入了美国中小学的学生阅读推介书单。这个发行渠道优势让很多译家望尘莫及。所以,尽管汉学界的专家们对她翻译杜甫诗歌的质量褒贬不一,她的《杜甫传》两卷本依然和她的其他书籍一起,是美国中小学生了解中华历史文化与社会风俗民情的常用读本。
历史上从事唐诗英译的域外译家们很多,若将他们以专业背景大略分组,则经院派学者们是一组,文学界译家们是另一组。通常情况下,当文学译家们对某位中国诗人的译介引起了共同关注,学者译家们便会继之以更“接近原文”的翻译,试图匡正、补充前者文本的缺失。李白、白居易、寒山、王维等诗人专门译介的发展,都清晰存在类似轨迹,到了杜甫也一样。
1952年,华裔学者洪业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TuFu:China’sGreatestPoet)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按杜甫年谱次序编排,译介了杜诗374首,体例和艾斯珂夫人的两卷本类似。为了更准确地传达杜甫的思想和精神,译文中带有大量注释。虑及大众读者和学术界读者不同的阅读需要,这些注释被作为姐妹篇单独成书,《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参校副本》(ASupplementaryVolumeofNotesforTuFu:China’sGreatestPoet),也于同一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洪业一生的学术成果大多散逸,这两本书是他仅存的专著。两书相继,洪业不仅系统译介了大量杜甫作品,还对选译过同一首杜诗的其他译者和译本情况做了专门的评点、说明,在英美的杜甫和杜诗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洪业因此成为英语世界一流的杜甫评传作家和评论家。
洪业,字鹿芩,号煨莲,福建侯官人,以编纂引得(Index)知名,治学严谨细密,享誉历史学界。其生平可参考陈毓贤所作洪业访谈回忆录《洪业传》。洪业于1923年起任教于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1930年领衔筹办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引得编纂处”,期间主持编纂了64 种、81册的中国古典文献引得,并曾亲自为《白虎通》《仪礼 》《春秋经传》及《杜诗》等《引得》作序,其中的《〈杜诗引得〉序》篇幅最长、内容与考据最为详实。文中梳理了大量杜诗学的传统文献资料,将有关杜集的许多伪作、辗转因袭的版本讹误及权威评述一一列举说明,使杜甫生平行迹与杜诗集的面貌更为清晰,赋予了杜工部诗集文献学的价值。
洪业曾在1962年发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文中追叙他从事杜诗研究的动机,提及他幼得家学陶养,及至年长,“对于杜诗的了解欣赏,我自觉有猛进的成绩。”且生逢国家多难之时,“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日本侵华期间,洪业及多位名教授因反日被捕下狱,洪业曾在狱中立誓,一旦重获自由必加倍努力研究杜甫。战后赴美讲学,适逢意象派诗人们掀起的“东方文化热”余响犹在,而杜诗却长期遭英美译家冷遇甚至曲解。这种现象终于促使洪业决心在讲学之余,更为系统地译介杜甫。
《杜甫传》叙事、翻译兼备,洪业以其独到的史学眼光考据杜诗系年,精益求精,很多驳正旧说的观点也为本土的传统杜甫诗学研究提供了新参考。他的杜诗评析,将杜甫的创作置于其生平行迹的脉络中,勾勒语言背后的深层隐喻。以《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一诗为例:
“明妃的故事是绘画、戏剧和音乐中(被广泛引用)的题材。杜甫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他是否想到了明妃不肯屈服于卑劣行为的举动?是否想到明妃最终离乡背井,和许多因忠诚正直而被朝廷贬谪放逐的朝臣很相似——其中包括他自己?”
这一番说明,不仅提供了“王昭君(明妃)”这个典故本身蕴含的深意,也提供了通过典故对杜甫内心世界的推测。也就是说,他为英语读者展示了一个母语读者进入中国古典诗歌途径的观念与方法,纠正了长期以来域外译家们有意回避典故的弊端。同时,洪业重点突出杜诗因时因事而作,批判褒贬的现实主义诗史精神,刻画杜甫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情怀,也为西方此时已经成形的,一味“空灵超脱”“清新淡雅”的片面中国诗印象,提供了一个用意深刻的对照文本。
洪业立足于中国诗学传统,去辨析、重构杜甫作为“中国最伟大诗人”的人品与文化性格,和艾斯珂夫人的译介方向有相当程度的类似。但他作为学贯中西的母语译家,对原文词汇的理解、对典故的把握、对文化渊源的体认,远非西方的非母语译家们所能比。他与杜诗的形神合一,和艾斯科夫人单纯的崇敬又不一样,对杜诗意蕴的揣摩更能体贴入微。比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译为“Thestateis destroyed,but thecountryremains./In the city in spring,grass and weedsgrow everywhere”; 或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译为:“Behindthe red lacquered gates,wine is left to sour,meat to rot./Outside the gateslie the bones of the frozen and the starved.” 其中加点的词汇各有增删与补出,都不是原文的严格对应,却自然醇厚,更接近杜甫的创作场景及其志节与寄托,和非母语译家们习惯于撷取词汇“意象”自行铺衍完全不同。诚如书写洪业传记的作家陈毓贤所言:
“洪业英译时把杜甫省略的代词和连接词都补上了,又解释了诗里的典故或没有言明的内涵。这样一来,固然牺牲了原诗的韵味,却把意思说明白了。……许多中国古名称,译成现代英文反而更清楚,譬如黄粱是小米,蕃部落是藏人,交河是今天地图上的吐鲁番,司功参军是管一州教育的。各种植物和官职,我看了英译才恍然大悟。”
陈毓贤(Susan Chan Egan)是菲律宾华侨,自小接受中英文双语教育。自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后来在美国的华盛顿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是一位经过世界文学专业训练,却没有很深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积淀的特殊读者。她在感觉洪业译诗“牺牲了原诗的韵味”之余,又有诸多的“恍然大悟”,很能代表大众读者们的普遍感受。洪业译介的读者预设最初肯定是所有西方民众,但他毕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杜甫传》内容之厚重,决定了主要受众在知识精英阶层。关于译诗,洪业也明白自己的散文化处理缺乏诗意,未能尽善,不过他的大多数读者并不那么介意书中的杜诗到底有几分像“英文诗”,他们只在其中印证杜诗存在的整体价值,尤其是杜陵精神与现代的对话意义:
“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s)。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忧患(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s)。尽管他深深欣赏世间之美,其中也包括女性美,但从无证据表明他和女性的关系超乎社会规范的一般界限。……他为人一贯实诚可敬,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如此。”
当洪业的《杜甫传》于2014年再版,半个世纪已过去,期间杜诗域外英译发展迅速,洪业的著述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要参考书。他为世界文坛所确立的杜甫形象,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堪与莎士比亚、但丁比肩,几乎无人能质疑。“洪业的杜诗学体现了他朴实学术的风貌,既有考证、编年等维系传统的一面,也有文献化及英译等向外开展的一面,他是将‘真杜’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让杜甫成为世界的杜甫,洪业与时代对话的精神和实质发生于海外的影响,正是杜诗学史上一页崭新的篇章。”《杜甫传》再版之际,洪业虽已作古,此书却得到更多重视,先后被不少美国资深传记作家、书评人大力推荐过。Richard Clair认为这本“不算容易读也不便宜”的书最可贵之处在于,清晰展现了杜甫的创作意图和“自然性世界观(naturalness of worldview)”;Derando Glen称扬洪业对杜甫生平的勾勒、描画让此前此后如“孤立珠宝(isolated jewels)”一般,其他版本的英译杜诗有了厚实的依托,更容易被年轻一代读者所理解。两位书评家也都建议读者不妨参看其他文学译家,比如大卫·辛顿(David Hinton,1954—)的译本,以便更完整地了解杜诗风格,因为辛顿等人的译法“更接近于诗歌”。实际上《杜甫传》在英语世界的不少高校里被用作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东方学、历史学、世界民俗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阅读材料,杜诗的内容加上洪业散文诗式的译语周到细致,叙议沉着,也很受青年学生欢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最新的《世界名人名言必读》(OxfordEssentialQuotations,2017)一书中收入杜甫诗句“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采用的就是洪业译本。
当然,洪业自身与杜甫同气相求的个人情感因素,使得《杜甫传》中难免存在武断或过度引申之处,“失去了一份作传人应与传主间保持的距离,汉学家一向认为这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瑕疵。”但从厘清英美汉学界和文学界对杜诗乃至于唐诗的理解偏误,弥补他们的想像缺失和认识断裂这个角度来讲,洪业的杜甫译介具有为唐代诗坛在异邦重树典范、恢弘气韵的重要意义。
四、 20世纪后期的域外杜甫英译专著
1967年,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完成了一个和过去几乎所有的英译汉诗文本都大不一样的杜诗译介专著,《杜诗初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霍克思更关注诗歌作品,而不是诗人的生平,他虽然只译出了35首杜诗,但在每一首原文下标注了汉语拼音,给出单一字词对应的英文单词,然后每一句诗逐行译,从创作背景、题目和主题展开赏析,还有格律形式的专门介绍,最后给出一个散文化的译文,作为读者完整理解这首诗的参照。从分层解读到分类呈现,霍克思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语言转换对原文的损害,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诗歌原意,可谓用心良苦。《杜诗初阶》因此获得有名的经典大部头文学选集,《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TheNortonAnthologyofWorldMasterpieces,1997 )的特别推荐,成为高等院校研学杜甫的经典文本。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的杜甫译介文本的影响力,很难超越《杜诗初阶》和洪业的《杜甫传》,包括1971年,“TWAYNE世界作家”系列丛书推出的,澳大利亚汉学家Albert Richard Davis(1924—1983)的《杜甫》。该书全面介绍杜甫的生平、经历和作品,算得是汉学界杜甫研究的又一力作,但发行量很有限。
汉诗的域外英译发轫以来,文坛译家们一直是一支主力军,也是将英译汉诗推向世界文坛经典化的生力军。到80年代,这支队伍的汉语言文化素养大大提高了。美国知名的反战主义者,翻译家、出版家兼诗人山姆·哈米尔(Sam Hamill,1943—2018)也非常崇拜杜甫“独立、完善的人格”,推举杜诗的“深刻寓意”。他在1988年出版的杜诗专门译本,用杜甫的五律《对雪》作为书名,题为《对雪:杜甫的视野》,译出了101首杜甫诗歌,还附有原文的书法插图。他后来编译的《午夜之笛:中国爱情诗选》(MidnightFlute:ChinesePoemsofLoveandLonging)、《禅诗选》(ThePoetryofZen)两本译诗集里也都包括杜甫的作品。
哈米尔师从美国20世纪文坛上以特立独行知名的诗人、翻译家王红公(Kenneth Rexroth,1905—1982),自5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到英译汉诗,对英美译家们的成果很熟悉。和这些前辈们一样,他的汉诗翻译也主张保证原诗“精义”的存续,不能受外在形式的机械捆绑。不过他对中国诗歌“精义”的认识包括了语意、风格和音乐性三方面的有机结合,而非单一地强调字词、韵脚或节奏对应,比他的前辈们更全面。哈米尔精通古汉语,十分重视读懂原文,并强调充分了解汉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完全不懂中文或中文水平未达到一定程度的译家,实际上无法真正把握原诗“精义”,即便连他的老师王红公也不能例外。其实除了在技术层面的处理方法不同之外,哈米尔的译介动机与王红公也不一样。他是禅宗的忠实追随者,积极投入禅修,研究中国禅宗公案,向往山水间中国士人的隐逸生活方式。译介中国古典诗歌,是他深入体味中国文士文化的一种途径,也是他描绘“禅悦”境界的载体。因此,他特别偏重山水田园题材。在翻译实践中,尽管他重视读懂原文,也并非读不懂,他的英文译本却大多存在对原文明显的删减和修改:强化诗句中的自然物象,突出寂静安然的自然氛围,弱化甚至于湮灭其中“人”的自我存在,渲染坐禅之际“天人合一”的效果,称扬禅修之余“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也就是说,他那些简约优美,大受读者欢迎的译文所再现的原诗“精义”,并不完全是细读文本“把握”住的,而有相当成分由他在“预设”的禅意境界中营造出来。
1988年,新一代汉诗英译的文坛名家大卫·辛顿的《杜甫诗选》,选译了180多首杜诗。出版社称“本版《杜甫诗选》是目前唯一的英文版该诗人作品选集”,显然与事实不符,不过,译介杜甫是辛顿进入唐诗世界的开端。他的翻译理念和哈米尔有很多共同之处。在实践中,他认为翻译是以“谦虚的态度”完全沉浸在原作者构筑的文字世界里,“学习用英文再现他们的声音”,必须了解原作产生的文化精神土壤。他的翻译一方面继承陶友白(Burton Watson,1925—2017)以降当代英语诗歌浅白、平易的语言风格,努力凸显原作蕴含的文化神韵,一方面着重营造杜甫达观知命的形象。他将《梅雨》(PlumRains)中“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译作“All day long,dragons delight:swells coil/and surge into banks,then startle back out”;或者《进艇》(OutintheBoat)中的“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译作“Today,my wife and I climb into a little river-boat.Drifting,/skies clear,we watch our kids play in such crystalline water.”的确非常形象生动,行文简洁而富于感染力。评家因此普遍认为他的译文“用当代英语而不是洋泾浜英语努力再现古汉语的凝炼,如古典诗词一样,言近旨远,耐人寻味。……揭开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新篇章。”
但正如辛顿在此书前言中的表述:“我尽可能忠实于杜甫诗的内容,但我无意去模拟原诗的形式或语言特点,因为模拟会导致彻底的误译。古诗词语言的本体性架构与当代英语诗歌差别甚大,甚至每一个单一特点在这两种诗歌体系中都往往有着不同的涵义。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在英语中再造与原文的互惠架构。因此,对于杜甫诗的种种不确定性,我努力让它们以一系列新样式去再现,而不是去消解不确定性。就好像杜甫是当今的英语诗人,在用当今的英语写诗。”
所谓“不确定性”,指的是汉语动词无词根变化,加上诗歌字词极其精炼所带来的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非写实性特征,给读者带来了多重诠释的可能。辛顿很重视自己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他所采用的“一系列”当代英文诗歌“新样式”,“与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的诗歌语言手段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只是用当代英文的句法与词法,英文诗歌的诗行发展逻辑,描摹杜甫的诗意诗境。换言之,这个译本呈现的杜诗,充满关注现时现事的“深刻当代性”品格,符合辛顿的个人阅读感悟,同时满足了这一时期美国民众对“中国最伟大诗人”杜甫的审美期待:向往和平宁静的生活,热爱自然以及自然界的一切,用质感鲜活的“及物”创作,直面世间坎坷,体贴平民苦难,抚摸草根命运。
与此同时,汉学界的杜甫研究也稳步行进。1992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推出该校汉学家David R.McCraw的译本《杜甫的南方悲歌》,译出杜诗115首。McCraw的翻译处理,过份依赖早期汉学界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带着浓重的学究气。虽然他预设的读者群是英语世界的普通大众,但此书中关于汉语言和汉语诗歌的一些介绍性文字并没有多少新意,文本中的引文、注释也繁杂,译诗语言又把原诗中的汉语典故和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典故搅在了一起。学界或文坛或普通读者,对这个译本的兴趣都不大。
1995年,美国汉学界又出了一本杜甫研究专著,即华裔学者周杉(Eva Shan Chou)的《重议杜甫:文学泰斗与文化语境》。周杉在序言中言明,她的译介目的是回归中国传统的杜诗学视角,面向“认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西方学生,提高他们对杜甫作品的理解,避免‘新西方诠释的幼稚’”。周氏首先回顾了唐、宋时期对杜甫评价的演变,认为杜甫之成名很大程度上出于人们钦敬他的儒家传统道德风范,“实际上超出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范围。因此,现代批评以客观语气去评价他的倾向,往往失于过度客观。”周氏主张关注“更纯粹”的文学问题来纠正这种失衡,将杜诗研究的重点从杜甫生平经历转移到诗歌文本,和洪业论杜诗的立场完全不同。她随即引入一些新的文学批评概念,从杜甫的政治观点、社会良知和杜甫“真诚”的本性,展开各种文学问题的讨论,构成此书的核心部分。她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诸如杜诗内容的“社会话题性”;“现实主义”与“程式化现实主义”如何先相互冲突,后归于融合并影响杜甫的后期创作;杜甫如何通过混用不同层级的语言模糊民歌与古体诗之间的界限,都比较引人注目。针对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盛唐诗》杜甫专章中所论及的,杜诗中独特的“风格转换”——即主题、情绪和措辞的突然转变,使杜甫诗句能够在很小的篇幅之内链接不同的情绪和观点——周氏选择称之为“并列”,且置于诗体结构框架下去讨论。周杉的批评性再思考,注重文本而非理论教条,颇具原创性与洞察力,为英语世界深入探讨杜诗的美学特征、杜甫的文化形象和文学成就,助益良多。
五、 余论
综观20世纪的域外杜甫英译与研究,不仅驳正了此前西方世界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误读与谬解,确立了杜甫是“中国最伟大诗人”的世界文学地位,也丰富了中国本土杜诗学研究的谱系和维度。此后英语世界里关注杜甫的译家渐多,文学翻译与学术翻译并行,当然首先是被杜诗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吸引,更是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老杜甫所感动。在域外唐诗英译发展的历程中,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推崇从发轫之时一直绵延到美国新诗运动的黄金期,和当时的译家群体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是有直接关系的。二战以后,英美世界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发生很大转变,杜陵精神从灵魂层面触动了人们心底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担当社会责任的意识,新崛起的一代学者、译家所携带的欧洲贵族文化传统基因日渐淡薄。杜甫置身于俗世红尘中,以切入时代现实的真实叙事加大诗歌文本情感容量的创作方法,促使诗人们竞相仿效,也是对新诗运动以来,一味讲究词、句“意象”并置,追求“空灵超逸”诗风的一种纠偏现象。
前文提及的美国当代诗人王红公,自19岁经陶友白介绍得识杜诗,很崇拜杜甫用生命与创作实践所彰显的儒家正统的人本主义基本精神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风范。王红公生平虽然只译出过36首杜诗,却对杜诗在英语文坛的流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他认为诗歌创作就应该表现个人生命体验,歌颂大自然和新生事物,关注底层民生疾苦,抨击腐朽传统和社会罪恶。他曾数次在公开场合承认最欣赏的诗人是杜甫,极大推动了世界文坛上的杜甫文化形象建构。不过也正因为追宗杜甫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王红公的翻译实践延续了新诗运动的“仿汉风”方式,有比较明显的“征用性”特征。他首先在诗歌选目中刻意回避杜诗里忠君忧国的主题,其次在诗句处理中略去典故或隐喻,只突出词语本身构成的“意象”。哈米尔曾提到过的,他的老师王红公汉语水平之有限,无法做到精准把握原诗内涵。王红公的杜诗译介因此在“质”与“量”两方面都不如辛顿,也不如陶友白。
从域外汉诗文学译家们代际更迭的关系上看,陶友白上承庞德、韦利,下启辛顿、哈米尔,是美国当代文学译坛上一代领军人物。他遵循庞德、韦利的翻译理念,摈弃维多利亚英语诗风,应用当代英语诗歌的诗学理念和审美标准,追求译诗文本通俗、浅白,易于被大众读者接受:“我所有翻译活动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用易于理解的方式让英语读者阅读亚洲文明的思想与文学著作,因此我对那些故意使读者与译文产生距离的翻译方法丝毫不感兴趣。”同时,他强调翻译对原诗的内容忠实度,尤其强调优先考虑“自然意象”的精准、清晰传递,因为“自《诗经》开始,自然意象就一直在中国文学中举足轻重”,也是最具有异质文学特性,最能打动西方读者之所在。在诗歌语言转换的技术层面,他比辛顿更在意适度保留中国故事的韵律、诗节,不轻易更动词序,也不拘泥于生硬对应。2002年,他出版《杜甫诗选》(TheSelectedPoemsofDuFu),译出杜甫诗歌127首,附有诗中所涉典故、历史背景、神话传说的大量注释,是一个带有大学入门教材或读本性质的译本。
2008年,美国诗人、翻译家大卫·杨出版《杜甫:诗里人生》(DuFu:AlifeinPoetry),这是当代美国文坛译介杜甫的又一力作。该译本根据杜甫年谱分十一章,每章都简要介绍了当时杜甫的生活状态和所在地的社会、地理情况,试图纵向呈现杜甫诗艺的成长历程。大卫·杨译出杜诗168首,突出其内容贴近平民生活的亲和力,强化杜甫攫取日常生活素材进行诗意转换对于当代诗歌创作的借鉴作用,营造出一个“经历过政治理想幻灭、社会动荡与个人情感纷扰”而不断自我调适,始终坚持创作并在诗歌的世界里求得自足圆满的杜甫形象。与辛顿、陶友白相比,大卫·杨所呈现的杜甫更富于“烟火气”,被认为是引领当代普通读者进入杜诗世界最成功的一个译本。
世界文坛和汉学界对杜甫的推重持续到今天,终于抵达宇文所安集大成的六卷本《杜甫诗全集》(ThePoetryofDuFu),在杜诗的文本基础上,深入探讨杜诗的美学特征、杜甫的文化形象和文学成就。这说明无论文化和价值观有多么大的差异,又如何不断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真正伟大的作家从来都不止代表他们自己或者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那个民族,而是总能够用他们真诚的诗性的声音,让世界发现他们个体情感与思想中的普世意义。2020年4月,长达一小时的电视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Fu,China’sGreatestPoet)由英国BBC电视台制作完成并播出,令世界文化界瞩目,也是唐诗向西方传播百年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当代知名历史纪录片编剧Michael Wood依据洪业《杜甫传》的内容,编写出了同名剧本,把杜甫放在历史视野和比较文化的语境中展开讲述,标志着域外唐诗的译介已经由书本、音乐等传统的传播媒介,走向了英语世界的主流大众媒体,迈上了一个进一步扩张受众规模,深化世界文学“汉风”传统的新台阶。当域外的杜甫译介如“不尽长江滚滚来”,实际上也就是唐诗,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全球多元文化生态圈里和其他族群、其他文化互通有无,共生共荣,走向更广阔、更深层次的对话。
注释:
①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37页。
②Ayscough,Florence;Lowell,Amy:Fir-FlowerTablets,PoemstranslatedfromtheChines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1
③Florence Ayscough:TuFu,TheAutobiographyofaChinesePoet,London:Jonathan Cape; Boston &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9
④Craine,Carol Ward:Mrs.Underwood:Linguist,Littérateuse,Fort Hays Studies Series,1965
⑤Edna Worthley Underwood,Chi-Hwang Chu:TuFu:WandererandMinstrelunderMoonsofCathay,Portland,Maine:Mosher Press,1929.xxii.
⑥Edna Worthley Underwood,Chi-Hwang Chu:TuFu:WandererandMinstrelunderMoonsofCathay,Portland,Maine:Mosher Press,1929.
⑦这种随书附赠的小册子没有专门记录,此书内容尚待查考。
⑧L.Cranmer-Byng,AGardenofBrightGhosts,The Poetry Review,Nov.-Dec.,1929,PP.409-418.
⑨Florence Ayscough:TravelsofaChinesePoet:TuFu,GuestofRiversandLakes,London:Jonathan Cape; Boston &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4
⑩Émile Lucien Hovelaque(1865—1936),法国作家、东方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