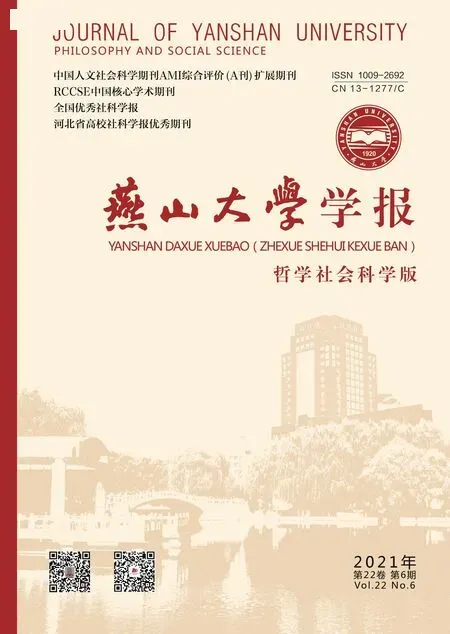论“器物教化”
韩建磊
(景德镇陶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把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器物教化”作为一种在我国有着几千年应用历史的特殊的教育方式,因其独特的机制与优势至今依然在某些场合以不同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去研究“器物教化”,并创新地应用于当前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器物教化”?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有什么优势与劣势?这是本文所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 什么是“器物教化”?
“器物教化”是一种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特殊的思想教育方式,是指赋予特定器物以特定的思想观念,比如某些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等,并通过这些器物对特定的人群实施教化,以达到预定的目标。由于这种教化不同于传统的“人教人”,而在形式上表现为“物教人”,故称之为“器物教化”。在这个概念中,“器物”主要是指人造物,因为只有设计制造出来的器物才能更有效地承载特定思想,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教化功能。虽然有些自然物也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但因其不属于人造器物,也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从范围上讲,“器物”不再局限于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礼玉等,而是泛指生活中为人们所用所接触的各种器具物品等。而“教化”一词虽然可以从政治、教育、社会等多个视角来解读[2],但就本文而言,则主要侧重于教育视角的阐述,把“教化”理解为一种思想教育活动。
虽然“器物教化”是一个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实际上我国自古至今一直存在“器物教化”这一社会现象。商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青铜“礼器”,“主要使用于贵族宴饮或祭祀等各种礼仪场合……可以用以表明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地位和衡量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等级关系的准则”[3]278。青铜礼器之所以有这些作用,就是由于被人为地赋予了特定的“礼”,而那些看到或接触到这些青铜礼器的人则会马上意识到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并自觉地去遵循相应的礼数而避免出现僭越之言行,这就是通过特定器物实施的教化。当前社会也有类似的应用,比如火车站的单向门与导向栏杆,它以巧妙的设计来引导乘客只能朝一个方向前进而不能插队或逆行,久而久之,人们就有可能从中悟到其所试图传递的规则,并认可与遵守这些规则,从而实现德育的效果。虽然“器物教化”现象一直存在,但当前很少有学者会基于思想教育的视角去关注这一现象,直到张卫、王前在《哲学动态》等期刊上发表了介绍西方“道德物化”的文章[4],中国式的“道德物化”,也就是“器以藏礼”才重新为部分学者所关注。西方的“道德物化”是指什么?张卫等人将之定义为:“把抽象的道德理念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使之在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4]不难看出,西方的“道德物化”与中国的“器以藏礼”实际上是相通的,只不过前者更侧重于理论的探索,而后者更侧重于实践的应用。如果能从中国这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现象中找到一些有助于当前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的元素,并提升至理论层面,“器物教化”研究也就具备了应用价值与理论价值。
二、 器物为何具有教化功能?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器物教化历史,然而并没有对“器物为何能用于教化”这一问题给出详细的解答。虽然先秦时期就有了“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的说法,但也仅限于对一种重要社会现象的简单抽象与记载,而对于这种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当时的工匠以及记载这种现象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缺乏理论思考的。其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5]之后又出现过“器以载道”“藏礼于器”等说法,但均与“器以藏礼”一样,缺乏理论的阐述。相比较而言,西方思维“更注意理性的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5],相应的“道德物化”理论明确指出器物之所以能发挥德育功能,是因为设计者“将一定的道德规范‘写入’人造物之中,从而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调节”[4]。然而这种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器物教化,其所谓的道德引导功能更侧重对“技术物”或“人造物”的依赖,甚至要“技术物规定着使用者的使用行为”[6],也就是,使用者更倾向于被动地去合乎道德规范,至于使用者是否意识到“技术物”中的道德理念,则不是“道德物化”理论讨论的问题。而中国通过“器以藏礼”来实施的教化更强调被教化者(不仅仅是“使用者”)的主动性,被教化者往往是先认识到、悟到其中的道理,而后才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这对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是有增益的。总体而言,西方的“物化道德”理论与中国的“器物教化”在利用器物实施教育这一思路上是相似的,但在具体的应用实践、器物种类、教育方式效果等诸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所以“物化道德”理论并不适合解释中国的“器物教化”,我们需要基于中国器物教化的具体情况去探索其背后的理论问题,去解释为什么器物具有教化功能。关于器物为什么能具备教化功能这一问题,笔者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 人类赋予器物以教化思想
考查中国的器物应用历史就会发现,凡是被官方明确用于教化的器物均是经过特意选择、设计并有意地赋予“等级贵贱”之类思想的器物,比如青铜礼器、玉礼器、金器,以及官方指定或设计的“舆服”等。而非官方主导的能够起到特定教化作用的某些器物,同样是因为被人为地赋予了特定的思想,比如一些道德、宗教观念。除此之外,没有被赋予特定思想的普通日用器物基本上不具备教化功能,比如家用的饭碗、农耕工具等,人们很难从中获得什么思想教育或启示。由此可知,器物的教化功能源于人类的赋予,是人类把特定的思想通过特定的方式赋予器物之中,然后,器物又把这些思想传递给特定的受众,从而取得类似“人教人”的教化效果。“被赋予思想”是器物具备教化功能的关键,而这又可分为有意赋予与无意赋予两个方面。
有意赋予是指,“礼器”等特定的器物从产生之日起就被人为地赋予了特定思想以用于教化。比如,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就被人为地赋予了“等级贵贱”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即成为社会等级名分制度的重要物质标志”[3]278,以“明贵贱,辨等列”(《古文观止·臧僖伯谏观鱼》)。而这些思想又往往通过器物材质、造型、图案或者文字等表达。以材质为例,历朝历代的礼器的选材均非常讲究与挑剔,多选用青铜、和田玉、金等材料,这些材料在当时非常珍贵,只有贵族阶层才能用得起,才有权力用。商周时期,仅仅是一套青铜打造的酒品,就足以清晰地显示器物主人的身份地位,客人或其他人见到这些青铜酒器则立即明白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礼节,而这正是青铜酒器设计者所试图向外界传递的思想。同样道理,和田玉器、金器、漆器等都曾被用作礼器,材质也是它们能入选的重要原因,很少有哪个朝代会把粗糙的陶器用作礼器,也未发现哪个朝代会把麻布衣物当作身份的象征。造型、图案与文字等也是器物设计者用于承载思想的重要方式,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无意赋予是指,器物中的思想不是设计者有意赋予其中的。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某些器物与特定思想之间慢慢地产生了关联,于是器物就承载了某些思想。但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出明显的赋予意图,亦无法准确找到思想的赋予者是谁,而表现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如,自古就有“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礼记·聘义》),“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说文解字》)之类的说法,然而没有资料显示,普通玉器中的道德思想是玉器设计者或官方有意赋予的,也无法定位第一个“比德于玉”的人是谁,而更倾向于自然而然地无意赋予。不仅是玉器,很多日常器物也是如此,虽是人造,但是设计制造者并没有刻意地去融入一些思想,而只是一个单纯的生活日用器物而已,但是这些器物有时也能起到教化作用。比如一些有着梅兰竹菊“四君子”图案的器物,有些人就是喜欢把这种器物摆在客厅或书房里,甚至带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要学习“四君子”的品格,这就是器物教化。问题是,这些器物的制造者真的是想通过这些器物来实施某些教化吗?不一定。对于器物生产者,尤其是批量生产者而言,“四君子”就是一种图案而已,至于“四君子”品格,那纯粹是部分文人想象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四君子”图案的器物确实具有道德层面的教化功能。
通过上述可知,“有意赋予”与“无意赋予”差别非常大,前者所造就的往往是“明贵贱,辨等列”的“礼器”,其目的在于维护阶级统治,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而后者所造就的往往是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普通教化器物。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二者均赋予器物以特定的思想,这是器物获得教化功能的关键步骤,进而可知,器物的教化功能并非天生,而是人类赋予的。
(二) 人类成就器物的教化功能
赋予器物以特定思想只是器物教化的开始,而器物能否顺利完成教化任务最终取决于教化客体,也就是教化所指向的特定人群。这些人在感悟能力、知识储备、道德素养、文化归属等方面可能会千差万别,这就导致他们面对特定器物的反应也可能会千差万别。有的人感悟能力强,很容易睹物生情;有的人感悟能力差,启而不发。有的人知识储备丰富,知道器物所要表达的意思;有的人完全缺乏相关知识,在其眼里,这件器物跟其它的没有什么区别。有的人道德素养高,面对器物马上意识到应该遵守某种特定的规则;而有的人道德素养低下,他即使看懂了器物,但偏要我行我素。举例来说,在把玩铜“制钱”时,有人会受到做人要“外圆内方”的启迪,有人只想知道这老物件能卖多少钱,而在儿童眼里,这只是缝制毽子的好东西。无论器物设计制造者如何的高明,他们也不敢确保自己的器物就一定能实现预期的教化与德育功能,即便西方精心设计的刻有栩栩如生的苍蝇雕像的小便池,也不能确保男性小便时不会尿液四溅[4],因为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教化的客体手里,这就是器物教化的局限性。也正因此,器物只有在特定的场所、特定的情境中,针对特定的人群,才有可能完美发挥其教化功能,否则,即使是蕴含严格等级思想的礼器,也无法杜绝“僭越”行为的发生。简言之,器物教化是否有效,能否能起到预期效果,最终取决于被教化的人,取决于这些人对器物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否敏感,是否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人类成就了器物的教化功能。这就提醒我们,如果要通过器物来实现特定的教化与德育,是一定不能忽略教化客体的实际情况的,孔子的“因材施教”教育观也同样适用于“器物教化”。
这里必须指出,有些器物教化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保障的,比如元朝规定“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玉质茶器、酒器”[7]121,“禁止民间穿赭黄、柳芳绿……等颜色的服饰”[7]138等,被教化者似乎没有选择的空间,必须接受服饰、玉器等器物所预设的等级思想。而实际上,这种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器物教化最终还是要体现在被教化者的言行举止中,遵循者有之,僭越者亦有之,虽然被教化者的主动性严重受限,但并未完全丧失,他们依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展示他们对这种强制性教化的态度。
综上所述,器物的教化功能源于人类,而非器物自身。具体来说,教化主体或设计者赋予了器物教化功能,而教化客体则成就了器物的教化功能。
三、 器物教化的方式
器物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在没有教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它是如何发挥预定的教化作用的呢?“道德物化”理论解释为,“技术物”具有特殊的外形或特征,能引导人做出某些符合既定规则的行为。比如,设计者在小便池中心安装一只苍蝇的小雕像,男人看了苍蝇往往试图用尿“射击”它,结果就避免了“乱尿”而导致的尿液四溅的不文明不卫生现象。相比于西方这种颇费心思的,且作用范围严重受限的“物化道德”,中国通过“器以藏礼”来实施教化的方式就简单且作用范围大的多了。根据对中国器物教化应用的考察,笔者归纳出三种器物教化方式。
(一) 强制引导
所谓强制引导主要是指,当使用特定器物或进入特定器物的作用范围时,就必须做出某些符合规则的特定动作,否则就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久而久之,教化客体就会主动去遵守预设的规则,进而形成习惯。比如流行于清代中后期的“公平杯”,就是一种具有强制性引导功能的器物,它要求斟酒者必须公平、公道,如果给某一位客人“黑心多斟”了,那么客人所用的公平杯中的酒就会很快流光。[8]90直到今天,很多饭店依然会提供公平杯,或许这些公平杯已经没有了“再添漏尽空”的功能,但就其“公平杯”这一名字,也足以提醒在座的酒友要有一颗公平公道之心。古代的枷锁也具有强制约束引导功能,犯人戴枷锁时,必须双手置于胸前,微微含胸,方能舒服,否则极为难受。而双手置于胸前,微微含胸,正是中国古代君子的标准形象,孔子、老子等先哲的雕像、画像均体现了这一特征。犯人在枷锁的强制下,必须做出符合君子的动作,久而久之,使其起码就外表来看更像君子,更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观。[9]今天,很多现代器物依然以“强制性引导”的方式发挥着教化或德育功能,比如上文提到的很多火车站都在使用的单向门、导向栏杆,以及随处可见的汽车减速带等等。
强制引导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上文所讲的某些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器物教化,要求人们必须遵循某些礼仪规则而不能违反。这种强制性引导多发生于政治教化过程中,在历朝历代均有出现,虽然不太适用于普通道德思想或其它非政治思想,但必须肯定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承认其依然是中国传统社会比较常用的器物教化方式,即使是今天,这种“强制引导”对思想道德教育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主动警醒
一些器物具有明显的意在引导人去遵守特定规则的特征、外表或文字图案,一接触到或看到这些器物,受众马上能感觉到器物欲传递的思想,从而自觉地遵守某些规则并约束自己的言行。在特定的场合放置这些器物,或者设计成可把玩的物件,就能时刻提醒或警示受众要如何,而不能如何,从而实现教化目标。比如在古代有一种叫做“攲器”的器物,“虚则攲,中则正,满则覆”(《荀子·宥坐》),而孔子就从中体悟到了“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荀子·宥坐》)的人生道理。再比如,封建社会有“贞节牌坊”这么一种东西,“作为贞节观念及其正式制度的物化载体, 其核心功能,就在于表彰丈夫死后不再改嫁的中青年妇女, 特别是这些妇女中的典型代表。”[10]官方通过树立这些牌坊而时时刻刻向女性传递“贞节”“从一而终”等封建道德思想。过往女性,尤其是过早守寡的年青女性看到这些牌坊,肯定会有所触动甚至产生思想压力,进而效仿,从而实现当时官方的教化目的。除此之外,各种器物上的铭文,各种书画作品上的文字等,亦可能具有“主动警醒”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在传统社会能起到“主动警醒”的器物非常多,而今天,有类似功能的器物依然不少,比如各种主题雕像,各种标识,各种小挂件,以及宗教场所的器物等,人们总是能从中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器物所要传递的思想,从而反思、约束自己的言行。
(三) 被动启发
“被动启发”是指由于器物本身没有明确地表达特定思想,或者其所预设的受众是数量极少的特定群体,或者设计制造者根本没有使其蕴含任何思想,所以这些器物的教化功能主要取决于受众,故称之被动启发。以“被动启发”的方式发挥教化功能的器物,其能否发挥教化功用及教化程度完全取决于受众。具体来说,取决于受众主观上能否从器物中感知、联想或者臆造出某种道理,而这又与受众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人生阅历、情商智商等因素息息相关。比如古人认为玉器是蕴含美德的,即所谓“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所以有些人佩戴玉器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要学习玉器中蕴含的美德。是不是什么人都能感悟到其中的美德呢?肯定不是。在很多人看来,玉器就是一种饰品,或者就是一种可以把玩的物件而已,别无其它。同样,传统社会的铜“制钱”,有些人能从中感悟到“外圆内方”的人生道理,而对于大多数古人来说,铜钱就是可以购买商品的货币而已,哪里有什么人生道理。各种宗教场所的器物也是如此,信众或许能从中感受到某种心灵启迪或人生教诲,但对于大多数无相关宗教信仰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些就是一些宗教器物而已,很难从中获得什么启发或教诲。虽然“被动启发”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受众,但并不意味其效果不佳,相反,对于特定的人群,有可能效果非常显著。一件在普通人看来平凡无奇的器物,却有可能让一个“睹物生情”,从而产生教化作用。比如一个刚刚丧母的人,看到母亲遗留下的任何用品,均有可能痛哭流涕而感悟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道理。由此来讲,任何器物均有“被动启发”的潜质,当然这种潜质即便偶尔发挥出来,也都不太可能具有普遍性。
综上,器物教化主要存在以上三种方式,除了“强制引导”跟西方“道德物化”理论所表达的通过“技术物”将人们的行为导入预定的道德规则这一方式有些相似之外,其它两种方式均是中国的“器物教化”所特有的。相比较而言,“器物教化”更强调受众的主观领悟,且适用领域特别广;而西方的“道德物化”则更强调通过巧妙设计来引导受众,使其行为在形式上符合特定道德规范,而不关心受众主观上是否领悟。
四、 器物教化的性质、优势与劣势
(一) 性质的界定
器物教化最明显的特点是“物教人”,有别于人们所熟悉的“人教人”。有些研究者发问,“器物教化”会不会成为“人教”之外的另一种教化形态?会不会对现有伦理学理论构成冲击?[4]笔者在上文已经解释过,器物教化功能源于人类的赋予,虽然形式上表现为“物教人”,而实质上依然是“人教人”,只不过是人类的教化通过特定的器物表现出来而已。与其称器物为教化主体,不如称其为教化中介、教化工具更确切。进而推知,也不会对当前伦理学理论构成什么冲击,而只是一种教育思路的创新罢了。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器物教化实践,而且直到今天,器物在很多领域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教化作用,比如前面所讲的单向通行门、导向栏杆等等。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器物对人在教化中的主体地位有什么威胁。我国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的观点,也就是说,古人早就知道器物中的“礼”是人类赋予其中的。器物能起什么教化作用,完全取决于人类赋予了什么思想,即便有些自然形态的物体有教化功能,其所传递出来的思想依然是人类思想外化于其中的,而非什么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奇异思想。
可见,器物教化是人类教化的一种独特形式,教化主体只能是人,器物只是人类思想的载体与中介,而非什么完全独立于人类教化之外的另一种教化形式。虽然“器物教化”现象不会对现有伦理学理论构成冲击,但却是一种有别于“人教人”的特殊的思想教育方式。“器物教化”理应在伦理学领域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理应为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探索其在当前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实践应用。
(二) 器物教化的优势
“器物教化”之所以能存在几千年,并且现在依然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而未被淘汰,这就说明它有特定的优势。
1. 节约大量人力。只要设计好器物或者赋予器物特定的思想,那么就基本上可以“一劳永逸”。比如,先秦时期的食器被赋予了“尊老”的道德思想,规定“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礼记·乡饮酒义》)。看到这些器物则“民知尊长养老”(《礼记·乡饮酒义》)而无需任何人现场说教。当前高速公路边上的那些非常逼真的警察模型也是一样的道理,过路司机看到这些模型,马上意识到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超速,要注意安全等。这些模型一旦放置好,将一直起作用,直到损毁,期间基本无需真的警察的参与。
2. 在特定场合能发挥比人们亲自“教导”更好的作用。单纯的口头说教无法保障教育效果,且由于说教者的个人能力与素养问题,有时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而有些专门设计的器物由于教化原理不一样,具有强制性,则往往会无声胜有声,比如上文所讲的枷锁、公平杯等,均是这种情况。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火车站里的导向栏杆,它就能非常有效地引导乘客有次序地购票、进站、上车。乘客除了按照导向栏杆前进而别无选择,这就是强制性。如果没有这些导向栏杆、单向门,而仅依靠工作人员现场指挥乘客排队,在当前社会动辄几千上万的乘客同时要进站上车的情况下,工作负担不敢想象。在学校路口等人员密集通过的地方安装汽车减速带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怕颠坏车子或者受不了那种心惊肉跳的颠簸,司机通过减速带时基本上都会主动降速,从而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单纯依靠交警或其他人员现场提醒“减速”,其效果未必胜过一条廉价的日夜无休的减速带。值得关注的是,购票排队、过减速带提前降速等有可能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而这正是我们思想道德教育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
3. 引导人们自我反思,进而促进各种规则、思想的内化。前面已述,器物教化更多地强调人的主观领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因为某些器物而遵守某些规范时,往往是他领悟到了其中所蕴含的规范思想,并且认可这些思想,所以他才会遵守,这种主动遵守更倾向于“自律”。而在他人的劝说、教导下去遵守某些规范则未必是内心的真实意愿,更有可能是迫于舆论压力的结果,更多属于“他律”。很明显,“自律”比“他律”更接近道德。
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器物教化才能在中国应用了几千年而未被淘汰,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发挥特定的作用。也是基于上述优势,笔者认为,“器物教化”一定会在当前的伦理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 器物教化的劣势
器物教化始终没有成为人类教化的主流方式,是因为它存在许多劣势。
1. 能藏于器的“礼”是非常有限的。一种观念如果要成功地外化于器物中,并能用于教化世人,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是,这种观念在外化于器物之前,已经为世人所认知甚至接受,毕竟器物是死的,它没有能力去强迫人们接受一个不为人们认可的观念。考查中国器物教化应用历史会发现,器物所承载的思想均是这种情况。二是,通过器物来教导、传递一种思想观念的成本与收益要远远优于人的直接教化,否则,器物教化将成为不可思议的行为。三是,这种观念适合外化于器物。比如,古人通过器物承载的政治思想多是“等级贵贱”思想,其它的政治思想则很少见,就是因为不太适合外化于器物。四是,人们能比较容易地感悟到器物中的观念,否则器物教化的效果很难保证。因此,不是任何思想观念都能适合通过器物来表达的,绝大数的道德、政治思想观念还是要通过人的直接教育、教导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 对客体有一定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文化素养或者人生经历等方面与器物产生了共鸣,才能更容易、更有效地感悟到器物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否则教化效果无法保证。比如,面对一个画有梅兰竹菊图案的瓷瓶,文人很容易从中悟到君子品格,但是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或者一个外国人,就不一定能感悟的到。正是因为器物教化对客体的选择性、挑剔性,决定了它很难具有普适性,而只适合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群。
3. 缺乏灵活性。器物中的思想观念,无论是设计时“藏”于其中的,还是人们外化于其中的,均是相对固定的。一种器物往往只能固定地从事某一特定思想的教化,尤其是那些传统器物,其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已约定俗成而无法改变。但是,人类的思想是千变万化的,新的道德观、政治观随时会涌现出来,我们很难赋予老器物以新的思想观念,重新设计器物以承载新思想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人的直接教化就方便、灵活的多了,正因为如此,人的直接教化一直是人类教化的主流方式。
总之,正是由于器物教化存在这些劣势,它才无法成为人类教化的主流方式,更不可能取代人的直接教化,所以我们不应过高地估量器物教化的现实应用价值。器物教化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应用,且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如何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扬弃”的原则来对待这一民族文化遗产,如何将其应用于当前的社会道德教育与道德建设,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