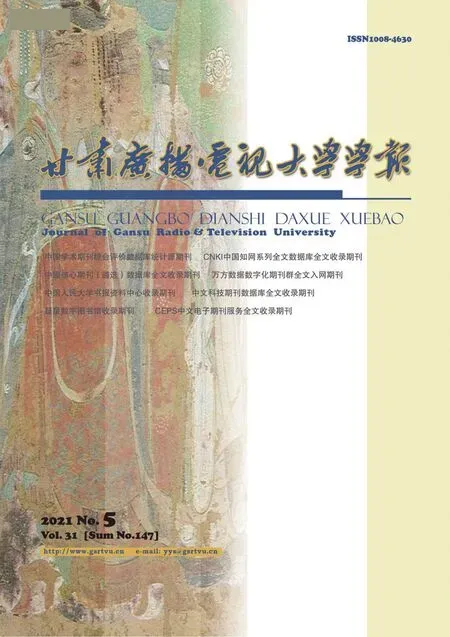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曾纪泽控御藩国属地的思想及实践
伊纪民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受20世纪反帝反侵略的革命叙事体系的制约,有关曾纪泽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主导的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南交涉等外交活动。21世纪以来,对曾氏的外交思想方面的研究得到重视,并有不少成果涌现①。研究主要围绕曾氏的公法外交思想方面,但专门涉及曾氏维存藩国属地的外交实践与思想方面的研究却极为薄弱。
就已有的公法外交方面研究成果所沿用的研究范式而言,学界主要是围绕“革命史”与“现代化”的研究范式进行的。前者很大程度从属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叙事,缺乏实证研究。而现代化范式构建的“传统与现代”两分法的思维模式,使研究局限于“退步与进步”的二元对立价值论,带有单线性和目的论的倾向,这就使得论者将国际公法与旧有观念、秩序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国际公法是外来的,与中国“体制”不可并存,如果采用它,就必须放弃原有的中国中心秩序与宗藩体制。事实上,曾氏对国际公法的认识是多面的,其对公法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他既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公法,又在不同情境下对公法作出不同诠释,公法与原有的天朝中心观念、宗藩体制的矛盾并非是水火不容,即这两种国际秩序并非简单的对立冲突关系,更重要的是二者彼此渗透与兼容的“过渡相”。换句话说,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在维存藩国属地的外交实践中呈现出彼此交融、相辅相成的重要功用[1]。
有鉴于此,本文探析曾氏运用国际公法与传统宗藩关系这两种体制对藩国属地控御思想与实践。
一、援引国际公法维存属国以遏制列强对中国藩属国的野心
中国自步入近代以来,列强环伺,因军事国力无法与之抗衡,从而被迫与之媾和。于是,“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世界文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2]。曾纪泽分析道:“西洋大小各邦,越海道数万里与中华上国相通,商舶循环于海上,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奇局。”[3]44中国再也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4]840-841。就西方各国而言,“咸自命为礼仪教化之国,平心而论,亦诚与岛夷、社番、苗猺獠课,情势判然”,决不能因两国礼仪教化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陈言”[3]184加以鄙视。因此,国人必须改变“屏斥洋货,言中国修德力政,而远人自然宾服者”[5]的拒外观念,化封闭为开放,转而“熟于条约、熟于公事”[4]817。况且,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列强开始以条约或者国际公法为基础构建近代国际关系(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谓“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6]5,“今中外相睦,动须循理,不得不以万国公法为法”[7]。基于交涉需要,曾氏等知识分子加强了对“国际公法”②的重视。
藩属体制作为中国对外关系最为重要的一种制度,对中国而言,这是证明其文明辐射天下的凭据。同时,藩属国也是中国的外围屏障,即“守在四夷”。随着西方势力向东方延伸,中国主要的藩属国受到了侵略威胁。曾纪泽看到,中国自与西洋交好通商以来,“属邦附庸之被侵侮”[3]173成为常事。这就使得固有的宗藩体制受到一定冲击。要想维系传统“守在四夷”的宗藩体制,就必须维存藩属国。
一方面,曾纪泽极力倡议利用国际法均势理论即公法约束大国的制衡作用以谋求中国周边属国的维存,即“《万国公法》,西人未必尽遵,然大小相维,强弱相系,诚能遵行,可以保世滋久”[4]843。就日本觊觎琉球的问题,他曾向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发出倡议:“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盖国之大小强弱,与时迁变,本无定局;大国不存吞噬之心,则六合长安,干戈可戢。吾亚细亚诸国,大小相介,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则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力以凌人也。”[4]905面对日、俄欲谋取高丽一事,曾氏坦言:以中国之力,断难保朝鲜和局。朝鲜仅对日本一国开放,只能助长日本的侵略野心,故“预防之法,独有劝高丽与西洋大国开口通商,则高丽之国,可藉公法以保全”[3]1009。在以曾氏为代表驻外公使及国内官僚的建议下,朝鲜与美、英、法、德、俄、意等国缔结《通商条约》。以美国为例,朝鲜作出如下申明:“大朝鲜国为中国属邦,其分内应行各节,均与大美国毫无干涉。”[8]中朝宗藩体制得到欧美各国的认可,中朝宗藩体制也得以暂时的维持和巩固。中法越南交涉时,为抵制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与独占,他奏陈总署,力主越南同各国与西方列强缔约,如“将红江开埠通商,……允与西洋各国贸易”[3]182以借助西力制约法国,达到保存越南的目的。针对法国强迫越南签订地条约,曾氏指出:“西洋各国公例,凡条约有一句不认,即系不认全约之据,当时罗淑亚公使将法越稿钞咨总理衙门,衙门覆以越南系朝贡中国之国,即系认越南为属国,而驳正约中法国认越南为自主之国一句也,此等紧要语言为全局之关键,既有彼此意见不合之处,即系中国未认该约之明证”[9]230-231。由此打破了法国的舆论垄断。这是曾氏以条约不可违反国际公法规范来遏制列强侵略野心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曾氏主张援引国际公法中的定界条例厘定边疆界限,确定边疆属地的权益。1880年,曾纪泽兼任使俄公使,负责修改前头等公使兼全权大臣崇厚所订丧权辱国之约。谈判尚未开始,俄方即以他“职居二等且无全权之称”加以诘难,蔑言:“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全权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曾纪泽援引公法力斥其说:“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3]44在谈判中,他积极运用公法中关于分界、通商的规定挽回国家权益。根据西方定约之例:“长守不渝者,分界是也。……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如两方对通商条约不甚认同,则正需要公法中的“修改之文”,才能“挽回于异日”[3]21-22。在具体交涉中,曾纪泽按照这一谈判思路成功改订中俄之约,成功收回伊犁南境地区,确立了新疆与沙俄的边境界限。
二、利用公法强化宗藩体制以及边疆属地的统御
维系藩属关系的传统方式大体是:中国王朝的统治者给予藩属国家以册封,以此来肯定其继任者的正统地位。藩属每隔一定时期,应该来中国朝贡,同时进行贸易,而中国的中央政府也以恩赐的形式赐给大量礼物。宗主国秉着“王者不治夷狄”[10]的理念,对藩属国内政、外交等事务向不过问。在国际公法中,藩属国的政治、外交皆由主国全权掌控,中国传统的松散的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中的属国制度产生了严重分歧。于是,西方列强一面以武力相挟制,另一方面则援引国际公法的属国制度加以辩护:“如作某国之主,则该国一切政事吏治皆为之作主,代其治理。”[11]日本和欧美列强一样,都试图以国际法的主权观念和属国理论,将中国的藩部称为“无主之地”,把中国的属国视为“独立之国”,最终将它们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保护国。于是,1876年暹罗成为英、法所划定的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间的缓冲国。1879年,日本又吞并琉球,终结了暹罗、琉球与中国宗藩关系。
1880年以来,中法越南交涉日棘,法国故伎重施,强要以西方国际法的独立国或附属国概念对越南身份做出非此即彼的区分,声言中国以越为属国,自称上国,“只是虚名”[12],没有真正管辖越南,越南一直是“自主之国”[13]927。然而,中越之间确实不存在西方式的殖民关系。诚如曾纪泽所言:“中国处待属邦与西法不同,中国只管属邦大事及大变故,至于盗贼及国之内政从不干预。不特越南为然,即高丽国如此亲近,亦以此法处之。”[13]642而“不以西洋治属地之法”[13]1003,针对法方之言论。曾纪泽认识到,如不加以反诘,则不仅“有关中国颜面”,更“恐将来他国因此生心,俄国、日本将有事于高丽,推之中国设官之属邦,亦恐他国凯觑,如英国之西藏,俄国之于蒙古,皆难保其无事”[9]150-151。因此,曾纪泽一面向法方提出严正声明:
越南为中国属国,二百余年以来,历受册封,朝贡不绝,为天下各国所共知……。夫以中国二百余年册封朝贡、历经保护之国,乃竟不认为中国属国,曲直是非,昭然可见,天下各国当有公论。凡有属国者,孰能受此蔑视耶?在中国素笃邦交,如果贵国愿敦睦谊,彼此尚可和平商议,言归于好。倘竟不顾名义,径意以行,侵我北圻驻兵之地,是贵国有意失和,我驻越之兵不能坐视,必致接仗。若因此致伤和好,岂不可惜!是启衅败盟,贵国实独任之,中国不执其咎也。为此照会贵大臣,即悉详察一切可也。[13]1558-1559
另一方面,曾氏建议中国方面做出某些调适以迎合公法,即坚持藩国属地隶属中国的前提下移植并援用国际公法中的属国与属地理论,赋予东方宗主国保护藩国属地、干预其内政外交的合法性,以强化宗藩体制及边疆属地的统御。曾氏力陈总署“不宜稍存畛域之心,越南不宜自外生成之德,必须声气相通,谋猷不紊,乃得辅车唇齿之益”[3]182。基于此,曾氏建议总署着手改变原先对属国与属地的宽松政策,转而“总揽大权”,加强对越南的统御,以消弭法国为侵占越南而炮制的舆论。而西洋各国则“既服中国之能调停,又见我与越南情无隔阂,可省无数窥伺之心”[3]182。所陈建议大致如下:其一,“越南除例遣贡使之外,宜专派精通汉文明白事体大员,长住京师,听候分示”。其二,“乞谕越南切不可与法人轻立新约”。其三,“劝越南慨然将洪江开设通商埠头,……允与西洋各国贸易”[3]182-183。除了向总署奏陈外,曾纪泽还向越南国王发出倡议,劝说越南对法国提出的要求“惟当正辞拒绝,明告以须禀明天朝”[3]190,以增强越南对中国的向心力。可以看出,这些办法或要求都大大突破了传统中越朝贡关系。
就朝鲜问题,曾氏也极为关注。1880年初,一方面中日琉球交涉日棘,清廷面临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压力;另一方面,自日朝双方签订《江华条约》,朝鲜内部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③。曾纪泽函请总署以朝鲜发生教案为契机,出面与法国办结该案,借以表示:“高丽为中国属邦,令之行而禁之止,足以见圣朝怀柔之德,即可以杜绝他国觊觎之心,异日不致复有琉球之事。”[3]159曾氏自欧返国后,建议总署进一步加强对朝鲜内政的干预,“更郡县之”,决“不能任其自主独立”[14]。这是曾氏欲借用公法中关于属国管理方式以此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的重要体现。
三、一种外交,两种体制:国际公法与宗藩体制并行
曾纪泽希冀借助国际公法维护国家主权,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宗藩体制作为长久以来维系中国与周边小国君臣关系的重要制度,尽管受近代西方国际关系体制及西方势力的冲击而渐显脆弱,但终归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及其以‘和’为主旨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扩展和应用”[15],具有“天然合理性”式的依恋感。因为周边藩属国与中国素来和睦,既无威逼中国的实力,又深切仰慕中国文化。因此,传统的体制与思想仍有“用武之地”,于是出现了“一种外交两种外交体制”[16]的独特现象。
(一)曾氏对国际公法的认识及运用
曾纪泽对国际公法本身的认识体现在其对公法现实价值、道德价值的评判上,肯定公法的现实与精神意义,理论上主张接纳公法。其一,公法对于维持国际间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曾纪泽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挈大”[3]184。在这样一个列国纷争之世,“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盖国之大小强弱,与时迁变,本无定局”。只要“大国不存吞噬之心,则六合相安,干戈可戢”。也就是说,在各国交涉不逾公法的前提下,此法可为“息兵安民最善之法”[4]905。尤其是当宗藩体系在东西两侧同时受到列强的侵袭时,这种对正义和道德的诉求,对于缺少实力的宗主国中国而言,却显得如此重要。关于1880—1881年的中俄伊犁交涉,曾氏在使俄前曾建议总署通过仲裁的方式评断中俄纷争。所陈如下:
泰西各国遇有争持不决之案,两雄争竞,将成战斗之局,而有一国不欲成争杀之祸者,可请他国从中评断事理。所请之国宜弱小不宜强大,恐其存乘间渔利之心也。宜远不宜近,恐其于事势有所牵涉也。既请小国评断,则两大国皆当惟命是从,……计不如由中国发议,请以西洋小国评定是非,剖断交易,使因此而原约稍有更改,固属甚佳。……凡有一国请他国评断,而一国不受评断者,则不受之国显悖公论,各国将群起而非之,俄人必不出此。[3]162-163
曾氏相信调停制度背后“公义”的存在,以及国际法“公义”的道德约束力,即便这种“公义”的裁判最终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这是曾氏坚守公法之“道义性”以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初步尝试。
其二,曾纪泽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推衍出国际公法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和情理观念,认为“公法不外情理二字,诸事平心科断,自与公法不相违背”[4]939。“情理”不仅是人与人交往的道德规范,也可作为国与国平等往来的有效借鉴。因此,中西交涉必以“情理”为要,“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绌。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不自恃中华上国欺陵远人”。当然,两国风俗不同,“刑律亦殊”,如只论情理,“诚未必纤悉必合”。但两国官绅若能“细询彼国风俗、刑律所以致异之源,亦不难详论婉商,折衷一是也”[3]184-185。在他看来,“公法与公理与以诚信治天下,守四夷的思想是相吻合的,不悖于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儒家理想的政治境界是天下大同,公法同样致力于人类这一最崇高的理想”[17]。曾纪泽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将公法和中国的天道观念进行贯通阐释的尝试,为国际公法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曾纪泽对国际公法的理解及运用不仅反映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殖民竞争时代的国际社会及国际秩序的体认,更展现出近代中国逐渐走向世界的开放心态与进取意识。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清廷对边疆形势、藩属国的重视以及加速了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引入与运用,增强了清廷统治全国的权威性以及对西北边疆政务的介入力度,也是晚清中国与西方社会交融互通、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及扩大中国影响力的有力体现。诚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悠久,封闭与保守因素浓厚,传统儒学占主导地位并且遭受外力逼迫的国家里,这种体认与开放进取心态不能说是带有极大地勉强意味,但此举却是对长久以来,传统士人所持有的“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观念的一种否定。新的、与时俱进的外交观念确立的过程也即传统外交观念意识向近代外交转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贯穿于曾纪泽等知识分子公法维权的一些列实践当中。
(二)曾纪泽对宗藩体制的坚守
尽管国际公法因素在外交中日益增长,但曾纪泽认为宗藩体系的价值和地位始终比公法优越,他对宗藩体制也保有强烈信心。因为近代外交体制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而传统羁縻政策失效的背景下为调适中西关系而逐渐确立的,是一种被迫建立的新制度,因而存有本能的抵触心理。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曾纪泽并无意将公法作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准则。在他看来,这些藩属国之所以尊中国为宗主,与国际公法毫不相干,而是长期感佩于皇朝的“深仁厚泽”与华夏文化所致。诚如所言,“我朝绥驭属国,平时无所取利,遇有事故,则不惜内地之力,安辑而保字之”,且“彼之军国内政,从不牵掣而遥制之”[3]170。如“越南国王既受封于中朝,即为中国篱屏,倘该国有关紧要事件”,中国固有权处置,必不会“置若罔闻”[9]148。因此,他所说的公法主要适用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涉,而依靠大国庇护的小国则与公法无甚关联。也就是说,国际公法在宗藩体系中的作用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若将这种宗藩观念扩大,则能看到曾纪泽对中国固有制度、文化所保有的强烈信念。这从他积极阐扬“西学中源”理论可窥见一二。这种将全部西学视作中学的衍生物,即西学从属中学、西学是就是中国上古之学的观念深刻反映出曾纪泽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眷恋。
曾氏以宗藩朝贡体制延续中国与周边国的君臣关系,虽与公法的主权平等原有所违背,但却维护了“天朝上邦”的宗主形象。这种“天朝上国观念与主权观念的杂糅”[18]心理既体现了曾纪泽在对外关系中既进取又保守的的双重心态,同时也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一种过渡性的表征。
四、曾氏运用国际公法维存藩国属地的局限性
曾纪泽运用国际公法加强对藩国属地的控御思想与实践需放到时代中作进一步探讨。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正在整合国内、国外的两个资源向帝国主义过渡,“国际关系中充满着强国欺弱国,国家之间互相倾轧,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掠夺别国领土,掠夺殖民地”[19]13。如英人“以强凌弱,东侵西夺,动引万国公法附会其说,利则就之,害则避之,衅邻之意荡然无存”[20]。因而,运用公法维权缺乏适宜的外在环境。曾纪泽对此也有深切认识:“各国齐心借条约为言,以与我国为难,明知其未为公允,然其势似难骤改。”[3]188此外,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接触的国际法并不是通行于欧洲原始的国际法,而是为使中国顺从西方要求进而加以修改阉割的“特殊国际法”。
以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为例,关于国家主权,书中一面指出:
各国平战、交际,皆凭此权,而不听命于他国也。[6]27-28
又言及:
然此说若无限制,恐贻错误,盖国之全然自主,惟认天地至尊之主宰,不认他主者有之,国之主权被限者有之,且此中复有等差也。[6]37
就殖民征服而言:
自主之国,各有权掌已之土地公物,或由开拓,或由征服,或由推让,历时既久,他国立约认之,其权皆坚固焉。[6]131
欧罗巴洲各国掌其本土之权,几尽由征服而来,惟其掌之既久,并得他国立约认之,即为牢固。至其属地,或在亚美利加或在阿非利、亚细亚与各海洲等处,其掌之之权,或由寻觅,或由征服迁居,既经诸国之立约认字,亦为牢固。[6]132
关于国家管辖权,一方面:
自主之国,莫不有内治之权,皆可制律,以限定人民之权利分位等事,有权可管辖疆内之人,无论本国之民及外国之民,并审罚其所犯罪案,此常例也。[6]84-85
另一方面:
其所异者,或由公法而起,或因诸国相约而定其限制。[6]85
自主之国,审办犯法之案,尽可自秉其权,不问于他国,此大例也。然若其国与他国有盟约相连,或特立字据,则此权或有所减。[6]107-108
关于西方各国强迫弱小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书中称:
至于各国相待,有被逼立约者,被逼维何,即兵败民饥、敌人盘踞地方等类。如此被逼立约等类,倘不遵守,则战争了无定期,必至被敌征服,尽灭而后已。[6]163-164诚如论者所言,“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缔结既是西方国家拒绝中国适用主权平等、国家独立自主等国际法原则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非西方国家新国际法原则的创造”[21]。因此,“一些进步原则、规则名存实亡了,相反,却确立了一些与帝国主义政策相适应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19]13。国际法在中国实际上是“作了调整的失衡的国际规范”[22]。曾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阿礼国谓,为符合和平正义的需要,“对国际法中某些法规和原则加以特殊的修改,这已为欧洲国家所理解和承认。”当然,其中某些规则,“肯定是专为东方民族而拟定的”④。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也曾说道:“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而全然不顾我们的评价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的武断专横,如何浅薄狭隘。”[23]
注释:
①如蒋跃波《试评曾纪泽的近代外交思想》,《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第37-41页;黄小用著《曾纪泽外交活动与外交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51页。②本文所指“公法”主要指晚清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公法类著作,包含一些列交涉通例、通商条约公法知识。如供职于京师同文馆的美国传教士兼学者丁韪良编译的《万国公法》(1864)、《星招指掌》(1876)、《公法便览》(1877)等书目。参见李恩涵《外交家曾纪泽》,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34-37页。
③以金玉均为代表的朝鲜开化派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凭借日本及欧美的力量,彻底摆脱中朝宗藩关系。1883年7月2日金玉均在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笔谈中就朝鲜是否立即成为独立国家问题征求其意见,“我国已与贵美两国结成对等条约,因此已呈独立之态,可支那依然派兵驻军视我国为属国。”井上馨指出:“依拙者局外人之见,贵国依然如属国般遵从支那。七年前江华事件之际,(贵国)已稍稍呈现独立之萌芽,今又与美国缔结法约,进一步增加了独立倾向。然而(中朝)有三百年之久的关系,欲割断(与中国)关系,谋完全之独立,势必与支那干戈相争,此事一定要避免。因此不要步激进之道,而是循序渐进,争取各国对独立的支持,谋求纯粹无瑕之独立。”金玉均表示:“不可激进不仅是小生之见,我国政府人士均对此予以认可。现在应立即断绝支那的干涉。假如此设想难以实现,就不得不走激进之道。”井上馨认为:“日美两国承认(朝鲜)独立,而支那依然不改旧见,盖因有三百年来关系之故。”转引自祝曙光《朝鲜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近代转型》,《江汉论坛》2021年第2期,第85-86页。
费正清也曾说:“条约制度靠武力建立起来,也只有用炮舰外交去维持。”参见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上卷,第224页。
④洛里默在《国际法精义》中将人类分为三等,分别适用“完全的政治承认”“部分的政治承认”“自然的或单纯的人类承认”。其中非欧洲附属国的土耳其、波斯、中国、日本、暹罗等归于第二类。参见李家善《国际法史新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7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