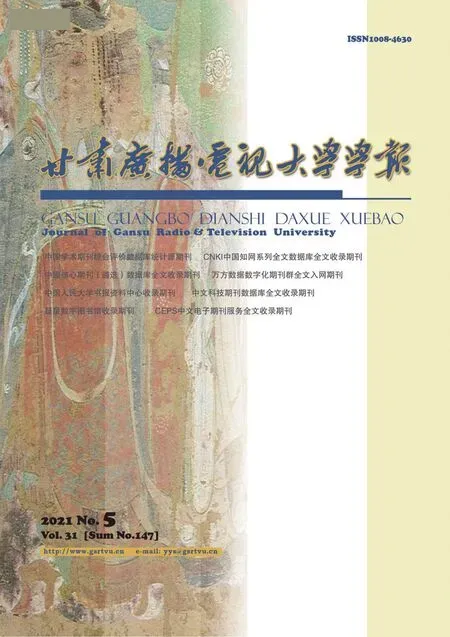从《古都》看战后西方影响下日本传统美的机遇
丁雯清
(上海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444)
川端康成(1899—1972)作为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三部小说均以日本本土作为故事发生背景,体现了川端康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着力于复兴日本本土文化的责任意识。1984年,林武志在《川端康成战后作品研究史·文献目录》中把川端的这种创作动机称为“日本(古典)的回归”,由此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1995年,刘劲予在《试论川端康成〈睡美人〉的美学意义》提出,川端康成通过鉴赏丑而去否定丑,进行超越精神、心灵净化的过程,实现了对美的意义与价值的再确认。叶渭渠在1993年《川端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肯定了川端文学的艺术性,并提出川端是在东洋与西洋的文学比较之下,探究日本民族文化根源。此后,国内开始有黄嗣、俞利军、乔丽媛等学者将川端文学与国内文学家贾平凹、余华,国外泰戈尔等人的文学作品作比较研究。先行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着眼于川端康成小说的古典回归、视觉色彩以及女性魅力等,鲜有探讨川端康成作品中体现出的对西方美学的积极吸收。
文章着眼于小说中古老京都的新旧更替,仔细分析文本中川端康成对西洋事物的不避讳的表述以及角色思想体现,探究二战后西方影响给予京都传统美的机遇。
一、《古都》之名包含的“旧”与“新”
《古都》语言质朴,通篇缓缓叙述日本京都的古老传统文化,以一年四季时间跨度的方式,自吃食住行至节日庆典,充分展现出一幅京都全景卷轴画。川端康成赋予日本京都“古都”之名,除了对古老京都的热爱与留恋,也饱含着对即将消逝的传统之美的哀叹。川端康成曾这样说:“最近我想写一部探寻日本‘故乡’的小说,我所说的古都,当然是指京都。比起写人物和故事来,也许写风物是主要的。”[1]
《古都》之“旧”不仅体现在京都三大祭典(时代祭、葵祭和祇园祭)、鞍马寺的伐竹节、“大”字篝火仪式等日本传统节日之上,也体现在小说主人公千重子移步换景而寻的平安神宫的樱花、嵯峨的竹林、北山的杉木等自然景色之中。与此同时,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各种人物也大多怀揣着怀旧之思,在无法阻止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或消极或积极地寻找一席之位。小说中作为怀旧派主要代表人物,无论是千重子父女,还是和服衣带织工的秀男,他们都用只言片语谨慎地探讨西洋的郁金香,而对日式庭院中的盆栽流连忘返;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触西洋公司制度,又与此同时不知所措、常常避而不谈;他们欣赏西方图样的热情开放,却仍然坚守日式传统图案。在这样的对比之下,怀旧派人物表现出来的对古都之“旧”的敏感以及虔敬之心正是川端对日本传统美学的追求。
然而,有“旧”即有“新”,《古都》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故事中的现代风气的浸染,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涵。面对二战失败后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本传统文化日益衰落,古都不得不面对西方传来的“新”事物。川端抱着探寻日本“精神故乡”的愿望开始《古都》创作,在《独影自命》中川端写道:“我把战后自己的生命作为我的余生。余生已不为自己所有,它将是日本美的传统的表现。”
小说通篇以平缓笔调叙述古老京都的一切,甚而将丝丝孤独与哀愁潜藏于千重子思想之中,与其说这是囿于传统的表现,不如说这是千重子对父亲太吉郎的一种诗意性的传承与沿袭。太吉郎对旧事物的依恋与对新事物的小心尝试,正是川端康成思想中体现的因传统之美逐渐消失的哀伤惆怅与无可奈何。而小说主人公千重子作为新旧环境交替下的典型人物,虽成长于日本传统家父长制之下,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古老京都大家闺秀之风,但其思想在战后日本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也逐步丰富起来。千重子眼里不仅仅有款式随四季转换的和服之美,也有青梅竹马的大学生真一身上西式校服的英姿;不仅有对日式杉木巍峨的同理之心,也有对西洋郁金香的积极赏味。小说最后千重子也是接受爱慕对象龙助的意见,开始亲自打理家族店铺。千重子本身年轻的血液正给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源源不断的力量。作为并非盲目消沉的主人公,千重子的言行是作者在新旧更替社会环境下对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传入的接受与肯定。
在这样“旧”与“新”的碰撞之间,涌出的无数难以释怀与爆发的情感,反而更添《古都》的韵味,川端康式将故事的发展与人物的刻画融合在京都的四季风景与节日风俗之中[2],新旧二者并非渐行渐远,而是以一种日式的无尽的时间感相互融合。川端康成借《古都》中所宣扬的并不是固守日本传统,而是在充分理解融合西式思想之后,呼吁日本传统文化之美的再回归。
二、川端康成日式与西式思想的兼容并蓄
《古都》中“出世”的消极精神中潜藏着“入世”的积极态度。川端康成曾表明过自己的精神境界,他说“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他把禅宗的“悟”同真善美的艺术追求联系在一起,创作出幽玄而又返朴归真的艺术意境[3]。生于佛教世家的川端,幼年失去双亲,由最疼爱他的佛教徒祖父三八郎抚养,禅宗的无常观早已渗透他的内心。另外川端很早就接触到了《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其中朦胧与含蓄的虚无色彩更成为川端康成一生的的思想源泉。深谙日本传统物哀、虚无之美的川端康成尊重个人思想私密体验,使《古都》于苗子的离去时戛然而止,将结局留给读者去细品猜测。
其实《古都》是可以有结局的,无论作为孪生姐妹的苗子最终是否会嫁给秀男,是否还会回到千重子身边,还是佐田家的店铺是否会吸取西方企业制度继续经营,任何发展都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小说的整体走向。但是,川端康成缄口不提,而是使孪生姐妹在最后的对话中反复提及“幻”字,以一种日式虚无主义结束全文。《古都》最后,秀男和苗子在山里相见时看错的“虹”,苗子常向千重子提到的“幻灭”“幻影”,乃至最后晨曦中的“霞”,都与川端的思想告白有着密切联系。像千重子和苗子这一对孪生姐妹,自小分离竟能再次相遇,并互生怜惜之情,这些情节似乎也在阐释川端心中的“虚空”或“无”,此处川端已经在着力输出自己对于日本传统美的理解。正如川端所言,他所提及的是与西方的虚无主义完全不同的概念,他所体验并宣扬的日式传统之美,重在感知,而非逃避,一切本是无,若偏要在这无中追寻有,那么结果只能是“空”,而“空”又将引发阅读的“虚无”。虚无不可解,唯有感知,这也是川端作品中美而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4]。
同时,西方现代文学及审美意识在川端康成的创作生涯中从未缺席。川端康成自学生时代起,就广泛涉猎日本及世界名著,阅读惠特曼、乔伊斯、泰戈尔等人的作品,对其日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5]4。20世纪中叶,尚处于战后恢复阶段的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文学界大多主张要以“新的感觉”表现自我,兴起了表达颓废思想的“新感觉派”。其成员之一的川端康成于运动前期以理性构筑“新感觉派”的理论基础,促进了新文学的诞生。但由于“新感觉派”无视现实,单纯追求以新奇的形式创作,未能在宣传日本传统文化中发挥效果,只能以失败告终。新感觉派解体后,川端康成进行了学习西方现代文学的第二次尝试,即新心理主义时期。由于川端康成未能很好地总结新感觉派时期失败的经验教训,仅仅停留在意识流技法的简单模仿之上,因此第二次文学尝试也以失败告终[5]6。但川端康成在这些尝试中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经验,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之路后,他将目光再次转向传统。再次进行探索的川端康成并非简单地继承日本传统,而是以西方现代的思考和审美方式去看待日本传统,以期获得中西方都为之感动的作品。《雪国》开篇,岛村从车窗玻璃上看见叶子的美,窗外是飞逝的景物,窗内是叶子清秀的面庞,这种以个人视点描述的方式就是利用了西方的先锋叙述技巧[5]31,同时也兼顾到了日本传统的表现美学,避免了对叶子美貌的直接描述。而《古都》中,虽然全文景物描写泼墨更多,但川端康成以双胞胎姐妹的不同命运为主线,将一个人的出生、生命、宗教信仰以及个人存在意识等问题逐个抛出,提出了很多关于人类生存的本源问题[6],这也是西方现代文学创作中所一直关注的话题。此外,在西方现代文学中,人和自然的描写往往是分割开来的,一般都是着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很少将人物的心理感情融入到自然当中[7],但川端巧妙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可见,经过长期探索,川端康成终于在将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手法有机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步入创作成熟期。
《古都》中,川端康成常常通过描写千重子父女对同一事物不同态度,来体现日式与西式美学的交融与碰撞。川端康成在描写太吉郎时,刻画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京都人,他拒绝时兴的和服展览等活动,偏居一隅,独自欣赏设计素雅的日式传统图案。女儿千重子为了使父亲有好的灵感,给父亲买一些有瑞士抽象派画家保尔·克利、法国印象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等人作品的现代画册。然而两人又如此惺惺相惜,千重子坚持穿戴父亲设计的素雅图案织物,父亲太吉郎也并非将西方画册束之高阁,而是努力研究克利的画册,为千重子设计了让他人都为之一惊的华丽腰带。可见,比起川端前期小说对西式美学含蓄地引用转换,在《古都》中西式美学要素的引用更显直白明朗。在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京都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川端康成并没有一昧表达衰颓无望的态度,而是借不同群体之间的思想碰撞探讨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共存,一边沉着自信地描绘京都四季之美,一边旁征博引西式美学,将《古都》的古老传统以鲜活的方式展现出来。虽然小说自始至终都带有难以摆脱的怀旧哀情,但是这种基于动荡社会的现实的悲哀,加上川端康成叙述的从容态度,使得小说更具感染力,也使得小说添加了一层积极的色彩。可以说《古都》体现出川端康成在吸收西式美学后,达到了一种成熟的思想境界,从而再实现日式美学的回归,这种尝试对于传统美学的回归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古都》传统之美的机遇
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整个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手工业界更逃避不了被机器大工业批量生产取代的命运,这正是川端康成对即将消亡的传统技艺的忧伤和悲哀[8]。作为一家之主的太吉郎,对生活一直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动辄赴山中修身养性,更因对西方公司制的抵触,放任管家经营自家和服店铺。当他看到附近大街上的住家已变成能接待大旅行团的饭店旅馆,由此联想到古雅的京都风光不久就要被喧闹的工业区所取代,不由得发出了阵阵哀伤,流露出无可奈何与惋惜的哀叹。作为传统派代表的太吉郎身上,体现出了川端康成怀旧的哀怨,“日本的战败也加深了我的凄凉。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死去了,自己的骨头被日本故乡的秋雨浸湿,被日本故乡的落叶淹没,我感受到了古人悲哀的叹息”[9]。
然而,《古都》中处处埋着推陈出新的伏笔:千重子和朋友们逗养铃虫,壶中天地的金钟儿若保持亲近交配,幼虫就会不健康,所以千重子和朋友经常交换雄虫以新的血液以保持传承;千重子经常购置西方现代画册送给父亲太吉郎以激发他的灵感,虽然太吉郎才思一度闭塞,但从父女两人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其跃跃欲试的心态;植物园一行,被太吉郎嗤之以鼻的西洋郁金香在秀男眼里却是生机勃勃,秀男认为即使郁金香有凋落之时,但能够灿烂一时也是一种“活着”的体现;大丝绸批发商长子龙助传授现代企业经营思想给千重子,使其成功震住自家一度被父亲太吉郎放任不管、野心勃勃的店铺掌柜;小说最后千重子也开始敢于表露心态,积极引导喜爱日式盆景的父亲去看自由生长、千姿百态的樟树……这一切的一切,是新旧事物的交替冲撞,也是一代人不同于另一代人的思想交鸣。宛如川端康城本人的太吉郎虽然对传统文化遭受冲击感到万分悲哀,但他也并没有一昧囿于自我牢笼之中。在《古都》中,太吉郎从给爱女千重子设计充满现代感的腰带,对偶尔爆发出现代灵感的织匠秀男另眼相看,到跟随老一辈京都人去乘电车,再到最后认同女儿对樟树的一番见解,无一不体现出他对时代变更的些许理解之意。如太吉郎这样的京都传统派,尽管不愿看到京都的改变,消极应对历史潮流的变化,但不是一昧地固守陈规。面对战后西方现代工业化对日本传统各方面的冲击,川端康成通过自己文学性的观望明确表达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古都》中穿插出现的西方美术与现代工业并未带给小说冷冰冰的不适之感,即使是谈及西方事物时,川端康成也以同样的表达方式处理文本,缓缓叙述发生在古老京都的一切。尤其在日文文本中,千重子用京都方言谈及周遭事物,更能体现出古老京都所特有的别样优美情调。川端康成选择最具日本传统之美的京都来探求现代化进程下的新机遇,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尝试,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对比效果,更使小说在平淡无奇的情节之下展现出日本传统之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融与碰撞。虽然叶渭渠针对《古都》提出:“这部作品所抒发的怀旧之情,感叹日本传统的不继和衰落,实际上是感时伤世,嗟叹战败后京都的荒芜,以图唤起国人对保护京都传统和发扬民族精神文化的热忱。”[10]但细读《古都》可看出,川端康成并不是一昧消沉,竭力抵抗现代化进程,而是通过对千重子与周围新旧人物以及事物的描写,呼吁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之时要保护好日本传统文化,与其哀叹时运不济,不如奋力将美好的日本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四、结语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曾说:“玫瑰,就是玫瑰长成玫瑰的样子(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川端康城可谓成功地将京都及其所有的形象记录了下来。通过《古都》,视线于四季之中从古寺游移到竹林、山杉、和服织带、祭典、格子门……触目所及的一屋一瓦、一草一木,甚至是这城市本身,作为传统的媒介,早已在世人的脑海中转化为一种川端那哀愁虚无的言语[11]。京都,就是京都的样子。即使京都是个拥有超过百万居民的现代都市,在古老的寺庙神社与传统庆典意象之下,历史重量和传统力量仍然赋予这个城市的街道一种毋庸置疑的、统一而和谐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