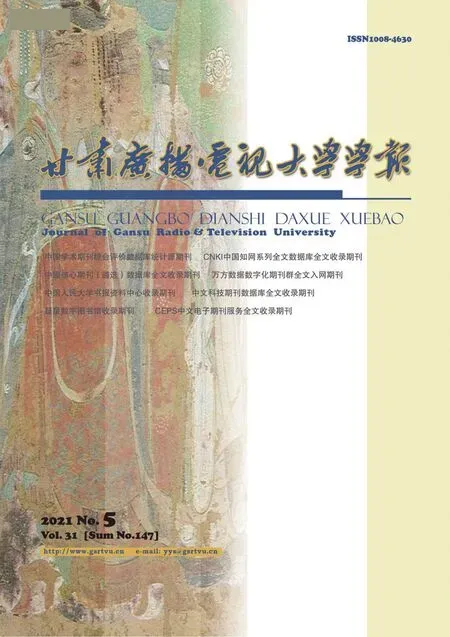罗兰·巴特“中性之欲”中的道家色彩探究
孙 婷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引言
“中性”思想在巴特的理论生涯中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虽然直到巴特晚年时,“中性”才在其所授课程中被单独探讨,但在此之前就已经不断出现在他不同时期的理论中。按照贝纳尔·科芒在《罗兰·巴特,走向中性》一书中所称:“(中性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并且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因为这种观念在巴特兴致不减的写作形成的不同阶段中不曾有过任何收敛。”[1]巴特早在《关于〈局外人〉风格的思考》一文中就提出“中性”的概念,此时“中性”作为一个形容词来描述加缪书中古怪的文本风格。后在《零度的写作》中巴特将“中性”与“零度”同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性”思想都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结合,并始终带有一种剔除主体的决断性。在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之后,伴随着结构主义的逐渐瓦解,“中性”思想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以一个形容词的身份寄居于语言学的王国之下,而是成为一种不同于二律背反位于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状态[2]。巴特本人也逐步从符号的悖论之中跳出来,不同于倾向用宏大的符号学或结构主义体系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他通过“中性之欲”,一种更为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为其晚期思想增添新鲜的生命力。
1978年巴特在讲授课程“中性”时所采取的方式并非传统的系统性框架,而是一种片段式讲授,并且他在授课时反复强调“中性”是无法被定义的。对于这样一个无法被概念化的观念,巴特将其融入到二十多个熟语当中,并借助卢梭、布朗肖、皮浪主义的怀疑论等思想将“中性之欲”呈现出来,其中便包括对中国道家学说的大量引用。巴特在整个课程的讲稿中直接提到道家思想有二十余次。长久以来,我国都习惯于直接引入西方文化对本土问题进行阐释,这种行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惰性,另一方面,我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又曾遭受重创,这导致我国本土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断层。巴特作为西方思想家将东方文化融入自身的理论建构,并对中国传统道家学说的思想大加肯定,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的注意。正如《中性》一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老子的自画像……宣告了老子的神秘主义将在中性的营造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3]7笔者从“中性之欲”的思想出发,对于巴特如何将其思想与道家学说结合以及为什么这样结合进行探究,并从作为参照物的道家学说、作为身体建构的道家学说以及作为批判工具的道家学说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作为理论阐释的参照物
(一)对“中性之欲”内容的阐释
首先,巴特通过道家思想解释了为什么要用“欲望”一词来表达“中性”概念。巴特之所以将“中性”视为一种欲望,原因在于他反对将这个概念进行断言式的判断,“中性之欲”的源头便是对二元性的聚合关系以及意义产生的破除,对于巴特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去追究中性的涵义到底是什么,而是欲望的产生。这种欲望似乎是不可言的,因为它无法体系化,只能被展示出来从而唤起人们对于差异和完满性的追求。我们无法用判断性的话语来为“中性”定性,因为它不是通过否定其他项来凸显自身的正确性,也不是用强势的力量与其他项进行对抗,它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状态,对于巴特而言更是一种新的起点。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状态就是老子所说的“了解道的人不谈论道,谈论道的人不了解道”[3]48。
其次,巴特将“道家”思想中的具体言论与“中性”思想包含的不同元素相连接。巴特将开篇引入《道德经》第二十章的内容作为权充题铭之一,通过“我”与众人之间状态的对比呈现出一种平和、淡然的状态,而这也为“中性之欲”的阐发奠定了非对抗性的基调。之后在“色彩”这个熟语的论述中,巴特再次引用了老子的话“我是无色的……中性的,就像尚无最初的情感的婴儿,没有意图,没有目标”[3]80,老子崇尚对人性对自然最初状态的复归,他虽然允许不同色彩的存在,但却采取一种差别之上的无差别状态。对于“中性之欲”而言,不需要通过色彩的划分来区别意义,不对任何色彩做出选择则意味着没有任何权力的压迫让“我”做出判断。巴特在表达对言语行为的看法时引用了《道家精义》的话“为什么要用词语来区分事物呢?词语只能表达对于事物的主观的想象的理解”[3]195。在道家思想中,语言并非具有无法撼动的地位,物我归一,无需用言语进行阐释,不同的言语所表达的不同意义反而会背离最初的涵义。在这里道家学说与巴特对言语进行排斥的出发点不同,巴特是将言语看成一种法西斯式的权威进行干预,而道家则出于一种朴素的辩证哲学。
再次,巴特在谈论“中性之欲”时,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描述道家的“无为”思想。很多西方学者将“无为”的“为”译为reaction,“无为”的意思也因此变成了“什么都不做”,但事实上“无为”是顺应自然与天命而“为”,或是说,与“有为”相比,换一种视角与方式“为”。巴特在这里用“无为”来阐述“中性之欲”,意在揭示某种生存意志,在面对广泛存在的差异时,无需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进行取舍,只需采取“无为”的态度即可,也就是道家文化中的“撄宁”。所谓的不做取舍或是贤者模式看似与传统的主流观念相左,但“中性之欲”是将其看成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方式,站在更高角度对于人生过往的反思与对现实社会的审视。
(二)消极背后的积极性
巴特将道家学说作为自己的参照物来描述“中性之欲”的内涵时,由于中西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其部分内容偏离了道家学说本身的出发点,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揭开了“中性之欲”的神秘面纱。“中性之欲”反对意义对立的聚合体,反对断言式的言语活动,它所走的是一条将沉默作为能指,优雅完善的道路。那么这种“中性之欲”是否只是晚年巴特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消极逃避呢?对于这一疑问,“中性之欲”与道家学说做出了类似的回答。巴特在《中性》开头这样描述“中性”与“非此即彼”的区别:“非此即彼好像是对中性的滑稽模仿。非此即彼是断言性的,然而是反动的;中性是否定的,然而是积极的。”[3]147对于“中性之欲”的积极性我们需要从其反面进行理解,它之所以与现有的思考方式,甚至与言语活动相背离,其原因在于它将长久存在的意义聚合体视为一种无生命的惰性,同时这种聚合体所具有的强大意志和权威让众人在几乎没有任何反抗性的前提下进行选择。“中性之欲”正是立足于此,它试图打开一个小孔,让长久被动的人们落入充满激情的思考与反叛之中,只是这次的反叛巴特没有选择最激烈的方式,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因此,我们无法断言“中性之欲”是巴特丧失思考与批判意识的消极之举,相反它具有某种积极性。
道家学说与“中性之欲”似乎有着同样的境遇。道家学说在中国长期处于对儒家学说的补充地位,并且大众习惯于将其与儒家学说的对立称为“积极入世”与“消极出世”。与“中性之欲”类似,道家反对一味地积极进取,崇尚返归自然,不断回眸进行审视,同时也反对战争,主张以柔克刚。可见,与儒家所推崇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相比,道家似乎是在逃避对现实事物的摄取与对人生目标的争取,实则不然。首先,道家对于放缓锐意进取的行为而维护自然和谐的看法正是来自于更高层次的智慧,当儒家反复强调要走不断进取的人生道路时,道家对此进行善意提醒,只有进取之路上时时回头反思才不至于偏离原有的方向,否则就会造成自然与社会的不和谐。其次,在面对复杂社会时,儒家强调不断向前主动克服艰难困苦,而道家则强调“无为”“大智如愚”等,这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以柔克刚的应对之法。再次,儒家更多的立足于社会性群体活动,而道家则更关注个人的精神生活,通过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去指导人们更好地生活。与儒家学说和与擅长论辩的西方文化而言,道家学说与“中性之欲”显得更为轻盈而有力,这再次呼应了二者内涵中的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解释巴特为什么用道家学说来对自身进行新的身体建构。
三、作为身体建构的方法论
(一)精神依托的丧失
巴特在撰写“中性”课程文稿中途母亲离世,这件事对其课程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伴的巴特来说,这件事导致了他内心情感的崩溃,也使他的理论在最后几年转入新的方向。在此事发生之前,巴特几乎从未在自己的理论创作中揭露个人的生活或心理状况,但母亲离世后,他先后在《明室》《哀痛日记》中表达了个人的悲痛。正如他在《哀痛日记》中所言“时间不会使任何东西消失;它只会使哀痛的情绪消失”[4]。与此同时,在这种焦虑痛苦的情绪笼罩下,巴特对于死亡的意识发生改变,并通过新的身体建构来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缓解内心的悲痛。母亲的离世之所以会使巴特走向带有神秘色彩和空想色彩的世界,其原因首先在于母亲是巴特与外界世界产生联系的依托。巴特从青年时代便饱受肺结核的困扰,独自生活在疗养院中。与外界隔绝是巴特生活的常态,同时他同性恋的身份以及身体的肥胖更使他处于社会的边缘。对于巴特而言,母亲是他生活的动力,母亲的离世对于巴特意味着安全感的缺失,这导致巴特对如何继续生活产生疑惑,并转向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巴特在《自述》中写到自己小时候和同伴玩耍时不慎落入基坑,当其他人都爬出去了,自己正因爬不上去而感到绝望时,是母亲跑过来欢呼着他的名字[5]。
母亲对于巴特而言是一个多重符号,象征着安全、自由以及女人的身份。当这个符号缺失时,一方面会导致巴特陷入情感危机之中,虽然他试图通过母亲的照片,母亲的遗物甚至模仿母亲生前的生活习惯来唤回过去的生活经验,但最终却带来了个人状态的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则促使巴特寻找新的精神依托,这时他将“中性之欲”作为通往完满生活的新起点,或许这是他最好的选择。而崇尚自然,对人性给予终极关怀的道家学说也自然成为“中性之欲”的一个理论支撑点。
(二)道家学说的身体实践
道家学说涵盖范围非常广,从辩证的宇宙观、自然观,到国家管理理论,再到修身养性,它几乎包罗万象。巴特在阐述“中性之欲”时,除了借用二者在思想上的相似性之外,更是将道家关于个人生活的学说作为自己新的身体实践的方法论。首先,巴特借鉴了道家学说中的贤者状态。对于真正的贤者而言,善意并非是出于功能的功利性判断,而应该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柔性的善意,一种‘超越’的善”[3]132,也就是说贤者不会因为事物之间的差别性而区别对待,因为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平等的存在,并最终可以达到一种平和无所谓的姿态。此外,巴特还引入道家的美德“大智若愚”,以愚笨的状态示人是为了摆脱他人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本真的自我。如同巴特在《明室》中所论述的,当人处于摄影机之下,便不自觉地将自己变为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带有表演性质的符号,处于他人目光之下的人也同样会产生非真实的状态。巴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其本身对外界社会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无法忍受来自外界的指责,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给予的种种头衔也深感厌倦。
道家学说中的不同养生之法为人们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尤其是道家所提倡的“辟谷”。道家认为人的身体是由三条虫子所组成的,为了驱逐这三条虫子,人必须停止进食谷物,只有身体清瘦才能达到中性。还有“赤贫”的状态,巴特将这种状态形容为:“我常常有一个梦,下决心终有一天把家什清空:预想中的举动,手边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物什:什么都不留双份。”[3]239巴特在这里所提到的身体实践几乎都是远离尘世的,并且保持对边缘人的宽容,包括最后提出的以“雌雄同体”消解性别之间的对立,这一切都可看作巴特借助道家学说创建的新的生活愿景。这种愿景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巴特对现有世界的不满以及建立新起点的迫切性。
四、作为西方视角的批判工具
(一)为什么选择道家学说
中国的道家学说在巴特晚年关于“中性之欲”的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于道家思想的青睐难道仅仅是因为其与“中性之欲”在内涵上朦胧的相似性吗?其实不然。在20世纪,将道家思想引入自身理论建设的西方思想家,还有海德格尔、韦伯等。可以说,西方在20世纪之后掀起了一股具有神秘色彩的“道家热”,就如荣格所描述的“对道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似乎已成了一种集体现象,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6]。道家学说之所以会在西方盛行一时,甚至引起了比儒家学说更为巨烈的反响,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西方人对于本土文化的怀疑。频繁的战争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让西方学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个人的精神危机,他们对和谐自然的状态充满期待,道家学说也因此成为他们所要找寻的精神家园。此外,在20世纪,道家学说的译本开始在西方流行,这些译本并非完全是从原文出发,但却代表了西方人借助老庄的形象表达出个人的现代思想。巴特在“中性”课程中引用的道家学说也多出自于西方学者对其的阐释,其中包括法国学者亨利·马伯乐的《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作》以及让·罗格尼耶的《道家精义》[7]。可见,巴特对于道家的青睐并非偶然,更多的是历史与个人原因的相互交杂。
(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批判
巴特在直接描述道家思想的过程中,也将其与西方文化作了比较。比如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大男子主义”的,擅长宣扬困难与挑战,而道家文化则擅长转换方式从细微处入手。在描述“悟”与其他的思维方式时,巴特指出“悟”并非出自传统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一种偶然性的契机。巴特还将道家的镜子与西方的镜子作比较,前者是优雅自得的,保持对外物的回应但从未希望从中摄取什么,而后者多是有目的的机械式行动。从这些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巴特的“中性之欲”中除了包含对于个人生活与思维方式的思考,同样隐藏着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实则贯穿于巴特的一生,他最初通过神话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符号学系统在语言学层面理解世界,又用结构主义来划分秩序,揭露世界的真实本原。他一直反对学院派,反对权威,但他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可颠覆性,所以在生命的后半段,他转向了一种新的方式,打破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二元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西方社会象征体系,并提出掺杂了中国道家学说的“中性”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道家思想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关注个人命运以及自然和谐的任务,它不断提醒人们在不断前进的时候需要不断回眸,也需要包容差异性的存在。对于巴特而言,他本身的存在就代表了某种差异性,而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更注重的是利益的最大化,会为了成本的最低化抹杀差异的存在。虽然巴特自身的思想也曾引起他与其他人的争辩,但他真正渴望的仍是平等与包容,他对于“中性之欲”的尝试也是他对建立真实性与平等性的尝试。“中性”一词,看似平淡甚至悲观,却包含了巴特最后的批判活力。
五、结语
巴特在晚年经历了生活的创伤之后,对个体身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中性之欲”的概念。“中性之欲”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态度,它内在的积极性是他反抗权势规则的印证,也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重新解读。他晚年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他早期思想中鲜明的批判性与对抗性形成鲜明反差,二元对立的语言结构也有所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显得更为柔和的处世之道。正如中国道家学说的“虚静”一词所揭示的那样,“中性”虽然掩盖了冲锋陷阵的光芒,但内在却更加具有力度。巴特对于道家学说的引用,既让我们窥探到这位思想家后期思想的转变,同时也印证了强调生命意识的中国哲学的普世性。道家学说没有创造宗教中的上帝,甚至不具备一个完整鲜明的系统,但依旧可以跨越文化抚慰个体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