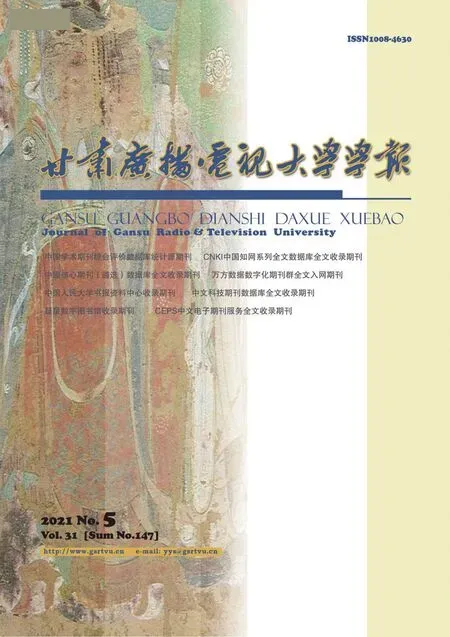理想主义视域下海子的流浪与还乡
段 曦
(菏泽学院 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浪子”“远方”等意象与“故乡”“家园”等意象在海子诗歌中相互呼应,构成了流浪与还乡的一组对应主题。海子对“流浪”的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与他自身的浪漫主义气质密不可分,“浪漫主义者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加偏爱流浪”,因为“流浪最能实现浪漫情调,满足浪漫主义者的心理上与美学上的需要”[1]252。在《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这一诗体小说中,海子塑造了一群流浪艺人并不止一次地借“我”之口吐露自己对远方的向往:“流浪的人,你不是对草原尽头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吗?说出来你就心安了。他甚至把流浪视为“朝圣”,对远方充满着执着与渴望,在浪漫主义情愫的裹挟下,海子以一种绝对的、毋庸置肄的态度肯定了远方与流浪。
海子如此钟情于流浪,同时又不断地渴望还乡。在《太阳·弑》中,流浪的剑回到故乡巴比伦,与他一起长大的吉普赛和青草冥冥中也来到巴比伦,还乡的冲动更像是源于一种本能的指引,一种命运的推动。对海子而言,故乡一词所具有的吸引力并不亚于流浪,在他的诗歌中,无不充斥着对故乡的眷恋、对乡村的强烈认同,甚至当故乡成为回不去的家园时,海子试图依靠诗歌的力量完成精神上的还乡。在海子这里,还乡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一如流浪。关于海子的还乡书写已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关注,而流浪意识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某种程度而言,在海子的诗歌中不论是流浪还是还乡都具有多重指涉,只有将二者并置才能深入海子的诗歌世界触摸其所具有的独特性与矛盾性,才能理解海子所营造的精神家园及其诗歌的精神突围的意义。
一
流浪在海子这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而是具有多重含义。首先,流浪指向海子在异乡的漂泊。15岁的海子离开安徽老家到北京大学求学,毕业之后留在北京政法大学教书,离开了生养自己的故乡,独自在北京生活,于海子而言这是远离故乡的流浪。海子曾在《昌平柿子树》一诗中感叹道:“柿子树下/不是我的家”。而在《日落时分的部落》中,北京在海子眼里只是“内部空空”的“破碎的城”,“凄凉而尖锐”,这些都是海子身在他乡时真实的心理写照。
海子将漂泊在外的自己定义为“浪子”,但显然在都市的流浪并没有多少潇洒的成分,更多的是思乡的痛苦与生存的辛酸。海子将自己比作叶赛宁,那个身处莫斯科却对故乡一往情深的俄罗斯诗人,“我饱经忧患/一贫如洗/昨日行走流浪/来到波斯酒馆/别人叫我/诗人叶赛宁/浪子叶赛宁/俄罗斯的嘴唇/梁赞的屋顶/黄昏的面容/农民的心”(《诗人叶赛宁(组诗)》)。叶赛宁在城市中感受到的隔阂海子也心有戚戚,毕竟二人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农村出身的他们都留在了都市,可心却记挂着遥远的乡村,乡村记忆和情结在他们的诗歌中留下了代表性的印记。叶赛宁将自己称为“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献给马里延果夫》),海子则说:“我是中国诗人/稻谷的儿子。”(《诗人叶赛宁(组诗)》)海子描述在城市中的流浪时不忘调侃一番:“我是浪子/我戴着水浪的帽子”,但仍难掩凄凉:“我戴着漂泊的屋顶/灯火吹灭我/家乡赶走我/来到酒馆和城市。”海子主动走出家乡,不曾料到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他负气般地责怪家乡,是“家乡赶我走”,借叶赛宁之口叹出自己的无奈:“我本是农家子弟/……/但为什么/我来到了酒馆/和城市”(《诗人叶赛宁(组诗)》)。
“农家子弟”是海子难以忘记和抹去的身份,尤其是农村出身的他曾因家境贫穷导致初恋失败,这一事件深深打击了诗人单纯质朴的心“一颗农民的心”。他曾说:“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我粗笨/善良的只有我/熟悉这些身边的木头/瓦片和一代代/诚实的婚姻”(《门关户闭》)。这仿佛是一种自我证明,证明“粗笨”却“善良”是来自农村的人特有的气质。海子对这一身份的肯定,潜意识中已经把自己与城市、与周围的人隔开。可以说,海子在城市中体会到的疏离感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海子的流浪体验。尽管满怀着对土地与田野的深情,海子却早已远离了熟悉的乡村,“如今我坐在街镇的一角”也意味着“远离了五谷丰盛的村庄”(《长发飞舞的姑娘(五月之夜)》)。
其次,海子曾几次出门远行,据燎原考证,海子于1984年七八月份去了陕西,可能还顺便到了甘肃兰州。1986年七八月间,海子从北京出发到达青海西宁后进入西藏,而后返回青海经过祁连山、甘肃敦煌等地进入内蒙古。1988年夏季海子再次进入西藏。此外,海子曾多次到过四川,1987年的寒假海子由四川广元进入九寨沟,而后经由达县返回安徽老家。1988年初海子到了四川成都、乐山等地,还带去了《太阳·七部书》中已完成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海子的四川之行更多是为了与四川诗人交流,以慰藉身处北京时不得志的失意,而其他几次远行则与他的诗歌写作密切相关。燎原认为在海子的诗歌生涯中“诸多最重要的诗歌都与出门远旅相关”,海子自己“则把这称作‘流浪’,并把这种流浪视作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2]80。
海子曾到过内蒙古额济纳旗,在与此相关的诗作中诗人写道:“还有十天我就要结束漂泊的生涯”(《北斗七星七座村庄——献给萍水相逢的额济纳姑娘》)。而在另一首与青海湖有关的诗中海子提到:“其他的浪子,治好了疾病/已回原籍,我这就想去见你们”(《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漂泊”与“浪子”分别是海子给自己的旅程以及旅程中的自己所下的定义,不可否认的是,出门远旅给海子带来了创作灵感,他的不少佳作均是“流浪”的成果。作于1985年1月20日的《熟了麦子》提到“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燎原认为该诗极可能与海子1984年暑期的兰州之行相关,而《北斗七星七座村庄——献给萍水相逢的额济纳姑娘》《黄金草原》《怅望祁连(之一)》《怅望祁连(之二)》《敦煌》等诗由标题便可看出1986年暑期之行带给海子的灵感,《云朵》《西藏》等诗也都与西藏远旅相关。1988年暑期海子的青藏之行更是令他创作出不少名篇佳作。海子在一些诗歌的结尾处将作品完成的时间、地点清晰地标出,可见都是在出门远旅的“流浪”之中所作,如“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的《远方》一诗,诗后落款为“1988.8.19萨迦夜,21拉萨”,由此得知该诗作于海子途经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一个夜晚,并于21日在拉萨修改而成。又如《日记》一诗的落款为“1988.7.25火车经德令哈”。海子的几次出门远旅,如果就其经济情况而言,确实有些“流浪”的意味,但如果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称为采风。据说海子曾经为了验证“米脂的姑娘,绥德的汉”从山西进入陕北采风,“还先后两次去了西藏采风”[3],可见海子将这种“流浪”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与诗歌相关,海子对诗歌的热爱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谈,而是处处体现在他生命、生活的点滴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海子曾两次赴西藏,可见海子对西藏、青藏高原的痴迷。海子对青藏高原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海子”这一笔名的使用。海子最初在自印诗集《小站》中使用的是“査海生”的本名,毕业后在政法大学校报工作时曾以“扎卡”作为笔名(这一笔名也颇有藏族风格),直到1984年创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时第一次使用“海子”作为笔名。关于“海子”笔名的由来,苇岸曾以为取的是“大海的儿子”之意,但遭到海子的否认。苇岸自述道:“当时我孤陋到尚不知蒙藏高地的湖泊,是被诗意地称为‘海子’的”[4]44。可能早在1984年之前海子已经注意到“海子”这个词,并多少对青藏高原有所了解。居住在青海、西藏等地的人们将湖泊称为海子,取其广阔无边像极了大海之意。而对于杨炼的史诗追寻、对昌耀诗歌的关注则使得海子对西藏、青藏高原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杨炼的现代史诗书写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海子,也使得海子在认同这一风格的创作试炼中逐渐形成色彩鲜明的个人风格,一如杨炼诗歌中“元素”(《土地》)、“石头”(《西藏》)等意象在海子诗歌中的延伸与再创造。燎原认为杨炼是对海子影响最大的当代诗人,两人“极其相似”,都以“地理和文化背景”作为写作资源,并且海子“一直追踪着杨炼的史诗路径”由《礼魂》进入西安、敦煌和青藏高原,在海子诗歌中呈现为以半坡、长安、敦煌等地为核心的诗意书写,之后杨炼的组诗《西藏》更是对海子“显示了特殊的意义”[2]105。西藏逐渐成为诗人的精神家园,成为不同于安徽怀宁査湾的第二故乡,西藏对海子而言不再是“流浪”旅程中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承载了更多浪漫情怀和诗意寄托的精神圣地。当海子面对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脉时,他说:“我是在故乡的海底——/走过世界最高的地方”(《喜马拉雅》)。由九首短诗组成的《汉俳》中,第五首名为《西藏》,海子写道:“回到我们的山上去/荒凉高原上众神的火光。”西藏于海子而言已具有一种神性的指引,让海子不自觉地萌发了精神归属与依赖的需求。1988年8月写于拉萨的《我飞遍草原的天空》一诗中海子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写道:“今天有家的必须回家。”与其说“草原的天空不可阻挡”,毋宁说草原对海子的吸引不可阻挡,海子置身西藏,有一种“飞回家乡”的自在。同样写于8月的《雪》,开篇便是“千辛万苦回到故乡/我的骨骼雪白也长不出青稞”。
此外,对昌耀诗歌的关注也使海子对西藏、青藏高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燎原认为昌耀以青藏高原为主的“大地本相”的诗作以及骆一禾对昌耀的欣赏,都不同程度导致了海子对昌耀的关注,而且海子作品中不时表现出对昌耀诗歌的“折射”与“暗合”。在《河床(〈青藏高原的形体〉之一)》中,昌耀写道:“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腭骨化石。是始皇帝。……”诗人从黄河的发源地写起,暗示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源头,整首诗大气豪迈,虚实结合的意象使“河床”真实可感。陈超认为在众多书写黄河的诗作中,该诗“真正称得上独标逸韵另铸伟辞了!”[5]可以说,这首诗的风格贴近海子心中的“大诗”构想,更为重要的是海子对昌耀诗歌中的青藏高原这一地理版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海子亲自抵达西藏,亲身感受青藏高原的自然、人文风光后,被深深吸引。海子还收藏了很多关于西藏人文地理历史的书籍,可见,他对西藏的痴迷,这种痴迷进一步强化了海子对西藏的精神归属意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海子对于长期生活之地——昌平的疏离之感。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海子精神上的流浪,一方面海子选择了诗歌理想,选择了独自一人前行的远方,注定了他在诗歌道路上的流浪。另一方面出于对现实的逃避,海子最终走向自我放逐式的流浪与逃亡。前文已提及海子在城市生活的流浪之感,乡村出身的他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身居偏远的昌平,缺少交流的孤独令海子痛苦,一度带给他幸福的爱情体验也因物质的贫穷而中途夭折,置身于双重压迫的漩涡之中,海子以诗歌之名进行反抗,“城市破碎/流浪的国王/我为你歌唱”(《黎明和黄昏——两次嫁妆,两位姐妹》)。面对生存的压力与物质的“凶相毕露”,海子“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选择永恒的事业”(《祖国(或以梦为马)》)。“远方”代表着海子渴望企及的诗歌理想,他反复在诗歌中吟咏远方:“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奔向远方,你去而不返,是哪辆马车”(《夜晚亲爱的朋友》),海子认定“遥远的路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月全食》),然而他却一再提及“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地方”(《龙》)。诗人内心的矛盾已然显露无疑,然而即便一无所有,他仍然选择坚定地走向远方,坚持自己的诗歌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海子对远方的无限憧憬,恰恰显示出他对现实的忽视,乃至逃避。海子说:“那时我在远方/那时我自由而贫穷”(《远方》)。在海子短暂的一生中,贫穷一直如影随形,海子成长的“高河地区过去一直很穷”,农家孩子都要帮家里干活挣工分,海子从小亦是如此。上中学后海子住校,买不起食堂饭票的的他只好“从家里背着粮到学校食堂入伙,吃杂粮、就家里带去的腌咸菜”,周末回家照例干农活。海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他微薄的工资需要垫付家里的种子、化肥钱,还要资助三个弟弟上学,再加上海子喜欢购买书籍,种种开销之外工资所剩无几,可以说海子的生活是十分拮据的。贫穷的家境导致初恋的失败,贫穷的生活亦是现实的状况。当海子说“我在远方”“我自由而贫穷”时,对贫穷的指认仿佛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不论在远方抑或在现实中,贫穷都一直存在,然而海子认为只有在远方时,“我”才是自由的,海子所需要的自由,其实更像是对贫穷乃至现实的逃避。
流浪情怀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是拒绝坠入庸常现实、反抗现实,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逃避现实的倾向。在海子这里,现实更像是他心底无法触碰的伤疤,所以他要远离贫穷的现状,远离周遭的现实生活。不论是出门远旅,还是精神遨游,他渴望摆脱现实对自己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海子在诗歌道路上独自前行,在西藏等地独自行走,与此同时,独自一人的行走或流浪所带来孤独感与悲壮感,也使海子获得了“人生的快感”,或者说使他“领略到了人生的快意”[1]269。这种快感在海子诗歌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飞翔”。“飞翔”“飞”等语词在海子诗中十分常见,“飞翔”既是一种惬意的幻想,又蕴藉着理想与远方的意味,如“野鸽子打开你的翅膀/飞往何方?在永久之中/你将飞往何方?!/野鸽子是我的姓名”(《野鸽子》)。海子将自己比作野鸽子,十分有心地与豢养的家鸽作了明显的区别。可见海子不止满足于飞翔,更渴望自由地飞翔,飞向远方。所以他说“远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站立的地方”(《遥远的路程》。换言之,“我”就是远方,在今天看来,远方确实已经成为海子的标志之一,而海子无疑也成为象征理想与远方的代表性人物。
二
尽管流浪对海子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但当他远离家乡独自一人,面对陌生而冰冷的城市时,海子又一次次想起故乡。故乡是海子内心的牵挂与寄托,他对故乡的书写既有着对故乡土地的依恋,更饱含着对母亲的殷殷思念。“母亲”总是出现在海子的故乡书写中,如“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妈妈的屋顶/明天早上/霞光万道/我要看到你/妈妈,妈妈/你面朝谷仓/脚踩黄昏/我知道你日见衰老”(《给母亲(组诗)》),“村庄里住着/母亲和儿子/儿子静静地长大/母亲静静地注视”(《村庄》),等等。在外漂泊的海子想起家乡,便想起“日渐衰老”的母亲,想起母亲也在“想我”,想起母亲“面朝谷仓”,“脚踩黄昏”,还在为生计忙碌。海子的心情十分复杂,正是这份真挚而复杂的情感,使得海子对故乡的书写既饱含深情,又富有深度。
海子将满含回忆与思念的脉脉温情融入到诗歌之中,在诗歌中呈现出以麦子、土地、村庄等意象构成的乡村图景,如“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寥寥数语,海子在家乡田野间的安然与惬意跃然纸上,像一幅静止的画,海子既是画家亦是画中人。在海子眼里故乡是美好的,“故乡晴空万里/故乡白云片片/故乡水声汨汨”(《春天(断片)》),“故乡的星和羊群/像一支支白色美丽的流水”(《我,以及其他的证人》),“故乡,一个姓名/一句/美丽的诗行/故乡的夜晚醉倒在地”(《诗人叶赛宁(组诗)》),故乡是“最靠近荣光的地方”(《河流》)。故乡是血缘亲情的所在,“是叔叔和弟弟的故乡/是妻子和妹妹的故乡”(《传说》),故乡也是生命终结的归宿:“在危险的原野上/落下尸体的地方/那就是家乡。”落叶归根被海子视为理所应当,当他写下“我的自由的尸体在山上将我遮盖 放出花朵的/羞涩香味”(《在家乡》)。“自由”一词凸显了海子对死亡的向往,可以说海子视死如归,然而只有回到故乡的“山上”,我的“自由的尸体”将“我”遮盖,肉体与灵魂相结合,那时才完成了真正的“归”。
海子在乡村生活了15年,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经验使海子对乡村持有一种本能的亲昵,故乡的记忆萦绕在心头,诉诸笔端自然得心应手,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15年”[6]11,尽管过早离去的海子并未能实现自己当年的诺言,但他对故乡、乡村饱含深情的诗意书写无疑是成功的,是独属于海子的诗性创造。海子执着于关注生命存在本身,对故乡的深厚情感与深刻体察使他对乡村的书写深入到乡村生活的本质,散发出泥土的气息与生命力。如《活在珍贵的人间》一诗,诗人刻画幸福的感觉时写道:“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脚踩在青草上的愉悦触感将海子与土地合为一体,他甚至愿意成为地上的“黑土块”,而这“黑土块”在他看来是“彻底干净”的。如果没有对土地的真挚情感,如果不是从小赤脚奔跑在田野之上,不可能写出这样自然动人的句子。又如《日光》一诗:“梨花/在土墙上滑动/牛铎声声/大婶拉过两位小堂弟/站在我面前/像两截黑炭/日光其实很强/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乡村的生活经验渗透文本,全诗散发出强劲的生命张力,既源自太阳,也同属于土地,既生机勃勃,又暗藏苦难与艰辛,这种复杂与包容正是土地的本质。乡村在海子笔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宁静与美好,海子不曾忘记乡村的苦难与贫穷:“至今故乡仍在有水的地方生长/在苦难的枝叶间生长”(《但是水、水》),“村庄中痛苦女神安然入睡”(《秋日想起春天的痛苦也想起雷锋》),“我们在愤怒的河谷滋生的欲望/围着夕阳下建设简陋的家乡”(《你和桃花》),甚至在想起母亲时,乡村生活的苦难记忆竟与现实的生存困境纠缠在一起:“远方寂寞的母亲/也只有依靠我这/负伤的身体”(《春天(断片)》),“周围是坐落山下的庄稼/双手纺着城市和病痛/母亲很重,负在我身上”(《太阳·土地篇》)。
海子对故乡的眷恋还表现为强烈的还乡冲动,他多次在诗中流露出返回故乡的愿望。海子的还乡冲动一方面缘于渴望“回家”的本能。在外漂泊时诗人渴望回家,“神秘的流浪国王/在夜色中回到故乡”(《黎明和黄昏——两次嫁妆、两位姐妹》),出门远旅时亦期盼归家。前文提及1986年的暑假海子远游至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在《北斗七星七座村庄——献给萍水相逢的额济纳姑娘》一诗中海子写到:“还有十天我就要结束漂泊的生涯/回到五谷丰盛的村庄废弃果园的村庄。”“还有十天”表明对归期的计算,可见诗人对“回到五谷丰盛的村庄”的期待。在《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中,海子再次以死亡想象表达回家的强烈愿望:“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又如“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守望平静家园”。回归家园的倾向在海子的诗中比比皆是,不论是精神还是肉体,海子都渴望重返故乡,渴望再次亲近熟悉的乡村与土地。
海子出身农村,他的还乡意识中还包含着对乡村强烈的归属感。“我本是农家子弟/我本该成为迷雾退去的河岸上/年轻的乡村教师……但为什么/我来到了酒馆/和城市……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我要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诗人叶赛宁(组诗)》)。海子时刻表明自己的“乡村”身份,一如沈从文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乡村是二人共同的出身和情感认同,但他们都已身居都市,“知识分子”相较于“乡下人”更能指认他们的文化身份,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当初的乡村世界。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发现二者文本中的精神还乡倾向以及对城市文明的拒斥态度。囿于现实的工作需要以及对诗歌理想的追寻,海子意识到到自己其实不可能重返乡村,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正在发生变化,故乡已经不再是海子所熟悉的模样。1989年初海子回到安徽老家,然而“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他说:“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6]1160记忆中的小山村已经改变,而诗人自己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农家少年,于故乡而言他亦成为了一个“陌生人”,乡村其实已经成为“回不去的故乡”,这对海子的情感冲击可想而知。“一滴无名的泪水/在乡村长大的泪水/飞在乡村的黑夜”(《一滴水中的黑夜》),乡村只剩无边无际的黑夜,诗人的悲伤化为“一滴无名的泪水”,此时海子仍在强调这是“在乡村长大的泪水”,可见海子对乡村的归属感,对土地的深情厚谊。可是乡村的改变令他再也无法感受到如从前回到故乡时的舒适与惬意,海子曾在《村庄》一诗中写道:“村庄,在五谷丰盛的村庄,我安顿下来/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所谓“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未尝不是意味着回到家乡精神的充实感与满足感,与之相比,物质的重要性则被淡化。然而面对乡村的变化,曾经舒适的感觉不再,海子伤感于心,曾经充满快感的“飞翔”意象在这里也意外地呈现出一种空空荡荡的失落感。
三
故乡成为回不去的家园,海子试图依靠诗歌的力量完成精神上的还乡。故乡、乡村已经根植于海子的记忆深处,成为其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乡村既是海子抒情的来源,亦是海子抒情的对象,海子以真挚的情感、天才般的创造力将乡村的美好与苦难一一呈现。在海子的抒情诗中常带有一种农耕庆典的意味,不论是植物庄稼、还是天空河流,均带有古老的农业文明气息,与其说乡村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成为诗人抒情的背景,不如说它们是海子笔下烘托诗意氛围的独特意象。如《新娘》一诗中“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和以后许许多多日子/许许多多告别/被你照耀”。“小木屋”“筷子”“清水”等意象来自海子的故乡记忆,经过海子的提炼与组合,呈现出一种干净、纯粹的美好与瓷质的温暖。“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树上”“地下”等语词散发出清新的乡土气息,“新娘”幸福的生活即将开花结果,朴实无华的乡土岁月正悄然展开,全诗透着一股淡淡的诗意之美。
随着海子抒情的深入,诗人由田园风光进入对生命存在的追问。村庄、河流、土地、麦子等意象逐渐跃出乡土主题的统辖范围延展成为海子诗歌的基本元素,可以说“民间资源的滋养下所呈现出来的乡土性和本原性”[7]是海子诗歌创作的独特成就所在。有学者认为海子把故乡“心象化”了,即“海子诗中故土情结在表述上带着很大的虚拟性”[8]38,故乡的一事一物已非具体的实指,更多是一种“心象”,一种情绪,尤其是海子诗中不时弥漫的悲伤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乡村、土地的深切体验在诗意转换的过程中,血缘性的、乡村生活中的痛苦感觉不自觉地渗透进入文本,甚至成为抒情的主基调。如“村庄啊,我悲欢离合的小河”(《传说》),“天鹅像我黑色的头发在湖水中燃烧/我要把你接进我的家乡/有两位天使放声悲歌/痛苦地拥抱在家乡屋顶上”(《四行诗》)。家乡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悲伤情绪的寄托,在《泪水》一诗中也同样如此:“在十月的最后一夜/穷孩子夜里提灯还家泪流满面/一切死于中途在远离故乡的小镇上/在十月的最后一夜。”
乡村在海子的诗中已经超越了真实的乡村,更多呈现为一种想象性的建构,如“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麦地与诗人》)。麦地已经不仅仅是现实的土地,更被诗人赋予了一种精神内涵,“融合了生命的苦痛、对贫乏的意识和一种信仰冲动”[9]123。麦地作为“神秘的质问者”,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是“在本体上神圣化了”[4]71,因而海子笔下的麦地或土地常带有神性色彩。在《五月的麦地》中,“麦地”更成为承载诗歌精神的理想家园,“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此外,海子以乡村作为出发点将视野扩展至整片土地,深入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内核,他想“触到真正的粗糙的土地”[6]1017,探寻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可以说,海子心中的故乡是原始的——“原始的淳朴、原始的生命力、原始的宁静与原始的艰辛”[8]40,海子对原始的自发性向往始于对故乡、土地的追问与思考,在他看来生命、土地、河流、故乡是一体的,但他由景色进入生命,“将自然和生命融入诗歌”[6]1072,显然海子对故乡、乡村的书写已经跳出了传统的“乡愁”情结,逐步深入生命诗学的探索。
海子对乡村、土地的想象性建构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大地乌托邦,暗含着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的意味,这也是海子还乡意识的最终指向。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这样写道:“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可见我们丧失了多少东西。”[6]1038海子将物质文明、现代文明置于土地、精神的对立面,对于土地的丧失,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的海子深有体会。他深刻地洞察到现代人“漂泊无依的灵魂”,这是一种精神的无家可归状态,当“我们”面对欲望的侵袭,“我们”所“丧失”的东西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了出来。在《太阳·土地篇》中他亦写下了这样的题记:“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代替他吗?”海子使用“他”而非“它”,可见海子并非将土地视为纯然的物,而是赋予了更多的灵性与内涵。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也意味着失去了赖以依附的精神归属,欲望与精神、理性共同构成了人的三大属性,三者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彼此平衡而对立。如果象征着精神的“土地死去了”,欲望显然是不能够替代他的,这是海子的提问中明显表露出的价值取向。海子有感于乡村的改变,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他的精神还乡轨迹逐渐从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心灵寄托发展至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
面对土地的丧失,海子感到一种强烈的精神危机:“现代人一只焦黄的老虎/我们已经丧失了土地/替代土地的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肤浅的积木玩具般的欲望”(《太阳·土地篇》)。在海子那里,土地其实是一种精神性的隐喻:“远去的、被遗弃的土地,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上的被放逐、飘泊不定;土地的‘饥饿’,也是人们精神上的饥渴、焦虑、流离失所;土地的悲剧,折射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痛失‘精神家园’、无可依傍的悲惨处境。”[10]在《太阳·土地篇》中海子多次提到“饥饿”,其中第四章名为《饥饿仪式在本世纪》,开篇第一句“饥饿是上帝脱落的羊毛”喻示着“上帝死了”,人类的精神陷入迷惘之中。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海德格尔指出尼采出于对形而上学的反动,把超感性的世界完全否认,而“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即“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11],这种贫困并非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精神的缺失,它处于一种双重的匮乏之中,即“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来的神之尚未中”[12]。对西方世界而言,精神与信仰的危机恰恰就如同这“世界的黑夜”,显然,海子也注意到了上帝/神的缺席,他说“诸神疲乏而颓丧”“诸神之夜何其黑暗啊”,而最具隐喻性的莫过于第九章《家园》中“神祇从四方而来往八方而去/经过这座村庄后杳无音信”,而“这座村庄”正是“中国的村庄”,在这座中国的村庄中,自从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后,神就被悬置起来,“汉语世界是一个‘天地人’的三维世界,在此,没有神的容身之地。”[13]一方面,海子意识到传统文化中神/神性的匮乏,另一方面,被其赋予“神性”与“灵性”的土地渐渐失去生命力,“故乡阴郁而瘟疫的粘土堆砌王座”“土地故乡景色中那个肮脏的天使”。海子甚至疑惑地问道:“大地啊伴随着你的毁灭/我们的酒杯举向哪里?/我们的脚举向哪里?”(《太阳·土地篇》)海子的精神危机意识就是在这样一种双重匮乏的背景中产生,但他毅然决然地背负起寻找精神家园的重任,“把一种灵魂的乡愁和信仰冲动带入了一个贫乏时代的诗与言中”[9]128,海子的这种义无反顾,甚至具有了某种精神突围的意义。
海子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中引用了荷尔德林的《面包与美酒》一诗:“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荷尔德林的还乡也令海子产生了共鸣,“我也要这样回到生长我的土地/倘使怀中的财货多得和痛苦一样”。海子说:“看着荷尔德林的诗,我内心的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沙漠,开始有清泉涌出。”[6]1069面对神的缺席,土地的“饥饿”,精神的的缺失,海子的内心不可避免地感到迷茫,但荷尔德林启发了他,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诗人之天职》一诗中提炼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这一命题,海子正是以诗歌返回故乡,返回“诗意栖居”的场所,重新寻找精神和灵魂的归属。“故乡领着饥饿仿佛一只羔羊/酷律:刻在羊皮上我是诗歌/是为了远方的真情?而盲目上路”,“盲目上路”多多少少流露出一丝悲壮的情绪。在海子的诗歌中常有一种牺牲意味的悲壮感与崇高感,这与他追求伟大的诗歌、伟大的诗歌精神是一致的。海子意识到“过去的诗歌是永久的炊烟升起在亲切的泥土上/如今的诗歌是饥饿的节奏”,所以他更要承担起贫困时代诗人的职责,以诗歌的力量重新寻获此在的意义,“众神的黄昏他大概也梦见了我/盲目的荷马你是否依然在呼唤着我/呼唤着一篇诗歌歌颂并葬送土地/呼唤着一只盛满诗歌的敏锐的角”。可以说,海子的诗歌返乡之路是十分艰辛的,“回返的道路水波粼粼/有一次大地泪水蒙蒙”,但他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冲动:“黄昏不会从你开始也不会到我结束/半是希望半是恐惧面临覆灭的大地众神请注目/荷马在前在他后面我也盲目紧跟着那盲目的荷马”(《太阳·土地篇》)。希望与恐惧掺半,但海子并未却步,他甚至提出让“面临覆灭的大地众神注目”,海子的这种信念与勇气,既是对诗歌力量的坚信,更是对理想主义的坚持。
荷马与荷尔德林其实都是海子的精神导师,是海子在迷茫和黑夜中独自行走的精神指引和支撑。盲目在这里也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我们睁开眼睛——其实是险入失明状态。原生的生命涌动蜕化为文明形式和文明类型。我们开始抱住外壳。拼命地镌刻诗歌——而内心明亮外壳盲目的荷马只好抱琴远去。荷马——你何日能归?!”[6]1039与其说海子呼唤荷马的归来,不如说海子是在表明自己追随荷马的决心,要祛除现代文明的遮蔽,重新返回生命本源,正像他所说“荷马在前在他后面我也盲目”,但内心因为有着对精神家园的追求而充满光明。海子的还乡意味着重返生命本源,重新抵达生命的本真状态,这也是海子本能地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出发点,即为了保持生命的本真状态,“竭力保持生命的灵性、丰盈与淳朴状态”[4]194。尽管海子的内心充满希冀,但他的大地乌托邦最终却只能走向幻灭,他悲哀地感叹“故乡和家园是我们唯一的病不治之症啊”,故乡、家园的不在,他只能继续上路,寄希望于更遥远的远方,“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家乡”(《太阳·土地篇》)。前文提及海子曾有过两次西藏之行。对海子而言,西藏逐渐成为那个可以寄托心灵的“远方”,成为不同于査湾的第二故乡。然而“远方”与“故乡”的并置实际上是矛盾而背离的,当海子自我安慰般地说出“我是在我自己的故乡/在我自己的远方”时,他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悲凉。“如果我中止诉说,把我自己的故乡抛在一边/我连自己都放弃,更不会/回到秋收农民的家中温暖而贫困/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地回到荒凉/赶上最后一次/我戴上麦秸,安静地死亡/这一次不是葬在山头故乡的乱坟岗”(《太阳·大札撒》)。海子曾多次以死亡意象表达还乡的强烈愿望,在他看来故乡是生命的归宿,然而这一次“安静”的“死亡”,却并“不是葬在山头故乡的乱坟岗”,这显然暗示着故乡的虚无性抑或“不存在”。海子内心的荒凉由此可见,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如果”,事实上尽管海子意识到还乡的不可能,故乡的不存在,但他始终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路上不曾停歇。或许海子的努力是徒劳的,或许他对家园的寻找只能证明家园的不存在,但他的尝试与坚持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支点,能带给那些漂泊无依的灵魂些许慰藉。
身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海子对流浪有着一种天然的青睐,他曾多次在暑期独自出门远游,其中包括两次西藏之行,这些远游带给海子诗歌创作的灵感,其中不少佳作的产生均与出门远旅相关,因此他把这种流浪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海子更是自觉地选择了在追寻诗歌理想道路上的流浪。然而独自在城市漂泊的流浪却令海子萌生了还乡的愿望,他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渴望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乡村,于是他以诗歌还乡,在诗歌中构建了一个想象性的乡村即大地乌托邦。海子的还乡意识中有着对乡村强烈的归属感,与乡村的血缘性联系使他深刻地感受到乡村、土地的变化,因而他的还乡意识中显然还包括“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一命题的指向,在贫乏时代诗人以诗歌返回“诗意栖居”的场所,重新寻找精神和灵魂的归宿。可以说,海子由寻找自己的心灵寄托出发最终指向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大地乌托邦的幻灭,海子对家园的寻找却指向家园的不存在,还乡的不可能恰恰意味着他注定处于流浪之中,看似矛盾的流浪与还乡倾向至此形成了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统一。但是,无论如何,海子追寻精神家园的努力,他对“‘远方’的信仰、质疑、嘲讽甚至那种饱含疲倦与忧伤的失败感,都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精神上‘永在漂浮状态’中的现代人”[14],或许海子在诗歌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与尝试趋于徒劳,但这一努力和尝试的过程却使其诗歌本身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