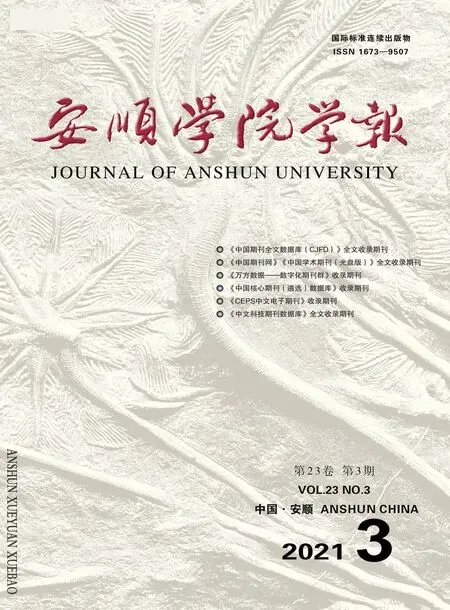从翻译伦理看《论语》英译
张小曼 闵 强
(1.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2.常州市第一中学,江苏 常州213003)
作为一种交际活动,翻译不仅是跨语言的沟通,更是跨文化的交流。20世纪90年代后期,翻译研究掀起了一场变革,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11。该转向推动译学研究走出语言学的藩篱,把视野投向更为宽广的文化领域。伦理研究是文化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此,翻译伦理得到翻译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伦理”这一观念是由法国学者贝尔曼(Antoine Berman)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2]26。此后,皮姆(Anthony Pym)提出,让翻译研究回归伦理学是“社会的总趋势之一”[3]129-138。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根据西方译界现有的理论研究,把翻译伦理划为四种相互重叠的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4]139-154,这对加强翻译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了西方学者,中国学者也非常关注伦理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就认为中国译学界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危机,坏译本的数量超过了好译本的数量,因此需要“加强翻译评论,加强监督”[5]25。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对翻译伦理愈发关注。孙致礼认为,为了把翻译事业推上新的台阶,我国翻译工作者应该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6]17。可见,伦理已经成为当今翻译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翻译伦理对翻译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英文中,“伦理”用来描述“支配或影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7]680,那么“翻译伦理”指的就是“支配或影响人类翻译行为的道德规范”[2][7]680。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不是仅局限于翻译行为主体的道德评判,如忠实等与译者专业责任相关的“译者道德”类的问题,而是涉及包括翻译目的、翻译规范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翻译在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这项战略任务中的作用自不待言,而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论语》迄今已有几十种英译本,其中理雅各(James Legge)译本和中国文化巨儒辜鸿铭译本影响深远。1861年,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出版[8]序12。该译本参考了《论语注疏》《四书改错》等中国儒学古注,内容详实,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辜鸿铭英译本于1898年出版,该译本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旁征博引西方名言警句,以帮助对儒家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读者了解古老的东方文明。该译本文笔流畅,通俗易懂,颇受西方读者青睐,流传甚广。因此,本文以翻译伦理为视角,从译者动机、责任履行和交际效果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理、辜二人的《论语》英译本,探求翻译伦理对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一、译者动机:决定翻译活动运行的伦理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的动机或目的是翻译活动的首要环节,它不仅确立翻译活动的产生,决定翻译文本的选择,甚至会影响到翻译过程的运行。德国学者威密尔(Hans Vermeer)认为“目的法则”是翻译活动应遵循的首要法则,翻译活动的目的决定了这一活动的过程[9]252。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动机也是对其所引发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依据。美国哲学家梯利(Frank Thilly)指出,“道德的标准就是它的目的和效果”[10]80。可以说,作为不同语言文本间的交流、沟通与转换,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有其动机。这种动机对翻译活动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指导作用。因此,衡量翻译动机的伦理性是从伦理层面审视整个翻译活动的必经之路。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动机去从事这一活动的?这种动机的伦理依据到底是什么?该伦理依据是否合情合理?这些问题不仅对后续的翻译过程发挥作用,而且还对译作的交际效果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从伦理层面对翻译动机进行审视,有助于衡量整个翻译行为的伦理性。
尽管理雅各的译本内容丰富而忠实,但是辜鸿铭却觉得这样的译文难以让读者满意,他甚至觉得理雅各虽然博学于中华古籍,但了解的却都是一些“死板的知识”[11]2。这些冗长的译文不免会让西方读者觉得“怪诞荒唐”。虽然辜鸿铭少年时代一直都是在西方度过,精于西学,但他归国后又研读经史,对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儒学思想甚为服膺,认为西方虽然船坚炮利,科技先进,但儒学思想中的精髓与其相比毫不逊色。儒家思想不仅不会随着国门的打开而逐步弱化消亡,反而会对全世界的文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弥此过耳”[12]13449。他认为孔子所倡导的“道”是“君子之道”。他曾对西方友人说,“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把“君子之道”与人类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13]43辜鸿铭一方面对儒学经典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又对理雅各学究式的译文感到不满,认为理雅各的译文影响了西方受众对《论语》的解读,难以传递真正的儒学精髓。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产生了翻译《论语》的念头,希望通过自己的译本,让“受过教育、有思想的英国人能在读完后更正他们对中国人固有的看法”,因为这样做除了可以“让英国人改变他们此前对中国人所产生的种种偏见,还能够从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改换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的看法”[11]6。不难看出,在那个神州大地饱受列强蹂躏,中华文明被西方人误解、嘲弄甚至是忽视的年代,辜鸿铭译介《论语》的动机既是为了向西人传播儒家文化,希望崇尚“枪炮”“武力”的欧洲人转化为“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也是为了增强中国的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帮助中国摆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局面。这种伦理动机与同一时代的林纾、严复等翻译大家为国民译介西方著作如出一辙,都是本着一种“救国”“益群”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不断被列强瓜分之际去履行译者文化交流的使命,其翻译动机具有一定的爱国精神和理想色彩。理、辜二人翻译动机的迥异体现了“中土伦理与政治结合,远西伦理与宗教结合”[14]83-89的特点。译者的伦理观与自身的文化背景、身份地位和时代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尽管理、辜二人的翻译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翻译动机皆有其伦理依据,都让两位译者选择《论语》作为实现其翻译目的的源语文本,并确定之后的翻译策略,可见译者动机的伦理依据在翻译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译者应以此为鉴,从伦理的角度来衡量自身的翻译动机,提升翻译活动的伦理性,取得更佳的翻译效果。
二、责任履行:考核译者职责行使的伦理规范
虽然理辜二人的翻译动机皆有其伦理依据,但这些伦理依据并不能作为衡量二人整个翻译活动伦理性的唯一标准。个体的行为动机与其随后的行为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即使译者的翻译动机有其道德依据,这些道德依据也无法证明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因此,翻译批评需考虑译者的个性与主观取向[15]5,而这些与译者的责任行使密切相关,译者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体现其专业个性,关系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完整履行了职责。作为翻译活动具体的实施人,译者肩负的责任极为重要,而忠实则是翻译工作者进行翻译活动的首要责任。切斯特曼把译者誓词归纳为九条,其中第四条就与译文的真实性有关,“我宣誓,本人会公证地再现源语文本”[4]139-154。该条誓言对应了他提出的“再现”伦理,即“准确地再现源文或作者的意图,不予以增添,不加以删减,不进行改变”[4]139-154。这一伦理并不要求译者生搬硬套,对原作进行逐字翻译,而是准确再现源文的核心思想,如泰特勒所说的“译文应当完全复制原作的思想”[16]129。由此可见,忠实是检验译者责任履行的标准之一,是衡量翻译活动的伦理规范。下文将以译者责任为伦理依据,从源文思想及内容两个方面对理、辜二人的译本进行分析。
例1: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17]61
理译: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 “Gifted with ability, and yet putting questions to those who were not so; possessed of much, and yet putting questions to those possessed of little; having, as though he had not; full, and yet counting himself as empty; offended against, and yet entering into no altercation: — formerly I had a friend who pursued this style of conduct.”[8]262
辜译: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Gifted himself, yet seeking to learn from the ungifted; possessing much information himself, yet seeking it from others possessing less; rich himself in the treasures of his mind, yet appearing as though he were poor; profound himself, yet appearing as though he were superficial: — I once had a friend who thus spent his life.”[11]162
对这段话的叙述者曾子,理雅各采用音意合译,即用“Tsang”体现其汉语读音,用“philosopher”反映其学识水平,与“子”这一古代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相呼应,以强化读者对曾子这一人物的了解。辜鸿铭则略去对“曾子”人名的翻译,将其简化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减少了普通西方读者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事实上,除了对子路、颜回等人采用音译法外,对孔子的其他学生,辜鸿铭均译为“孔门弟子”,以降低译文的陌生感。然而,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曾子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的“忠恕之道”便是从曾子口中提出。辜氏将其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人而省略不译,固然可以降低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读者的阅读难度,但客观上也造成了源文化信息的丢失,让其无法将此句与《论语》中曾子的其他言论联系起来。在对后文的翻译中,理雅各不仅都按照源文语序译出了曾子的原意,而且还在译文的注释中指出,曾子在这段话中提到的“吾友”应为颜渊[8]264,这既与我国历代注释者的理解一致[18]92,又增进了读者对源文以及文中人物的理解。但辜氏在译文中对“犯而不校”一语进行了省略,未曾译出。“犯而不校”指的是颜渊“纵被欺侮,也不计较”[18]92的高尚品德,但在神州大地备受列强欺辱的年代,许多有识之士并不赞同这一处世之道。梁启超曾指出,虽然“犯而不校”在古时值得推崇,但在此弱肉强食之时却不仅“不适于生存”,而且“更增其耻辱”[19]121。辜氏的翻译目的是为了更正西方人对中国的固有看法,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笔者猜测,可能由于“犯而不校”的意思与其翻译伦理观相违背,辜氏对其没有翻译。
例2: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17]146
理译:The viscount of Wei withdrew from the court.The viscount of Ke became a slave to Chow.Pe-kan remonstrated with him and died.Confucius said, “The Yin dynasty possessed these three men of virtue.”[8]659
辜译:At the time of the downfall of the Imperial Yin dynasty(the one preceding that under which Confucius lived) of the three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family, one left the country; one became a court jester; and one, who spoke the truth to the Emperor, was put to death.Confucius, remarking on the above, said, “The House of Yin in their last days had three men of moral character.”[11]406
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人是殷商的肱股之臣,在昏庸无道的纣王面前,微子选择辞官归隐,箕子和比干因仍有“亲属之恩”而“不忍去之”[20]714,一为奴,一死谏。虽然三人对君主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孔子认为他们都符合“仁”的标准。孔子这段话的背景是我国商周时期,在处理西方读者知之甚少的历史典故时,理雅各选择直译加注释法。首先,理氏对微子、箕子、比干和殷这些体现中国文化的专有词汇进行了音译,并按源文语序对译文进行了处理,反映了源文的原貌。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孔子的原意,理氏接着在注释中对背景知识进行了补充说明。他指出,“《微子》这一章(共十一节)对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辞官归隐的事迹表达了高度赞扬。同时这一章也纪念了孔子所处时代的那些名士,因为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这些名士选择辞官归去而非继续任职。这一章的主旨是证明孔子自身经历的合理性”[8]660,让读者认识到这一章的核心思想。随后,理雅各又在注释中对微子等人的生平进行了详细介绍,让读者对这段话的背景和语境有了深入的理解。与理译本相同,辜译本也对西方读者陌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详细阐述,比如辜氏在括号内对殷商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描述,即“孔子所处时代之前的那个朝代”。辜氏虽然没有将微子等人的姓名译出,但他在译文中对三人的事迹以及他们与商朝的关系做了说明,通过对这些增补内容的阅读,西方读者不难发现孔子称赞三人具备“仁”这一品质的原因。对于《论语》中涉及我国历史文化等背景知识的内容,理辜两位译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通过注释来增补信息的方法,对西方读者较为陌生的文化负载词作出解释,将译文放置在源文所提及的文化背景中,不仅如实地反映了源文的核心思想,也有助于增进读者对源文的理解。综上所述,从“责任履行”这一伦理要求分析,两位译者都努力以“忠实再现源文”为标准,理雅各对人物身份的介绍更加准确,更加详实,有利于目的语读者对人物细节的辨别与把握;辜鸿铭对人物身份的简单化处理虽然降低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但在文化信息上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可见,责任履行反映译者应尽义务的完成度,是考核译者职责行使的重要伦理规范。
三、交际效果:衡量译文交流功能的伦理标准
作为连接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译文能否实现预期的交际效果,也是衡量译文质量的重要伦理标准之一。切斯特曼在交际伦理中指出,对译者来说,通过译文实现交际目的,是首要的伦理行为[4]139-154。皮姆也指出,翻译的任务是帮助两种不同文化进行长期且稳定的合作[21]135-137。在这一伦理标准下,译文的交际效果成为衡量译文交流功能的伦理标准。下文将从文化异质性和译本接受性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文化异质性
文化异质性是指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气质,是体现文化交流必要性的内核,也是衡量译文交际效果的伦理标准之一。翻译活动因“异”而生,缺少它,翻译就会失去“必要性”[22]71。在译文中呈现与目的语文化不同的文化信息,不仅符合读者对译文的期待,也是翻译活动中不同文化的交际核心。
例3: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17]91
理译:Yen Yuan asked about perfect virtue.The Master said, “To subdue one’s-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is perfect virtue.”[8]395
辜译:A disciple of Confucius, the favourite Yen Hui, enquired what constituted a moral life.Confucius answered, “Renounce yourself and conform to the ideal of decency and good sense.”[11]248
“仁”和“礼”在《论语》中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同时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历代儒者所推崇的行为准则。如何将这些充满异质性的文化负载词准确地表达在译文中,是译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对于“仁”,理雅各将其译为“完美的德行”(perfect virtue),从道德层面阐释了“仁”的精神内涵。对于《论语》中其他章节出现的“仁”,理氏基本也采用“virtue”或其形容词“virtuous”进行解释。辜鸿铭认为“仁”与品行有关,用“道德”(moral)对其进行释义。朱熹也将“仁”解释为“本心之全德”[23]155,把个人内心中的“德”看作“仁”的本质。可见两位译者将“仁”与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与我国古代学者的看法具有一致性。对于“克己复礼”中的“礼”,理雅各将其解释为“礼仪”(propriety),辜鸿铭则将其解释为“拥有礼貌与理智的理想”(the ideal of decency and good sense)。有学者指出,“礼”在儒家思想中有三层含义,除了理辜二人译出的“礼节”“礼貌”外,还可用来表示社会等级制度(如尊卑贵贱之礼)与各种仪式(如婚丧嫁娶之礼)的礼仪[24]127,可见“礼”这一充满儒学特色的词汇含义之丰富。事实上,体现《论语》中核心思想的概念词往往一词多义,辐射范围较广,译者在翻译时难免会出现语义空缺,顾此失彼,难以完全转达原作的意图。从文化异质性的角度分析,理译本和辜译本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我国独有的儒学思想,这对其他中华典籍英译,特别是涉及多元含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译本接受性
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无疑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读者对译文接受性的程度,决定了译文传播性、流通性和交际性的高低。林语堂认为,译者一方面需对原作负责,另一方面还需对读者负责[25]502。这就要求译者除了要在目的语中尽可能保持原著的风姿,达到忠实可信的标准,还要求译员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习俗,实现为读者服务的目标。如果译文因为晦涩难懂而失去了读者群,那么翻译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为读者服务”这一伦理不仅要求译文的语言流畅易懂,还要求译文的内容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伦理规范。
例4: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7]85
理译:When Yen Yuan died, the Master said, “Alas! Heaven is destroying me! Heaven is destroying me!”[8]359
辜译:When Confucius first heard the news of the death of his disciple, the favourite Yen Hui, he cried out in an outburst of grief, “Oh! Oh! God has forsaken me! God has forsaken me!”[11]226
理译在句式上紧贴源文,而辜译为了突出孔子对颜回逝世的悲哀,不仅补充说明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还加入了对孔子悲恸时的描写,加深了文章的渲染气氛,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对于“天”这个具有多种语义的汉字,理雅各将其译为“heaven”,虽然译出了天空的意思,但“天”蕴涵的其他意义,如上苍、神明等却没有表达出来。辜译则对“天”进行了引申,将其译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的“上帝”。辜氏此举是为了方便西方读者阅读,用目的语读者耳熟能详的词汇去覆盖源语文本中陌生的信息。韦努蒂认为,归化和异化不仅反映了译者对于外语源文或外语文化所持的伦理态度,还体现了译者运用某些翻译策略后引起的伦理效果[26]210。理氏为了凸显源语的异质性,采用了异化翻译,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而辜氏为了顺应目标语文化,采取了归化翻译,使文章通俗、流畅、易懂。可以说,辜氏的译文虽然在忠实度上略逊于理译本,但却更容易为西方读者所阅读和理解,他的归化策略显然是出于为目的语读者服务的伦理。除了将“天”译为God外,辜译还尽可能地引用西方的文化和名言警句来解释中国特有的文化,如2.23节中对“夏”“商”这两个朝代,辜译不仅在注释中给出了两个朝代的具体年代,还将其比喻成东方的古希腊与古罗马[14]43,以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为依托,拉近读者与源文的距离。
儒莲奖以法籍犹太汉学家儒莲的名义命名,被称为西方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儒莲生前对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推崇备至, 而理雅各则于1875年成为该奖的首位得主,足见理氏译本在西方的影响力[27]38。相对而言,辜氏的译本也不遑多让。据《清史稿》记载,西方人在读完辜鸿铭的译文之后,“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12]13449。林语堂认为辜鸿铭的译文不仅忠实,而且颇有创造性,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名“电镀匠”[28]61。由此可见,理辜两位译者的译本均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交际效果。
四、理雅各《论语》翻译伦理给典籍英译带来的启示
1934年,鲁迅先生写下《拿来主义》一文,主张有选择地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以为国人所用。从那时起,我国从西方译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以供国人学习。这些作品种类繁多,涉及科技、文学、法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它们不仅为我国奋起直追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中华文化的凤凰涅槃创造了精神养料。但是,在翻译西方著作的同时,我国对外译介自身优秀文化的活动却显得极为单薄。季羡林先生曾经提出,在“拿来”的同时还要“送去”,并且要“送之有术”[5]141。
那么,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如何做到“送之有术”呢?笔者认为,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因素依旧是不容忽视的要素之一。翻译的伦理动机、译者的责任履行和译文的交际效果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考核标准。它们分别对应译介目的、译介内容和译介效果。首先,从译介目的来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这规定了译者总体的翻译动机,即向全球传递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价值观。因此,在译介中国优秀文化的过程中,译者必须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它不仅包括物质回报,更包含一种伦理责任,即通过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来打破西方世界的文化垄断,粉碎西方污蔑中国的论调,树立中国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地位,提高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积极影响,推动中西文化间的优势互补,促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明确伦理动机后,译者就会对译介内容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在选择译介文本时,译者不仅要筛选中华文化中的精髓,还需剔除一些与现代文明不相符合的糟粕。在此基础上,忠实地传达源文的内容,为外国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他们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以及中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为达到这一译介效果,译者需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
例5: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7]35
理译:The Master said, “If the son for three years does not alte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8]125
辜译:Confucius remarked, “A son who for three years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does not, in his own life, change his father’s principles,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son.”[11]76
在儒家思想中,“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深深影响了国人数千年,早已标上了浓浓的中国烙印。相比之下,西方人对于“孝”这一伦理观念却没有那么深刻地关注。理雅各采用与源文语义较为接近的“孝道”[8]41-45来处理,以传播中国的孝道文化;辜鸿铭则进行了简化处理,把“孝顺的”译为“好的”。在《为政》篇第5至第8节与“孝”有关的句子里,辜译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法,把“孝”译为“作为好儿子的责任”[11]26-28。虽然辜译实现了为目的语读者服务的伦理初衷,方便了读者阅读,但这不免会降低读者、特别是现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理解。笔者认为,尽管理译本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但译文中浩如烟海的注释可以为读者提供不可多得的背景知识和文本信息。这种注释法,也是出于为读者服务的伦理目的。理雅各曾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读者愿意阅读他的注释,他也会继续把注释写下去[27]40。虽然这些注疏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但与辜译的简化法相比,它们的确会加深读者对源文的理解。如在11.8节中,颜路请求孔子把自己的马车卖掉为颜渊置办棺椁。虽然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孔子仍然以自己曾做过大夫所以不能步行为由拒绝了颜路。辜氏的译本未加注释直接译出,这样难免会让读者觉得孔子有些不近人情,甚至是冷血,与之前孔子仁厚的形象有所出入。对此,理译本则在注疏中作出了解释。理雅各将其解释为孔子仍在朝廷为官,若政事紧急则需用马车赶路参与政事,故而无法变卖马车,为读者理解孔子的这一不合情理的举动提供了参考,维持了孔子在读者心目中“仁”的形象,产生了更好的译介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辜氏译本获得了当时西方读者的青睐,取得了良好的交际效果,但在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今天,异化的翻译策略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交流效果。韦努蒂认为,异化是反抗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不平等价值观的一种手段[26]208。如果采用归化翻译,顺应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将会无法达到打破西方文化垄断霸权的目的。因此,在译介中华优秀文化作品,特别是传统经典时,采取异化翻译加注释的方法可能会产生较好的沟通效果。理雅各的长篇注释不仅促进了西方读者对《论语》源文的理解,也为他们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详细的参考,理译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源文的精髓,也取得了极佳的交际效果。笔者认为理氏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对我国向国外译介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经典,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借鉴汉学家的翻译策略,甚至还可以与他们合作,共同译介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大中华文库》收录的《论语》译本便是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通过东西方译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优势互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会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