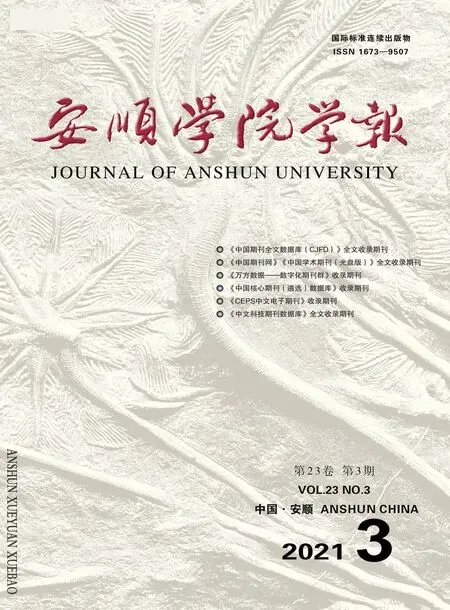清末民初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原因探析
宋可平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间文献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550025)
学者探讨民间借贷原因时,多认为是土地的贫乏、生产力的落后、天灾人祸的破坏以及婚丧陋习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李金铮认为贫困是农民负债之源,民间借贷的产生主要是土地缺乏、家庭副业的艰难生存、商业资本的剥削以及婚丧陋习等因素。[1]俞如先认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捐税、天灾动乱、嗜赌等原因。[2]安尊华以天柱高酿镇木杉村为例,指出生产、家庭收支不平衡以及天灾人祸是借贷的一般原因。[3]陈铮认为其原因除了贫困化以外,村寨的传统宗族活动支出、民众的生活陋习也是借贷原因之一。[4]丁强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借贷原因主要为经济原因、赋税滥征、战争与匪祸、陋俗赌风吸毒。[5]本文将立足于清水江民间借贷实际,探究出清水江苗侗地区民间借贷的原因。
一、生活消费性借贷
清末至民初的贵州仍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土地占有量少,“绝大多数的好田好土,都掌握在封建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大商人、天主教堂、寺庙以及土司等人手中,这些人用霸占、侵吞、插签、高利贷、低价购买等方式,侵占各族农民的田土与山林”[6]。清水江流域同样也不例外,这就加剧了农民的贫困,使得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同时农民赋役繁重。民国时期田赋主要以地丁和秋粮为主,地处清水江流域锦屏县的一份政府公文便可窥见一斑:“但本县丁粮,科则复杂。如原粮一项,每石由一两增至十两零六钱一分,其余类皆一科数则,因地各异,廒册既无记载,征收何所适从……不料空前洪水为灾,沿溪附河之田园屋宇,漂流殆尽,灾黎哀嗷,不忍闻见……。”[7]从中可以看出清水江流域赋税的沉重。一般来说,民间借贷形式大致为两种,即实物借贷和货币借贷。实物借贷主要以稻米等粮食为主,货币借贷主要以铜元、银元、法币等,如《彭普求立典田字》:
立典田字人本村彭普求,为因家下缺少粮食,母子二人商议,自愿将到对门榜田一坵,约谷一挑,上抵典主之田,下抵普菱之田,左抵荒坪,右抵典主之田,要洋出典,先问亲房无洋承典,自己请中登门问到堂兄彭普亨名下存(承)典为业,当面凭中三面议定典价洋钞洋七十圆零八十亿正(整),其田限至三年价到归赎,其田至(自)典之后,任凭典主下田耕种收花管业,恐后无凭,立有典字为据是实。
凭中 彭仁章
代笔 彭泽润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立[8]398
本契中彭普求母子因缺少口粮,只得商议将产量为1挑的1坵田出典与堂兄彭普亨,其典当物为田,约定期限为三年,三年后拿银将田赎回,三年间由银主耕种收花。所谓“收花”主要是指该坵田所产的谷物由钱主所占有,虽然该典契并没有说明借谷利息问题,但我们认为三年该田所产谷物即洋钞的利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民借贷是出于维持生计,是迫不得已而产生的,可以想象农民生活的现状是如此凄惨,以至于连吃饭都成为最大的问题。当然除了实物借贷以外,还有货币借贷。如《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日吴恒锟借光洋字》:
立借光洋字人吴恒锟,以今手中空乏缺少用费,无处设发(法),亲□登门问到族嫂、族侄媳吴杨引弟、吴孙三妹婆媳二人各借光洋伍圆正(整),齐(其)洋当日交清,行息三回,月一圆,周年四圆正(整),不得短少,借主愿将祖业作抵,坐落地名堰头老秧地田一坵,有花二十箩,以水论上抵河,下抵大田,左抵河,右抵瓦厂田,四[抵]分明并无混杂,为有本息不归,钱主下田耘种收花作息,借主不得异言,此光洋不限远近相还,凭世市扣用,二边不得相亏,今口无凭,立有借字为证,洋到契回。
凭中 吴天才
代笔 吴从周
民国三十八年冬月中浣日吴恒锟请立[9]
在统计的五百多份借贷文书中,其中近450份借贷文书,其借贷原因常写作为“手中空乏”“无钱用度”“家下空乏,无钱用度”“手中拮据”等简洁性表述,我们一般都将其归类为生活消费型借贷。《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日吴恒锟借光洋字》订立时,中国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社会混乱,人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典主吴恒锟因家中无钱可用,只得向族嫂、族侄媳处分别借到光洋5元,利息为3分,将1坵收花12箩田作典,但是本契并没有规定赎回的期限,其中规定每月固定利息为1元,每年固定利息为4元,这在所统计的契约文书中属于比较少见的类型。在借贷契约文书中,除了上述将田作为抵押品之外,我们还发现有将菜园、耕牛、猪、房屋、油山等作抵,如《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罗克聪借谷子字》:
立借谷子字人罗克聪,今因家缺少日食用度,无从得处,亲自请中上门问到刘应田名下承借净谷六箩,自借之后,每年加五行息,不得短少,倘有拖欠短少本利无还,自愿将到己面之业,坐落地名冲沙坡之山土一幅作抵,其界上抵高岭,下抵田,左抵刘应辉之山,右抵刘应珍山为界,四抵分明并无混杂,任从刘姓砍伐与蓄收捡茶油、杉蜡、竹木等项,罗姓不得异言另生枝节走挡等情。恐口无凭,立借字一纸为据。
凭中 罗克元
刘应先
代笔 栗宏动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罗克聪立[10]123
本契中罗克聪因缺少口食而陷入生存窘境,只得从刘应田名下借谷6箩,以山土作抵,利息率为五行,即50%,每年需还利谷3箩,可见粮食借贷的利率通常较高于货币借贷,应属于高利贷。在赎回之前,由钱主砍伐、蓄木,以及茶油、杉树、竹木等一并由钱主占有,从侧面我们可以看出村民对粮食需求的迫切性,以至于村民不得不以较高的利率来借粮以维持生存。从以上三则借贷契约可以看出,晚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农民由于土地不足以及赋税的繁重,导致生活困难,入不敷出,以至于连口粮都得四处筹借。生活消费性借贷是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借贷。李金铮认为“乡村借贷主要是消费性借贷,是糊口借贷,是维持或消极性的贫困借贷”[11],虽然作者指的是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清水江流域亦然。
二、婚娶费用的支出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清水江流域地区,婚姻缔结过程一般包括提亲、订亲、接亲、坐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苗族聚居地区盛行姑舅表婚,也就是甥女嫁出之后,甥婿须给舅家一笔身价钱,通常是大洋4元4,最多5元5,少则3元3,甚至还要另交谷200斤,如苗族叙事诗《娥娇与金丹》这样唱到:“舅家的外甥钱呀/放在牛背上/牛背就要弯啊/放在马背上/马背就要断……谷仓装不下”[12]。可见舅家所要的“外甥钱”是十分惊人的,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在此过程中酒席、彩礼等的花费较多,但在婚事操办过程中的讲排场等婚事陋习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并时常导致负债及至破产。如《姜老甲立典田字》:
立典田字人姜老甲,为因前年亲事,缺少艮(银)用,欠到姜盛勇名下宝银一十三两二钱,无银归还,自愿将到先年得买姜克荣东牛大田一坵,约谷九旦(担),其田至典之后,任凭银主下田耕种,限至三年价到续(赎)回,不得有误,口说无凭,立此典田字为据。
凭中 姜登云
代笔 傅志怔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五日立[13]120
本契中姜老甲由于亲事欠下姜盛勇12两2钱宝银,只能将收谷九担的一坵田典当,典当期限为三年,三年期间由银主耕种收谷,利息为耕种所收获的产量。婚事中仅彩礼钱一项的花费就已经使农民不堪重负,多者一两百元,往往小康之家也无法承受。如《石正邦借字约》:
立借字约人石正邦,为因缺少财(彩)理(礼)银用,无出,自己愿将便老佃母田大小十坵,载禾五十把,今凭中作当与石长生名下,实借过色银五十六两四钱三分,连中人钱在内,其艮(银)限到开年三月之内一并交足,入(如)有不足,艮(银)主照当管业,二比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借字为据,日后准色艮(银)十两,余下钱禾交足。
石永望
石永贵
凭旦中 石声总
石宗贵
亲笔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立借[14]
本契中石正邦,因彩礼钱难以筹措,将收禾50把的10坵田作抵押,从石长生手中借得银56两4钱3分,利息为10两,可见典主用钱的迫切性,从中也可以看出典主为了筹到彩礼费用,不惜借高利贷,冒着可能面临田产收回无望的风险。
三、丧葬费用的支出
对于个体家庭来说,丧事办理的好坏,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生者的颜面。清水江流域地区苗族丧葬一般有吊丧、入殓、送葬等流程,“其丧事费用包括棺材、宰杀牲畜、饮食等全部,除贫雇农以外,一般都要花150—200元左右”[15]。可见,丧葬费用对于农民来讲可能是一辈子都难以偿还的债。如《民国二年四月初六日杨应江、杨应湖出典田契》:
立典田契字人杨应江、杨应湖,今因前岁伯父杨志林病故,手中空乏无钱用度,将到伯父得买之业,座(坐)落地名槁见坡黄家井田一坵,有花四箩,上抵莫姓坡,下抵李姓田,左抵李姓坡,右抵黄姓田,四抵分明并无混杂,要行出典,先问亲房人等无钱承领,后请中上门问到牛场河坝典与黄政春名下承典,三面言定典价一九大钱四千文整,其钱即日凭中亲手领清并无下欠分文。自典之后,邦(帮)差粮钱十六文整,其田任从钱主拔庄耕种,典主族内人等不得异言,日后不限远近赎取,钱到契回,恐口无凭,特立典字一纸为据。
若有抵当不清,典主上前理落,不与钱主相干。
内添花文字二颗。
凭中 李石林
亲笔立
民国癸丑年四月初六日杨应江、杨应湖立典[10]179
本契中杨应江、杨应湖因伯父去世,无钱进行打理,只得将1坵收花4箩的田作典,先问亲房人等无人承典,后问到黄政春承典,典价钱为4,000文,典主还应帮交差钱16文,值得注意的是本契没有固定的利息和赎取期限,这反映典主对利率的不敏感。只是简略的“日后不限远近”,即钱随到田随赎。笔者在整理借贷契约文书时,还发现有因做法事超度亡灵进而产生借贷的,巫师在法事中祭亡灵时,同时也祭山水龙脉,希望死者平安、家人清吉。如《彭仁清立典田字》:
立典田字人□仁清,为因追荐道场,缺少用费,无处得出,自愿将到九鲁所共之田二坵,约谷六担,上抵井边,下抵普开之园,左抵普儒坐屋,右抵坡,四至分明,其田分为二大股,普亨弟兄占一大股,本名占一大股,今将本名一大股出典与胞兄彭仁彬名下承典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言定典价元钱六十三千六两八十文,其钱当日亲手领正应用并不下欠分文,自典之后,任凭胞兄耕种收花管业,典主不得异言,其田不限远近,价到归赎,恐后无凭,立有典为据。
外批:其田赎转,日后以作祭祀之田
内添十颗字
凭中代笔 彭普云
民国十六年丁卯岁三月三十日立典[8]120
本契中典主因做法事缺少费用,只得将2坵收谷6担的田出典,但是该田分为两股,即两份,典主占一份即1坵田出典与胞兄彭仁彬,典价钱为63,000两80文,从中可见法事费用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在笔者统计的借贷契约文书中发现关于婚丧借贷仅有三十余份,但这并不能代表关于婚丧产生借贷的只是少数。据丁道谦先生的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农户平均每年支出为154.19元,婚嫁和丧葬支出为11.30元,占7.29%。[17]从中可以窥视婚姻和丧葬给农民产生的负担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
四、清还旧账需要
清水江流域是南方盛产木材的重要区域,自清雍正年间开辟苗疆以来,商人觊觎于木材丰厚利润,纷至沓来,络绎不绝,锦屏地区林业经济便应运而生,锦屏地区的木材贸易兴起于明,盛于清,锦屏地区的王寨、茅坪、卦治扼清水江下游,由于水流平稳,河面开阔,具有发展木材的天然优势,成为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集散地,随后形成了“三帮”“五勷(襄)”木商集团和诸如姚百万、姜志远这样财势大的山客。许多擎天巨木源源不断的通过清水江流向全国各地,使锦屏地区成为贵州为数不多的较为富庶的地区之一。一幅林业繁荣、舟楫穿梭的景象跃然纸上。在清水江文书中,多为山林买卖契约和山林租佃契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锦屏地区林业生产关系提供了鲜活资料。如《姜海珑立典田字》:
立典田字[人]姜海珑,为因扒洞生理折本无归,替众伙计还账,自愿将手勿田一坵,污扒田岭上三坵,冲三加一出典与姜东凤名下承典为业,当日凭中将账扣清,余本利文艮(纹银)八十二两七钱,将田作典,日后限三年之内价到赎回,恐口无凭,三年之外价随到随赎,立典田字为据。
外批:添三字涂三字
杨世英
凭中 姜卓英
光绪三年八月十二日这年东凤先收禾花亲笔立[13]350
本契中姜海珑因在扒洞经营木植中亏损而借银,需要说明的是契约中扒洞现属于锦屏县的启蒙镇,现改为华洞村。扒洞村清至民国时期林业资源丰富,人民素以林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替众伙计还账表明典主应是木商主,为替众伙计还账,将4坵田作典,将亏损额偿还后,剩余纹银82两7钱。可以看出木植生意投资成本大,个体户抗风险弱,因而亏损也较其他小生意如杂货业数额大,具有较大风险,对个体户来讲,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同时,经营木植生意可以弥补小生产的入不敷出,实现收入的多元化,进而抵消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笔者发现有些因欠账而借贷的只是简单地描述为“无处出钱还清”“生理要银还账”“要银还为明账”等。如《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唐李氏等出典田契》:
立典田契字人母唐李氏年妹、儿唐仕文母子,商议所该各处小账无处出钱还清,自愿将到主(祖)遗之业田,坐落地名甲马坪河边田大小三坵,有花十六箩,其田上抵杨姓田,下抵业祖(主)田,左抵张田,右抵河,四抵分明,要钱出典,亲自请中上门问到寨塘杨德芳名下承典为业,凭中议定铜元一百六十封文整,其铜元凭中亲手领足并无下欠分文,自典之后,任从钱主剥(拔)庄耕种,田主母子并无异言,若有洪水充(冲)崩打滥(烂)砂(沙)压,田主修捕(补),不光(关)钱主之事,限至三年未满,本到契回,今恐人心不佑(古),特立典字一纸为据。
美(每)年那(纳)粮钱三百五十文
凭中 杨普侯
杨心保 父子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立唐李氏儿唐仕文亲笔立典[18]
本契中唐李氏母子因欠账无法按时偿付,只好将收花13箩的3坵田作抵,借得铜元160封来偿付旧债。借新债还旧债,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缓解了资金紧张甚至促进了再生产,是积极的,但是旧债和新债的叠加,使得典主可能失去赎回被典土地的可能性,甚至面临着绝卖、断卖的风险。同时也不利于保持封建统治的稳固性和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不利于农村金融良性发展。显然属于一种无奈之举。
五、天灾人祸
清水江流域自然灾害频繁,有水灾、旱灾、风灾、倒春寒等,尤以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及林业贸易影响最大、破坏性最强。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仅使农业产量下降,甚至导致农田绝收,出现饿殍遍野,场景甚是悲惨,有些农民只能选择逃荒,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另外,清水江流域林业繁荣,若遇上洪水的话,对山客以及从事林业生意的木商也会造成重大损失,尤其是对于通过借贷来从事木植生意的商人更是雪上加霜。如《石光辉典田字约》:
立典田字约人岑胡寨石光辉,为因木植生理所借赀(资)本,奈命运不佳,还被水流,无处归还,自愿将土名套敲田一坵,载禾十六把,弟兄二股均分,本名占八把,请中出典与容嘴寨银主姜包九名下承典为业,当面凭中议定典价新宝纹银二十六两正(整),亲手领会应用,其田自典之后,任从银主上埂收禾花,不拘远近,典主发达,照价归赎,二比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此典字为据。
外批:每年帮禾五十斤
石芝佩
凭中 石和玉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六日亲笔立[19]
本契中石光辉通过借贷获得资金,并将资金投入林业经营,本可以将木材卖出后获取利润以偿还借债,不料遇到洪水将所购买的木材冲走,无钱可还,只好将收花16把的1坵田自己所占一股作抵,借得姜包九名下银两26两,典田由钱主耕种和收获粮食。除了自然灾害的不可抗之外,清朝末年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和赋税的繁重,加上战争不断以及匪患猖獗,使本就脆弱的农民更加是苦不堪言。总之,天灾人祸的不可预测性、破坏性为农民的又一借贷原因。
六、结论
清末民初,虽然农村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作为贵州经济支柱产业的农业经济远远未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基本上仍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的状态。[20]这种停滞和衰退直接表现为农业产量的下降以及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据《黎平县志》记载,清水江流域的黎平地区历史上经济形态主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沿河两岸少数村寨每年砍伐少量木材外销……(但到清末民初)苛捐杂税繁重,地租、高利盘剥,绝大多数侗族人民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21]在古代堪称富庶地的黎平地区尚且如此,清水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大抵都是生活维艰,在极端贫困化边缘徘徊。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从借贷目的来看,借贷既用于生产,也用于生活,主要是以生活为主,是一种维持性和消费性借贷,是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化的反映。从借贷原因来看,生活消费所产生的借贷虽然解决了生存需求问题,使农民免于忍饥挨饿,但也产生了农民极端贫困化的隐忧;婚娶、丧葬产生的借贷虽解决了燃眉之急,但金钱的大量耗费恶化了农民的经济状况;清欠旧账产生的借贷清偿了债务,但新债务的产生无异于饮鸩止渴,甚至成为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天灾人祸的破坏性不仅使农民财产和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使农民摆脱贫困的梦想成为幻影。总的来说,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具有一定剥削性和残酷性,甚至导致农业衰败、农村萧条、农民破产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产生。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官方借贷机制滞后、农民借贷无门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也在客观上对维持农民的家庭生活、促进简单再生产、降低借贷成本、活跃农村金融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