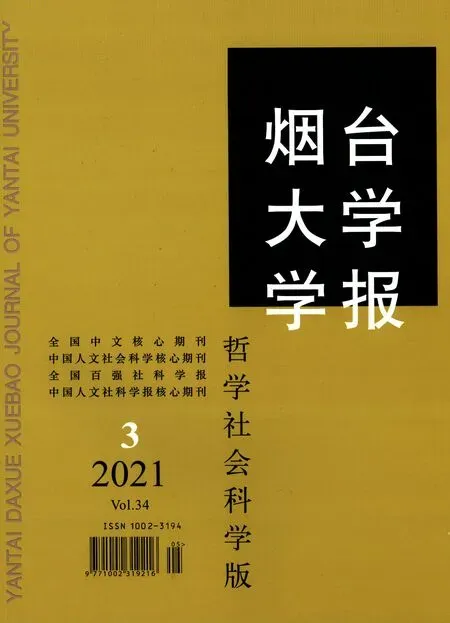王充文体意识的文学史价值
——以“论”体为中心
倪晓明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学界对王充的“论”体意识已有一定关注,李春青《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是其中代表 。(1)李春青:《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李氏将汉代“论”体的演变置于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多重维度之下予以观照,并对《论衡》的文体意识予以揭橥,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论证过程也体现出极强的逻辑思辨能力。或许是通论视角无法给《论衡》更多篇幅,(2)这是《论衡》的“文体研究”较为普遍的情况,专著如吕逸新:《汉代文体问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论文如杨东林:《汉代文体观念论略》,《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这些都是宏观视角下的讨论,总体上都对汉代文体研究有着重要贡献。其中虽然有涉及《论衡》“文体研究”的内容,但限于体例,未能进一步展开。有些问题未能展开。例如,王充自觉的文体意识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论衡》的文体特征是什么?王充文体意识的文学史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值得深入探索。鉴于此,笔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此作进一步分析。
一
文体意识指作家对其文体创作有着自觉的反思与认识。之所以用“文体意识”而不是“文体理论”,旨在强调作者的主体性。与“理论”相比,“意识”更具有自觉属性。王充《论衡》中的文体表述较为朴素,尽管论述相对集中,但并未达到“文体理论”层面,故本文以“文体意识”表述。在王充的视野中,“论”的意义首先在于“正俗”:
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对作》)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对作》)
在王充看来,“论”体之文“以觉失俗”“以讥世俗”,具有鲜明的正俗属性。实际上,汉代不乏关于“论”的表述,大多将“论”与参政议政的现实指向相挂钩。如《说文解字·言部》云:“论,议也。”《释名·释典艺》云:“论,伦也,有伦理也。”(3)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2页。郑玄曰:“论者伦也,可以经纶世务。”(4)王应麟辑:《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1204页。王充的意义在于他不仅认识到“论”体指涉现实政治特点,更将这一理念认识贯彻到创作实践。《对作》篇言: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人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
这段材料表明,一方面《论衡》以社会问题为立足点,以正俗为旨归;另一方面王充能够将其对“论”体的反思融入创作实践之中,在实践与观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论”体的意识。有学者指出,今日所谓《论衡》的文学思想,乃是王充社会与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5)张峰屹:《“气命”论基础上的王充文学思想》,《文学遗产》2020年第4期。这种观点可谓深得作者之心。《论衡》本是王充对社会现实与文化学术的思考合集,“论”体起到表达思想成果的重要作用。王充认识到“论”体具有辨然否、正流俗的意义,便不惜付出耗损精神、危害养生的代价,也要以“论”体正俗:“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对作》)王充运用“论”体匡正流俗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虽对王充的非圣无法颇有微词,但也指出《论衡》有些篇目“大抵订伪贬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
其次,王充之所以注重“论”体,是因其看重“论”体不偏不倚的精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字:“平”。《自纪》篇言:“《论衡》者,论之平也。”《须颂》篇言:“《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王充将《春秋》视为指导汉家施政的法典,同时也是自身著作追求的标尺。王充将《论衡》视为《春秋》的有益补充,表明他对《论衡》有着较高的自我期待。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论衡》为汉平说”一语,因为这涉及到《论衡》一书的核心主旨。《自纪》篇言:“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王充在《自纪》篇中将《论衡》创作宗旨概括为“论之平”“如衡之平”,足见“平”在他心中的分量非比寻常,“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王充的“文心”,是《论衡》的“书眼”。那么,王充本人如何理解“论之平”呢?《须颂》篇有典型论述:
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镢锸平而夷之,为平地矣。世见五帝、三王为经书,汉事不载,则谓五、三优于汉矣。或以论为镢锸,损五、三,少丰满汉家之下,岂徒并为平哉?汉将为丘,五、三转为洿矣。湖池非一,广狭同也,树竿测之,深浅可度。汉与百代,俱为主也,实而论之,优劣可见。故不树长竿,不知深浅之度;无《论衡》之论,不知优劣之实。
上文“平”字集中出现四次,分别为“高平”“平而夷之”“平地”“并为平”。“高平”之“平”,是与“高”相对的一种状态;“平而夷之”,有“铲平”之义。“平地”“并为平”与“高平”意义相同,指的是与“高”相对的状态。其中关键的是第二处,即“平而夷之”,其言“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镢锸平而夷之,为平地矣”。镢锸是维持事物平衡的重要工具,土地有高下,镢锸使之平。“或以论为镢锸,损五、三,少丰满汉家之下,岂徒并为平哉?汉将为丘,五、三转为洿矣。”在王充看来,“论”的意义与“镢锸”相同,高者使之下,下者使之高,最终达到“平”的宗旨。“镢锸”与“论”体都是裁决的工具。前者致力于解决土地沟壑的高下不齐问题,后者则致力于认识理念的价值重估。一言以蔽之,“论”体实为“平”而生,“平”是“论”的价值追求与使命。
不过,土地之高下不齐,乃造化为工、自然而成的结果;汉德之下,却是人为造就的结果,《须颂》篇载:“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儒者掌握话语权,拥有评判优劣的权力,然而过于崇古的儒者往往贵古贱今,抬高“五、三”(指“五帝”“三王”),贬斥汉代,最终造成了汉德的“失语”。《论衡》为汉代价值观念作平说,便是要用“论”体纠正“周优汉劣”的不平衡局面,故“损五、三,少丰满汉家之下”。简言之,王充作《论衡》,是要确立周汉优劣的价值尺度,并起到铨衡政治乃至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充已经具备了“论”体意识的初步自觉。
二
近些年来,中国文体学的研究颇为兴盛,众多学者在此领域作出许多有益尝试,成绩斐然,(6)详参吴承学:《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当然在一些问题上尚有诸多学术争论。罗宗强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对这种现象作出总结:“或说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性;或说包括体裁、文章风格、篇章体制;或说包括体裁、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性体貌;或说包括体裁、体制、样式、语体、风格等等。”(7)罗宗强:《因缘居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14页。基于学界对“文体特征”及其文化意味的理解共识,可以对《论衡》“论”体文作一学术鸟瞰。概而言之,《论衡》“论”体文特征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曰“杂”,二曰“浅”;这两种文体特征又蕴含深厚的文化意味。
“杂”,是指文体之散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论式》中指出:“今汉籍见存者,独有王充,不循俗迹,恨其文体散杂,非可讽诵。”(8)章太炎著,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卷五·国故论衡校定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9页。章氏所谓“文体散杂”显然是就《论衡》一书的文体风格展开的讨论,其实质是文体批评。嗣后,容肇祖、缪钺、裴斐持有类似观点。(9)“《论衡》的文体,与他的《讥俗节义》一书大致相同”,均以“明白浅露”为其著述风格。载容肇祖:《容肇祖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3411页。“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自露其文,集以俗言。’其作《论衡》,文体亦然。”载缪钺:《缪钺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裴斐指出:“从文笔看,《论衡》文体散杂,文学性不强,文字比较啰嗦冗长。”载裴斐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9页。实际上,对《论衡》文体之杂的抨击,自该书成书之日起便已产生。《论衡》成书后,外界批评其“不能纯美”。《自纪》篇载外界批评:“口无择言,笔无择文。……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文虽众盛,犹多谴毁。”外界所谓“不能纯美”“笔无择文”“不美好”“多谴毁”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在说《论衡》不够精纯,较为驳杂,瑕疵较多;简言之,外界批判《论衡》“芜杂不精”。此后,《抱朴子·喻蔽》载时人对《论衡》的评价:“王充著书,兼箱累帙,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10)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3页。宋高似孙《子略》评《论衡》“乏精核而少肃括”,(11)高似孙撰,司马朝军校释:《子略校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7页。《四库全书总目》亦言“儒者病其芜杂”。(12)《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32页。这些批判虽无“文体散杂”之名,但本质上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只不过彼时的评判较为隐微,不像后世明标“文体散杂”的概念。文学的实践往往会先于概念理论,这在后世文学史的总体鸟瞰中更加清晰。
《论衡》文体之杂与汉代讲论经义的风气有关。以往对《论衡》文体之杂的表述大多停留在文体批评层面,对这种文体特征的成因并未过多涉及。《文心雕龙·时序》载:“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1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3页。《论说》篇又指出:“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论家之正体也。”(1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7页。刘勰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论衡》之所以具备芜杂的“论”体文特征,与东汉讲论经义风气的盛行密不可分。盖因儒者讲经,千头万绪,各执一词;王充又对此心有未惬,便一一与之论辩。《对作》篇言:“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这种鲜明的问题指向性,一方面使得文本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因讨论问题多而容易分散不能聚焦;主题太过庞杂,便容易陷入班固所言“漫羡而无所归心”(15)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2页。的境地。因此,这种文体层面的散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本层面所涉问题头绪纷繁所决定。
“浅”,指其“论”体文之浅近。王充自觉追求浅近的“论”体风格,对深覆的“论”体风格敬而远之。在王充看来,“论”分为“口论”与“笔论”两种,两者载体不同,但都应以浅近为旨归。《自纪》篇言:“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同篇又言:“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文字记载贵在深入浅出,语言表达注重传辞达义,二者皆以达义为宗旨,而浅近是达义的前提。“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在王充看来,语言与文字功能相通,只是由于口头传说容易亡佚,才催生出文字记事;既然口头传说崇尚简单明了,那么文字记载也就无需推崇深覆的“论”体风格。
《论衡》“论”体的浅近特征主要通过广泛罗列常见事物来实现。王充在《论衡》写作过程中,时常引用耳闻目见之事物。例如:
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逢遇》)
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幸偶》)
春种秋收、火烧野草,都是众人耳闻目见的寻常事物,这类事例在《论衡》中俯拾皆是。习见事物的广泛罗列客观上造就了浅近的“论”体风貌,而这正是王充主动追求的结果。《自纪》篇言:“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深入浅出,喻难于易,这是王充自觉的论说策略的体现。《论衡》“论”体的浅近风格有何意义呢?常见的文学史著作认为王充譬喻常引用常见事物,是因为他对此感到熟悉,而对于自身不熟悉的内容却无法作出解释。这属于表面之论,实则不然。王充引譬连类时运用习见事物,乃是其自觉追求浅近“论”体文风的必然结果。
如果基于知人论世的原则继续深入追溯,王充对“浅近”的文体风貌自觉追求与其教化民众的目的有关。从作者身份角度来看,王充是一名汉代的基层文官;尽管其日常工作颇为繁杂琐碎,但教化民众始终是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若要有效实现教化民众的目标,便不能不注意方式方法。《自纪》篇载:“《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王充的《讥俗》虽早已亡佚,但从学界“形露其指”“文之察”的评价来看,此书与《论衡》俱为浅近的文体风格,同时这也体现出王充对所谓“俗人”的阅读接受能力有着明确的认知。《自纪》篇载:“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质言之,从“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以及“喻深以浅,喻难以易”的表述来看,浅近的文体风格是王充主动追求的结果,也是其自觉的文体意识的明证。否则,如果文风过于深闳,民众难以读懂,那么教化的功能也就无法实现。
文体的浅近之风,折射出的是王充创作的自我期待。有学者指出,秦汉以降的文士以民众之导师自居,且这种导师的社会身份是社会结构赋予他们的一种功能。(16)李春青:《新传统之创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学术轨迹与文化逻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页。今日看来,士人以民众的精神导师自居,这种自我期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著述内容的现实指向性。章学诚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7)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18)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8页。章氏指出,六经是蕴含着先王治国理念的历史实录,而创作六经的初衷并不为著述,而是治国理政。孔子删订六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舜徽也指出:“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19)张舜徽:《广校雠略 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王充也是用文章寄托自身的用世之志。《对作》篇言:“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讦而情实。……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同篇又言:“《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人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对作》篇是王充对其作品主旨的阶段性总结,从这段自述中能够看出《论衡》的很多篇章都以教化民众为旨归。如此一来,浅近的文体风貌在其言说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不难理解了。总起来看,教化民众是目的,文风浅近是手段,引用常见事物又是实现文风浅近的方式;王充对浅近的文体风貌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也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
三
王瑶先生在谈到文学史研究的目标时指出:“它(文学史)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20)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重版题记”,第2页。评判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价值也应当延续这一思路。基于文学史的总体观念,王充的“论”体意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王充的“论”体意识在“论”体发展中有着过渡性的作用。王充的“论”体意识在“论”体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摆渡人”的角色,它起到积极的过渡作用,大体分为以下两个层面:从“论”体实践向“论”体理论的过渡;“论”体理论从浅显简单向深刻复杂的过渡。
《文心雕龙·论说》将《论语》视为“论”体的开端:“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2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7页。这种论断属于一家之言,更多学者认为“论”体的发端始于《荀子》。《荀子》一书的《天论》《正论》《礼论》《乐论》具备论体文章更多显著特点:其一,篇题明标“论”体之名;其二,篇首明标所“论”主题;其三,论说方式已经较为成熟。实际上,先秦时期的多部典籍都在“论”体实践层面取得相当程度发展;除《荀子》外,《墨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在“论”体实践层面取得不俗成就。与此同时,在理论探索方面,这些典籍又都相对缺乏对“论”体本身的总结,“论”体意识显得不足。直到西汉时期这一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贾谊的《过秦论》堪称汉代“论”体文的典范之作,其对“论”体本身的探究也略显欠缺。先秦西汉的“论”体文,其成绩集中在“用”的层面,“体”的层面则相对不足。王充则有明显突破,他在“体”的层面作出了初步总结。王充在文体实践层面对先秦与西汉的“论”体实践予以继承,而在文体意识层面有了一定的发展。清黄承吉对文章“体”“用”有深刻的见解,“黄承吉认为,人心人情有诸内必发诸外,以文辞发诸外的表现形式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文章体式”。(22)孙晶:《黄承吉“雕虫篆刻”与扬雄之微意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因此,我们说王充是处在由“论”体实践向“论”体理论过渡的阶段,其自觉的“论”体意识也发挥了一定的过渡作用。
王充的文体意识集中在“论”体层面。对于“论”的特点,王充将其概括为“应理”。《超奇》篇:“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王充强调“论”体“应理”的核心特点,此后“论”体尚理的观念也逐渐得到众家认可。曹丕《典论·论文》:“书论宜理。”(2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71页。李充《翰林论》:“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24)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0页。陆机《文赋》:“论精微而朗畅。”包咸注:“论者,论事得失,必须精审微密明朗而通畅于情。”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25)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74页。尽管各家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在“论”体重“理”的核心观念上能够达成共识。当然,王充所做文体辨析工作,只是筚路蓝缕的初步工作,而刘勰则登堂入室,臻于完备。
文体探究其实是一个由简至繁、由个别到普遍的过程,(26)王充对“论”体的辨析,是就单一文体展开,而后世对文体的辨析则较为全面。从《典论·论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四科八体,到挚虞《文章流别集》赋、诗、七、设论、颂、箴、铭、诔、哀(哀辞、哀策同属哀体)、碑、图谶、符命、史述等十三种文体,到陆机《文赋》的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到《文心雕龙》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笺记等三十四种文体,文体的数量逐渐增繁,文学批评家对文体的辨析与探究也逐渐深入。王充对“论”体的辨析,实为整个文体研究脉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不是说王充对“论”体的辨析直接推动了后世文体研究的发展,而是说后世文体研究的逐渐深入与普遍推进离不开王充的“论”体意识,后世的文体探究是建立在汉代学者已有的文体论述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探究在深刻性、系统性层面较此前真正取得明显突破。
第二,从作者与文体的关系角度来看,王充的“论”体意识初步表明了文体与作者之间存在“双向选择”的关系。《论衡·佚文》篇载: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在王充视野中,文章包括经艺、诸子传书、论说、上书奏记、文德之文五种类型,是为“五文”。除文德之文外,其余“四文”都是秦汉时代的著述文体,有学者将“五文说”看作中国文体论的嚆矢。(27)蒋祖怡:《王充的文学理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8页。将“五文说”与文体学相联系的思路是对的,同时王充的表述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体对作者的“选择权”。这主要体现在“论”体文层面:“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经生无法胜任“论”体文的写作,其言外之意是“论”体文有其自身规律,它对作者有一定的写作要求(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作者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够写出合格的“论”体文。这就是从“论”体层面揭示了文体对作者的“选择权”。那么,哪些人具备写作“论”体文的条件呢?王充指出:
(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超奇》)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案书》)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
在王充看来,桓谭是写作“论”体文的典范,而从他对桓谭的赞美之词中,我们能够总结出王充视野中“论”体文的写作要求。概括来讲,就是能够别嫌疑、定是非、辨然否。具备这种素质的作者能够选择“论”体,也能够为“论”体展开提供保障。
根据王充对“论”体文的表述,作者固然能选择文体,而文体也会“选择”作者。王充的表述较为简略,是仅仅局限在“论”体文层面的理论雏形。近两个世纪之后,曹丕在其《典论·论文》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28)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270页。这八个字震古烁今,明确表达了作者与文体“双向选择”的含义。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进一步指出: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2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271页。
曹丕先称赞王粲、徐干长于辞赋,随即又言“然于他文未能称是”,这说明作者固然有作者的个性,文体也有文体的个性。前者由时代、地域、家庭、阅历等多种因素综合造就,是每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点;后者是一种“层累构造”,从萌芽到定型经历漫长的时间,期间经过众多作者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究后渐趋稳定。无论作者还是文体,都有一定的识别性。即就文体而言,人有其长,必有所短。一方面,作者对某种文体有着特殊的心得,往往能够达到体性交融的效果。另一方面,兼善众体的作者的确是少之又少。不是说作者在文体层面有着广泛的尝试,就可以说他成功地选择了文体,更不必说被文体“选择”。所谓“双向选择”,其实质是一种互动:文体之性与作者之性能够相互交融,便能够形成默契,相互成就;如果二者方枘圆凿,即便作者“强行选择”文体,也很可能只会产生一些平庸的作品。
对“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刘勰也有类似观点。《文心雕龙·才略》云:“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谕,不及丽文也。”(30)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1781页。同篇又言:“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3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1796页。刘勰认为桓谭长于撰写讽谕说理的“论”体文,却短于创作尚“丽”的赋体文;曹丕虽在五言诗与赋作层面不如曹植,但其乐府诗自有高格,《典论》辨理扼要,也非曹植所能比拟。刘勰的表述证明才兼众体的作家少之又少,进一步强化了文体与作者“双向选择”关系的存在。
通观王充、曹丕与刘勰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王充在“论”体层面初步表明了作者与文体之间存在“双向选择”的关系,曹丕在王充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明确表达了文体与作者存在“双向选择”的关系,刘勰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价值在于为曹丕、刘勰提供了文体辨析的话语基础。
第三,从文学思潮与文体功能的关系角度来看,王充的“论”体意识表明东汉前期的颂汉思潮对“论”体功能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东汉前期文学的颂汉思潮,学界已经多有论述,在此基础上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是王充以“论”体颂汉的意义,二是文体功能与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
在王充的视野中,汉人颂汉是理所应当之事,他将“颂汉”视为文士的责任。《须颂》篇对此有着明确表述:
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
王充注意到五经之中具有颂美当代的深厚传统,这为其颂汉提供了重要的话语资源与学术基础。王充先是罗列五经颂赞之篇目,指出历朝历代凡有善政必有颂音,随后得出当今盛世应当歌颂的结论,并明确表达了颂美当代的必要性。“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须颂》)“论”体原本是以析理为主要文体功能,以辨然否、别嫌疑、定是非为旨归,赋颂之类原本便含有颂美功能的文体内容,如何实现颂汉的目的呢?王充选择改造文体,以“论”为颂:
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佚文》)
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
王充有意识地为“论”体赋予颂美的功能属性,并实际创作了一批颂汉为主题的“论”体文。这种“文体互渗”的尝试一定意义上拓展了“论”体的文体功能。
当然,以“论”为颂并不是王充的原创,至少班彪《王命论》便对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王命论》的核心理念,是从命定论的角度论证东汉政权王权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其中言:“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32)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第4208-4209页。班彪先明言汉绍唐尧之德,又说王祚禀自上天,最终得出“王命不可以力求”的结论。王充与班彪有师承关系,接受班氏思想十分合理。在《论衡》中,王充曾就光武受命中兴反复加以论列申说。《初禀》篇言:“光武生于济阳宫,夜半无火,内中光明。军下卒苏永谓公曹史充兰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时已受命。”《吉验》篇言:“继体守文,因据前基,禀天光气,验不足言。创业龙兴,由微贱起于颠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尝无天人神怪光显之验乎?”这显然是师承班彪的《王命论》。此外,王充论述时强调光武受命胜过往古帝王。《恢国》篇言:“酒食之赐,一则为薄,再则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汉独再,此则天命于汉厚也。如审《论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汉家所禀厚也。绝而复属,死而复生。世有死而复生之人,人必谓之神。汉统绝而复属,光武存亡,可谓优矣。”在王充看来,汉家二次受命,较五代为多,相形之下,优劣立判,这是其对《王命论》的发挥发展。可见,在文体和主旨两个层面,《王命论》都对《论衡》具有重要影响。只不过与班彪相比,王充的写作论题更加集中,形成了一系列以颂汉为主题的文章。“论”体是王充颂汉的重要工具,而从王充对“论”体的灵活运用也可看出,其与“论”体之间存在较强的默契性。
王充以“论”颂汉,反映了文体功能让步于文学思潮的事实。在文学思潮面前,文体功能的转移或改变并不罕见。以“论”体为例,东汉中期以后,政局震荡,风俗衰败,有识之士纷纷以“论”体为凭借批判社会风俗;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崔寔《政论》和荀悦《申鉴》,大都运用“论”体对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予以批判。魏晋以降,玄学兴起,“论”体功能日益拓展,集中的作用是阐释玄理。刘永济指出:“(魏晋之际)辨析玄理之论,尤为繁博。综其大体,固不出聃、周之旨归。析其枝条,则或穷有无,或言才性,或辨力命,或论养生,或评出处,或研易象。”(33)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9-171页。若将视野扩展至文学发展史,那么从先秦至魏晋时期,“论”的文体功能已经发生众多变化。
章太炎曾经指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对这种变化有精妙总结:“凡此五变,各从其世。云起海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触高岗,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于草昧,而最下矣。”(34)章太炎著,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1页。从文体发展流变的历史来看,汉晋间“论”体功能实现了从析理到颂美,从颂美到批判,再从批判到谈玄的转变。“论”体功能的转变深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在文学思潮的席卷之下,文体与文士必然受其影响。王充的“论”体文恰好处在由析理到颂美的转型阶段,《论衡》的文本主题清晰表明这一点。总体来讲,在创作的早期阶段,王充深受桓谭的影响,致力于批判谶纬虚妄,以“疾虚妄”为主题,以“释物类之同异,正时俗之嫌疑”为旨归,“论”体功能在于析理。在创作的后期,兰台文士为代表的“颂汉”作家群登上历史舞台,在东汉初期帝王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背景之下进行大规模的颂汉写作,风头一时无两。王充受“颂汉”文学思潮影响,也投身进时势大潮之中,致力于以“论”为颂,“论”体文的功能由析理转为颂美。站在文学思潮的立场看,这种转变体现的是文学思潮对文体功能转变所施加的重要影响。站在文体功能的角度看,这种转变反映的是文体功能对文学思潮的让步,同时也反映出文体以及文体作者在帝制时代的工具属性。总结来讲,王充以“论”为颂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其反映了文体功能会随着文学思潮的改移而转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