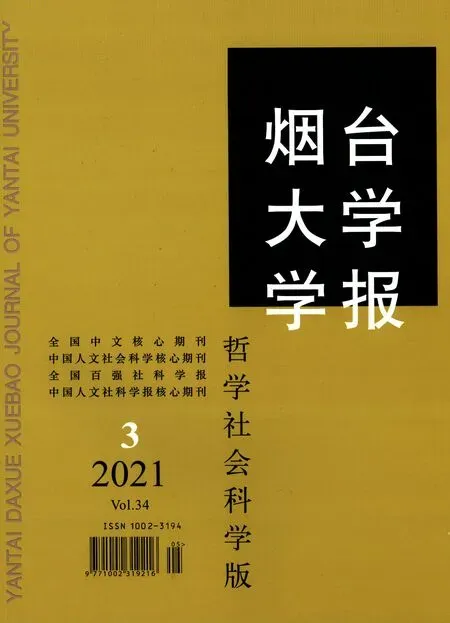符号的构建
——沈一贯反东林形象的历史考察
宋立杰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在晚明的政治史研究尤其是有关晚明党争的研究领域,沈一贯属于不可能绕开的一个人物。沈一贯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入阁,三十四年致仕,在阁时间长达十三年之久,是后张居正时期在阁时间最长的阁臣。史家多认为沈一贯对晚明党争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浙党的首揆,齐楚宣诸党又是沈一贯的追随者分化而成,但学界对浙党、沈一贯与浙党的实际关联的研究并不充分。(1)相关研究成果可参阅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0-689页;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1-473页;梁绍杰:《“国本论”与晚明政争》,博士学位论文,香港大学中文系,1994年,第84-95页;朱子彦:《中国朋党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94-422页;杨向艳:《沈一贯执政与万历党争——以楚宗、妖书、京察三事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商务印书馆,2018年;宋立杰:《理身理国:沈一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历史系,2018年,第123-145页。晚明党争作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其中对东林党(书院)研究颇多,对浙齐楚诸党则研究甚少,目前似只有日本学者城井隆志曾撰专文阐述以顾天埈为中心的反东林势力的形成,但是他没有进行浙党形成的考述。(2)参见城井隆志:《明末の一反东林派势力について——顾天埈めぐって》,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上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pp.263-282;城井隆志:《万历三十年代における沈一贯の政治と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1985年,pp.95-135.本文着重探讨沈一贯与当时清流官员的关系演变轨迹、浙党的形成轨迹和沈一贯与浙党的关系,并将其置于晚明这一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为便于行文,笔者先假定存在浙党这一实体。
一、沈一贯与东林的关系实态
万历三十三年以降,舆论纷纷弹劾攻诋沈一贯,皆言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人士尽锢于沈一贯之手。史家也多指出,沈一贯入阁后,“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致使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等人致仕。(3)吴应箕:《东林本末》卷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标点本,第12-13页。但具体的情形是否如此呢?
万历二十二年,廷推阁臣,沈一贯与陈于陛名列其中,最终被明神宗点用入阁。因明神宗对首次廷推名单甚为不满,曾责备吏部。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上疏辩解,为明神宗斥责,遂上疏乞休。而高攀龙于是年因弹劾王锡爵而被贬谪广东揭阳;赵南星是在万历二十一年京察中,受到弹劾,被削籍为民。依此而论,沈一贯的入阁与顾宪成等人的致仕并无必然关联。
从入京任职到万历二十二年间的仕宦轨迹来看,沈一贯与上述几人似无交集,但身为京官,应无不听闻之理,尤其是沈一贯曾在吏部任职,吏部又专管人事调动。此外,顾宪成曾代人为沈一贯的父亲作寿序,文中对沈一贯称赞不已。(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九《奉寿慕闲沈老先生八十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16-117页。但查阅顾宪成、高攀龙与赵南星论及时弊的奏疏、书信,皆未提及沈一贯,相关史籍中也未记载他们存在正面或者直接政治冲突。
揆诸明清史籍所载,似只有于玉立、刘元珍二人与沈一贯存有直接的政治冲突。史载于玉立曾上万言疏,“语稍侵正辅”,以此得罪沈一贯,遂上疏乞休;再次任官后,他与沈一贯的关系仍旧紧张,沈一贯便声称“刽子手至矣”。(5)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476-477页。但此记载实不能令人信服,于玉立上万言疏是在万历二十年,而沈一贯此时家居不仕,更不是首辅,故而此疏不可能讽刺他,且沈一贯也曾自言二人有师生之情。刘元珍因在乙巳京察中,弹劾沈一贯,被明神宗贬谪。刘元珍的致仕与沈一贯有直接关系,但后者曾有密揭救护,已得明神宗批准。刘元珍之所以弹劾沈一贯,究其原因是不满被察官员钱梦皋的留用,他与沈一贯之间并没有直接政治冲突,且明神宗认为刘元珍弹劾沈一贯别有他意。(6)周永春:《丝纶录·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565-566页。
此外,温纯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清流,舆论以及明清文献多指出,“卒以忤沈一贯致仕”。但是他与沈一贯有私交,沈一贯任职礼部期间,温纯曾致书沈一贯,言“称名贤大君子也,相与持衡,称量海内人才拔茅”。(7)温纯:《温恭毅集》卷二六《与沈蛟门宗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第735页。万历十三年,京师大旱,明神宗亲自步行三十余里祈雨,沈一贯特与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的温纯谈及此事。(8)沈一贯:《喙鸣诗文集》文集卷二一《与温一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6册,第399-400页。温纯连疏乞休时,亦致书沈一贯等人,希望他们为其周旋。因此沈一贯与温纯并没有政治冲突,应是第三方的介入,才令他们的关系产生裂痕。万历三十年,因于永清、姚文蔚事,他们的关系始有裂痕。此事起因为秦人刘九经上疏言时事,中有“十月南山之语”,被于永清、姚文蔚认为此举是排挤沈一贯,故而上疏弹劾,但温纯与沈一贯曾相互辩解。
史家多强调东林与反东林的纷争始于国本、历次京察等事,但是沈一贯在国本一事上出力甚多,见于《敬事草》《明神宗实录》《辑校万历起居注》的奏疏揭帖就达四十余封,甚至封还御批,促使明神宗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二十七年以后,明神宗关于国本的谕旨一般都是直接发给沈一贯,或者经由他传示礼部、户部。明神宗很少批复其他官员的奏疏揭帖,而沈一贯的揭帖却时有被批复,虽不是关注其每封,但在关键时期的揭帖皆是批准沈一贯的奏请。万历三十六年的考选事件、王元翰案、李三才案、万历辛亥京察、丁巳京察等事,朝野纷争不已,但沈一贯此时早已致仕多年,并不再过问世事。
如非要指出沈一贯与东林的分歧,似乎只有理念与施政方针的歧异,较为明显之处则为君子小人之辨。国本一事最能体现沈一贯“得君行道”之意,他所主张的权变尽现无疑,所收效果优于强谏。沈一贯的权变主要考虑皇权,力求与明神宗同心,满足明神宗的心理需求。他没有直言谏诤,只是婉承帝意。这和清流官员的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但沈一贯在明神宗与外廷官员之间进行调护,确实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经城井隆志梳理,弹劾沈一贯及其党羽的官员有69人,其中名列东林党的有10人,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反对东林的官员有12人,(9)城井隆志:《万暦三十年代における沈一貫の政治と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pp.119-120.东林所占人数并不多。当然数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我们要考虑一点,即城井隆志依据万历三十六、三十七年的弹劾疏,时沈一贯已于万历三十四年致仕,如此,万历中后期尤其是沈一贯在阁期间,将政局特点概括为东林与沈一贯的对立,甚至是清流与沈一贯的对立,值得商榷。总之,沈一贯与东林早期主要成员皆没有正面的、直接的政治冲突。樊树志认为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弹劾沈一贯,不是“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显现,而是阁部之争。(10)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上,第530-537页。但三人不是吏部官员,亦不是六部中高级官员,与六部官员的关系如何亦很难界定,因此不能简单地归为阁部之争。他们弹劾沈一贯,并不仅仅针对沈一贯,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
二、浙党与沈一贯之关联
现今研究者大多以先入的观念确定此时期已有浙党这一实体,再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拼凑出浙党,从而忽略浙党成员是否是有意识的集合、浙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历史事实。
(一)浙党成员内部联系的缺失
晚明诸党派的界定,学界一般有两种意见,一是以党魁之籍贯命名,(11)朱子彦:《中国朋党史》,第456页。二是以科道官籍贯命名。(12)汤纲、南炳文:《明史》,第691-692页;《明史》卷二三六《夏嘉遇传》,第20册,第6160-6163页。“浙党”的“浙”应如何解释?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以“浙党”名之,似为恰当。综合分析明人奏疏、文集等史料,笔者认为浙党的“浙”是就沈一贯的籍贯而言的,如叶向高言沈一贯当国时,“浙中颇有附丽之者”。(13)叶向高:《蘧编》卷九,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标点本,第64页。清初浙江人朱彝尊言:“浙人不幸,万历以来,执政者前有四明,后有乌程、德清,以是朝士不附‘东林’者,概目之曰‘浙党’,……”(1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〇《施邦耀》,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标点本,第614页。
万历后期,内阁首辅叶向高虽似持调停之术,然其整体上偏向东林诸人。受困的浙人不甘于此,联合其他不得势之人,纷纷上疏弹劾叶向高等人,看似成为一个实体。围绕李三才、王元翰的争论,促使邵辅中等人认为东林在背后支持。以君子清流自居的官员则认为邵辅中等人是邪派小人,承袭故辅沈一贯之术。双方相互争论,浙人渐处下风。万斯同总结万历三十至四十年朝中官员情形时,指出沈一贯的“乡人官于朝者,亦多被诋諆”。(15)万斯同:《明史》卷三一一《沈一贯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6册,第417页。吴应箕亦称浙人因赵志皋、沈一贯、朱赓三人相继为相,为西北官员攻诋,“困阨日久”。(16)吴应箕:《东林本末》卷中,第18页。与此相反的则是西北、东林势力在朝堂的高涨。
然此时沈一贯已致仕多年,其子嗣未曾干涉朝堂纷争。(17)清人全祖望便评论道:“尚宝好兄弟,超然谢党论。”尚宝指沈泰鸿,沈一贯长子。参见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九《沈氏畅园》,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标点本,第2265页。查阅明清文献,亦未见致仕的沈一贯与朝臣有所联系。只是朝臣并未遗忘他,犹如他第一次归隐时,只是境遇不同而已。被认为是浙党首揆的沈一贯已是众矢之的,即使与之不相识,只要言语稍异,便被指为其党。如同魏忠贤专权时期,将反对者一概目为东林,浙党规模也不断地被扩张,成员不断地被增加,致使朝局愈发混乱,党派罗织愈演愈烈。李邦华攻诋王之桢是沈一贯的护法,李廷机是衣钵传人,顾天埈为其幕下宾;汤宾尹是李廷机的门生,王绍徽是汤宾尹的高足;徐兆魁为王绍徽主盟,又是沈一贯之门客。李邦华遂将被正人君子视为小人之人统归于沈一贯的门下。(18)李邦华:《李忠肃先生集》卷一《西台疏草·分别邪正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第32-35页。御史张养正亦以沈一贯为线索,将王之桢、李廷机、岳和声等人捆绑在一起。(19)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七《岳元声传和声附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364-365页。不只是浙人受到牵连,凡是与沈一贯有牵涉的官员亦受到攻诋,如杨时乔力推李廷机入阁,又推黄汝良、全天叙,遂为攻诋沈一贯者所不喜。
学者们只是笼统地把一些人看作是沈一贯的党羽。城井隆志认为沈一贯的党羽共有71人,(20)城井隆志只统计了万历三十六、三十七年间被认为是沈一贯的党羽。城井隆志:《万暦三十年代における沈一貫の政治と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pp.115-122.但他以晚明官员之间相互攻诋弹劾疏作为依据以判定是否为沈一贯之党,此举略为不妥。孙立辉虽梳理浙党成员,但未说明标准。综观名列浙党之人,与沈一贯的关系实态尚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探究,最令人困惑的便是张问达,既有将他当作沈一贯党羽者,又有归为东林成员者。目前见于文献记载的,只有钱梦皋曾参与沈一贯组织的聚会,(21)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一,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影印本,第45页。但该记载的真实性也有待考证。依据郭正域等明人的记载,沈一贯的党羽成员主要有萧大亨、康丕扬、姚文蔚、杨应文、钱梦皋等五人。康丕扬、钱梦皋、杨应文则是核心人物,在与温纯的争论、楚事、续妖书等特定的事件中,确实迎合或者谄媚于沈一贯。康丕扬等人曾辩解不是沈一贯党羽,沈一贯也说他们没有私交,并且康丕扬曾弹劾沈一贯。沈一贯致仕后,蔡献臣、李廷机等人纷纷言及与沈一贯没有私交。其余诸人,皆未见有私下往来的记载,故而他们内部联系并不紧密。王锡爵、朱赓与沈一贯是同年,方从哲是沈一贯的门生,而私交如何,我们也不甚清楚。
乙巳京察后,言路疯狂攻诋沈一贯。明清史家与当代学者皆言浙党势力极为强大,为何在沈一贯备受攻诋之时,却无人为他辩解?史家亦认为浙党是以科道官为主体,既如此,他们掌握言路的话语权,为何不维护沈一贯,任由其被言路攻诋?是沈一贯授意,还是他们见沈一贯大势已去,遂不再为之出面?
(二)浙党成形与沈一贯致仕
查阅《万历疏钞》《明神宗实录》《万历邸钞》《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等明代史籍,我们发现在沈一贯致仕之前,言路攻诋沈一贯者,虽有称其结党营私,却未有“浙党”“浙党首揆”等类似言语。目力所及,最早提出“浙党”一词的应是郭正域。在为王述古所作的墓碣中,他使用“浙党”一词指代沈一贯及其党羽,该文大概写于万历四十五年或四十六年间,当时朋党之争已是既成事实。(22)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六《明封户部郎禹川王公墓碣》,《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册,第437-438页。晚明,官员间相互攻诋,皆加对方以“党”名,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便有所描述,“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牍者,不曰苏脉、浙脉,则曰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23)《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1201-1202页。该疏写于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24)《万历邸钞》所记二十八年事情应是错页,观前后所言,似是万历三十八年之后的事情。而观叶向高的记载,张延登此疏应上于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参见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一七《请补阁臣第五十二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7册,第206-207页。我们可以肯定“浙脉”“秦党”等诸党名,在此前业已出现。一般认为东林与浙党对立存在,东林书院修建于万历三十二年,被冠以“党”名,是在争淮抚、王元翰事件之时,为万历三十七、三十八年间,那么浙党——或者被时人认为是一个朋党——是否也是在此时形成?
揆诸夏允彝、孙承泽、蒋平阶等人的著作,只言党争始于沈一贯的“持权求胜”,但并未明言浙党的形成轨迹。这些文献皆产生于明清易代之际,反思明亡之原因。晚明党争是学界研究热点,王天有、谢国祯、小野和子等学者多立足于上述文献,进行再阐释,但颇多歧异。(25)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3-26页;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64页;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以浙党形成时间而言,城井隆志认为浙党形成于沈一贯担任首辅期间。王克婴则认为浙党“是明末第一个出现的有政治影响的朋党”,入阁后沈一贯便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势力,并指出援朝御倭是浙党形成的初始时期;与秦党的斗争是浙党发展时期;与沈鲤、郭正域的斗争中,浙党基本形成。(26)王克婴:《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在认同王克婴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孙立辉指出浙党最终成型于沈一贯与秦党的斗争,与郭正域、沈鲤的纷争是浙党规模扩展时期。(27)孙立辉:《沈一贯与浙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2页。然他们都没有考虑明清文献关于“浙党”一词的记载,且观念上先入为主,即确定此时期有“浙党”这一称呼,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浙党”这一实体。学术界另有与之相反的阐释。汤纲等人认为齐楚宣昆浙诸党是沈一贯在朝时的追随者分化而成。(28)汤纲、南炳文:《明史》,第691-692页。依据《明史》的记载,林立月认为浙党形成于万历四十年以后,昆宣二党形成于淮抚之争时期,早于浙党。(29)林立月:《明末东林运动新探》,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年,第290页。也就是说,沈一贯在阁期间,并没有产生浙党。
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古代的党是朋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他们的结合也是需要条件的,不是仅仅利益相同,或者品性相近,就是一个团体、党派。而且,即使利益相同,也应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三、沈一贯:被编织的党魁
通过前文所论,我们可以确定浙党内部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大部分成员与沈一贯也没有私交,甚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沈一贯致仕后被他人攻诋为其党羽,这也意味着沈一贯与浙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为何沈一贯会被舆论认为是浙党首揆?揆诸明清史籍,再考虑当时的政治生态,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乡谊与师生关系
在晚明舆论与相关文献中,顾宪成等人占据道德制高点,与他们对立之人,自然被视为小人邪派。沈一贯等人身在官场,又要为仕途考虑,自然受官场规则所限。而他们的对立面东林则以道德相标榜,在野清议时政,无所顾忌。万历三十六年,得再起之命时,顾宪成断然拒绝。他如此解释不仕的原因:“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30)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简修吾李总漕·又》,第58-59页。
万历初期的张居正、申时行等阁臣虽亦与“公论忤”,备受言路攻诋,但因时隔多年,他们逐渐淡出舆论视野,以此作文章,所起的效果并不理想,很难引起他人共鸣。沈一贯却不失为最佳人选,尤其是当东林得势时,郭正域、沈鲤等人被认为有再起复的可能。换句话说,沈一贯只是一个引子,一个符号,如果没有他,可能就会是汪一贯、徐一贯等等,此时也许就不是“浙党”。彭宗孟对此有深刻解释:
年来争淮抚,争考察,争东林,玄黄之战已酣,泾渭之来未判,雪消见,无路藏身,计惟有旧辅沈一贯夙犯公论,可借以笼罩言官,掩遮垢秽。于是不问其人之曾否识面,官之曾否同时,一触邪锋,即推四明之党,甚至如诸臣驳正起废一事,有何相渉,亦牵附于四明之流毒,浙人之主盟。则凡宫府朝野之间,礼乐刑政之类,少持正论,便纳党中,使言官无一事得关其说,而后谓之非党欤。(31)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二三《彭宗孟》,《四库全书项目丛书》史部第125册,第475页。
黄景昉亦云自沈一贯致仕后,官员皆以浙为口实。(32)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十,陈士楷、熊德基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标点本,第310页。当然被认为是浙党成员之人,或多或少与沈一贯有些关联。在争淮抚中,率先弹劾李三才的卲辅忠是沈一贯的姻亲。沈一贯致仕后,又有多名浙人先后入阁,且存有师生关系。方从哲、温体仁在职期间,对政事处理不当,亦无多少政绩,致使朝局日益混乱。言路遂将产生此种局面的原因皆追溯、归咎于沈一贯。全祖望便言康熙年间修《明史》者“欲痛抑沈文恭公,以为亡国之祸由于党部,党部之祸始自文恭”。万斯同却不认同此论,他指出:
由其后而言,一变而为崔、魏,再变而为温、薛、杨、陈,三变而为马、阮,清流屏尽,载胥及溺,而温则文恭之门下也,东林诸子所以尤憾文恭。然此乃流极之运,未可尽归之一人。(3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九《沈文恭画像记》,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111-1112页。
万斯同认为东林仇视温体仁,后者恰是沈一贯的门生,所以东林“尤憾文恭”。崇祯三年(1630),温体仁入阁,不久成为首辅,在阁时间达八年,是崇祯五十相中在阁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阁期间,他结党营私,倾陷东林或与东林交好的阁臣,使得朝局大坏,致使当时舆论与后世史家对温体仁多有批评。(34)舆论对温体仁的评价可参阅李文玉:《崇祯朝士论困局与明末政治文化解析——以对温体仁的评价为例》,《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
(二)沈一贯与郭正域、沈鲤的矛盾
郭正域曾选庶吉士,沈一贯为馆师,因此他们有师生情谊,但他们的关系却甚为紧张。明清史籍对二人矛盾记载颇详,如张岱便言:“……时馆师四明沈一贯……每与谈天下事,一贯岳岳自负,正域意殊轻之,不为降也。”(35)张岱:《石匮书》卷一七九《郭正域传》,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标点本,第8册,第2557-2561页。万斯同对沈一贯与郭正域交恶事亦有记载,并如此定性:“……正域既积忤一贯,一贯深憾之。”(36)万斯同:《明史》卷三一七《郭正域传》,第6册,第491-494页。
张岱等人皆强调郭正域与沈一贯品性不同,在叙述上皆扬郭抑沈,但所叙事情,尚需探究。如冯琦反对秦王请立庶长子事,《明神宗实录》《宗伯集》中皆未见相关奏疏。惟万历三十一年,礼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机上疏持不可,所言诸语与万斯同所述郭正域的反对理由类似。秦王又先后为宗室子嗣请名封,皆为李廷机所阻。万历三十五年三月,明神宗特许封秦藩庶长子为郡王,时沈一贯已致仕。《明神宗实录》《敬事草》《辑校万历起居注》等文献亦未记载沈一贯有秦藩事的奏疏,且他曾在礼部为官,应知晓宗藩条例内容。惟议夺吕本谥号事,郭正域确曾言及沈一贯以此怨恨他。吕本,嘉靖年间阁臣,依附严嵩,劣迹较多,“廷臣争言本辅相无状,请追夺其谥”。(37)万斯同:《明史》卷二八八《吕本传》,第6册,第140页。此事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七月。关于沈一贯、朱赓为何有所庇护,一般认为囿于乡谊,但朱赓、沈一贯则没有言及此事。明代中后期,阁部矛盾较为尖锐,通过张岱等人的记载,沈一贯与郭正域之间的矛盾似是围绕内阁与礼部的权力争夺而展开,并不能仅仅说是个人品性所导致。
沈鲤与沈一贯应早已相识,万历十二年十月,沈鲤担任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沈一贯担任礼部右侍郎,是沈鲤的副手,但是他们具体的关系实态似不易定论。
沈鲤入阁一事,明清史籍多载沈一贯颇多不满、存有疑虑,有记载述及沈一贯顾虑沈鲤颇得士心,致书李三才言:“归德公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38)《明史》卷二一七《沈鲤传》,第19册,第5735页。考此语来历,似承袭申时行贻书沈一贯之事。当得知沈鲤入阁后,申时行致书沈一贯言:“蓝面贼来矣,当备之。”(39)吴应箕:《东林本末》卷上,第9页。卫威认为两种记载语气相仿,“应当是传闻之歧”。(40)卫威:《沈鲤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7页。此论不无道理。李庆综合考量沈一贯的为人处世态度,指出此说“实可再考”。(41)李庆:《论沈一贯及其〈老子通〉——明代的老子研究之四》,《金沢大学外语研究中心论丛》(日本)2001年第5辑,第216页。吴应箕、张廷玉等人距当时已有数十年之久,所述内容应是转述他人之言。万历二十九年,沈一贯正处于仕宦生涯中政治声誉最高峰,而沈鲤阔别朝堂已十多年,根基较浅,不可能因此而嫉恨沈鲤。该说未见于明代文献中,似最先为清人所述。(42)陈梦雷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收有此说,并注明转引自《明外史·沈鲤传》。参见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33册《明伦汇编·交谊典》,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40784页。但查阅《明史·艺文志》并未发现有《明外史》。对比《明史·沈鲤传》所述,二者用语相同,应是互相转引,或者是同出一源。张廷玉等编纂的《明史》成书于清代雍正年间,而查阅万斯同、王鸿绪本明史,俱未载沈一贯致书李三才事。沈鲤之所以入阁,在某种程度上与沈一贯的奏请密切相关。沈一贯曾多次奏请补阁臣,明神宗点用朱国祚、冯琦,因沈一贯言二人年纪尚轻,应重用老成之人,于是明神宗点用了沈鲤与朱赓。(43)《明史》二一六《冯琦传》,第19册,第5705页。
在阁期间,明清史籍又多述沈鲤与沈一贯不合:“鲤遇事秉正不挠,以压于一贯,志不尽行。”(44)万斯同:《明史》卷三一〇《沈鲤传》,第6册,第391-394页。“入内阁,议论与四明沈一贯相左。”(45)张岱:《石匮书》卷一七九《沈鲤传》,第2557页。故而渐生冲突。然亦有不同记载。孙承宗便言沈一贯与沈鲤、朱赓三人起初相得甚欢,“盖龙江、金庭由先生揭恳而下”。三人存在政见分歧实属常事,但政治冲突实由各自门人所致。(46)孙承宗:《敬事草叙》,见沈一贯:《敬事草》,《续修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4-9页。除此之外,二者的纷争在于阁臣之间的权力差异,下文再予以详细阐释。
查阅《明神宗实录》《万历疏钞》《万历邸钞》等,我们可知弹劾沈一贯的官员多假以郭正域、沈鲤的名义。毫不夸张地说,若无郭正域、沈鲤,沈一贯的名望不会受损,甚至可以贤相之名致仕,即使名望稍损,亦不会如此不堪。万历三十三年之前,沈一贯声望较高,成为首辅,当沈鲤、郭正域逐步走入权力中心后,沈一贯的声望才逐步跌落。郭正域的名望与沈一贯息息相关,朱国桢认为:“正域才情自是不群,然废而名愈高,没而赠甚厚,皆四明成之。刘文简每言浙中相公造化低,遇着对头不好。信然,信然。”(47)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四四《楚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9册,第115页。黄景昉亦指出:“自四明去,而郭江夏之望愈重。”(48)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十,第305页。沈一贯与沈鲤、郭正域的冲突似被史家认为是沈一贯反东林立场的直接原因。郭正域、沈鲤、温纯等人与东林人士交好,高攀龙等人还曾为沈鲤祝寿。郭正域自言沈一贯等人构陷于玉立,是因为他们认为于玉立起官出自他之意。(49)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五,第477页。
人与人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即使是在交恶时,亦会有所往来。同时,沈一贯与清流关系的恶化,大多是围绕郭正域这一中心人物而产生。我们截然将双方纳入清流与小人之列,无意或者有意地将他们归为理念、品质上的差异,且不自觉地将郭正域、沈鲤等人塑造为刚正不阿、为国为民之形象,而沈一贯则被塑造为植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奸臣形象,进而认为小人与君子水火不容,小人不断倾陷君子,从而导致他们发生政治冲突。固然他们存在理念上的冲突,但实际上是他们政治地位的不同、政治环境的改变才导致他们的关系发生变化。
(三)沈一贯的事迹与党争话语分析
沈一贯在阁时间长达十三年,几乎参与了万历朝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在万历朝政治网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于东征、立国本、平播战争诸事都有功劳,可配得上贤相之称,尤其是促使明神宗立皇长子为太子一事,使他的声望达到顶峰,时人多以此赞誉沈一贯。矿税一事,沈一贯曾多次谏止,也产生一定效果,然他确实缴还废除矿税的圣谕。楚王案中,楚王真假一事事关天潢贵胄,年代久远,实不好定论,沈一贯与郭正域存在分歧,但实属正常,朝臣也是各有主张。而郭正域公然表明二人的对立关系,并言沈一贯对他的痛恨,以及唆使私人对他进行攻击,似乎颇为不妥。续妖书案中,沈一贯亦名列其中,在家戴罪之时,亦关注时事,最终却未受干连,反而是沈鲤受到牵涉,郭正域几乎不保。乙巳京察事,在察前,沈一贯确实奏请选任吏部尚书一职,但此为常情,吏部作为行政机构之重镇,不可无首脑,但容易被人界定为争夺吏部之用人权。楚王案、续妖书案、乙巳京察,作为重要政治事件引起朝野纷争,被时论认为是清流的官员深受其害,“奸臣”沈一贯亦深陷其中,但未遭受较大冲击,依然深得明神宗宠信。沈鲤与郭正域持论相同,与沈一贯则有分歧。如沈鲤曾致书沈一贯,他指出刑部惩治叛乱的楚宗人过于严苛,认为应减轻罪责。(50)沈鲤撰,刘榛辑:《亦玉堂稿》卷九《与元辅议处楚宗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第323页。这也成为后世以此批判沈一贯倾陷郭正域等人的间接证据之一。
我们若仔细分析楚王案与续妖书案发生前后的官员议论,会发现晚明舆论对它们的定性存在一个演变过程。两案发生时,没有人弹劾沈一贯,也没有指责沈一贯倾陷清流,反而是在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发生后,舆论开始重新塑造二案。钱梦皋声称他被察是主察官员为郭正域复仇所致,继而指出在楚事和续妖书两案中,他秉公办事,未曾倾陷他人,两案的处理及其结果也是公正的。既然钱梦皋如此自解,攻诋他的刘元珍等人必然要“翻案”,继而直指他们所认为的钱梦皋的后台——沈一贯。乙巳京察,也是沈一贯与舆论关系的转折点。晚明舆论“翻案”癸卯二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楚事、续妖书案可谓是万历舆论热点,犹如史学迁所言:“今日所称不平之甚者,孰有过于楚事妖书耶?而今所称失刑失政之极者,亦孰有过于楚事妖书耶?”(51)史学迁:《大冤未剖尽言披陈以明奸贼弄权以纾人心积愤疏》,载吴亮:《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9册,第58页。天启初期,由张惟贤、叶向高等人奉敇修撰的《明光宗实录》,对楚事与续妖书案的叙述,代表着当时社会主流意见,其确定了沈一贯利用续妖书案构陷郭正域、沈鲤之说。(52)《明光宗实录》卷一,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65册,第12-13页。但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即直至明亡官方再未重新审理两件案件。
终万历朝,东林与齐楚浙诸党互有胜负。天启朝初期,东林势胜,但囿于门户之见,不断清算政敌;天启朝后期,明熹宗崇信魏忠贤,被东林步步紧逼的齐楚浙诸党人纷纷投靠魏忠贤,开始反攻东林人士。崇祯年间,朝堂又为东林平反,但阉党分子仍有在朝者,以致反复争论。南明朝廷中,党争时有爆发。对立诸党皆无力挽救时弊,最终使明遗民、清人认为明朝亡于党争,继而追溯党争始于万历朝,并直指沈一贯对东林的倾陷。
随着“明亡于党争”之说被认同,沈一贯被纳入党争话语体系之中,更加促使史家认为沈一贯借助主事打击异己,结党营私。沈一贯的这些事迹皆是围绕其政治角色而展开的,若其不为首辅,甚至是不为阁臣,可能便不会介入到这些事情当中,亦不会为人所攻诋。沈一贯对万历朝中后期政局的改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局势更加混乱,也是他被舆论怒斥为权奸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沈一贯的政治角色
沈一贯阁臣这一政治角色是他被冠以浙党首揆的主因,也是被史家认为对朝局败坏负主要责任的原因所在。有明一代,阁臣虽只为五品,但经过嘉靖朝以来的政治衍变,内阁被舆论认为是政本之地,阁臣亦被认为是前朝之相。自首辅制确立后,首辅与其他阁臣间的权力与地位差距日益增大,围绕首辅地位,阁臣及其党羽之间相互斗争。阁臣最重要的权力便是票拟权,一般由首辅负责。乙巳京察后,因受言路弹劾,沈一贯注籍不出,明神宗仍将奏疏发送至其私邸,由其票拟。为此,沈鲤上疏言章奏不应发至私邸。这实际上是要取消由首辅专有票拟权,也含有对沈一贯(首辅)的不满。
首辅值阁时,其他辅臣犹如属吏,所有事情皆由首辅负责,以至于功归首辅,过亦归首辅。反观明中叶以来阁臣情形,大多是首辅备遭攻诋,其他阁臣则多脱尽干系,或被责以依附首辅,只有现任首辅致仕后,言路才弹劾攻诋其他阁臣。沈一贯于万历二十二年入阁,同时期阁臣共四人。陈于陛于万历二十四年去世;万历二十六年,次辅张位因丁应泰弹劾致仕;首辅赵志皋老弱多病,长年告假。自万历二十六年底至三十年初,近四年的时间里,只有沈一贯一人值阁,实际上成为除明神宗外的政治核心人物。梳理明神宗在国本、矿税等事的行为,可知他对沈一贯颇为满意,圣眷不衰。万历二十九年,赵志皋病逝,沈一贯成为名副其实的内阁首辅。但沈一贯没有起到辅政作用,没有改变万历时期朝局混乱状态,没有废除矿税,四境战事仍然频发,明神宗一直怠政,行政运转几近瘫痪,这一切导致官员对其渐渐失望。在众人弹劾沈一贯时,明神宗明显偏袒后者,贬斥弹劾者,使得群臣愈加愤懑。再者,时人不会将过错归咎于明神宗,势必要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沈一贯便成为最理想的选择,此在郭正域笔下或者是在他心中显露无疑。他因楚事、续妖书案而面临险境,但对沈一贯不满之人不说困境是由明神宗亲手造成的,而认为是沈一贯假借圣意,从中倾陷,这归根结底亦是源于对阁臣政治地位的认知。
沈一贯成为首辅前,见于《明神宗实录》《万历邸钞》等史籍记载的被弹劾只有一次,即丁应泰弹劾事件。实际上,沈一贯只是被附带弹劾,张位是丁应泰弹劾的主要目标。成为首辅后,沈一贯的仕途与名望却陡升变故。先是秦人刘九经上疏弹劾,随后郭正域等人与沈一贯发生分歧,再者便是乙巳京察后,刘元珍等人的攻诋。弹劾之语也无所不用其极,然内容无外乎是沈一贯蒙蔽明神宗,千方百计招权等。遍览诸言路对严嵩、徐阶、张居正等人的弹劾,内容亦无外乎如此。这种情况出现实际上是言路对阁臣与内阁不满的表达,是内阁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阁权上升的结果。另外,沈一贯确实与郭正域、沈鲤发生矛盾,并有较大的政治冲突,这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站在郭正域、沈鲤的视角而言,沈一贯欲置他们于死地;然以沈一贯的视角而言,似并不如此,他也是受害者,何况又在案件中积极调护。
沈一贯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即使左右逢源,亦会招致他人的非议与不满。沈一贯好权谋,品性委婉,在婉承帝意的基础上劝谏明神宗,此举在以道德名节自许的官员中,并不被赞许。这不仅是沈一贯面临的问题,亦是所有阁臣面临的一个困境。黄景昉曾记载沈一贯与李廷机二人自言阁臣此种困境:
沈文恭有言:“每见世仕宦不得志者,没后志状,未尝不以忤时宰为词。时宰不能重人生,能重人死。”而李文节亦云:“近世君子,除却建言,别无人品。而其所建言,除却阁臣,别无题目。”辞虽激,情亦近似,恫乎其有余悲!(53)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十,第300页。
沈一贯身居高位,自会有迎合者,也会有反对者。所谓的浙党成员可能与沈一贯平日并无交集,但一有时机,自会奋勇而前。清流君子不屑如此之为,或许他们也曾无意为之。当他们无法走近权力中心,或者成为当权者的朋友幕僚,只能自寻出路,或另寻目标。叶向高曾指出以亓诗教为首的齐人攻诋他,原因在于齐人欲推荐方从哲入阁。(54)叶向高:《蘧编》卷五,万历四十年壬子,第38页。乙巳京察后,部分中下级官员掀起攻诋沈一贯之潮流,全面否定沈一贯的政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朝野诉求无法得到妥善回应的结果,由此导致舆论处于失序的状态,更成为晚明政治生态恶化的主要表现。
四、结 语
通过对沈一贯与东林的关系阐释、浙党的形成轨迹的分析,我们初步可以确定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浙党是一个不断被扩大的团体。在沈一贯当政时,并没有“浙党”这一称呼,应是在“东林”“秦党”诸党名业已出现后,浙党方“应运而生”,时沈一贯已致仕。因攻诋政敌的需要,郭正域、刘元珍等人不断将政敌称为沈一贯的党羽。被攻诋的官员为自保,便纷纷反击。如此看来,郭正域所言“浙党”与夏允彝等人所言“浙党”内涵并不一致,但都是在表述一个不断扩张的浙党。浙党起初并不是一个自发的实体,只是一个概念化的虚拟存在,因假借沈一贯之名,或仅仅是以地域而命名,而且也不是所谓浙党有意识地集聚。
第二,沈一贯只是被动地卷入到党争话语中,他并没有实际参与晚明党争。他的名字、政治地位与仕宦轨迹,只是为党争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特殊的政治生态与历任皇帝对内阁及阁臣的态度,致使内阁与阁臣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内阁缺少一个明确的法定地位,无法牵制外廷官员,只能在皇帝与外廷官员间虚与委蛇,最终导致既不能顺承帝意,又与外廷官员决裂,不断招致舆论攻诋。
第三,万历中后期,朝臣纷争、相互攻诋,致使朝局混乱、国势衰微,这是明神宗怠政的结果,其根源是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体制。政见与理念的分歧,在所难免,但应限制于合理的论争范围内,而不能无限制地攻诋。晚明党争的主体是科道官,而统治者设置科道官的本意是整肃朝政,如今却起到反面效果。为使文官制度发挥最大功效,必须建立健全合理完善的监督体制,同时应提高官员自身素质,引导他们意识到不可滥用权力。
沈一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晚明波诡云谲的政局中,他的行为举措备受舆论关注。生前,尤其是担任首辅期间,对沈一贯已毁誉参半;死后,亦难以对其一生盖棺定论。对沈一贯的定位,自明人始,便已出现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观点:一则推崇,一则极力贬斥。晚明舆论认为,沈一贯的倾陷致使郭正域等清流落难,遂认为沈一贯是权奸。明末清初对沈一贯的定位也没有形成归一之论,既有称其为贤相者,又有认为其是权奸者。清廷对全国的统治确立后,为维持这一局面,最高统治者必须借鉴前代经验,鼓励士人气节、贬斥奸险小人则是需要借鉴之事。清初诸帝对明代党争都有所评述,康熙指出明不是亡于阉祸,而是亡于党争;(55)《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册,第701页上栏。雍正曾作《御制朋党论》,严厉禁止朋党。至《明史》定稿,遂以党争视角贯穿晚明历史,虽然修史者对东林颇有微词,但他们的立场是“彻头彻尾亲东林的,凡是被东林党攻击过的人物,其传记的撰写全部都经过了这种有色眼镜的过滤”。(56)沟口雄三:《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时期中国思想的展开》,《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0页。从明末已出现的党争视角至清修《明史》最终定型,这种党争视角一直影响至今。党争是双向的,但在评判中,绝大部分史家是对东林抱有同情态度,而对以沈一贯为轴心形成的“小人党”多持批判态度。以此视域和心态出发,沈一贯等人便会以奸人形象固定到文献中,再展现给读者,最终形成定论。
(本文曾提交2019年于珠海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感谢与会学者的批评指正,特此致谢!)